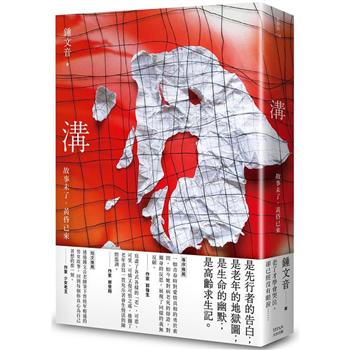如果不重逢
人逼近中年,幾年光景都是怵目驚心。
半夜有人打電話給她,問她有沒有認識的精神科醫生或是心理醫生。她沒有這樣的朋友,她的朋友都是病患,不是醫生。
她認真地問著打電話給她的朋友這一整天都在做什麼?
朋友說打太極練氣功,寫書法學瑜伽,學東學西,但仍感空虛。
這麼多的學習,妳為什麼還需要看醫生?她這樣想但並沒有說出口。因為同時間她想起「我尊重別人的恐懼」這句台詞,是她和電話那頭的朋友一起去看阿莫多瓦電影《悄悄告訴她》裡的對白。「我不懂鬥牛,但我懂絕望的女人。」阿莫多瓦,她那一代人曾仰望的男神,就像艾爾頓‧強,但都是不愛女人的人,她們只能在岸上看著。
半夜,如洪水猛獸的絕望情緒襲至。許多人只能盯著絕望看,看到最底層是什麼,但是這不易,因為絕望襲來時很難平息,需要如糖漿般的慰藉。所以說歸說,面對他人的恐懼與絕望,是無能的,光是懂得也還不足。比如,失聯很久的前情人突然打電話來說要請她寫傳記,會付錢給她。
菸嗓透過電話傳來,給她一種奇異的疼痛感。
她很想要那筆錢,但她知道她無法聽男人說他的故事,男人忘了她曾有的痛,她想這就是男女有別,以為錢就可以解決?
感謝對方曾給過妳困境的那一刻,她忽然就懂得慈悲了。
掛上電話,她更確立重逢不安好心,她心懷感謝男人帶給自己的成長,但再三提醒自己重逢沒安好心,小心重逢。
重逢設下機心處處,不是真來挽回或來懺悔的,寫傳記,她笑著想男人有什麼豐功偉業?寫傳記應是託詞,也不是真心想要看看她過得好不好吧,半是有點懺情是真的,畢竟她曾經為了這段感情付出不小的代價。半是來炫耀的吧,聽說男人是大老闆,底下員工不少。但這樣就可以寫傳?她不相信。給自己錢?她又開始有點心動,但最終還是過去的痛擋住了對自己的誘惑,被騙兩次就太傷了。她最後得一個結論,應該是男人過得不好,男人過得不好才會回首往事,才會想起誰是真正他傷過卻愛過他的人。男人過得不好,才會走回原地,要是過得好過得風光,早就四周美女環繞,哪裡想到褪色的舊情?且自戀男人會以為她的心還懸在過去的舊情,殊不知她的心懸的仍是情,但不是舊情,尤其是關乎愛的舊情。她現在懸的都是父母恩情,中年過後,父母雙老,她才看見陪伴她未來將度過高齡渡口的是此時父母老去的險灘風景。
但雖這樣想,這通突如其來傳進耳畔的熟悉聲音,仍如鬼魅地一時難以擺脫,過去的底片仍顯影曝光著如粗粒子般的刮痕傷害。
以前她只要一想起她的男人正在和另一個女人在一起,她一想起就感到痛,可這痛究竟是因為想才被呼喚而至,還是就一直寄存在她的本體?她真不知為何要保有對這個男人的記憶?是否也意味著她的害怕寂寞呢?也許她自己知道是她的懦弱所造成的。說來男人是愛她的,然而他有一般保守男人的無能與自私。但說他保守又顯得沒有道理,他老覺得自己前衛。
偏巧都是無緣的錯身倒也罷了,偏偏又不是這樣的絕然際遇,男人兩次遇到她時,都已經是身不由己的處境。
第一回,十幾年前,她剛從學校畢業,二十二歲的年華,任誰都要逼視一眼。
當年相逢,既不是前半生也不是後半生,就是剛巧卡在他的三十八歲,往前往後此生一樣遙遠,他相信他至少會活過七十歲。既無前生又無後生,那就是此生無緣了。
他們的緣總是不接在一塊,或者該說接到一塊時,他的這一方總是擠滿了無法鬆手的事物。
她開車回到家,手機早被她關了,她覺得智慧型手機真讓人厭惡,以前她談的戀愛也是這般不確定,但是總容易死了心,因為電話聯絡不到時就只好等待或放棄。然而現在有了手機,隨時都可以打電話追蹤。但是只要對方關機或者不接聽電話她就掉入無邊的痛苦,被想像劈得四分五裂的痛苦。因為這都意味著他和另一個女人在一起。因為他和她在一起時手段如出一轍,不接電話當然不會任憑電話在那邊無理地響著,而是改用振動。她的電話號碼會顯示在手機,但是他見了卻不回,這當然事有蹊蹺。何況,後來她知道他的事,他也就更擺明了如此,妳看著辦吧。
寧可不知道也不要知道的痛苦,她當時無法回頭。
知道另一個女人的存在,是一種奇異的心境。世界可真小,她想搞半天自己的閨密竟然和她有過同一個男人。我們的私密陰暗黑口曾經被同一個外來物進出過,這是何等奇怪的感受?她的閨密曾經這樣說過。
以前有好多個夜晚難入睡,她又按捺不住地撥了電話,週末依然空空地傳來電腦的虛假腔調。她寧可聽到他的冰冷回應都好,就是不要這樣無法找到人地墜入無邊想像的痛苦氛圍。冰冷至少是一種溫度,可以看清灼心的痛。
她經歷無數晚的揪心的這幾年做過一些蠢事,她太害怕造化弄人了,情慾海潮漲滿整個生命的孤島四周,任憑氾濫,無法防堵。
愛情潰散,她會去東海岸散心,看海。
夜裡四點醒轉,被海邊旅館人體雜沓的氣味喚醒,她推開蚊帳,步到屋外,海邊雲朵降到海平面上,遠看像山,她想是因為視野角度的關係,以致有一種雲朵全落在海面的錯覺,她想她對男人是氣憤的。他總是沒事就來惹她,然後又無能地在每每她心情不好爭吵時便亟欲走開,或者來個賴皮甚至不理不睬。賴皮時他說,妳罵我好了。竟有這樣的人,就是覺得放火燒了別人後無辜地說,我就是這樣嘛,妳罵我好了,不然怎麼辦?
有回她氣憤地說,那就走到大家都難堪的地步吧。
妳這話是什麼意思?喂,妳可別亂來喔。
你就生怕我毀了你的幸福城堡。她心寒極了。你只在乎這個的話又何必來招惹我呢?這話她在心頭響著,要吐出口又說不出,覺得整件事自己也有責任,不光是男人的招惹就可以脫身的。
她痛,她惱,她氣,但她無能且感虛無。既不在核心也不在邊緣。她什麼都不是。她就像她上班所寫的建案廣告詞般虛無、不真。
未完……
高齡求生
她是我見過最優雅的上了年紀的小販,她仔細地從報紙裡掏出銀壺銀飾玉鐲和幾個碗和銅飾品。
我發現兩個美麗的鑲銀邊的瓷瓶,如此深邃地展現手工情調,從路口灑進來的陽光正在減弱狀態,光陰陰幽地迆迆晃動在她擺的物件上。我蹲下身拿起,把看,老婦抬起頭微笑說我手上拿的很美,我點頭並問著她這些物件從哪裡來的?她怎麼會在這裡擺攤?
她說都是以前她自己買的,有在台灣也有在大陸買的,二十年前買的物品,當時就想若是老了沒錢時再拿出來賣,未料一下子光陰就走到了預言未來的此時此刻。沒錢時再拿出來賣,我似乎看到我老了的可能生活,但覺心驚。
我注意到她頭髮盤得光潔,臉色白淨,要不是白髮與皺紋橫生其間,她是可以藉著身上遺址以還原至年輕的型態。我花了五百元買了個銀飾瓶,她一直說值得值得的。
回程走同樣一條路見她仍在騎樓的角落裡,旁邊多了個擺舊雜誌的男老者,雜誌堆在腳踏車兩側的綠色麻袋上,男老者可能白天是送報的,我想。再次行經時老婦低頭在寫著字,筆記本看起來是舊了,不知道她在寫什麼,前面擺的物件和我先前離去時沒兩樣。我想我應該是她今天唯一達成交易的人。
她看著我,忽然叫著我的小名。
台北小販形形色色,我卻在街頭遇到母親以前的老鄰居阿桑,阿桑慢慢拼湊出我來,認出來之後就一直說我從小到大都長一個樣子,細粒仔(小個子)不顯老。
接著,她卻開始收拾攤子,我問她要收攤了?要去哪裡?
她收拾起大包小包,說等一下要去探望兒子。
兒子?我心想不是應該兒子來探望她老人家嗎?我問她兒子怎麼了?印象中她的兒子挺帥氣的。
她的眼神告訴了我這是一個冗長的故事,於是沒等她回話,我就說正好要去開車,想難得見到面,可以載她一程。
在車程中,隨著她的大致口述,我逐漸拼貼出阿桑人生的哀愁。
這阿桑年輕時也經常提食物去探望老公,年輕時跑監獄,年老時跑安養,只是食物從香菸罐頭變成看護墊尿片。
以前嫁錯郎,現在生錯兒,但千錯萬錯阿桑都說是自己的錯。年輕為愛盲,家人警告她匪類男勿嫁,她偏偏以為那是帥氣。臨老了兒子喝酒自撞,她自責教導無方。但夜晚到來,她又想自己確實教過兒子寧可傷己也不傷別人,這下可好,傷了自己也傷了她的人生晚景。
以前貧窮,沒錢買魚鬆,她都去黃昏市場買剩下的魚屍,魚頭魚尾魚骨外加一點肉,用力熱炒,炒到連骨頭都酥了,就是魚鬆了。現在她熬煮粥來看兒子,兒子因脊椎受傷,癱在輪椅上,從此只能隔窗看著他心愛的重機,日漸隨著時光黯淡的重機。
阿桑要賣掉重機,但發生過事故的汽機車彷彿凶宅,乏人問津。兒子看著重機,以為兒子會觸景傷情,沒想這重機卻成了兒子想要好起來的動力,重機成了眺望遠方的風景。
她以為自己也應該找個動力,一度以為將賺錢當動力,到處打工,還去賣玉蘭花,因疫情沒人敢開窗買花。發傳單也沒用,社交距離人人自危。以前就沒什麼人想拿了,疫情來襲,打工機會也沒了,於是她又開始走動黃昏市場,買便宜蔬果,甚至菜販不要的,說仔細挑揀也是一餐。
過老日子,成了艱難。
她身體不錯,年輕時勞動一直看起來精瘦,送走得癌的老公之後,更特別注意自己的身體,哪裡知道獨子出事,命運躲在暗處,給她重重一擊。往好處想是自己還可照顧自己,往壞處想是如果一直長生卻沒錢也無樂,這長生的意義何在?
我因媽媽中風,也曾為了安養問題,去看了許多安養院。我完全可以體會阿桑的心情,因為安養院表面是安養,但內裡有時卻不安,停滯的空氣不斷地爬上每個病體,那無助的眼神彷彿是一艘時間海洋裡的廢船,布滿了創傷的弧菌。
每一回來到安養院面對所愛的痛苦而暗自流淚,離開時身後的安養院則瞬間把心炸成無數的坑洞。每一回要轉身都成了艱難,每一回離開都是折騰。我不免憶起探望住家附近老人安養院的畫面。
未完……
謝謝你愛我這麼久
她將最好的生命時光都給了這家工廠,卻突然就被裁員。更糟糕的是工廠辭退她之前才為她做了年度健檢,什麼低密度膽固醇三酸甘油酯一片紅色,為此她感到憂心,但擔憂歸擔憂,日子也總是轉眼翻頁。
被辭退後,她常去住家附近的咖啡館發呆,在這家咖啡館出現她這種有著白髮的初老婦人並沒有太大的違和感,可能因為老城一帶經常出入三教九流的人,咖啡館也就錯落著各式各樣的五色人。
只是每回到櫃檯點咖啡她都覺得麻煩,她說一杯拿鐵咖啡,櫃檯小妹就開始問大杯中杯,要不要改成莊園咖啡豆,口感較好?她搖頭。那要不要來第二杯,現在第二杯半價喔,喝不完妳可以帶回去喝?她不好意思地搖頭。那要不要來份甜點,點飲料有折扣喔。她持續搖頭,得在櫃檯搖頭幾回才能結好帳。
喝拿鐵咖啡對她已是勉強,甜點對她更是負擔,麵包甜點在健檢報告出來後只好謝絕。她點好咖啡後,走向靠窗的位子,偶爾敲著風濕的臂膀想這年頭度日真難了。她在窗邊看見警察在對面麥當勞站崗,怕街上流鶯在那裡交易。她記得有回咖啡館太擠,一個老婦和她分享一張桌子時像老友似的跟她說,現在兩三天我能有一個客人就不錯了。
她聽了不禁想起自己那過世多年的母親,可憐的母親,生了一堆小孩,想起就淚濕眼眶之感。老婦卻在這時拉著她的衣袖問妳怎麼有閒坐在這裡飲咖啡?
她笑著說我只剩下時間,我們這種老婦人的時間是最不值錢的。
她每回在外面突然想上大號,找的廁所都得找至少有兩間廁所的連鎖速食店,只有一間廁所會讓她焦慮,她老怕有人在外面等,她就會很緊張地草草如廁,或者根本上不出來,但她又經常拉肚子找廁所。後來她終於找到一家有三間廁所的連鎖咖啡館,一杯咖啡六十五元,包廁所也包時間。冷氣、水都隨意,收留她的晚年。六十三歲,被提前辭退,很尷尬,看起來也不能說有多老,但絕對一看就空巢很久的人。
每天在咖啡館小桌前,她都當成是小小壇城,她會將佛經打開,電腦螢幕也打開,打開電腦不是為了打字,而是女兒早把她的佛像都存到了電腦,免得她東忘西忘。她對著佛像螢幕開始念經,每天都像以前在工廠上班時,在生產線準時報到般專注。
念經之後,拿出計數器念咒。以七為最小單位,每回她念經書或咒語都是以七為倍數。計數器的發明,多麼仁善又實用。所有當代的慈善都可以被數字代換。功德金換算成通往淨土的邀請或去卡位,以看得見的鈔票轉換成看不見的琉璃金殿。有人念了幾個億的咒語,有人賺了幾個億的錢。念珠和算盤滑過,開闔如唇語,通天的密碼日夜持誦。她逐漸養出一種即使和別人聊天也能在心裡持咒的習慣,功德未必獲得,但專注力倒是增加了,持續關注在一個咒語上且還要知道念了多少咒語的數字。她莞爾一笑,為了眾生而有了兩萬八千多種方便法門。兩萬八千種?女兒當時聽她說起這個數字時,還笑說這數字比她的薪水還多。
她在咖啡館一坐就會坐很久,一杯熱咖啡就待上一天,熱咖啡即使喝完了杯子也一定要擺著,代表自己可不是沒消費喔。朋友更狠,只帶咖啡杯來擺著,裡面的咖啡還是自己在家裡沖好的,根本連消費都不用。
咖啡館的WiFi好用,念完佛課,她上網追劇,打發時間,直到女兒下班來尋她回家,角色倒反,昔日接女兒下課,現在女兒下班接她。往昔工廠輸送帶的金屬氣味變成咖啡館的咖啡香,日子雖不好過,但比起以往,只要省著點錢花,收起慾望,也還能無風無雨。
她女兒長得素白美麗,但是她一直擔心女兒嫁不掉,因為她發現女兒常對男人有敵意。
女兒再次看見父親回到這個家是上大學那年,長年在外流連嬉遊的父親得了癌症才乖乖回到家裡,女兒簡直討厭極了父親。女兒記得童年時父親帶外面的女人回家,卻要她和媽媽去外面找旅社睡。
女兒被她牽在手上,母女倆在街上亂晃。她不懂為什麼她們要被趕出來,父親為何不帶女人在外面睡?媽媽說,他不想花錢。我們睡旅社要花錢,所以我們去公園好了。她們就這樣在家裡與公園間來來去去,有時父親沒回家,她們就很高興不用餐風露宿。
後來是因這個家窄小陰暗,外面的女人終於也受不了了,總之女人要男人做選擇,於是父親離開這個原本就簡陋的家。但在男人離家時,她才發現自己的肚皮又被搞大了,她懷孕,女兒自此多了個小弟阿良。
那時她每天騎腳踏車去工廠上班。
她一進工廠就成了工廠之花,被女兒父親追走又離棄之後,仍有不少中年喪偶男人或羅漢腳的王老五追著她。男人通常都會先去討好阿良,買肯德基麥當勞炸雞給阿良,女兒總是掐阿良的手臂,暗示弟弟不要拿男人的東西吃,但這阿良卻總是搶著拿,一張口就是吃得油滋滋的,雞皮和肉之間滑下了油水,沾得阿良肥胖的手臂油光光。
女兒父親在幾年後突然又跑回家,在染了一身病後。女兒對母親說,我不要照顧他,我不想幫他把屎把尿。她搖頭嘆氣,跟女兒說照顧父母不是數學,誰愛你多誰愛你少,這就是責任。
那爸爸怎麼忘了責任?
他是他,他忘了他的,妳不該忘了妳的,她跟女兒說。但後來想想也算了,畢竟女兒還年輕,看到老男身體,即使是父親的,也很難適應。
父親變成流浪狗,從暴力轉成哀矜,這姿態不屬於父親,女兒不習慣的其實不是身體而是姿態。
她跟女兒說把屎把尿媽媽來,妳只管買尿片尿布就好。
直到這個男人過世,女兒都冷眼旁觀。
對家庭不負責任,生病就注定被遺棄。她也怪自己曾對女兒說她出生那天,這男人還在牌桌上。之後這父親在其他女人的床上,所以女兒一直沒有被男人的大手抱過。
從小女兒不知道父親的手和母親的手有何差別?直到女兒有一天被父親打,用手摑了一個像是電視劇的耳光,她於是知道強弱決定了生存。打了一記疼痛劇烈的耳光,她甚至片刻恍然以為耳朵被削掉了。
都是破麻,女兒聽見父親甩門離開時拋下一個她聽不懂的字眼轉身。
女兒氣母親對父親的縱容。
但她不知道母親有著沒有對女兒說出的痛,縱容這個男人?她想那是因為當時這個男人是她唯一的浮木。
每回她看見甜美樣貌的電視主播以高八度的音感說著什麼假結婚真賣淫的新聞時,她都不禁失笑起來。彷彿不知人間有老苦疾苦的主播就那麼輕易地以天真的聲音且帶點鄙夷的文字殺得陌生人片甲不留。
那我們是真結婚假賣淫嘍,她跟其他女工們經常邊聽著新聞邊開玩笑邊如此自嘲著。
她知道自己結婚後關於每一次的性都是佯裝的快樂,其實是無魚也無水,她的腦子還裝著另一個人。
女兒有一天跟她說要帶男朋友回家。
她打開門時,瞬間嚇了好大一跳,彷彿看見往昔那生產線冒出的一道犀利目光,光打在女兒身旁的年輕男子臉上。
有長得這麼像的人?
未完……
人逼近中年,幾年光景都是怵目驚心。
半夜有人打電話給她,問她有沒有認識的精神科醫生或是心理醫生。她沒有這樣的朋友,她的朋友都是病患,不是醫生。
她認真地問著打電話給她的朋友這一整天都在做什麼?
朋友說打太極練氣功,寫書法學瑜伽,學東學西,但仍感空虛。
這麼多的學習,妳為什麼還需要看醫生?她這樣想但並沒有說出口。因為同時間她想起「我尊重別人的恐懼」這句台詞,是她和電話那頭的朋友一起去看阿莫多瓦電影《悄悄告訴她》裡的對白。「我不懂鬥牛,但我懂絕望的女人。」阿莫多瓦,她那一代人曾仰望的男神,就像艾爾頓‧強,但都是不愛女人的人,她們只能在岸上看著。
半夜,如洪水猛獸的絕望情緒襲至。許多人只能盯著絕望看,看到最底層是什麼,但是這不易,因為絕望襲來時很難平息,需要如糖漿般的慰藉。所以說歸說,面對他人的恐懼與絕望,是無能的,光是懂得也還不足。比如,失聯很久的前情人突然打電話來說要請她寫傳記,會付錢給她。
菸嗓透過電話傳來,給她一種奇異的疼痛感。
她很想要那筆錢,但她知道她無法聽男人說他的故事,男人忘了她曾有的痛,她想這就是男女有別,以為錢就可以解決?
感謝對方曾給過妳困境的那一刻,她忽然就懂得慈悲了。
掛上電話,她更確立重逢不安好心,她心懷感謝男人帶給自己的成長,但再三提醒自己重逢沒安好心,小心重逢。
重逢設下機心處處,不是真來挽回或來懺悔的,寫傳記,她笑著想男人有什麼豐功偉業?寫傳記應是託詞,也不是真心想要看看她過得好不好吧,半是有點懺情是真的,畢竟她曾經為了這段感情付出不小的代價。半是來炫耀的吧,聽說男人是大老闆,底下員工不少。但這樣就可以寫傳?她不相信。給自己錢?她又開始有點心動,但最終還是過去的痛擋住了對自己的誘惑,被騙兩次就太傷了。她最後得一個結論,應該是男人過得不好,男人過得不好才會回首往事,才會想起誰是真正他傷過卻愛過他的人。男人過得不好,才會走回原地,要是過得好過得風光,早就四周美女環繞,哪裡想到褪色的舊情?且自戀男人會以為她的心還懸在過去的舊情,殊不知她的心懸的仍是情,但不是舊情,尤其是關乎愛的舊情。她現在懸的都是父母恩情,中年過後,父母雙老,她才看見陪伴她未來將度過高齡渡口的是此時父母老去的險灘風景。
但雖這樣想,這通突如其來傳進耳畔的熟悉聲音,仍如鬼魅地一時難以擺脫,過去的底片仍顯影曝光著如粗粒子般的刮痕傷害。
以前她只要一想起她的男人正在和另一個女人在一起,她一想起就感到痛,可這痛究竟是因為想才被呼喚而至,還是就一直寄存在她的本體?她真不知為何要保有對這個男人的記憶?是否也意味著她的害怕寂寞呢?也許她自己知道是她的懦弱所造成的。說來男人是愛她的,然而他有一般保守男人的無能與自私。但說他保守又顯得沒有道理,他老覺得自己前衛。
偏巧都是無緣的錯身倒也罷了,偏偏又不是這樣的絕然際遇,男人兩次遇到她時,都已經是身不由己的處境。
第一回,十幾年前,她剛從學校畢業,二十二歲的年華,任誰都要逼視一眼。
當年相逢,既不是前半生也不是後半生,就是剛巧卡在他的三十八歲,往前往後此生一樣遙遠,他相信他至少會活過七十歲。既無前生又無後生,那就是此生無緣了。
他們的緣總是不接在一塊,或者該說接到一塊時,他的這一方總是擠滿了無法鬆手的事物。
她開車回到家,手機早被她關了,她覺得智慧型手機真讓人厭惡,以前她談的戀愛也是這般不確定,但是總容易死了心,因為電話聯絡不到時就只好等待或放棄。然而現在有了手機,隨時都可以打電話追蹤。但是只要對方關機或者不接聽電話她就掉入無邊的痛苦,被想像劈得四分五裂的痛苦。因為這都意味著他和另一個女人在一起。因為他和她在一起時手段如出一轍,不接電話當然不會任憑電話在那邊無理地響著,而是改用振動。她的電話號碼會顯示在手機,但是他見了卻不回,這當然事有蹊蹺。何況,後來她知道他的事,他也就更擺明了如此,妳看著辦吧。
寧可不知道也不要知道的痛苦,她當時無法回頭。
知道另一個女人的存在,是一種奇異的心境。世界可真小,她想搞半天自己的閨密竟然和她有過同一個男人。我們的私密陰暗黑口曾經被同一個外來物進出過,這是何等奇怪的感受?她的閨密曾經這樣說過。
以前有好多個夜晚難入睡,她又按捺不住地撥了電話,週末依然空空地傳來電腦的虛假腔調。她寧可聽到他的冰冷回應都好,就是不要這樣無法找到人地墜入無邊想像的痛苦氛圍。冰冷至少是一種溫度,可以看清灼心的痛。
她經歷無數晚的揪心的這幾年做過一些蠢事,她太害怕造化弄人了,情慾海潮漲滿整個生命的孤島四周,任憑氾濫,無法防堵。
愛情潰散,她會去東海岸散心,看海。
夜裡四點醒轉,被海邊旅館人體雜沓的氣味喚醒,她推開蚊帳,步到屋外,海邊雲朵降到海平面上,遠看像山,她想是因為視野角度的關係,以致有一種雲朵全落在海面的錯覺,她想她對男人是氣憤的。他總是沒事就來惹她,然後又無能地在每每她心情不好爭吵時便亟欲走開,或者來個賴皮甚至不理不睬。賴皮時他說,妳罵我好了。竟有這樣的人,就是覺得放火燒了別人後無辜地說,我就是這樣嘛,妳罵我好了,不然怎麼辦?
有回她氣憤地說,那就走到大家都難堪的地步吧。
妳這話是什麼意思?喂,妳可別亂來喔。
你就生怕我毀了你的幸福城堡。她心寒極了。你只在乎這個的話又何必來招惹我呢?這話她在心頭響著,要吐出口又說不出,覺得整件事自己也有責任,不光是男人的招惹就可以脫身的。
她痛,她惱,她氣,但她無能且感虛無。既不在核心也不在邊緣。她什麼都不是。她就像她上班所寫的建案廣告詞般虛無、不真。
未完……
高齡求生
她是我見過最優雅的上了年紀的小販,她仔細地從報紙裡掏出銀壺銀飾玉鐲和幾個碗和銅飾品。
我發現兩個美麗的鑲銀邊的瓷瓶,如此深邃地展現手工情調,從路口灑進來的陽光正在減弱狀態,光陰陰幽地迆迆晃動在她擺的物件上。我蹲下身拿起,把看,老婦抬起頭微笑說我手上拿的很美,我點頭並問著她這些物件從哪裡來的?她怎麼會在這裡擺攤?
她說都是以前她自己買的,有在台灣也有在大陸買的,二十年前買的物品,當時就想若是老了沒錢時再拿出來賣,未料一下子光陰就走到了預言未來的此時此刻。沒錢時再拿出來賣,我似乎看到我老了的可能生活,但覺心驚。
我注意到她頭髮盤得光潔,臉色白淨,要不是白髮與皺紋橫生其間,她是可以藉著身上遺址以還原至年輕的型態。我花了五百元買了個銀飾瓶,她一直說值得值得的。
回程走同樣一條路見她仍在騎樓的角落裡,旁邊多了個擺舊雜誌的男老者,雜誌堆在腳踏車兩側的綠色麻袋上,男老者可能白天是送報的,我想。再次行經時老婦低頭在寫著字,筆記本看起來是舊了,不知道她在寫什麼,前面擺的物件和我先前離去時沒兩樣。我想我應該是她今天唯一達成交易的人。
她看著我,忽然叫著我的小名。
台北小販形形色色,我卻在街頭遇到母親以前的老鄰居阿桑,阿桑慢慢拼湊出我來,認出來之後就一直說我從小到大都長一個樣子,細粒仔(小個子)不顯老。
接著,她卻開始收拾攤子,我問她要收攤了?要去哪裡?
她收拾起大包小包,說等一下要去探望兒子。
兒子?我心想不是應該兒子來探望她老人家嗎?我問她兒子怎麼了?印象中她的兒子挺帥氣的。
她的眼神告訴了我這是一個冗長的故事,於是沒等她回話,我就說正好要去開車,想難得見到面,可以載她一程。
在車程中,隨著她的大致口述,我逐漸拼貼出阿桑人生的哀愁。
這阿桑年輕時也經常提食物去探望老公,年輕時跑監獄,年老時跑安養,只是食物從香菸罐頭變成看護墊尿片。
以前嫁錯郎,現在生錯兒,但千錯萬錯阿桑都說是自己的錯。年輕為愛盲,家人警告她匪類男勿嫁,她偏偏以為那是帥氣。臨老了兒子喝酒自撞,她自責教導無方。但夜晚到來,她又想自己確實教過兒子寧可傷己也不傷別人,這下可好,傷了自己也傷了她的人生晚景。
以前貧窮,沒錢買魚鬆,她都去黃昏市場買剩下的魚屍,魚頭魚尾魚骨外加一點肉,用力熱炒,炒到連骨頭都酥了,就是魚鬆了。現在她熬煮粥來看兒子,兒子因脊椎受傷,癱在輪椅上,從此只能隔窗看著他心愛的重機,日漸隨著時光黯淡的重機。
阿桑要賣掉重機,但發生過事故的汽機車彷彿凶宅,乏人問津。兒子看著重機,以為兒子會觸景傷情,沒想這重機卻成了兒子想要好起來的動力,重機成了眺望遠方的風景。
她以為自己也應該找個動力,一度以為將賺錢當動力,到處打工,還去賣玉蘭花,因疫情沒人敢開窗買花。發傳單也沒用,社交距離人人自危。以前就沒什麼人想拿了,疫情來襲,打工機會也沒了,於是她又開始走動黃昏市場,買便宜蔬果,甚至菜販不要的,說仔細挑揀也是一餐。
過老日子,成了艱難。
她身體不錯,年輕時勞動一直看起來精瘦,送走得癌的老公之後,更特別注意自己的身體,哪裡知道獨子出事,命運躲在暗處,給她重重一擊。往好處想是自己還可照顧自己,往壞處想是如果一直長生卻沒錢也無樂,這長生的意義何在?
我因媽媽中風,也曾為了安養問題,去看了許多安養院。我完全可以體會阿桑的心情,因為安養院表面是安養,但內裡有時卻不安,停滯的空氣不斷地爬上每個病體,那無助的眼神彷彿是一艘時間海洋裡的廢船,布滿了創傷的弧菌。
每一回來到安養院面對所愛的痛苦而暗自流淚,離開時身後的安養院則瞬間把心炸成無數的坑洞。每一回要轉身都成了艱難,每一回離開都是折騰。我不免憶起探望住家附近老人安養院的畫面。
未完……
謝謝你愛我這麼久
她將最好的生命時光都給了這家工廠,卻突然就被裁員。更糟糕的是工廠辭退她之前才為她做了年度健檢,什麼低密度膽固醇三酸甘油酯一片紅色,為此她感到憂心,但擔憂歸擔憂,日子也總是轉眼翻頁。
被辭退後,她常去住家附近的咖啡館發呆,在這家咖啡館出現她這種有著白髮的初老婦人並沒有太大的違和感,可能因為老城一帶經常出入三教九流的人,咖啡館也就錯落著各式各樣的五色人。
只是每回到櫃檯點咖啡她都覺得麻煩,她說一杯拿鐵咖啡,櫃檯小妹就開始問大杯中杯,要不要改成莊園咖啡豆,口感較好?她搖頭。那要不要來第二杯,現在第二杯半價喔,喝不完妳可以帶回去喝?她不好意思地搖頭。那要不要來份甜點,點飲料有折扣喔。她持續搖頭,得在櫃檯搖頭幾回才能結好帳。
喝拿鐵咖啡對她已是勉強,甜點對她更是負擔,麵包甜點在健檢報告出來後只好謝絕。她點好咖啡後,走向靠窗的位子,偶爾敲著風濕的臂膀想這年頭度日真難了。她在窗邊看見警察在對面麥當勞站崗,怕街上流鶯在那裡交易。她記得有回咖啡館太擠,一個老婦和她分享一張桌子時像老友似的跟她說,現在兩三天我能有一個客人就不錯了。
她聽了不禁想起自己那過世多年的母親,可憐的母親,生了一堆小孩,想起就淚濕眼眶之感。老婦卻在這時拉著她的衣袖問妳怎麼有閒坐在這裡飲咖啡?
她笑著說我只剩下時間,我們這種老婦人的時間是最不值錢的。
她每回在外面突然想上大號,找的廁所都得找至少有兩間廁所的連鎖速食店,只有一間廁所會讓她焦慮,她老怕有人在外面等,她就會很緊張地草草如廁,或者根本上不出來,但她又經常拉肚子找廁所。後來她終於找到一家有三間廁所的連鎖咖啡館,一杯咖啡六十五元,包廁所也包時間。冷氣、水都隨意,收留她的晚年。六十三歲,被提前辭退,很尷尬,看起來也不能說有多老,但絕對一看就空巢很久的人。
每天在咖啡館小桌前,她都當成是小小壇城,她會將佛經打開,電腦螢幕也打開,打開電腦不是為了打字,而是女兒早把她的佛像都存到了電腦,免得她東忘西忘。她對著佛像螢幕開始念經,每天都像以前在工廠上班時,在生產線準時報到般專注。
念經之後,拿出計數器念咒。以七為最小單位,每回她念經書或咒語都是以七為倍數。計數器的發明,多麼仁善又實用。所有當代的慈善都可以被數字代換。功德金換算成通往淨土的邀請或去卡位,以看得見的鈔票轉換成看不見的琉璃金殿。有人念了幾個億的咒語,有人賺了幾個億的錢。念珠和算盤滑過,開闔如唇語,通天的密碼日夜持誦。她逐漸養出一種即使和別人聊天也能在心裡持咒的習慣,功德未必獲得,但專注力倒是增加了,持續關注在一個咒語上且還要知道念了多少咒語的數字。她莞爾一笑,為了眾生而有了兩萬八千多種方便法門。兩萬八千種?女兒當時聽她說起這個數字時,還笑說這數字比她的薪水還多。
她在咖啡館一坐就會坐很久,一杯熱咖啡就待上一天,熱咖啡即使喝完了杯子也一定要擺著,代表自己可不是沒消費喔。朋友更狠,只帶咖啡杯來擺著,裡面的咖啡還是自己在家裡沖好的,根本連消費都不用。
咖啡館的WiFi好用,念完佛課,她上網追劇,打發時間,直到女兒下班來尋她回家,角色倒反,昔日接女兒下課,現在女兒下班接她。往昔工廠輸送帶的金屬氣味變成咖啡館的咖啡香,日子雖不好過,但比起以往,只要省著點錢花,收起慾望,也還能無風無雨。
她女兒長得素白美麗,但是她一直擔心女兒嫁不掉,因為她發現女兒常對男人有敵意。
女兒再次看見父親回到這個家是上大學那年,長年在外流連嬉遊的父親得了癌症才乖乖回到家裡,女兒簡直討厭極了父親。女兒記得童年時父親帶外面的女人回家,卻要她和媽媽去外面找旅社睡。
女兒被她牽在手上,母女倆在街上亂晃。她不懂為什麼她們要被趕出來,父親為何不帶女人在外面睡?媽媽說,他不想花錢。我們睡旅社要花錢,所以我們去公園好了。她們就這樣在家裡與公園間來來去去,有時父親沒回家,她們就很高興不用餐風露宿。
後來是因這個家窄小陰暗,外面的女人終於也受不了了,總之女人要男人做選擇,於是父親離開這個原本就簡陋的家。但在男人離家時,她才發現自己的肚皮又被搞大了,她懷孕,女兒自此多了個小弟阿良。
那時她每天騎腳踏車去工廠上班。
她一進工廠就成了工廠之花,被女兒父親追走又離棄之後,仍有不少中年喪偶男人或羅漢腳的王老五追著她。男人通常都會先去討好阿良,買肯德基麥當勞炸雞給阿良,女兒總是掐阿良的手臂,暗示弟弟不要拿男人的東西吃,但這阿良卻總是搶著拿,一張口就是吃得油滋滋的,雞皮和肉之間滑下了油水,沾得阿良肥胖的手臂油光光。
女兒父親在幾年後突然又跑回家,在染了一身病後。女兒對母親說,我不要照顧他,我不想幫他把屎把尿。她搖頭嘆氣,跟女兒說照顧父母不是數學,誰愛你多誰愛你少,這就是責任。
那爸爸怎麼忘了責任?
他是他,他忘了他的,妳不該忘了妳的,她跟女兒說。但後來想想也算了,畢竟女兒還年輕,看到老男身體,即使是父親的,也很難適應。
父親變成流浪狗,從暴力轉成哀矜,這姿態不屬於父親,女兒不習慣的其實不是身體而是姿態。
她跟女兒說把屎把尿媽媽來,妳只管買尿片尿布就好。
直到這個男人過世,女兒都冷眼旁觀。
對家庭不負責任,生病就注定被遺棄。她也怪自己曾對女兒說她出生那天,這男人還在牌桌上。之後這父親在其他女人的床上,所以女兒一直沒有被男人的大手抱過。
從小女兒不知道父親的手和母親的手有何差別?直到女兒有一天被父親打,用手摑了一個像是電視劇的耳光,她於是知道強弱決定了生存。打了一記疼痛劇烈的耳光,她甚至片刻恍然以為耳朵被削掉了。
都是破麻,女兒聽見父親甩門離開時拋下一個她聽不懂的字眼轉身。
女兒氣母親對父親的縱容。
但她不知道母親有著沒有對女兒說出的痛,縱容這個男人?她想那是因為當時這個男人是她唯一的浮木。
每回她看見甜美樣貌的電視主播以高八度的音感說著什麼假結婚真賣淫的新聞時,她都不禁失笑起來。彷彿不知人間有老苦疾苦的主播就那麼輕易地以天真的聲音且帶點鄙夷的文字殺得陌生人片甲不留。
那我們是真結婚假賣淫嘍,她跟其他女工們經常邊聽著新聞邊開玩笑邊如此自嘲著。
她知道自己結婚後關於每一次的性都是佯裝的快樂,其實是無魚也無水,她的腦子還裝著另一個人。
女兒有一天跟她說要帶男朋友回家。
她打開門時,瞬間嚇了好大一跳,彷彿看見往昔那生產線冒出的一道犀利目光,光打在女兒身旁的年輕男子臉上。
有長得這麼像的人?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