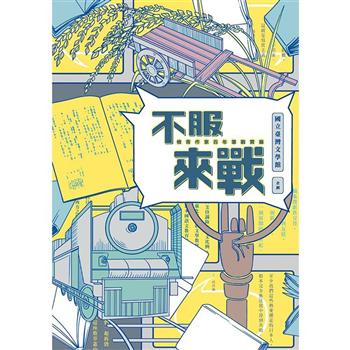臺灣「新舊文學論爭」的語文改革與思想啟蒙/楊傑銘(節錄)
《臺灣青年》創刊號,陳炘以〈文學與職務〉一篇,說明了文學對啟蒙人心與改造民族性之重要。「文學者,乃文化之先驅也。文學之道廢,民族無不與之俱衰;文學之道興,民族無不俱盛。故文學者,不可不以啟發文化、振興民族為其職務。」陳炘作為新一代知識份子的代表,他認為,文學的興衰等同民族的興衰,文學在社會現實中肩負著啟蒙與改革之任務。文學之用是用來改善社會、建構理想世界,並於創作中表現個人個體的解放,展現以人為主體的價值觀。
陳炘的觀點,已透露出新一代知識份子對於文學、文化看法﹕文學不能僅是濃麗之外觀,還須具備傳播文明、教化世人之功用,是改革社會的重要工具。而對於傳統文學中「有濃麗之外觀,而無靈魂腦筋」的創作,認為這是「死的文學」。而真正提出使用中國白話文的,為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臺灣青年》中,陳端明於〈日用文鼓吹論〉一文,認為白話文有助於臺灣學習世界最新思潮之知識,擺脫傳統文化之窠臼,以及日本殖民體制的收編。這些論點一直為新文學陣營所承襲,也成為新舊文學論爭時,新文學陣營的立論基礎。
而處於如此的新舊變動階段,已有文化人詹炎錄看到新舊文學水火不容的情況,遲早會有衝突發生。「當今臺灣為新舊學過渡時代。以舊學而攻擊新學。新學剌謬舊學。往往若水火不相容者。是由二者各執著門戶。不知我外有物。」詹炎錄認為新舊文學的衝突是種門戶之見,反映了在立論基礎上的不同。
張我軍於一九二四年四月於《臺灣民報》發表〈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對於臺灣傳統詩文的價值提出質疑,可以算是新舊文學論爭的第一聲砲火。同年十一月以筆名「一郎」發表〈糟糕的臺灣文學界〉,文章內容針對傳統文學的陋習提出批評,攻擊力道之猛烈,也引來傳統文人的不滿與回擊。他在文中提到,傳統文人在全臺各地創立的詩會、詩社,打著文學交流的名義,創作遊戲之作的作品。文章中他說道﹕「做詩的儘管做,一般人之於文學儘管有興味,而不但沒有產出差強人意的作品,甚至造出一種臭不可聞的惡空氣出來,把一班文士的臉丟盡無疑,甚至埋沒了許多有為的天才,陷害了不少活潑的青年。」他文章對傳統文學強烈針對性的攻擊,其後接連的數篇文章包括了〈為臺灣文學界一哭〉、〈請合力拆下這一座拜草叢中的破舊殿堂〉等。另外,也有蘇維霖、張梗、楊雲萍、陳虛谷等新文學支持者的評論文章,將新舊文學的衝突檯面化。
新舊文學論戰:要古典文學,還是要白話文學?(1924-1926)
古典文學是否導致文壇「佈滿破敗草叢」?是「敗草中的破舊殿堂」嗎?受到中國五四運動影響的張我軍,熱烈地提問,直指古典文人:文學要這樣繼續了無生氣嗎?
◆來戰
張我軍:我們一起拆毀「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建立新文學吧!
「新舊文學論戰」,由一群青年知識份子啟動。他們反省臺灣當前文壇處境,認為文學應該革命,文化生命應該更新。
「新文學」陣營主將張我軍。 一九二一年前往中國,後進入北平師範大學國文系。他接收中國「五四運動」的文學改革思潮,對臺灣古典文學提出批判,認為應該推行白話文學。
一九二四年開始,他如同戰神般連續發表多篇文章挑戰古典文學。他認為這些「舊文學」埋沒有為的天才,陷害活潑的青年。他的主張獲得賴和、蔡孝乾的支持。
推行白話文學,不僅在討論「用什麼語言寫」,同時也蘊含「為群眾而寫」的信念。
因此,與其說他們反對古典文學,不如說是反對古典文學背後的貴族屬性,以及反對日本殖民政府「用古典文學拉攏舊仕紳」的政治盤算。
◆不服
連雅堂:你們只是「拾西方之餘唾」啊!
「舊文學」陣營的主將,則以連雅堂為主。連雅堂號稱「日治時期臺灣三大詩人」之一,為古典漢詩費盡心力。在論戰爆發的一九二四年,他開始出版《臺灣詩薈》,直到一九二五年十月止,共發行22期,是古典文學的重要陣地。
連雅堂透過出版、創作、結社,苦心維繫古典漢文學。他強調文學的審美功能,不認為文學必須涉入現實、為群眾而寫。他認為張我軍所提倡的新文學只是「拾西方文化之餘唾」,是「陷穽之蛙,不足以語汪洋之海」。
同屬「舊文學」陣營者,另有鄭坤五、黃文虎等人。
值得注意的是,這場論戰雖然造成臺灣新文學的崛起,卻並沒有造成臺灣古典文學的衰亡。日治時期的古典詩社林立,也在通俗小說領域產生強大的影響,榮景空前絕後。「新舊文學論戰」的結果不是「以新代舊」,而是成為「新舊並行」的兩大主軸。
《臺灣青年》創刊號,陳炘以〈文學與職務〉一篇,說明了文學對啟蒙人心與改造民族性之重要。「文學者,乃文化之先驅也。文學之道廢,民族無不與之俱衰;文學之道興,民族無不俱盛。故文學者,不可不以啟發文化、振興民族為其職務。」陳炘作為新一代知識份子的代表,他認為,文學的興衰等同民族的興衰,文學在社會現實中肩負著啟蒙與改革之任務。文學之用是用來改善社會、建構理想世界,並於創作中表現個人個體的解放,展現以人為主體的價值觀。
陳炘的觀點,已透露出新一代知識份子對於文學、文化看法﹕文學不能僅是濃麗之外觀,還須具備傳播文明、教化世人之功用,是改革社會的重要工具。而對於傳統文學中「有濃麗之外觀,而無靈魂腦筋」的創作,認為這是「死的文學」。而真正提出使用中國白話文的,為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臺灣青年》中,陳端明於〈日用文鼓吹論〉一文,認為白話文有助於臺灣學習世界最新思潮之知識,擺脫傳統文化之窠臼,以及日本殖民體制的收編。這些論點一直為新文學陣營所承襲,也成為新舊文學論爭時,新文學陣營的立論基礎。
而處於如此的新舊變動階段,已有文化人詹炎錄看到新舊文學水火不容的情況,遲早會有衝突發生。「當今臺灣為新舊學過渡時代。以舊學而攻擊新學。新學剌謬舊學。往往若水火不相容者。是由二者各執著門戶。不知我外有物。」詹炎錄認為新舊文學的衝突是種門戶之見,反映了在立論基礎上的不同。
張我軍於一九二四年四月於《臺灣民報》發表〈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對於臺灣傳統詩文的價值提出質疑,可以算是新舊文學論爭的第一聲砲火。同年十一月以筆名「一郎」發表〈糟糕的臺灣文學界〉,文章內容針對傳統文學的陋習提出批評,攻擊力道之猛烈,也引來傳統文人的不滿與回擊。他在文中提到,傳統文人在全臺各地創立的詩會、詩社,打著文學交流的名義,創作遊戲之作的作品。文章中他說道﹕「做詩的儘管做,一般人之於文學儘管有興味,而不但沒有產出差強人意的作品,甚至造出一種臭不可聞的惡空氣出來,把一班文士的臉丟盡無疑,甚至埋沒了許多有為的天才,陷害了不少活潑的青年。」他文章對傳統文學強烈針對性的攻擊,其後接連的數篇文章包括了〈為臺灣文學界一哭〉、〈請合力拆下這一座拜草叢中的破舊殿堂〉等。另外,也有蘇維霖、張梗、楊雲萍、陳虛谷等新文學支持者的評論文章,將新舊文學的衝突檯面化。
新舊文學論戰:要古典文學,還是要白話文學?(1924-1926)
古典文學是否導致文壇「佈滿破敗草叢」?是「敗草中的破舊殿堂」嗎?受到中國五四運動影響的張我軍,熱烈地提問,直指古典文人:文學要這樣繼續了無生氣嗎?
◆來戰
張我軍:我們一起拆毀「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建立新文學吧!
「新舊文學論戰」,由一群青年知識份子啟動。他們反省臺灣當前文壇處境,認為文學應該革命,文化生命應該更新。
「新文學」陣營主將張我軍。 一九二一年前往中國,後進入北平師範大學國文系。他接收中國「五四運動」的文學改革思潮,對臺灣古典文學提出批判,認為應該推行白話文學。
一九二四年開始,他如同戰神般連續發表多篇文章挑戰古典文學。他認為這些「舊文學」埋沒有為的天才,陷害活潑的青年。他的主張獲得賴和、蔡孝乾的支持。
推行白話文學,不僅在討論「用什麼語言寫」,同時也蘊含「為群眾而寫」的信念。
因此,與其說他們反對古典文學,不如說是反對古典文學背後的貴族屬性,以及反對日本殖民政府「用古典文學拉攏舊仕紳」的政治盤算。
◆不服
連雅堂:你們只是「拾西方之餘唾」啊!
「舊文學」陣營的主將,則以連雅堂為主。連雅堂號稱「日治時期臺灣三大詩人」之一,為古典漢詩費盡心力。在論戰爆發的一九二四年,他開始出版《臺灣詩薈》,直到一九二五年十月止,共發行22期,是古典文學的重要陣地。
連雅堂透過出版、創作、結社,苦心維繫古典漢文學。他強調文學的審美功能,不認為文學必須涉入現實、為群眾而寫。他認為張我軍所提倡的新文學只是「拾西方文化之餘唾」,是「陷穽之蛙,不足以語汪洋之海」。
同屬「舊文學」陣營者,另有鄭坤五、黃文虎等人。
值得注意的是,這場論戰雖然造成臺灣新文學的崛起,卻並沒有造成臺灣古典文學的衰亡。日治時期的古典詩社林立,也在通俗小說領域產生強大的影響,榮景空前絕後。「新舊文學論戰」的結果不是「以新代舊」,而是成為「新舊並行」的兩大主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