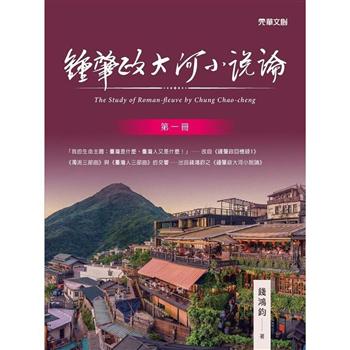第一章 鍾肇政大河小說緒論
第一節 前言
鍾肇政的代表作是所謂的「大河小說」(Roman-fleuve),並且他還有兩部,一是《濁流三部曲》,一是《臺灣人三部曲》。而臺灣文學似乎也因為有大河小說的產生與後續的影響,而有一系列下來以臺灣歷史為背景的創作,大多以三部曲的形
式,如李喬的《寒夜三部曲》、東方白的《浪淘沙》、黃娟的《楊梅三部曲》,甚至於施叔青的《臺灣三部曲》。讓臺灣評者認為臺灣文學能夠在世界文壇上有一地位而挺起胸膛。對於臺灣作家而言好像必須有一個三部曲的大河小說,才夠格
擠身大作家行列,或者自我認同作為一個臺灣作家的使命感。
當然也持續有其他作家或完成,或在努力當中,如莊華堂《臺北四部曲》、邱
家洪《臺灣大風雲》等。甚至於較少被列入受到鍾肇政影響的脈絡中,或者並非以臺灣歷史為背景的,其他長篇巨構而也被稱為大河小說的,如李榮春的《祖
國與同胞》、李永平的《海東青》。而鍾肇政個人的《濁流三部曲》因為故事發展時間只有短短三年,並以自傳體形式,而被認為不具大河小說資格。最後似乎只有《臺灣人三部曲》這類相當於歷史小說的作品,才是大河小說,或者說是臺灣大河小說的代表作。確實在影響力來說,《臺灣人三部曲》居首位是正確的。
不過,黃娟的《楊梅三部曲》也是自傳體小說,雖然是時間從戰前跨及至2000年之後,也會如《濁流三部曲》一般產生爭議。可以說《楊梅三部曲》等於是將《亞細亞的孤兒》的體裁,跨越夠大的時間長度,而在敘事形式上結合了《濁流三部曲》的體裁。甚至另外,有施叔青的力作《臺灣三部曲》並非基於明顯的臺灣人意識的打造,也可能模糊了原本評者對臺灣大河小說,此一特定名詞的內涵。也就是,最後一般認定的臺灣大河小說的代表作,似乎指的只有鍾肇政的《臺灣人三部曲》、李喬的《寒夜三部曲》、東方白的《浪淘沙》三部作品。
二十年來對名詞「大河小說」的定義、誰是第一個臺灣的大河小說作者、鍾肇政又受了誰的影響等等討論與研究是非常有趣的研究主題。並且也有詹閔旭討論李永平小說,希望以跨界角度,豐富臺灣大河小說的範疇。這裡則對第一個造就「大河小說」之名的葉石濤說法開始討論起。
第二節 大河小說的辯證
葉石濤是1966年的《鍾肇政論》中對《濁流三部曲》提出的說法。一方面葉石濤說這一系列的長篇小說「是鍾肇政的自敘傳,而非私小說。因為有冷嚴的客觀性為其骨骼。」並且說明鍾肇政的手法是「把一個人的生長和時代、社會的動向緊密地連結在一起,企圖從一個人的生活史上發掘時代、社會蛻變的巨大力量。」
但是葉石濤又說:「凡是夠得上稱為『大河小說』(Roman-fleuve)的長篇小說必須以整個人類的命運為其小說的觀點。」因此在形式上葉石濤認為《濁流三部曲》是屬於大河小說之列,但內容上則待商榷。則該討論的問題將分為兩點: 首先是大河小說是翻譯名詞,原意來自於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
羅曼羅蘭在1908年的序中問自己,希望自己看待這個角色的故事像一首詩還是寫實小說?他回答的是,他看待克利斯朵夫的人生像流動的河。這個流動之河的隱喻,是有前途、有理想的,也就是詩意的表現。所以回歸這部小說的形式,可以說「大河小說」原意就是系列小說,長度當然是遠超過約二十萬字的長篇。在1930年代,才真正為法國人引申為「大河小說」,其內容是每部各自獨立,各部反映了一個社會或時代的,而以一個主要角色或者一個家族為核心來演出。然後評論者往前追溯,將巴爾札克、左拉的小說也稱為「大河小說」。只是這兩位作家的大河小說結構並不嚴密,僅僅是一部書中的次要人物,又出現在另外一部書而成為主要人物。倒是綜合起來是符合其題名如「人間喜劇」與「盧貢-馬卡爾家族」,都是描寫了廣泛的社會風貌,或者表現好幾代的家族的故事。其後則有馬塞爾•普魯斯特的自傳體小說《追憶似水年華》,結構更為繁密而完整。如此,比較接近羅曼羅蘭的作品的大河小說,反而是鍾肇政的個人自傳體的《濁流三部曲》。
再延伸到《戰爭與和平》、《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等超長篇小說被稱為大河小說。又特別是波蘭作家顯克微之的衛國三部曲之歷史小說《火與劍》、《洪流》、《伏沃迪約夫斯基先生》。其史詩內涵歌頌著民族英雄,這樣的形式與內容可與鍾肇政的《臺灣人三部曲》類比,其結構、歷史寫作與意圖是相當的類似。
基本上按照法語原意,翻譯成「長河小說」比較恰當而可以與一般的長篇小說區隔。或許葉石濤受到1963年日本NHK開播大河劇所影響,才翻譯成大河小說。最後,臺灣的評論者以葉石濤的翻譯與附加的小說內涵來探討,「大河小說」成為接近葉石濤所發明的新名詞,而為眾評者所認同。
其次,依照葉石濤對符合大河小說的思想內涵的說法,他對《濁流三部曲》表現整個人類命運的說法,予以質疑。重點在於《流雲》並未設定在臺灣戰後的狂風怒濤的情節,至少要能反映二二八前夕的臺灣風貌。而使得如葉石濤所言《流雲》止於賺取傷感的青年男女之眼淚。
因此本書在第二章〈大河小說的起點〉,與第二部份的第一篇,也就是第四章的〈《流雲》三論─顛覆、藝術與結構胚胎〉中,指出葉石濤囿於戒嚴時代所帶來的閱讀的侷限性,而未能發現,其實在隱喻的層面,《流雲》正表現了葉石濤所要求的歷史內涵與佈劃人類理想的前景。
而本書的第二部份:《濁流三部曲》論,也希望能夠從細節與結構面來探討《濁流三部曲》的藝術表現,重新定位《濁流三部曲》是愧於大河小說之名的。只是《濁流三部曲》影響不如《臺灣人三部曲》這麼大。這並非後者的藝術性就比較高。而是要以自傳為題材,有暴露個人生平的危險之外,眾多作家不一定敢為。並且《濁流三部曲》所選中的時代,或者鍾肇政在青年最敏感的時期,恰好是臺灣歷史變動最大的歷史轉捩點,如彭瑞金所說的歷史沸騰點。其他世代的作家,要仿造自傳性小說《濁流三部曲》外,還要找到帶有複雜的歷史背景,是相當困難的。
大河小說除了自傳體與歷史小說的分法,還可以採取分為長時間與短時間的大河小說。時間長,自然也會帶有大的空間與家族的角色,如《臺灣人三部曲》、《寒夜三部曲》與《浪淘沙》。但也有自傳性的方式,如黃娟的《楊梅三部曲》。短時間的只有鍾肇政的《濁流三部曲》,挖掘的是個人內心中的大河,比較以知識份子為核心,仍有觸及農民與百姓的生活。在愛情的描述中揭示了背後的文化意義。在使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探索後,可挖掘其含有豐富的家庭與社會史、以及表現出國家認同的細膩變化,絕不能輕忽自傳式的大河小說。
有論者陳芳明認為吳濁流的自傳體小說《亞細亞的孤兒》,再加上吳濁流的自傳《無花果》、《臺灣連翹》就有大河小說的樣子。由這三部小說綜合起來的字數、所跨越的時間來看,特別就《亞細亞的孤兒》一家三代的情節,而與大河小說的形式做連結,這是很值得注意的說法。如果,《無花果》專講二二八事件,《臺灣連翹》則談臺灣1950年代。那麼,吳濁流將是臺灣大河小說的第一人。超越了鍾肇政對於臺灣人的思考這個主題的創作規模。可是《無花果》、《臺灣連翹》重複性太高,於結構與藝術性上不免有損。但是陳芳明所指出的吳濁流始自《亞細亞的孤兒》所開拓的歷史規模,是相當可觀的。如果吳濁流能夠多寫胡太明的父親或者祖父為成長背景的歷史小說,那確實可列為大河小說之林的開創性成果。
因此,探討臺灣大河小說,由鍾肇政所開創的主題,其內涵是什麼呢?也就是「臺灣人是什麼」這個命題,這牽涉到的是身分的認同。這種身分,就是臺灣人如何被特殊的看待,並非一視同仁的。而無法歸到整個群體,那麼作為臺灣人的他應該要怎麼認知自己呢?於是,鍾肇政認為臺灣人有臺灣人的歷史、故事以及英雄。臺灣人有臺灣人的命運與精神。基本上是凝視了現實與鄉土,但是充滿理想性格與反抗精神的。現實與鄉土,其實簡單說就是臺灣的過去與未來、鄉村與城市。之所以有這樣的內涵,那是因為鍾肇政的思考核心就是臺灣。基本上鍾肇政是帶有浪漫精神的,也就是著重於理想面與精神。這接近於民族意識與精神,是要追求自由、平等與尊嚴,而且已經有現代國家的觀念,民主與法治。
而臺灣史在鍾肇政眼中是什麼呢?是被壓抑的歷史,是後來的強者統治先前早來到臺灣居住的弱者的歷史。客觀來說,戰後的時代是否認與漠視臺灣人的存在,抹消臺灣人有自由意志選擇未來的想法。如果臺灣人有任何違背反共與抗日的想法,就是受到外國勢力的影響,等於是間接否認臺灣人有自己的獨特的想法。或者否認臺灣人有深刻的想法,而僅僅是由政治、權力來思考,而非尊嚴與文化的思考。就是有自主文化的思考,也被貶為是狹隘的、存心不良的,等於否認臺灣人的智慧。
鍾肇政個人的祖國意識崩潰後,在遭受上述的打壓之下,鍾肇政的臺灣人身分與臺灣意識的原型、臺灣文學的創作歷程與學習中,逐漸發展為站在中國意識、中國文學與中國人的對立面。這也就是鍾肇政在這樣的環境中產生了大河小說的想法,並不斷的與這種高壓統治的鬥爭中,更進一步的感受到以臺灣人來發聲時,所受到的政治、文化環境的壓迫。從國族意識與文學的政治、民族文化面而言,鍾肇政是相當前衛的。
鍾肇政就是在這個弱者的歷史經驗中塑造出臺灣人,尋求突破。並且反思更早來到臺灣的少數民族與弱者如原住民,將早來後到的臺灣人,融合為一整體的歷史,希望超脫這個罪孽,一起產生新的希望、再生的信心。這也是鍾肇政之後,李喬、東方白、黃娟等一起構建出來的臺灣大河小說的思考方式。這 四位作者的作品,除了採寬鬆的小說長度來認定大河小說外,在臺灣的大河小說還可分為歷史、自傳性,或者混合型三類。
第三節 傳承與定位
那麼鍾肇政作為臺灣大河小說的開創者,在藝術形式上的表現,其地位無可質疑外。在內容上卻必須追溯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以及鍾理和的《笠山農場》。在此脈絡來展開討論。因為無論是《濁流三部曲》或者《臺灣人三部曲》,其主題都與臺灣人是什麼有關,而無論吳濁流是否影響了鍾肇政,在這個「臺灣人的形象」主題上,《亞細亞的孤兒》佔了歷史的先機。而《笠山農場》卻是表現了臺灣文學第一個永恆的女性形象。而永恆的女性是鍾肇政在兩個三部曲中,分別在第三部的重要主題。並且也是因為這個完美的女性的形象的刻畫與著重於愛情的書寫,而非之前兩部以英雄反抗事件為核心,而改變了讀者的閱讀期待,造就了鍾肇政模式的三部曲的結構。
因此以臺灣文學史的定位角度來看,鍾肇政在這兩個角度上,是承續前人的。但是另一個角度,鍾肇政卻也是集其大成的。傳承並非指直接的影響,而是鍾肇政在臺灣文學史中的定位中,前人總是披荊斬棘,先佔了歷史先行者的有利位置。
首先就超越《亞細亞的孤兒》之處來討論。吳濁流是第一個描繪出臺灣人的形象,並且帶有預言性。與《濁流三部曲》的關連性、二二八的主題,值得比較。但是創作上的影響是難以判斷。可是內涵上則有重疊之處。在下一節,比較了兩書,而斷言鍾肇政文學在內涵上的獨特性在那裡。而文字、藝術、結構的龐大完整,當然更是鍾肇政藝術獨特之處,這是顯而易見的。只是吳濁流也在臺灣人形象佔了臺灣人創作者的書寫首位位置。
第一節 前言
鍾肇政的代表作是所謂的「大河小說」(Roman-fleuve),並且他還有兩部,一是《濁流三部曲》,一是《臺灣人三部曲》。而臺灣文學似乎也因為有大河小說的產生與後續的影響,而有一系列下來以臺灣歷史為背景的創作,大多以三部曲的形
式,如李喬的《寒夜三部曲》、東方白的《浪淘沙》、黃娟的《楊梅三部曲》,甚至於施叔青的《臺灣三部曲》。讓臺灣評者認為臺灣文學能夠在世界文壇上有一地位而挺起胸膛。對於臺灣作家而言好像必須有一個三部曲的大河小說,才夠格
擠身大作家行列,或者自我認同作為一個臺灣作家的使命感。
當然也持續有其他作家或完成,或在努力當中,如莊華堂《臺北四部曲》、邱
家洪《臺灣大風雲》等。甚至於較少被列入受到鍾肇政影響的脈絡中,或者並非以臺灣歷史為背景的,其他長篇巨構而也被稱為大河小說的,如李榮春的《祖
國與同胞》、李永平的《海東青》。而鍾肇政個人的《濁流三部曲》因為故事發展時間只有短短三年,並以自傳體形式,而被認為不具大河小說資格。最後似乎只有《臺灣人三部曲》這類相當於歷史小說的作品,才是大河小說,或者說是臺灣大河小說的代表作。確實在影響力來說,《臺灣人三部曲》居首位是正確的。
不過,黃娟的《楊梅三部曲》也是自傳體小說,雖然是時間從戰前跨及至2000年之後,也會如《濁流三部曲》一般產生爭議。可以說《楊梅三部曲》等於是將《亞細亞的孤兒》的體裁,跨越夠大的時間長度,而在敘事形式上結合了《濁流三部曲》的體裁。甚至另外,有施叔青的力作《臺灣三部曲》並非基於明顯的臺灣人意識的打造,也可能模糊了原本評者對臺灣大河小說,此一特定名詞的內涵。也就是,最後一般認定的臺灣大河小說的代表作,似乎指的只有鍾肇政的《臺灣人三部曲》、李喬的《寒夜三部曲》、東方白的《浪淘沙》三部作品。
二十年來對名詞「大河小說」的定義、誰是第一個臺灣的大河小說作者、鍾肇政又受了誰的影響等等討論與研究是非常有趣的研究主題。並且也有詹閔旭討論李永平小說,希望以跨界角度,豐富臺灣大河小說的範疇。這裡則對第一個造就「大河小說」之名的葉石濤說法開始討論起。
第二節 大河小說的辯證
葉石濤是1966年的《鍾肇政論》中對《濁流三部曲》提出的說法。一方面葉石濤說這一系列的長篇小說「是鍾肇政的自敘傳,而非私小說。因為有冷嚴的客觀性為其骨骼。」並且說明鍾肇政的手法是「把一個人的生長和時代、社會的動向緊密地連結在一起,企圖從一個人的生活史上發掘時代、社會蛻變的巨大力量。」
但是葉石濤又說:「凡是夠得上稱為『大河小說』(Roman-fleuve)的長篇小說必須以整個人類的命運為其小說的觀點。」因此在形式上葉石濤認為《濁流三部曲》是屬於大河小說之列,但內容上則待商榷。則該討論的問題將分為兩點: 首先是大河小說是翻譯名詞,原意來自於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
羅曼羅蘭在1908年的序中問自己,希望自己看待這個角色的故事像一首詩還是寫實小說?他回答的是,他看待克利斯朵夫的人生像流動的河。這個流動之河的隱喻,是有前途、有理想的,也就是詩意的表現。所以回歸這部小說的形式,可以說「大河小說」原意就是系列小說,長度當然是遠超過約二十萬字的長篇。在1930年代,才真正為法國人引申為「大河小說」,其內容是每部各自獨立,各部反映了一個社會或時代的,而以一個主要角色或者一個家族為核心來演出。然後評論者往前追溯,將巴爾札克、左拉的小說也稱為「大河小說」。只是這兩位作家的大河小說結構並不嚴密,僅僅是一部書中的次要人物,又出現在另外一部書而成為主要人物。倒是綜合起來是符合其題名如「人間喜劇」與「盧貢-馬卡爾家族」,都是描寫了廣泛的社會風貌,或者表現好幾代的家族的故事。其後則有馬塞爾•普魯斯特的自傳體小說《追憶似水年華》,結構更為繁密而完整。如此,比較接近羅曼羅蘭的作品的大河小說,反而是鍾肇政的個人自傳體的《濁流三部曲》。
再延伸到《戰爭與和平》、《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等超長篇小說被稱為大河小說。又特別是波蘭作家顯克微之的衛國三部曲之歷史小說《火與劍》、《洪流》、《伏沃迪約夫斯基先生》。其史詩內涵歌頌著民族英雄,這樣的形式與內容可與鍾肇政的《臺灣人三部曲》類比,其結構、歷史寫作與意圖是相當的類似。
基本上按照法語原意,翻譯成「長河小說」比較恰當而可以與一般的長篇小說區隔。或許葉石濤受到1963年日本NHK開播大河劇所影響,才翻譯成大河小說。最後,臺灣的評論者以葉石濤的翻譯與附加的小說內涵來探討,「大河小說」成為接近葉石濤所發明的新名詞,而為眾評者所認同。
其次,依照葉石濤對符合大河小說的思想內涵的說法,他對《濁流三部曲》表現整個人類命運的說法,予以質疑。重點在於《流雲》並未設定在臺灣戰後的狂風怒濤的情節,至少要能反映二二八前夕的臺灣風貌。而使得如葉石濤所言《流雲》止於賺取傷感的青年男女之眼淚。
因此本書在第二章〈大河小說的起點〉,與第二部份的第一篇,也就是第四章的〈《流雲》三論─顛覆、藝術與結構胚胎〉中,指出葉石濤囿於戒嚴時代所帶來的閱讀的侷限性,而未能發現,其實在隱喻的層面,《流雲》正表現了葉石濤所要求的歷史內涵與佈劃人類理想的前景。
而本書的第二部份:《濁流三部曲》論,也希望能夠從細節與結構面來探討《濁流三部曲》的藝術表現,重新定位《濁流三部曲》是愧於大河小說之名的。只是《濁流三部曲》影響不如《臺灣人三部曲》這麼大。這並非後者的藝術性就比較高。而是要以自傳為題材,有暴露個人生平的危險之外,眾多作家不一定敢為。並且《濁流三部曲》所選中的時代,或者鍾肇政在青年最敏感的時期,恰好是臺灣歷史變動最大的歷史轉捩點,如彭瑞金所說的歷史沸騰點。其他世代的作家,要仿造自傳性小說《濁流三部曲》外,還要找到帶有複雜的歷史背景,是相當困難的。
大河小說除了自傳體與歷史小說的分法,還可以採取分為長時間與短時間的大河小說。時間長,自然也會帶有大的空間與家族的角色,如《臺灣人三部曲》、《寒夜三部曲》與《浪淘沙》。但也有自傳性的方式,如黃娟的《楊梅三部曲》。短時間的只有鍾肇政的《濁流三部曲》,挖掘的是個人內心中的大河,比較以知識份子為核心,仍有觸及農民與百姓的生活。在愛情的描述中揭示了背後的文化意義。在使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探索後,可挖掘其含有豐富的家庭與社會史、以及表現出國家認同的細膩變化,絕不能輕忽自傳式的大河小說。
有論者陳芳明認為吳濁流的自傳體小說《亞細亞的孤兒》,再加上吳濁流的自傳《無花果》、《臺灣連翹》就有大河小說的樣子。由這三部小說綜合起來的字數、所跨越的時間來看,特別就《亞細亞的孤兒》一家三代的情節,而與大河小說的形式做連結,這是很值得注意的說法。如果,《無花果》專講二二八事件,《臺灣連翹》則談臺灣1950年代。那麼,吳濁流將是臺灣大河小說的第一人。超越了鍾肇政對於臺灣人的思考這個主題的創作規模。可是《無花果》、《臺灣連翹》重複性太高,於結構與藝術性上不免有損。但是陳芳明所指出的吳濁流始自《亞細亞的孤兒》所開拓的歷史規模,是相當可觀的。如果吳濁流能夠多寫胡太明的父親或者祖父為成長背景的歷史小說,那確實可列為大河小說之林的開創性成果。
因此,探討臺灣大河小說,由鍾肇政所開創的主題,其內涵是什麼呢?也就是「臺灣人是什麼」這個命題,這牽涉到的是身分的認同。這種身分,就是臺灣人如何被特殊的看待,並非一視同仁的。而無法歸到整個群體,那麼作為臺灣人的他應該要怎麼認知自己呢?於是,鍾肇政認為臺灣人有臺灣人的歷史、故事以及英雄。臺灣人有臺灣人的命運與精神。基本上是凝視了現實與鄉土,但是充滿理想性格與反抗精神的。現實與鄉土,其實簡單說就是臺灣的過去與未來、鄉村與城市。之所以有這樣的內涵,那是因為鍾肇政的思考核心就是臺灣。基本上鍾肇政是帶有浪漫精神的,也就是著重於理想面與精神。這接近於民族意識與精神,是要追求自由、平等與尊嚴,而且已經有現代國家的觀念,民主與法治。
而臺灣史在鍾肇政眼中是什麼呢?是被壓抑的歷史,是後來的強者統治先前早來到臺灣居住的弱者的歷史。客觀來說,戰後的時代是否認與漠視臺灣人的存在,抹消臺灣人有自由意志選擇未來的想法。如果臺灣人有任何違背反共與抗日的想法,就是受到外國勢力的影響,等於是間接否認臺灣人有自己的獨特的想法。或者否認臺灣人有深刻的想法,而僅僅是由政治、權力來思考,而非尊嚴與文化的思考。就是有自主文化的思考,也被貶為是狹隘的、存心不良的,等於否認臺灣人的智慧。
鍾肇政個人的祖國意識崩潰後,在遭受上述的打壓之下,鍾肇政的臺灣人身分與臺灣意識的原型、臺灣文學的創作歷程與學習中,逐漸發展為站在中國意識、中國文學與中國人的對立面。這也就是鍾肇政在這樣的環境中產生了大河小說的想法,並不斷的與這種高壓統治的鬥爭中,更進一步的感受到以臺灣人來發聲時,所受到的政治、文化環境的壓迫。從國族意識與文學的政治、民族文化面而言,鍾肇政是相當前衛的。
鍾肇政就是在這個弱者的歷史經驗中塑造出臺灣人,尋求突破。並且反思更早來到臺灣的少數民族與弱者如原住民,將早來後到的臺灣人,融合為一整體的歷史,希望超脫這個罪孽,一起產生新的希望、再生的信心。這也是鍾肇政之後,李喬、東方白、黃娟等一起構建出來的臺灣大河小說的思考方式。這 四位作者的作品,除了採寬鬆的小說長度來認定大河小說外,在臺灣的大河小說還可分為歷史、自傳性,或者混合型三類。
第三節 傳承與定位
那麼鍾肇政作為臺灣大河小說的開創者,在藝術形式上的表現,其地位無可質疑外。在內容上卻必須追溯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以及鍾理和的《笠山農場》。在此脈絡來展開討論。因為無論是《濁流三部曲》或者《臺灣人三部曲》,其主題都與臺灣人是什麼有關,而無論吳濁流是否影響了鍾肇政,在這個「臺灣人的形象」主題上,《亞細亞的孤兒》佔了歷史的先機。而《笠山農場》卻是表現了臺灣文學第一個永恆的女性形象。而永恆的女性是鍾肇政在兩個三部曲中,分別在第三部的重要主題。並且也是因為這個完美的女性的形象的刻畫與著重於愛情的書寫,而非之前兩部以英雄反抗事件為核心,而改變了讀者的閱讀期待,造就了鍾肇政模式的三部曲的結構。
因此以臺灣文學史的定位角度來看,鍾肇政在這兩個角度上,是承續前人的。但是另一個角度,鍾肇政卻也是集其大成的。傳承並非指直接的影響,而是鍾肇政在臺灣文學史中的定位中,前人總是披荊斬棘,先佔了歷史先行者的有利位置。
首先就超越《亞細亞的孤兒》之處來討論。吳濁流是第一個描繪出臺灣人的形象,並且帶有預言性。與《濁流三部曲》的關連性、二二八的主題,值得比較。但是創作上的影響是難以判斷。可是內涵上則有重疊之處。在下一節,比較了兩書,而斷言鍾肇政文學在內涵上的獨特性在那裡。而文字、藝術、結構的龐大完整,當然更是鍾肇政藝術獨特之處,這是顯而易見的。只是吳濁流也在臺灣人形象佔了臺灣人創作者的書寫首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