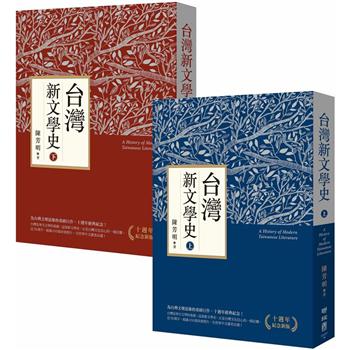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是在一八九五年台灣淪為日本殖民地之後才發生的。大清帝國在甲午戰爭挫敗後割讓台灣給日本,等於是全盤改寫這塊島嶼的歷史。島上的原住民社會與漢人移民社會,在一夜之間,被迫迎接一個全新的殖民社會。在日本殖民體制的支配之下,不僅使台灣與中國之間的政經文化聯繫產生嚴重的斷裂,也使島上住民固有的生活方式受到徹底的改造。原是屬於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傳統封建社會,在殖民政策的影響下,急劇轉化成為以工業經濟為基礎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台灣社會的傳統漢文思考,也正是受到整個大環境營造的改變而逐漸式微,而終至沒落。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化知識的崛起,以及資本主義的擴張與再擴張。就是由於這種新世紀的到來,台灣新文學才開始孕育釀造。
台灣新文學是二十世紀的產物,也是長期殖民統治刺激下的產物。站在二十世紀的終端,回首眺望整部文學史的流變軌跡,彷彿可以看到這個傷心地的受害歷史,也好像可以見證島上住民的奮鬥歷史。從最初的荒蕪未闢到今天的蓬勃繁榮,台灣文學經歷了戰前日文書寫與戰後中文書寫的兩大歷史階段。在這兩個階段,由於政治權力的干預,以及語言政策的阻撓,使得台灣新文學的成長較諸其他地區的文學還來得艱難。考察每一歷史階段的台灣作家,都可發現他們的作品留下了被損害的傷痕,也可發現作品中暗藏抵抗精神。從這個角度來看,要建構一部台灣新文學史,就不能只是停留在文學作品的美學分析,而應該注意到作家、作品在每個歷史階段與其所處時代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
朝向一部文學史的建立,往往會牽涉到史觀的問題。所謂史觀,指的是歷史書寫者的見識與詮釋;任何一種歷史解釋,都不免帶有史家的政治色彩。史家如何看待一個社會,從而如何評價一個社會中所產生的文學,都與其意識形態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在建構這部文學史時,對於台灣社會究竟是屬於何種的性質,就成為這項書寫過程的一個重要議題。台灣既然是個殖民的社會,則在這個社會中所產生的文學,自然就是殖民地文學。以殖民地文學來定位整個台灣新文學運動,當可清楚辨識在歷史過程中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權力消長關係;也可看清台灣文學從價值壟斷的階段,如何蛻變成現階段多元分殊現象;更可看清台灣作家,如何在威權支配下以雄辯的作品進行抵抗與批判。
後殖民史觀的成立
台灣新文學運動從播種萌芽到開花結果,可以說穿越了殖民時期、再殖民時期與後殖民時期等三個階段。忽略台灣社會的殖民地性格,大約就等於漠視台灣新文學在歷史進程中所形塑出來的風格與精神,這部文學史的史觀,便是建立在台灣社會是屬於殖民地社會的基礎之上。
在台灣新文學史上的第一個殖民時期,指的是從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時期。這段時期見證了日本資本主義在台灣的奠基與擴張,同時也見證了日本霸權文化在島上的鞏固與侵蝕。在這個歷史轉型期,新興的知識分子日益成為社會的重要階層。就像其他殖民地社會的情況一般,台灣知識分子扮演了啟蒙運動的角色。他們參與的啟蒙工作,包括政治運動、社會運動與文化運動。日據時期的知識分子,一方面批判性地接受日本統治者所攜來的資本主義與現代化,一方面也相當自覺地對於隱藏在資本主義與現代化背後的殖民體制;從而進行長期的、深刻的抵抗行動。他們領導了近代式的民族民主運動,介入了農民與工人運動,並且也從事喚醒女性意識的運動。伴隨著政治運動與社會運動的展開,當時的知識分子也開始舉起新文學運動的大纛,對殖民者進行思想上、精神上的對抗。台灣作家以文學形式對日本統治者展開的抗拒行動,可以說與殖民體制的興亡相始終。
文學史上的再殖民時期,則是始於一九四五年國民政府的接收台灣,止於一九八七年戒嚴體制的終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全球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與土地,都有過被殖民的經驗。非洲、中南美洲與亞洲(日本、中國除外),幾乎都淪為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人類史上的殖民時期,都隨著終戰的到來而告一段落。每一個有過殖民經驗的國家裡,大部分都可以發現其國內的知識分子開始檢討反省各自在歷史上的受害經驗。這種受害經驗的整理與評估,後來就衍化成為今日後殖民論述的主要根據。
台灣在戰後並沒有得到反省歷史的空間與機會。國民政府來台接收,帶來了強勢的中原文化;他們鄙視台灣的殖民經驗,並且將之形容為「奴化教育」。尤其是在一九五○年以後,國民政府基於國共內戰的失敗教訓,更加強化其既有的以中原取向為中心的民族思想教育,同時以武裝的警備總部為其思想檢查的後盾。為了配合反共國策,國民政府相當周密地建立了戒嚴體制。這種近乎軍事控制式的權力支配方式,較諸日本殖民體制毫不遜色。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來看,將這個階段概稱為再殖民時期,可謂恰如其分。
進入戰後的再殖民時期,台灣作家的創造力與想像力都受到高度的壓制。這種壓制,既表現在對台灣歷史記憶的扭曲與擦拭,也表現在對作家本土意識的歧視與排斥。就像日據時期官方主導的大和民族主義對整個社會的肆虐,戰後瀰漫於島上的中華民族主義,也是透過嚴密的教育體制與龐大的宣傳機器而達到囚禁作家心靈的目標。這樣的民族主義,並非建基於自主性、自發性的認同,而是出自官方強制性、脅迫性的片面灌輸。因此,至少到一九八○年代解嚴之前,台灣作家對民族主義的認同就出現了分裂的狀態。認同中華民族主義的作家,基本上接受文藝政策的指導;他們以文學形式支持反共政策,並大肆宣揚民族主義。這種文學作家,可以說是屬於官方的文學。另一種作家,則是對中華民族主義採取抗拒的態度。他們創造的文學,以反映台灣社會的生活實況為主要題材,對於威權體制則進行直接或間接的批判諷刺。這是屬於民間的文學。
官方文學與民間文學,一直是戰後文學史上的兩條主要路線。這兩種文學經歷過規模大小不等的論戰,而終於在一九七七年的鄉土文學論戰中發生了對決。通過鄉土文學論戰之後,民間文學開始獲得台灣社會的首肯。無論這樣的民間文學在此之前,稱為鄉土文學也好,或是稱為本土文學也好,在論戰之後都正式以「台灣文學」的名稱得到普遍的接受。如果說,戰後文學發展的軌跡便是一段台灣文學正名的掙扎史,應該不是過於誇張的說法。那種掙扎,毋寧是延續日據時期台灣作家的抵抗與批判的精神。
不過,戰後作家從事的抵抗工作,較諸日據時期作家還來得加倍困難。因為,日據時期台灣作家所投入的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運動,純粹是針對日本殖民體制而展開的。戰後作家的去殖民工作,則不僅要批判日本統治者所遺留下來的殖民文化殘餘,同時也要抵制政治權力正在氾濫的戒嚴體制。這雙重的去殖民化,構成了再殖民時期台灣文學的重要特色。
文學史上的後殖民時期,當以一九八七年七月的解除戒嚴令為象徵性的開端。所謂象徵性,乃是指這樣的歷史分水嶺並不是那麼精確。進入八○年代以後,以中國為取向的戒嚴文化已開始出現鬆綁的現象。在政治上,要求改革的聲音已經傳遍島上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個階層。在經濟上,由於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台商突破禁忌,逐漸與中國建立通商的關係。在社會上,曾經被邊緣化的弱勢聲音,例如原住民的復權運動、女性主義運動、同志運動、客語運動等等都漸漸釋放出來。因此,在正式宣布解嚴之前,依賴思想檢查與言論控制的威權體制,次第受到各種社會力量的挑戰而出現傾頹之勢。
解嚴後表現在文學上的後殖民現象,最重要的莫過於各種大敘述之遭到挑戰,以及各種歷史記憶的紛紛重建。大敘述(grand narrative)指的是文學上習以為常的、雄偉的審美觀念與品味。在中華民族主義當道的年代,文學的審美都是以地大物博的中原觀念為中心。這種審美是以中華沙文主義、漢人沙文主義、男性沙文主義、異性戀沙文主義為基調。具體言之,大敘述的美學,不免是一種文化上的霸權論述。文化霸權之所以能夠蔓延橫行,乃是拜賜於威權式的戒嚴體制之存在。在霸權的支配下,整個台灣社會必須一律接受單元式的、壟斷式的美學觀念。這種一致性的要求,使得個別的、差異的、弱勢的審美受到強烈的壓制。然而,緊跟著戒嚴體制的崩解,大敘述的美學也很快就引起作家的普遍質疑。
後殖民文學的一個重要特色,便是作家已自覺到要避開權力中心的操控。這種去中心(decentering)的傾向,與後現代主義的去中心有異曲同工之處。因此,有人常常把解嚴後台灣文學的多元化現象,解釋為後現代狀況(postmodern condition)。不過,這裡必須辨明的是後殖民與後現代之間有一很大的分野,乃在於前者側重強調主體性的重建(re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而後者則傾向於強調主體性的解構(de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後現代主義者並不在意歷史記憶的重建,後殖民主義者則非常重視歷史記憶的再建構。以這個觀點來檢驗解嚴後文學蓬勃的盛況,當可發現那是屬於後殖民文學特徵,而非後現代文學的精神。有關這兩種文學的發展概況,當於本書的最後一章詳細討論。
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曾經被權力邊緣化的弱勢聲音,在後戒嚴時期所形成的挑戰格局是相當多元化的。中國大敘述的文學,開始遭逢台灣意識文學的挑戰。然而,台灣意識文學不免帶有大敘述的色彩時,也終於受到原住民作家與女性意識作家的挑戰。同樣的,當女性意識作家開始出現異性戀中心的傾向時,也不免受到同志作家的質疑。這說明了後戒嚴時期的後殖民文學之所以特別精采的原因。台灣意識文學、女性文學、原住民文學、眷村文學、同志文學都同時並存的現象,正好反證了在殖民時期與再殖民時期台灣社會的創造心靈是受到何等嚴重的戕害。潛藏在社會內部的文學思考能量一旦獲得釋放以後,就再也不能使用過去的審美標準當作僅有的尺碼。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應該分別放在族群、階級、性別的脈絡中來驗證。
每一個族群,每一個階級,每一種性別取向,都有各自的思維方式與歷史記憶。彼此的思維與記憶,都不能相互取代。不同的族群記憶,或階級記憶,或性別記憶,都分別是一個主體。在日據的殖民時期與戰後的再殖民時期,主體似乎只有一個,那就是以統治者的意志作為唯一的審美標準。在單一標準的檢驗下,社會內部的不同價值、欲望、思考都完全受到忽視。但是,在後殖民時期,威權體制已不再像過去那樣鞏固,劃一的、全盤性的美學也逐漸讓位給多樣的、局部的、瑣碎的美學。因此,在後殖民時期,有關台灣文學的定義概念也有著相應的調整與擴張。
在日據時期,台灣文學是相對於日本殖民體制而存在的。那時期的台灣文學,是以台灣人作家為主體,文學作品內容則充滿了抗議,甚至是抗爭的聲音。到了戰後,台灣文學則是相對於戒嚴體制而存在。這段時期的台灣文學,乃是以受威權干涉或壓迫的作家為主,文學作品如果不是與戒嚴體制保持疏離的關係,便是採取正面或迂迴的抗拒態度。進入解嚴時期之後,台灣文學主體性的議題才正式受到檢討。這個階段的文學主體,就再也不能停留在抗爭的、排他的層面。沒有任何一個族群、階級或性別能夠居於權力中心。在台灣社會裡,任何一種文學思考、生活經驗與歷史記憶,都是屬於主體。所有的這些個別主體結合起來,台灣文學的主體性才能浮現。因此,後殖民時期的台灣文學,應該是屬於具有多元性、包容性的寬闊定義。不論族群歸屬為何,階級認同為何,性別取向為何,凡是在台灣社會所產生的文學,便是台灣文學主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正是站在這種後殖民史觀的立場上,台灣文學史的建構才獲得它的著力點與切入點。更確切地說,本書所依據的後殖民史觀,便是通過左翼的、女性的、邊緣的、動態的歷史解釋來涵蓋整部新文學運動的發展。
重新建構台灣文學史
豐碩的台灣文學遺產,誠然已經到了需要重估的時代。自一九八○年以降,台灣文學被公認是一項「顯學」。然而,這個領域逐漸提升為開放的學問時,它又立即成為各種政治解釋爭奪的場域。從這個角度來看,它其實也是一項「險學」。淪為危險學問的主因,乃在於台灣文學主體的重建不斷受到嚴厲的挑戰。
挑戰的主要來源之一,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在最近十餘年來已出版了數冊有關台灣文學史的專書,例如白少帆等主編的《現代台灣文學史》、古繼堂的《靜聽那心底的旋律—台灣文學論》、黃重添等的《台灣新文學概觀》(上)(下),以及劉登翰等的《台灣文學史》(上)(下)。這些著作的共同特色,就是持續把台灣文學邊緣化、靜態化、陰性化。他們使用邊緣化的策略,把北京政府主導下的文學解釋膨脹為主流,認為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不可分割的一環,把台灣文學視為一種固定不變的存在,甚至認為台灣作家永遠都在期待並憧憬「祖國」。這種解釋,完全無視台灣文學內容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不斷在成長擴充。僵硬的、教條的歷史解釋,可以說相當徹底地扭曲並誤解台灣文學有其自主性的發展。從中國學者的論述可以發現,他們根本沒有實際的台灣歷史經驗,也沒有真正生活的社會經濟基礎。台灣只是存在於他們虛構的想像之中,只是北京霸權論述的餘緒。他們的想像,與從前荷蘭、日本殖民論述裡的台灣圖像,可謂毫無二致。因此。中國學者的台灣文學史書寫,其實是一種變相的新殖民主義。
現階段台灣文學史的重建,並不只是受到來自中國的挑戰,存在於台灣學界的還是有很多障礙。其中以族群與性別的兩大議題,仍有待克服。在族群議題方面,漢人沙文主義事實上還相當程度地瀰漫於知識分子之間。原住民文學的書寫,在八○年代以後有盛放之勢。不過,在一些文學選集與學術會議裡得到的注意,與其生產力似乎不成比例。族群議題中的另一值得重視的問題,便是外省作家或眷村作家的作品,常常必須受到「本土」尺碼的檢驗。在威權時代,本土也許可以等同於悲情的、受難的歷史記憶。但是,在解嚴後,本土應該是跨越悲情與受難,而對於島上孕育出來的任何一種文學都可劃歸本土的行列。
更擴大一點來說,既然是經過台灣風土所釀造出來的文學都是屬於本土的,則皇民運動時期的日本作家如西川滿、庄司總一、濱田隼雄等人的作品,也都可以放在台灣文學的範疇裡來討論。同樣的,戰後的官方文學,或少數被指控為「御用作家」的作品,當然也可以納入台灣文學史的脈絡裡來評估。歷史原是不擇細流才能成其大。有過殖民經驗的台灣,自然比其他正常的社會還更複雜,因此表現出來的歷史記憶與文學思考也來得出奇的繁複。從後殖民史觀的立場來看,代表不同階級、不同族群的文學,都是建構殖民地文學的重要一環。
性別議題帶來思考上的障礙,可能較諸族群議題還嚴重。對於同性戀或同志文學,台灣學界似乎還未能保持開放尊重的態度。異性戀中心觀念的支配,使得同志文學長期被邊緣化。事實上,同性戀的存在,乃是構成台灣歷史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擦拭同志文學的重要性,等於也是在矮化、窄化台灣歷史的格局。九○年代同志文學點燃了前所未有的想像,也挖掘了許多未經開發的感覺。那種細膩的書寫,早已超越了異性戀中心的文學傳統。
世紀的大門就要啟開,重新回顧台灣文學史,為的是要迎接全新的歷史經驗。在前人辛勤建立起來的研究基礎上,這部文學史試圖做一些可能的突破。日據時期的左翼文學,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本書希望提升其能見度。皇民文學的爭議,到現階段仍未嘗稍止,本書將以後殖民的觀點進行討論。反共文學的評估,至今也還是猶豫未決,本書固然不在平反,但必須做某種程度的翻案。台灣意識文學長期受到霸權論述的打壓,現在也似乎應該給予恰當的定位。然而更重要的是,女性作家的書寫在過去都一直被刻意忽視,本書將予以審慎評價。沒有一成不變的歷史經驗,自然也就沒有一成不變的歷史書寫。建構這部文學史,既然是在挑戰舊思維,那麼,新世紀到來時,這本書也應該接受新的挑戰。歷史巨門已然打開,就沒有理由不勇敢向前邁出。
台灣新文學是二十世紀的產物,也是長期殖民統治刺激下的產物。站在二十世紀的終端,回首眺望整部文學史的流變軌跡,彷彿可以看到這個傷心地的受害歷史,也好像可以見證島上住民的奮鬥歷史。從最初的荒蕪未闢到今天的蓬勃繁榮,台灣文學經歷了戰前日文書寫與戰後中文書寫的兩大歷史階段。在這兩個階段,由於政治權力的干預,以及語言政策的阻撓,使得台灣新文學的成長較諸其他地區的文學還來得艱難。考察每一歷史階段的台灣作家,都可發現他們的作品留下了被損害的傷痕,也可發現作品中暗藏抵抗精神。從這個角度來看,要建構一部台灣新文學史,就不能只是停留在文學作品的美學分析,而應該注意到作家、作品在每個歷史階段與其所處時代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
朝向一部文學史的建立,往往會牽涉到史觀的問題。所謂史觀,指的是歷史書寫者的見識與詮釋;任何一種歷史解釋,都不免帶有史家的政治色彩。史家如何看待一個社會,從而如何評價一個社會中所產生的文學,都與其意識形態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在建構這部文學史時,對於台灣社會究竟是屬於何種的性質,就成為這項書寫過程的一個重要議題。台灣既然是個殖民的社會,則在這個社會中所產生的文學,自然就是殖民地文學。以殖民地文學來定位整個台灣新文學運動,當可清楚辨識在歷史過程中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權力消長關係;也可看清台灣文學從價值壟斷的階段,如何蛻變成現階段多元分殊現象;更可看清台灣作家,如何在威權支配下以雄辯的作品進行抵抗與批判。
後殖民史觀的成立
台灣新文學運動從播種萌芽到開花結果,可以說穿越了殖民時期、再殖民時期與後殖民時期等三個階段。忽略台灣社會的殖民地性格,大約就等於漠視台灣新文學在歷史進程中所形塑出來的風格與精神,這部文學史的史觀,便是建立在台灣社會是屬於殖民地社會的基礎之上。
在台灣新文學史上的第一個殖民時期,指的是從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時期。這段時期見證了日本資本主義在台灣的奠基與擴張,同時也見證了日本霸權文化在島上的鞏固與侵蝕。在這個歷史轉型期,新興的知識分子日益成為社會的重要階層。就像其他殖民地社會的情況一般,台灣知識分子扮演了啟蒙運動的角色。他們參與的啟蒙工作,包括政治運動、社會運動與文化運動。日據時期的知識分子,一方面批判性地接受日本統治者所攜來的資本主義與現代化,一方面也相當自覺地對於隱藏在資本主義與現代化背後的殖民體制;從而進行長期的、深刻的抵抗行動。他們領導了近代式的民族民主運動,介入了農民與工人運動,並且也從事喚醒女性意識的運動。伴隨著政治運動與社會運動的展開,當時的知識分子也開始舉起新文學運動的大纛,對殖民者進行思想上、精神上的對抗。台灣作家以文學形式對日本統治者展開的抗拒行動,可以說與殖民體制的興亡相始終。
文學史上的再殖民時期,則是始於一九四五年國民政府的接收台灣,止於一九八七年戒嚴體制的終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全球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與土地,都有過被殖民的經驗。非洲、中南美洲與亞洲(日本、中國除外),幾乎都淪為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人類史上的殖民時期,都隨著終戰的到來而告一段落。每一個有過殖民經驗的國家裡,大部分都可以發現其國內的知識分子開始檢討反省各自在歷史上的受害經驗。這種受害經驗的整理與評估,後來就衍化成為今日後殖民論述的主要根據。
台灣在戰後並沒有得到反省歷史的空間與機會。國民政府來台接收,帶來了強勢的中原文化;他們鄙視台灣的殖民經驗,並且將之形容為「奴化教育」。尤其是在一九五○年以後,國民政府基於國共內戰的失敗教訓,更加強化其既有的以中原取向為中心的民族思想教育,同時以武裝的警備總部為其思想檢查的後盾。為了配合反共國策,國民政府相當周密地建立了戒嚴體制。這種近乎軍事控制式的權力支配方式,較諸日本殖民體制毫不遜色。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來看,將這個階段概稱為再殖民時期,可謂恰如其分。
進入戰後的再殖民時期,台灣作家的創造力與想像力都受到高度的壓制。這種壓制,既表現在對台灣歷史記憶的扭曲與擦拭,也表現在對作家本土意識的歧視與排斥。就像日據時期官方主導的大和民族主義對整個社會的肆虐,戰後瀰漫於島上的中華民族主義,也是透過嚴密的教育體制與龐大的宣傳機器而達到囚禁作家心靈的目標。這樣的民族主義,並非建基於自主性、自發性的認同,而是出自官方強制性、脅迫性的片面灌輸。因此,至少到一九八○年代解嚴之前,台灣作家對民族主義的認同就出現了分裂的狀態。認同中華民族主義的作家,基本上接受文藝政策的指導;他們以文學形式支持反共政策,並大肆宣揚民族主義。這種文學作家,可以說是屬於官方的文學。另一種作家,則是對中華民族主義採取抗拒的態度。他們創造的文學,以反映台灣社會的生活實況為主要題材,對於威權體制則進行直接或間接的批判諷刺。這是屬於民間的文學。
官方文學與民間文學,一直是戰後文學史上的兩條主要路線。這兩種文學經歷過規模大小不等的論戰,而終於在一九七七年的鄉土文學論戰中發生了對決。通過鄉土文學論戰之後,民間文學開始獲得台灣社會的首肯。無論這樣的民間文學在此之前,稱為鄉土文學也好,或是稱為本土文學也好,在論戰之後都正式以「台灣文學」的名稱得到普遍的接受。如果說,戰後文學發展的軌跡便是一段台灣文學正名的掙扎史,應該不是過於誇張的說法。那種掙扎,毋寧是延續日據時期台灣作家的抵抗與批判的精神。
不過,戰後作家從事的抵抗工作,較諸日據時期作家還來得加倍困難。因為,日據時期台灣作家所投入的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運動,純粹是針對日本殖民體制而展開的。戰後作家的去殖民工作,則不僅要批判日本統治者所遺留下來的殖民文化殘餘,同時也要抵制政治權力正在氾濫的戒嚴體制。這雙重的去殖民化,構成了再殖民時期台灣文學的重要特色。
文學史上的後殖民時期,當以一九八七年七月的解除戒嚴令為象徵性的開端。所謂象徵性,乃是指這樣的歷史分水嶺並不是那麼精確。進入八○年代以後,以中國為取向的戒嚴文化已開始出現鬆綁的現象。在政治上,要求改革的聲音已經傳遍島上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個階層。在經濟上,由於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台商突破禁忌,逐漸與中國建立通商的關係。在社會上,曾經被邊緣化的弱勢聲音,例如原住民的復權運動、女性主義運動、同志運動、客語運動等等都漸漸釋放出來。因此,在正式宣布解嚴之前,依賴思想檢查與言論控制的威權體制,次第受到各種社會力量的挑戰而出現傾頹之勢。
解嚴後表現在文學上的後殖民現象,最重要的莫過於各種大敘述之遭到挑戰,以及各種歷史記憶的紛紛重建。大敘述(grand narrative)指的是文學上習以為常的、雄偉的審美觀念與品味。在中華民族主義當道的年代,文學的審美都是以地大物博的中原觀念為中心。這種審美是以中華沙文主義、漢人沙文主義、男性沙文主義、異性戀沙文主義為基調。具體言之,大敘述的美學,不免是一種文化上的霸權論述。文化霸權之所以能夠蔓延橫行,乃是拜賜於威權式的戒嚴體制之存在。在霸權的支配下,整個台灣社會必須一律接受單元式的、壟斷式的美學觀念。這種一致性的要求,使得個別的、差異的、弱勢的審美受到強烈的壓制。然而,緊跟著戒嚴體制的崩解,大敘述的美學也很快就引起作家的普遍質疑。
後殖民文學的一個重要特色,便是作家已自覺到要避開權力中心的操控。這種去中心(decentering)的傾向,與後現代主義的去中心有異曲同工之處。因此,有人常常把解嚴後台灣文學的多元化現象,解釋為後現代狀況(postmodern condition)。不過,這裡必須辨明的是後殖民與後現代之間有一很大的分野,乃在於前者側重強調主體性的重建(re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而後者則傾向於強調主體性的解構(de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後現代主義者並不在意歷史記憶的重建,後殖民主義者則非常重視歷史記憶的再建構。以這個觀點來檢驗解嚴後文學蓬勃的盛況,當可發現那是屬於後殖民文學特徵,而非後現代文學的精神。有關這兩種文學的發展概況,當於本書的最後一章詳細討論。
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曾經被權力邊緣化的弱勢聲音,在後戒嚴時期所形成的挑戰格局是相當多元化的。中國大敘述的文學,開始遭逢台灣意識文學的挑戰。然而,台灣意識文學不免帶有大敘述的色彩時,也終於受到原住民作家與女性意識作家的挑戰。同樣的,當女性意識作家開始出現異性戀中心的傾向時,也不免受到同志作家的質疑。這說明了後戒嚴時期的後殖民文學之所以特別精采的原因。台灣意識文學、女性文學、原住民文學、眷村文學、同志文學都同時並存的現象,正好反證了在殖民時期與再殖民時期台灣社會的創造心靈是受到何等嚴重的戕害。潛藏在社會內部的文學思考能量一旦獲得釋放以後,就再也不能使用過去的審美標準當作僅有的尺碼。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應該分別放在族群、階級、性別的脈絡中來驗證。
每一個族群,每一個階級,每一種性別取向,都有各自的思維方式與歷史記憶。彼此的思維與記憶,都不能相互取代。不同的族群記憶,或階級記憶,或性別記憶,都分別是一個主體。在日據的殖民時期與戰後的再殖民時期,主體似乎只有一個,那就是以統治者的意志作為唯一的審美標準。在單一標準的檢驗下,社會內部的不同價值、欲望、思考都完全受到忽視。但是,在後殖民時期,威權體制已不再像過去那樣鞏固,劃一的、全盤性的美學也逐漸讓位給多樣的、局部的、瑣碎的美學。因此,在後殖民時期,有關台灣文學的定義概念也有著相應的調整與擴張。
在日據時期,台灣文學是相對於日本殖民體制而存在的。那時期的台灣文學,是以台灣人作家為主體,文學作品內容則充滿了抗議,甚至是抗爭的聲音。到了戰後,台灣文學則是相對於戒嚴體制而存在。這段時期的台灣文學,乃是以受威權干涉或壓迫的作家為主,文學作品如果不是與戒嚴體制保持疏離的關係,便是採取正面或迂迴的抗拒態度。進入解嚴時期之後,台灣文學主體性的議題才正式受到檢討。這個階段的文學主體,就再也不能停留在抗爭的、排他的層面。沒有任何一個族群、階級或性別能夠居於權力中心。在台灣社會裡,任何一種文學思考、生活經驗與歷史記憶,都是屬於主體。所有的這些個別主體結合起來,台灣文學的主體性才能浮現。因此,後殖民時期的台灣文學,應該是屬於具有多元性、包容性的寬闊定義。不論族群歸屬為何,階級認同為何,性別取向為何,凡是在台灣社會所產生的文學,便是台灣文學主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正是站在這種後殖民史觀的立場上,台灣文學史的建構才獲得它的著力點與切入點。更確切地說,本書所依據的後殖民史觀,便是通過左翼的、女性的、邊緣的、動態的歷史解釋來涵蓋整部新文學運動的發展。
重新建構台灣文學史
豐碩的台灣文學遺產,誠然已經到了需要重估的時代。自一九八○年以降,台灣文學被公認是一項「顯學」。然而,這個領域逐漸提升為開放的學問時,它又立即成為各種政治解釋爭奪的場域。從這個角度來看,它其實也是一項「險學」。淪為危險學問的主因,乃在於台灣文學主體的重建不斷受到嚴厲的挑戰。
挑戰的主要來源之一,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在最近十餘年來已出版了數冊有關台灣文學史的專書,例如白少帆等主編的《現代台灣文學史》、古繼堂的《靜聽那心底的旋律—台灣文學論》、黃重添等的《台灣新文學概觀》(上)(下),以及劉登翰等的《台灣文學史》(上)(下)。這些著作的共同特色,就是持續把台灣文學邊緣化、靜態化、陰性化。他們使用邊緣化的策略,把北京政府主導下的文學解釋膨脹為主流,認為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不可分割的一環,把台灣文學視為一種固定不變的存在,甚至認為台灣作家永遠都在期待並憧憬「祖國」。這種解釋,完全無視台灣文學內容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不斷在成長擴充。僵硬的、教條的歷史解釋,可以說相當徹底地扭曲並誤解台灣文學有其自主性的發展。從中國學者的論述可以發現,他們根本沒有實際的台灣歷史經驗,也沒有真正生活的社會經濟基礎。台灣只是存在於他們虛構的想像之中,只是北京霸權論述的餘緒。他們的想像,與從前荷蘭、日本殖民論述裡的台灣圖像,可謂毫無二致。因此。中國學者的台灣文學史書寫,其實是一種變相的新殖民主義。
現階段台灣文學史的重建,並不只是受到來自中國的挑戰,存在於台灣學界的還是有很多障礙。其中以族群與性別的兩大議題,仍有待克服。在族群議題方面,漢人沙文主義事實上還相當程度地瀰漫於知識分子之間。原住民文學的書寫,在八○年代以後有盛放之勢。不過,在一些文學選集與學術會議裡得到的注意,與其生產力似乎不成比例。族群議題中的另一值得重視的問題,便是外省作家或眷村作家的作品,常常必須受到「本土」尺碼的檢驗。在威權時代,本土也許可以等同於悲情的、受難的歷史記憶。但是,在解嚴後,本土應該是跨越悲情與受難,而對於島上孕育出來的任何一種文學都可劃歸本土的行列。
更擴大一點來說,既然是經過台灣風土所釀造出來的文學都是屬於本土的,則皇民運動時期的日本作家如西川滿、庄司總一、濱田隼雄等人的作品,也都可以放在台灣文學的範疇裡來討論。同樣的,戰後的官方文學,或少數被指控為「御用作家」的作品,當然也可以納入台灣文學史的脈絡裡來評估。歷史原是不擇細流才能成其大。有過殖民經驗的台灣,自然比其他正常的社會還更複雜,因此表現出來的歷史記憶與文學思考也來得出奇的繁複。從後殖民史觀的立場來看,代表不同階級、不同族群的文學,都是建構殖民地文學的重要一環。
性別議題帶來思考上的障礙,可能較諸族群議題還嚴重。對於同性戀或同志文學,台灣學界似乎還未能保持開放尊重的態度。異性戀中心觀念的支配,使得同志文學長期被邊緣化。事實上,同性戀的存在,乃是構成台灣歷史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擦拭同志文學的重要性,等於也是在矮化、窄化台灣歷史的格局。九○年代同志文學點燃了前所未有的想像,也挖掘了許多未經開發的感覺。那種細膩的書寫,早已超越了異性戀中心的文學傳統。
世紀的大門就要啟開,重新回顧台灣文學史,為的是要迎接全新的歷史經驗。在前人辛勤建立起來的研究基礎上,這部文學史試圖做一些可能的突破。日據時期的左翼文學,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本書希望提升其能見度。皇民文學的爭議,到現階段仍未嘗稍止,本書將以後殖民的觀點進行討論。反共文學的評估,至今也還是猶豫未決,本書固然不在平反,但必須做某種程度的翻案。台灣意識文學長期受到霸權論述的打壓,現在也似乎應該給予恰當的定位。然而更重要的是,女性作家的書寫在過去都一直被刻意忽視,本書將予以審慎評價。沒有一成不變的歷史經驗,自然也就沒有一成不變的歷史書寫。建構這部文學史,既然是在挑戰舊思維,那麼,新世紀到來時,這本書也應該接受新的挑戰。歷史巨門已然打開,就沒有理由不勇敢向前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