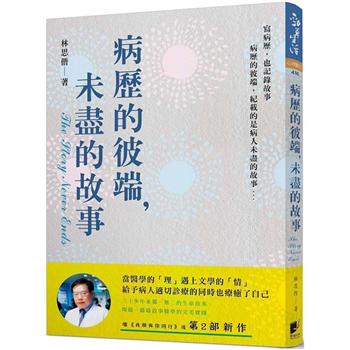越老越相信,了解一個病人,必須從病歷之外的角度,「面對面」熟悉他的職業、家人、嗜好;越老越喜歡,像「老朋友」一樣,告訴病人我自己的見解和興趣,update一下彼此的生活。
總是習慣聆聽病人在病歷之外的那些故事,掌握最真實的「病人敘事」。
以簡馭繁,三言兩語交代病況的電子病歷,令我覺得堅硬難以穿透,電腦就像我和病人之間的「第三者」。
我更喜歡那些堆滿檔案櫃,散發溫度的手寫病歷,我是個舊版醫生……
舊版醫師
查房時,我問住院醫師一個病人的實驗室數據,他拿出他的iPad,簽入,開始滑……
在他還沒查到之前,他驚訝地發現,我居然能不用查什麼,就說出四個病人三天前的血清鉀離子濃度……
對一九九○年後出生的這一代,「何處可以找到資料」比「資料是什麼」還重要。
他們認為,數秒內可以查到的事,為什麼要「知道」?我再也回不去那個可以電人而後快的尊師重道年代。
我發現自己是一隻恐龍,只是還沒完全絕跡而已。
過年前幾天,管理處給我一個Email,告訴我,我是全科唯一仍在用His2.0(舊版電腦)的主治醫師。
(我是個念舊的人。)
我曾經歷一段不算短的手寫病歷年代。自從有了電子病歷,電腦成為我和病人之間的「第三者」。
(我很氣它破壞我跟病人之間的好事。)
我越老越相信,了解一個病人,必須從病歷之外的角度,「面對面」熟悉他的職業、家人、嗜好……
我越來越喜歡,像「老朋友」一樣,告訴病人我自己的見解和興趣,聊聊彼此的生活,這樣,我就會得到的更多……
看到「報表」上敬陪末座的,我的「劣跡」。要是我年輕幾歲,一定打電話去抗議的。
這些年「電腦」所企圖阻擋我不成、我和病人間建立「深刻連結」所產生的喜悅,終究化解了我的衝動。
某天門診,一位建築設計師鉅細靡遺告訴我他一天的「生活日常」,我聽得入神。
他離去後,我對護理師說:「他說那麼多,應該要向我收錢的。」
她一面理解表示同意,一面微笑對我說:「林醫師你要看快一點,後面還很多人呢!」
病歷
「大腸桿菌泌尿道感染合併敗血症」,我的手機簡訊顯示。這就是這男孩在醫院的唯一辨識記號。堅硬而難以穿透,他已經不能多嘴。
醫學訊息要求以簡馭繁。三言兩語就把病人交代清楚,當然最好。「電子病歷」井然有序,或許可以勝任吧。
可是一旦戰線拉長,醫病的交鋒超過數週、甚至數月,電子病歷提供的訊息就不知所云了。它總結疾病還可以,但不足以捕捉病人的全貌。
病人過什麼樣的生活?我們要成為什麼樣的醫師?
我們的醫療照顧把病人變成什麼模樣?他的生活品質有提升嗎?疼痛減除否?
我們需要觀察在病房之外行動的病人,並且聽到他們講的話。我們需要一些「病人敘事」。
可惜電子病歷上看不到故事。它的功能是把每個疾病都編個代碼(Code),以便向健保局申報費用……
一個許久前看過診的小朋友長大要當兵了,回來找我要病歷。我從大學校本部倉庫借到,應該是所剩無幾的手寫病歷了,在我還是住院醫師的那個年代。
我一頁頁小心翻動,這斑駁而滄桑的回憶,深怕它破碎。
他的童年風雨飄搖,還住過幾次加護病房。我看到好友二十幾年前當實習醫師時在急診的筆跡,那麼果斷,那麼殷切,像現在一樣。
我也看到當時醫學系四年級生寫的progress note,端正而拘謹,現在是某科的當紅炸子雞;我更看到寫過這本病歷的醫師與護士,有的退休,有的逝世,有的則成了另一部病歷上的主角,正在生死線上掙扎。
最後我看到我自己的文字,上頭記錄著現在早已遺忘,但曾確確實實參與病人生命的那一小段旅程。
多寫幾個字,總是好的。
昨天門診來了一位我在二○○一年診斷的「低免疫球蛋白血症」病患,那時她才六歲。
她的身體無法自行製造免疫球蛋白。李醫師和我已經追蹤治療她近二十個年頭。方法就是按月注射IVIG。(註)
正處荳蔻年華的她,從事醫療器材相關行業。生活與常人無異,只是還得每個月向醫院報到。
記得診斷之初,我向她爸爸說,別灰心,基因醫學的研究終會找出根治的方法,有一天她將不必再依賴藥物。
但仍不免擔心,這孩子有未來嗎?她能活到我退休那一天嗎?
二十年過去了。這病根治的希望依然像「隧道盡頭的微光」,治療的方式還是和二十年前一樣。但孩子勇敢茁壯,李醫師和我的頭已灰白。
我們照顧她,曾經混亂、曾經遲疑、曾經恐慌,且情況勢必仍會持續。
她的故事並非全然關乎科學,我們更從她身上學到了無價的人生課程。
那是面對人生無法改變的逆境時,人的決心和勇氣。
拉下病歷捲軸(現在已經不能用翻的),仔細審思。病人教我們,面對自己人生劇變時,保持樂觀,欣然接受挑戰。
註:IVIG,靜脈注射免疫球蛋白。
病歷背後的人
病人明天要做「心導管」,我必須確定病人所有「過去病史」都已經「問好問滿」。
我先看了一下病歷,一個四十五中年男性,糖尿病、肥胖、高血壓、高血脂症,加上痛風……
「他不得心臟病才怪……」我在心裡嘀咕。
他是再「典型」不過的病人,即使對我這個實習醫師來說。他的病歷還真的有點厚。他曾經走到末期腎病,接受透析四年,後來幸運接受「腎臟移植」……
裡面有許多我看不懂的「術式」和「移植藥物」。總之,他最近心臟功能有點下降。
雖然心裡有個底,我還是得進去病房問一問。
我(自認)很親切的自我介紹並打招呼,可是病人看起來十分遙遠而焦慮。病史詢問時,他顯得不耐煩,甚至有一點惱怒。
我問他:「了不了解明天要做的手術?」他竟然大聲咆哮。
「你最好別傷到我的腎臟!」
我向他詳細解釋手術的流程,包括會用到一些含碘的顯影劑,他又再次打斷我。
「如果會傷我的腎臟,不如就把我殺了。」
病人如此絕決的宣示,使我懷疑,他是不是患了「憂鬱症」,正不知如何回話時,他又說:「你大概不知道我做血液透析那四年,日子是怎麼過的。我被迫換工作,家人朋友遺棄我,直到我接受腎臟移植,生活才回歸正途……」
我還是很盡職的說明手術可能的「風險」。
他搖搖頭,挑釁的說:「我不能接受任何風險。我寧可死,也不能再讓我的腎臟壞掉……」至此,我已經完全確定我無法完成他的「術前表格」了。
這是我接過第一個病人如此清楚表達:腎臟疾病對他造成的,深刻的身體創傷和心理波折。他的哀傷跟憂慮「信而有徵」。那些待填的「表格」聽起來如此敷衍,顯然無法化解他對「風險」的疑慮。
我有深深的罪惡感,覺得自己不該以「病歷」取人,只給他一些輕率而制式的回應。不要因為病人住了院、穿著「病袍」,就把他看成是某種「病」。別忘了,他也是一個「人」。而「人」,有時遠比你看病歷所能想像的,複雜而難解。
電子病歷一位阿公帶著孫子來看病。他們是「常客」,孫子有氣喘,規律回來拿藥。我跟阿公也熟了起來。
看完孫子,阿公問我,可不可以幫他掛號,他說他最近不太舒服,也想給我看看。
他有高血壓和糖尿病,本來在內分泌科定期追蹤。最近因太常爽約,掛不回原來的主治醫師。
我說好。阿公遞給我健保卡,我在電腦上操作。我心想,頂多按照原來的藥開給他。
電子病歷有一種好處,看不出病歷有多厚。
阿公上次抽血報告,HbA1C(上個月的平均血糖值)8.2,超標。他的血壓,170/110,也偏高。
「阿公,你的血糖和血壓都不及格。是不是沒吃藥?這樣不行喔。」
阿公說:「對不起,醫師,我是一個很壞的病人。最近我老伴走了,走得太突然了。」
我把目光從電腦螢幕移到他的臉。驚鴻一瞥,這才看到,一張憔悴的臉。歷盡滄桑的臉。目光泛淚的臉。
「平常都是她測我的血糖、量我的血壓,把我該吃什麼藥,整齊排列在藥盒子裡。」
「她生病的時候,換我很用心照顧她。不知道我到底做錯了什麼?她……」
「孩子們都長大離開了。我們有筆積蓄,正要購置新房,安度餘年,沒想到她……生病不到五個月就走了。」
「梳妝台上堆了一山的藥,我老是忘記吃。我哪有心情吃?這一切還有什麼意義?」
我看到一個極度疲憊、眼神呆滯的男人,雙手交疊放在膝上,坐在懸崖邊緣。
我感到驚慌失措,久久不能自已。
沉默半晌,我對他說:「阿公你不要自責,有些病,發現時就很嚴重。你一定要節哀。我猜,夫人在天上一定希望你好好照顧自己,乖乖吃藥。」
阿公哽咽的說:「我太太是很仔細的人。我該吃的藥有四組:起床吃的、飯後一小時吃的、空腹吃的、需要的時候吃的,她清清楚楚。」
「我建議您按照太太的方法,整理那堆藥,你就不會忘記吃了。」我說。
阿公點點頭說:「她在的時候,看到我乖乖的把藥吞下,才放心走開。」
吃藥的時候,感覺太太就在身邊。也算是紀念她的一種方式吧?
電子病歷有一種壞處,使你只看「數字」治療病人。
螢幕上看不出,坐在你前面這個病人,他的氣色如何,他過得好不好,他到底怎麼了。
一切都得要你關掉電腦,轉過頭來,看著他的眼睛,好好的聽,好好的問。
突襲
很久沒有孩子拿我的書來「突襲」我了。上星期六又來一次。
作為一個提倡「敘事醫學」的老師,我承認看診時花在孩子身上的時間太少。
我是指再挖掘「深入」一點;了解孩子做什麼、爸媽是怎樣的人?疾病帶給孩子的困擾?什麼是他們認為最重要的?
齊一公式的症狀列表容易陷入疲憊。只有問點別的,可以打破看診的沉悶和枯燥。
孩子進門那一剎那,我會給他一聲大大的招呼,去掉姓,直呼其名,試圖尋找共同點,問他住哪兒、學些什麼,給他一個真心的問候。
有時候病人說的一句話,像不知哪裡傳來的一陣花香,引發我繽紛的幻想,使我覺得,這輩子當醫師值了。
所以病童回診時,我會多問一句:「最近有沒有去哪裡玩?」
「回外婆家。」
「在附近公園走走。」
「去小人國六福村玩。」
「去澎湖。」
「去花蓮。」……
我順著線索一路問下去,像當場打開孩子送我的禮盒,裡頭有無限的驚喜。
直到有一位病童說:「哪兒也沒去,在家吃你的藥。而且一點也沒效。」
(是不是該拖出去……)
一位約五歲男童不時探頭進診間問我:「醫師,你欸賽看卡緊欸否?」(台語,意思是你可以看快一點嗎?)
終於輪到他。我問孩子:「我講台灣話,你聽有否?(我講台灣話,你聽得懂嗎?)」
他不作聲。
「恁叨有幾欸人?」(你家幾個人?)
他不作聲。
「你呷飽未?」我再問。
他回:「你呷飽太閒啦。」
媽媽連忙喝止。
他是阿嬤帶大的,啥米攏嘛會曉貢……
病人媽媽說孩子的爸學做紅豆餅(純興趣),看病送來一盒五個:抹茶、紅豆、起司、玉米、芋泥;要我試吃看看。
個個晶瑩飽滿,皮薄餡多。我拿回家,用烤箱烤五分鐘,端上桌,孩子們一掃而光。絕對到達開店水準。
老三說:「下次可不可以叫他多做一點紅豆的……」
醫師不只是開藥者、旁觀者,還會交到朋友、成為一樁美事的參與者……
醫病間詼諧的對話,讓人得到片刻喘息。雖然隱藏在所有笑容下的,是不折不扣的嚴酷人生。
診間永遠充滿不請自來的意外……
每個孩子背後都有一個世界,必須跳脫傳統醫病框架,和孩子一起探索,用微笑找回行醫的感動。
於是我寫了《我願與你同行》。
總是習慣聆聽病人在病歷之外的那些故事,掌握最真實的「病人敘事」。
以簡馭繁,三言兩語交代病況的電子病歷,令我覺得堅硬難以穿透,電腦就像我和病人之間的「第三者」。
我更喜歡那些堆滿檔案櫃,散發溫度的手寫病歷,我是個舊版醫生……
舊版醫師
查房時,我問住院醫師一個病人的實驗室數據,他拿出他的iPad,簽入,開始滑……
在他還沒查到之前,他驚訝地發現,我居然能不用查什麼,就說出四個病人三天前的血清鉀離子濃度……
對一九九○年後出生的這一代,「何處可以找到資料」比「資料是什麼」還重要。
他們認為,數秒內可以查到的事,為什麼要「知道」?我再也回不去那個可以電人而後快的尊師重道年代。
我發現自己是一隻恐龍,只是還沒完全絕跡而已。
過年前幾天,管理處給我一個Email,告訴我,我是全科唯一仍在用His2.0(舊版電腦)的主治醫師。
(我是個念舊的人。)
我曾經歷一段不算短的手寫病歷年代。自從有了電子病歷,電腦成為我和病人之間的「第三者」。
(我很氣它破壞我跟病人之間的好事。)
我越老越相信,了解一個病人,必須從病歷之外的角度,「面對面」熟悉他的職業、家人、嗜好……
我越來越喜歡,像「老朋友」一樣,告訴病人我自己的見解和興趣,聊聊彼此的生活,這樣,我就會得到的更多……
看到「報表」上敬陪末座的,我的「劣跡」。要是我年輕幾歲,一定打電話去抗議的。
這些年「電腦」所企圖阻擋我不成、我和病人間建立「深刻連結」所產生的喜悅,終究化解了我的衝動。
某天門診,一位建築設計師鉅細靡遺告訴我他一天的「生活日常」,我聽得入神。
他離去後,我對護理師說:「他說那麼多,應該要向我收錢的。」
她一面理解表示同意,一面微笑對我說:「林醫師你要看快一點,後面還很多人呢!」
病歷
「大腸桿菌泌尿道感染合併敗血症」,我的手機簡訊顯示。這就是這男孩在醫院的唯一辨識記號。堅硬而難以穿透,他已經不能多嘴。
醫學訊息要求以簡馭繁。三言兩語就把病人交代清楚,當然最好。「電子病歷」井然有序,或許可以勝任吧。
可是一旦戰線拉長,醫病的交鋒超過數週、甚至數月,電子病歷提供的訊息就不知所云了。它總結疾病還可以,但不足以捕捉病人的全貌。
病人過什麼樣的生活?我們要成為什麼樣的醫師?
我們的醫療照顧把病人變成什麼模樣?他的生活品質有提升嗎?疼痛減除否?
我們需要觀察在病房之外行動的病人,並且聽到他們講的話。我們需要一些「病人敘事」。
可惜電子病歷上看不到故事。它的功能是把每個疾病都編個代碼(Code),以便向健保局申報費用……
一個許久前看過診的小朋友長大要當兵了,回來找我要病歷。我從大學校本部倉庫借到,應該是所剩無幾的手寫病歷了,在我還是住院醫師的那個年代。
我一頁頁小心翻動,這斑駁而滄桑的回憶,深怕它破碎。
他的童年風雨飄搖,還住過幾次加護病房。我看到好友二十幾年前當實習醫師時在急診的筆跡,那麼果斷,那麼殷切,像現在一樣。
我也看到當時醫學系四年級生寫的progress note,端正而拘謹,現在是某科的當紅炸子雞;我更看到寫過這本病歷的醫師與護士,有的退休,有的逝世,有的則成了另一部病歷上的主角,正在生死線上掙扎。
最後我看到我自己的文字,上頭記錄著現在早已遺忘,但曾確確實實參與病人生命的那一小段旅程。
多寫幾個字,總是好的。
昨天門診來了一位我在二○○一年診斷的「低免疫球蛋白血症」病患,那時她才六歲。
她的身體無法自行製造免疫球蛋白。李醫師和我已經追蹤治療她近二十個年頭。方法就是按月注射IVIG。(註)
正處荳蔻年華的她,從事醫療器材相關行業。生活與常人無異,只是還得每個月向醫院報到。
記得診斷之初,我向她爸爸說,別灰心,基因醫學的研究終會找出根治的方法,有一天她將不必再依賴藥物。
但仍不免擔心,這孩子有未來嗎?她能活到我退休那一天嗎?
二十年過去了。這病根治的希望依然像「隧道盡頭的微光」,治療的方式還是和二十年前一樣。但孩子勇敢茁壯,李醫師和我的頭已灰白。
我們照顧她,曾經混亂、曾經遲疑、曾經恐慌,且情況勢必仍會持續。
她的故事並非全然關乎科學,我們更從她身上學到了無價的人生課程。
那是面對人生無法改變的逆境時,人的決心和勇氣。
拉下病歷捲軸(現在已經不能用翻的),仔細審思。病人教我們,面對自己人生劇變時,保持樂觀,欣然接受挑戰。
註:IVIG,靜脈注射免疫球蛋白。
病歷背後的人
病人明天要做「心導管」,我必須確定病人所有「過去病史」都已經「問好問滿」。
我先看了一下病歷,一個四十五中年男性,糖尿病、肥胖、高血壓、高血脂症,加上痛風……
「他不得心臟病才怪……」我在心裡嘀咕。
他是再「典型」不過的病人,即使對我這個實習醫師來說。他的病歷還真的有點厚。他曾經走到末期腎病,接受透析四年,後來幸運接受「腎臟移植」……
裡面有許多我看不懂的「術式」和「移植藥物」。總之,他最近心臟功能有點下降。
雖然心裡有個底,我還是得進去病房問一問。
我(自認)很親切的自我介紹並打招呼,可是病人看起來十分遙遠而焦慮。病史詢問時,他顯得不耐煩,甚至有一點惱怒。
我問他:「了不了解明天要做的手術?」他竟然大聲咆哮。
「你最好別傷到我的腎臟!」
我向他詳細解釋手術的流程,包括會用到一些含碘的顯影劑,他又再次打斷我。
「如果會傷我的腎臟,不如就把我殺了。」
病人如此絕決的宣示,使我懷疑,他是不是患了「憂鬱症」,正不知如何回話時,他又說:「你大概不知道我做血液透析那四年,日子是怎麼過的。我被迫換工作,家人朋友遺棄我,直到我接受腎臟移植,生活才回歸正途……」
我還是很盡職的說明手術可能的「風險」。
他搖搖頭,挑釁的說:「我不能接受任何風險。我寧可死,也不能再讓我的腎臟壞掉……」至此,我已經完全確定我無法完成他的「術前表格」了。
這是我接過第一個病人如此清楚表達:腎臟疾病對他造成的,深刻的身體創傷和心理波折。他的哀傷跟憂慮「信而有徵」。那些待填的「表格」聽起來如此敷衍,顯然無法化解他對「風險」的疑慮。
我有深深的罪惡感,覺得自己不該以「病歷」取人,只給他一些輕率而制式的回應。不要因為病人住了院、穿著「病袍」,就把他看成是某種「病」。別忘了,他也是一個「人」。而「人」,有時遠比你看病歷所能想像的,複雜而難解。
電子病歷一位阿公帶著孫子來看病。他們是「常客」,孫子有氣喘,規律回來拿藥。我跟阿公也熟了起來。
看完孫子,阿公問我,可不可以幫他掛號,他說他最近不太舒服,也想給我看看。
他有高血壓和糖尿病,本來在內分泌科定期追蹤。最近因太常爽約,掛不回原來的主治醫師。
我說好。阿公遞給我健保卡,我在電腦上操作。我心想,頂多按照原來的藥開給他。
電子病歷有一種好處,看不出病歷有多厚。
阿公上次抽血報告,HbA1C(上個月的平均血糖值)8.2,超標。他的血壓,170/110,也偏高。
「阿公,你的血糖和血壓都不及格。是不是沒吃藥?這樣不行喔。」
阿公說:「對不起,醫師,我是一個很壞的病人。最近我老伴走了,走得太突然了。」
我把目光從電腦螢幕移到他的臉。驚鴻一瞥,這才看到,一張憔悴的臉。歷盡滄桑的臉。目光泛淚的臉。
「平常都是她測我的血糖、量我的血壓,把我該吃什麼藥,整齊排列在藥盒子裡。」
「她生病的時候,換我很用心照顧她。不知道我到底做錯了什麼?她……」
「孩子們都長大離開了。我們有筆積蓄,正要購置新房,安度餘年,沒想到她……生病不到五個月就走了。」
「梳妝台上堆了一山的藥,我老是忘記吃。我哪有心情吃?這一切還有什麼意義?」
我看到一個極度疲憊、眼神呆滯的男人,雙手交疊放在膝上,坐在懸崖邊緣。
我感到驚慌失措,久久不能自已。
沉默半晌,我對他說:「阿公你不要自責,有些病,發現時就很嚴重。你一定要節哀。我猜,夫人在天上一定希望你好好照顧自己,乖乖吃藥。」
阿公哽咽的說:「我太太是很仔細的人。我該吃的藥有四組:起床吃的、飯後一小時吃的、空腹吃的、需要的時候吃的,她清清楚楚。」
「我建議您按照太太的方法,整理那堆藥,你就不會忘記吃了。」我說。
阿公點點頭說:「她在的時候,看到我乖乖的把藥吞下,才放心走開。」
吃藥的時候,感覺太太就在身邊。也算是紀念她的一種方式吧?
電子病歷有一種壞處,使你只看「數字」治療病人。
螢幕上看不出,坐在你前面這個病人,他的氣色如何,他過得好不好,他到底怎麼了。
一切都得要你關掉電腦,轉過頭來,看著他的眼睛,好好的聽,好好的問。
突襲
很久沒有孩子拿我的書來「突襲」我了。上星期六又來一次。
作為一個提倡「敘事醫學」的老師,我承認看診時花在孩子身上的時間太少。
我是指再挖掘「深入」一點;了解孩子做什麼、爸媽是怎樣的人?疾病帶給孩子的困擾?什麼是他們認為最重要的?
齊一公式的症狀列表容易陷入疲憊。只有問點別的,可以打破看診的沉悶和枯燥。
孩子進門那一剎那,我會給他一聲大大的招呼,去掉姓,直呼其名,試圖尋找共同點,問他住哪兒、學些什麼,給他一個真心的問候。
有時候病人說的一句話,像不知哪裡傳來的一陣花香,引發我繽紛的幻想,使我覺得,這輩子當醫師值了。
所以病童回診時,我會多問一句:「最近有沒有去哪裡玩?」
「回外婆家。」
「在附近公園走走。」
「去小人國六福村玩。」
「去澎湖。」
「去花蓮。」……
我順著線索一路問下去,像當場打開孩子送我的禮盒,裡頭有無限的驚喜。
直到有一位病童說:「哪兒也沒去,在家吃你的藥。而且一點也沒效。」
(是不是該拖出去……)
一位約五歲男童不時探頭進診間問我:「醫師,你欸賽看卡緊欸否?」(台語,意思是你可以看快一點嗎?)
終於輪到他。我問孩子:「我講台灣話,你聽有否?(我講台灣話,你聽得懂嗎?)」
他不作聲。
「恁叨有幾欸人?」(你家幾個人?)
他不作聲。
「你呷飽未?」我再問。
他回:「你呷飽太閒啦。」
媽媽連忙喝止。
他是阿嬤帶大的,啥米攏嘛會曉貢……
病人媽媽說孩子的爸學做紅豆餅(純興趣),看病送來一盒五個:抹茶、紅豆、起司、玉米、芋泥;要我試吃看看。
個個晶瑩飽滿,皮薄餡多。我拿回家,用烤箱烤五分鐘,端上桌,孩子們一掃而光。絕對到達開店水準。
老三說:「下次可不可以叫他多做一點紅豆的……」
醫師不只是開藥者、旁觀者,還會交到朋友、成為一樁美事的參與者……
醫病間詼諧的對話,讓人得到片刻喘息。雖然隱藏在所有笑容下的,是不折不扣的嚴酷人生。
診間永遠充滿不請自來的意外……
每個孩子背後都有一個世界,必須跳脫傳統醫病框架,和孩子一起探索,用微笑找回行醫的感動。
於是我寫了《我願與你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