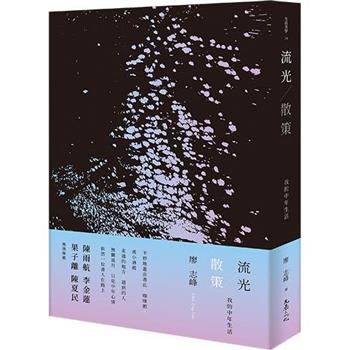1.夜間書店
我們如今還是以書街記憶著重慶南路一段,短短的一段路,許多書店早已撤守,被遺棄的陣地,開始賣起咖啡,炸雞,麵包和彩券。書街最後的句點,就落在衡陽路和重慶南路交會的轉角口,金石堂書店,再往下走,就是有一陣子經常被拒馬圍繞的總統府。
在所有的金石堂書店中,這是我最常路過的一家,也可以說是最喜歡的一家,因為它所在的街區,因為它獨特的建築體,書店連結起時代的記憶,讓人經過時都可以感覺到一種時代的文本在上空交錯盤繞,這種記憶的氣味在高樓大廈群集的城市裡是顯現不出來的;它就像是冬夜餘燼的殘溫,只有貼近時才感受得到,也微具著一種堡壘意象,尤其是當你就站在街角望著時,白色的書店聳立在黑夜的長街中,是唯一的光亮。
綠燈亮的時候,有片刻的錯覺,好像所有人都朝著書店走去,像是趕赴一場約會,但人一下子又從左右兩側的騎樓散去,瞬間無影無蹤。美麗的誤會。夜晚的沉靜事實上是最適合逛書店的,白天的工作告一段落,到書店翻翻書,轉換個心情,喘口氣,再回家,最好離去時還帶著一本書。但這只是我的隨想,很少發生。從書店窗口透出的明亮光影,你可以察覺得出,並沒有多少人在書店裡。室內明亮的燈光一無阻隔地灑落街道,被燈光暈染和街燈投設照明的書店,竟異樣地顯露出一種教堂般的莊嚴。街角的聖殿。在城市的一角,有一間燈火通明的書店是一種幸福,一種讓人可以在書店隨意翻閱著書,被書包圍的幸福,但對書店店員來說,他可能會為這樣的冷清煩惱,為沒有讀者前來向書告解而犯愁;而對整理退書的出版社倉管人員來說,被書包圍從來就不是一種幸福,而是殘酷。冷酷異境。
我站在街角望著這白色書店時,有一種看電影般的不真實感,也像看著一種三D風景。街道在沒有汽機車通行時,異常地安靜冷清,每個人都只是路過,我明明應該覺得感傷,又覺得好像毫不相干,原來我也只是個偶然的旅人。
44.沙漠人生
多年前,先後從幾個中國作家口中聽到高爾泰先生的名字,他們異口同聲地說:年輕時讀高爾泰先生的文章,深受啟發。在《尋找家園》出版之前,曾透過曹長青先生聯繫這部回憶錄出版的可能,但我說得太晚。
李劼曾經造訪住在沙漠的高先生,我很好奇,一位中國當代美學大師和文化思想學者,怎麼適應異域的沙漠生活?後來,我才知道,他早習於沙漠,在中國的日子,歷經人世粗厲如荒漠般的洗禮,沙漠已內化,怡然安頓,他說:我這輩子,和沙漠有緣。青年夾邊溝,中年敦煌,老年內華達。
他對沙漠別有寄懷,在舉世文人中,也是罕見:變化不可逆轉,唯有沙漠無恙。有時面對海外的沙漠,恍若身在海內從前。似乎兒時門巷,就在這太古洪荒後面,綠蕪庭院,細雨濕蒼苔。收入《草色連雲》中的文字,大都是在這裏寫的。斷續零星,雜七雜八。帶著鄉愁,帶著擰巴,一肚子不合時宜。就像沙漠植物,稀疏憔悴渺小,賴在連天砂石中綠著。綠是普世草色,因起連雲之想。
我很久沒讀到如此簡潔優雅,又饒富情味的文字,反覆咀嚼,愛不能捨。散文之為文體,易寫難工,而高爾泰的文字,悠然,飄然,如天外驚鴻。和高先生聯繫上是意外,也不全是意外,畢竟他和我的許多作者都有交集。年初,來自中國的徐曉老師到台北開會,有一天她和尉天驄、錢永祥兩位老師小聚,突然提到想找我,然後錢老師就撥了電話來,接起電話的我,滿心驚疑,不知發生何事,徐老師說:高爾泰先生想找你。
這樣,我接到了《草色連雲》的書稿,高先生對這本正體版的出版,寄望很高︰ 我還沒看到中國的《草色連雲》簡體本,據說已經出版,但是被刪改了很多,十分遺憾。特別希望在正體版中補救損失,包括在簡體版中被刪去的兩篇散文〈老莫〉 和〈大江東去〉……。和高先生的通信,在五月間戛然而止,更離奇的是,信箱中所有和高先生往返的通信,一封不存,其中包括他傳來的書法題字,我花了一個下午找信,百思不解。奇怪的是,同一時間和其他作者的通信都仍在信箱中,我後來想,這個信箱被監控了嗎?誰的手伸進了我的電子信箱?
我後來又從另一個信箱寫信給高先生,告訴他這個離奇荒謬的悲劇,先向他請罪,並請他再把編輯的修正意見告訴我一次,他後來寄來了用毛筆寫的親筆函。如果說,信箱中的信件消失是意外,這封親筆函的寄來,則屬意外中的驚喜了,感謝老大哥。
和高先生的通信,除了書稿的細節討論,有時也可以讀到他對文學作品的看法,如我其他的作者所說,深受啟發。有一回,他談起了韓秀的《長日將盡》。
他說︰剛讀完《長日將盡》,很受震撼。作者閱歷豐富,觀察敏銳,文字蘊藉洗練。且有獨特的風格,京味兒十足。那個特定歷史社會條件下各色人等,從高官名流、才子佳人,到盲流白丁街頭混混的表現,寥寥數語活靈活現。包括隱藏在這表現後面的複雜心態和生存努力,都歷歷在目。批判中含著同情,女性的溫婉中透著陽剛之氣,一瀉千里,至為難得!
高爾泰的文字在極簡的白話中有濃濃的古典情懷,在現實的擾人纏繞中,還有著過去的溫暖成為暗黑世途依稀的指引。我很久沒有讀到這樣的散文,一篇一篇地讀,忍不住就要手舞足蹈起來,他的文字是那麼地暗藏著音律,敲動你的心弦,讓你忍不住移情,忍不住潸然,但是絕不矯情。
「加加減減滋味,我未老已經深諳:已省名山無我份,八十行吟跡近癡」,這樣的一種與世不容的癡,我在康正果,李劼身上見過,如今在高爾泰身上又見到。總是讓我肅然。世俗的名聲終究要伏應世俗的方式取得,他們之不遇,實是必然。高爾泰說他至今還學不會平仄,無法寫出一首合格律的古典詩,我卻想,我大學時平仄聲調極熟,交作業的詩,有如機器樣模,充滿套路,終究難有性情。性情最難。
高爾泰應美國國會圖書館演講的那篇文章十分精采,充分顯示他的文學觀和審美趣味,尤其在評斷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部份更是明揭:莫言的問題在於,他沒說什麼?為什麼沒說。這種說與不說的閃躲,已存有價值取向在其中。人焉廋哉?某種程度來說,文如其人是對的。但編輯檯上多年,我採分離主義,有時作品是好的,但做為人的部份,天知地知。
有時你會不期然遇到一個人,你發覺為他花力氣編書是值得的。五十歲時給自己的座右銘是︰俯首甘為孺子牛——為值得的人和值得的書。
90.夜遊
上次和任之一起經過這區,大約是一年前,和簡白、任之在錦西街上的米粉伯攤子上吃完米粉,喝點小酒後,漫步走過。我帶著任之遊走我童年時的街區,正走過的這個街區,那時是不存在的,完全是屬於北淡線的鐵道範圍,被柵欄封住,童年也早不存在,僅以記憶的方式存在於這個街區的空氣中。這是無法抵擋的力量,驅動著你信步至此。我們在赤峰街,舊鐵道區,和中山北路的巷弄中,穿來穿去,同時找賣水的便利商店,像神遊物外的狀態,在赤峰街的一棟老屋前,看著二樓陽台上雕花銹蝕的鑄鐵欄杆,我對任之說,我第一次讀到蒙迪安諾的時候,十分喜歡,因為他的敘述完全撞擊到我這種在街道漫遊的心理狀態,當然蒙迪安諾的小說中還帶著戰後濃重的陰鬱氣味,我並不十分熟悉。
任之突然想起我對他提起過的,隱藏在巷弄間的居酒屋,他對夾雜在巷弄公寓裡,那間居酒屋的木製拉門印象深刻,想去看一下。走近時,居酒屋不在了,變成了明亮的服飾店。這間居酒屋曾和玉山社魏淑貞總編輯來過,我因為滿牆貼著線裝書頁大為驚詫,而寫了一篇文章,不知何時,店已撤離,真可惜。我探頭進店中一望,牆上貼著的書頁仍在,提醒著曾在的痕跡,我曾為這些書頁惋惜,惋惜他們成為裝飾的壁紙。我現在又再一次為它們惋惜,惋惜他們的存在——雖然,我不應該這麼說——事實上還是適合居酒屋的。
不論人事,一年的變化很大,也有不變的,像居酒屋斜對角的咖啡館。咖啡館的主人還是那個留著小鬍子的青年男子,像個藝術工作者安安靜靜地站在櫃檯後面調製咖啡,一如咖啡館安安靜靜地佇立巷角。我問店主要張店卡,因為任之想知道這店的確實地址和名稱,他說,他沒有印店卡。一如以往。他不特別熱絡,也不特別冷淡,就像是溫開水的溫度。我很高興這迷人的咖啡館仍在這裡。
我對任之說,我喜歡這區,這區是我的巴黎。那裡,雨後總是一片寧靜,蒙迪安諾這麼說。
127.冬日風景
到印刷廠的這條路應該很熟悉,卻也陌生,只要錯過一個路標或一個路口,你就找不到通往印刷廠的路徑。迷宮般的巷弄,像橫生的枝枒,在中和區的地域上任意歧出。我過去常從中正橋邊的河堤道路前往印刷廠,幾乎沒有紅綠燈,十分通暢,我倚賴的座標是一座鐵皮屋工廠,從工廠旁的路口切進去,很快就可抵達印刷廠,不會塞在中山路或橋和路上。後來鐵皮屋廠房賣給建設公司,蓋起成群的高樓豪宅,形成突兀的景觀,高樓與工廠群,錯置的繁華與蒼茫,我再也找不到那條熟悉的路。
這次從捷運站過來,出了景安站卻不知怎麼搭公車到印刷廠,於是搭計程車。運匠問︰你剛剛不是要搭公車嗎?我說︰是啊!但不知搭哪一路。幾乎一路塞到印刷廠,與景氣無關,車流就是多,現在的人在道路上奔波的時間要更長才能換來生活所需嗎?我們閒聊了一陣,運匠嘆口氣說︰這種日子要怎麼過啊。我只好說:加油。加油也是對自己說的。
接了一批卡片的設計印製,委託者不滿意印出的結果,只好重印,我沒想到我會為了一千張的卡片到印刷廠看印。重印也意味著我把新台幣灑向淡水河餵魚蝦了,意外的是印刷廠的冷清。我進到印刷廠時,機器正在換版,為將到來的客戶準備著,過去那種轟隆隆如火車行駛的振動沒有了,也沒聞到空氣中濃重的油墨味。印刷廠的老闆,廠長,工務,全圍過來與我熱烈寒暄著,我受寵若驚,從沒有接受過這種禮遇,但這種禮遇又讓我有些難受。我不是說他們的勢利,而是他們以前時間的短缺,沒辦法友善地招呼。看見他們的白髮和蒼老,其實也想像著自己,他們就是你。只有一千張卡片,不好意思,我對老闆抱歉沒有更大的案子。
離開印刷廠時,送我的是廠裡製版的師傅,我從沒見過他。我問他:在這裡服務多久了?二十年。二十年?我竟沒見過你?製版都在裡間,所以你見不到。時代果真不一樣了,電腦可以拼版,不需要製版師傅。師傅說︰到了週末,這裡就像鬼城,連小吃店的生意也受影響。閒聊中又錯過一個路口,迷宮般的中和。我對他說︰你送我過華中橋吧,過了橋,我就可以找到我要搭的公車了。
十足冬日的陰雨,和心情。我想起桑貝畫中孤獨的自行車手,加油,加油。
我們如今還是以書街記憶著重慶南路一段,短短的一段路,許多書店早已撤守,被遺棄的陣地,開始賣起咖啡,炸雞,麵包和彩券。書街最後的句點,就落在衡陽路和重慶南路交會的轉角口,金石堂書店,再往下走,就是有一陣子經常被拒馬圍繞的總統府。
在所有的金石堂書店中,這是我最常路過的一家,也可以說是最喜歡的一家,因為它所在的街區,因為它獨特的建築體,書店連結起時代的記憶,讓人經過時都可以感覺到一種時代的文本在上空交錯盤繞,這種記憶的氣味在高樓大廈群集的城市裡是顯現不出來的;它就像是冬夜餘燼的殘溫,只有貼近時才感受得到,也微具著一種堡壘意象,尤其是當你就站在街角望著時,白色的書店聳立在黑夜的長街中,是唯一的光亮。
綠燈亮的時候,有片刻的錯覺,好像所有人都朝著書店走去,像是趕赴一場約會,但人一下子又從左右兩側的騎樓散去,瞬間無影無蹤。美麗的誤會。夜晚的沉靜事實上是最適合逛書店的,白天的工作告一段落,到書店翻翻書,轉換個心情,喘口氣,再回家,最好離去時還帶著一本書。但這只是我的隨想,很少發生。從書店窗口透出的明亮光影,你可以察覺得出,並沒有多少人在書店裡。室內明亮的燈光一無阻隔地灑落街道,被燈光暈染和街燈投設照明的書店,竟異樣地顯露出一種教堂般的莊嚴。街角的聖殿。在城市的一角,有一間燈火通明的書店是一種幸福,一種讓人可以在書店隨意翻閱著書,被書包圍的幸福,但對書店店員來說,他可能會為這樣的冷清煩惱,為沒有讀者前來向書告解而犯愁;而對整理退書的出版社倉管人員來說,被書包圍從來就不是一種幸福,而是殘酷。冷酷異境。
我站在街角望著這白色書店時,有一種看電影般的不真實感,也像看著一種三D風景。街道在沒有汽機車通行時,異常地安靜冷清,每個人都只是路過,我明明應該覺得感傷,又覺得好像毫不相干,原來我也只是個偶然的旅人。
44.沙漠人生
多年前,先後從幾個中國作家口中聽到高爾泰先生的名字,他們異口同聲地說:年輕時讀高爾泰先生的文章,深受啟發。在《尋找家園》出版之前,曾透過曹長青先生聯繫這部回憶錄出版的可能,但我說得太晚。
李劼曾經造訪住在沙漠的高先生,我很好奇,一位中國當代美學大師和文化思想學者,怎麼適應異域的沙漠生活?後來,我才知道,他早習於沙漠,在中國的日子,歷經人世粗厲如荒漠般的洗禮,沙漠已內化,怡然安頓,他說:我這輩子,和沙漠有緣。青年夾邊溝,中年敦煌,老年內華達。
他對沙漠別有寄懷,在舉世文人中,也是罕見:變化不可逆轉,唯有沙漠無恙。有時面對海外的沙漠,恍若身在海內從前。似乎兒時門巷,就在這太古洪荒後面,綠蕪庭院,細雨濕蒼苔。收入《草色連雲》中的文字,大都是在這裏寫的。斷續零星,雜七雜八。帶著鄉愁,帶著擰巴,一肚子不合時宜。就像沙漠植物,稀疏憔悴渺小,賴在連天砂石中綠著。綠是普世草色,因起連雲之想。
我很久沒讀到如此簡潔優雅,又饒富情味的文字,反覆咀嚼,愛不能捨。散文之為文體,易寫難工,而高爾泰的文字,悠然,飄然,如天外驚鴻。和高先生聯繫上是意外,也不全是意外,畢竟他和我的許多作者都有交集。年初,來自中國的徐曉老師到台北開會,有一天她和尉天驄、錢永祥兩位老師小聚,突然提到想找我,然後錢老師就撥了電話來,接起電話的我,滿心驚疑,不知發生何事,徐老師說:高爾泰先生想找你。
這樣,我接到了《草色連雲》的書稿,高先生對這本正體版的出版,寄望很高︰ 我還沒看到中國的《草色連雲》簡體本,據說已經出版,但是被刪改了很多,十分遺憾。特別希望在正體版中補救損失,包括在簡體版中被刪去的兩篇散文〈老莫〉 和〈大江東去〉……。和高先生的通信,在五月間戛然而止,更離奇的是,信箱中所有和高先生往返的通信,一封不存,其中包括他傳來的書法題字,我花了一個下午找信,百思不解。奇怪的是,同一時間和其他作者的通信都仍在信箱中,我後來想,這個信箱被監控了嗎?誰的手伸進了我的電子信箱?
我後來又從另一個信箱寫信給高先生,告訴他這個離奇荒謬的悲劇,先向他請罪,並請他再把編輯的修正意見告訴我一次,他後來寄來了用毛筆寫的親筆函。如果說,信箱中的信件消失是意外,這封親筆函的寄來,則屬意外中的驚喜了,感謝老大哥。
和高先生的通信,除了書稿的細節討論,有時也可以讀到他對文學作品的看法,如我其他的作者所說,深受啟發。有一回,他談起了韓秀的《長日將盡》。
他說︰剛讀完《長日將盡》,很受震撼。作者閱歷豐富,觀察敏銳,文字蘊藉洗練。且有獨特的風格,京味兒十足。那個特定歷史社會條件下各色人等,從高官名流、才子佳人,到盲流白丁街頭混混的表現,寥寥數語活靈活現。包括隱藏在這表現後面的複雜心態和生存努力,都歷歷在目。批判中含著同情,女性的溫婉中透著陽剛之氣,一瀉千里,至為難得!
高爾泰的文字在極簡的白話中有濃濃的古典情懷,在現實的擾人纏繞中,還有著過去的溫暖成為暗黑世途依稀的指引。我很久沒有讀到這樣的散文,一篇一篇地讀,忍不住就要手舞足蹈起來,他的文字是那麼地暗藏著音律,敲動你的心弦,讓你忍不住移情,忍不住潸然,但是絕不矯情。
「加加減減滋味,我未老已經深諳:已省名山無我份,八十行吟跡近癡」,這樣的一種與世不容的癡,我在康正果,李劼身上見過,如今在高爾泰身上又見到。總是讓我肅然。世俗的名聲終究要伏應世俗的方式取得,他們之不遇,實是必然。高爾泰說他至今還學不會平仄,無法寫出一首合格律的古典詩,我卻想,我大學時平仄聲調極熟,交作業的詩,有如機器樣模,充滿套路,終究難有性情。性情最難。
高爾泰應美國國會圖書館演講的那篇文章十分精采,充分顯示他的文學觀和審美趣味,尤其在評斷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部份更是明揭:莫言的問題在於,他沒說什麼?為什麼沒說。這種說與不說的閃躲,已存有價值取向在其中。人焉廋哉?某種程度來說,文如其人是對的。但編輯檯上多年,我採分離主義,有時作品是好的,但做為人的部份,天知地知。
有時你會不期然遇到一個人,你發覺為他花力氣編書是值得的。五十歲時給自己的座右銘是︰俯首甘為孺子牛——為值得的人和值得的書。
90.夜遊
上次和任之一起經過這區,大約是一年前,和簡白、任之在錦西街上的米粉伯攤子上吃完米粉,喝點小酒後,漫步走過。我帶著任之遊走我童年時的街區,正走過的這個街區,那時是不存在的,完全是屬於北淡線的鐵道範圍,被柵欄封住,童年也早不存在,僅以記憶的方式存在於這個街區的空氣中。這是無法抵擋的力量,驅動著你信步至此。我們在赤峰街,舊鐵道區,和中山北路的巷弄中,穿來穿去,同時找賣水的便利商店,像神遊物外的狀態,在赤峰街的一棟老屋前,看著二樓陽台上雕花銹蝕的鑄鐵欄杆,我對任之說,我第一次讀到蒙迪安諾的時候,十分喜歡,因為他的敘述完全撞擊到我這種在街道漫遊的心理狀態,當然蒙迪安諾的小說中還帶著戰後濃重的陰鬱氣味,我並不十分熟悉。
任之突然想起我對他提起過的,隱藏在巷弄間的居酒屋,他對夾雜在巷弄公寓裡,那間居酒屋的木製拉門印象深刻,想去看一下。走近時,居酒屋不在了,變成了明亮的服飾店。這間居酒屋曾和玉山社魏淑貞總編輯來過,我因為滿牆貼著線裝書頁大為驚詫,而寫了一篇文章,不知何時,店已撤離,真可惜。我探頭進店中一望,牆上貼著的書頁仍在,提醒著曾在的痕跡,我曾為這些書頁惋惜,惋惜他們成為裝飾的壁紙。我現在又再一次為它們惋惜,惋惜他們的存在——雖然,我不應該這麼說——事實上還是適合居酒屋的。
不論人事,一年的變化很大,也有不變的,像居酒屋斜對角的咖啡館。咖啡館的主人還是那個留著小鬍子的青年男子,像個藝術工作者安安靜靜地站在櫃檯後面調製咖啡,一如咖啡館安安靜靜地佇立巷角。我問店主要張店卡,因為任之想知道這店的確實地址和名稱,他說,他沒有印店卡。一如以往。他不特別熱絡,也不特別冷淡,就像是溫開水的溫度。我很高興這迷人的咖啡館仍在這裡。
我對任之說,我喜歡這區,這區是我的巴黎。那裡,雨後總是一片寧靜,蒙迪安諾這麼說。
127.冬日風景
到印刷廠的這條路應該很熟悉,卻也陌生,只要錯過一個路標或一個路口,你就找不到通往印刷廠的路徑。迷宮般的巷弄,像橫生的枝枒,在中和區的地域上任意歧出。我過去常從中正橋邊的河堤道路前往印刷廠,幾乎沒有紅綠燈,十分通暢,我倚賴的座標是一座鐵皮屋工廠,從工廠旁的路口切進去,很快就可抵達印刷廠,不會塞在中山路或橋和路上。後來鐵皮屋廠房賣給建設公司,蓋起成群的高樓豪宅,形成突兀的景觀,高樓與工廠群,錯置的繁華與蒼茫,我再也找不到那條熟悉的路。
這次從捷運站過來,出了景安站卻不知怎麼搭公車到印刷廠,於是搭計程車。運匠問︰你剛剛不是要搭公車嗎?我說︰是啊!但不知搭哪一路。幾乎一路塞到印刷廠,與景氣無關,車流就是多,現在的人在道路上奔波的時間要更長才能換來生活所需嗎?我們閒聊了一陣,運匠嘆口氣說︰這種日子要怎麼過啊。我只好說:加油。加油也是對自己說的。
接了一批卡片的設計印製,委託者不滿意印出的結果,只好重印,我沒想到我會為了一千張的卡片到印刷廠看印。重印也意味著我把新台幣灑向淡水河餵魚蝦了,意外的是印刷廠的冷清。我進到印刷廠時,機器正在換版,為將到來的客戶準備著,過去那種轟隆隆如火車行駛的振動沒有了,也沒聞到空氣中濃重的油墨味。印刷廠的老闆,廠長,工務,全圍過來與我熱烈寒暄著,我受寵若驚,從沒有接受過這種禮遇,但這種禮遇又讓我有些難受。我不是說他們的勢利,而是他們以前時間的短缺,沒辦法友善地招呼。看見他們的白髮和蒼老,其實也想像著自己,他們就是你。只有一千張卡片,不好意思,我對老闆抱歉沒有更大的案子。
離開印刷廠時,送我的是廠裡製版的師傅,我從沒見過他。我問他:在這裡服務多久了?二十年。二十年?我竟沒見過你?製版都在裡間,所以你見不到。時代果真不一樣了,電腦可以拼版,不需要製版師傅。師傅說︰到了週末,這裡就像鬼城,連小吃店的生意也受影響。閒聊中又錯過一個路口,迷宮般的中和。我對他說︰你送我過華中橋吧,過了橋,我就可以找到我要搭的公車了。
十足冬日的陰雨,和心情。我想起桑貝畫中孤獨的自行車手,加油,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