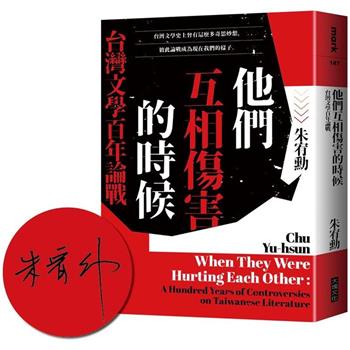一、開啟新時代的戰術,有時不太光彩:新舊文學論戰
本來是一個反派角色
如果要在一百年前的台灣文化界,找一個最被唾棄的「反派角色」,你會想到誰?在我的學生時代,我第一個想到的會是政治人物連戰的祖父、連勝文的曾祖父,台南出身的詩人連雅堂。那時候我對他沒什麼好印象,雖然知道他撰寫的《台灣通史》和編著的《台灣語典》是重要文獻,但相比於此,我更記得他某些討人厭的言行。若要在他身上蓋個「反派」的印章,我是不會猶豫的。
然而,現在我卻不是那麼篤定了。
連雅堂之所以常被視為台灣史上的反派角色,主要有兩個理由。第一是著名的「鴉片有益論」事件。日本殖民政府統治台灣期間,為了增添財政收入,明知鴉片對人民健康有害,但還是保有鴉片專賣制度。到了一九二九年,甚至大開政策倒車,頒布《改正阿片令》,放寬鴉片牌照的發放。這件事引起台灣各界的反彈,殖民政府長期以來指責台灣人有種種陋習,並且以此歧視台灣人。結果在台灣人自己正努力革除陋習的時候,怎麼日本人反過來鼓勵台灣人吸鴉片?
就在一片罵聲中,連雅堂站上了逆風的位置,發表了〈台灣阿片特許問題〉。這篇文章用許多極為扭曲的思路,來幫殖民政府的鴉片政策辯護。其中最神奇的論點,就是主張台灣自古以來多瘴厲之氣,勞工需要吸食鴉片才能存活,因此:「台灣人之吸食阿片,為勤勞也,非懶惰也;為進取也,非退守也!」由此論點出發,連雅堂甚至主張台灣之能夠開發繁榮,還應該感謝鴉片:「平心而論,我輩今日之得享受土地物產之利者,非我先民開墾之功乎?而我先民之得盡力開墾,前茅後勁,再接再厲,以造成今日之基礎者,非受阿片之效乎?」既然鴉片這麼好,那殖民政府多發牌照,自然也不是什麼糟糕的政策了。
此文一出,立刻轟動全台知識分子——當然是負面的轟動。連雅堂主要活動的圈子,是日治時期非常活躍的「漢詩」社群。所謂「漢詩」,就是現在我們所稱的古典詩,包含絕句、律詩、古詩等等。日治時期是台灣漢詩的黃金時代,光是目前可考的詩社數量就超過三百八十個。現在你把全台灣大大小小、不分小說新詩散文的文學社團通通加在一起,恐怕也沒有三百八十個。連雅堂在漢詩圈中頗富名望,甚至有「台灣三大詩人」的封號,並非等閒之輩。然而在他發表了〈台灣阿片特許問題〉之後,整個詩壇和文化界一致唾棄他。他被台中的重要詩社「櫟社」開除會籍,也被台北和台南的詩壇排斥。最終,連雅堂實在待不下去,只好黯然離台,遠赴中國。
第二個討厭他的理由,就跟本書主題大有關係了:在「新舊文學論戰」期間,連雅堂是站在「舊文學」一邊,反對「新文學」的陣營。所謂「新文學」和「舊文學」,我們可以先暫時想像成「白話文」和「文言文」(這個想法實際上有點不精準,我們在後面會陸續討論)兩大陣營。而「新舊文學論戰」,就是一批新銳作家要求打倒「舊」的文言文學,建立「新」的白話文學所引發的論戰。如前所述,連雅堂主要的文學修養是古典文學——他連幫殖民政府辯護都寫文言文——,會反對新生的、還沒那麼典雅的白話文學,是完全不奇怪的。
少時研究現代文學、熱愛現代文學的我,當然是完全不能接受他的立場。特別是在我閱讀了論戰期間,連雅堂作為舊文學陣營主將,與新文學陣營主將張我軍的論戰文章之後,我更是覺得這人不但趨炎附勢、道德水準低落,文學思想也十分落伍。要討厭他,是完全站得住腳的吧!
但現在的我,卻發現這裡面可能有點誤會。
「新舊文學論戰」的爆發
在說明誤會之前,我們先回到事情的起點,概略說明一下「新舊文學論戰」到底是怎麼發生的。然後,我們才能有足夠的線索,去理解其中複雜的文學糾葛。
在坊間通說裡,我們會認為「新舊文學論戰」爆發於一九二四年。不管你是研讀台灣文學史的研究生,還是只在通識課聽過一點台灣文學課程的人,都會聽到類似說法: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留學於北京的台灣人張我軍,因為有感於中國的「白話文運動」發展得如火如荼,決心將這道文學之火引入台灣。於是從一九二四年的〈糟糕的台灣文學界〉開始,到一九二五年的一年左右,張我軍至少就在《台灣民報》上發表了九篇文章,大聲疾呼要打倒腐敗的舊文學、建立有益於社會改革的新文學。
說張我軍發表了九篇文章,你可能沒什麼感覺,但我們還得考慮以下兩件事:其一,《台灣民報》是當時民間最重要的報刊,號稱「台灣人唯一的言論機構」,因此在上面連續發表文章是非同小可的。其二,一九二四年的《台灣民報》還是「旬刊」,直到一九二五年改為「週刊」,分別是十天一刊、七天一刊。再加上張我軍的論述氣勢磅礡,一篇文章常常要分好幾天連載,因此如果你實際去翻閱舊報紙,你會有一種幾乎每一期都有張我軍、他根本一直洗版的感覺。
張我軍的文章不只數量多,內容也火力強大,毫無疑問是台灣新文學的第一位戰神。他的鋒銳風格,從標題便可略見一二,比如〈糟糕的台灣文學界〉、〈為台灣的文學界一哭〉、〈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欉中的破舊殿堂〉、〈絕無僅有的擊缽吟的意義〉⋯⋯都是直接點名整個文學界來挑戰的。當時「新文學」還沒崛起,被點名的當然就是盤據文壇主流的「舊文學」了。一般認為,論戰是從〈糟糕的台灣文學界〉開始的。在這篇文章裡,他對全體古典文人開了地圖砲:
這幾年台灣的文學界要算是熱鬧極了!差不多是有史以來的盛況。試看各地詩會之多,詩翁、詩伯也到處皆是,一般人對於文學也興致勃勃。這實在是可羨、可喜的現象。那末我們也能從此看出許多的好作品,而且乘此時機,弄出幾個天才來為我們的文學界爭光,也是應該的。如此纔不負這種盛況,方不負我們的期望,而暗淡的文學史也許能藉此留下一點光明。然而創詩會的儘管創,做詩的儘管做,一般人之於文學儘管有興味,而不但沒有產出差強人意的作品,甚至造出一種臭不可聞的惡空氣來,把一班文士的臉丟盡無遺,甚至埋沒了許多有為的天才,陷害了不少活活潑潑的青年,我們於是禁不住要出來叫嚷一聲了。
這段頗有時代風味的白話文戰文,若要很簡化地摘要其主張,其實就一句話:「你們在座的古典文人,通通都是垃圾。」
都罵到這個份上了,古典文人焉有忍氣吞聲之理?其實,古典文人多半是地主仕紳出身,並不依靠文學維生,寫作純粹是一種文化教養與傳統的生活方式。大多數報刊也都掌握在古典文人手上,發表版面十分暢通。因此,面對來勢洶洶的張我軍和其他主張新文學的後生小輩,古典文人的基本態度是「冷處理」——幹嘛跟你戰呢?你罵半天也不能改變什麼呀,我們有錢有勢,根本不會被幾篇戰文動搖地位。說是這樣說,人心畢竟是肉做的,就算理智上知道不必回應,還是會有人沉不住氣。於是,沉不住氣的連雅堂參戰了,他在〈台灣詠史.跋〉寫了這樣一段文字:
今之學子。口未讀六藝之書。目未接百家之論。耳未聆離騷樂府之音。而囂囂然曰。漢文可廢。漢文可廢。甚而提倡新文學。鼓吹新體詩。秕糠故籍。自命時髦。吾不知其所謂新者何在?其所謂新者,特西人小說戲劇之餘,丐其一滴沾沾自喜,是誠坎阱之蛙,不足以語汪洋之海也。
以文言文的標準來說,這段可以說是回得很酸了。特別是「丐其一滴沾沾自喜」這句,頗有點打蛇在七寸的味道:張我軍等「新文學」支持者,其主要的理論和模仿對象,確實都以西方世界為根源。然而,這些人是不是真的很懂西方文學?在創作上,是否又真能掌握西方文學的精髓?這都是不無疑問的。對此,張我軍顯然沒有想要在西方文學的認知程度上一較高下,反而回頭去反駁連雅堂前半關於「你們都沒讀過六藝百家等古書」的說法。他接著發表了〈為台灣的文學界一哭〉回擊:
請問我們這位大詩人,不知道是根據什麼來斷定提倡新文學,鼓吹新體詩的人,便都說漢文可廢,便都沒有讀過六藝之書和百家之論、離騷樂府之音。而你反對新文學的人,都讀得滿腹文章嗎?
張我軍與連雅堂的這幾個來回,從文學思想上、到筆戰戰術上,都有許多可玩味之處,值得讀者細細品讀。我會在稍後提出自己的想法,暫且先不細說。但可以確認的是,在張我軍與連雅堂來回駁火之後,這場「新舊文學論戰」正式掀開序幕,古典文學方被迫應戰,再也無法冷處理了。雙方陣營都拉起旗號,各有論點、各有隊友,一時之間風風火火,彼此打得好不熱鬧。如果你去閱讀這段文學史,也多半會得到一個印象:這場論戰最大的得益者,絕對是新文學陣營。自此一戰,他們確立了自身的文學地位,開啟了未來一百年,台灣文壇以白話文學為主流的發展方向。至於古典文學,由於觀念顢頇守舊、不符合社會需求,自然慢慢被文壇淘汰,失去了影響力⋯⋯
但其實,上述主流說法卻存在一些微妙的錯誤。
戰術藏在細節裡
上述對「新舊文學論戰」的通說,主要來自一九五四年廖漢臣的〈新舊文學之爭——台灣文壇一筆流水賬〉這篇文章。廖漢臣是日治時期的作家、記者,在戰後敘寫這段文壇往事,自然讓人覺得有幾分權威性。而他所勾勒出來的故事框架,也很自然而然被後世的讀者採用,成為我們想像這場論戰始末的認知框架。我們上一節所講的「張我軍引戰、連雅堂迎戰」之過程,基本上就是脫胎於廖漢臣的文章。
廖漢臣的這篇「流水賬」記錄了台灣新文學誕生的重要事件,並且穿越歷史的壁障,將本來可能隱沒在故紙堆中的文學回憶帶到戰後,就這一點來說是功不可沒的。但是,如果我們仔細考察張我軍和連雅堂幾篇論戰文章的發表時間,馬上就會發現不對勁了。依照廖漢臣的敘述,兩人的發表順序應是:
1、張我軍〈糟糕的台灣文學界〉引戰
2、連雅堂〈台灣詠史.跋〉回擊
3、張我軍〈為台灣的文學界一哭〉再回擊
但是,這三篇文章實際上的發表時間卻是這樣的: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連雅堂〈台灣詠史.跋〉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張我軍〈糟糕的台灣文學界〉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張我軍〈為台灣的文學界一哭〉
發現問題了嗎?廖漢臣所敘述的故事,讓我們搞錯了一個時間點:連雅堂〈台灣詠史.跋〉不太可能是回應張我軍〈糟糕的台灣文學界〉,因為他的文章比這篇還要早發表六天!
事實上,〈糟糕的台灣文學界〉並不是「新舊文學論戰」的起點。根據日本學者河原功的研究,其實早在同年四月,張我軍就已經發表了〈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這篇文章並沒有專門論述「新文學」,而是張我軍以一名北京留學生的口吻,向島內青年呼籲要累積自身實力、為改革社會做準備的勉勵性文章。也許是有感而發,他在文章最後突然酸了「舊文學」兩句:
不然諸君怎的不讀些有用的書,來實際應用於社會,而每日只知道做些似是而非的詩,來做詩韻合解的奴隸,或講什麼八股文章,替先人保存臭味。(台灣的詩文等,從不見過真正有文學價值的,且又不思改革,只在糞堆裡滾來滾去,滾到百年千年,也只是滾得一身臭糞。)想出出風頭,竟然自稱詩翁、詩伯,鬧個不休。這是什麼現象呢?
這段文字雖然很酸,卻只占全文的一小部分,絕非文章主題。但也許就是這一小段文字,讓舊文學陣營的文人在心頭記了一筆。隨後,這篇文章沒有產生太多迴響。直到同年九月,才有一位張梗寫了〈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繼續討論舊文學的弊病。
因此,如果我們追隨廖漢臣的框架,把論戰起點訂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的〈糟糕的台灣文學界〉,整件事就會變得完全不合邏輯,彷彿那時台灣已經有時光機一樣。但如果把起點訂在四月的〈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不但邏輯會完全合理,也更能窺測作家之間的微妙互動。這便是研究文學論戰的有趣與困難之處,光是起點和終點的認知差異,就能說出完全不一樣的故事。廖漢臣的說法,是將「新舊文學論戰」說成十一月間短兵相接爆發的大戰。然而依照我們排出的時序,狀況或許更像是:張我軍和連雅堂兩人,最早都只是隨口互酸,並沒有拉下陣勢大打一架的計畫。而到了十一月,張我軍才真正想要拉高聲調,把「新文學」這個議題炒起來,因此發表了言詞尖銳的〈糟糕的台灣文學界〉。而〈台灣詠史.跋〉雖然比較早發表,但張我軍寫這篇文章時,顯然還沒讀到連雅堂所發行的那一期雜誌,因此在文章裡並沒有任何回應、也沒有指名道姓。過一陣子,他讀到了連雅堂的那段酸文,才又以〈為台灣的文學界一哭〉重砲回擊,終於釀成大戰。
由此,也就可以解釋連雅堂為什麼會在〈台灣詠史.跋〉這麼奇怪的場合回應張我軍。因為這本來就不是一篇應戰文字。從標題便可知,這是一篇「跋」,跋是在他人完成作品之後,寫在後面的「後記」或「推薦文」。有點像是我現在寫完一篇小說,然後找一位前輩來美言幾句,附錄在書後以吸引讀者的。〈台灣詠史.跋〉是為了詩人林小眉所作,當時林小眉寫了三十首「詠史詩」,發表在連雅堂所主辦的漢詩刊物《台灣詩薈》上。因此,這確實不是一篇參戰文,更像一篇廣告文。如果真要全力參戰,連雅堂大可以在自己的刊物上專門發一篇文章,甚至要每期都發文洗版也沒問題,何必委身於一篇跋文當中?顯然他只是想小酸一下張我軍及其「同黨」,並沒有要應戰的意思。
另外,我們前一節所引述的連雅堂文字,也是張我軍在回擊連雅堂時,所引述的一段著名文字。這段文字往往被人們視為舊文學陣營的代表性論述。然而,這段文字其實是經過剪裁的,如果我們再往前加個兩行,意思可能就會產生微妙的變化:
林君身世華膴,英年駿發,介弟六人,皆畢業東西洋大學,各擅專科,而林君讀湛深國故,兼善英文,顧不為時潮所靡,嘗謂文學一途中國最美,且治之不厭,此誠有得之言。今之學子。口未讀六藝之書。目未接百家之論。耳未聆離騷樂府之音。而囂囂然曰。漢文可廢。漢文可廢。甚而提倡新文學。鼓吹新體詩。秕糠故籍。自命時髦。吾不知其所謂新者何在?其所謂新者,特西人小說戲劇之餘,丐其一滴沾沾自喜,是誠坎阱之蛙,不足以語汪洋之海也。
上面畫線的部分,是原文就有、但後世很少徵引的段落。這段文字當然是在誇獎林小眉兄弟幾人有多優秀,但可以注意的是,連雅堂特別強調林家兄弟都畢業於「東西洋大學」,並且林小眉本人的英文也很好。因此,連雅堂想要表達的是:像林小眉這樣喜歡舊文學的人,並不是抱殘守缺之士,反而是在融會中西學問之後,還是比較喜歡古典文學,這是一種有意識的選擇。由此連結,就可以知道他為何會罵許多新文學支持者只是「特西人小說戲劇之餘,丐其一滴沾沾自喜」——因為舊文學陣營所懂的西方文學,很可能是不亞於新文學陣營的。
另一個證明連雅堂並非「迎戰」張我軍、只是在偷酸的細節,在「漢文可廢」這四個字。連雅堂的批評,翻成白話文就是:「你們這些搞新文學的,沒讀過幾本古典文學書,就妄想把『漢文』給廢掉。」然而,如果我們翻遍張我軍的一系列論戰文章,是找不到任何一處「漢文可廢」的論述的。所以,連雅堂一說「漢文可廢」,張我軍立刻反駁:「不知道是根據什麼來斷定提倡新文學,鼓吹新體詩的人,便都說漢文可廢,便都沒有讀過六藝之書和百家之論、離騷樂府之音?」張我軍的立場,一直都是鼓吹新文學,但並沒有真的要消滅舊文學。事實上,張我軍這位出版了台灣第一本新詩詩集的詩人,本人是會寫漢詩的。
如果我們依照廖漢臣的框架來看,就很容易理解成「張我軍沒講『漢文可廢』、連雅堂曲解張我軍的意思、張我軍精準反擊這個曲解」。但是,如前所述,連雅堂很可能根本不只是在講張我軍,他只說「今之學子」——這些「學子」,也可以是其他支持新文學的青年,但並不特指張我軍。就像我們在網路上酸人,也會故意講得很模糊,讓人知道我大概在講哪一群人,卻無法精準定位是哪一個人。張我軍跳出來說「我哪有要廢漢文」,就頗有一種自己搶椅子坐的意味了。
(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