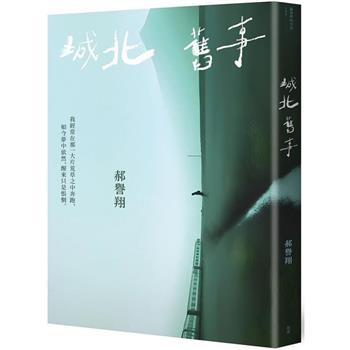【內文試閱一】
在山與海的交界
早晨一睜開雙眼,所見到的竟全是山,峰與峰之間錯落相連,直到天邊。
但山巒的顏色並不翠綠,就像是被誰兜頭潑了一盆冷水似的,淋漓灰青,又像是淚水幽幽滲出了紙端,教人看了只是莫名地一怔。
所以這哪裡能算得上是城市呢? 或許因為如此,我總是堅持說自己是「北投人」,而不是「台北人」。
也或許是,北投原來就不屬於台北。
清朝時,北投歸於淡水廳的管轄,日治時期又以大屯山系的最高峰「七星山」為名,劃入了七星郡。這一帶向來就是山高水遠,自成一處化外之地,我因此愛淡水和七星之名,遠遠勝過於台北。
♦
北投正式被納入台北市的範圍,竟是遲至一九六〇年代末期的事了。
但即使如此,當一九七五年我們全家人從高雄北上,落腳在北投之時,住家的附近卻仍然多是一派農村的恬淡氛圍,而日常生活中所慣見到的風景,也大多是蒼茫無邊的淡水河以及關渡平原,總是讓我不禁聯想到「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之類的詩句,和現代化的城市根本沾不上邊。
也或許我只是不明白,所謂的城市究竟應該是什麼模樣?
來到北投的那一年我才七歲,先前只是一個懞懂的孩子,回憶起來,在高雄的日子唯有窗外周而復始的日升日落,歲月無聲無息地滑過,就像是一部靜默的黑白電影,竟想不出有什麼悲哀和歡喜可言。
但來到北投以後世界卻大不相同了。陌生的異鄉忽然跳出了顏色、聲音和氣味,強烈的光影不安地閃爍著,躁動著,讓我驚怯睜大了眼,惶惶不知所措。我開始懷念起高雄那份明亮到過分純粹的陽光了,乾燥無雨的天氣,空中總是白雲朗朗,以及左營鄉下外婆家的磨石子地面,即便是在炎炎的夏日赤腳踩上去,也是傳來一股透澈心肺的冰涼。
然而這一切全都消失無蹤了。
就連高雄鄰居皮鞋店和我同年紀的小女孩,天天一起結伴上學玩耍,我卻也想不起她的名字和長相了,只剩下一團朦朧的黑影。反倒是她家店門口擺在玻璃櫃中的一排黑色男鞋,始終令我印象深刻。在無人的午後陽光籠罩之下,它們顯得既無助又徬徨,彷彿困惑著不知道下一步該要走向何方?
那些皮鞋還在玻璃櫃中等待著未知的主人,但我卻已經提早一步先行離開了。搬家那天,我坐上了載滿舊家具的卡車,準備一路搖搖晃晃地北上。鄰居小女孩就坐在皮鞋店前的小圓凳上,望著我,遲疑地揮了揮手。
那是道別的手勢,從此不復得見。
我想我必然是哭了。遷徙是啟蒙的開始,我的生命將要退回到一片空白的原點,重新來過一遍。我沉默地抵抗著,為注定即將失去的一切流下了絕望的淚水。但這有什麼用呢? 又有誰會覺得孩子的眼淚是珍貴的?
♦
接近傍晚的時分,搬家卡車終於來到了尊賢街,那是我們在北投的第一個住家。夕陽昏黃的餘暉鋪滿了巷子兩側的公寓,映襯得一樓鐵門的朱紅油漆更加斑駁,像是誤闖入一齣未老先衰的夢境,黯然得教人心驚。
後來,我們多半把那一帶稱之為「石牌」,而認為更往北走越過公館路以後才能夠算是北投。但「石牌」這兩個字總是讓我覺得又硬又冷,像是鐫刻著某種權威話語的石碑,神聖而不可侵犯,並不存在一絲一毫可以妥協的柔軟空間。
果然那附近也大多是些道德意味濃厚的街名,從「尊賢」、「實踐」、「明德」、「自強」到「立農」,再再向我們訓示著一種理想崇高的人格。
這些街名雖然取得堂皇,卻也多是些狹窄的尋常巷弄罷了,以柏油瀝青鋪成,縱橫交錯,切割出來一大片六〇年代以後才在台北街頭大量湧現,清一色是灰色洗石子牆的四層樓公寓。它們的造型方正,中規中矩,一如居住在其中的也大多是些勤勉樸實而面容拘謹的軍公教人員。
我們在尊賢街只住不到短短的兩年,又改搬到實踐街去。就像蒼蠅飛起在空中盤旋數圈之後,總會固執地又要落回原點,日後我們就在這些巷弄之間搬來搬去的,而新舊的住處往往不出三百公尺遠。
也是要等到多年以後,我才恍然大悟「實踐」之名的源頭,竟是因為街尾有一座國民黨專門訓練高階軍官的「實踐學社」,前身還是日本帝國陸軍的軍事顧問組織「白團」。
我從未意識到,原來住家的附近就隱藏著一個如此神祕的軍事組織?只知道實踐街口確實終年瀰漫著一股令人敬畏的氣息。那是四棟中央社的宿舍,同樣是低調的灰色公寓,我每天上學放學都必定會打門口經過,得以窺見出入在其中的社員。他們大多身穿白襯衫手提黑色的公事包,低著頭行色匆匆,彷彿包裡裝的全是一些不可洩漏的天機。
這就是我所認知的石牌。
至於北投,還要落在更遠之處,那朝向地平線盡頭綿延的大屯山脈,終年飄散著青白的山嵐和硫磺煙霧,以及更遠的淡水,日復一日向這片陸地送來海洋鹹濕的氣息,彷彿以一個更加遼闊而美的世界在殷殷召喚著我。
那是山與海混沌的交界,夜與夢的黑洞,我生命中最初讀到的一首詩,句句都是命運的隱喻,讓我不禁悠然神往,卻又每每悵然若失於它是如此的晦澀不可解。
【內文試閱二】
那正在街頭燃燒的一切
關於八〇年代,我特別記得的就是一九八七年,並不是因為台灣解嚴──我還沒有如此巨大的歷史感,而是那一年我恰好高三,畢業前夕教官突然在朝會上宣布:因為解嚴,學校的髮禁也一併宣告解除,從現在起你們可以把頭髮留長了。
雖然搞不清楚戒嚴和髮禁究竟有什麼關係?但對於十八歲的女孩而言,頭髮之事非同小可,念茲在茲,操場上爆出歡聲雷動,大家感動得相擁幾乎掉下熱淚。只可惜畢業在即,頭髮又不能在一瞬之間留長,我們只好跑到美容院去把頭髮削得更薄更短,一種當時最流行的羽毛剪,也算是以頭髮來宣告了解嚴之後的自主權。
所以解嚴是從自己的身體開始的,接下來才輪到了大腦。
七月揮汗如雨考完了聯考,我把高中三年下來累積的教科書一頁頁撕開,本來想放一把火將它們燒得精光,才算是壯烈,後來又嫌麻煩,乾脆全扔給垃圾車運走,不但毫無留戀之情,還有如釋重負的快樂,卻又不免詫異著自己居然可以痛恨知識到這種地步。
於是就這樣稀里糊塗畢了業,我從聯考的桎梏中解脫,也脫下高中三年身上那襲一陳不變的白衣黑裙,從此青春的小鳥拍拍翅膀飛出牢籠,自由自在海闊天空,哪裡還有時間回顧?
只記得為高中生涯劃下句點的,不是畢業典禮,而是體育老師帶我們去石門水庫露營。他是台灣赤足滑水的國手,特地要在我們這群女孩前大顯一番身手,只見他光著雙腳被一艘白色快艇拖著,輕功水上飄似的快速從藍綠色的湖水上掠過,濺出了一道道驚人的水花,現出繽紛而迷離的七彩虹暈,彷彿是我們一場告別青春的成年禮。
就在那天傍晚我和K共划一艘木舟,一直划入石門水庫的最深處。K是我高中三年最要好的同學,相較於我的急躁粗心,她總是溫柔而嫻靜。黃昏時分環湖四周的林蔭幽幽,我一不小心手一滑,木槳居然掉落水中,沒幾秒就直直沉到湖底。
沒了槳,要如何把船划回岸去?我只好急著向碼頭上的同學招手求救,也不知道她們到底有沒有看見?夕陽西下,山裡的天色迅速轉暗,只見岸上遙遙的燈光閃爍,傳來隱約的笑語,卻都被湖水一一吞沒,而四下靜悄悄地只聽得見我和K的呼吸。
百年修得同船渡。所以我和K真是有緣,但不知是緣深還是緣淺?當時的我們渾然不知十多年過後,K會喪生於高速公路上的一場客運大火。
我卻始終清晰地記得,那天石門水庫所蕩漾著夢幻般的紫藍色光影,映照她一雙深邃又烏黑的大眼,而我在K的眼裡看見了自己:同樣是十八歲,同樣對於即將迎來的大學生涯充滿了樂觀期待。我們於是忘了對未來本該有的忐忑與不安,就在那一年的九月分手,迫不及待飛往了各自的校園。
♦
日後屬於我的這一世代經常被稱之為「學運世代」。
這個標籤難免以偏概全,卻也多少具有某種程度的準確,因為就算我們不是學運中的一分子,也必定是一個旁觀者或是路過之人,而在有意無意之中對於運動有了深淺不一的涉入。
尤其我讀的又是台大政治系,這是我在大學聯考填下的第一志願,如今回頭再看這個選擇未免有點古怪,卻都該歸咎於八〇年代成功的黨國教育,使我到了十八歲卻依然懷抱著一種天真到近乎愚騃的理想,以為一個有志的青年就該從政報效國家。
當我果真如願以償進入了政治系,所經歷到的第一次震撼洗禮就是學生會長選舉,如火如荼在校園中展開。那其實也不過是一場學生級的選舉罷了,但兩位候選人的背後卻有不同的政黨在支持,彼此之間廝殺激烈,謠言耳語不斷,黑函和黑金滿天飛,儼然已經是一個社會選舉的小小雛形。
才剛從漫長威權年代之中掙脫出來的我們,形同是一群民主的新生兒,還停留在牙牙學語的階段,又如何能夠懂得文明的規範? 於是選舉時一拚鬥起來,就不免原形畢露,全淪為了一隻隻齜牙咧嘴的野獸。
我這才發現自己是何等的幼稚和愚蠢,原來政治不是青年報效國家的浪漫理想,而是血淋淋的權力運作。大一的必修課是政治學,教授在黑板上寫得密密麻麻,我拚命地抄著筆記,卻都是紙上談兵。一整年的課堂下來我只記得一句話:「政治就是眾人的利益分配」,而其餘全都還給了教授忘得一乾二淨。
♦
原來說到底,政治無關個人的理想和犧牲奉獻,而是眾人的利益分配。
我腦筋卻一時運轉不過來,就這樣茫茫然度過了新鮮人的一年,聽學長姊說社團才是大學的必修學分,便嘗試去造訪一些頗為活躍的學運社團如大新社、大陸社和大傳社,卻多半是躲在角落,默默聆聽那些嘴裡叼著香菸、腳趿藍白拖的社團老骨頭們口沫橫飛。
後來又在同學的慫恿下參加了一些服務性社團,這是七〇年代鄉土文學運動的產物,來到八〇年代在台大的校園仍屬主流。但我依然不免懷疑上山下海走入偏鄉,除了造就一個熱情滿滿的暑假之外,究竟是在服務自己?還是服務別人?
當年流行學者從政,政治系有幾位留學歸國的年輕老師投入選舉,我也自告奮勇到競選總部幫忙,成為學生助選員之一,沒日沒夜站在街頭發傳單,綁布條,插旗子。我還在學長的指導下模仿海德公園的「演說之角」(Speakers' Corner),也搬了一張小圓凳拿起擴音器,就站在北投的黃昏市場前拉票演說。
但我一站上去才發現凳子居然有這麼高? 眼見底下一大片黑壓壓的頭顱洶湧,雙腿就忍不住發抖,聽到自己的聲音從擴音器中傳出來,更是尖銳刺耳得陌生,反倒能聽得一清二楚的,是從夜市傳來人們吃吃的嘲笑聲。
一個大學生究竟是否知道得比一個賣菜的攤販還多? 我連自己都沒辦法說服了,更何況是他人? 我成了一個徹底的懷疑論者,對於那些堂而皇之的宣言或口號,不管是來自哪一方的,我都懷疑。
想像之中的浪漫青年,來到現實竟成了一個行動上的侏儒。
原來我根本不適合吃政治和選舉這行飯,相較於站在舞台上,我更喜歡當一個台下的觀眾,隱身於茫茫的人海之中,只在一旁觀察,而不會輕易地站起身來介入。
幸好八〇年代末的台北街頭,尤其是我居住的北投更是黨外重要的起源地之一,幾乎天天都在上演集會遊行和大大小小的政見發表會,到處都是可以湊熱鬧的政治嘉年華,而那才是活生生的教室,比起大學課堂不知有趣幾百倍。
這時對岸也恰好爆發六四天安門學運,我們每天一進教室,就和同學熱切傳閱報紙上的新聞,以為這正是二十世紀關鍵性的一刻,而歷史即將就要全盤改寫。但年輕的我們又怎麼能夠預知,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這場運動卻幾乎被人遺忘消失?
然而我仍記得當時因蓬萊島案坐牢而出獄的陳水扁,在北投走進某間中學操場的政見發表會時,被民眾高高扛在肩頭上,有如神降人世一般穿過人群,接受成千上萬民眾膜拜歡呼的光榮,讓整個夜都因此熊熊地燃燒沸騰。
我甚至有好幾次走到政見會的台前,以最虔誠而且神聖的心,掏出一個大學生口袋中僅有的紙鈔,鄭重地把它們投入捐款箱。
我甚至握過台獨教父的手,而他的另一隻手在二次大戰中被炸斷,始終藏在西裝褲的口袋中。
我家附近也常有封街演講,人潮塞滿了整條巷子幾乎見不到盡頭。我擠在隊伍中拚命踮起腳尖,才勉強瞧見以美麗島事件辯護而聞名的律師,正站在木板臨時搭出來的簡陋講台上,用激動的語氣搭配誇張的手勢演說。
我已經完全忘了他說些什麼?但那似乎不重要,反而是街道兩旁高高懸起的昏黃燈泡,照耀著不安蠕動的人們,有如黑夜的大海暗潮洶湧卻又金波蕩漾。那是星星點點的革命之火,正在翻滾醞釀著,只等待風起,火勢就足以一路延燒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