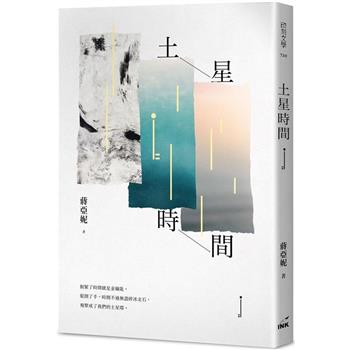好好呼吸
一、腹式呼吸
我從沒有寫過日記,沒有留下什麼手寫貼膚能把掌邊染上原子筆色的本子,不管是讀書時被逼著寫的週記、暑期日誌,沒有被逼卻也說不上多熱衷的交換日記,因為沒有寫進心裡也不夠日常,多年後再回頭看,那些只是日子,不是記錄,更不是記憶。
開始認識死亡,像是在街角撞見了陌生人,比如最早時讀到的死亡,幾乎全來自同學與課本文章中的他人,某個同學寫了自小帶他的阿嬤離開、另個同學也寫了親如兄長的鄰居哥哥意外離世……在讀了沒有成千也有上百的死亡後,在自己也開始以一本、一本的散文靠近某些現場後,我更理解沒有任何死亡能被作文與真正記載,那些百千萬字的重現與重整,都是創作;亡者沒有紙筆、沒有時間,只有觀眾能以虛構補足死亡的內心活動。
因此每一次,當我親身遇見死亡時,總感覺身在一部紀錄片中,從遠到近。許多年前看了電影《百日告別》,並不是看的時候會在影廳無聲痛哭,淚水從臉頰滑進衣領的那種存在,卻像啟蒙般,將死亡降臨時的感受拉到了更真實的現場,意識到死,得從死的那一天開始算起。
父後百日,我終於能寫下一些關於自己的字。
早在父親的死亡到來之前,死氣與臨終的影子已拖得太長,斷開了我逐漸找回真正說話能力的路,將我一瞬拉進了他的片場,如同其他人,總在逼我創作。沒有人可以為別人的死亡代言,我好想這樣回答那個才是真正已無法說話的父親,關於他如何走到這一步,沒有人比他清楚,看得再近都是旁觀。我只能說說在這百日間,自己的身與生。
夏天與無父的日子一起開始。不知怎麼我開始察覺到喉間總有永遠吸不完、嚥不進的鼻水,抗組織胺和洗鼻器、鼻噴霧與中藥,我試了無數方法、去了許多診間,沒有得到任何有用的診治,也沒有人可以診斷。這團其實(可能)並不存在的鼻水,並沒有影響我的生活,最多就是在這後疫病的年代,讓人擔憂我是否帶著什麼病毒。在一場像是大地遊戲,前一晚就得開始準備的大型健檢結束後,沒有紅字的報告上,我忽然才意識到自己無病,只是怕死。怕誰死了又比怕自己會死,再多上一些。
在逃避著死的時間裡,我在網路上跟隨著一對狗子們的旅行長達兩個月時間。阿拉斯加雪橇犬與柯基的主人想趁著小狗未老,帶他們從居住的上海開車自駕到中國最北端的城市漠河,那個中國博主每日更新Vlog,載著一整車的物資與最好的鮮食罐頭,她每日油頭素臉,只顧著狗子們是否笑得開心,即使是一趟遠征,該補充的營養素、每日的幾次散步與刷牙護蹄一次不少。旅程的後段,小柯基與大阿拉斯加輪流出現一些毛病,她便幾次徹夜開車不眠休地回到大城市,只為確認狗子平安。旅程中斷,但不曾停止,諾言的重量總來自被履行的過程,他們終於抵達漠河,也抵達她對自己小狗的承諾。在最後一部更新的影片裡頭,她邊開車邊錄音,影片是狗子們在草原跑的空景,而背景音是她獨自說著小狗的生命很像沙漏,剛開始時總覺得沙那麼多又流得那麼慢,越到後來,才發現沙漏的殘酷。殘沙就是時間,盡頭就是死亡,而她帶著體力漸漸不好的小狗才發現:「如果沒有死亡,時間就沒有意義。」
就這樣一句話又把我推回死亡的現場,雖然是現場,但不是直播,只不過在記錄片中補上與書寫其後,一個個與亡者無關,我自己的現場。
我曾經在更年輕時,發現一個時間的分野,權當成自己內心看世界的無聊把戲,當一個人開始得面臨父母的老病與死亡時,那個瞬間就是中年。有些中年來得早,有些很遲,像是孩堤的時光被諸神庇佑,偷偷延長了一些。而我的中年一瞬,雖稱不上早衰,卻也稍稍的提前了點。
藉由死亡的提點,我才確實知曉殘時珍貴,一天竟是一整天、一個月也能如此豐滿。二○二二年秋天,父親和許多癌症患者一樣,從一處肩頸或者大腿的骨痛,進而發覺自己罹癌。真正的病灶總不在現在,可能在許多年前他忽然找不著原因的沙啞、在他開始不斷大火燉炒的職涯開始時,便已發生。無數次生命演習裡,我都推演過父親的終局,這幾年裡我與他的距離變遠,物理與精神上都是。因我終於明白,一個人的極限如此微小,那個我好幾次跑得遠遠仍要繞回的中部小鎮,那個明知不是親生,彼此卻仍勉力維持住的「父女」關係,終究像是十幾季的漫長美劇一樣,花光製作費與消耗掉死忠粉絲般地只能爛尾。
有些人的生命很像囤積癖,任憑你替他清理掉多少次舊塑袋、爛瓶罐、無法使用的被巾與無數小而無用的皮繩廢紙,對你說完感謝,他轉身便再次找回所有垃圾棄物們,每一次都更凶猛。父親就是被這般堆滿的老屋,我一次次為他推開與清掃,直到他終於和我說,妳不要再管了。當然,他的房間並沒有堆滿東西,嚴格說來,甚至沒有什麼自己的痕跡(當他確診肺腺癌戒菸後,連味道都淡去了),我試圖用文學的隱喻為他的一團亂找尋另一種說法。而這座父親的老屋,就這樣在他開口說出放棄後,一次性傾頹。
每一次我到醫院看他,他都更瘦了,那是自我出生以來、有記憶後,從未看過的他,而他留給我的只有沉默與笑,叫我快點回家,回去看看自己終於組建的家庭與裡頭的家人。那般詞窮,或許是關於家的模版,他無法多談,因為他比我更不常在自己的家中。從秋天跨了剛好四個季節,直到二○二三年的夏天,他離開,似乎都沒有留下給我的話語,我只從他在醫院的看護那聽說、聽說他只有一次淡淡地說,真希望看孫子長大。平安長大也是咒語,所有美好與善意的集合,加上一點幸運,人們才能抵達。不知道是不是多一些人為一個孩子叨唸,咒語的效力更強,父親早已經放棄為自己唸咒,他的生命是一輪又一輪的迴向,除了賭桌上的那個他,每一個他都認了。
二○二二年的父親,從年頭似乎就讀出了一些不祥的癥兆,夜裡胸悶送急診,就這樣裝上了心導管,而我是在他出院才得知消息,因我同時也接著不同管線,在北部的醫院裡頭產子。當我離開醫院,住進了許久前便訂好的月子中心,看著窗外的綠地與按摩師聊起產程時,有好幾次心生愧疚到反胃;父親在那個春天,也是疫情最狠的那一段,與那家他開了半生的餐廳從小鎮一端遷至另一端,說好聽點是遷址,但我比誰都明白,是因為再也無力負擔房租。這個春天之前,孩子來臨之前,我也幾次私下轉了房租給那時房東,直到我明白其實很多事自己總也不能夠,不能也不夠。
在這些時候,我會想起許多人與書,想起一直沒有機會見到本人的陳俊志與他筆下的「台北爸爸」;想起許多年後,終於寫出《彼岸》的田威寧,我在父親遷店那陣子,也開始回到工作現場,許多年來第一次見到了田威寧。看她寫到自己的父親也曾搬去逼仄店面賣食營業,而她父親有一天就這樣拉下鐵門無蹤……看她寫幾十年後,終於跨洋見到遠嫁夏威夷的生母,看她寫及親緣的無邊離散,如此強大無恨。那些曾經想問的,關於父親該怎麼寫好(或寫不好),關於散文裡頭的自己,那個「自」,該站在自我還是自私那邊?全都無法再問,也不用問,答案一直都在書裡。
多年的摯友百合,早我一些,在幾年前也送父親遠行。我與她,或許也與許多人都共享某個父親的原型,在人生的賭桌上好賭、沉默、逃避與延遲。我一直記得那時與她的密語,怕被這人間聽見般地說著,(或許離開了比較好)、(對大家都好)、(我們還有自己的人生)……那些被消音的對話,父親在最後也用他的選擇一一應允。當久未回去的我再見到父親站在窄小的新店裡頭時,我知道他也終於不再相信有好轉的可能,於店裡、於命、於他,他開始有了認命的氣味,沒過多久,從以為的筋骨痠痛處,發現不好的東西,終於照出了肺裡頭的一團死霧。
多事之秋接著多事之冬,不到一年的夏天,我從醫院走到火葬場、從殯儀館到寶塔,因父已離妻也無子,我一個人揹著「女兒」的透明名牌,走得無比壓抑。當所有儀式完結,所有佛經都(可能)迴向後,我在下山的路上、回到自己家的公路上,沒有哭,卻開始一聲一聲吸起鼻子。
每一天都比前一天吸得更用力,有時肋骨與前胸都隱隱痛著,自律神經總是在努力告訴每個人別太神經。我的神經與我也是後來才明白,記念與創作、悼亡或者梳理都好,從來沒有人可以逼另一個人寫下,日記當然也是。我還是不會寫日記,也一直沒有人(包含自己)能逼著我開始寫作
當然,也無人能逼使我不寫。
上了許多年的瑜珈課,這幾年更喜歡練習空中掛布與吊環,將力量分解到一小塊背肌時、指尖的收束與旋繞時,一次下身跳躍與上臂的施力間,把自己舉放進空中,只有那時,我才會停止吸鼻子。也是在夏天的一次大休息時,我忽然理解了沒有什麼事情,比活著的人能好好呼吸重要,他者都不是我的時間。
腹式呼吸時,我跟著氣息通過鼻腔、呼吸道抵達身體核心,發現一路都沒有阻礙,要能確實地腹式呼吸,其實得靠胸,把呼吸盈滿胸腔,像充飽一個救生衣那樣。把胸打開,腹部與身體都會配合它,那時才能真正吸好一口氣,再把自己像是放進溫泉那般,吐氣到底。記得,要一吐到底。
二、死神的呼吸
父走前的一百多日,是那年農曆春節的尾聲,後來覺得他的瀟灑多少也展現在他只收紅包不收白包的決定。那是最後一個像是年畫與會打開春節特別節目的年節了,我能如此確定是因為早在許多年前,就不再有這樣的日子。
像是一齣話劇,父親的弟與妹們,將所有人都叫回了不再敞亮一如童年的店裡,一家家合照、發紅包與圍爐,留下了唯一一張我父與我子的合照,那是一張充滿死氣的好照片。死,並不來自我父親與畫面中的任何人,而是當下的不(可能)再,時間不只是缺席與不在,而是死去。我想起巴特的死亡觀,或許才是他理解攝影的真實經驗,攝影的刺不來自如生,更是停格瞬間,記錄下一個時間的同時發生與終結。因此我越年長越不忍心看人物照與留下合影,每一次說,來拍照吧,都帶著一種絕決,我想記住什麼,最好是記住一切的狠絕。
這樣晦氣的話,當然不能輕易和別人說,尤其與朋友合照時。但其實死這件事,不也和生一樣,是一種反向的儀式與節慶,這幾年裡最愛的音樂現場,坂本龍一的「async紐約現場」,就像是一次生的告別式,他在無蓋平台鋼琴、電子樂器、吉他,甚至是一片玻璃間輪流演奏,演奏、轉身、徐行,現場的觀眾如此逼近,他知道有人在拍他,他也知道這場音樂會是他癌末身體能做的最後一次完整演出了(二○二二年那場純鋼琴的線上演奏會則更像是為遺照留下的一張招牌動作)。那是演奏更接近攝影能凝結與滯空魔力的地方,而寫作怎麼都到不了,只能是時間的之前、時間的之後,無限想靠近與重現當下,也因此我才能一直寫下去。
後來發現,總是後來才能發現,不只是我,當然也不非得是羅蘭巴特與坂本龍一,我父親也以他的方式,留下與告別。整理遺物時,與父親同住的姑姑在他的手機中看見了在其他家人傳給他的照片裡、在不小心誤觸截圖與滿是晃動不知焦點何處的照片中,有兩張他穿著病服的自拍,一張側臉、一張正面,直視鏡頭沒有晃動也沒有不確定,臉頰因為削廋而垂下刻痕般的法令紋,但眉眼不曾變過,嘴唇抿得很緊,沒有笑容,但絕對也說不上悲傷,那是屬於父的最後一次觸鍵。姑姑在夜裡把這兩張照片傳到了我手機,它們至今都待在裡頭,沒有歡樂,但也並不難過。
許多紀念都是如此,我存在過,登入打卡,登出打卡。
比起許多與死亡有關的現場,比如醫生宣告死亡,比如法事、出殯、火化、納骨進塔、祭拜,比如收到死亡證明、比如簽下拋棄繼承的文件等等,現場總沒有實感,現場只剩過場。我總在現場的衍生事件裡,才能清醒感受。父臨終前七天,依然能清醒自理與我簡單通話,簡單的原因並不來自他的不能,而是他的不想,越是病重,他越無話與我說。直到那幾日,我才接受(只有我自己)和他說好的家族旅行,不會再來。
夏末總是校園文學獎的熱區,預計週末要再回去陪他,父親離開前六天,忽然陷入呼吸困難,能下床的時間變得極少,從定期的返院化療轉往了專責病房。而我在那六天裡從南而北,有三場早早說好的工作得完成,那一季夏末變成了無數次來往高鐵再轉往父親所在醫院的季節,我在一場高雄的文學評審會議結束後,原要返回台北準備隔日的工作,卻在南方一處被阿勃勒樹影覆蔭的校園裡,聽見了呼吸聲。
枝葉與風擦出的聲音是一整片的,像是隔著氧氣呼吸罩睡著的父親,他的呼聲也與塑料與打出的高氧氣體摩成一片。我才清醒地想起醫生說,可能就在這幾天,哪幾天?醫生無法說出幾天,有些時候臨終會拉成數月、有些時候從紅線一腳再踏回綠區,當然更有時候,就是明確的一、二、三天。我不喜歡賭,大賭小賭拿生命賭,都是傷情,我跟著阿勃勒一起深呼吸,好好地取消了隔日的工作,致歉、說明,好好地回到高鐵、回到醫院、回到父的床前。
沒有參加與告假的文學相對論,是為了展開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相對論,我相對於父,死相對於生,痛相對於活,最後我再相對於自己。回來的隔日,父的呼吸開始變了,氧氣罩底下的呼吸片狀剝離,像是被切成了一顆一顆的氣泡,偶爾傳來清楚卻非人般的嘎嘎聲,醫生來時聽見,只說了可以請想見他的人來看看他了。我一邊打給父親的朋友,怎麼想來都只剩兩個人名,一邊從文獻中自己找說明,當病人走向臨終,會先失去吞嚥的功能,使痰卡在喉嚨,痰音與氣泡相融,醫學上也有人說那是「死亡的嘎嘎聲」……而他在進入這樣的呼吸前,死神的呼吸開始前,只告訴了所有人,一根管子都不插。
我在白日裡放歌,放西洋老歌,隨著嘎嘎的呼吸持續,他的嘴無法閉上,也失去了語言,接著是雙眼開始長時的閉上,我只能從他眼皮的跳躍程度,感受自己放的歌曲是否得他鍾意,木匠兄妹始終是他年少至今的愛歌,貓王還可以,披頭四時皺了一次眉頭。我反覆替他以棉棒沾水濕潤雙唇,補上護唇膏,在漸漸水腫的雙手雙手裡不間斷地擦好乳液,卻更感受不到父親還在這個身體裡頭,如果他在,他想必也想離開。我沒有權力請一個人留與走,連在文章中、連在愛情裡,都做不到如此橫行,何況是對父親,就像他這一生裡頭,想必連女兒的一次「爸爸不要走」都沒有聽過。爸爸如果想走,就走吧,從我很小的時候開始,就這樣想了。
因為他也從未逼我去過不想去的地方,當我和他說自己不愛誰了、傷害了誰或被誰傷害了,他都只是說那你想清楚就好,其實沒想清楚也沒關係,什麼都沒關係。所以我知道自己永遠可以走,邊走邊寫、邊走邊哭、邊走邊吃,甚至是不寫了、不哭了、不吃了,他也不會怪我,因為他總是在被其他人責怪。那一個週五的夜晚,我沒有和父的弟弟交班,回家補眠,我總想著陪他一起深呼吸。有些人天生就會用嘴巴呼吸,因為鼻過敏、因為運動、因為習慣,這樣的人適合潛水,我忽然從病房想到了大海。
這一年裡,我到海邊練習了好幾次潛水,先在岸邊的深水池裡頭,在裡頭平衡耳壓、摘除面鏡,體育課般,每個動作我都能做得極好,甚至是在淺海區練習中性浮力,在上下浮沉間的一口呼吸,得提前卻又不能真正過早開始呼與吸的準備,對我來說是腹式呼吸的精準度。但只要來到深海,當我從腹部意識到嘴巴時,總會吸嗆進海水,無法完成考核。我是無法好好用嘴巴呼吸的人,不知道父親是不是呢?每一次的呼吸,開始無法被讀秒計算,我只看得出來,每一次的呼吸都讓整座身體骨架上下移動,胸腹卻沒有被擴張與舒壓,他已經無法好好呼吸,就像在海底的我。
死亡是沒有聲音的,沒有配樂與倒計時,連眼淚掉下去都比平常安靜,人的體溫也不會在瞬間就冷去。那個夜晚,父與我不再相對,他真正躺下,而我只能站在其後。有些時間被快轉壓縮,不是因為不重要,而是因為它無法被賦予太過密集與高壓的情感,太多就變得麻木,麻木的記憶與書寫,不如留白。這些都發生在我開始吸起鼻子、不能好好呼吸的那個夏天,如果說,關於那個夏天還有什麼想補充的事件,可能只剩一首歌與幾部電影。
父親火化那天,我的伴侶第一次在他面前演奏(雖然人最後失去的是聽覺,但應該再怎麼久也聽不見七天後的聲音)。大度山火葬場裡,他拿出那把從克里蒙納來的琴,我猜他沒有多想就拉起了也來自義大利的《新天堂樂園》,同名電影裡頭,主角成為名導演,多年後回到西西里的老家、老電影院,即使當年啟蒙他的放映師和他說過,這個城鎮太小無法裝下他的夢想,要他捨棄鄉愁,專心工作,別再回來,就像我父總和我說著的,「妳回家」,可主角仍然回來參加他的喪禮,如父、如我。名為「新天堂樂園」的戲院在最後被拆除了,我與父親第一次看電影的戲院,多年前就停止了營業。
樂園不一定是天堂,第一部他帶著我看的電影是《獅子王》,辛巴的父親木法沙早早就離開世間了,七歲的我還不懂得什麼是生,更遑論死。我只記得走出戲院,轉身和他說,爸爸,我也要和辛巴一樣飛高高。
他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