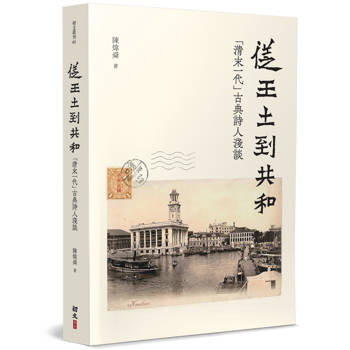根據導言,我們在「清末一代」詩人中首先列出的就是皇族遺少溥儒。先介紹一下他的背景。溥儒(1896-1963)姓愛新覺羅氏,字心畬,齋號寒玉堂,滿洲鑲藍旗人。他是道光皇帝曾孫、恭忠親王奕訢次孫、小恭王溥偉之弟,家世顯赫。在辛亥革命之際,溥心畬已經十六歲,家世、國族的認同感已經形成了,對於西太后還有特殊的好感。作為皇室子弟,他自然對已經滅亡的清朝有依戀和懷舊之情。在這裡,容我先轉述一則聽自孔德成老師的故事。
老師說,溥心畬的詩書畫造詣非凡,他一邊畫畫一邊構想詩作,畫畫好了,詩也成了,可見他的捷才。現在很多人要用現成的句子題畫,而溥心畬的題詩一定是原創。(近人李猷《近代詩選介》也記載:「其作詩尤迅捷而有才華,嘗比賽作題畫詩,先生每二分鐘成七絕一首。而余則需五六分鐘,惟有拜佩。」)1894年甲午戰後,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李鴻章失勢,中樞乏人,朝堂上下十分惶恐,孔老師的父親,也就是老衍聖公孔令貽(1872-1919,孔子七十六代嫡長孫)在西太后面前力薦老恭王奕訢出山,衍聖公府因此和恭王府成為了世交。
為什麼當時朝堂一眾大臣不敢推薦老恭王呢?原因要回溯至1861年咸豐皇帝去世之際。當時老恭王身為咸豐之弟,與兩宮太后一起扳倒了八顧命大臣,從此兩宮垂簾,老恭王輔政。後來老恭王和慈禧鬧矛盾,下臺了,史稱「甲申易樞」。老恭王因此閉門隱居,絕交息遊十年之久。甲午後,敢推薦他出山的竟只有從前並無深交的一品大員衍聖公,足見世態炎涼、患難真情。因此,孔老師和溥心畬雖然年齡相差近三十歲,卻也成為世交好友。有次孔老師對溥心畬說:「你的詩寫得又快又好,不如作一首來敘一敘我們兩家的世誼吧。」但溥心畬回答道:「此詩不能寫。我們兩家是因為老恭王復出才成為世交的。如果詩中稱頌先祖,就對太后不敬;如果稱頌太后,又委屈了先祖。」所謂「忠孝兩難全」,最終一字未寫。
溥心畬有一個別號叫「西山逸士」,而西山就是北京的香山。清亡後,溥心畬隱居西山多年,觀摩家藏書畫,無師自通,成為大家。「西山逸士」的典故,同時也出自《史記.伯夷列傳》。武王伐紂之後,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居西山,時常唱一首〈采薇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吾適安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所以溥心畬以前清遺少自居,是很明顯的。有傳聞說,1949年之後國府遷臺,宋美齡要學國畫,想拜溥心畬為師。溥心畬拒絕道:「你是新朝元首夫人,我是前朝王孫,怎麼可以成為師徒呢?」後來宋美齡只好隨黃君璧學畫。
李猷先生論溥心畬詩:「五言全然唐音,而自具蕭逸之致。……神似王、韋,加以身世關係,低徊故國,身遘亂離,亦有傷感與蒼老成分也。」(《近代詩選介》)我們可以把溥心畬的詩作分為大陸、臺灣兩個時期,聊舉一二看看。他在北京隱居的時候,看到玉泉山靜明園裡乾隆御題詩的詩碣,於是寫了一首七言絕句:
玉階青瑣散斜陽。破壁秋風草木黃。
只有西山終不改,尚分蒼翠入空廊。
此詩表面上寫景,但西山就意味著逸民、不與新朝合作。「西山終不改」,一方面指西山的山色蒼蒼、依然不變,另一方面也是講自己的志節不變。西山蒼翠的山色映入空蕩蕩的走廊,照在乾隆的御碑上,這不是相映成趣嗎?所以這首詩顯然表達了替清朝守節的心志。
又如1918年秋,溥心畬到濟南大明湖遊覽。他在歷山——亦即千佛山參觀舜祠,作過一首七絕:
濟南城下明湖水,取薦重華廟裡神。
寂寞空祠叢竹淚,九嶷深處望何人。
歷山相傳為虞舜早年躬耕之處,也就是所謂的「龍興之地」吧。而根據劉向《列女傳》、張華《博物志》等書的記載,虞舜在禪位予大禹之後南巡,考察民風,結果在湖南一帶染上時疫而病故,就地安葬九嶷山。娥皇、女英二妃得知噩耗,前往尋找亡夫的墳墓,流下的眼淚揮到竹子上,令當地的竹子都成了特殊的斑竹。後來她們在途經洞庭湖時恰好遭逢風暴,遇溺身亡,成為了湘妃。當時的溥心畬從未去過湖南,但他身處大明湖這個「龍興之地」,卻聯想起千里以外虞舜二妃的葬所。大明湖、洞庭湖,分別是虞舜起家與駕崩之處,可以說象徵著有虞一朝的起點與終點。溥心畬短短一首七絕,將兩處湖山的影像疊加、融會到一起,言在此而意在彼,透過歌頌二妃之忠貞,來表達對清朝興亡的感慨,以及自己身為宗臣、不改初心的立場。
1930年代,溥儒應邀南下參與各種美術活動,名聲鵲起。到抗戰之際,他不跟日本合作,不加入偽滿洲國,氣節非常高尚。因此勝利後,蔣介石就邀請他當了國大滿族代表。他這個時期的詩,依然在講述遺民情懷,對於民國雖然不能說認同,但態度卻也軟化了一些。他不苟同蔣介石的政見,但蔣畢竟領導了八年抗戰,令溥心畬有所頷首。蔣宋夫婦對溥心畬的生活也一直十分關心。
到了臺灣之後,溥心畬走南闖北,飽覽各地美景,創作了很多詩詞。他這些作品有個共同點:往往會將臺灣的風物比擬成大陸某處。去過臺灣的朋友都知道,慈湖是蔣介石陵寢暫厝之處,因為那裡和他老家溪口的景色非常接近,令他想起亡母,因此被稱為慈湖。這種心態在那批渡海的人士之中是很普遍的,無論政界還是文化界都如此。臺灣青草湖有一座武侯廟,是祭祀諸葛亮的,溥儒有詩吟詠:
湖光樹色遠涵空。丞相祠堂在此中。
寒食杜鵑啼不盡,春風猶似錦城東。
根據我們考據,溥心畬大概一輩子都沒去過四川,但此詩為什麼會提到四川呢?可以想見,當他還在大陸時,北京是清朝的象徵、故國的象徵,但渡海之後,這個故國的概念就從一個北京城擴展到整個中國大陸。雖然他從未去過四川,但四川此時已屬於他故國版圖的一部分。
再如描寫臺灣原住民(大陸稱為高山族)的詩〈高山番〉:
構木棲巖穴,攀藤上杳冥。
射生循鹿跡,好武冠雕翎。
箭影穿雲白,刀光照水青。
聖朝同化育,嗟爾昔來庭。
前三聯六句對原住民的情態描寫極為生動,末聯引用了《詩經.大雅.常武》的句子:「四方既平,徐方來庭。」所謂「來庭」,指四方蠻夷遠道而來朝覲中央天子。清朝之世,朝廷已在臺灣替平埔族、高山族辦學,移風易俗。這就是「化育來庭」的註腳。不過,王家誠在《溥心畬傳》中論此詩時補充道:「原住民構木棲穴、勇武善戰、以狩獵為主,前清曾被德化,進貢朝廷,也算是一方的藩屏;這就是溥心畬對臺灣原住民最早也是最粗淺的看法。當他旅臺日久,對原住民保鄉衛土,抵抗日本殖民戰爭的忠勇壯烈,所知愈多,他的看法,也大為改觀。」王氏還列舉溥心畬後來所作〈石門銘〉、〈霧社山銘〉、〈太魯閣記〉等篇為例,指出他在文中稱頌原住民的義烈必將光耀史冊,對守義不屈的「高山番」的敬重,以及對甲午之戰喪權割地的深切反省。由此可見溥儒對於臺灣高山族原住民的認知,還是有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的。
1963年,溥心畬在臺灣去世,享年六十八。他晚年曾對弟子說:「如果你要稱我為畫家,不如稱我為書家;如果稱我為書家,不如稱我為詩人;如果稱我為詩人,更不如稱我為學者。」近一二十年來,我們對溥心畬的書畫作品已日益珍視,但對他的詩歌創作和學術研究工作依然關注不足,這些無疑都是我們值得努力的探討方向。
2022.08.12.
老師說,溥心畬的詩書畫造詣非凡,他一邊畫畫一邊構想詩作,畫畫好了,詩也成了,可見他的捷才。現在很多人要用現成的句子題畫,而溥心畬的題詩一定是原創。(近人李猷《近代詩選介》也記載:「其作詩尤迅捷而有才華,嘗比賽作題畫詩,先生每二分鐘成七絕一首。而余則需五六分鐘,惟有拜佩。」)1894年甲午戰後,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李鴻章失勢,中樞乏人,朝堂上下十分惶恐,孔老師的父親,也就是老衍聖公孔令貽(1872-1919,孔子七十六代嫡長孫)在西太后面前力薦老恭王奕訢出山,衍聖公府因此和恭王府成為了世交。
為什麼當時朝堂一眾大臣不敢推薦老恭王呢?原因要回溯至1861年咸豐皇帝去世之際。當時老恭王身為咸豐之弟,與兩宮太后一起扳倒了八顧命大臣,從此兩宮垂簾,老恭王輔政。後來老恭王和慈禧鬧矛盾,下臺了,史稱「甲申易樞」。老恭王因此閉門隱居,絕交息遊十年之久。甲午後,敢推薦他出山的竟只有從前並無深交的一品大員衍聖公,足見世態炎涼、患難真情。因此,孔老師和溥心畬雖然年齡相差近三十歲,卻也成為世交好友。有次孔老師對溥心畬說:「你的詩寫得又快又好,不如作一首來敘一敘我們兩家的世誼吧。」但溥心畬回答道:「此詩不能寫。我們兩家是因為老恭王復出才成為世交的。如果詩中稱頌先祖,就對太后不敬;如果稱頌太后,又委屈了先祖。」所謂「忠孝兩難全」,最終一字未寫。
溥心畬有一個別號叫「西山逸士」,而西山就是北京的香山。清亡後,溥心畬隱居西山多年,觀摩家藏書畫,無師自通,成為大家。「西山逸士」的典故,同時也出自《史記.伯夷列傳》。武王伐紂之後,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居西山,時常唱一首〈采薇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吾適安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所以溥心畬以前清遺少自居,是很明顯的。有傳聞說,1949年之後國府遷臺,宋美齡要學國畫,想拜溥心畬為師。溥心畬拒絕道:「你是新朝元首夫人,我是前朝王孫,怎麼可以成為師徒呢?」後來宋美齡只好隨黃君璧學畫。
李猷先生論溥心畬詩:「五言全然唐音,而自具蕭逸之致。……神似王、韋,加以身世關係,低徊故國,身遘亂離,亦有傷感與蒼老成分也。」(《近代詩選介》)我們可以把溥心畬的詩作分為大陸、臺灣兩個時期,聊舉一二看看。他在北京隱居的時候,看到玉泉山靜明園裡乾隆御題詩的詩碣,於是寫了一首七言絕句:
玉階青瑣散斜陽。破壁秋風草木黃。
只有西山終不改,尚分蒼翠入空廊。
此詩表面上寫景,但西山就意味著逸民、不與新朝合作。「西山終不改」,一方面指西山的山色蒼蒼、依然不變,另一方面也是講自己的志節不變。西山蒼翠的山色映入空蕩蕩的走廊,照在乾隆的御碑上,這不是相映成趣嗎?所以這首詩顯然表達了替清朝守節的心志。
又如1918年秋,溥心畬到濟南大明湖遊覽。他在歷山——亦即千佛山參觀舜祠,作過一首七絕:
濟南城下明湖水,取薦重華廟裡神。
寂寞空祠叢竹淚,九嶷深處望何人。
歷山相傳為虞舜早年躬耕之處,也就是所謂的「龍興之地」吧。而根據劉向《列女傳》、張華《博物志》等書的記載,虞舜在禪位予大禹之後南巡,考察民風,結果在湖南一帶染上時疫而病故,就地安葬九嶷山。娥皇、女英二妃得知噩耗,前往尋找亡夫的墳墓,流下的眼淚揮到竹子上,令當地的竹子都成了特殊的斑竹。後來她們在途經洞庭湖時恰好遭逢風暴,遇溺身亡,成為了湘妃。當時的溥心畬從未去過湖南,但他身處大明湖這個「龍興之地」,卻聯想起千里以外虞舜二妃的葬所。大明湖、洞庭湖,分別是虞舜起家與駕崩之處,可以說象徵著有虞一朝的起點與終點。溥心畬短短一首七絕,將兩處湖山的影像疊加、融會到一起,言在此而意在彼,透過歌頌二妃之忠貞,來表達對清朝興亡的感慨,以及自己身為宗臣、不改初心的立場。
1930年代,溥儒應邀南下參與各種美術活動,名聲鵲起。到抗戰之際,他不跟日本合作,不加入偽滿洲國,氣節非常高尚。因此勝利後,蔣介石就邀請他當了國大滿族代表。他這個時期的詩,依然在講述遺民情懷,對於民國雖然不能說認同,但態度卻也軟化了一些。他不苟同蔣介石的政見,但蔣畢竟領導了八年抗戰,令溥心畬有所頷首。蔣宋夫婦對溥心畬的生活也一直十分關心。
到了臺灣之後,溥心畬走南闖北,飽覽各地美景,創作了很多詩詞。他這些作品有個共同點:往往會將臺灣的風物比擬成大陸某處。去過臺灣的朋友都知道,慈湖是蔣介石陵寢暫厝之處,因為那裡和他老家溪口的景色非常接近,令他想起亡母,因此被稱為慈湖。這種心態在那批渡海的人士之中是很普遍的,無論政界還是文化界都如此。臺灣青草湖有一座武侯廟,是祭祀諸葛亮的,溥儒有詩吟詠:
湖光樹色遠涵空。丞相祠堂在此中。
寒食杜鵑啼不盡,春風猶似錦城東。
根據我們考據,溥心畬大概一輩子都沒去過四川,但此詩為什麼會提到四川呢?可以想見,當他還在大陸時,北京是清朝的象徵、故國的象徵,但渡海之後,這個故國的概念就從一個北京城擴展到整個中國大陸。雖然他從未去過四川,但四川此時已屬於他故國版圖的一部分。
再如描寫臺灣原住民(大陸稱為高山族)的詩〈高山番〉:
構木棲巖穴,攀藤上杳冥。
射生循鹿跡,好武冠雕翎。
箭影穿雲白,刀光照水青。
聖朝同化育,嗟爾昔來庭。
前三聯六句對原住民的情態描寫極為生動,末聯引用了《詩經.大雅.常武》的句子:「四方既平,徐方來庭。」所謂「來庭」,指四方蠻夷遠道而來朝覲中央天子。清朝之世,朝廷已在臺灣替平埔族、高山族辦學,移風易俗。這就是「化育來庭」的註腳。不過,王家誠在《溥心畬傳》中論此詩時補充道:「原住民構木棲穴、勇武善戰、以狩獵為主,前清曾被德化,進貢朝廷,也算是一方的藩屏;這就是溥心畬對臺灣原住民最早也是最粗淺的看法。當他旅臺日久,對原住民保鄉衛土,抵抗日本殖民戰爭的忠勇壯烈,所知愈多,他的看法,也大為改觀。」王氏還列舉溥心畬後來所作〈石門銘〉、〈霧社山銘〉、〈太魯閣記〉等篇為例,指出他在文中稱頌原住民的義烈必將光耀史冊,對守義不屈的「高山番」的敬重,以及對甲午之戰喪權割地的深切反省。由此可見溥儒對於臺灣高山族原住民的認知,還是有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的。
1963年,溥心畬在臺灣去世,享年六十八。他晚年曾對弟子說:「如果你要稱我為畫家,不如稱我為書家;如果稱我為書家,不如稱我為詩人;如果稱我為詩人,更不如稱我為學者。」近一二十年來,我們對溥心畬的書畫作品已日益珍視,但對他的詩歌創作和學術研究工作依然關注不足,這些無疑都是我們值得努力的探討方向。
2022.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