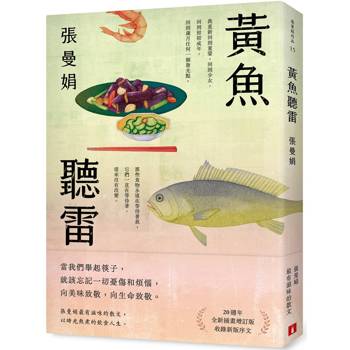張家小館餃子兵
星期三在學校裡有八堂課,中午一小段空檔,我並不很餓,卻覺得有進食的必要,於是,便來到大直,走進一家餃子館吃午餐。在我想來,既是標舉餃子館,他們的餃子應該很不錯。服務生問我要幾個餃子,十個吧,我說,在家裡吃餃子,我都能吃十幾個的。餃子上桌了,我有點錯愕,這……是餃子,不是水煮包子吧?它們的個頭還真大,皮尤其厚,內餡粗糙,我用了好多醬油、醋和辣椒醬,勉強啃完五個,已經棄械投降,誰要再逼我吃完,我鐵定和他翻臉。當我結賬時,服務生還追上來問:「要不要打包?」不用不用,我差不多是逃出來的。一個人緩緩走在秋日街頭,忽然覺得感傷了,我知道終有一天,我會沒有餃子可吃的。
說到底,都是因為我家是餃子世家,而傳到我這一代,看起來是要徹底失傳了。我家有一個擀麵板和一支擀麵棍,年紀都比我大,應該是這個家庭剛剛組成就來到的。新鮮麵條還不好買的時代,父母親要想吃麵條,就得自己和麵擀麵拉麵條。每當有客人上門,像是父親的海員朋友,或是母親的護士同學,小小的屋子擠滿最能吃的青年,大家便一起包餃子,每個人都動手做,邊包邊聊,親密又合作。所以,從我有記憶以來,包餃子就是最平常的活動了。
父母親說在他們黃河流域的老家,通常是過年才包餃子的,而在我們台灣島上的家裡,只要市場有賣韭菜的,就是包餃子的好時節了。
有客人來我家,常常也指定了要吃餃子。吃餃子其實並不省事,從一早起床就開始準備,揉麵啦、料理餃子餡啦,包心菜洗好切碎之後要用紗布包起來將菜汁擠乾;絞肉買回來總還得剁個好幾遍才能生黏;細細的韭菜一支支揀乾淨,再加上蝦米之類的配料,可得忙和個半天。所以,每當有客人指定吃餃子,並且順道加一句:「簡單點,就吃餃子吧。」我總有點不忿,吃餃子哪裡簡單?等我長大一些,稍稍見過世面才明白,吃餃子確實是可以「簡單點」的,而是我們家把它複雜化了。
到底有多少人在我家吃過餃子,已經無法記數,但是,吃完之後最常有的建議就是:「張伯伯張媽媽開個張家小館賣餃子吧。」在那些人丁興旺的時代裡,我家的餃子都是一板一板的堆放著,大鍋煮著滾水,要煮好幾鍋才歇火。母親負責擀麵皮,父親負責包餃子,一顆顆皮薄而飽滿的餃子,每一顆的大小形狀幾乎一模一樣,端端正正排在板上,直著看橫著瞧,都能成排成列,就像精神抖擻、制服筆挺的士兵,踢著正步從司令臺前經過。朋友有一次驚呼:「哇!好像在閱兵喔。」從此之後,只要包餃子,就覺得父親好像餃子兵團的總司令。
我家過年當然也吃餃子,卻是選在大年初五,說是「破五」,把過去一些不好的事都破除掉;又有一說是「捏小人嘴」,吃了初五的餃子便能封住小人的口舌。有幾年我的年輕女學生總要在初五趕來吃餃子,像是一種祝福的儀式。母親的麵皮要揉很久,愈揉愈柔軟,再放兩個小時,讓麵醒一醒。父親在餡裡加了金黃蝦米、拌肉時加入生蛋增加鮮嫩,還有一個秘方,便是自煉花椒油。將花椒在油裡炸得快要變黑了,花椒的氣味全化進油裡,便將花椒丟棄,等油降溫再淋進餡料裡,撲鼻的香味噴起來,全體拌勻之後,就可以包餃子了。
我待在家裡的星期日,有時還沒起床便聽見剁餡兒的聲音,我知道有餃子可以吃了,便覺得一整天都讓人喜悅。人口簡單的家裡只包出一板餃子,我看著頭髮斑白的父母親,依然專注的擀麵,將包好的餃子排列成兵,覺得上天對我確是特別恩寵的。
* * *
甜蜜如漿烤番薯
小時候回家的路上都要經過一片番薯田,綠油油的番薯葉長得好茂盛,大人說這些葉子要餵給豬吃的,我們吃的是埋在地下的番薯。我家裡並不烹煮番薯,卻在菜市場裡買一包用糖熬煮的竹山甜番薯,黏黏地,曾經,咬一口就黏下了我已經脫搖的門牙。
最讓人期待的還是天冷以後的烤番薯,賣烤番薯的都是推著車的老人家,穿一身洗得泛白的藍色厚棉衣,搖一節嘩啦嘩啦的竹子,我們一聽見便圍聚攏來,一塊錢、兩塊錢就可以買一隻肥肥的番薯了。多年之後,我挑了一個肥肥的番薯,老闆慎重其事的秤了秤,說:「五十元。」我嚇得半天不敢伸手去接,一塊錢是怎麼變成了五十元了?如果烤番薯可以買來囤積,我對它的信心會比股票和房地產強很多。母親每次聽見我花那麼多錢買一隻烤番薯,都替我不值,她說五十元她可以買一大袋生番薯。
家裡的番薯多半都是煮稀飯吃的,這還是在「清粥小菜」的情調彌漫開來之後興起的,母親去吃過一碗「地瓜稀飯」,問出價錢之後,當下就說,她的五十元生番薯可以煮一個月的地瓜稀飯,於是,每次吃地瓜稀飯都覺得是一種賺錢的行為。番薯煮得將化未化,白色米粒也熬出了番薯的甜香味,我喜歡從稀飯裡挑出糯糯的番薯,滿滿咬一口,既不會掉牙又好滿足。
地瓜湯是番薯壯烈成仁之後的另一道美味。那一年為了泡溫泉與朋友入山去,山上霧氣濃重,寒意砭骨,一個轉彎,山道旁懸一盞燈,上面寫著「地瓜湯」三個字。我們下車,絲絲細雨裡鑽進空無一人的小店,爐灶上煮著地瓜湯,鍋旁豎著牌子:「十五元.請自取」。我們一人一碗加了薑的地瓜湯,吃得臉頰潮紅,整個身子都暖起來。老闆始終沒出現,我們付了錢繼續上路。泡完湯回程時霧開了,一路下山都沒看見那個小店,後來再去也沒遇見。我和朋友常常提起這件事,笑說我們闖進了聊齋,吃了蒲松齡的番薯。
我在春日裡的最後一道冷空氣裡下車,穿越馬路,入夜的街道,熙來攘往的人群,便利商店的門一開,便聽見「歡迎光臨」的呼喊聲,充滿元氣。而我停在便利商店旁邊,一間幽暗的小店門口,對著一整排垂掛如魚的番薯,扯開嗓子喊:「老闆!要買烤番薯喔。」老闆娘從暗處走出來,戴上棉手套,她問:「要幾個?」我喋喋地說著,不要紅的,要黃色的喔,我要烤得很軟很軟,有蜜油流出來的那一種。老闆娘會心一笑,戴著手套的手探進甕窯,熱騰騰一隻番薯在她掌上滾來滾去,像剛剛捕捉住的黃色小老鼠。老闆娘說有人喜歡軟的有人喜歡硬的,各人有各人的喜愛。我捧著我的烤番薯,香味撲鼻。
我等著過馬路的時候,忽然,時光的甬道裂了一個口子,也是在人來人往的街道上,與我相戀的那個情人,倚著街邊的欄杆,雙手交握,注視我捧著烤番薯,一步步向他走去。
那是一個陌生的城市,是一段初初開展的情愛,我們沿著街道走,常常迷路了,便停下來休息。我看見一個賣烤番薯的自行車,歡天喜地跑去買了,再與他一起分食。我是那麼專注於手中的番薯,他是那麼專注於吃番薯的我,專注,絕對是愛情中最迷人的部分。
他後來是怎麼失去專注的?而我又怎麼始終沒失去對於番薯的專注呢?我迷戀於那甜蜜如漿的滋味,那是愛情中最難保持的滋味。
* * *
敲開一隻蛋
中國開天闢地的神話裡,有一則是這樣說的,說在宇宙初生的時候,是混沌不清的,如一隻雞子,後來,濁氣下沉成了大地,清氣上升便是天空,天地都安排好,就生出了第一個人,一個孤獨的巨人,叫做盤古。我喜歡這個神話,喜歡他們將那清濁相混的鴻蒙比喻成雞蛋,雞蛋變成了宇宙。
誰不愛吃雞蛋呢?在平底鍋裡煎一個荷包蛋,當做早餐,嗅聞著咖啡香氣,聽著油鍋裡吱吱吱蛋在凝結的聲音,真是非常幸福的感受啊。我喜歡半生熟的荷包蛋,蛋白邊緣最好還有一點焦脆,淋幾滴醬油,配全麥吐司麵包吃。輕輕挑破蛋黃,金黃色的汁液湧出來,像陽光溫柔篩過窗邊掛在睫間。用烤過的麵包蘸著蛋汁吃,然後再將凝固的部分切成小片,細細吃盡,可以抵得過一個甜蜜的親吻。
我也曾在酒店的早餐桌旁,看過一個彷彿宿醉還未醒來的男人,整張臉埋在碟子上,噘起嘴來囌囌囌地將蛋汁全部吸進嘴裡,這或許是對於蛋的禮讚,卻顯得太過貪狠。
小孩子多半都滿喜歡蛋,端午節爭先恐後的搶著將蛋豎起來,常常是失敗的,而且還要經過冗長的過程。大人陪著我們豎蛋,說是念書都沒有這樣的誠意專心。母親說起她小時候的故事,說起她家裡養的雞生了蛋,便讓母雞孵,母雞孵了好多天也沒動靜,外婆便盛一盆溫水來,將雞蛋擱在水上,如果雞蛋在水面上滾啊滾的轉動,就表示小雞幾乎生成了,在踩水呢。若沒生成小雞的蛋,便靜靜沉下盆底。「可以撈起來吃啊。」我們一旁嚷嚷。母親說孵不出來的蛋也壞了,吃不成,只得丟掉。我想像著在黃土高原上,那個被太陽曬得黧黑的小女孩,滿懷希望的在母雞肚子下面取出孵過的蛋,卻都是吃不得的。
四十年後,我們在黃土高原,在那座傾圮的院落裡,遇見最豐盛的雞蛋宴。陪著母親返鄉探親時,外婆已經過世好些年了。十一、二歲的母親離家時只當是去遠方旅行,腳步如此輕巧的跨過院牆,卻花了四十幾個寒暑,才又走回來。姨媽們一路哭著迎著我們回家,稍稍休息之後,為我們端上一大碗一大碗補品,白糊糊的,原來全是水包蛋煮白糖水。每人的碗裡大約有七、八隻水包蛋,我們五個人可能吃掉他們半年或者一年的蛋了。在圍繞著的孩子歆羨的眼光中,親人催促我們,吃吧,吃吧,多吃點,好補的。那個黧黑的小女孩,隱約也在窗邊,看著我的蛋。我將白糖水喝了幾口之後,放下筷子說,我不喜歡吃蛋,給小孩子吃吧。孩子歡快的一擁而上,他們的大快朵頤減輕了我說謊的愧疚感。
其實,我是愛吃水包蛋的,特別是酒釀煮蛋。從小家裡總有親朋好友送的自製酒釀,寒流來臨的夜晚,就用小鍋煮甜酒釀,廚房裡全是甜酒蒸發的香氣。起鍋前敲開蛋殼將生蛋墜入酒釀裡,整顆水包蛋浮在酒釀上,我故意戳破蛋黃,就成了黃金酒釀了。
有些人不敢吃生蛋,如果可以吃生蛋,這裡倒有一個治久咳的秘方:沒進過冰箱的粉紅色土雞蛋,在一個碗裡打勻,灑少許碎冰糖,放一、兩滴麻油,煮沸的熱水澆下去,再用盤子蓋起來,等蛋汁似凝非凝趁熱飲下。母親得了這秘方便做給我和父親吃,味道不錯,也還有效。
我近來感到興趣的是蝦仁烘蛋。新鮮蝦仁先用薑和酒浸過,再用蛋清裹一裹,放進油鍋裡炒熟,撈起備用。打幾個蛋放進油鍋裡翻炒,將熟時放入蝦仁,再翻幾回,兩面都呈現麥黃色,成一個蛋餅。蝦仁埋在蛋裡,保持幼嫩;蛋汁吸收了蝦的鮮甜,特別惹味。
不會做菜的人常會說:「我會炒蛋啊。」連蛋都不會炒的人,煮泡麵時也會放一顆蛋,蛋是這麼親切的東西。或許是受了母親講的故事的影響,我在敲開一隻蛋的時候總會想,這個未知的小宇宙裡,是否曾經發生過一隻雞的可能?
* * *
飛翔的雲雀
我一直不喜歡菜肉餛飩,總覺得它們很粗,皮是厚而硬的,餡也是粗的顆粒,嚼在嘴裡喀啦響,個頭又大,要幾口才能吃完。我認識過一個朋友,是溫州人,認定溫州餛飩是天下最美味的吃食,他帶著我吃過幾次,我把湯逼著喝乾了,餛飩沉在碗底,像臥著一隻隻的白兔子。他嘀咕著:「食量怎麼這麼小?」一邊把餛飩撿出來吃淨了。他也曾疑惑的問我:「不好吃喔?」我搖了搖我的頭,努力的微微笑。我想,我對於菜肉餛飩的感覺,不見得是實質的,卻一定是精神上的。
我家的餛飩比較小,去市場買餛飩皮的時候,一定要指名小而薄的那一種,拿回家之後,便開始剁肉做餡兒。以前肉攤沒有絞肉機,我喜歡聽見砧板上菜刀上上下下的剁肉聲音,那種韻律中有著歡慶的意味,剁到碎肉發黏了,再加進蔥末,或者是韭黃,一齊剁得細碎,用調料拌香了。將一張張餛飩皮攤整齊,把餡料放在四方麵皮的中央,對角包住餡料摺成三角形,再將裹住餡的一邊往三角尖端滾摺幾圈,左右兩邊成了細長的翅膀尖,用一點涼水沾著其中一根翅膀,將另一邊交疊黏住,就成了。從來我捏不成水餃的荷葉邊,卻可以輕易做成一隻隻餛飩,所以,參與感更強些也更雀躍些。
我家的餛飩個頭雖然小,卻仍裹著飽飽的餡兒。我看過外面店裡的餛飩,店家用竹片抹一層薄薄的肉末,便迅捷地裹出一隻餛飩,我算過,總共三秒,一隻餛飩。我看著那樣的神乎其技,幾乎獃了,等候已久的公車從我面前經過,我卻渾然未覺。可是,要吃餛飩,還是愛吃家裡包的。這種薄皮餛飩不能久煮,因為麵皮很容易就化去了,要煮得將化未化,呈現出明瑩的剔透感,其實是需要經驗的。一口咬下去,豐潤的汁液迸出來,齒頰溢香。
那時候家裡有個常常往來的親戚,我們小孩子喊做伯母的,她也有很好的手藝,能包菜肉餛飩。她特別瞧不上我家的小餛飩,而我還懵懂無知,熱烈的拉著她:「來吃餛飩,很好吃的餛飩喔。」她斜著眼瞄了一桌餛飩,頗為嫌棄地說:「那有什麼好吃?你們家就愛吃鼻涕餛飩。」我愣在那裡,半天回不過神。我偷偷看著正忙碌地招呼大家吃餛飩的父母親,彷彿完全沒聽見這樣的嘲諷,仍很起勁的笑著,張羅著芹菜、胡椒和醋。但,我的童稚的世界確實不一樣了,認識到被糟蹋是怎麼一回事,熱情與善意,原來是會遭到這種待遇的。那一整天,過度敏感的我與所有人都保持著距離,因為我頭一次意識到,人會不為什麼原因的傷害另一個人。
後來,去那位伯母家,她包了菜肉餛飩給我們吃,大家都吃得很起勁,而我吃得很少,胃裡鼓得脹脹地,什麼也吃不下,像是噎了太多東西,無法化解。我進入難堪的少女時代,什麼都不如意,不知道自己的價值在哪裡。伯母似有若無的嫌棄和嘲笑,都令我想到鼻涕餛飩,我甚至覺得自己根本就是鼻涕餛飩。
好幾年之後,母親的一位好友來家裡做客,我們叫她阿姨,她笑起來有個美麗的酒窩,她又愛笑,總是開開心心的,那天家裡包餛飩,阿姨一旁幫忙,我們都圍在桌旁,母親忽然說:「妳嘗嘗我們家的鼻涕餛飩。」我一時詫異,原來,母親一直都聽見的。阿姨搖搖頭說:「我們管這種餛飩叫做雲雀餛飩。」「雲雀?」我脫口而出。「嗯。飛在天上的那種小雲雀,體態又美,聲音又好聽。」阿姨滿心喜悅地說。她一定不知道,雲雀餛飩釋放了被憂鬱囚禁的我,使我相信自己展翅便可以高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