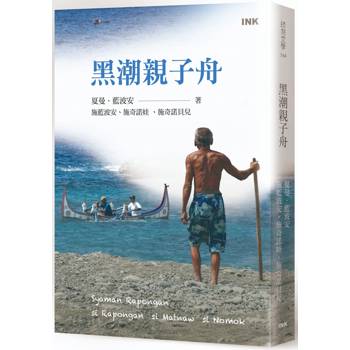航向大海的心願
彷彿心海的底層,某種古老的歌聲一直迴盪的旋律,像是來自最最遙遠的,我部落伊姆洛庫面海左邊,東南方小島傳來的歌聲,時而清澈得怡人悅耳,時而模糊,低沉的朦朧神祕。如此的歌聲已糾纏了我好多的年月。從我捨棄木船,不再使用它做為獵魚的生產工具的時候。我因而思索著,好像自己不使用拼板船舉行招飛魚儀式,不運用木船獵魚,彷彿不是達悟「男人」似的。沒有拼板船的數年中,嚴重困擾著我的意志,是我人生到了中老年紀之後,命格裡的沉重債務,壓著自己千頭萬緒,生活失去了重心,以及頓失踏實感。我因而不時的問自己,沒有自己拼板船,為何讓我感受日常生活,如是沒有重心的彩雲,在天宇隨風遊走:也如是折了雙翼的黑翅飛魚任千億尾沙丁魚嘲諷譏笑。
父親 ,以及他的兄長、小弟,他們三人生前給我的遺訓,說:
「假使我們部落的灘頭沒有了拼板船,那也就是失去了黑翅飛魚神的傳說,等於不是這個島嶼原初的主人了。人類終將老去,終將死亡,當我們死亡之後,你要造一艘拼板船,讓我們古老的灘頭,還有存留一艘木船,以海洋之名,舉行招飛魚的儀式,讓航向大海的灘頭存留應有的尊嚴,在夕陽餘暉的照射下,它會呼喚海神的名字。孩子,你就領著我們的孫子、你的兒子造一艘航向大海的拼板船吧!」
「航向大海的拼板船」,這句話在父親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仙逝的那一天起,就如刀斧深深的鑿刻在我的心海裡,也像一尾俊拔的、游姿優雅的浪人鰺遨遊在我奔騰的血脈裡。
記憶如是每一日的旭日,從兩歲會走路起,父親就領著我瘦弱的身子走向灘頭,站在家族的十人大船上,一同與父祖輩們面對廣袤的海洋,他們高舉似是漏斗般的銀帽,呼喚海洋的名字,呼喊黑翅飛魚的聖名:
「回來吧!回來吧!人之島是祢們孵化出生的原初之島,歸來吧!歸來吧!」
「這是我們人之島島民,對飛魚神的誓言盟約,歸來吧!歸來吧!」
「公雞的鮮血已沾上鵝卵石,浪紋暗流帶進外洋,歸來吧!歸來吧!」
每一年的飛魚招魚祭典,父祖輩們年年重複諸如此類的祈福詞,從小的記憶如是每一日的旭日,最後醞釀成熟,成為我的信仰。
我開始有記憶的時候,應該是我五歲,我的小叔公當舵手船主,那時是一九六二年的夏季,家族雕刻了一艘十人大船,在隔年的招魚祭,父祖輩們深夜出海獵魚,記得他們只撈到三尾飛魚,一尾是留給船主家庭獨吃,那是舵槳手的傳統福利,兩尾就由九個家庭均分享用,每個家庭只分得幾片飛魚鮮肉,但家族裡的男性用兩具陶鍋沸煮兩尾飛魚的鮮湯,放的淡水約莫是六十公升,然後再把飛魚湯平均分享給九個家庭。若是一個家庭有五個,六個小孩,每個小孩也只能分得如小拇指般小的飛魚肉,一大清早,孩子們飢腸轆轆,哭泣是唯一的理由,淚水與魚湯混著飲喝。然而,每一天的鮮魚湯,卻是讓我們知足飽足,讓我們漸漸長大的食物。之後,就是男人們閒聊的時段,昨夜的故事,去年的故事,古老的故事,就在那個時候,如是波浪宣洩般的被重複口述。我的記憶,那是感情的記憶,也是海洋智慧的記憶,也因而成為我的信仰,夢寐以求的願望。
一九六四年進入華語學校,學校就在我的部落內,學生每天依校規,都必須在國民黨的蘭嶼鄉黨部的小廣場排隊集合上學,毗鄰的是一間水泥房、鐵皮屋頂的興隆雜貨店,另一間是木頭樁柱、茅草屋頂的人人商店,這兩個雜貨店是蘭嶼島近代史上,最早進駐在我們島嶼部落的外資,必須使用金錢買東西的店面。無庸質疑的,買東西的顧客全然就是漢族的公務員、軍人,我們在地人只能用眼睛觀賞那些台灣本島貨船運送過來的那些新穎的雜貨,吸著我們潔白的瞳孔,此時我察覺一個有趣的場景是,漢人不時地叮嚀我們,說:
「小鬼們,你們要好好念書,將來我們收復大陸以後,你們就可以拯救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熱的大陸同胞。」
此類的話語,像是不定時的炸彈灌進我們乾淨的耳根、質樸的思維。當時,我認為這些話語是具體的「語言暴力」。島嶼的漢人不時地告訴我們在地人說:「你們達悟人是漢族的一支?」
然而,除去老兵士官等軍人外,學校的老師們,鄉公所的職員們,警員都不曾走進我們的部落,甭提走向海邊灘頭觀賞,從海上捕飛魚豐收歸來的部落人。對於我,我一直弄不清楚,漢人膽怯步向灘頭是什麼原因?
時間到了一九八○年,即使我部落的祖父輩們大多已凋零仙逝,部落海邊灘頭的船隻依然維持在四十艘以上,換言之,家家戶戶都有一艘拼板船,於是沒有拼板船的男人被歸類為次等男人。顯然,廣袤的海洋,近岸魚類生態的多樣是激起島民創造西太平洋獨具一格的拼板船,利於切風切浪的,流線優美的造型。
我從小在家族男性長輩的薰陶下成長,每一年飛魚季節的前期是部落裡獵魚家族夜航持火把,使用掬網撈魚的季節。祖父不時的經常對我耳提面命地說:
「黑翅飛魚神說:『飛魚汛期的四個月期間,不可以獵捕海裡的底棲魚類,這是讓牠們休養生息,海底生活不被干擾。飛魚是迴游魚群,每年的二月到六月游到我們的島嶼。結束之後,才可以獵捕底棲魚類:相對的,我們就不可以捕飛魚,釣鬼頭刀魚了。』孫子,你必須牢記黑翅飛魚神的話語。」當然,是否真的有「飛魚神」的存在,我幾乎未曾質疑過祂的存在,我反倒質疑,我部落頂端那個山腰下的天主堂的神父,說我們是「有罪惡的人」,必須每一年跟「上帝」告解,跟「上帝」說,你犯下的罪孽。我因而也從小質疑西方基督宗教的上帝的存在,也在深深的質疑神父說我們有「罪」。質疑白人跟非白人說:「你們是有罪。」此語也近乎是「暴力語言」。
祖父的這一席話宛如山谷裡的小葉桑樹 ,年年結實纍纍,深深根植在我成長時的歲月記憶,幾乎就是斧刻在我的腦海紋路,心靈裡的生態時鐘,「飛魚汛期嚴禁獵捕底棲魚類,讓它們安靜地覓食生息」,我卻是深信這個,如是自然律則似的,不得違背。我們食用的飛魚,不是身體的富足,而是精神層次的知足。
時光的隧道是讓幼樹長成成樹,成樹變為老樹,終將成為山谷裡的枯木,孕育成土壤的有機肥,再孕育下一代的幼苗。人類何嘗不也如此呢!
那一年,兒子未滿三十歲,若有所思地跟我說:
「爸,我想回家了!」
「回家的海很近,回家的心卻是遙遠的」,我心裡如此思索。孩子在台北也生活了十七年,心靈裡的茫然是必然的,朝九晚五的生活,也必然不是他想追求的生活模式,都市也必然是沒有海洋的風的吹拂,或許兒子也想追求海洋的風的味道吧!也或許在都會,一個海洋民族的孩子心沒有一絲眷戀吧!也如同當年的自己,有相似的心靈處境,就連下的雨水的感受也不同。
「你就回家吧!」我說。
他媽媽的心情,心疼兒子在外外食十多年,總覺得那是她欠兒子青少年成長時的「營養費」。「回家」也或許是媽媽回饋他身體健康的主因,然而,孩子回家可以做什麼呢?這是現實的生存問題!
「回家」,他敬愛的爺爺已仙逝了十多年,帶走了許多許多的傳說,許多許多的傳統技能,許多的島嶼的民族知識。而我,可以給他什麼呢?
「回家」,是這個西太平洋的小島民族共通的課題,另一共通的課題是,這個島嶼是被觀光的,眾多回歸祖島的族人大半從事了民宿經營的自主事業,浮潛,夜觀,解說導覽等等之。朝現代性發展自主事業,推動文化導覽的工作,勢必也是生存之道的選項之一。然而,他必須從頭學習,跟誰學習親海的活動呢?這是一本沒有教學進度的課程,唯有親自下海,上山,身體先到的傳統教育,方可讓兒子體悟,我們在漢族教學體制學習不到的在地知識。於斯,也只能親自帶領兒子上山,下海,甭說,這是一條長遠的路,而我的身體,究竟還能夠支撐多久呢?
父親生前的矯健身影,像濤聲一樣活現闖入我的腦海螢幕,他在山林深谷領我伐木的情境,傳遞著島嶼民族尚未被殖民化的原初深情,一隅沒有被現代化開發傷害的雨林,他的一把斧頭可以輕易的砍伐直徑六十公分的麵包樹,他七十餘歲的伐木身影,流動著古老的勞動者的美學縮影,為了海洋的名字,為了飛魚的聖名,浪人鰺魚的俊俏,建造一艘海洋波浪的玩偶──拼板船,是為了儀式,為了生存,也為了傳承,這正是達悟男性們集體性的海洋使命使然,我見習到了父親那個世代的島民,對雨林生態環境的敬愛,敬畏的質樸信仰,讓我深深的感動,彷彿自己的肉體也為林木樹神的一份子似的。然而,建造一艘拼板船,並非是我個人的意願即可,於斯,某種傳統禮俗的習慣法,悄悄地浮現在心坎,某個心靈角落的壓力,也悄悄的浮生在我漸漸衰退的體能上,這是不可能否認的事實。日升日落是自然界的不變的定律,身體結構,由出生到衰老,當然也是不可改造的定律,但是,我的擔憂不是我體能的問題,而是我孩子們的母親是否允諾我們父子共造一艘船的,「航向大海的心願」的親子舟。
彷彿心海的底層,某種古老的歌聲一直迴盪的旋律,像是來自最最遙遠的,我部落伊姆洛庫面海左邊,東南方小島傳來的歌聲,時而清澈得怡人悅耳,時而模糊,低沉的朦朧神祕。如此的歌聲已糾纏了我好多的年月。從我捨棄木船,不再使用它做為獵魚的生產工具的時候。我因而思索著,好像自己不使用拼板船舉行招飛魚儀式,不運用木船獵魚,彷彿不是達悟「男人」似的。沒有拼板船的數年中,嚴重困擾著我的意志,是我人生到了中老年紀之後,命格裡的沉重債務,壓著自己千頭萬緒,生活失去了重心,以及頓失踏實感。我因而不時的問自己,沒有自己拼板船,為何讓我感受日常生活,如是沒有重心的彩雲,在天宇隨風遊走:也如是折了雙翼的黑翅飛魚任千億尾沙丁魚嘲諷譏笑。
父親 ,以及他的兄長、小弟,他們三人生前給我的遺訓,說:
「假使我們部落的灘頭沒有了拼板船,那也就是失去了黑翅飛魚神的傳說,等於不是這個島嶼原初的主人了。人類終將老去,終將死亡,當我們死亡之後,你要造一艘拼板船,讓我們古老的灘頭,還有存留一艘木船,以海洋之名,舉行招飛魚的儀式,讓航向大海的灘頭存留應有的尊嚴,在夕陽餘暉的照射下,它會呼喚海神的名字。孩子,你就領著我們的孫子、你的兒子造一艘航向大海的拼板船吧!」
「航向大海的拼板船」,這句話在父親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仙逝的那一天起,就如刀斧深深的鑿刻在我的心海裡,也像一尾俊拔的、游姿優雅的浪人鰺遨遊在我奔騰的血脈裡。
記憶如是每一日的旭日,從兩歲會走路起,父親就領著我瘦弱的身子走向灘頭,站在家族的十人大船上,一同與父祖輩們面對廣袤的海洋,他們高舉似是漏斗般的銀帽,呼喚海洋的名字,呼喊黑翅飛魚的聖名:
「回來吧!回來吧!人之島是祢們孵化出生的原初之島,歸來吧!歸來吧!」
「這是我們人之島島民,對飛魚神的誓言盟約,歸來吧!歸來吧!」
「公雞的鮮血已沾上鵝卵石,浪紋暗流帶進外洋,歸來吧!歸來吧!」
每一年的飛魚招魚祭典,父祖輩們年年重複諸如此類的祈福詞,從小的記憶如是每一日的旭日,最後醞釀成熟,成為我的信仰。
我開始有記憶的時候,應該是我五歲,我的小叔公當舵手船主,那時是一九六二年的夏季,家族雕刻了一艘十人大船,在隔年的招魚祭,父祖輩們深夜出海獵魚,記得他們只撈到三尾飛魚,一尾是留給船主家庭獨吃,那是舵槳手的傳統福利,兩尾就由九個家庭均分享用,每個家庭只分得幾片飛魚鮮肉,但家族裡的男性用兩具陶鍋沸煮兩尾飛魚的鮮湯,放的淡水約莫是六十公升,然後再把飛魚湯平均分享給九個家庭。若是一個家庭有五個,六個小孩,每個小孩也只能分得如小拇指般小的飛魚肉,一大清早,孩子們飢腸轆轆,哭泣是唯一的理由,淚水與魚湯混著飲喝。然而,每一天的鮮魚湯,卻是讓我們知足飽足,讓我們漸漸長大的食物。之後,就是男人們閒聊的時段,昨夜的故事,去年的故事,古老的故事,就在那個時候,如是波浪宣洩般的被重複口述。我的記憶,那是感情的記憶,也是海洋智慧的記憶,也因而成為我的信仰,夢寐以求的願望。
一九六四年進入華語學校,學校就在我的部落內,學生每天依校規,都必須在國民黨的蘭嶼鄉黨部的小廣場排隊集合上學,毗鄰的是一間水泥房、鐵皮屋頂的興隆雜貨店,另一間是木頭樁柱、茅草屋頂的人人商店,這兩個雜貨店是蘭嶼島近代史上,最早進駐在我們島嶼部落的外資,必須使用金錢買東西的店面。無庸質疑的,買東西的顧客全然就是漢族的公務員、軍人,我們在地人只能用眼睛觀賞那些台灣本島貨船運送過來的那些新穎的雜貨,吸著我們潔白的瞳孔,此時我察覺一個有趣的場景是,漢人不時地叮嚀我們,說:
「小鬼們,你們要好好念書,將來我們收復大陸以後,你們就可以拯救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熱的大陸同胞。」
此類的話語,像是不定時的炸彈灌進我們乾淨的耳根、質樸的思維。當時,我認為這些話語是具體的「語言暴力」。島嶼的漢人不時地告訴我們在地人說:「你們達悟人是漢族的一支?」
然而,除去老兵士官等軍人外,學校的老師們,鄉公所的職員們,警員都不曾走進我們的部落,甭提走向海邊灘頭觀賞,從海上捕飛魚豐收歸來的部落人。對於我,我一直弄不清楚,漢人膽怯步向灘頭是什麼原因?
時間到了一九八○年,即使我部落的祖父輩們大多已凋零仙逝,部落海邊灘頭的船隻依然維持在四十艘以上,換言之,家家戶戶都有一艘拼板船,於是沒有拼板船的男人被歸類為次等男人。顯然,廣袤的海洋,近岸魚類生態的多樣是激起島民創造西太平洋獨具一格的拼板船,利於切風切浪的,流線優美的造型。
我從小在家族男性長輩的薰陶下成長,每一年飛魚季節的前期是部落裡獵魚家族夜航持火把,使用掬網撈魚的季節。祖父不時的經常對我耳提面命地說:
「黑翅飛魚神說:『飛魚汛期的四個月期間,不可以獵捕海裡的底棲魚類,這是讓牠們休養生息,海底生活不被干擾。飛魚是迴游魚群,每年的二月到六月游到我們的島嶼。結束之後,才可以獵捕底棲魚類:相對的,我們就不可以捕飛魚,釣鬼頭刀魚了。』孫子,你必須牢記黑翅飛魚神的話語。」當然,是否真的有「飛魚神」的存在,我幾乎未曾質疑過祂的存在,我反倒質疑,我部落頂端那個山腰下的天主堂的神父,說我們是「有罪惡的人」,必須每一年跟「上帝」告解,跟「上帝」說,你犯下的罪孽。我因而也從小質疑西方基督宗教的上帝的存在,也在深深的質疑神父說我們有「罪」。質疑白人跟非白人說:「你們是有罪。」此語也近乎是「暴力語言」。
祖父的這一席話宛如山谷裡的小葉桑樹 ,年年結實纍纍,深深根植在我成長時的歲月記憶,幾乎就是斧刻在我的腦海紋路,心靈裡的生態時鐘,「飛魚汛期嚴禁獵捕底棲魚類,讓它們安靜地覓食生息」,我卻是深信這個,如是自然律則似的,不得違背。我們食用的飛魚,不是身體的富足,而是精神層次的知足。
時光的隧道是讓幼樹長成成樹,成樹變為老樹,終將成為山谷裡的枯木,孕育成土壤的有機肥,再孕育下一代的幼苗。人類何嘗不也如此呢!
那一年,兒子未滿三十歲,若有所思地跟我說:
「爸,我想回家了!」
「回家的海很近,回家的心卻是遙遠的」,我心裡如此思索。孩子在台北也生活了十七年,心靈裡的茫然是必然的,朝九晚五的生活,也必然不是他想追求的生活模式,都市也必然是沒有海洋的風的吹拂,或許兒子也想追求海洋的風的味道吧!也或許在都會,一個海洋民族的孩子心沒有一絲眷戀吧!也如同當年的自己,有相似的心靈處境,就連下的雨水的感受也不同。
「你就回家吧!」我說。
他媽媽的心情,心疼兒子在外外食十多年,總覺得那是她欠兒子青少年成長時的「營養費」。「回家」也或許是媽媽回饋他身體健康的主因,然而,孩子回家可以做什麼呢?這是現實的生存問題!
「回家」,他敬愛的爺爺已仙逝了十多年,帶走了許多許多的傳說,許多許多的傳統技能,許多的島嶼的民族知識。而我,可以給他什麼呢?
「回家」,是這個西太平洋的小島民族共通的課題,另一共通的課題是,這個島嶼是被觀光的,眾多回歸祖島的族人大半從事了民宿經營的自主事業,浮潛,夜觀,解說導覽等等之。朝現代性發展自主事業,推動文化導覽的工作,勢必也是生存之道的選項之一。然而,他必須從頭學習,跟誰學習親海的活動呢?這是一本沒有教學進度的課程,唯有親自下海,上山,身體先到的傳統教育,方可讓兒子體悟,我們在漢族教學體制學習不到的在地知識。於斯,也只能親自帶領兒子上山,下海,甭說,這是一條長遠的路,而我的身體,究竟還能夠支撐多久呢?
父親生前的矯健身影,像濤聲一樣活現闖入我的腦海螢幕,他在山林深谷領我伐木的情境,傳遞著島嶼民族尚未被殖民化的原初深情,一隅沒有被現代化開發傷害的雨林,他的一把斧頭可以輕易的砍伐直徑六十公分的麵包樹,他七十餘歲的伐木身影,流動著古老的勞動者的美學縮影,為了海洋的名字,為了飛魚的聖名,浪人鰺魚的俊俏,建造一艘海洋波浪的玩偶──拼板船,是為了儀式,為了生存,也為了傳承,這正是達悟男性們集體性的海洋使命使然,我見習到了父親那個世代的島民,對雨林生態環境的敬愛,敬畏的質樸信仰,讓我深深的感動,彷彿自己的肉體也為林木樹神的一份子似的。然而,建造一艘拼板船,並非是我個人的意願即可,於斯,某種傳統禮俗的習慣法,悄悄地浮現在心坎,某個心靈角落的壓力,也悄悄的浮生在我漸漸衰退的體能上,這是不可能否認的事實。日升日落是自然界的不變的定律,身體結構,由出生到衰老,當然也是不可改造的定律,但是,我的擔憂不是我體能的問題,而是我孩子們的母親是否允諾我們父子共造一艘船的,「航向大海的心願」的親子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