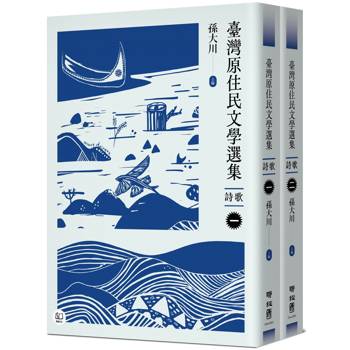▉莫那能/〈歸來吧,莎烏米〉(一九八九)
Maljaljaves Mulaneng,一九五六年生,臺東縣達仁鄉安朔部落(Aljungic)排灣族。一九七九年因車禍使眼疾惡化,而至全盲。一九八四年與胡德夫等人成立臺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長期參與黨外運動、原住民社會運動。一九九六年莫那能在臺北成立「阿能按摩院」,九二一大地震時亦擔任「九二一原住民部落工作隊召集人」。
莫那能在原運時期,受陳映真、楊渡等人的鼓勵和啟發,開始以口述吟誦方式進行詩歌創作,一九八九年出版《美麗的稻穗》,是臺灣原住民族文學中第一本詩集,表現了詩人對族群處境的深刻關懷。著有《美麗的稻穗》、《一個臺灣原住民的經歷》等書。
〈歸來吧,莎烏米〉
檳榔樹的葉尖刺頂著圓月
明亮的光穿過了柴窗
照著準備上山的哥哥
照著屋角的背簍和彎刀
背上背簍喲
裝滿小米的種子和芋頭
束緊腰頭喲
繫上祖父遺傳下來的彎刀
上山去喲上山去
雞啼已在催促沉重的步履
早春,早春的空氣
像是剛從地窖起出的小米酒一般
那開封的清香和著情歌
在百蟲交鳴的山徑旁沿途伴我上山
上山去喲上山去
莎烏米啊莎烏米
唱著妹妹的名字
不論太陽在雲海裡經過幾次的升落
不論月亮在夜空中經過幾次的圓缺
我都不疲倦
莎烏米啊莎烏米
唱著妹妹的名字
我將芋頭一粒粒地埋在土層裡
將小米一把把地播撒在田間
興奮地等待未來的豐收
哥哥帶著彎刀和火種
翻過一山又一山
莎烏米啊莎烏米
一遍又一遍地唱著妳的名字
妳的名字喲是永遠的食糧
像土層裡的芋頭
像田間的小米
莎烏米啊莎烏米
哥哥帶著背簍和種子
翻過一山又一山
在夜鴞咕嚕聲的引領下
探索古老的神話和傳説
隨著淙淙的泉水聲
思念離鄉多年的莎烏米
啊,被退伍金買走的姑娘
當妳想起山上的哥哥時
是否也一遍遍地唱著那首情歌:
妳是誰呀妳是誰
站在高岡上對著我唱
妳的人兒妳的歌聲
漂亮得超過了彩虹
你是誰呀你是誰
站在高岡上對著我唱
你的人兒你的歌聲
雄壯得超過了瀑布
啊,哥哥的思念
被綿延無際的山嶺圍困
被此起彼落的泉聲纏繞
日復一日,一山又一山
通過了夏季的炎熱和暴風雨
黝黑的身體更加健壯了
厚實的手足也結滿了繭
終於,在秋蟬頌夏的歌聲中
芋頭已累累碩大
田間的小米也翻起了鼓鼓的金浪
歸來吧,莎烏米
讓我們一起合唱豐收的歡歌
歸來吧,莎烏米
讓我摘下一片亮綠的芋葉盛滿晶瑩的露珠做聘禮
讓我釀一甕甜美的小米酒
用傳統的共飲杯和妳徹夜暢飲
莎烏米啊莎烏米
哥哥帶著彎弓和火種懷著不滅的愛和希望
一山又一山地
一遍又一遍地唱著妳的名字
歸來吧歸來
歸到我們盛產小米和芋頭的家園吧!
▉林志興/〈時田釀的愛情酒〉(二〇一一)
Agilasay Pakawyan,一九五八年生於臺東,父親來自卑南族南王部落,母親為阿美族人,妻子為屏東的排灣族人,家庭組和多元。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學士、碩士、博士。
自青年時期便參與詩歌與文學創作及卑南遺址的搶救工作,後來受邀到臺東史前博物館工作,擔任過助理研究員、研究典藏組主任、南科分館籌備處主任、副館長等多項職務,發表過多首詩作及研究論文。曾自影印詩集《檳榔詩稿》與排灣族詩人溫奇互為唱和,而早期〈鄉愁〉、〈我們是同胞〉、〈穿上彩虹衣〉等作品,經由金曲歌王陳建年譜曲演唱而廣為流行。另著有詩集《族韻鄉情》。
〈時田釀的愛情酒〉
被稱作「時田」
我以為那是殖民的標記
是皇民化的烙印
萬萬沒想到
那是你們愛情的印記
在冰冷的殖民主義者面前
誰說我們只是被動
男的Tuki和女的Daduway
結合為Tuki-da
再轉音為ときだ
最後標上時田的漢文
誰也看不出那是愛情的配方
如詩如酒的芳香
只會心地流轉在孩子們的口語裡
成為新的傳說
被稱作「時田」
原來是你們愛情的印記
在冰冷的殖民主義者面前
誰說我們只是被動
這愛情的配方
如詩如酒芳香孩子們的心
後記: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四日在二叔Toyosi(林仁誠)Papuru(寶桑部落)的居所裡,我聽到他向日本學者山本芳美解釋,咱們家日本姓氏「時田」的由來。
二叔說:「會取時田(ときだ)兩個字的原因,是我的父親Tuki把他的名字和我的母親的名字Daduway的第一個音Da放在一起的關係,Tuki加Da等於Tukida,變成了我們的日本姓。」當時在旁聆聽的我直誇祖父的聰明,還未領會其中更深的寓意。這新鮮的故事在我腦海裡晃盪了幾天,居然愈陳愈香,讓我從名字的故事裡聞到愛情釀的酒香味,原來我那從未謀面的祖父和數年前才以高齡九十五逝世的祖母,竟然相愛得那麼深刻。
原來祖父藉著日本皇民化的歷史大戲,悄悄地把自己對妻子的真愛刻到不得不配領的姓氏裡去;他讓兩個人的名字緊連在一起,讓那新起的姓氏中「有我也有你」,深刻到讓子子孫孫們都能透過這個姓氏記住他倆的結合才有我們,我們的繁衍是對他們永生的紀念。不過誰也沒有料到歷史的弔詭,那個外來的、強勢的日本政權只維持了五十年,而讓我們掛勾的日本文化,也只在我們的家族史裡渡了二代就消失了,但當年Tuki藉著自我取名時刻寫進去的愛情,卻美麗透頂。
也許Tuki加Da幻化為「時田」(ときだ)的文字排列組合只是一場偶然(到底,對他們來說文字書寫是新鮮的事,取一個血緣主義的姓名代表自己更是新鮮的事),但是Tuki加Da的聲音和「時」與「田」的文字結合裡,卻充滿愛情的宣示,宣示「我倆永遠在一起」,透過字的選取,更預告愛情與生活的田園會在時間和空間的交錯結合下發展與延續。
雖然,祖父識字不多,但無妨他胸腹中天生富有的浪漫與詩意。也難怪,我聽說當祖父罹患肝病之際,我們的祖母寧願「傾家蕩產」,賣田賣地,盡一切可能力挽祖父於世,那怕片刻也行。但,天地不仁,即使散盡他們曾經共同擁有的田園,就是不讓她如願繼續擁有相處的時間。田留不住,時間卻證明了無形而永存的愛情。
我的祖母,為他,我的祖父,終身未再依卑南之俗招贅新夫。那時間之河裡發酵的愛情田園,始終在他們真實生活和相互記憶的時光裡醞釀。「時田」這個姓氏,雖然只是偶然地在我們pakawyan家族歷史的長河裡漂過,一九四五年之後,又在新的歷史洪流、中華國族主義漢化運動之中,被「林」字替代,無緣伴隨pakawyan的子孫繼續前進,但我們仍要記住這兩個字的組合,重點不在歷史,而是因為那兩個字有Tuki和Daduway堅貞又美麗的愛情灌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