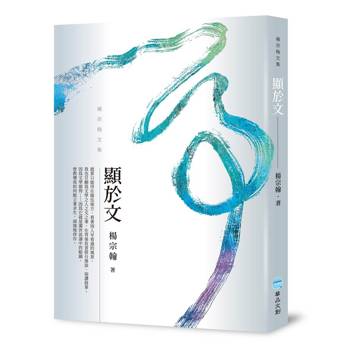〈人不耕莘枉少年——以寫作會為中心的文學私地圖〉
以時間而論,與同世代眾多早慧的創作者相較,我的文學啟蒙相當遲緩;從空間而觀,雖自幼居住在台北文山區,我也是很晚才知道「台灣韓波」詩人黃荷生、小說家朱西甯住家,以及曾遭警總包抄的「神州詩社」皆步行可至。時間與空間都不站在平凡的我這邊,幸好還有辛亥路上的耕莘青年寫作會為人生定錨,讓慘綠少年得以認識文學之繽紛多彩。
想報名參加文學活動,最初起於自己對「作家」身分的好奇。高二獲得《明道文藝》與《中央日報》合辦的全國學生文學獎首獎,頒獎典禮上我才初次見到評審黃永武、鄭明娳等「學者作家」;高三穿著卡其校服直奔圓山飯店,在聯合報系主辦的「四十年來中國文學會議」上,更首度看到高行健等「海外作家」;同年參與在陽明山華興中學旁一所教會的台灣文藝營,換成第一次認識這麼多「本土作家」。上述零星接觸經驗,顯然無法滿足我亟欲認識「作家本質」的渴望。偏偏自己雖對台上侃侃而談的作家們充滿敬意,卻只是低頭抄筆記一族,從不敢貿然提問或索取簽名。像這樣本性孤僻、寧願抱字取暖的人,高三升大一前夕卻想跟人合辦「植物園」現代詩社及詩刊,簡直是自找麻煩。詩社要怎麼組?稿子該怎麼約?文壇長什麼樣?不是校刊的文學刊物該怎麼編?……千頭萬緒,無一通曉,只好先報名聯合文學文藝營跟耕莘寫作會活動,多少帶著賭氣兼賭運的心態。當時的聯文偏重短期密集講授,耕莘則是長期互動課程,我遂選擇成為一屆聯文生、四年耕莘人。
年紀太輕、識見太淺、膽子太小,我跟作家們還是搭不上話,幸好在別處另有收穫。興隆路住家雖離公館不遠,但直到進了耕莘,我才知道這一帶竟有許多秘密基地──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剛升大學時我的文學私人地圖,完全是以耕莘寫作會為中心來繪製。若唐山書店算是老窟,甫創辦的女書店便是新巢,再加上耕莘所設「寫作小屋」,連結起來便是座偌大書房,負責餵養我知識,一新我視野。小屋所藏上個世紀七、八〇年代詩集甚多,除了提供我自行閱讀補課的資源,亦開啟我日後蒐購文學舊書之動機。連「植物園」成立後的第一次聚會,都是向耕莘商借小屋舉行。迄今我仍記得,後來遠赴南非的第二期主編林怡翠、不幸早逝的封面設計劉信宏,與大夥或坐或躺在塌塌米上的身影。「植物園」的定期聚會隨後雖改往波西米亞人咖啡館,依舊位於耕莘文教院後巷,直到該店搬往長安西路現址。
除了地理位置上的文學私地圖,以寫作會成員為中心的「耕莘人地圖」對我更顯重要。因為參加耕莘,遂得以認識許多欲把金針度與人的文學良師,以及一批結交至今的人生益友。我的九〇年代文學旅途,正是在陸神父、楊昌年、白靈、陳銘磻等師長呵護甚至縱容下開展,也有幸獲得已享文名的凌明玉、管仁健等「同班同學」指正扶持。其中擔任寫作會秘書長暨《旦兮》雜誌主編的黃玉鳳(詩人葉紅),對我個人而言堪稱亦師亦姐,她更具體示範了何謂耕莘人的多才多藝。二〇〇四年某日突然接到玉鳳姐於上海辭世、即將舉辦追思會的電郵,我在震驚錯愕之餘,也徹底斷了與寫作會的最後聯繫。
此後我便成為耕莘失聯份子,不曾再踏入寫作會一步。路過那棟被拆除的大樓時,亦不免自嘲關卿何事、莫生感嘆。當過輔導員、得過文學獎、演過小劇場……我的人生中有不少與耕莘相關的小事,甚至曾因為寫作會要在聖本篤修道院舉辦文藝營,生平才首度造訪淡水。豈能料到二十年後,我竟有緣在淡江大學任教?人不耕莘枉少年,很慶幸在九〇年代初識文學的「青春期」,我也曾經那麼耕莘。
寫作會所在地耕莘文教院,藏有我十七到二十一歲最美好的文學經驗——愛與錯愛,離世友人,詩的聲光,植物園詩社,而今一切俱往矣。其實辛亥路到新生南路一帶文學作家及藝文團體「密度」頗高,耕莘附近還曾有文殊院寫作班,我在那裡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了林燿德(一九六二~一九九六)。現在連這個寫作班的「遺址」都不好找了,倒是各大學自辦的寫作營跟校內開設的創作課越來越多。學院外的民間寫作班曾有輝煌的過去,至盼它們都能挺過不確定的未來。
〈詩是永遠的初戀:從為詩狂,到隱於詩〉
我常跟學生說:能夠為詩而瘋狂,是多麼幸福的青春。跟現在吾輩只能困在帳單房貸、考績評等、體衰保健的議題相較,他們的生活樣態或日常作息,還真是讓人羨慕。我讀大學時,絕不會錯過**每個月「詩的星期五」,像是追星族一樣看著洛夫等前輩在台上朗誦,整個氣氛迷人到極點,空氣中都是幾分苦澀幾分甜的詩味。白靈老師在耕莘小劇場辦「詩的聲光」,可能是缺人吧,竟把我也拉去演。我只好應付一下必修的聲韻學期中考,飛快繳卷後騎機車急馳下山,就是為了趕演詩劇。林煥彰〈十五‧月蝕〉原本不算難懂:「八點鐘,月在我二樓/企圖穿窗而過//十五那個晚上,/我捉住了她/所以,你們就有了一次/月蝕//而午夜/她將衣裳留在我床上/所以,那晚/她/特別明亮」,而我被導演要求先屈身蹲在一個橘黃色大筒子裡,算好時間再跳出來,大跨步蟹行橫走。我到現在都還不知道在演什麼,只覺得肢體可以這樣展示,既害羞,又得意。近日發覺YouTube上竟還找得到三十年前的演出影像紀錄,幸好畫質甚差,什麼都看不清楚。果然印證了,模糊的青春才是最美。
那次「詩的聲光」跟我們一起登台瘋詩的,還有大前輩管管。這位文學史上超級大玩家兩年前逝世,享耆壽92歲。那一輩資深詩人都對我極好,甚至有時容忍我刻意胡搞,譬如把寫實風格的詩投稿給《創世紀》,把不避艱澀或超現實風的詩投稿給《笠》。年輕氣盛的我,不知道從哪借來的勇氣,覺得別人都搞不懂,所以自行翻譯了「意象派」的信條,投稿後也蒙《笠》採納刊出。我在2000年這篇〈意象派諸信條新譯〉中寫道:「古有所謂『詩辯』者;生此紛紛詩壇,擾擾詩潮之世,以此『譯辯』明志,誰云不宜?余豈好譯哉?余不得已也!」現在看來,就是兩個字:屁孩。
雖然樂於為詩瘋狂,但我後來幾乎完全走向文學評論,很少寫詩。立志要寫《台灣新詩史》後,更要求自己把創作放到這書出版之後再談。沒想到這本新詩史花了廿年才問世,中間實在蹉跎耽誤太久。去年既然出版了新詩史,今年我就該重回創作隊伍,遂推出第一部個人詩集《隱於詩》。遲到總比不到好。人生已過中場,不能浪擲耗費。回到寫作隊伍,容我隱藏於詩。
〈行動派的機智編輯生活:像我這樣一個編輯〉
六年級世代的文學人,有不少曾經或正在以編輯為業。這個「業」可以是職業,可以是事業,也可以是志業。我這幾年對「以編輯為業」很感興趣,故先後主編了《大編時代》與《話說文學編輯》兩本書,欲藉助眾人之力,一方面重現過往瘂弦等偉大編輯的事功與啟示;另一方面也想激勵一下吾輩或更年輕的文學人,別再一天到晚喊著或自比為「小編」。小編滿街走,氣短志不高,還能夠承擔什麼大任?「大編」之所以為大,是大在心態,大在視野,大在對於編輯這份職業/事業/志業的企圖與實踐。文藝可以成學,編輯足以成家,所以我主張這些大編應該被正名為「編輯家」。其言行必須記錄,其編事值得研究。
這些編輯家中兼有詩人身分,於編事及創作上皆卓然成家者,至少有楊牧、向明、張默、瘂弦、蕭蕭、白靈、向陽……我認為應該冠他們以「詩人編輯家」榮銜。當我在擔任編輯、講授編輯、研究編輯、想像編輯時,這些「詩人編輯家」都是學習的模版跟最好的典範。不過世代有別,環境殊異,我們這些歲數坐四望五的「六年級生」,畢竟再也回不去前行代的紙本媒體盛世了。我在公元兩千年前後開始接觸編務,何其有幸,見證到紙媒王國的夕陽餘暉;在編輯工作之餘,還因緣際會成為部落格或新聞台的首批投入者。在homepage或blog上,每個人都突然變成(自己的)總編輯,過癮極了。可以單槍匹馬,可以詩妖8P,一時之間好不熱鬧。豈料廿年過去了,一切都變成失效連結,再怎麼refresh都杳無蹤影。想起來也蠻可怕的:原來網路世界遇到金流斷絕,任何遺跡都可能被完全移除。
像我這樣一個編輯,廿年過去了仍然在編編寫寫,樂此不疲。昔日我曾編過《勁晚報》副刊,待過出版社與雜誌社,邊做邊學該如何編輯、企劃、業務、行銷、策展;現在既主編學報《臺灣詩學學刊》,又替中華民國筆會英文季刊《譯之華》(Florescence)選稿件與訂專題,偶爾也受邀策劃雜誌或協力專案。雖然身居學院圍牆之內,但能夠藉此維持編輯手感,我很樂意,也很珍惜。尤其這些編選企劃都是文學之事,而我本來就很想終生作一名文學編輯——堂堂正正、不容蔑視、不需理由的文學編輯。因為我篤信:文學,就是最好的理由。
以時間而論,與同世代眾多早慧的創作者相較,我的文學啟蒙相當遲緩;從空間而觀,雖自幼居住在台北文山區,我也是很晚才知道「台灣韓波」詩人黃荷生、小說家朱西甯住家,以及曾遭警總包抄的「神州詩社」皆步行可至。時間與空間都不站在平凡的我這邊,幸好還有辛亥路上的耕莘青年寫作會為人生定錨,讓慘綠少年得以認識文學之繽紛多彩。
想報名參加文學活動,最初起於自己對「作家」身分的好奇。高二獲得《明道文藝》與《中央日報》合辦的全國學生文學獎首獎,頒獎典禮上我才初次見到評審黃永武、鄭明娳等「學者作家」;高三穿著卡其校服直奔圓山飯店,在聯合報系主辦的「四十年來中國文學會議」上,更首度看到高行健等「海外作家」;同年參與在陽明山華興中學旁一所教會的台灣文藝營,換成第一次認識這麼多「本土作家」。上述零星接觸經驗,顯然無法滿足我亟欲認識「作家本質」的渴望。偏偏自己雖對台上侃侃而談的作家們充滿敬意,卻只是低頭抄筆記一族,從不敢貿然提問或索取簽名。像這樣本性孤僻、寧願抱字取暖的人,高三升大一前夕卻想跟人合辦「植物園」現代詩社及詩刊,簡直是自找麻煩。詩社要怎麼組?稿子該怎麼約?文壇長什麼樣?不是校刊的文學刊物該怎麼編?……千頭萬緒,無一通曉,只好先報名聯合文學文藝營跟耕莘寫作會活動,多少帶著賭氣兼賭運的心態。當時的聯文偏重短期密集講授,耕莘則是長期互動課程,我遂選擇成為一屆聯文生、四年耕莘人。
年紀太輕、識見太淺、膽子太小,我跟作家們還是搭不上話,幸好在別處另有收穫。興隆路住家雖離公館不遠,但直到進了耕莘,我才知道這一帶竟有許多秘密基地──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剛升大學時我的文學私人地圖,完全是以耕莘寫作會為中心來繪製。若唐山書店算是老窟,甫創辦的女書店便是新巢,再加上耕莘所設「寫作小屋」,連結起來便是座偌大書房,負責餵養我知識,一新我視野。小屋所藏上個世紀七、八〇年代詩集甚多,除了提供我自行閱讀補課的資源,亦開啟我日後蒐購文學舊書之動機。連「植物園」成立後的第一次聚會,都是向耕莘商借小屋舉行。迄今我仍記得,後來遠赴南非的第二期主編林怡翠、不幸早逝的封面設計劉信宏,與大夥或坐或躺在塌塌米上的身影。「植物園」的定期聚會隨後雖改往波西米亞人咖啡館,依舊位於耕莘文教院後巷,直到該店搬往長安西路現址。
除了地理位置上的文學私地圖,以寫作會成員為中心的「耕莘人地圖」對我更顯重要。因為參加耕莘,遂得以認識許多欲把金針度與人的文學良師,以及一批結交至今的人生益友。我的九〇年代文學旅途,正是在陸神父、楊昌年、白靈、陳銘磻等師長呵護甚至縱容下開展,也有幸獲得已享文名的凌明玉、管仁健等「同班同學」指正扶持。其中擔任寫作會秘書長暨《旦兮》雜誌主編的黃玉鳳(詩人葉紅),對我個人而言堪稱亦師亦姐,她更具體示範了何謂耕莘人的多才多藝。二〇〇四年某日突然接到玉鳳姐於上海辭世、即將舉辦追思會的電郵,我在震驚錯愕之餘,也徹底斷了與寫作會的最後聯繫。
此後我便成為耕莘失聯份子,不曾再踏入寫作會一步。路過那棟被拆除的大樓時,亦不免自嘲關卿何事、莫生感嘆。當過輔導員、得過文學獎、演過小劇場……我的人生中有不少與耕莘相關的小事,甚至曾因為寫作會要在聖本篤修道院舉辦文藝營,生平才首度造訪淡水。豈能料到二十年後,我竟有緣在淡江大學任教?人不耕莘枉少年,很慶幸在九〇年代初識文學的「青春期」,我也曾經那麼耕莘。
寫作會所在地耕莘文教院,藏有我十七到二十一歲最美好的文學經驗——愛與錯愛,離世友人,詩的聲光,植物園詩社,而今一切俱往矣。其實辛亥路到新生南路一帶文學作家及藝文團體「密度」頗高,耕莘附近還曾有文殊院寫作班,我在那裡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了林燿德(一九六二~一九九六)。現在連這個寫作班的「遺址」都不好找了,倒是各大學自辦的寫作營跟校內開設的創作課越來越多。學院外的民間寫作班曾有輝煌的過去,至盼它們都能挺過不確定的未來。
〈詩是永遠的初戀:從為詩狂,到隱於詩〉
我常跟學生說:能夠為詩而瘋狂,是多麼幸福的青春。跟現在吾輩只能困在帳單房貸、考績評等、體衰保健的議題相較,他們的生活樣態或日常作息,還真是讓人羨慕。我讀大學時,絕不會錯過**每個月「詩的星期五」,像是追星族一樣看著洛夫等前輩在台上朗誦,整個氣氛迷人到極點,空氣中都是幾分苦澀幾分甜的詩味。白靈老師在耕莘小劇場辦「詩的聲光」,可能是缺人吧,竟把我也拉去演。我只好應付一下必修的聲韻學期中考,飛快繳卷後騎機車急馳下山,就是為了趕演詩劇。林煥彰〈十五‧月蝕〉原本不算難懂:「八點鐘,月在我二樓/企圖穿窗而過//十五那個晚上,/我捉住了她/所以,你們就有了一次/月蝕//而午夜/她將衣裳留在我床上/所以,那晚/她/特別明亮」,而我被導演要求先屈身蹲在一個橘黃色大筒子裡,算好時間再跳出來,大跨步蟹行橫走。我到現在都還不知道在演什麼,只覺得肢體可以這樣展示,既害羞,又得意。近日發覺YouTube上竟還找得到三十年前的演出影像紀錄,幸好畫質甚差,什麼都看不清楚。果然印證了,模糊的青春才是最美。
那次「詩的聲光」跟我們一起登台瘋詩的,還有大前輩管管。這位文學史上超級大玩家兩年前逝世,享耆壽92歲。那一輩資深詩人都對我極好,甚至有時容忍我刻意胡搞,譬如把寫實風格的詩投稿給《創世紀》,把不避艱澀或超現實風的詩投稿給《笠》。年輕氣盛的我,不知道從哪借來的勇氣,覺得別人都搞不懂,所以自行翻譯了「意象派」的信條,投稿後也蒙《笠》採納刊出。我在2000年這篇〈意象派諸信條新譯〉中寫道:「古有所謂『詩辯』者;生此紛紛詩壇,擾擾詩潮之世,以此『譯辯』明志,誰云不宜?余豈好譯哉?余不得已也!」現在看來,就是兩個字:屁孩。
雖然樂於為詩瘋狂,但我後來幾乎完全走向文學評論,很少寫詩。立志要寫《台灣新詩史》後,更要求自己把創作放到這書出版之後再談。沒想到這本新詩史花了廿年才問世,中間實在蹉跎耽誤太久。去年既然出版了新詩史,今年我就該重回創作隊伍,遂推出第一部個人詩集《隱於詩》。遲到總比不到好。人生已過中場,不能浪擲耗費。回到寫作隊伍,容我隱藏於詩。
〈行動派的機智編輯生活:像我這樣一個編輯〉
六年級世代的文學人,有不少曾經或正在以編輯為業。這個「業」可以是職業,可以是事業,也可以是志業。我這幾年對「以編輯為業」很感興趣,故先後主編了《大編時代》與《話說文學編輯》兩本書,欲藉助眾人之力,一方面重現過往瘂弦等偉大編輯的事功與啟示;另一方面也想激勵一下吾輩或更年輕的文學人,別再一天到晚喊著或自比為「小編」。小編滿街走,氣短志不高,還能夠承擔什麼大任?「大編」之所以為大,是大在心態,大在視野,大在對於編輯這份職業/事業/志業的企圖與實踐。文藝可以成學,編輯足以成家,所以我主張這些大編應該被正名為「編輯家」。其言行必須記錄,其編事值得研究。
這些編輯家中兼有詩人身分,於編事及創作上皆卓然成家者,至少有楊牧、向明、張默、瘂弦、蕭蕭、白靈、向陽……我認為應該冠他們以「詩人編輯家」榮銜。當我在擔任編輯、講授編輯、研究編輯、想像編輯時,這些「詩人編輯家」都是學習的模版跟最好的典範。不過世代有別,環境殊異,我們這些歲數坐四望五的「六年級生」,畢竟再也回不去前行代的紙本媒體盛世了。我在公元兩千年前後開始接觸編務,何其有幸,見證到紙媒王國的夕陽餘暉;在編輯工作之餘,還因緣際會成為部落格或新聞台的首批投入者。在homepage或blog上,每個人都突然變成(自己的)總編輯,過癮極了。可以單槍匹馬,可以詩妖8P,一時之間好不熱鬧。豈料廿年過去了,一切都變成失效連結,再怎麼refresh都杳無蹤影。想起來也蠻可怕的:原來網路世界遇到金流斷絕,任何遺跡都可能被完全移除。
像我這樣一個編輯,廿年過去了仍然在編編寫寫,樂此不疲。昔日我曾編過《勁晚報》副刊,待過出版社與雜誌社,邊做邊學該如何編輯、企劃、業務、行銷、策展;現在既主編學報《臺灣詩學學刊》,又替中華民國筆會英文季刊《譯之華》(Florescence)選稿件與訂專題,偶爾也受邀策劃雜誌或協力專案。雖然身居學院圍牆之內,但能夠藉此維持編輯手感,我很樂意,也很珍惜。尤其這些編選企劃都是文學之事,而我本來就很想終生作一名文學編輯——堂堂正正、不容蔑視、不需理由的文學編輯。因為我篤信:文學,就是最好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