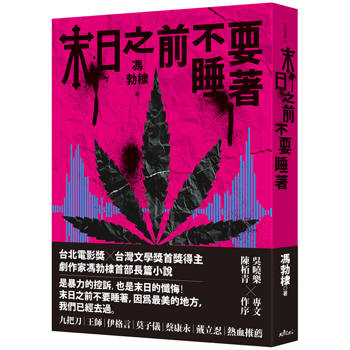末日以前
有一則美麗的傳說,叫做新天新地。
據說,人在經歷了痛苦漫長的人生後,會在生命終結後走入一片嶄新的世界。在那,日月照耀,河水喧騰,鬱鬱蒼蒼,萬物和諧相處。人們肢體健壯,身心開朗。在那,陽光總暖暖地穿透眼皮,暈出一片燦紅,再浸入肌膚,沈澱於靈魂深處。在那,冰寒不刺骨,焰火不燒燙;行走者必定抵達,告別者注定遺忘。
在新天新地中,淚水在臉頰上流淌出一道刻痕,我們卻再也想不起來哭泣的理由;痛苦在我們靈魂上烙印了美麗的紋路,我們卻不必再體會痛苦本身;遺憾在我們心靈中鍛鍊出堅韌的哀傷,我們卻已經不遺憾了。
在新天新地中,人們被拋出暫存界,墜入了無始無終的永恆。永恆中,珍愛的都無限巨大,心碎的都無限渺小。填補一片無垠無際的,名之為愛。
很美的傳說,但在新天新地來臨之前,我們得先度過今生。
而今生,有時也會有著不輸新天新地的美好時光,像他們,像當時的他們。母親偶爾缺席,父女兩人也能歡快無憂、自由自在。
那時,父女兩人會一起站在地與海的邊緣,一起朝海的對岸大喊「我們在這!」他們會一起打羽毛球,一起對著高掛空中的羽毛球說「敢下來,我就再把你打飛!」他偷偷把口香糖黏在她的頭髮上,她偷偷拔他的腿毛;她會為了氣球不會飛而鬧脾氣,他會翻遍整座城市只為獲得一顆氫氣球然後放手;她的笑容像是在臉頰上播放的可愛電影,雙方的笑聲成了動人的配樂;他載著她啟程去遠方,不在乎遠方在哪;他希望她永遠不要長大,她不知道他會變老。
那段時光好輕巧、好可愛,父女像情人。那時,嘴唇還可以拿來親吻,手掌可以拿來緊握;那時,溫柔與衝突都尚未失控,還能恰如其分地存在與散置。
只是,生命有時會粗暴地將一切終止,當我們以為正朝向無垠的天際飛翔,卻撞到了一堵畫著白雲的藍色牆面。航道軋然而止,我們朝下墜落。當翅膀再也不飛,人就只得蹣跚地用走的了。
脆弱無靠之時,我們渴望新天新地,只是新天新地只發生在末日之後。
而在末日之前,我們得先迎向末日。
在小茜十歲那年,母親離家出走,音訊全無,再也沒有回來了。
溫馨的家庭劇變成一部殘酷的電影,完整的家頓時只由戴立齊與小茜兩人來展演。名之為家的碉堡坍塌了,磚瓦如雪花般紛飛下落。她開始躲避,他則鬆開了她的手,停在崩塌處等著被埋滅。
戴立齊崩解了,自那之後,清醒是為了喝醉,醉倒是為了醒來,再迎接下一次的迷茫。他把人生活得像幅雜亂無章的畫、一首走調跑拍的歌。他捲縮進封閉的世界,中斷與人的社交。他唯一有的,就只有小茜了。事情剛發生時,兩人還會一起去看海,只是戴立齊再也不笑了;後來,戴立齊說騎車一個小時太累,海聲從此只在夢中迴盪;他們偶爾會打羽毛球,只是球拍變重了;有時,小茜仰望著陽光之下、飄蕩在半空中的球,會輕輕對它說,「地表太多的憂傷,自己飛走吧。」
小茜恨媽媽,也恨自己沒有療癒爸爸的能力。戴立齊會在小茜面前將她母親形容成蕩婦,小茜不喜歡聽,也不願如此相信。但為了成為爸爸的安慰,她總會說,是,她知道了,媽媽是個爛人,是個賤貨。戴立齊邊罵邊喝,唯有酒精能讓他的喝斥轉為呢喃,呢喃轉為沈睡。父親退縮至自己的世界,甚至認為療癒他是小茜的責任,忘了孩子也是獨立的個體,不是為了醫治爸媽而存在。隨著小茜的發育長成,父女間畫上了一條界線,除了身體之外,兩人的心靈也漸漸分道揚鑣。
小茜在國中時接觸到文學,文學告訴她,傷口與疼痛是可以深掘的,結的痂會開花結果,綻放光芒。小茜栽了進去,尤其是詩。詩很模糊,詩很曖昧,很多最真實的感覺,說出來就不見了,而詩介於說與不說之間,告訴她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不如率性往下跳,文學會接住她。
在小茜十五歲的時候,母親似乎是良心發現,無端打了一通電話給小茜約見面,說想要看看她。思及五年不見的母親,小茜期盼赴約。兩人約在百貨大樓門口,母親遲到了半小時,出現後第一句話就是問小茜「吃飽沒?」聽聞此言,小茜掉頭就走,胸口燃起無名的憤怒。這五年來,母親從來沒有擔心過她的溫飽,關照過她的身心狀況,如今見面的第一句話「吃飽沒?」對小茜而言,根本羞辱。
小茜易感,有愛有恨。事後,她做了一個夢,夢中,她打開時常躲進去的衣櫃,將鞋帶綁在娃娃的脖子上,將娃娃吊在衣櫃上處以絞刑。夢醒,小茜並不驚恐,反倒是平靜讀懂了夢的隱喻。她在將從前的自己給吊死,不願再當一個乖順的小娃娃,再也不要當一個無助的人。她殺死了自己的某一塊,再用剩下的部分暴力地活著。
她立志要當一個很酷的少女,寧願有媽媽的無情,也不要有爸爸的軟弱。在她心中,酷是瀟灑,是真的不在乎,是擦乾眼淚之後承諾自己不再哭;酷的人說走就走,酷的人不輕易回頭。上高中後,她瘋狂探索世界上很多很酷的玩意,發現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連疼痛都繽紛。她瘋狂墜入文學、音樂、電玩、角色扮演與外拍之中。這些都是逃逸路徑,讓她得以暫且遁離令人窒息的現實。
高一時,她被醫生診斷出了憂鬱症。
她需要逃,需要躲起來,只是逃逸與躲藏的地方都再也沒有父親的位子了。她並非不想將父親帶上,只是戴立齊也在自身的悲傷中沒有走出來。悲傷不見得能同理悲傷,有時反而拉開了更遠的距離。愛並非不存在,只是失能。人們都相信明天之後還有明天,所以就算今天去恨去傷害,也總是有挽回與修復的機會,但真正的末日總是如小偷般到來,默默搬走那些珍貴的一切後再悄然溜走,留下無止盡的愕然與喟嘆,散逸在一片無際的荒原。
此時,人們再次渴望能有新天新地,但新天新地只發生在末日後。
在末日之前,我們得先迎向末日。
小茜消失的那一天,就是戴立齊的末日。
真希望消失的是那一天,而不是小茜。
有一則美麗的傳說,叫做新天新地。
據說,人在經歷了痛苦漫長的人生後,會在生命終結後走入一片嶄新的世界。在那,日月照耀,河水喧騰,鬱鬱蒼蒼,萬物和諧相處。人們肢體健壯,身心開朗。在那,陽光總暖暖地穿透眼皮,暈出一片燦紅,再浸入肌膚,沈澱於靈魂深處。在那,冰寒不刺骨,焰火不燒燙;行走者必定抵達,告別者注定遺忘。
在新天新地中,淚水在臉頰上流淌出一道刻痕,我們卻再也想不起來哭泣的理由;痛苦在我們靈魂上烙印了美麗的紋路,我們卻不必再體會痛苦本身;遺憾在我們心靈中鍛鍊出堅韌的哀傷,我們卻已經不遺憾了。
在新天新地中,人們被拋出暫存界,墜入了無始無終的永恆。永恆中,珍愛的都無限巨大,心碎的都無限渺小。填補一片無垠無際的,名之為愛。
很美的傳說,但在新天新地來臨之前,我們得先度過今生。
而今生,有時也會有著不輸新天新地的美好時光,像他們,像當時的他們。母親偶爾缺席,父女兩人也能歡快無憂、自由自在。
那時,父女兩人會一起站在地與海的邊緣,一起朝海的對岸大喊「我們在這!」他們會一起打羽毛球,一起對著高掛空中的羽毛球說「敢下來,我就再把你打飛!」他偷偷把口香糖黏在她的頭髮上,她偷偷拔他的腿毛;她會為了氣球不會飛而鬧脾氣,他會翻遍整座城市只為獲得一顆氫氣球然後放手;她的笑容像是在臉頰上播放的可愛電影,雙方的笑聲成了動人的配樂;他載著她啟程去遠方,不在乎遠方在哪;他希望她永遠不要長大,她不知道他會變老。
那段時光好輕巧、好可愛,父女像情人。那時,嘴唇還可以拿來親吻,手掌可以拿來緊握;那時,溫柔與衝突都尚未失控,還能恰如其分地存在與散置。
只是,生命有時會粗暴地將一切終止,當我們以為正朝向無垠的天際飛翔,卻撞到了一堵畫著白雲的藍色牆面。航道軋然而止,我們朝下墜落。當翅膀再也不飛,人就只得蹣跚地用走的了。
脆弱無靠之時,我們渴望新天新地,只是新天新地只發生在末日之後。
而在末日之前,我們得先迎向末日。
在小茜十歲那年,母親離家出走,音訊全無,再也沒有回來了。
溫馨的家庭劇變成一部殘酷的電影,完整的家頓時只由戴立齊與小茜兩人來展演。名之為家的碉堡坍塌了,磚瓦如雪花般紛飛下落。她開始躲避,他則鬆開了她的手,停在崩塌處等著被埋滅。
戴立齊崩解了,自那之後,清醒是為了喝醉,醉倒是為了醒來,再迎接下一次的迷茫。他把人生活得像幅雜亂無章的畫、一首走調跑拍的歌。他捲縮進封閉的世界,中斷與人的社交。他唯一有的,就只有小茜了。事情剛發生時,兩人還會一起去看海,只是戴立齊再也不笑了;後來,戴立齊說騎車一個小時太累,海聲從此只在夢中迴盪;他們偶爾會打羽毛球,只是球拍變重了;有時,小茜仰望著陽光之下、飄蕩在半空中的球,會輕輕對它說,「地表太多的憂傷,自己飛走吧。」
小茜恨媽媽,也恨自己沒有療癒爸爸的能力。戴立齊會在小茜面前將她母親形容成蕩婦,小茜不喜歡聽,也不願如此相信。但為了成為爸爸的安慰,她總會說,是,她知道了,媽媽是個爛人,是個賤貨。戴立齊邊罵邊喝,唯有酒精能讓他的喝斥轉為呢喃,呢喃轉為沈睡。父親退縮至自己的世界,甚至認為療癒他是小茜的責任,忘了孩子也是獨立的個體,不是為了醫治爸媽而存在。隨著小茜的發育長成,父女間畫上了一條界線,除了身體之外,兩人的心靈也漸漸分道揚鑣。
小茜在國中時接觸到文學,文學告訴她,傷口與疼痛是可以深掘的,結的痂會開花結果,綻放光芒。小茜栽了進去,尤其是詩。詩很模糊,詩很曖昧,很多最真實的感覺,說出來就不見了,而詩介於說與不說之間,告訴她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不如率性往下跳,文學會接住她。
在小茜十五歲的時候,母親似乎是良心發現,無端打了一通電話給小茜約見面,說想要看看她。思及五年不見的母親,小茜期盼赴約。兩人約在百貨大樓門口,母親遲到了半小時,出現後第一句話就是問小茜「吃飽沒?」聽聞此言,小茜掉頭就走,胸口燃起無名的憤怒。這五年來,母親從來沒有擔心過她的溫飽,關照過她的身心狀況,如今見面的第一句話「吃飽沒?」對小茜而言,根本羞辱。
小茜易感,有愛有恨。事後,她做了一個夢,夢中,她打開時常躲進去的衣櫃,將鞋帶綁在娃娃的脖子上,將娃娃吊在衣櫃上處以絞刑。夢醒,小茜並不驚恐,反倒是平靜讀懂了夢的隱喻。她在將從前的自己給吊死,不願再當一個乖順的小娃娃,再也不要當一個無助的人。她殺死了自己的某一塊,再用剩下的部分暴力地活著。
她立志要當一個很酷的少女,寧願有媽媽的無情,也不要有爸爸的軟弱。在她心中,酷是瀟灑,是真的不在乎,是擦乾眼淚之後承諾自己不再哭;酷的人說走就走,酷的人不輕易回頭。上高中後,她瘋狂探索世界上很多很酷的玩意,發現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連疼痛都繽紛。她瘋狂墜入文學、音樂、電玩、角色扮演與外拍之中。這些都是逃逸路徑,讓她得以暫且遁離令人窒息的現實。
高一時,她被醫生診斷出了憂鬱症。
她需要逃,需要躲起來,只是逃逸與躲藏的地方都再也沒有父親的位子了。她並非不想將父親帶上,只是戴立齊也在自身的悲傷中沒有走出來。悲傷不見得能同理悲傷,有時反而拉開了更遠的距離。愛並非不存在,只是失能。人們都相信明天之後還有明天,所以就算今天去恨去傷害,也總是有挽回與修復的機會,但真正的末日總是如小偷般到來,默默搬走那些珍貴的一切後再悄然溜走,留下無止盡的愕然與喟嘆,散逸在一片無際的荒原。
此時,人們再次渴望能有新天新地,但新天新地只發生在末日後。
在末日之前,我們得先迎向末日。
小茜消失的那一天,就是戴立齊的末日。
真希望消失的是那一天,而不是小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