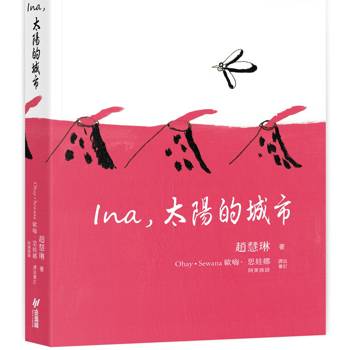作者的證詞
伊娜(ina) ,妳的大兒子打電話給我。那是在您出事一、兩個月之後。大兒子尊稱我為老師,是跟著您就讀小學的孫子女,沿用相同輩分。我猜想是為了便捷快遞伊娜的口信吧。他的謙遜間隔了好幾層山巒,當中捉摸不定遠距,比惆悵的失聯更令人困惑。我們之間通訊也像文明食品內超標的化學添加物,保存不了伊娜濃重託付的生鮮原味。
我細瘦身形哪裡承擔得起。我開始幻聽,話筒另一端的伊娜大兒子不過是一縷狼煙,終究是要沉降。殘酷時間必將未曾與我面對面交談的他,列隊為蔣公陵寢兩側,行禮如儀的一只玩具憲兵。這是國族打敗我們的精神勝利法則。向永恆的統治者舉杯。
他浮拋出來的每一段精實語句都是最嚴重等級的預警。我這類型握筆謀生的薪資女,社會本性是懸高吊掛在山壁邊的大石塊。活在族群土石流潛勢區的人們越是謹慎應對,越無力防範對方可預知的崩落。
我記得。每回他久久一次返家,現身舞台聚光效果十足的都會板模屋前,總是讓兩道濃眉內鬥似的用力扭擠。那兩道濃眉是祖先暗示的火車脫軌劇本。伊娜的大兒子像是急欲掩埋,台鐵平快車一節一節運載北上,沉入秋芒的溪畔滿目荒涼。
那是他因應社交需求,從皮肉淺層苦笑了起來,才從慣常沉默嘴角,拉出極其不自然的兩道摺痕,和不請自來的我這名訪客對撞。他從那對深窩流露出遠洋船員專屬,漂泊中殷殷思念陸地上親人的海上憂傷。那是比老樹年輪還久遠,圈圈繞繞的男子戀家吟唱。雖然我不確定他是否跑過大船。
來電中,他的語氣輕緩,忽近、忽遠,岸浪般在我耳際響起。我解讀那是溯源自古民族的天然優雅。
我們總共沒聊上幾句話。他就掛斷了電話。太陽落下。
妳的大兒子膚色比部落其他邦查(Pangcah) 黝黑許多。我記得妳是台東馬蘭的邦查。我看過伊娜屋簷底下接受庇護的每一個受傷孩子,從失婚失能的大女兒到這個唯一兒子,從單親的小女兒到她獨立扶養的三名孫子女,全部都浸墨在最靠近赤道烈焰的深色皮膚內。伊娜孩子們襯膚的晶亮眼神,足讓另一種祖先做記號的濃黑膚色,升格為侵入白浪城市的武勇黑潮。汐止哪裡是你們遷徙海潮停止的死線。
墨黑膚色來自伊娜老公的遺傳。他們一起漂流,找到飢餓都市計畫還來不及腹吞的這塊原生地。他們老早厭倦了多足爬行的建地工寮。他們是洪水退去後的男女始祖。他們共同開天闢地的是白浪原來不管轄的這處隱僻棄地。他們哪裡知曉這裡是國家有權趕逐的公有地。他們哪裡料想得到,中央部會撐腰、優越感十足的BOT大咖,仗勢欺人,也來覬覦已有邦查祖靈入厝的這塊經歷水火之地。
原鄉族人細聽奄奄一息都會溪流的引路,伊娜和她老公有幸成為最早遷徙這一小段都市盲腸的先驅者。可惜他也是伊娜早逝的男人。我和盲飛他們板模簷內,吉兆卻迷途的烏秋一樣,終究是跟伊娜的老公緣慳一面。
他是排灣。我怎麼間接發現的呢?妳的長孫女有一回跟我抱怨,她如願以償入籍都市,正式上學的校內美勞課上,用祖傳的手感捏陶,竟神力長出了從鄉下老房子隔代懷胎的靈感—室內某處涼蔭森森的地方,總是有超過屋齡的長輩,木刻雕像般獨坐;不是現世、也還沒有攀登到更高靈界,一支蠟燭燃盡了都還是文風不動。活的擺設,不明用途陶罐之類,老人家是舊器物堆裡頭,訪客們最熟悉的那片裝飾風景。長者噤語,當下時間內徘徊不去的祖先,只能取暖室內柴燒火堆,噗噗爆響星苗紅光,又活了過來,那是好幾代以前巫術指導成孕,不為國民小學課綱所規範的古造形。長孫女完成捏塑之後,祭祀力附身的這只陶製物件,像是合法奪取了和過去世代溝通的特權,開始吱吱喳喳,和祖先們革命密會。課堂上白浪教師,哪裡能夠理解拒絕以美白膚色為面具的這名他族女孩,如何捏造出來令人抖瑟不安的排灣和邦查聯姻古造形?!
伊娜,妳的長孫女從汐止鄰近小學,好容易爭取到正式學籍,卻無法實質保護她。歷經教改洗禮的體制內教育,原意是要來安頓學童身心的美勞才藝作業,少女直觀文化投射的日常,竟也戰爭砲彈似的,引爆出來師長們的異族驅逐戰線。那是成人教師們面對異質造形的類器官移植排斥吧。
他們瘦削但堅韌,像妳。伊娜,我覺得妳是不會死的。就像所有的伊娜和阿嬤。也包括我的平埔阿嬤。同為以女為尊為傲的母系文化讓妳指認出來我是妳的同盟戰友?
早幾年,我接到祖母喪聞,也類似是從嗶嗶扣的例常回覆,才協尋找到了遊歷遠方的至親晚輩。難道伊娜已經將我看作家人?
一開始是妳主動出擊,要來和我有來有往地交個朋友吧,伊娜。即便我不過是意外捲入了以你們為主角的公共演劇情節,我,猶然是都市部落領土內的無名入侵者,我,頂多是個滿載演出意志的閒置人形道具罷了。
我們一起叛逆了族群刻版印象。妳我都是不勝酒力的南島後裔。妳我滴酒不沾體質,都是瘦巴巴的無肉女。但是我們強過樑柱的纖細骨架可撐天。我們一起反神話。
那幾年間,劉老師固定進部落,陪伴孩子們畫圖。我是經常跟班,但是忘記帶槍,滿腹空包子彈的假游擊隊成員。現在回想,我根本是什麼也沒做,保有不錯正職工作的女廢青,那幾年。妳一定在忙碌於家務的同時,旁邊仔細偷瞥過,我不時晃進部落來的鬆散舉止。有好長一段時間了。我才終於看見妳對著我直視在發笑。訊號明確。妳想認識我。伊娜是在認親嗎?可是我每天都在大地震後不停餘震的搖晃中胡亂活著。還沒有打下蓋房子地基,只會拿筆拿相機。陰魂不散。用福林門(film)年代光學鏡頭猛開空頭支票的一面蒼白臉孔。只會粗魯來去。而不懂得生活當中確實苦難的一知半解知識寄生蟲。如果我是闖進了蓋上威武官印、擁有房契、地契、登錄戶籍等合法文件保障的其他高樓層集合住宅,是不是老早被警衛列為最不受歡迎的人類。是破壞族群生態系的外來物種?或者自從妳在都市裡呼吸。汐止地區連陡坡山邊都長滿了高樓的那麼長一段期間,妳早已熟悉了角色扮演,想像自己是藏身叢林內的一隻護幼母獸就對了。當妳出自本能,以銳利目光持續掃射我身上沾黏的城市冷漠,偵查我那一雙經常走錯方向的浮華腳印,重複,卻又不是返家歸鄉,從車水馬龍的境外走了進來。
都會浮萍如我,每回在古怪時段出現的前奏曲,可都是不明原因的落單吶。
請不要盡信,我徒勞東拼西湊,餓壞了的水溝內老鼠,匆促喫咬過的昨日記憶。
什麼是真的呢?我慣常從唯一出入口的那一條無名小徑,走進伊娜的「手作」部落。沿途大致是礫石與泥濘在摔跤的浙布俄草欉,和用絕望堆疊出來,末世景象的工業廢棄物小丘。那是沒有過去,也走不到明天,沒有房地產抗原體的三不管地景。
人為棄置的廢鋼、銹鐵和沒有屍臭味的塑料堆疊成比情色片還縱慾的垃圾山巒。他們與詭譎色澤的天空一起發出了令人作嘔氣味,而在都會文明獨裁的最強地表上,和自然廢墟似的淺溪共構成遺世獨立的地景。這是連非常沒有方向感的我,也都能夠憑藉比腫瘤生成還惡性的這一段沿途劇碼,取得安全辨識的定位系統吧。
當我越發走近了部落,時而路面上不是陷入了颱風來襲之後,不會有媒體報導的無害淹水災情,印象中溪魚都要翻蹦、游登上岸來閒逛了。要不,部落果真又上新聞,幾棟板模家屋燒毀了又建,建成了又在幾週後一夕燒成灰燼,而頻仍造就了慈濟師兄師姐們,在距離首善都會區舉臂之遠的這處「山上」部落,有本事展開急難快速救援的強大慈善動員力。對喔,我記起來了,大小不一的幾場連環災事,有一回暗夜火勢兇猛,竟將伊娜妳的家屋給大半吞喫。伊娜就此失去珍貴保存,等到伊里信(Ilisin) 才盛裝穿載的那套傳統服飾。
事隔十多年,果真我來個翻箱倒櫃,或許還能夠找到我在伊娜家屋火劫以前拍攝,全身穿戴邦查傳統服飾的那幅舊照吧。當年伊娜是怎麼動心起念,讓我穿戴起她在跳舞的伊里信上,都市戰袍的全副盛裝呢?我清晰記得,她鄭重盯著我穿戴傳統服的時候,如何顯露出來滿意神色。我當時並沒有一丁點兒穿戴上伊娜族服的想望。總覺得自己只是個硬邦邦體態的外來者,無權文化偽裝,輕藐了伊娜身份認同的族服。
只有伊娜她們從童稚到年老,年復一年,讓部落伊里信歌舞如祖先禱詞一樣浸透她們的身軀與官能,黏貼她們和祖先之間溝通密道的這個第二層皮膚—族服的穿戴,方才真正得到了祖先的恩福。尤其當年我略知一二,都市部落最早請示原鄉耆老能否將伊里信搬過來汐止舉辦?他們等到老人家同意點頭,真是比工地裡往往返返連續幾趟的沉重板模搬運還更艱辛不易。伊娜穿戴族服時頓踏、移位的每一個伊里信舞步,都是在剪斷後,又縫補連結起來的原鄉臍帶。
那時候我一度猶豫,自我批判恐怕成了許多伊里信現場,膚淺形式主義,跟著族人們跳舞、喝酒,又刻意穿上人家族服拍照,留下浮誇不實影像的一名都市部落觀光客。當我面對邦查母親的贈衣,笨拙不知所措,卻又雍容儀式似的接受盛裝那一刻,伊娜鄭重其事,微笑注視著我的表情。她很會講故事的骨感臉孔,至今停留在我腦海。我解讀那是來自優勢母系文化的伊娜,慷慨接納了我這個血統上異族的晚輩。
當年我還年輕,萬萬沒有料想到,這套活的族服會在短期內失喪。等不到明年伊里信了。伊娜一度為我隆重穿戴的這套文化戰服,伴隨脆弱營建環境下的板模家屋,葬身火海罹難了。
跳舞就是太陽。族服就是聖殿。
我感覺長老會設立的那座都市部落禮拜堂是生長在地球另一端熱帶雨林內的母樹原幹。邦查信眾以日常勞動最貼近膚觸的工地板模,穩穩當當打造出可啟示他們自身不滅感的這座禮拜堂。我參加過這群都市邦查的母語主日崇拜。短暫用後即丟的板模建材是這座基督聖堂永生的身體。我總覺得它們一點兒也不寒愴,是能夠在聖徒們疲憊時刻,彈性展延開來,柔軟包裹住聖邦查們挫敗淚光的大片襁褓布。我唯一一次在那兒禮拜的早晨,汗顏不是很認真在祈禱,反倒忙著以膽怯目光逐一觸摸,將聖堂英雄式拼築起來的四周一塊塊板模,懷想它們頻仍流浪的克難身世。它們又是無固定棲身處所的這一群都市營造工人們,鷹架叢林中一齊高高抬舉起敬拜靈魂的日常夥伴。我當時感覺這座聖堂一點兒也不卑微。記憶中,它一直隨著聖邦查們吟唱聖詩旋律,飄散出來原鄉工寮才有,青澀中滲透腥香草味的荒山氣息。聖堂旁邊又有小溪澗流淌過去的微音伴奏。禮拜座位上敬謹身姿的男、女聖徒,則用他們慣常攀爬巔危鷹架的氣勢神威,與高揭十字架的聖講台上,晨霧般輕薄易散的教會牧者講道聲,展開直球對決的一場又一場靜坐陳抗。
體格微胖但不失精壯的那位中年部落頭目,也是這間都市教會長老。我不禁懷想,當年他面對國家拆遷壓力,是如何尋求上帝的引導?等到他不得不屈服於技術官僚專斷的治理邏輯,部落內部議決,接受集體遷住租賃集合大樓的安置方案,上帝又怎麼親自安慰了他?
都市部落拆遷十餘年後,我在他們集體移住的集合大樓生活區,不期而遇這位末代頭目的輕度智障兒子。當時他正在街路上無所事事遊蕩。我先自動矯正,這是不負責任的形容。他是在巡視政府假面恩賜的部落領土,尋覓著他年少熟悉的板模鄰里。那兒佈滿邦查眼線,即刻有族人在我耳側證詞媒體漏網的後續發展:前幾年間,連堅定基督信仰的頭目也付不出所謂的優惠房租,親歷隱性的二度迫遷,黯然搬離了由官方安置謊言所編織,合乎房市開發律則,但比蜘蛛網絲還易破折摧毀的那座集合住宅部落。
部落烽煙四起。祖先走了。表面是平和自願撤離的族人們親手燃起燒滅部落的自殺火苗,狠狠除滅掉自己一手營建的板模家屋。板模尚未焚燒為徹底的灰燼。難民在戰火下拋棄世代家園的淒清景象,也不過如此。我沿著同一條野性的荒路進到部落。那是即將迎接夜幕垂憐的普通黃昏時刻。我唯一可預知是這個地方將不再出現濕冷冬夜裡圈圍升起的溫暖柴火。廣場上孩童嬉戲聲比未成年而死更哀傷地停止了。
那是我最後一次進去瀕死的伊娜部落。我如昔一個人走入無政府規劃的部落心臟。難道是為了搜尋任何活口?
我在近乎飛灰滅燼的部落遺址上,慌張搜索著伊娜身影。我一邊手握簡易型號的數位錄影機。邊行走,邊拍錄下來沿途景象。那是仿效伊里信在呼吸的舞步。那是一心一意要淨化族群違建的白浪國策已然成功清洗掉的自焚部落,誰有能力進行歷史蒐證呢?
只她一人,遇難似的驚恐瑟縮在親手搭建的板模家屋內。四面八方烽火未熄。她的孩子、孫子女們都已馴服搬遷,數百萬都會人口中一線浮光似的住進了理應安適,卻已有提前衰敗跡象的新租賃集合大樓內。但願那是我的幻想錯覺,她是不是已將今夜唯一活口的這棟板模小屋,看作自己終老的孤獨墓穴?她若離開這個帶有體溫的熟悉穴窩,就將淪為無處藏身的都市叢林內困獸?
難道我來,是要扮裝城市女超人,隔空將她帶離被迫自焚棄守的部落?難道我信心十足,她有辦法逃離到別的地方,十年、二十年繼續活下去?女超人是要手攬伊娜易脆折腰部,一起飛翔,回到台東原鄉?或者女超人協助政府,說服伊娜,遠離生病了卻還會呼吸的土地,住進去集合大樓,接受都會文明永不休止的情感勒索?
困獸。伊娜,那一回終曲的部落最後黃昏,我親睹妳已經不願意再流浪下去。
「還不走?」我的眼神像是在探詢伊娜遺願。
「今天晚上我要住在這裡。」記得她是這樣堅定回覆我的多餘提問。她的決絕超過了前朝教科書中記載,死守四行倉庫的愛國戰士。只是,她那枯老目光猶然滿佈著覆巢時刻雛鳥求助的驚悚。
烽煙四起。棄守。公權力越強大,越吝於施捨他們更多商榷餘地。之後。部落滅絕。
雄心規劃,板模營建,蓋到一半就開始啟用的未完成部落活動中心;詩歌如輕霧瀰漫的板模基督聖堂;蜿蜒小徑更深走進去樹林子,那個偷偷親吻外來種入侵者臉頰的美少年有他高大威嚴伊娜營建起來的家屋;男童灑尿如灌籃的部落正中央籃球場;暑假回到花東老家潛海採集海帶被大浪捲走的青年阿道,留下他的少婦遺孀將四名稚齡子女帶在身邊,繼續經營大路邊的板模小店,一如既往任性擺放著不畏寂寥桌椅,等候族人下工返回,圍滿了一起吃吃喝喝,部落族人哪裡捨得它隨著阿道的離去而結束營業……都從盤踞十多年的都市邊陲地帶全體消失了。
伊娜的大兒子打電話給我。他那兩道濃眉鎖住的苦悶其實是我們之間未完成的交談。
他說了什麼?
那是漢人的清明掃墓時節。一輛廂型車運載了伊娜全家老小。下行返回台東老家。車體翻覆。伊娜大兒子無一字車禍現場景象的倒帶描述。像是事故發生的時日久遠,他是連輕描淡寫回溯的意向都枯死。受傷更為嚴重的家人全數倖存下來。唯獨傷勢不重的伊娜走了。
我只在話筒另一端點點頭。我是伊娜求死的知音。
伊娜停止呼吸以前,叮囑大兒子,要來跟我惜別。
我在邦查族人自行摧毀都市部落的最後一夜,前去探望她。我們之間生出某種神秘共感的默契。伊娜可能感知到,對於她如何活下去?餘生在哪個地方度過?以至於她單單要勉強自己繼續呼吸下去,都變成是那麼高難度挑戰,我這個不負責任的旁觀者已然有了不必言說的理解。就在迎接流浪伊娜進來與我一起呼吸的分秒之間。
伊娜若非喪失了活下去的意願,怎麼會僅只是輕傷就放棄了呼吸?
伊娜活不下去的事實,是在都市邊陲戰火連天,她一個人孤單住了下來,和部落一起死去的最後一晚,我就看到了伊娜的結局。
這是我對妳一個人的遲來承諾:寫下曾經讓妳勇敢呼吸的那些部落裡頭,所有都市流浪的伊娜們共同故事。
都市裡年輕一輩、年輕兩輩、年輕三輩的伊娜們,老早遺忘了妳清唱給我聽的那首暗啞木工之歌?
每回我再進中正紀念堂的兩廳院內觀賞藝文表演,我總會記起,伊娜妳在猶然恐懼的情緒網羅中,怎麼證詞當年這個偉大人文地標在如火如荼工程營建期間,工班族人們如何攀爬上去好幾層樓高度鷹架頂上,任何稍無力踏穩腳步的疲累瞬間,他(她)們可能掉落下來,摔碎了伊里信當中不止息海浪般歌舞的身軀,以及他(她)們還來不及訴說給孩子們聽,移動在歡樂與控訴邊界的原鄉遷徙者共同證詞。
這是紀念伊娜的遺言之書;也是來自政經同源的邦查大遷徙年代,最終結局殊異,所有吉能能麥伊娜們不死的證言之書。
太陽的城市,日不落的明天。
伊娜(ina) ,妳的大兒子打電話給我。那是在您出事一、兩個月之後。大兒子尊稱我為老師,是跟著您就讀小學的孫子女,沿用相同輩分。我猜想是為了便捷快遞伊娜的口信吧。他的謙遜間隔了好幾層山巒,當中捉摸不定遠距,比惆悵的失聯更令人困惑。我們之間通訊也像文明食品內超標的化學添加物,保存不了伊娜濃重託付的生鮮原味。
我細瘦身形哪裡承擔得起。我開始幻聽,話筒另一端的伊娜大兒子不過是一縷狼煙,終究是要沉降。殘酷時間必將未曾與我面對面交談的他,列隊為蔣公陵寢兩側,行禮如儀的一只玩具憲兵。這是國族打敗我們的精神勝利法則。向永恆的統治者舉杯。
他浮拋出來的每一段精實語句都是最嚴重等級的預警。我這類型握筆謀生的薪資女,社會本性是懸高吊掛在山壁邊的大石塊。活在族群土石流潛勢區的人們越是謹慎應對,越無力防範對方可預知的崩落。
我記得。每回他久久一次返家,現身舞台聚光效果十足的都會板模屋前,總是讓兩道濃眉內鬥似的用力扭擠。那兩道濃眉是祖先暗示的火車脫軌劇本。伊娜的大兒子像是急欲掩埋,台鐵平快車一節一節運載北上,沉入秋芒的溪畔滿目荒涼。
那是他因應社交需求,從皮肉淺層苦笑了起來,才從慣常沉默嘴角,拉出極其不自然的兩道摺痕,和不請自來的我這名訪客對撞。他從那對深窩流露出遠洋船員專屬,漂泊中殷殷思念陸地上親人的海上憂傷。那是比老樹年輪還久遠,圈圈繞繞的男子戀家吟唱。雖然我不確定他是否跑過大船。
來電中,他的語氣輕緩,忽近、忽遠,岸浪般在我耳際響起。我解讀那是溯源自古民族的天然優雅。
我們總共沒聊上幾句話。他就掛斷了電話。太陽落下。
妳的大兒子膚色比部落其他邦查(Pangcah) 黝黑許多。我記得妳是台東馬蘭的邦查。我看過伊娜屋簷底下接受庇護的每一個受傷孩子,從失婚失能的大女兒到這個唯一兒子,從單親的小女兒到她獨立扶養的三名孫子女,全部都浸墨在最靠近赤道烈焰的深色皮膚內。伊娜孩子們襯膚的晶亮眼神,足讓另一種祖先做記號的濃黑膚色,升格為侵入白浪城市的武勇黑潮。汐止哪裡是你們遷徙海潮停止的死線。
墨黑膚色來自伊娜老公的遺傳。他們一起漂流,找到飢餓都市計畫還來不及腹吞的這塊原生地。他們老早厭倦了多足爬行的建地工寮。他們是洪水退去後的男女始祖。他們共同開天闢地的是白浪原來不管轄的這處隱僻棄地。他們哪裡知曉這裡是國家有權趕逐的公有地。他們哪裡料想得到,中央部會撐腰、優越感十足的BOT大咖,仗勢欺人,也來覬覦已有邦查祖靈入厝的這塊經歷水火之地。
原鄉族人細聽奄奄一息都會溪流的引路,伊娜和她老公有幸成為最早遷徙這一小段都市盲腸的先驅者。可惜他也是伊娜早逝的男人。我和盲飛他們板模簷內,吉兆卻迷途的烏秋一樣,終究是跟伊娜的老公緣慳一面。
他是排灣。我怎麼間接發現的呢?妳的長孫女有一回跟我抱怨,她如願以償入籍都市,正式上學的校內美勞課上,用祖傳的手感捏陶,竟神力長出了從鄉下老房子隔代懷胎的靈感—室內某處涼蔭森森的地方,總是有超過屋齡的長輩,木刻雕像般獨坐;不是現世、也還沒有攀登到更高靈界,一支蠟燭燃盡了都還是文風不動。活的擺設,不明用途陶罐之類,老人家是舊器物堆裡頭,訪客們最熟悉的那片裝飾風景。長者噤語,當下時間內徘徊不去的祖先,只能取暖室內柴燒火堆,噗噗爆響星苗紅光,又活了過來,那是好幾代以前巫術指導成孕,不為國民小學課綱所規範的古造形。長孫女完成捏塑之後,祭祀力附身的這只陶製物件,像是合法奪取了和過去世代溝通的特權,開始吱吱喳喳,和祖先們革命密會。課堂上白浪教師,哪裡能夠理解拒絕以美白膚色為面具的這名他族女孩,如何捏造出來令人抖瑟不安的排灣和邦查聯姻古造形?!
伊娜,妳的長孫女從汐止鄰近小學,好容易爭取到正式學籍,卻無法實質保護她。歷經教改洗禮的體制內教育,原意是要來安頓學童身心的美勞才藝作業,少女直觀文化投射的日常,竟也戰爭砲彈似的,引爆出來師長們的異族驅逐戰線。那是成人教師們面對異質造形的類器官移植排斥吧。
他們瘦削但堅韌,像妳。伊娜,我覺得妳是不會死的。就像所有的伊娜和阿嬤。也包括我的平埔阿嬤。同為以女為尊為傲的母系文化讓妳指認出來我是妳的同盟戰友?
早幾年,我接到祖母喪聞,也類似是從嗶嗶扣的例常回覆,才協尋找到了遊歷遠方的至親晚輩。難道伊娜已經將我看作家人?
一開始是妳主動出擊,要來和我有來有往地交個朋友吧,伊娜。即便我不過是意外捲入了以你們為主角的公共演劇情節,我,猶然是都市部落領土內的無名入侵者,我,頂多是個滿載演出意志的閒置人形道具罷了。
我們一起叛逆了族群刻版印象。妳我都是不勝酒力的南島後裔。妳我滴酒不沾體質,都是瘦巴巴的無肉女。但是我們強過樑柱的纖細骨架可撐天。我們一起反神話。
那幾年間,劉老師固定進部落,陪伴孩子們畫圖。我是經常跟班,但是忘記帶槍,滿腹空包子彈的假游擊隊成員。現在回想,我根本是什麼也沒做,保有不錯正職工作的女廢青,那幾年。妳一定在忙碌於家務的同時,旁邊仔細偷瞥過,我不時晃進部落來的鬆散舉止。有好長一段時間了。我才終於看見妳對著我直視在發笑。訊號明確。妳想認識我。伊娜是在認親嗎?可是我每天都在大地震後不停餘震的搖晃中胡亂活著。還沒有打下蓋房子地基,只會拿筆拿相機。陰魂不散。用福林門(film)年代光學鏡頭猛開空頭支票的一面蒼白臉孔。只會粗魯來去。而不懂得生活當中確實苦難的一知半解知識寄生蟲。如果我是闖進了蓋上威武官印、擁有房契、地契、登錄戶籍等合法文件保障的其他高樓層集合住宅,是不是老早被警衛列為最不受歡迎的人類。是破壞族群生態系的外來物種?或者自從妳在都市裡呼吸。汐止地區連陡坡山邊都長滿了高樓的那麼長一段期間,妳早已熟悉了角色扮演,想像自己是藏身叢林內的一隻護幼母獸就對了。當妳出自本能,以銳利目光持續掃射我身上沾黏的城市冷漠,偵查我那一雙經常走錯方向的浮華腳印,重複,卻又不是返家歸鄉,從車水馬龍的境外走了進來。
都會浮萍如我,每回在古怪時段出現的前奏曲,可都是不明原因的落單吶。
請不要盡信,我徒勞東拼西湊,餓壞了的水溝內老鼠,匆促喫咬過的昨日記憶。
什麼是真的呢?我慣常從唯一出入口的那一條無名小徑,走進伊娜的「手作」部落。沿途大致是礫石與泥濘在摔跤的浙布俄草欉,和用絕望堆疊出來,末世景象的工業廢棄物小丘。那是沒有過去,也走不到明天,沒有房地產抗原體的三不管地景。
人為棄置的廢鋼、銹鐵和沒有屍臭味的塑料堆疊成比情色片還縱慾的垃圾山巒。他們與詭譎色澤的天空一起發出了令人作嘔氣味,而在都會文明獨裁的最強地表上,和自然廢墟似的淺溪共構成遺世獨立的地景。這是連非常沒有方向感的我,也都能夠憑藉比腫瘤生成還惡性的這一段沿途劇碼,取得安全辨識的定位系統吧。
當我越發走近了部落,時而路面上不是陷入了颱風來襲之後,不會有媒體報導的無害淹水災情,印象中溪魚都要翻蹦、游登上岸來閒逛了。要不,部落果真又上新聞,幾棟板模家屋燒毀了又建,建成了又在幾週後一夕燒成灰燼,而頻仍造就了慈濟師兄師姐們,在距離首善都會區舉臂之遠的這處「山上」部落,有本事展開急難快速救援的強大慈善動員力。對喔,我記起來了,大小不一的幾場連環災事,有一回暗夜火勢兇猛,竟將伊娜妳的家屋給大半吞喫。伊娜就此失去珍貴保存,等到伊里信(Ilisin) 才盛裝穿載的那套傳統服飾。
事隔十多年,果真我來個翻箱倒櫃,或許還能夠找到我在伊娜家屋火劫以前拍攝,全身穿戴邦查傳統服飾的那幅舊照吧。當年伊娜是怎麼動心起念,讓我穿戴起她在跳舞的伊里信上,都市戰袍的全副盛裝呢?我清晰記得,她鄭重盯著我穿戴傳統服的時候,如何顯露出來滿意神色。我當時並沒有一丁點兒穿戴上伊娜族服的想望。總覺得自己只是個硬邦邦體態的外來者,無權文化偽裝,輕藐了伊娜身份認同的族服。
只有伊娜她們從童稚到年老,年復一年,讓部落伊里信歌舞如祖先禱詞一樣浸透她們的身軀與官能,黏貼她們和祖先之間溝通密道的這個第二層皮膚—族服的穿戴,方才真正得到了祖先的恩福。尤其當年我略知一二,都市部落最早請示原鄉耆老能否將伊里信搬過來汐止舉辦?他們等到老人家同意點頭,真是比工地裡往往返返連續幾趟的沉重板模搬運還更艱辛不易。伊娜穿戴族服時頓踏、移位的每一個伊里信舞步,都是在剪斷後,又縫補連結起來的原鄉臍帶。
那時候我一度猶豫,自我批判恐怕成了許多伊里信現場,膚淺形式主義,跟著族人們跳舞、喝酒,又刻意穿上人家族服拍照,留下浮誇不實影像的一名都市部落觀光客。當我面對邦查母親的贈衣,笨拙不知所措,卻又雍容儀式似的接受盛裝那一刻,伊娜鄭重其事,微笑注視著我的表情。她很會講故事的骨感臉孔,至今停留在我腦海。我解讀那是來自優勢母系文化的伊娜,慷慨接納了我這個血統上異族的晚輩。
當年我還年輕,萬萬沒有料想到,這套活的族服會在短期內失喪。等不到明年伊里信了。伊娜一度為我隆重穿戴的這套文化戰服,伴隨脆弱營建環境下的板模家屋,葬身火海罹難了。
跳舞就是太陽。族服就是聖殿。
我感覺長老會設立的那座都市部落禮拜堂是生長在地球另一端熱帶雨林內的母樹原幹。邦查信眾以日常勞動最貼近膚觸的工地板模,穩穩當當打造出可啟示他們自身不滅感的這座禮拜堂。我參加過這群都市邦查的母語主日崇拜。短暫用後即丟的板模建材是這座基督聖堂永生的身體。我總覺得它們一點兒也不寒愴,是能夠在聖徒們疲憊時刻,彈性展延開來,柔軟包裹住聖邦查們挫敗淚光的大片襁褓布。我唯一一次在那兒禮拜的早晨,汗顏不是很認真在祈禱,反倒忙著以膽怯目光逐一觸摸,將聖堂英雄式拼築起來的四周一塊塊板模,懷想它們頻仍流浪的克難身世。它們又是無固定棲身處所的這一群都市營造工人們,鷹架叢林中一齊高高抬舉起敬拜靈魂的日常夥伴。我當時感覺這座聖堂一點兒也不卑微。記憶中,它一直隨著聖邦查們吟唱聖詩旋律,飄散出來原鄉工寮才有,青澀中滲透腥香草味的荒山氣息。聖堂旁邊又有小溪澗流淌過去的微音伴奏。禮拜座位上敬謹身姿的男、女聖徒,則用他們慣常攀爬巔危鷹架的氣勢神威,與高揭十字架的聖講台上,晨霧般輕薄易散的教會牧者講道聲,展開直球對決的一場又一場靜坐陳抗。
體格微胖但不失精壯的那位中年部落頭目,也是這間都市教會長老。我不禁懷想,當年他面對國家拆遷壓力,是如何尋求上帝的引導?等到他不得不屈服於技術官僚專斷的治理邏輯,部落內部議決,接受集體遷住租賃集合大樓的安置方案,上帝又怎麼親自安慰了他?
都市部落拆遷十餘年後,我在他們集體移住的集合大樓生活區,不期而遇這位末代頭目的輕度智障兒子。當時他正在街路上無所事事遊蕩。我先自動矯正,這是不負責任的形容。他是在巡視政府假面恩賜的部落領土,尋覓著他年少熟悉的板模鄰里。那兒佈滿邦查眼線,即刻有族人在我耳側證詞媒體漏網的後續發展:前幾年間,連堅定基督信仰的頭目也付不出所謂的優惠房租,親歷隱性的二度迫遷,黯然搬離了由官方安置謊言所編織,合乎房市開發律則,但比蜘蛛網絲還易破折摧毀的那座集合住宅部落。
部落烽煙四起。祖先走了。表面是平和自願撤離的族人們親手燃起燒滅部落的自殺火苗,狠狠除滅掉自己一手營建的板模家屋。板模尚未焚燒為徹底的灰燼。難民在戰火下拋棄世代家園的淒清景象,也不過如此。我沿著同一條野性的荒路進到部落。那是即將迎接夜幕垂憐的普通黃昏時刻。我唯一可預知是這個地方將不再出現濕冷冬夜裡圈圍升起的溫暖柴火。廣場上孩童嬉戲聲比未成年而死更哀傷地停止了。
那是我最後一次進去瀕死的伊娜部落。我如昔一個人走入無政府規劃的部落心臟。難道是為了搜尋任何活口?
我在近乎飛灰滅燼的部落遺址上,慌張搜索著伊娜身影。我一邊手握簡易型號的數位錄影機。邊行走,邊拍錄下來沿途景象。那是仿效伊里信在呼吸的舞步。那是一心一意要淨化族群違建的白浪國策已然成功清洗掉的自焚部落,誰有能力進行歷史蒐證呢?
只她一人,遇難似的驚恐瑟縮在親手搭建的板模家屋內。四面八方烽火未熄。她的孩子、孫子女們都已馴服搬遷,數百萬都會人口中一線浮光似的住進了理應安適,卻已有提前衰敗跡象的新租賃集合大樓內。但願那是我的幻想錯覺,她是不是已將今夜唯一活口的這棟板模小屋,看作自己終老的孤獨墓穴?她若離開這個帶有體溫的熟悉穴窩,就將淪為無處藏身的都市叢林內困獸?
難道我來,是要扮裝城市女超人,隔空將她帶離被迫自焚棄守的部落?難道我信心十足,她有辦法逃離到別的地方,十年、二十年繼續活下去?女超人是要手攬伊娜易脆折腰部,一起飛翔,回到台東原鄉?或者女超人協助政府,說服伊娜,遠離生病了卻還會呼吸的土地,住進去集合大樓,接受都會文明永不休止的情感勒索?
困獸。伊娜,那一回終曲的部落最後黃昏,我親睹妳已經不願意再流浪下去。
「還不走?」我的眼神像是在探詢伊娜遺願。
「今天晚上我要住在這裡。」記得她是這樣堅定回覆我的多餘提問。她的決絕超過了前朝教科書中記載,死守四行倉庫的愛國戰士。只是,她那枯老目光猶然滿佈著覆巢時刻雛鳥求助的驚悚。
烽煙四起。棄守。公權力越強大,越吝於施捨他們更多商榷餘地。之後。部落滅絕。
雄心規劃,板模營建,蓋到一半就開始啟用的未完成部落活動中心;詩歌如輕霧瀰漫的板模基督聖堂;蜿蜒小徑更深走進去樹林子,那個偷偷親吻外來種入侵者臉頰的美少年有他高大威嚴伊娜營建起來的家屋;男童灑尿如灌籃的部落正中央籃球場;暑假回到花東老家潛海採集海帶被大浪捲走的青年阿道,留下他的少婦遺孀將四名稚齡子女帶在身邊,繼續經營大路邊的板模小店,一如既往任性擺放著不畏寂寥桌椅,等候族人下工返回,圍滿了一起吃吃喝喝,部落族人哪裡捨得它隨著阿道的離去而結束營業……都從盤踞十多年的都市邊陲地帶全體消失了。
伊娜的大兒子打電話給我。他那兩道濃眉鎖住的苦悶其實是我們之間未完成的交談。
他說了什麼?
那是漢人的清明掃墓時節。一輛廂型車運載了伊娜全家老小。下行返回台東老家。車體翻覆。伊娜大兒子無一字車禍現場景象的倒帶描述。像是事故發生的時日久遠,他是連輕描淡寫回溯的意向都枯死。受傷更為嚴重的家人全數倖存下來。唯獨傷勢不重的伊娜走了。
我只在話筒另一端點點頭。我是伊娜求死的知音。
伊娜停止呼吸以前,叮囑大兒子,要來跟我惜別。
我在邦查族人自行摧毀都市部落的最後一夜,前去探望她。我們之間生出某種神秘共感的默契。伊娜可能感知到,對於她如何活下去?餘生在哪個地方度過?以至於她單單要勉強自己繼續呼吸下去,都變成是那麼高難度挑戰,我這個不負責任的旁觀者已然有了不必言說的理解。就在迎接流浪伊娜進來與我一起呼吸的分秒之間。
伊娜若非喪失了活下去的意願,怎麼會僅只是輕傷就放棄了呼吸?
伊娜活不下去的事實,是在都市邊陲戰火連天,她一個人孤單住了下來,和部落一起死去的最後一晚,我就看到了伊娜的結局。
這是我對妳一個人的遲來承諾:寫下曾經讓妳勇敢呼吸的那些部落裡頭,所有都市流浪的伊娜們共同故事。
都市裡年輕一輩、年輕兩輩、年輕三輩的伊娜們,老早遺忘了妳清唱給我聽的那首暗啞木工之歌?
每回我再進中正紀念堂的兩廳院內觀賞藝文表演,我總會記起,伊娜妳在猶然恐懼的情緒網羅中,怎麼證詞當年這個偉大人文地標在如火如荼工程營建期間,工班族人們如何攀爬上去好幾層樓高度鷹架頂上,任何稍無力踏穩腳步的疲累瞬間,他(她)們可能掉落下來,摔碎了伊里信當中不止息海浪般歌舞的身軀,以及他(她)們還來不及訴說給孩子們聽,移動在歡樂與控訴邊界的原鄉遷徙者共同證詞。
這是紀念伊娜的遺言之書;也是來自政經同源的邦查大遷徙年代,最終結局殊異,所有吉能能麥伊娜們不死的證言之書。
太陽的城市,日不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