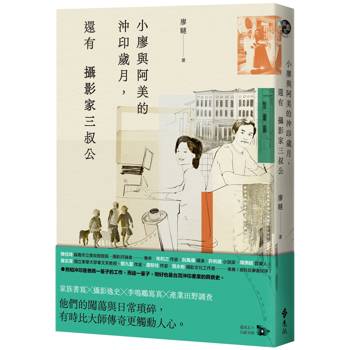2 西門町的小廖,羅東的阿美
問媽媽寫到她,要叫她什麼呢?阿美好了,「阿bí。」台語發音。阿美,一九五三年生,「小時候大家都叫我阿美。」家裡有五個小孩,她是中間那一個,「連我弟都叫我阿美。」阿美出生在宜蘭羅東,小時習舞,獲獎無數,這是後來我看照片才知道的,如果沒有照片,我大概不會相信媽媽以前跳舞。
「我跳舞很認真啊,常常跳主角。」阿美說。認真就可以跳到主角?我還以為跳舞比較看天分。我看著媽媽跳舞時的裝扮,「這是跳民俗舞蹈嗎?」「可以這樣講吧。」阿美說。
家裡的阿美相本,有小時候的,上台北讀書工作的。小時照片都是黑白照,尺寸不一,不像後來彩色沖印時期都是三乘五或四乘六那樣整齊。阿美真的很會整理東西,想想她小時住羅東,大學上台北,後來跟我爸結婚,搬到高雄,生我時回台北,沒多久去羅東,之後又下高雄工作,再跟著我爸去台南種菇,最後搬回高雄。這樣前前後後奔奔波波,她小時候的照片都還留得好好的,不僅還在,且全數整理到精裝大相本裡。
而小廖幾乎沒有小時照片。我爸說可以叫他「小廖」,「我們家四個男生嘛,我最小,大家就叫我小廖。」小廖,一九五○年生,老家在台北西門町,近今日紅樓。原本以為小廖有個開設照相材料行的三叔李鳴鵰,洗照片容易也便宜,他的照片應該不少,但並沒有。
從前對小廖的想像是:因為喜歡拍照,所以走上沖洗照片這途。結果小廖說,他去三叔的公司上班之前,沒有拿過相機,他是先學會了沖洗照片,才開始拍照。原來小廖跟李鳴鵰一樣,李鳴鵰是先學會了修片,開始賺錢存到錢之後,才為自己買了台雙眼相機。
「以前相機很貴啊。」小廖說他第一台相機也是雙眼,一台三千多,牌子忘了。一九七○年代的三千多,大約是小廖一個月的薪水。單眼相機就更貴了,他的第一台單眼是奇農(Chinon),一台要一萬多塊錢。
不是因為喜歡拍照,才去學沖洗,而是先學會了沖洗,對拍照有了一點興趣,有經濟能力後才買相機來拍。但也不是接觸沖洗這行的人,都會對拍照感興趣。像阿美,印象中沒看過她拍照,阿美雖然洗了一輩子的照片,但她會使用單眼相機嗎?我以為阿美不會,結果一問,阿美說,有學過,但不熟練。我太小看阿美了,畢竟阿美年輕時還沒有傻瓜相機,想拍照只能用單眼。既然都在沖印公司工作了,就算平常沒拿相機,但對相機的基本概念還是有的,我怎麼會覺得阿美不會用單眼相機呢?
阿美去沖印公司上班前,打過許多工。她大學讀夜間部,白天工作,晚上讀書。阿美跟同鄉的國中同學在外租屋,房間很小,是房間裡的房間,要爬木梯子上去,「我才一百五十五公分,但上去之後也只能彎腰,不然會頂到天花板。」阿美說的時候,一種媽媽以前好辛苦你知道嗎的感覺,學費生活費都要自己來,只能住在連腰都站不直的閣樓。
一九七二年,政府推動「客廳即工廠」政策,阿美和幾個蘭陽女中畢業的同學,也做過這種家庭代工,「做清潔液分裝,大家在業主的一間空房,把一大桶成品分裝成小瓶小瓶。工作很單調,但一起打工聊天很有趣。」後來外公幫忙牽線,阿美到貿易公司當小妹,可是主管會毛手毛腳,阿美又不敢講,「做了一陣子之後,我說做不習慣,你阿公就再幫我問別的工作,最後到菱天上班。」
菱天,就是三叔公李鳴鵰的沖印公司。安排媽媽到菱天上班的,是五叔公廖名雁。五叔公跟外公是師專同學。
廖名雁,一九二六年生。師專畢業後當小學老師,兩年後被派到台北市教育局做教育行政。過沒多久,李鳴鵰對廖名雁說,「你做公務員賺不到錢啦,賺不到錢賺不到吃,我這裡需要人,你來我這裡。」當時李鳴鵰正開始跟日本三菱(Mitsubishi)做生意,他希望廖名雁去日本受訓,回來幫他。
受日本教育長大的廖名雁,日語說得比國語好。我看「臺灣傑出攝影家紀錄片—李鳴鵰」,聽著這個未曾謀面的五叔公說話,他說的是國語,但聽得出那個口音,平常應該是說台語。他講話講一講,有時會說,「那個國語怎麼講……」五叔公說話的聲音、速度、氣質,都跟外公好像。那個年代受日本師範教育的人,是不是都有一種溫儒的氣質?
「後來我就跟我哥哥在一起,從那裡開始到現在,就是這個緣分還在。」廖名雁說「在一起」時,我覺得這個詞好美。有多少人能跟自己的兄弟或姊妹一直在一起呢?長大後分開是自然,更有的是相敬如冰互不往來。而廖名雁從李鳴鵰做照相沖印器材生意開始,當時兩人都還不滿三十歲,一直在李鳴鵰公司直到退休,再到在紀錄片中回憶哥哥。
每次小廖和阿美提起廖名雁,都會說,你五叔公人真的很好。這個好比起三叔公李鳴鵰更立體。我問小廖,三叔公教過你什麼?結果小廖每次講,最後都在講廖名雁,「五叔教我切相紙、放大、改色,教我沖片,我會的都是五叔教的。」問到阿美也是一樣,「廖名雁是總經理,公司是他在管事。我好像很少看到你三叔公。」「你五叔公個性就是很溫和啊,跟外公很像。我沒有看過他兇員工。」
李鳴鵰派廖名雁去日本京都受訓,實習三個月,學習彩色沖印原理、沖洗照片,「回來就買機器,後來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大。」「我哥工作都交給我,所有工作都交給我,他有閒啦,常常相機帶了就出去拍照。」廖名雁提到他哥時,呵呵呵地笑。
有張照片,擔任總經理的廖名雁和兩個公司職員打著領帶,他穿著卡其色制服外套,在菱天大樓大門前,站得很正,看起來拘謹又老派。
小廖成淵中學畢業後,考上北市高工機械科,也就是現在的大安高工,在復興南路上。「我不喜歡讀書啊,不像我們學校對面的附中。」「畢業後五叔說他缺人,我就去那邊當學徒。」那時是一九六九年,小廖十九歲。
「你剛開始學彩色沖印時,感覺是什麼?你有覺得這很新奇、很有趣嗎?」我問小廖。小廖想了一下,說,都很順。我說不是要問順不順啦,是想知道你心裡的感覺,比如會覺得很難嗎?或是,你喜歡這個工作嗎?
小廖說喜歡啊。「喜歡什麼?」我問。
「因為那時候也只能做這個啊。」小廖說。過了一會又說,因為很驕傲,非常驕傲。「那時候的國小老師,一個月薪水只有兩千八,我一個小師傅就有一萬。」
一九六八年的台灣,基本月薪六百元,而小廖在一九六九年當學徒時,月薪一千元,當時他才十九歲。一九七四年小廖當兵退伍,回菱天上班,正職員工薪水調至三千元,過沒多久又加薪至三千五百元。之後菱天與高雄的照相器材行合夥成立沖印公司,派小廖下去擔任手工組組長,月薪一萬元。而台灣的基本薪資直到一九七八年,才調至二千四百元。就算不以基本薪資來看,而是看平均薪資:一九七四年的國民平均所得,一個月是二千六百八十三元,小廖的薪水幾乎是當時平均月薪的四倍,那時他才二十四歲。
小廖的回答令我感覺微妙。一開始他說,那時候只能做這個啊,好像沒有什麼好選,遇到了就做,就要喜歡。接著他似乎想起這份工作高薪所帶來的成就感,有一種―雖然我學歷不怎麼樣,但薪水待遇可不輸老師喔,這樣的感覺,「我覺得有一技之長很好,而且在當時是很新的技術。」小廖說。
我感覺到小廖的樂天,但並不明白他真正的感受。小廖不太會講,他不太會說自己。但阿美會講。阿美說,起初她沒有那麼喜歡這份工作,「剛進公司時,被安排在技術部門,但學技術沒那麼簡單,要學怎麼在暗房裝紙,還有藥水什麼的,我覺得很難。」阿美喜歡做行政,行政工作她可以做得很好,而技術部門要學的東西很多,承擔的責任也比較大,「可是我的個性不會去表達我不喜歡,既然被安排進技術部門,我就認命好好學好好做。」
但阿美說,還好當初有學這些,「這樣後來才可以跟你老爸一起開店。」
曾經採訪維修相機的師傅,我問他為什麼做這行呢?他聽到時愣了一下,那反應像是「這是什麼問題?」「這要怎麼回答?」師傅想了一下說,那時候出路沒有很多啊,「要不工廠工作,不然就當學徒,除非你念書念得很好,或是家境不錯可以培養。」「我是跟我大哥學,我大哥是跟一個 Canon 的師傅學。」一副理所當然,哪有什麼為什麼。
(未完待續)
問媽媽寫到她,要叫她什麼呢?阿美好了,「阿bí。」台語發音。阿美,一九五三年生,「小時候大家都叫我阿美。」家裡有五個小孩,她是中間那一個,「連我弟都叫我阿美。」阿美出生在宜蘭羅東,小時習舞,獲獎無數,這是後來我看照片才知道的,如果沒有照片,我大概不會相信媽媽以前跳舞。
「我跳舞很認真啊,常常跳主角。」阿美說。認真就可以跳到主角?我還以為跳舞比較看天分。我看著媽媽跳舞時的裝扮,「這是跳民俗舞蹈嗎?」「可以這樣講吧。」阿美說。
家裡的阿美相本,有小時候的,上台北讀書工作的。小時照片都是黑白照,尺寸不一,不像後來彩色沖印時期都是三乘五或四乘六那樣整齊。阿美真的很會整理東西,想想她小時住羅東,大學上台北,後來跟我爸結婚,搬到高雄,生我時回台北,沒多久去羅東,之後又下高雄工作,再跟著我爸去台南種菇,最後搬回高雄。這樣前前後後奔奔波波,她小時候的照片都還留得好好的,不僅還在,且全數整理到精裝大相本裡。
而小廖幾乎沒有小時照片。我爸說可以叫他「小廖」,「我們家四個男生嘛,我最小,大家就叫我小廖。」小廖,一九五○年生,老家在台北西門町,近今日紅樓。原本以為小廖有個開設照相材料行的三叔李鳴鵰,洗照片容易也便宜,他的照片應該不少,但並沒有。
從前對小廖的想像是:因為喜歡拍照,所以走上沖洗照片這途。結果小廖說,他去三叔的公司上班之前,沒有拿過相機,他是先學會了沖洗照片,才開始拍照。原來小廖跟李鳴鵰一樣,李鳴鵰是先學會了修片,開始賺錢存到錢之後,才為自己買了台雙眼相機。
「以前相機很貴啊。」小廖說他第一台相機也是雙眼,一台三千多,牌子忘了。一九七○年代的三千多,大約是小廖一個月的薪水。單眼相機就更貴了,他的第一台單眼是奇農(Chinon),一台要一萬多塊錢。
不是因為喜歡拍照,才去學沖洗,而是先學會了沖洗,對拍照有了一點興趣,有經濟能力後才買相機來拍。但也不是接觸沖洗這行的人,都會對拍照感興趣。像阿美,印象中沒看過她拍照,阿美雖然洗了一輩子的照片,但她會使用單眼相機嗎?我以為阿美不會,結果一問,阿美說,有學過,但不熟練。我太小看阿美了,畢竟阿美年輕時還沒有傻瓜相機,想拍照只能用單眼。既然都在沖印公司工作了,就算平常沒拿相機,但對相機的基本概念還是有的,我怎麼會覺得阿美不會用單眼相機呢?
阿美去沖印公司上班前,打過許多工。她大學讀夜間部,白天工作,晚上讀書。阿美跟同鄉的國中同學在外租屋,房間很小,是房間裡的房間,要爬木梯子上去,「我才一百五十五公分,但上去之後也只能彎腰,不然會頂到天花板。」阿美說的時候,一種媽媽以前好辛苦你知道嗎的感覺,學費生活費都要自己來,只能住在連腰都站不直的閣樓。
一九七二年,政府推動「客廳即工廠」政策,阿美和幾個蘭陽女中畢業的同學,也做過這種家庭代工,「做清潔液分裝,大家在業主的一間空房,把一大桶成品分裝成小瓶小瓶。工作很單調,但一起打工聊天很有趣。」後來外公幫忙牽線,阿美到貿易公司當小妹,可是主管會毛手毛腳,阿美又不敢講,「做了一陣子之後,我說做不習慣,你阿公就再幫我問別的工作,最後到菱天上班。」
菱天,就是三叔公李鳴鵰的沖印公司。安排媽媽到菱天上班的,是五叔公廖名雁。五叔公跟外公是師專同學。
廖名雁,一九二六年生。師專畢業後當小學老師,兩年後被派到台北市教育局做教育行政。過沒多久,李鳴鵰對廖名雁說,「你做公務員賺不到錢啦,賺不到錢賺不到吃,我這裡需要人,你來我這裡。」當時李鳴鵰正開始跟日本三菱(Mitsubishi)做生意,他希望廖名雁去日本受訓,回來幫他。
受日本教育長大的廖名雁,日語說得比國語好。我看「臺灣傑出攝影家紀錄片—李鳴鵰」,聽著這個未曾謀面的五叔公說話,他說的是國語,但聽得出那個口音,平常應該是說台語。他講話講一講,有時會說,「那個國語怎麼講……」五叔公說話的聲音、速度、氣質,都跟外公好像。那個年代受日本師範教育的人,是不是都有一種溫儒的氣質?
「後來我就跟我哥哥在一起,從那裡開始到現在,就是這個緣分還在。」廖名雁說「在一起」時,我覺得這個詞好美。有多少人能跟自己的兄弟或姊妹一直在一起呢?長大後分開是自然,更有的是相敬如冰互不往來。而廖名雁從李鳴鵰做照相沖印器材生意開始,當時兩人都還不滿三十歲,一直在李鳴鵰公司直到退休,再到在紀錄片中回憶哥哥。
每次小廖和阿美提起廖名雁,都會說,你五叔公人真的很好。這個好比起三叔公李鳴鵰更立體。我問小廖,三叔公教過你什麼?結果小廖每次講,最後都在講廖名雁,「五叔教我切相紙、放大、改色,教我沖片,我會的都是五叔教的。」問到阿美也是一樣,「廖名雁是總經理,公司是他在管事。我好像很少看到你三叔公。」「你五叔公個性就是很溫和啊,跟外公很像。我沒有看過他兇員工。」
李鳴鵰派廖名雁去日本京都受訓,實習三個月,學習彩色沖印原理、沖洗照片,「回來就買機器,後來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大。」「我哥工作都交給我,所有工作都交給我,他有閒啦,常常相機帶了就出去拍照。」廖名雁提到他哥時,呵呵呵地笑。
有張照片,擔任總經理的廖名雁和兩個公司職員打著領帶,他穿著卡其色制服外套,在菱天大樓大門前,站得很正,看起來拘謹又老派。
小廖成淵中學畢業後,考上北市高工機械科,也就是現在的大安高工,在復興南路上。「我不喜歡讀書啊,不像我們學校對面的附中。」「畢業後五叔說他缺人,我就去那邊當學徒。」那時是一九六九年,小廖十九歲。
「你剛開始學彩色沖印時,感覺是什麼?你有覺得這很新奇、很有趣嗎?」我問小廖。小廖想了一下,說,都很順。我說不是要問順不順啦,是想知道你心裡的感覺,比如會覺得很難嗎?或是,你喜歡這個工作嗎?
小廖說喜歡啊。「喜歡什麼?」我問。
「因為那時候也只能做這個啊。」小廖說。過了一會又說,因為很驕傲,非常驕傲。「那時候的國小老師,一個月薪水只有兩千八,我一個小師傅就有一萬。」
一九六八年的台灣,基本月薪六百元,而小廖在一九六九年當學徒時,月薪一千元,當時他才十九歲。一九七四年小廖當兵退伍,回菱天上班,正職員工薪水調至三千元,過沒多久又加薪至三千五百元。之後菱天與高雄的照相器材行合夥成立沖印公司,派小廖下去擔任手工組組長,月薪一萬元。而台灣的基本薪資直到一九七八年,才調至二千四百元。就算不以基本薪資來看,而是看平均薪資:一九七四年的國民平均所得,一個月是二千六百八十三元,小廖的薪水幾乎是當時平均月薪的四倍,那時他才二十四歲。
小廖的回答令我感覺微妙。一開始他說,那時候只能做這個啊,好像沒有什麼好選,遇到了就做,就要喜歡。接著他似乎想起這份工作高薪所帶來的成就感,有一種―雖然我學歷不怎麼樣,但薪水待遇可不輸老師喔,這樣的感覺,「我覺得有一技之長很好,而且在當時是很新的技術。」小廖說。
我感覺到小廖的樂天,但並不明白他真正的感受。小廖不太會講,他不太會說自己。但阿美會講。阿美說,起初她沒有那麼喜歡這份工作,「剛進公司時,被安排在技術部門,但學技術沒那麼簡單,要學怎麼在暗房裝紙,還有藥水什麼的,我覺得很難。」阿美喜歡做行政,行政工作她可以做得很好,而技術部門要學的東西很多,承擔的責任也比較大,「可是我的個性不會去表達我不喜歡,既然被安排進技術部門,我就認命好好學好好做。」
但阿美說,還好當初有學這些,「這樣後來才可以跟你老爸一起開店。」
曾經採訪維修相機的師傅,我問他為什麼做這行呢?他聽到時愣了一下,那反應像是「這是什麼問題?」「這要怎麼回答?」師傅想了一下說,那時候出路沒有很多啊,「要不工廠工作,不然就當學徒,除非你念書念得很好,或是家境不錯可以培養。」「我是跟我大哥學,我大哥是跟一個 Canon 的師傅學。」一副理所當然,哪有什麼為什麼。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