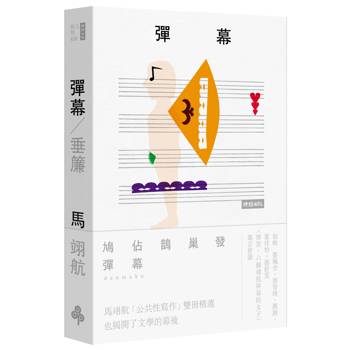片刻的指認
移動不多的夏日,我向家裡附近的花藝工作室,定了花材包。猩紅、毛綠、掌型葉的熱帶風格,包在牛皮紙束裡,隱密而豪華。也追加了一朵粉紅色的芍藥,玻璃紙限縮它豐沛的複瓣,在機車後座吹風的花,看起來像逃亡。第一次擁有一朵芍藥,它的氣息與光場,祕密地將房間帳了起來。它來自哪裡?它能保持多久?半透明的花瓣包圍花藥,我躺在床上,在略帶奢侈的「只是看著」的時間,察覺那嬌薄的片狀,收藏一種悚然的威武。觀察那一層一層地展開,又展開,不知為何,使人有種退與還的驚懼。
柴柏松的詩集《許多無名無姓的角落》,也像某些質地迷幻的植物,例如琉璃唐棉。纖薄的霧覆在書上,像粉翅滲出水光,移開書衣,其實是藍粉末披在粉紅墨痕。詩集裡的〈藍色矢車菊〉,旋開了砂穴,在那無動於衷的世界,時間的頸子內,有一種陷落與流亡在發生。〈一滴藍絲柏是一個童年童年的時差〉寫,「如果你知道氣味如何使記憶喚起多年前某個散失的畫面,它將擁有自己的生命,與另一種結局和情節。」文字與氣味同時在引渡。但記憶其實就是那植有荔枝樹的深林,盤據,停息,漲縮,插滿了許多關於「留神」的警戒牌。
芍藥香味清淡,需要主動尋思。跟原先房裡的絲柏精油相撞,空間中心的無色並不空曠,像石雨打落木枝,各有敗退與佔領--我聞到的是氣味的傷痕。看與聞,本質上是一種認領,光線,色彩,記憶原是自由的。Mei-Mei Berssenbrugge的〈你好,玫瑰〉,是這樣與玫瑰的質量相遇:
整朵玫瑰、流動空氣中的花瓣、香氣的情感,被記錄為一個球體,所以當我回想起那情感,我觸碰到維度。
從一個小花苞冒出,緊旋束狀珊瑚色嬰兒皮膚的花瓣,以半球體托住,彷彿讓杯狀的手掌捧住。
花瓣不可勝數,散狀,複疊,豪華,統一。
柏松詩集的〈自序〉有這樣一句「而在那片刻的指認之中,也彰顯了接下來我和這個人的關係,它是這樣具有開放性的,在一個人又一個人身上,打開詮釋的路徑。」說的是性別,但也不只是性別。Mei-Mei Berssenbrugge〈慢下來,現在〉裡說:「某天,你需要一種你不認得的植物,為了把你身體裡的碎片連起來,或者,碎片是在那個你想在一起的人裡面。」是植物,但也不只是植物。上星期我在都蘭山徑上,初次見到紫葉旗唇蘭,花朵細小,兩顆14級字的尺寸。它有獨立的花季,早於我片刻的指認以前又以前。
山並非自然站在那裡:帕里西歐.古茲曼的《浮山若夢》
回憶(Recordar):源自拉丁文re-cordis,意為再次經過心靈。
--愛德華多.加萊亞諾
帕里西歐.古茲曼的影像充滿暴力的餘震。包含古茲曼在內的「說話的人」,都是「活下來的人」,而為了「能夠訴說」,他們必須暫時或持續掩蓋,他們過去是如何被強烈震盪,幾近銷毀。烏拉圭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與帕里西歐.古茲曼一樣,因為政變與獨裁恐怖統治而流亡他鄉,此後他們面對的,是滿懷挫折的愛,也是心靈與現實的戰爭,日日夜夜的塌陷與重建。
1973年的9月11日,擔任陸軍總司令的奧古斯托.皮諾切在美國政府支持下,發動了流血軍事政變,智利一夜變色。民選總統薩爾瓦多.阿言德(智利作家伊莎貝.阿言德的堂伯父)在政變中身亡,智利陷入長達17年的獨裁恐怖統治,至少三千人被虐殺或失蹤,冤獄人數超過兩萬七千人。數字之下,是無法統計數算的受傷靈魂。軍事獨裁與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下,日後的智利取得穩定的經濟成長,然而智利的資源,仍然持續地被掠奪,痛苦與受難的記憶被遺留在光照不到的角落。
古茲曼在《智利不會忘記》(1997)這部紀錄片中,他帶著紀錄政變始末的影片《智利之戰》重新回到智利。智利的年輕一代,關於軍事政變的記憶模糊,或者未曾經歷。影片中一群青年,原本仍在辯論是否認同當年政變,然而當他們看見《智利之戰》中的暴力鎮壓場景後,人人淚流滿面,無法言語。無論立場為何,都意識到自身記憶,以及這片土地的歷史是如何被掩埋遮蔽。不復記憶,不代表未曾存在--這是驅動《智利不會忘記》的核心與意志。古茲曼在「智利三部曲」,他則是以一次次的「返回」之姿,轉開記憶的可能鎖孔。
三部曲分別是《星空塵土》、《深海光年》、《浮山若夢》,他以九年的時間展開記憶的亮與暗,以星空、海洋、山脈撐開世界,附著記憶在人類身體腔室內的迴響。他的「返回」有不同意義與方式的重返現場,也以影像與想像,倒帶回溯各種起點,對時間與記憶之奧秘與無情,刻下漫長的感嘆。起點之前往往還有起點,人類的殘酷,冷漠與暴行,從來不因重覆而漸趨緩和。《星空塵土》讓天文學家、考古學者、受難者親人訴說他們的「尋找」。骨骼內的元素就是宇宙,骨骸細小的孔洞特寫一如隕石或星球地表,解讀千萬年以前的光線即是對星空考古,在沙漠中尋找親人的遺骸是否也是渺無盡頭的希望?影片中的婦人說,我真希望天文學家們,能以功能強大、探測太空的望遠鏡向沙漠照一照,也許就能看見裡面的骨骸。古茲曼的影像詩意不只停留在極大至極小的對比,宇宙、人類與微塵的聯繫與聯想。我們以為的優美奇想,暴露的是記憶痛楚與重量的無從比擬。
《深海光年》是三部曲中,「自然」、「事件」、「物件」彼此聯結最緊密的一部,但記憶的水壓也令人難以換氣。水組成人體,也是淚水與記憶。航行與海洋連結了原住民族的生命與世界觀,但那些如珍珠般貴重的體感、語言、技藝,又是從何時開始消逝?人類遺忘的不只是與水的親密,人類用水殺人:19世紀,一個用珍珠鈕扣被交換至英國「開化」的原住民(因為這枚鈕釦,他得名Jemmy Button),後來他得雖返回舊地,卻死在一個他並不意欲成為的身體與身份裡;打擊異己的皮諾切政權之下,「被失蹤的人」從直升機上投海,一如那些沈入水中,攀附生物與腐朽的船骸。影片中眾人模擬失蹤,重建地圖,回想瀕危的語言,補充屍體的重量--水是存有,也是流逝。他們「還原」了喪失本身。
《浮山若夢》是三部曲的終曲嗎?柯迪勒亞山脈俯瞰著聖地牙哥城,超越人類的時間。古茲曼在這部片的口白,告訴觀眾他如何離家又返家,家又如何不存。一如前兩部作品,以極大與極小的畫面剪接組成:終年積雪的五千公尺以上高山,岩石的紋理,收藏著失蹤者與鎮壓者腳步聲的地磚。山脈守護、收藏、紀錄了這個國家與城市的夢想與邪惡。
移動不多的夏日,我向家裡附近的花藝工作室,定了花材包。猩紅、毛綠、掌型葉的熱帶風格,包在牛皮紙束裡,隱密而豪華。也追加了一朵粉紅色的芍藥,玻璃紙限縮它豐沛的複瓣,在機車後座吹風的花,看起來像逃亡。第一次擁有一朵芍藥,它的氣息與光場,祕密地將房間帳了起來。它來自哪裡?它能保持多久?半透明的花瓣包圍花藥,我躺在床上,在略帶奢侈的「只是看著」的時間,察覺那嬌薄的片狀,收藏一種悚然的威武。觀察那一層一層地展開,又展開,不知為何,使人有種退與還的驚懼。
柴柏松的詩集《許多無名無姓的角落》,也像某些質地迷幻的植物,例如琉璃唐棉。纖薄的霧覆在書上,像粉翅滲出水光,移開書衣,其實是藍粉末披在粉紅墨痕。詩集裡的〈藍色矢車菊〉,旋開了砂穴,在那無動於衷的世界,時間的頸子內,有一種陷落與流亡在發生。〈一滴藍絲柏是一個童年童年的時差〉寫,「如果你知道氣味如何使記憶喚起多年前某個散失的畫面,它將擁有自己的生命,與另一種結局和情節。」文字與氣味同時在引渡。但記憶其實就是那植有荔枝樹的深林,盤據,停息,漲縮,插滿了許多關於「留神」的警戒牌。
芍藥香味清淡,需要主動尋思。跟原先房裡的絲柏精油相撞,空間中心的無色並不空曠,像石雨打落木枝,各有敗退與佔領--我聞到的是氣味的傷痕。看與聞,本質上是一種認領,光線,色彩,記憶原是自由的。Mei-Mei Berssenbrugge的〈你好,玫瑰〉,是這樣與玫瑰的質量相遇:
整朵玫瑰、流動空氣中的花瓣、香氣的情感,被記錄為一個球體,所以當我回想起那情感,我觸碰到維度。
從一個小花苞冒出,緊旋束狀珊瑚色嬰兒皮膚的花瓣,以半球體托住,彷彿讓杯狀的手掌捧住。
花瓣不可勝數,散狀,複疊,豪華,統一。
柏松詩集的〈自序〉有這樣一句「而在那片刻的指認之中,也彰顯了接下來我和這個人的關係,它是這樣具有開放性的,在一個人又一個人身上,打開詮釋的路徑。」說的是性別,但也不只是性別。Mei-Mei Berssenbrugge〈慢下來,現在〉裡說:「某天,你需要一種你不認得的植物,為了把你身體裡的碎片連起來,或者,碎片是在那個你想在一起的人裡面。」是植物,但也不只是植物。上星期我在都蘭山徑上,初次見到紫葉旗唇蘭,花朵細小,兩顆14級字的尺寸。它有獨立的花季,早於我片刻的指認以前又以前。
山並非自然站在那裡:帕里西歐.古茲曼的《浮山若夢》
回憶(Recordar):源自拉丁文re-cordis,意為再次經過心靈。
--愛德華多.加萊亞諾
帕里西歐.古茲曼的影像充滿暴力的餘震。包含古茲曼在內的「說話的人」,都是「活下來的人」,而為了「能夠訴說」,他們必須暫時或持續掩蓋,他們過去是如何被強烈震盪,幾近銷毀。烏拉圭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與帕里西歐.古茲曼一樣,因為政變與獨裁恐怖統治而流亡他鄉,此後他們面對的,是滿懷挫折的愛,也是心靈與現實的戰爭,日日夜夜的塌陷與重建。
1973年的9月11日,擔任陸軍總司令的奧古斯托.皮諾切在美國政府支持下,發動了流血軍事政變,智利一夜變色。民選總統薩爾瓦多.阿言德(智利作家伊莎貝.阿言德的堂伯父)在政變中身亡,智利陷入長達17年的獨裁恐怖統治,至少三千人被虐殺或失蹤,冤獄人數超過兩萬七千人。數字之下,是無法統計數算的受傷靈魂。軍事獨裁與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下,日後的智利取得穩定的經濟成長,然而智利的資源,仍然持續地被掠奪,痛苦與受難的記憶被遺留在光照不到的角落。
古茲曼在《智利不會忘記》(1997)這部紀錄片中,他帶著紀錄政變始末的影片《智利之戰》重新回到智利。智利的年輕一代,關於軍事政變的記憶模糊,或者未曾經歷。影片中一群青年,原本仍在辯論是否認同當年政變,然而當他們看見《智利之戰》中的暴力鎮壓場景後,人人淚流滿面,無法言語。無論立場為何,都意識到自身記憶,以及這片土地的歷史是如何被掩埋遮蔽。不復記憶,不代表未曾存在--這是驅動《智利不會忘記》的核心與意志。古茲曼在「智利三部曲」,他則是以一次次的「返回」之姿,轉開記憶的可能鎖孔。
三部曲分別是《星空塵土》、《深海光年》、《浮山若夢》,他以九年的時間展開記憶的亮與暗,以星空、海洋、山脈撐開世界,附著記憶在人類身體腔室內的迴響。他的「返回」有不同意義與方式的重返現場,也以影像與想像,倒帶回溯各種起點,對時間與記憶之奧秘與無情,刻下漫長的感嘆。起點之前往往還有起點,人類的殘酷,冷漠與暴行,從來不因重覆而漸趨緩和。《星空塵土》讓天文學家、考古學者、受難者親人訴說他們的「尋找」。骨骼內的元素就是宇宙,骨骸細小的孔洞特寫一如隕石或星球地表,解讀千萬年以前的光線即是對星空考古,在沙漠中尋找親人的遺骸是否也是渺無盡頭的希望?影片中的婦人說,我真希望天文學家們,能以功能強大、探測太空的望遠鏡向沙漠照一照,也許就能看見裡面的骨骸。古茲曼的影像詩意不只停留在極大至極小的對比,宇宙、人類與微塵的聯繫與聯想。我們以為的優美奇想,暴露的是記憶痛楚與重量的無從比擬。
《深海光年》是三部曲中,「自然」、「事件」、「物件」彼此聯結最緊密的一部,但記憶的水壓也令人難以換氣。水組成人體,也是淚水與記憶。航行與海洋連結了原住民族的生命與世界觀,但那些如珍珠般貴重的體感、語言、技藝,又是從何時開始消逝?人類遺忘的不只是與水的親密,人類用水殺人:19世紀,一個用珍珠鈕扣被交換至英國「開化」的原住民(因為這枚鈕釦,他得名Jemmy Button),後來他得雖返回舊地,卻死在一個他並不意欲成為的身體與身份裡;打擊異己的皮諾切政權之下,「被失蹤的人」從直升機上投海,一如那些沈入水中,攀附生物與腐朽的船骸。影片中眾人模擬失蹤,重建地圖,回想瀕危的語言,補充屍體的重量--水是存有,也是流逝。他們「還原」了喪失本身。
《浮山若夢》是三部曲的終曲嗎?柯迪勒亞山脈俯瞰著聖地牙哥城,超越人類的時間。古茲曼在這部片的口白,告訴觀眾他如何離家又返家,家又如何不存。一如前兩部作品,以極大與極小的畫面剪接組成:終年積雪的五千公尺以上高山,岩石的紋理,收藏著失蹤者與鎮壓者腳步聲的地磚。山脈守護、收藏、紀錄了這個國家與城市的夢想與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