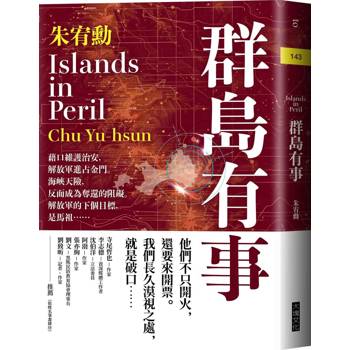第一部
水尾
他覺得海太可怕了,彷彿自己整個人就要被海壓倒似的,正當他想轉身回去的時候,偶然發現到前面靠近白色浪頭的海濱,正有四五個人聚在一起。
——呂赫若,〈風頭水尾〉
1
田浦水庫裡,一具男性身軀,正面朝下漂浮著。
那是我的。
很夜了,湖面有如暗室中的鏡子,鏡面內外兩個世界的影像都沒人看見。在第一批觀賞日出的觀光客抵達之前,暫時還不會有人發現我的新死。
載我來的那輛休旅車已經駛離,就像來時那樣低調,只引起了些許不大的波紋。沒有人看見那些波紋,也沒有人察覺休旅車微微散發出來的新鮮血腥味。包括我自己,也不算真切地「看見」。幾名精壯的、理著剽悍短髮的男子,剛剛才將我的身軀甩進田浦水庫。我不認識他們,但至少還慶幸一點:他們和一般的殺人犯不太一樣,沒有為了更徹底地隱匿罪跡,而將屍身分解;也沒有為了拖延事發的時間,在我屍身周邊繫上重物。
他們並不在乎——不,幾乎可以說,他們希望我早點被發現。
當然,最先發現我的是「水」。不,這不是在耍嘴皮子,雖然我很樂意博得一個白眼或笑容,如果我還能做得到的話。直到我陷入整座水庫的水體裡,我才知道,原來我一生都不曾真正認識「水」,不知道它們是一種有意志、有情感、能動作的族類。它們數量龐大,並且一體同心。整座島嶼上下左右,所有的水都彼此聯繫,不分鹹淡,都有著互相連通的集體意志,像是我生前看過的蟻群紀錄片。對它們而言,我的身軀落入湖中,與一粒飛沙飄落海面沒什麼差別。然而,在那一瞬間,每一滴水都分毫不差地記住了所有震波。在它們的懷裡,我面部朝下,屍身舒展開來,彷彿只是夜間偷偷戲水的觀光客。細小的氣泡聚集在我的膚表,浸透衣物,試探性滲入我每一處粗細不一的孔竅。我感受到它們好奇旋繞的影跡。它們拂掠而過,推搡著逐漸僵硬的肌肉。然後它們擴散開來,把我的氣味帶到水庫的每一個角落。
於是,魚群也好奇地聚攏了過來。田浦水庫是人為築起的,魚種本不算太複雜——我很瞭解這個地方,我寫過一系列關於「兩岸通水」的報導。大部分的小魚碰了碰我,很快就失去興趣。沒多久,還環繞著我的,大多都是肉食性的曲腰魚了。啊,曲腰魚,這些和我一樣,本不屬於這座島嶼的族類,如今已經繁衍眾多,以這座水庫為樂園了。不過,現在的牠們,似乎不像平常那樣害羞,紛紛從水底的藏身處圍攏過來。曲腰魚挺著微微翹起的唇吻,比水流更加點狀地啄咬漸漸浮腫的我。人類的身體,並不是曲腰魚習慣的食物,牠們嚥不下我那麼龐然的身軀。然而,在一回一回的啄咬裡,我身上剝落下來的皮屑,竟然讓曲腰魚群第一次體味到了「鄉愁」。沒錯,你們認得吧。對你們而言,我周身的氣味大部分都是陌生的,唯有軀幹上那幾十道鈍器重毆瘀血的傷處,散發了一點點曲腰魚群雖然不見得嘗過,卻已然記憶在基因裡的氣息。那是來自窄窄的海的另一邊,另一群古老陸塊上的人,他們身上的暴烈與生臊。魚群因此躁動而困惑,在我身邊又聚又散,終於把我最後的血汙擴散到整個田浦水庫。水從懷抱裡感受到了,於是發出了水域與水域才能共鳴的,類似嘆息的振波。
終於啊,雖然還是沒有任何人類聽到:這是最早最早的開戰訊號,而我是第一名陣亡者。
2
照理說,我不應當還有意識,因為我已經死了。
——我本來想這麼說的。但仔細一想,我並沒有死過,也沒有訪調過任何一名死者,所以其實沒有「理」可以「照說」。即便我現在已經死去,我也沒有見到其他亡靈,可以和他們交換經驗。所以,我也沒有辦法確定,我此刻的狀態是通案還是特例。再說了,就算我能夠搞清楚死後世界如何運作,也沒有辦法告訴任何人。
我甚至也無法確定,我的自言自語,是不是有人在聽。
啊。有點欣慰:和父親的溝通,不是唯一困難的事了。現在,我是與誰也沒辦法心意相通了,對於大半生奔走在群島之間,努力讓彼此稍通聲息的我來說,還真是最精準的刑罰了。
還是說,這就是「地獄」的樣子呢?不是千萬靈魂在煉獄燒烤,而是獨自一鬼漂浮在無人知曉的水域,掏擲無人回應的話語。
然而,我也並非一直意識清醒。死去的那一瞬間,就像猛然灌下烈酒而斷片那樣,所有尖銳的鈍重的疼痛同時消失,連時間感都被徹底擊碎。在體感上,幾乎就是斷片的下半秒,便立即感覺到田浦水庫濃烈的水草腥味,已然掩進了我的口鼻。但我赫然發現,我不會、也無法再被水嗆到了。於是,一點抵抗也沒有地,水流湧進了我的體內,稀釋了我本就損失不少的血液。水前進得很慢,因為早已沒有心臟來協助循環。但是水有它們的意志,也有它們不為人知的動能,一個分子接著一個分子,如同陣地戰那樣的緩慢滲透,還是讓水抵達了我身軀深處,某個內視鏡也找不到的隱密核心……。
我徹底「醒」了過來。
不,沒有睜開眼,不是那種恐怖片的情節。
就只是意識清醒,身軀仍然浮沉著,彷彿裝睡的孩子。
水分子繼續推進,一滴一滴替代我的血液,內內外外占據了我。這不合理,我的記憶如此抗議——猶記得在哪則新聞採訪裡,聽一位法醫說過:死亡後才落水的大體,由於循環系統已經停止運作,水是不可能大舉灌入體內的。然而水並不理會抗議,雖然它們似乎對記憶充滿興趣。如果有人能看見的話,或許會以為,我的肉身正以超乎尋常的速度浮腫、腐敗、潰散,無悲無喜,所有情緒都淡然遠去。但我的感受卻恰恰相反,水分子與微生物所到之處,它們所碰觸的每個部位,所有看似破壞、看似分解的沖刷,都更像是療癒與修復。身體只是回到生命的本來面目,浮腫、腐敗、潰散。漸漸地,湖水徹底占領了每一段微末的管竅,我的意識也隨之越來越清明,甚至超越了此生的任何一段時間。我開始能聽到以前聽不到的,看見以前不可能看見的。
就像是……。
就像是水把它們的感官借給了我一樣……它要我回憶,要我召喚所有曾有過的感受,因為它飽含億萬年來的一切回憶,從而也對我,這樣一個意外來到金門的青年人,有著毫不遺漏的好奇。它的探詢含蓄而堅定,以小小的漩渦,盤據在它有興趣的地方,反覆撫觸摩挲。如果我願意應答,它便會以更加強韌的耐心,滲透到我的腦裡、心裡、任何一個存放了感官與思緒之處……。
然後,和我一起,把已經歷和未經歷的故事,重新想一次。
3
首先,是後腦。
水流包覆住後腦,徒勞地冷卻著傷處。不必是專業的法醫,就能看出那是真正的致命傷。我並沒有看見甩棍擊中後腦的畫面,我唯一「看見」的,是棍棒落下時,從眼球後方漫掩而出的,帶有負片意味的黑霧。原來死去是那麼簡單的事,這應當是我最後半個念頭。那一瞬間很短,卻仍足以隱隱約約地在腦海裡抱怨:既然如此,前面那幾十分鐘的毆打,豈不都是浪費時間嗎?
當然,在他們眼中,這一切都不會浪費。天很快會亮,位在金門最東面的田浦水庫,是島上最熱門的日出景點。即便不是旺季,也總是有觀光客會驅車前來,在薄薄的黑暗裡等待。然後,他們就會發現淺水處,有一具面朝下的身軀。他們的驚叫會把一群曲腰魚嚇回水底的石窟,並且迅速引來這島上很少出動的刑警。警察局的發言人,會以困惑與驚奇兼有的語氣告訴記者:「本縣治安向來良好,如此殘酷的虐殺案件十分罕見。」除了後腦的致命傷之外,死者身上仍有近百處傷口,研判是因棍棒、石塊或硬底的皮鞋造成的。並且,從致傷的角度來看,至少有四人出手毆擊,甚至可能更多。死者在生前最後一段時間,應該受到長時間的虐打,然後才以甩棍處決,手法凶殘、毫無猶豫。
記者會問:這是仇殺事件嗎?
警局發言人遲疑了半秒,最後只說:犯案動機與過程,還需要進一步調查才能釐清。
警察的直覺是準確的,只是不能說出口。
從他呼吸裡散出的水汽,我聽到他欲言又止的心思。
這是警告。這不是仇殺。
仇恨多少會讓人興奮,讓人失控。但是,我身上的傷處,下手的力道與位置,在在顯示了他們的專業與冷靜。
沒錯,就是你猜的那樣子。如果他也聽得到水分子裡面,我所漫散出去的意念,他就會聽到我的嘉許:沒錯,你是個敏銳的好警察。
但他聽不見我。水分子猶如單向的電報,一滴一滴向我傳來世界的訊息。然而我的意念,就算已經隨著水蒸氣擴散全島,也沒有一個人類會聽到。
原來這就是靈魂的存在狀態嗎。人們時而覺得自己見過亡靈,時而斥為無稽之談,原來,只是因為水的性質:它們確實存在,但你們不一定都能看見。
人們只能感知非常狹窄的事物。線條,顏色,音訊,影像。透過遍布海底的電纜,所有訊號從金門島傳送回到台灣島,然後又漫射到更大的陸塊或更小的島嶼。符號在電纜裡面遊走,而我寄意念於晃動的海水之中,無法滲入,無法腐蝕,當然也就無法阻止它們傳遞。
父親啊,父親。
你若看到我凹陷的後腦,乾涸又被浸濕的血漬,你會露出怎樣的表情呢?
可惜,我似乎只能寄寓在金門的水體之中,去不了更遠的地方。去不了澎湖,去不了台灣。當然,更去不了海纜能夠輾轉抵達的家鄉,我那多坡多風的,瑩白剛硬的北竿……。
曲腰魚圍著我的屍身,輕輕啄吻。
別擔心呀,這樣的身體,已經不會再流淚了。
已是無喜怨悲怖,連血液都被置換成湖水的身軀……。
4
北竿是太小的島。或者應該說,就我和父親的關係而言,馬祖的五大島加起來,都是太小的島。
整個童年,我甚至常常忘記自己叫作曹以欽。當我放學走出塘岐國小,在島上最大的十字路口附近晃蕩,時時會聽到大人的耳語:那是曹祥官的兒子。不,別誤會,不是惡意的那種指指點點。正好相反。很小很小的時候,我就能聽出他們語氣裡的真誠、溫藹以及敬意。在耳語裡,我認識每一位大人,以及他們和父親之間的關係。多少家庭有人生了重病,曹祥官一通電話,就在台北排到了最好的病房和最有名的醫師;哪一家人又在東引辦事的時候,靠曹祥官坐上了本來不能出動的直升機,才見到老母親的最後一面……。
從有記憶起,我就知道自己的幸福,因為我生在能帶給所有鄰人幸福的曹祥官的家裡。
三十多年來,我的父親曹祥官,是馬祖唯一的那一席立委。
「唯一」不只是因為「選區劃分如此」,更是因為,包括我在內,我們想像不出來,還有誰能跟我的父親一樣,那麼適合坐住這一席立委。
念高中時,因為國民黨內部分裂,我父親退黨參選。國民黨提名的,是已經退休幾年的老縣長;民進黨則趁勢挖牆腳,提名了時任連江縣議會議長。我每天坐交通船到南竿上學,新聞沸沸揚揚,說馬祖許久沒有出現「三腳督」局面,恐怕真有機會變天;就算不變天,曹祥官大概也很難輕鬆過關。交通船上,連觀光客都在討論這件事。他們說,果然地方派系還是只能靠地方派系對付啊。有的人還會刻意放大聲量:真搞不懂,為什麼馬祖人都選出這種親中的立委?話畢,斜眼瞄了瞄穿著制服,在小風浪裡背單字的我們。
那時,我的後腦仍然渾圓無損,細草般的短髮總是有汗光。
自幼,父親最喜歡扶摸我非但不扁平、不凹陷,甚至有點球狀的後腦。
「這是福相。」
大多數人在嬰兒時期,頭骨還軟的時候,就不小心睡扁了。為了保護頭型,台北的許多家長甚至會購買輔具,或者讓小孩趴睡。但是,我似乎天賦頭型,父母沒怎麼特別照看,就這樣渾圓地長大。老一輩人說,頭腦渾圓的孩子聰明活潑,貼心好帶。我的學校成績確實還可以,但是否貼心就難說了,活潑更是稱不上。畢竟,母親在我十歲那年逝世後,我就由姑姑照看了。那時候開始,我就發現,其實人的一天並不需要說那麼多話。
父親每每從台北開會回來,便會用掌心撫著我的後腦。
「唉。」父親有時會說:「畢竟還是生了一副好相貌給你。」
那是在他想念母親的時候。對他們那一代人來說,這似乎就是愛情的極限了。我就這樣頂著泛青色的頭皮,沉默地看著那個頂著曹祥官之名,地方上無人不曉的中年男人,在島與島之間遊走。他能在幾通電話間,叫到二十分鐘飛抵東引的軍方直升機。但是他不,他更喜歡帶一名助理,和所有民眾一起坐兩個小時的船。他說,你不知道這兩個小時,可以和多少人講上多少話,又可以從中探知多少對手的動向。為什麼要告訴我這些?有時我會有明知故問的欲望,但最後都忍住了。
我畢竟是他即將成年的獨子。是最能繼承「曹祥官」這個名字,及其象徵的一切的人。
我沒有表現出熱誠,也沒有表現出反感。事實是,高中的我也不確定自己未來想做什麼。只是偶爾看到網路上激昂的新聞標題,會有種仿若平行時空的魔幻感。
三腳督?變天?可是,老縣長和議長,明明才前後來過家裡,對姑姑的一手好菜讚不絕口。
票一開出來,台北的媒體盡皆震驚。於是又出現了更多文章、影片,分析曹祥官為何能在連江縣坐島為王,顛撲不破。
島上的鄰居則安詳如常,遠遠看到我依然會說:那個曹祥官的兒子,長這麼大了!
也許就是那時開始,我對新聞工作有了興趣。
到底那些記者,是怎麼錯得這麼離譜的——這不是很簡單的,我每天身處其中的事實嗎?
高中畢業,我只填了兩個新聞系的志願,一個是目標,一個是保底。
最後,我進了世新新聞系。
父親自始至終都知道,他並不反對。毋寧說,他也許還有一點點高興。畢竟先當幾年記者,有一些媒體人脈之後,再來考慮子承父業,也是一條不錯的路徑。但他是一名有耐心的父親,正如他是一名有耐心與選民長談的立委。他沒有直接說破,我也就懷抱著霧氣般的不置可否,搬進了台北的宿舍。
水尾
他覺得海太可怕了,彷彿自己整個人就要被海壓倒似的,正當他想轉身回去的時候,偶然發現到前面靠近白色浪頭的海濱,正有四五個人聚在一起。
——呂赫若,〈風頭水尾〉
1
田浦水庫裡,一具男性身軀,正面朝下漂浮著。
那是我的。
很夜了,湖面有如暗室中的鏡子,鏡面內外兩個世界的影像都沒人看見。在第一批觀賞日出的觀光客抵達之前,暫時還不會有人發現我的新死。
載我來的那輛休旅車已經駛離,就像來時那樣低調,只引起了些許不大的波紋。沒有人看見那些波紋,也沒有人察覺休旅車微微散發出來的新鮮血腥味。包括我自己,也不算真切地「看見」。幾名精壯的、理著剽悍短髮的男子,剛剛才將我的身軀甩進田浦水庫。我不認識他們,但至少還慶幸一點:他們和一般的殺人犯不太一樣,沒有為了更徹底地隱匿罪跡,而將屍身分解;也沒有為了拖延事發的時間,在我屍身周邊繫上重物。
他們並不在乎——不,幾乎可以說,他們希望我早點被發現。
當然,最先發現我的是「水」。不,這不是在耍嘴皮子,雖然我很樂意博得一個白眼或笑容,如果我還能做得到的話。直到我陷入整座水庫的水體裡,我才知道,原來我一生都不曾真正認識「水」,不知道它們是一種有意志、有情感、能動作的族類。它們數量龐大,並且一體同心。整座島嶼上下左右,所有的水都彼此聯繫,不分鹹淡,都有著互相連通的集體意志,像是我生前看過的蟻群紀錄片。對它們而言,我的身軀落入湖中,與一粒飛沙飄落海面沒什麼差別。然而,在那一瞬間,每一滴水都分毫不差地記住了所有震波。在它們的懷裡,我面部朝下,屍身舒展開來,彷彿只是夜間偷偷戲水的觀光客。細小的氣泡聚集在我的膚表,浸透衣物,試探性滲入我每一處粗細不一的孔竅。我感受到它們好奇旋繞的影跡。它們拂掠而過,推搡著逐漸僵硬的肌肉。然後它們擴散開來,把我的氣味帶到水庫的每一個角落。
於是,魚群也好奇地聚攏了過來。田浦水庫是人為築起的,魚種本不算太複雜——我很瞭解這個地方,我寫過一系列關於「兩岸通水」的報導。大部分的小魚碰了碰我,很快就失去興趣。沒多久,還環繞著我的,大多都是肉食性的曲腰魚了。啊,曲腰魚,這些和我一樣,本不屬於這座島嶼的族類,如今已經繁衍眾多,以這座水庫為樂園了。不過,現在的牠們,似乎不像平常那樣害羞,紛紛從水底的藏身處圍攏過來。曲腰魚挺著微微翹起的唇吻,比水流更加點狀地啄咬漸漸浮腫的我。人類的身體,並不是曲腰魚習慣的食物,牠們嚥不下我那麼龐然的身軀。然而,在一回一回的啄咬裡,我身上剝落下來的皮屑,竟然讓曲腰魚群第一次體味到了「鄉愁」。沒錯,你們認得吧。對你們而言,我周身的氣味大部分都是陌生的,唯有軀幹上那幾十道鈍器重毆瘀血的傷處,散發了一點點曲腰魚群雖然不見得嘗過,卻已然記憶在基因裡的氣息。那是來自窄窄的海的另一邊,另一群古老陸塊上的人,他們身上的暴烈與生臊。魚群因此躁動而困惑,在我身邊又聚又散,終於把我最後的血汙擴散到整個田浦水庫。水從懷抱裡感受到了,於是發出了水域與水域才能共鳴的,類似嘆息的振波。
終於啊,雖然還是沒有任何人類聽到:這是最早最早的開戰訊號,而我是第一名陣亡者。
2
照理說,我不應當還有意識,因為我已經死了。
——我本來想這麼說的。但仔細一想,我並沒有死過,也沒有訪調過任何一名死者,所以其實沒有「理」可以「照說」。即便我現在已經死去,我也沒有見到其他亡靈,可以和他們交換經驗。所以,我也沒有辦法確定,我此刻的狀態是通案還是特例。再說了,就算我能夠搞清楚死後世界如何運作,也沒有辦法告訴任何人。
我甚至也無法確定,我的自言自語,是不是有人在聽。
啊。有點欣慰:和父親的溝通,不是唯一困難的事了。現在,我是與誰也沒辦法心意相通了,對於大半生奔走在群島之間,努力讓彼此稍通聲息的我來說,還真是最精準的刑罰了。
還是說,這就是「地獄」的樣子呢?不是千萬靈魂在煉獄燒烤,而是獨自一鬼漂浮在無人知曉的水域,掏擲無人回應的話語。
然而,我也並非一直意識清醒。死去的那一瞬間,就像猛然灌下烈酒而斷片那樣,所有尖銳的鈍重的疼痛同時消失,連時間感都被徹底擊碎。在體感上,幾乎就是斷片的下半秒,便立即感覺到田浦水庫濃烈的水草腥味,已然掩進了我的口鼻。但我赫然發現,我不會、也無法再被水嗆到了。於是,一點抵抗也沒有地,水流湧進了我的體內,稀釋了我本就損失不少的血液。水前進得很慢,因為早已沒有心臟來協助循環。但是水有它們的意志,也有它們不為人知的動能,一個分子接著一個分子,如同陣地戰那樣的緩慢滲透,還是讓水抵達了我身軀深處,某個內視鏡也找不到的隱密核心……。
我徹底「醒」了過來。
不,沒有睜開眼,不是那種恐怖片的情節。
就只是意識清醒,身軀仍然浮沉著,彷彿裝睡的孩子。
水分子繼續推進,一滴一滴替代我的血液,內內外外占據了我。這不合理,我的記憶如此抗議——猶記得在哪則新聞採訪裡,聽一位法醫說過:死亡後才落水的大體,由於循環系統已經停止運作,水是不可能大舉灌入體內的。然而水並不理會抗議,雖然它們似乎對記憶充滿興趣。如果有人能看見的話,或許會以為,我的肉身正以超乎尋常的速度浮腫、腐敗、潰散,無悲無喜,所有情緒都淡然遠去。但我的感受卻恰恰相反,水分子與微生物所到之處,它們所碰觸的每個部位,所有看似破壞、看似分解的沖刷,都更像是療癒與修復。身體只是回到生命的本來面目,浮腫、腐敗、潰散。漸漸地,湖水徹底占領了每一段微末的管竅,我的意識也隨之越來越清明,甚至超越了此生的任何一段時間。我開始能聽到以前聽不到的,看見以前不可能看見的。
就像是……。
就像是水把它們的感官借給了我一樣……它要我回憶,要我召喚所有曾有過的感受,因為它飽含億萬年來的一切回憶,從而也對我,這樣一個意外來到金門的青年人,有著毫不遺漏的好奇。它的探詢含蓄而堅定,以小小的漩渦,盤據在它有興趣的地方,反覆撫觸摩挲。如果我願意應答,它便會以更加強韌的耐心,滲透到我的腦裡、心裡、任何一個存放了感官與思緒之處……。
然後,和我一起,把已經歷和未經歷的故事,重新想一次。
3
首先,是後腦。
水流包覆住後腦,徒勞地冷卻著傷處。不必是專業的法醫,就能看出那是真正的致命傷。我並沒有看見甩棍擊中後腦的畫面,我唯一「看見」的,是棍棒落下時,從眼球後方漫掩而出的,帶有負片意味的黑霧。原來死去是那麼簡單的事,這應當是我最後半個念頭。那一瞬間很短,卻仍足以隱隱約約地在腦海裡抱怨:既然如此,前面那幾十分鐘的毆打,豈不都是浪費時間嗎?
當然,在他們眼中,這一切都不會浪費。天很快會亮,位在金門最東面的田浦水庫,是島上最熱門的日出景點。即便不是旺季,也總是有觀光客會驅車前來,在薄薄的黑暗裡等待。然後,他們就會發現淺水處,有一具面朝下的身軀。他們的驚叫會把一群曲腰魚嚇回水底的石窟,並且迅速引來這島上很少出動的刑警。警察局的發言人,會以困惑與驚奇兼有的語氣告訴記者:「本縣治安向來良好,如此殘酷的虐殺案件十分罕見。」除了後腦的致命傷之外,死者身上仍有近百處傷口,研判是因棍棒、石塊或硬底的皮鞋造成的。並且,從致傷的角度來看,至少有四人出手毆擊,甚至可能更多。死者在生前最後一段時間,應該受到長時間的虐打,然後才以甩棍處決,手法凶殘、毫無猶豫。
記者會問:這是仇殺事件嗎?
警局發言人遲疑了半秒,最後只說:犯案動機與過程,還需要進一步調查才能釐清。
警察的直覺是準確的,只是不能說出口。
從他呼吸裡散出的水汽,我聽到他欲言又止的心思。
這是警告。這不是仇殺。
仇恨多少會讓人興奮,讓人失控。但是,我身上的傷處,下手的力道與位置,在在顯示了他們的專業與冷靜。
沒錯,就是你猜的那樣子。如果他也聽得到水分子裡面,我所漫散出去的意念,他就會聽到我的嘉許:沒錯,你是個敏銳的好警察。
但他聽不見我。水分子猶如單向的電報,一滴一滴向我傳來世界的訊息。然而我的意念,就算已經隨著水蒸氣擴散全島,也沒有一個人類會聽到。
原來這就是靈魂的存在狀態嗎。人們時而覺得自己見過亡靈,時而斥為無稽之談,原來,只是因為水的性質:它們確實存在,但你們不一定都能看見。
人們只能感知非常狹窄的事物。線條,顏色,音訊,影像。透過遍布海底的電纜,所有訊號從金門島傳送回到台灣島,然後又漫射到更大的陸塊或更小的島嶼。符號在電纜裡面遊走,而我寄意念於晃動的海水之中,無法滲入,無法腐蝕,當然也就無法阻止它們傳遞。
父親啊,父親。
你若看到我凹陷的後腦,乾涸又被浸濕的血漬,你會露出怎樣的表情呢?
可惜,我似乎只能寄寓在金門的水體之中,去不了更遠的地方。去不了澎湖,去不了台灣。當然,更去不了海纜能夠輾轉抵達的家鄉,我那多坡多風的,瑩白剛硬的北竿……。
曲腰魚圍著我的屍身,輕輕啄吻。
別擔心呀,這樣的身體,已經不會再流淚了。
已是無喜怨悲怖,連血液都被置換成湖水的身軀……。
4
北竿是太小的島。或者應該說,就我和父親的關係而言,馬祖的五大島加起來,都是太小的島。
整個童年,我甚至常常忘記自己叫作曹以欽。當我放學走出塘岐國小,在島上最大的十字路口附近晃蕩,時時會聽到大人的耳語:那是曹祥官的兒子。不,別誤會,不是惡意的那種指指點點。正好相反。很小很小的時候,我就能聽出他們語氣裡的真誠、溫藹以及敬意。在耳語裡,我認識每一位大人,以及他們和父親之間的關係。多少家庭有人生了重病,曹祥官一通電話,就在台北排到了最好的病房和最有名的醫師;哪一家人又在東引辦事的時候,靠曹祥官坐上了本來不能出動的直升機,才見到老母親的最後一面……。
從有記憶起,我就知道自己的幸福,因為我生在能帶給所有鄰人幸福的曹祥官的家裡。
三十多年來,我的父親曹祥官,是馬祖唯一的那一席立委。
「唯一」不只是因為「選區劃分如此」,更是因為,包括我在內,我們想像不出來,還有誰能跟我的父親一樣,那麼適合坐住這一席立委。
念高中時,因為國民黨內部分裂,我父親退黨參選。國民黨提名的,是已經退休幾年的老縣長;民進黨則趁勢挖牆腳,提名了時任連江縣議會議長。我每天坐交通船到南竿上學,新聞沸沸揚揚,說馬祖許久沒有出現「三腳督」局面,恐怕真有機會變天;就算不變天,曹祥官大概也很難輕鬆過關。交通船上,連觀光客都在討論這件事。他們說,果然地方派系還是只能靠地方派系對付啊。有的人還會刻意放大聲量:真搞不懂,為什麼馬祖人都選出這種親中的立委?話畢,斜眼瞄了瞄穿著制服,在小風浪裡背單字的我們。
那時,我的後腦仍然渾圓無損,細草般的短髮總是有汗光。
自幼,父親最喜歡扶摸我非但不扁平、不凹陷,甚至有點球狀的後腦。
「這是福相。」
大多數人在嬰兒時期,頭骨還軟的時候,就不小心睡扁了。為了保護頭型,台北的許多家長甚至會購買輔具,或者讓小孩趴睡。但是,我似乎天賦頭型,父母沒怎麼特別照看,就這樣渾圓地長大。老一輩人說,頭腦渾圓的孩子聰明活潑,貼心好帶。我的學校成績確實還可以,但是否貼心就難說了,活潑更是稱不上。畢竟,母親在我十歲那年逝世後,我就由姑姑照看了。那時候開始,我就發現,其實人的一天並不需要說那麼多話。
父親每每從台北開會回來,便會用掌心撫著我的後腦。
「唉。」父親有時會說:「畢竟還是生了一副好相貌給你。」
那是在他想念母親的時候。對他們那一代人來說,這似乎就是愛情的極限了。我就這樣頂著泛青色的頭皮,沉默地看著那個頂著曹祥官之名,地方上無人不曉的中年男人,在島與島之間遊走。他能在幾通電話間,叫到二十分鐘飛抵東引的軍方直升機。但是他不,他更喜歡帶一名助理,和所有民眾一起坐兩個小時的船。他說,你不知道這兩個小時,可以和多少人講上多少話,又可以從中探知多少對手的動向。為什麼要告訴我這些?有時我會有明知故問的欲望,但最後都忍住了。
我畢竟是他即將成年的獨子。是最能繼承「曹祥官」這個名字,及其象徵的一切的人。
我沒有表現出熱誠,也沒有表現出反感。事實是,高中的我也不確定自己未來想做什麼。只是偶爾看到網路上激昂的新聞標題,會有種仿若平行時空的魔幻感。
三腳督?變天?可是,老縣長和議長,明明才前後來過家裡,對姑姑的一手好菜讚不絕口。
票一開出來,台北的媒體盡皆震驚。於是又出現了更多文章、影片,分析曹祥官為何能在連江縣坐島為王,顛撲不破。
島上的鄰居則安詳如常,遠遠看到我依然會說:那個曹祥官的兒子,長這麼大了!
也許就是那時開始,我對新聞工作有了興趣。
到底那些記者,是怎麼錯得這麼離譜的——這不是很簡單的,我每天身處其中的事實嗎?
高中畢業,我只填了兩個新聞系的志願,一個是目標,一個是保底。
最後,我進了世新新聞系。
父親自始至終都知道,他並不反對。毋寧說,他也許還有一點點高興。畢竟先當幾年記者,有一些媒體人脈之後,再來考慮子承父業,也是一條不錯的路徑。但他是一名有耐心的父親,正如他是一名有耐心與選民長談的立委。他沒有直接說破,我也就懷抱著霧氣般的不置可否,搬進了台北的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