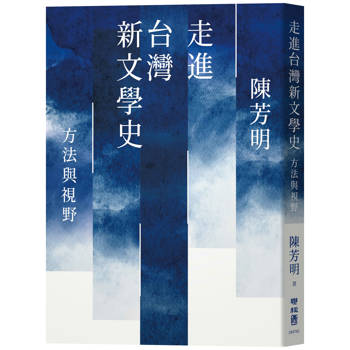第一章 後殖民史觀與歷史分期
為什麼是後殖民史觀
文學史書寫,牽涉到史家的政治立場與人文思考。從政治立場來看,一位右派思考的史家,可能會集中焦點於歷史過程中的主流價值。傳統的中國文學史,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的思想為基礎。儒家的文學史觀,表面上強調溫柔敦厚,事實上在書寫過程中卻往往排除異端。所謂異端,就是儒家所無法容忍的天下觀與政治觀。台灣學子受教過程中,最熟悉的思維方式莫過於「大一統」,「萬世一系」,「一以貫之」。所謂「一」,注重的是單一價值觀念。尤其是漢代以後,獨尊儒術的地位確立之後,就使多元、複數的觀念遭到封閉。這種單元論的價值觀念,甚至還放諸四海而皆準。因此,使一個屬於漢人的、男性的、異性戀的父權思維方式得以成立。這種大一統觀念,具體浮現在一個經典的論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是中國文化最早出現的霸權論述,再加上儒家思想的推波助瀾,正如儒家所說:「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換言之,這種同化的觀念根深蒂固,很早就深植在漢人的靈魂深處。
漢人文化凌駕於邊疆民族之上,已是習以為常的行為模式。文化的同化,在於強調「大同」。對於異族、異質的存在,都得不到文化上的寬容。這種歷史觀與文化觀的核心精神,就在於強調「同」(sameness),完全沒有空間容許平等性與差異性。從歷史書寫的內容來看,都可以發現千篇一律的模型。所有的「正史」,便是以帝王本紀作為開端,以王室為中心權力逐漸向周邊的土地擴張,最後才是有關邊疆或外國的書寫。二十五史相當有系統地貫穿了男性中心論,漢人中心論,異性戀中心論,從這樣的正史觀念延伸出去,文學史的書寫策略自然而然也符合這種要求。
凡是受過「中國通史」與「中國文學史」的教育訓練者,都相當熟悉這種文化位階(cultural hierarchy)的觀念。這種屹立不搖的位置,一直到一九七○年代的台灣歷史教育與文學教育,始終都沒有改變。伴隨著一九七○年代的黨外民主運動與鄉土文學運動,威權體制所堅持的儒家思想,才逐漸受到挑戰與質疑。確切而言,依附在戒嚴體制的文化中心論,自然而然也開始發生動搖。如果沒有威權體制的動搖,如果沒有民主運動的崛起,這種單元史觀與霸權史觀可能一直會沿用下去。在現階段的文學教育裡,大一統式的書寫其實還保留著一定程度的殘餘。民主運動帶來最大的衝擊,便是使人權觀念在漢人社會裡篤定浮現。人權觀念的確立,逐漸從政治層面而擴散到性別、階級、族群的文化領域。
民主運動的洗禮,無疑就是島上人權觀念的刷新。夾帶而來的衝擊,不能不使既有的歷史書寫模式受到改造。前面一章所提到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便是代表了一個轉變的信號。台灣的歷史與文學,一直受到中國霸權的支配。學界某些人曾經詬病《台灣文學史綱》過於簡略,這其實是皮毛之見。這部文學史的誕生,意味著一個全新思維的時代就要降臨。書中所暗藏的左翼史觀,便是從社會底層的弱者角度回望台灣文學發展的過程。這位文學史家已經開始注意到女性文學的存在,同時使歷史上毫無能見度的台灣本地作家大量浮出地表。這是一個重大突破,尤其在戒嚴體制還未宣告終結之前,他的文學史似乎已經預告下一輪的文化突破階段。
從台灣歷史的進程來看,一九八六年民主進步黨的成立,使得黨國體制終於遭到突破。政黨結構從單一變成雙元,預告了一個多元化的時代已經到來。更重要的是,葉石濤在戒嚴體制還未解除之前,就寫出了《台灣文學史綱》,1更是一種多元化的象徵。在黨國時期的歷史解釋,從政治史到文學史都完全受到國民黨的控制。葉石濤的文學史,另外開闢一個新的歷史軌跡,也意味著史觀多元化的時代已經到來。從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開始,一直到戒嚴體制宣布解除,四十二年已經過去,島上住民的心靈才有獲得解放的感覺。相對於非洲、拉丁美洲殖民地統治的終結,台灣社會的解放感可以說是遲到了。這說明了為什麼一九八七年代表著一個歷史的突破,具體而言,整個台灣的後殖民時期才正式降臨。
什麼是後殖民時期?正如前面所強調的,戰前的帝國統治與戰後的黨國支配,無論是政治結構、權力結構或文化結構,都受到嚴密的高度控制。所謂後殖民的「後」,指的是高壓統治結束之後,潛藏在社會底層的所有想像力,都全部釋放出來。這種文化想像跨越了族群、性別、階級,使過去未曾有過的創造能量獲得高度提升。當複數的、異質的能量爆發出來時,無疑是對過去的威權統治進行了強烈批判。後殖民所強調的正是這種批判精神,一方面糾正過去單方面的價值觀念,一方面則重新建構社會的文化主體。後殖民的主體重建,首要工作莫過於歷史記憶的恢復。從這個觀點來看,葉石濤所寫的《台灣文學史綱》就不容忽視。這位跨語言的資深作家,縱然對於中文書寫並不熟悉,卻願意窮畢生之力建構一部文學史。那種勇氣與識見,已經成為後殖民史觀的典範。
後殖民史觀,並非是全盤否定殖民地時期與再殖民時期的文學成就。一九四○年代的皇民化文學,一九五○年代的反共文學,無論內容的差異有多大,其為殖民體制的產物則完全相同。當一個社會開始發展出主體的解釋,同時對於過去被支配的文學產物具有反省能力時,歷史便開始進入另外一個全新的階段。從這個觀點來看,葉石濤的文學史觀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事件。沒有經過他,後來的文學史研究可能就不是今天這種樣貌。台灣文學研究開始進入一個開放、多元、異質的時期,使過去曾經被遮蔽或扭曲的美學精神與藝術內容又重見天日。後殖民強調的是文化的差異性與主體性,同時也在於強調邊緣文化的重要性。所謂邊緣文化,指的是女性、同志、原住民的文學生產力;這些邊緣文化所蘊藏的生產力,絕對高於殖民時期的主流文化。
文學史的建構,必須緊貼著歷史發展的脈絡進行觀察。過去的殖民史觀,大多側重於統治者所偏愛的主流價值。這種主流價值指的是男性、漢人、異性戀,並且以這三個元素作為歷史解釋的全部。在建構所有的知識論時,也從來不會脫離這三個元素,並且以這種觀點來解釋整個世界。只要權力的結構沒有改變,以這種知識論為基礎的世界觀,也從來不會改變。必須是殖民權力被顛覆了,偏頗的知識論才會跟著被顛覆。人類歷史走得那麼遙遠而漫長,已經非常習慣這種思維方式。一旦殖民體制瓦解之後,男性中心論、漢人中心論、異性戀中心論才開始受到挑戰並質疑。後殖民史觀的浮現,正代表一個新的知識地平線逐漸上升。歷史舞台上的女性、同志、原住民,曾經無法站在聚光燈下。後殖民史觀便是把舞台上的所有燈光都打亮,讓黑暗陰影裡不同族群、性別、階級的角色,終於都接受了聚光燈的照射。後殖民史觀的作用,便是讓所有被遮蔽的歷史主角全部都站到亮處。進入後殖民時期,我們才終於發現過去的歷史是如此精彩,如此豐富,如此多元。
為什麼是後殖民史觀
文學史書寫,牽涉到史家的政治立場與人文思考。從政治立場來看,一位右派思考的史家,可能會集中焦點於歷史過程中的主流價值。傳統的中國文學史,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的思想為基礎。儒家的文學史觀,表面上強調溫柔敦厚,事實上在書寫過程中卻往往排除異端。所謂異端,就是儒家所無法容忍的天下觀與政治觀。台灣學子受教過程中,最熟悉的思維方式莫過於「大一統」,「萬世一系」,「一以貫之」。所謂「一」,注重的是單一價值觀念。尤其是漢代以後,獨尊儒術的地位確立之後,就使多元、複數的觀念遭到封閉。這種單元論的價值觀念,甚至還放諸四海而皆準。因此,使一個屬於漢人的、男性的、異性戀的父權思維方式得以成立。這種大一統觀念,具體浮現在一個經典的論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是中國文化最早出現的霸權論述,再加上儒家思想的推波助瀾,正如儒家所說:「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換言之,這種同化的觀念根深蒂固,很早就深植在漢人的靈魂深處。
漢人文化凌駕於邊疆民族之上,已是習以為常的行為模式。文化的同化,在於強調「大同」。對於異族、異質的存在,都得不到文化上的寬容。這種歷史觀與文化觀的核心精神,就在於強調「同」(sameness),完全沒有空間容許平等性與差異性。從歷史書寫的內容來看,都可以發現千篇一律的模型。所有的「正史」,便是以帝王本紀作為開端,以王室為中心權力逐漸向周邊的土地擴張,最後才是有關邊疆或外國的書寫。二十五史相當有系統地貫穿了男性中心論,漢人中心論,異性戀中心論,從這樣的正史觀念延伸出去,文學史的書寫策略自然而然也符合這種要求。
凡是受過「中國通史」與「中國文學史」的教育訓練者,都相當熟悉這種文化位階(cultural hierarchy)的觀念。這種屹立不搖的位置,一直到一九七○年代的台灣歷史教育與文學教育,始終都沒有改變。伴隨著一九七○年代的黨外民主運動與鄉土文學運動,威權體制所堅持的儒家思想,才逐漸受到挑戰與質疑。確切而言,依附在戒嚴體制的文化中心論,自然而然也開始發生動搖。如果沒有威權體制的動搖,如果沒有民主運動的崛起,這種單元史觀與霸權史觀可能一直會沿用下去。在現階段的文學教育裡,大一統式的書寫其實還保留著一定程度的殘餘。民主運動帶來最大的衝擊,便是使人權觀念在漢人社會裡篤定浮現。人權觀念的確立,逐漸從政治層面而擴散到性別、階級、族群的文化領域。
民主運動的洗禮,無疑就是島上人權觀念的刷新。夾帶而來的衝擊,不能不使既有的歷史書寫模式受到改造。前面一章所提到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便是代表了一個轉變的信號。台灣的歷史與文學,一直受到中國霸權的支配。學界某些人曾經詬病《台灣文學史綱》過於簡略,這其實是皮毛之見。這部文學史的誕生,意味著一個全新思維的時代就要降臨。書中所暗藏的左翼史觀,便是從社會底層的弱者角度回望台灣文學發展的過程。這位文學史家已經開始注意到女性文學的存在,同時使歷史上毫無能見度的台灣本地作家大量浮出地表。這是一個重大突破,尤其在戒嚴體制還未宣告終結之前,他的文學史似乎已經預告下一輪的文化突破階段。
從台灣歷史的進程來看,一九八六年民主進步黨的成立,使得黨國體制終於遭到突破。政黨結構從單一變成雙元,預告了一個多元化的時代已經到來。更重要的是,葉石濤在戒嚴體制還未解除之前,就寫出了《台灣文學史綱》,1更是一種多元化的象徵。在黨國時期的歷史解釋,從政治史到文學史都完全受到國民黨的控制。葉石濤的文學史,另外開闢一個新的歷史軌跡,也意味著史觀多元化的時代已經到來。從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開始,一直到戒嚴體制宣布解除,四十二年已經過去,島上住民的心靈才有獲得解放的感覺。相對於非洲、拉丁美洲殖民地統治的終結,台灣社會的解放感可以說是遲到了。這說明了為什麼一九八七年代表著一個歷史的突破,具體而言,整個台灣的後殖民時期才正式降臨。
什麼是後殖民時期?正如前面所強調的,戰前的帝國統治與戰後的黨國支配,無論是政治結構、權力結構或文化結構,都受到嚴密的高度控制。所謂後殖民的「後」,指的是高壓統治結束之後,潛藏在社會底層的所有想像力,都全部釋放出來。這種文化想像跨越了族群、性別、階級,使過去未曾有過的創造能量獲得高度提升。當複數的、異質的能量爆發出來時,無疑是對過去的威權統治進行了強烈批判。後殖民所強調的正是這種批判精神,一方面糾正過去單方面的價值觀念,一方面則重新建構社會的文化主體。後殖民的主體重建,首要工作莫過於歷史記憶的恢復。從這個觀點來看,葉石濤所寫的《台灣文學史綱》就不容忽視。這位跨語言的資深作家,縱然對於中文書寫並不熟悉,卻願意窮畢生之力建構一部文學史。那種勇氣與識見,已經成為後殖民史觀的典範。
後殖民史觀,並非是全盤否定殖民地時期與再殖民時期的文學成就。一九四○年代的皇民化文學,一九五○年代的反共文學,無論內容的差異有多大,其為殖民體制的產物則完全相同。當一個社會開始發展出主體的解釋,同時對於過去被支配的文學產物具有反省能力時,歷史便開始進入另外一個全新的階段。從這個觀點來看,葉石濤的文學史觀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事件。沒有經過他,後來的文學史研究可能就不是今天這種樣貌。台灣文學研究開始進入一個開放、多元、異質的時期,使過去曾經被遮蔽或扭曲的美學精神與藝術內容又重見天日。後殖民強調的是文化的差異性與主體性,同時也在於強調邊緣文化的重要性。所謂邊緣文化,指的是女性、同志、原住民的文學生產力;這些邊緣文化所蘊藏的生產力,絕對高於殖民時期的主流文化。
文學史的建構,必須緊貼著歷史發展的脈絡進行觀察。過去的殖民史觀,大多側重於統治者所偏愛的主流價值。這種主流價值指的是男性、漢人、異性戀,並且以這三個元素作為歷史解釋的全部。在建構所有的知識論時,也從來不會脫離這三個元素,並且以這種觀點來解釋整個世界。只要權力的結構沒有改變,以這種知識論為基礎的世界觀,也從來不會改變。必須是殖民權力被顛覆了,偏頗的知識論才會跟著被顛覆。人類歷史走得那麼遙遠而漫長,已經非常習慣這種思維方式。一旦殖民體制瓦解之後,男性中心論、漢人中心論、異性戀中心論才開始受到挑戰並質疑。後殖民史觀的浮現,正代表一個新的知識地平線逐漸上升。歷史舞台上的女性、同志、原住民,曾經無法站在聚光燈下。後殖民史觀便是把舞台上的所有燈光都打亮,讓黑暗陰影裡不同族群、性別、階級的角色,終於都接受了聚光燈的照射。後殖民史觀的作用,便是讓所有被遮蔽的歷史主角全部都站到亮處。進入後殖民時期,我們才終於發現過去的歷史是如此精彩,如此豐富,如此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