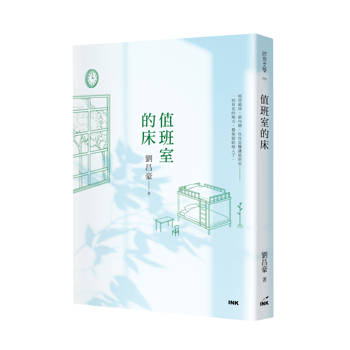Tiny Note
記起實習時候跟教學門診,開診之前,一群披掛著白袍的學生,總窩進主治醫師看診的座位後方,排成一列的圓形小凳,一張緊挨著一張坐下,一個個忙不迭地將頭埋進書本,就怕待會門診開診,得輪番坐上前頭看診的大位。沒來得及開口向病人問診,倒先被病人成堆的問題考倒。此際,眼尖的病人或會發現—後方每個醫學生的面孔看來雖是同樣生澀,可手上捧著的,卻是封面迥異、版本不一的書冊?
不錯,臨床知識的累積,並非義務教育的古文四十篇或聯立方程式,少了部編版課本,也未必有標準答案。兩、三年就更新一版的治療指引,不時就以簇新的檢查流程、用藥位階,將前一版推入歷史的行伍。大三記誦的藥物,等到大六畢業,療效早被新核准的藥物超前。住院醫師階段,終日在刀房苦行、磨礪而成的伎倆,等到升上主任,早已被新一代的器械、機械手臂取代。當醫學研究的論文發表呈指數成長,日新又新的科學實證,不僅推動醫療時代的齒輪,也鞭策一線醫護貫徹終身學習。
於是,課本寫的不總是等於正確答案,老師教的更多卻是過時資訊,醫學教育只好在幾十年前,就貫徹以學生報告,取代老師講課的翻轉教室。泰半是每兩週一次的英語報告,大夥輪流閱讀當期的學術刊物,及國際上的治療指引,爾或利用寒暑假,輪番出國交換、報名學術研討會,再將這些來不及編寫成冊的新知,收整成一篇、一篇的細瑣筆記。從傳統貼滿各色3M書籤及便利貼,大小恰好能塞入白袍口袋的小筆記本;爾或隨手拈來一張廢紙,就在背面,用三色原子筆抄起的潦草字跡(每次翻閱,都得如摩斯解密一般破譯)。時間來到當代,諸多筆記軟體橫跨手機、平板與網頁瀏覽器,拍照、截圖,俱能快速上傳數不清的書本內文或演講PPT—遂有略懂程式軟體的前輩,自個兒架起網站,取名「Tiny note」,讓樂善好施者,皆可新增頁面,貼上私房的筆記,成為實習醫師專屬的維基百科。於是一切的病歷報告、期刊重點、讀書摘要,俱開源式地供人品讀,不藏私、不隱匿,宣誓共享經濟的時代降臨。
那些筆記的上頭,或許是與疾病近距離搏擊以後,將種種戰果勝敗幾經編列、整理,成為其他人面對相同疾病的SOP;又或是主治醫師巡房時,隨口幾句經驗談,被抄寫成了逐字稿,使那畢生積攢的醫術得以流傳;抑或是分享不同的醫院,前人編纂成的工作手冊或教戰守則,經工人智慧式地交互比對、截長補短,擬出集各家大成的版本。
而我記憶最深刻的醫學筆記,是某一次的教學門診,病人報到的空檔,主治醫師見我們一群人熱烈翻找著書本,竟興奮地將隨身碟插入電腦,秀出由各種不同疾病的X光片,堆砌成的PPT檔,「這是我準備專科考試的筆記。我畢生所學,都整理在上頭了。」
於是我了解,每間門診的座椅上、每個手術台的邊旁,原來都祕密藏匿著一本微小的編年史。那裡頭,書寫著病情的章節、醫學的演化,分別在習醫的各個階段,逐一投稿、連載,輾轉成為一則一則篇幅各異,不斷迭代、演化的Tiny note—那些細小的文字,乘載了醫學的歷史、專科的知識;見過的病人、開過的藥方,還有動過的刀,與醫過的病。而這一切的微小足跡,日日夜夜地在不為人知的習醫里程中默默攢積—正是這些從醫院的各個邊角蒐羅而來,如拼圖般細瑣的筆記,一片鑲嵌過一片,組裝出每名醫師的腦中,那一幅碩大的醫學版圖。
這些筆記,因為微小,所以罕為人知。卻也正因它的微小,所以在漫漫行醫生涯中,顯得格外袖珍,並且別緻。
Off
從密封食物袋切出兩片吐司,銜著芝士樂起司片或塗抹Nutella可可醬,分別攤展於烤箱上下二層,旋鈕計時三分鐘。等待時,自冰箱取出預先泡製、冰鎮的三合一咖啡,再翻開一本村上春樹,就著窗外的細雨,津津地啜飲起來。如果前一日值夜班無事,又能準時交班準時off,命運許我的一個幸福早晨,當是如此。
「off」(一種可控的、機械式的隱喻),二十一世紀醫療最偉大的發明,是為值夜班的隔天,一日或半日的休假。十多年前,醫師未納勞基法,工時沒有上限。所謂的值班,便是從一早七、八點趕赴醫院晨會,緊接著是刀房、病房、門診、刀房、病房、急診……忙至傍晚六、七點,剛結束一日的「標準」工時,尚得留守在醫院,枕戈待旦:夜間辦入院的新病人、急診病人的專科照會,同時病房內病人的病情亦變幻莫測。無預警的一連串插管、電擊、CPR……待到隔天早上七、八點,復又拖著一日未梳洗、甚或未眠睡的軀殼,望回那機型老舊、畫面抖動,通宵一日看上去又更顯朦朧的晨會投影幕。好容易撐到一句今天晨會先到這邊,旋又接著繼續刀房、門診、病房、急診……待至向晚時分,方能步出醫院,等著明日,又一個超過三十四小時的值班日。
近年,各地屢傳醫師因過勞招致昏厥,甚或猝死,醫療工時勞權得到重視,才有了值班的隔日中午提前下班的PM off,乃至近年推行的,值班隔日的晨會結束就下班的Day off。「我今天off。你找cover我的○醫師。」於是任何不諳新制的來電,俱能以此為由回絕。
可疾病不受法規管轄。器官衰竭、敗血感染等重症病程往往來得迅猛,無早上、夜晚之別,亦沒有區分上班下班打卡。經常是(幾乎永遠是)在夜間或假日,人力俱乏的值班時段,無恙的病人突發高燒或哮喘、昏厥與癲癇,緊急處置一番後,遂將戰場轉至加護病房。當此時,仍未得勞基法保障的專科醫師、主治醫師,電話響徹,聽聞值班的下屬捎來病情,也不管是晝是夜,仍得盡責地在工時以外的時間,親赴醫院。
「以前覺得當醫生齁,坐在那邊講講話、開開藥就幾十萬入袋,實在好命。現在才知道,醫師工作不只歹命,怕是還會短命!」無怪乎逢年過節,但凡論及工時一事,長輩對我的態度便由羨煞,轉為同情了。
烤箱響起了。扳開烤門的時候,電子螢幕上亮閃著「OFF」的字樣。學生時代,初聞醫院慣用off來稱呼休假,以為那是種資本主義的、殖民式的征服,反映醫療體系亦難逃異化、生產工具化。可如今,一段無事之晨,足教人興起無比確幸與感恩。嘴邊銜起那烤得酥黃的吐司時,對著永遠按時開機、關機的氣炸烤箱,打從心底,我反倒湧起一股同我族類似的安慰,還有同情了。
時間的切片
我確信,那是一張罹病者的切片。
以脊柱為中心,上至頸椎,下至結腸,白色肋骨的細長投影,在暗片裡向著前方,伸展成U字的形狀。輻射底下,肺是兩顆漆黑色的蛹,密密包裹在蠶繭般的白色肋骨中央。其中,幾絲白色的細緻紋路,自中央半透明的氣道,向左右橫生、分岔,萌生出更細小的枝枒。底部,橫膈鎮著腹腔內的肝膽與脾胃,如楚河漢界,昭示呼吸與消化系統,於體內雄據一方。切片的中央近左方的位置,灰白色的陰影,投射出心的面積與形狀,向著左方,觸碰到一顆黑色的空心的圓,是胃裡的食糜幾經代謝後賸餘的氣泡。而切片的角落,本應清晰的雙側肋膈角,卻以近似於毛玻璃的樣態,蒙上了一層霧狀的白色薄紗。
我呆望螢幕上那凍結了的時間:黑白對比、色彩全無,卻書寫著肌理底下的諸多機密,遂帶著幾分欣賞藝術作品的神采,由左至右,自上而下,一毫、一米地細細打量。那一瞬間,我想到班雅明的靈光,一種只透過藝術瀰散的,遙遠之物的獨一顯現,彰顯古典的本真與不可複製性。而那張X光片,執拗地展現被拍攝者真實存在的轉瞬之間,在長時間的曝光下,留下靜止不動的表情和世界—那一隅真實轉錄的世界,一個角度、一個視野,就是一張充滿靈光的相片。
「玩過很多單眼,但再貴都不比這台!」放射師H說著,一面指向那以黃色輻射為記,重重鉛牆圈起的影棚。棚內,不單只有X光機,電腦斷層、核磁共振、正子造影也都鎮守其中,輪番錄下一齣齣不同病程的戲碼。每每我點開影像,無不是瞪大了眼,緩緩轉著滑鼠滾輪,一幕幕放映出隱匿皮下的血管、神經、臟腑、筋肉。過程,不時還得動用局部放大,來回審度這些看似暗了些、霧了點的區域,讓畫面數度停駐於那些明暗不一的光點,卻始終未能如放射師一般,只消隨手一滑,就明快指出一張切片裡頭的病灶。
幾次跟著H走進影棚,看他調閱指定的切片時,不單得一眼辨認出切片中的髂骨薦骨腓骨蹠骨,亦須熟習肩關節、腕關節攝影的不同視野。而每個骨幹的造影,亦有所謂的標準畫面,得依照前、後、側面等不同的成像角度,配置儀器與關節的正確擺位。隔著重重鉛板,車輪狀黃紅輻射標誌的背面,X射線將解剖的每一角度、人體的各個構面,俱皆投映上底片。只須等「喀擦」一聲,一張新鮮的人體成像,旋即出現在我眼前:上下邊界工工整整、亮度對比明明白白,肺與肺相對、骨與骨相銜,一如學生時代,教科書、投影幕上所聞所見。
步向隔壁的核磁共振室,不時便有疑似中風、癌症的病人被送到此,將身子轟隆隆地包裹進儀器內的金屬隧道。某次我送病人進來,不經意瞟向造影室的屏幕,卻訝於那上頭滿是我看不懂的、如加密符簶的英數簡寫,似詳載體內的氫原子和氧原子如何在人造的磁場當中共振,使指定的病灶區域能被精確顯影。而裡頭的放射師,不過是盯著螢幕,不時扣打幾下鍵盤,整個腦部平面的解剖工程,其成像和分析、運算與合成,都於他的執導下無聲完成。
成像完畢,H領我踅入檢查室,說要將病人挪出儀器。我立於病人頭側,雙臂勉力在軀體與平台間鑽出一條細隙,等床尾他喊三二一出力,病人仍紋風不動地固著於檢查台。我這才意識到,雙臂沉沉擔著的,是百餘公斤的肉身,卻只見放射師雙手在胸前彎成弧形,表情皺得像在健身房臥推那樣,病人的身體就硬生生地被移上床褥。而如此費力地挪移著受苦生命的重量,才不過是放射師精實的一天中,短短的幾幕過場。
然而理想總和現實相悖。執照或掙得溫飽,體制卻帶來馴化。當代的攝影師,沒有恣意取材、揮灑的空間,只留下工作服的口袋裡邊,幾捲失去自由的底片,滿腹的創作魂全都禁錮於胸前。
「拍照要能餬口,不只焦距、曝光,還要了解客戶!在醫院,就要弄懂你各位醫師奧客。」H喚來下一位病患,咂嘴將腫脹的患肢彎折成極不自然的角度,還得再三囑咐患者:痛歸痛,不准亂動。我聽H抱怨,開單的醫師幾次因攝下的照片不符預期,便直闖檢查室、責問放射師,還說要把病人從病房抓回來,重拍到滿意為止—成像不能糊、顯影不能遲,懂得標準擺位之餘,尚得細數各科醫師審視疾病之美的,浮動而多重的標準。是故醫院裡,光圈的縮放、快門的時機,未明言卻皆暗暗服膺於職別間的規訓,僵化且閉塞的階級。
倘若切換場景,將鏡頭聚焦急診,上述一切細軟,俱以兩倍速三倍速快轉播映:左手fracture的病人可以自己走嗎那肩膀靠那塊板子上不要動先等我一下CT室有病人我先去幫忙挪等等醫師你先別走幫我忙你要病人打這手contrast打完才能走……我聽急診的放射師三頭六臂忙至語序頓失,焦灼之際,儀器、擺位仍然標準,顯然是經過多年的經驗制約,講究且到位。
打完顯影劑,目送病人緩緩沒入轟耳的輻射隧道,不旋踵我又見鄰室骨折病人攝完相片,逕自踱回候診區。看放射師進出各個影棚,面色凝然地咒罵排班不勻,我心中不覺間竟升起一絲複雜之感,不知是懾服於那多機同步攝影的技藝,抑或是感慨那身三頭六臂的功夫,怕是臨床人力緊縮、身兼數職下的不得不吧!
一個月有那麼幾天,放射師也踱出棚,推著偌大的攝影車,來到病房、急診取景。那喚作portable的X光儀器,一鎖定欲攝像的model,放射師就吆喝著,將其C字形的鏡頭拗向病床上空,重又將鉛板矗於床的周身。當此時,看護、家人、護理者眾,至病室之外爭相走避輻射,唯有放射師一人貼在鉛板之後,確認儀器病人擺位俱妥,按下快門、確認成像,不多時又駕起portable,向著呼叫他的下一床啟航。
「也只有這種時候,可以像你們醫生,開一台法拉利跑上跑下。差在你們的法拉利是車載人,我這台是人推車。」談起portable班,H卻是兩手一攤,戲謔地說著。
而後,疫情熱烈,每日臉書IG,動態無論限不限時,盡是專責病房同事,穿著防護衣隔著N95,滿腹汗水苦水浸在其中,兀自淹積又兀自隱沒。輾轉我耳聞,H在他們單位,正輪值整個月的portable班,不分晝夜,替自己和愛車套上又卸下隔離裝,出入三五坪大的負壓病房,一遍又一遍貼著確診者,切下無數新冠肺炎的切片。
「防疫險都買好了,還怕啥?我可是連專責病房的護理長,都讚譽有加的防護衣穿脫大師呢!就差在我們照相仔命賤,沒得領防疫加給。」傳Messenger問起近況,H仍不改其自嘲本性。本想過問H,多時未見IG上傳新的攝影作品,卻很快想起受疫情耽待,鏡頭和腳架,怕是與他一同禁錮於幾坪大的租賃套房吧!
下班時分,踱出醫院路上,我想像專責病房的裡邊、鉛板的背面,放射師替疫情留下快照之時,會否也正替此時此刻的自己,攝下一張張記錄興趣與職涯、現實與理想的,人生的切片?點按滑鼠,就能見著他的名姓與攝像時間,俱皆固定於切片的右上;而他的心則禁錮在肋骨的中央,白色陰影投射出來的地方,唯有隔著重重鉛牆,能依稀聽聞埋藏在體制底下,淺淺的搏動聲響。
H的IG復有動靜,已是疫情過後的半年。那是赴西南岸漁村的生活邊角,裁下的幾張切片。切片右下用紅色的字體印有日期與時間。主角,則是戴漁夫帽、身形佝僂的長者。長者面海,臨著港埠、背著鏡頭,從站立的姿勢推估,他同那座質樸的漁村,已然憩居良久。夕陽斜照在碼頭之盡、海面之緣,我看見被鏡頭凍住的橘紅色波紋之上,他的面容與笑靨,都已完整映射在切片的世界。
並且真實而執拗地,鐫刻在用以轉錄的底片。
記起實習時候跟教學門診,開診之前,一群披掛著白袍的學生,總窩進主治醫師看診的座位後方,排成一列的圓形小凳,一張緊挨著一張坐下,一個個忙不迭地將頭埋進書本,就怕待會門診開診,得輪番坐上前頭看診的大位。沒來得及開口向病人問診,倒先被病人成堆的問題考倒。此際,眼尖的病人或會發現—後方每個醫學生的面孔看來雖是同樣生澀,可手上捧著的,卻是封面迥異、版本不一的書冊?
不錯,臨床知識的累積,並非義務教育的古文四十篇或聯立方程式,少了部編版課本,也未必有標準答案。兩、三年就更新一版的治療指引,不時就以簇新的檢查流程、用藥位階,將前一版推入歷史的行伍。大三記誦的藥物,等到大六畢業,療效早被新核准的藥物超前。住院醫師階段,終日在刀房苦行、磨礪而成的伎倆,等到升上主任,早已被新一代的器械、機械手臂取代。當醫學研究的論文發表呈指數成長,日新又新的科學實證,不僅推動醫療時代的齒輪,也鞭策一線醫護貫徹終身學習。
於是,課本寫的不總是等於正確答案,老師教的更多卻是過時資訊,醫學教育只好在幾十年前,就貫徹以學生報告,取代老師講課的翻轉教室。泰半是每兩週一次的英語報告,大夥輪流閱讀當期的學術刊物,及國際上的治療指引,爾或利用寒暑假,輪番出國交換、報名學術研討會,再將這些來不及編寫成冊的新知,收整成一篇、一篇的細瑣筆記。從傳統貼滿各色3M書籤及便利貼,大小恰好能塞入白袍口袋的小筆記本;爾或隨手拈來一張廢紙,就在背面,用三色原子筆抄起的潦草字跡(每次翻閱,都得如摩斯解密一般破譯)。時間來到當代,諸多筆記軟體橫跨手機、平板與網頁瀏覽器,拍照、截圖,俱能快速上傳數不清的書本內文或演講PPT—遂有略懂程式軟體的前輩,自個兒架起網站,取名「Tiny note」,讓樂善好施者,皆可新增頁面,貼上私房的筆記,成為實習醫師專屬的維基百科。於是一切的病歷報告、期刊重點、讀書摘要,俱開源式地供人品讀,不藏私、不隱匿,宣誓共享經濟的時代降臨。
那些筆記的上頭,或許是與疾病近距離搏擊以後,將種種戰果勝敗幾經編列、整理,成為其他人面對相同疾病的SOP;又或是主治醫師巡房時,隨口幾句經驗談,被抄寫成了逐字稿,使那畢生積攢的醫術得以流傳;抑或是分享不同的醫院,前人編纂成的工作手冊或教戰守則,經工人智慧式地交互比對、截長補短,擬出集各家大成的版本。
而我記憶最深刻的醫學筆記,是某一次的教學門診,病人報到的空檔,主治醫師見我們一群人熱烈翻找著書本,竟興奮地將隨身碟插入電腦,秀出由各種不同疾病的X光片,堆砌成的PPT檔,「這是我準備專科考試的筆記。我畢生所學,都整理在上頭了。」
於是我了解,每間門診的座椅上、每個手術台的邊旁,原來都祕密藏匿著一本微小的編年史。那裡頭,書寫著病情的章節、醫學的演化,分別在習醫的各個階段,逐一投稿、連載,輾轉成為一則一則篇幅各異,不斷迭代、演化的Tiny note—那些細小的文字,乘載了醫學的歷史、專科的知識;見過的病人、開過的藥方,還有動過的刀,與醫過的病。而這一切的微小足跡,日日夜夜地在不為人知的習醫里程中默默攢積—正是這些從醫院的各個邊角蒐羅而來,如拼圖般細瑣的筆記,一片鑲嵌過一片,組裝出每名醫師的腦中,那一幅碩大的醫學版圖。
這些筆記,因為微小,所以罕為人知。卻也正因它的微小,所以在漫漫行醫生涯中,顯得格外袖珍,並且別緻。
Off
從密封食物袋切出兩片吐司,銜著芝士樂起司片或塗抹Nutella可可醬,分別攤展於烤箱上下二層,旋鈕計時三分鐘。等待時,自冰箱取出預先泡製、冰鎮的三合一咖啡,再翻開一本村上春樹,就著窗外的細雨,津津地啜飲起來。如果前一日值夜班無事,又能準時交班準時off,命運許我的一個幸福早晨,當是如此。
「off」(一種可控的、機械式的隱喻),二十一世紀醫療最偉大的發明,是為值夜班的隔天,一日或半日的休假。十多年前,醫師未納勞基法,工時沒有上限。所謂的值班,便是從一早七、八點趕赴醫院晨會,緊接著是刀房、病房、門診、刀房、病房、急診……忙至傍晚六、七點,剛結束一日的「標準」工時,尚得留守在醫院,枕戈待旦:夜間辦入院的新病人、急診病人的專科照會,同時病房內病人的病情亦變幻莫測。無預警的一連串插管、電擊、CPR……待到隔天早上七、八點,復又拖著一日未梳洗、甚或未眠睡的軀殼,望回那機型老舊、畫面抖動,通宵一日看上去又更顯朦朧的晨會投影幕。好容易撐到一句今天晨會先到這邊,旋又接著繼續刀房、門診、病房、急診……待至向晚時分,方能步出醫院,等著明日,又一個超過三十四小時的值班日。
近年,各地屢傳醫師因過勞招致昏厥,甚或猝死,醫療工時勞權得到重視,才有了值班的隔日中午提前下班的PM off,乃至近年推行的,值班隔日的晨會結束就下班的Day off。「我今天off。你找cover我的○醫師。」於是任何不諳新制的來電,俱能以此為由回絕。
可疾病不受法規管轄。器官衰竭、敗血感染等重症病程往往來得迅猛,無早上、夜晚之別,亦沒有區分上班下班打卡。經常是(幾乎永遠是)在夜間或假日,人力俱乏的值班時段,無恙的病人突發高燒或哮喘、昏厥與癲癇,緊急處置一番後,遂將戰場轉至加護病房。當此時,仍未得勞基法保障的專科醫師、主治醫師,電話響徹,聽聞值班的下屬捎來病情,也不管是晝是夜,仍得盡責地在工時以外的時間,親赴醫院。
「以前覺得當醫生齁,坐在那邊講講話、開開藥就幾十萬入袋,實在好命。現在才知道,醫師工作不只歹命,怕是還會短命!」無怪乎逢年過節,但凡論及工時一事,長輩對我的態度便由羨煞,轉為同情了。
烤箱響起了。扳開烤門的時候,電子螢幕上亮閃著「OFF」的字樣。學生時代,初聞醫院慣用off來稱呼休假,以為那是種資本主義的、殖民式的征服,反映醫療體系亦難逃異化、生產工具化。可如今,一段無事之晨,足教人興起無比確幸與感恩。嘴邊銜起那烤得酥黃的吐司時,對著永遠按時開機、關機的氣炸烤箱,打從心底,我反倒湧起一股同我族類似的安慰,還有同情了。
時間的切片
我確信,那是一張罹病者的切片。
以脊柱為中心,上至頸椎,下至結腸,白色肋骨的細長投影,在暗片裡向著前方,伸展成U字的形狀。輻射底下,肺是兩顆漆黑色的蛹,密密包裹在蠶繭般的白色肋骨中央。其中,幾絲白色的細緻紋路,自中央半透明的氣道,向左右橫生、分岔,萌生出更細小的枝枒。底部,橫膈鎮著腹腔內的肝膽與脾胃,如楚河漢界,昭示呼吸與消化系統,於體內雄據一方。切片的中央近左方的位置,灰白色的陰影,投射出心的面積與形狀,向著左方,觸碰到一顆黑色的空心的圓,是胃裡的食糜幾經代謝後賸餘的氣泡。而切片的角落,本應清晰的雙側肋膈角,卻以近似於毛玻璃的樣態,蒙上了一層霧狀的白色薄紗。
我呆望螢幕上那凍結了的時間:黑白對比、色彩全無,卻書寫著肌理底下的諸多機密,遂帶著幾分欣賞藝術作品的神采,由左至右,自上而下,一毫、一米地細細打量。那一瞬間,我想到班雅明的靈光,一種只透過藝術瀰散的,遙遠之物的獨一顯現,彰顯古典的本真與不可複製性。而那張X光片,執拗地展現被拍攝者真實存在的轉瞬之間,在長時間的曝光下,留下靜止不動的表情和世界—那一隅真實轉錄的世界,一個角度、一個視野,就是一張充滿靈光的相片。
「玩過很多單眼,但再貴都不比這台!」放射師H說著,一面指向那以黃色輻射為記,重重鉛牆圈起的影棚。棚內,不單只有X光機,電腦斷層、核磁共振、正子造影也都鎮守其中,輪番錄下一齣齣不同病程的戲碼。每每我點開影像,無不是瞪大了眼,緩緩轉著滑鼠滾輪,一幕幕放映出隱匿皮下的血管、神經、臟腑、筋肉。過程,不時還得動用局部放大,來回審度這些看似暗了些、霧了點的區域,讓畫面數度停駐於那些明暗不一的光點,卻始終未能如放射師一般,只消隨手一滑,就明快指出一張切片裡頭的病灶。
幾次跟著H走進影棚,看他調閱指定的切片時,不單得一眼辨認出切片中的髂骨薦骨腓骨蹠骨,亦須熟習肩關節、腕關節攝影的不同視野。而每個骨幹的造影,亦有所謂的標準畫面,得依照前、後、側面等不同的成像角度,配置儀器與關節的正確擺位。隔著重重鉛板,車輪狀黃紅輻射標誌的背面,X射線將解剖的每一角度、人體的各個構面,俱皆投映上底片。只須等「喀擦」一聲,一張新鮮的人體成像,旋即出現在我眼前:上下邊界工工整整、亮度對比明明白白,肺與肺相對、骨與骨相銜,一如學生時代,教科書、投影幕上所聞所見。
步向隔壁的核磁共振室,不時便有疑似中風、癌症的病人被送到此,將身子轟隆隆地包裹進儀器內的金屬隧道。某次我送病人進來,不經意瞟向造影室的屏幕,卻訝於那上頭滿是我看不懂的、如加密符簶的英數簡寫,似詳載體內的氫原子和氧原子如何在人造的磁場當中共振,使指定的病灶區域能被精確顯影。而裡頭的放射師,不過是盯著螢幕,不時扣打幾下鍵盤,整個腦部平面的解剖工程,其成像和分析、運算與合成,都於他的執導下無聲完成。
成像完畢,H領我踅入檢查室,說要將病人挪出儀器。我立於病人頭側,雙臂勉力在軀體與平台間鑽出一條細隙,等床尾他喊三二一出力,病人仍紋風不動地固著於檢查台。我這才意識到,雙臂沉沉擔著的,是百餘公斤的肉身,卻只見放射師雙手在胸前彎成弧形,表情皺得像在健身房臥推那樣,病人的身體就硬生生地被移上床褥。而如此費力地挪移著受苦生命的重量,才不過是放射師精實的一天中,短短的幾幕過場。
然而理想總和現實相悖。執照或掙得溫飽,體制卻帶來馴化。當代的攝影師,沒有恣意取材、揮灑的空間,只留下工作服的口袋裡邊,幾捲失去自由的底片,滿腹的創作魂全都禁錮於胸前。
「拍照要能餬口,不只焦距、曝光,還要了解客戶!在醫院,就要弄懂你各位醫師奧客。」H喚來下一位病患,咂嘴將腫脹的患肢彎折成極不自然的角度,還得再三囑咐患者:痛歸痛,不准亂動。我聽H抱怨,開單的醫師幾次因攝下的照片不符預期,便直闖檢查室、責問放射師,還說要把病人從病房抓回來,重拍到滿意為止—成像不能糊、顯影不能遲,懂得標準擺位之餘,尚得細數各科醫師審視疾病之美的,浮動而多重的標準。是故醫院裡,光圈的縮放、快門的時機,未明言卻皆暗暗服膺於職別間的規訓,僵化且閉塞的階級。
倘若切換場景,將鏡頭聚焦急診,上述一切細軟,俱以兩倍速三倍速快轉播映:左手fracture的病人可以自己走嗎那肩膀靠那塊板子上不要動先等我一下CT室有病人我先去幫忙挪等等醫師你先別走幫我忙你要病人打這手contrast打完才能走……我聽急診的放射師三頭六臂忙至語序頓失,焦灼之際,儀器、擺位仍然標準,顯然是經過多年的經驗制約,講究且到位。
打完顯影劑,目送病人緩緩沒入轟耳的輻射隧道,不旋踵我又見鄰室骨折病人攝完相片,逕自踱回候診區。看放射師進出各個影棚,面色凝然地咒罵排班不勻,我心中不覺間竟升起一絲複雜之感,不知是懾服於那多機同步攝影的技藝,抑或是感慨那身三頭六臂的功夫,怕是臨床人力緊縮、身兼數職下的不得不吧!
一個月有那麼幾天,放射師也踱出棚,推著偌大的攝影車,來到病房、急診取景。那喚作portable的X光儀器,一鎖定欲攝像的model,放射師就吆喝著,將其C字形的鏡頭拗向病床上空,重又將鉛板矗於床的周身。當此時,看護、家人、護理者眾,至病室之外爭相走避輻射,唯有放射師一人貼在鉛板之後,確認儀器病人擺位俱妥,按下快門、確認成像,不多時又駕起portable,向著呼叫他的下一床啟航。
「也只有這種時候,可以像你們醫生,開一台法拉利跑上跑下。差在你們的法拉利是車載人,我這台是人推車。」談起portable班,H卻是兩手一攤,戲謔地說著。
而後,疫情熱烈,每日臉書IG,動態無論限不限時,盡是專責病房同事,穿著防護衣隔著N95,滿腹汗水苦水浸在其中,兀自淹積又兀自隱沒。輾轉我耳聞,H在他們單位,正輪值整個月的portable班,不分晝夜,替自己和愛車套上又卸下隔離裝,出入三五坪大的負壓病房,一遍又一遍貼著確診者,切下無數新冠肺炎的切片。
「防疫險都買好了,還怕啥?我可是連專責病房的護理長,都讚譽有加的防護衣穿脫大師呢!就差在我們照相仔命賤,沒得領防疫加給。」傳Messenger問起近況,H仍不改其自嘲本性。本想過問H,多時未見IG上傳新的攝影作品,卻很快想起受疫情耽待,鏡頭和腳架,怕是與他一同禁錮於幾坪大的租賃套房吧!
下班時分,踱出醫院路上,我想像專責病房的裡邊、鉛板的背面,放射師替疫情留下快照之時,會否也正替此時此刻的自己,攝下一張張記錄興趣與職涯、現實與理想的,人生的切片?點按滑鼠,就能見著他的名姓與攝像時間,俱皆固定於切片的右上;而他的心則禁錮在肋骨的中央,白色陰影投射出來的地方,唯有隔著重重鉛牆,能依稀聽聞埋藏在體制底下,淺淺的搏動聲響。
H的IG復有動靜,已是疫情過後的半年。那是赴西南岸漁村的生活邊角,裁下的幾張切片。切片右下用紅色的字體印有日期與時間。主角,則是戴漁夫帽、身形佝僂的長者。長者面海,臨著港埠、背著鏡頭,從站立的姿勢推估,他同那座質樸的漁村,已然憩居良久。夕陽斜照在碼頭之盡、海面之緣,我看見被鏡頭凍住的橘紅色波紋之上,他的面容與笑靨,都已完整映射在切片的世界。
並且真實而執拗地,鐫刻在用以轉錄的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