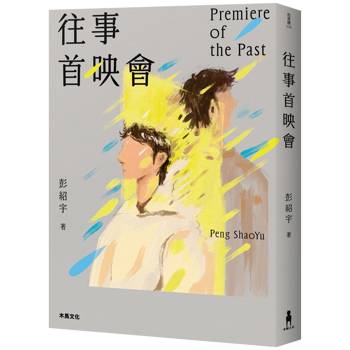1|千歲大樓 2035
西元二〇三五年,那是什麼樣的一年?
對陳敬來說,這不過是看似沒有終點的青春期中,又一段煩悶的時光。沒什麼特別的,儘管這是十七歲的他,能被稱作「未成年」的最後一年。
今年五月,他即將滿十八歲。
這一年,世界人口增長的速度已經放緩,但社會前進的步伐讓眾人都急忙向前看,唯獨沉默的陳敬例外。他不善言語,好似活在個人世界。
少男少女嘰嘰喳喳,彷彿有一整個池子般的感受,耐不住性子等待傾倒心中浪潮,相互灌溉滋養,彼此泛濫成災。陳敬不僅話不多,連表情都乏善可陳,矛盾的是,同學們覺得他難以親近,老師則認為他乖巧懂事。唯一靈活的是他的雙眼,一雙眼睛轉來轉去,帶點孩子氣,像在觀察四周卻默不作聲,更令人好奇他腦中到底裝些什麼了。
過去二十年來,人類生活的樣貌出現劇烈改變,近十年風起雲湧的人工智慧,在這個時代已是組成日常的必要元素,臺灣人口也即將跌破二千萬人。
這一年,臺灣再一次蟬聯出生率世界最低的寶座,幾乎很難在路上看見年輕的臉孔,就算有生,也普遍都只生一胎,兄弟姊妹的親屬概念,對於這時代的孩子而言只存在於課本裡。
但少子化問題已是老生常談,人們也逐漸放棄討論,因為此時更讓大眾興奮的,是機器人。
十多年前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是企業生產晶片,現在則是智慧機器人生產商。每年推出不同代的機器人滿足人類生活多種面向,其中最具革命性影響的莫過於長照機器人,照護問診開藥三合一,還能時時刻刻連結大數據給予問診服務,讓人們不再害怕老去。傳統養兒防老的概念過時,好處是老化不再那樣嚇人,副作用則是更加委靡的出生率。
縱使時代如何進步,十七歲少男少女內心的困惑彷彿沒有因為世界改變而消失。少子化衝擊教育體制,許多大專院校退場,但學子依然為了進入頂尖大學而競爭,在課業圈成的圍籬裡,探頭向外窺探世界。
為了趕上早自習考試,陳敬每天得六點起床,六點半準時出門趕四十分的自駕校車,才能準時抵達離家有段距離的學校。
陳敬不是家裡最早起的那個人,而是他的父親。陳敬是在他三十五歲那年生下的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孩子。看似晚生,但在這個年代早就不是什麼新鮮事,科技進步延長生育年齡,許多人花費數十年打拚,直到人生下半場才決定擁有孩子,這樣的選擇已是常態,也被視為是對自己、對孩子更「人性」的做法。
雖說人性,但畢竟年齡相差大,父子倆不太交心。比起一般家庭,他們的互動更像隔代教養家庭,儘管父親鮮少打罵,陳敬也特別早熟懂事,不曾經歷過什麼叛逆期,不過兩人之間似乎就是少了那麼點親密。
父親總是五點多就早早甦醒,簡單吃過早餐後便會出門運動。當他回家時,差不多就是陳敬該起床的時刻。陳敬相當自律,每天父親運動完打開門,便會發現陳敬早已起床準備,下樓趕校車。幾乎不需要父親擔憂。父子兩人會簡單互道「早安」,接著各自忙各自的事。這便是每個早晨的樣貌。
還沒找到志向的陳敬,去年寒假參加了文學營,暑假則去醫學營,他好像就是無法像某些學生一樣,感受到對某種領域的熱情。因此只是試著把每件事都做好,似乎這樣就沒有問題了,表現出某種「還在努力探索」的表象,便能堵住所有人的嘴。
※※※
他一如既往地上學、放學,日子似乎沒有什麼動靜。
「哇,天氣真好。」
陳敬半夢半醒,拉開窗簾,接著伸了伸懶腰,看一眼手機上的時間。
清晨五點五十八分。今天是一月七日,週日。
早晨的天空特別藍,空氣透著些微涼意,但體感舒適剛好。自從跨年開始冷了一週的寒流,終於在昨晚離開。
「厚被子可以先收起來了!」他喃喃自語。雖然今天不是上學日,但生理時鐘依然叫醒了他。
坐在床沿,陳敬從窗外看見天空,竟沒有一朵白雲,湛藍得像是海洋。
他嘴角輕輕微笑,拔去耳塞。
房門外頭空蕩蕩。爸還沒回來嗎?今天運動怎麼特別久。他心想。
不如上學時匆忙出門,陳敬比平常更從容地梳洗,一邊哼歌,一邊把房裡的棉被折疊整齊。
捷運上的乘客寥寥無幾,冬天早晨,城市還在熟睡。因為繞路,捷運比平常校車花更久時間到達學校,抵達校門口時,已經是七點半了。陳敬一手拿著課本,另一手轉動手機的音樂音量,那是他喜歡的搖滾樂團,只要聽著他們的歌,煩惱就像被靜音一樣。他不自覺哼出聲音,陶醉在重節拍的鼓聲,渾然不知背後有個人正向他走近。
那人拍了拍他的肩。
「同學,同學!」
陳敬嚇了一大跳,連耳機都被甩到地上。
「怎麼了?」
「同學!今天是週末喔,學校沒有開門喔。」
眼前站著的人,是學校的掃地阿姨。陳敬裝作看著手機日期,表情訝異。
「啊……謝謝。我是和同學有約,在學校附近。」
他尷尬地撒了個謊,好讓自己顯得不那麼狼狽。接著頭也不回地朝反方向走去。
哎啊……真的超尷尬……怎麼會呢?他心想。
要回家嗎?難得的藍天,就這樣走入地下鐵實在可惜。說來有趣,雖然這段路是他每天必經的路線,陳敬卻從沒有好好地走過、看過這段路,每天都是上課前昏昏沉沉坐在公車上,下課後又急忙搭車回家趕補習班。
「不如我慢慢走回去吧。」
三〇年代,每年的冬日只剩個位數,即使是一月,剛過去的寒流也代表著今年冬天正式結束了。臺北街頭不怎麼冷,太陽尚未躁動,是適合漫步的時間。街上行人不多,除了某些店家開始營業,只有清道夫緩緩掃著昨夜遺留的垃圾。
他很少見過這樣的臺北。比起平常的忙碌,他更喜歡這樣安靜的感覺。
一束光線照下,天光灑落,溫度又上升了一些。
陳敬往光線來自的方向望去,右手半遮瞇著的雙眼,偶然看到在那之下,有一幢正進行拆除工程的建築,不知不覺近在眼前。
「這是千歲大樓?」
曾目睹千歲大樓盛極一時的人,一定不會相信它現在的狼狽模樣。二十年前風光落成的摩登商辦大樓,是當時臺北前三高的建築,高價聘請國外得獎的「臺灣之光」建築師回臺設計,以「傑克與豌豆」裡的魔豆樹為理念,奇特的樹狀建築風格在天際線中特別突出,因此吸引許多外媒報導。霸氣名稱「千歲」特別請來知名書法家題字,烙印建築上方,是許多人對它的期許,但風光日子沒多久,進駐店面就換過一家又一家,不知為何,哪間國際品牌來此設店,幾乎都以賠錢收場,最終紛紛退出。
很快地,彷彿被詛咒的厄運讓它成為政論節目茶餘飯後的主題,有人說名字有諧音「碎」是不吉利的徵兆,有人說施工時死過工人但消息被壓下,死者怨靈不散讓它成為鬼樓,也有人說是因為一旁的高架橋造成「攔腰煞」破壞風水。
陰謀論滿天飛,經營大樓的董事長還接連爆出逃漏稅弊案,導致氣派的千歲大樓,成為人們口中戲稱的欠稅大樓。
什麼原因聽起來都有點荒唐,但假的說著說著就變成真的,人們嫌它晦氣,也逐漸不願光顧這棟樓。最終不堪營運壓力,走向不意外的退場結局,拆除日倒數計時。
千歲大樓旁矗立一幢豪宅,是有著L型特殊造型的高級別墅,中間挖空作為高空花園和游泳池,俯瞰周遭,彷彿咆哮自己的不可一世,在普遍低矮的臺北西區房舍間顯得格格不入。相形之下讓千歲大樓更淒涼了。
陳敬好奇地走進尚未成為廢墟的建築。
已經多久沒有來這裡了,什麼時候成了這模樣?他心想。
小時候每到週末,陳敬常與爸媽來到這裡。當同齡人對小螢幕聲光刺激感興趣,他卻迥然。他喜歡走出家裡,喜歡沿著河堤騎單車到家附近的公園,雖然不大,也早已充滿人工池、人工林、人工造景,但卻能讓他有種逃脫現實的放鬆感。
他真正喜歡的,是觀察人們。比起說話,他更常默默觀察、聆聽,因此大家都不怎麼知道他到底在想什麼。
尤其在千歲大樓,光顧的人各式各樣。觀光客和本地人,習慣週末早上來的和下午散步的人,都有著不一樣特徵。他喜歡猜測人與人的關係,為那些人想像他們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跨越圍籬,他張望四周,「千歲」題字夾在殘壁中顯得尤其淒涼。雖然地板布滿石礫,施工工程應該還沒開始,建築本體仍保留原本樣貌,只是和印象中的樣貌相比,這裡確實滄桑許多。
轉過頭,他看見牆壁上有個區塊明顯與周遭顏色不同。
「這是當時電影時刻表的位置吧。」他喃喃自語。
走上二樓,即使建築外觀破舊不堪,裡面樣貌仍維持體面。觀察某些店面留下未帶走的商品,大致可以猜測過去經營什麼樣的生意,而陳敬基本上對大多數的攤位都相當熟悉。
多次走過的記憶,彷彿潛意識設定,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正記憶著。
他幾乎能記得哪邊是什麼店,甚至店裡的老闆、氣味和燈光顏色,無一不記憶猶新。
低頭看,地板上貼的指引已斑駁,但依稀能看見密密麻麻寫著不同樓層的介紹文字。有些區域被多次覆蓋過,想必換過不少店家吧。不過,還是有些地方從一而終,例如眼前這間電影院。
他的記憶停留在某次與父母看完電影的盛夏。印象中後來一直在施工,有的地方漏水,有的結構不穩,似乎預示這棟大樓的未來,在那之後,好像就不曾來過這裡了。明明千歲大樓一直營業到他十六歲那年才正式歇業,中間的幾年卻像是空白一樣,許多事情改變了,他再也沒有踏進這裡。
抬頭看——週年慶,感謝祭,購物節,促銷季,出清廣告布條層層堆疊,資本主義暈頭轉向,店家張牙舞爪,遊客垂涎三尺,好個雙贏局面,如今都已是雲煙,只剩那些過度燦爛的行銷紙張,染料微粒散落一地,似乎一碰觸便會化為煙塵。行走其中,彷彿能嗅出一種由盛轉衰的蒼涼。
老實說,千歲大樓的失敗不完全能歸咎怪力亂神,大樓周邊算是比較早開發的區域,因為都市計畫重整,臺北市的商業中心逐漸轉移,再加上幾年前,陳敬家附近的重劃區,開幕了號稱全臺最大的複合式百貨商場,宛如致命一擊,年輕男女不再來到千歲大樓。這個區域於是呈現某種尷尬的過時氛圍,儘管外表壯觀大氣,還是給人怪異的老舊感。
縱使陳敬感受到曾經喧囂,如今只剩寂靜,彷彿連心跳都聽得一清二楚,只有偶爾風吹過響起的沙沙聲,才提醒著時間的流動。
※※※
他打開其中一扇門,記憶喚回,塵埃抹去,這裡就是當年和家人常來的電影院。空氣中還能聞見淡淡的爆米花氣味,這是屬於電影院的味道。然而此刻電影院瀰漫的爆米花氣味,不是溫熱的焦糖香,而是涼去的疲憊感。
陳敬往廳內走去。與過往不同,迎接他的不是剪票員,而是空蕩蕩的門口。他推了推門,似乎沒有鎖。走進漆黑影廳,開啟手機照明功能,暗紅漆皮座椅與深藍牆壁令人感覺像跨入不同世界,也似乎還能聽見隔壁大廳傳來震耳欲聾的特效音。
牆壁上的海報都還在,他欣喜。放眼望去,每幀都是影史經典作,像《日落大道》、《萬花嬉春》、《2001太空漫遊》和《八又二分之一》……巧合的是,那些電影海報都帶點紅色元素,似乎是為了與影城的紅色主視覺相互呼應。
雖然這些電影都在他出生前誕生,它們其中描寫的未來,甚至已是他的過去,陳敬卻認為它們一點都不遙遠,反倒感覺格外接近,加上修復技術日新月異,如果不是察覺到片中場景和人們的說話用字,幾乎就是一部新電影。
後來的很多電影,好像都拍不出這些經典的味道了,他心想。
其中最吸引人的海報,莫過於接近大銀幕的那張《一一》海報。紅色簾幕鋪滿底部,中間則有粉紅氣球,最前則是一個背對我們的男孩。
凝視海報,他自言自語:「離開前,為什麼沒把這些海報被帶走呢?」
出神之際,外頭突然傳來聲響,是人的聲音,而且有很多人。工人嗎?七嘴八舌地說他聽不太清楚的話。
比起聲音,飄來的味道更讓陳敬手足無措——某種藥水味,難以精準形容,又不知究竟何來,但令陳敬相當不舒服。
他一陣眩暈,心跳加速,幾乎要從胸口跳出來,陳敬伸出手想扶著座椅卻撲空,四肢震顫讓他失去重心,頓時跌坐在地。在沒有營業的戲院,原本無光的影廳變得更加漆黑,他伸手不見五指,意識到自己已汗流滿身,他找到座椅之間的一塊空地,先是趴跪而後躺下,喘息不止,最終昏了過去。
※※※
那是天空暈黃的午後,他緩緩走回家。家門外,他隱約聽見門內傳來大聲的爭執聲,「本來以為我再活一次的話,也許會有什麼不一樣。但是,我突然覺得再活一次的話,好像真的沒那個必要,真的沒那個必要。」
似是母親的聲音,陳敬將耳朵靠上門前,試圖聽得更清楚一些。
接著,他聽見父親說,「每天醒來,我都覺得對接下來的生活一點把握也沒有。有時……有時會覺得好不容易睡著了,幹嘛又要醒來,然後得去面對那些煩惱,一次又一次發生。」
父親的聲音顫抖著。
他們怎麼了?
時不時傳來母親的哭泣聲。嗚咽中,他聽見母親嘶吼著,「為什麼這個世界和我們想的都不一樣呢?」
等等……這些話語彷彿特別熟悉。不正是電影《一一》中的對白嗎?
疑惑時,陳敬同時睜開眼睛。
「原來是一場夢。不過……也太真實了。」
「天啊,我昏了多久!」
擦去額頭的汗水,讓他不適的氣味不再,四周聲音靜默。
他緩緩起身,沿著門口方向走去,確定外頭沒人後,趕緊推開大門。臨走前不禁回頭看一眼,這可能是最後一次來到這裡了,他心想。
陳敬熟門熟路地往樓梯方向走去,步下一樓,儘管身體恢復平靜,剛剛發生過的事依然讓他餘悸猶存。
人們總說逝去的事物是時代的眼淚,但如果時間會哭泣,會不會,其實人們才是時代流下的眼淚?曾經鮮豔興奮的事物,終有一天都會成為讓人提不起興致的話當年。
十七歲的陳敬第一次感受到時間的重量,如晨一般壓境,也如塵一吹即散。
走出大樓,陳敬混亂的思緒還沒來得及梳理清楚,卻發現周遭景象已經變得陌生。
(未完待續)
西元二〇三五年,那是什麼樣的一年?
對陳敬來說,這不過是看似沒有終點的青春期中,又一段煩悶的時光。沒什麼特別的,儘管這是十七歲的他,能被稱作「未成年」的最後一年。
今年五月,他即將滿十八歲。
這一年,世界人口增長的速度已經放緩,但社會前進的步伐讓眾人都急忙向前看,唯獨沉默的陳敬例外。他不善言語,好似活在個人世界。
少男少女嘰嘰喳喳,彷彿有一整個池子般的感受,耐不住性子等待傾倒心中浪潮,相互灌溉滋養,彼此泛濫成災。陳敬不僅話不多,連表情都乏善可陳,矛盾的是,同學們覺得他難以親近,老師則認為他乖巧懂事。唯一靈活的是他的雙眼,一雙眼睛轉來轉去,帶點孩子氣,像在觀察四周卻默不作聲,更令人好奇他腦中到底裝些什麼了。
過去二十年來,人類生活的樣貌出現劇烈改變,近十年風起雲湧的人工智慧,在這個時代已是組成日常的必要元素,臺灣人口也即將跌破二千萬人。
這一年,臺灣再一次蟬聯出生率世界最低的寶座,幾乎很難在路上看見年輕的臉孔,就算有生,也普遍都只生一胎,兄弟姊妹的親屬概念,對於這時代的孩子而言只存在於課本裡。
但少子化問題已是老生常談,人們也逐漸放棄討論,因為此時更讓大眾興奮的,是機器人。
十多年前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是企業生產晶片,現在則是智慧機器人生產商。每年推出不同代的機器人滿足人類生活多種面向,其中最具革命性影響的莫過於長照機器人,照護問診開藥三合一,還能時時刻刻連結大數據給予問診服務,讓人們不再害怕老去。傳統養兒防老的概念過時,好處是老化不再那樣嚇人,副作用則是更加委靡的出生率。
縱使時代如何進步,十七歲少男少女內心的困惑彷彿沒有因為世界改變而消失。少子化衝擊教育體制,許多大專院校退場,但學子依然為了進入頂尖大學而競爭,在課業圈成的圍籬裡,探頭向外窺探世界。
為了趕上早自習考試,陳敬每天得六點起床,六點半準時出門趕四十分的自駕校車,才能準時抵達離家有段距離的學校。
陳敬不是家裡最早起的那個人,而是他的父親。陳敬是在他三十五歲那年生下的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孩子。看似晚生,但在這個年代早就不是什麼新鮮事,科技進步延長生育年齡,許多人花費數十年打拚,直到人生下半場才決定擁有孩子,這樣的選擇已是常態,也被視為是對自己、對孩子更「人性」的做法。
雖說人性,但畢竟年齡相差大,父子倆不太交心。比起一般家庭,他們的互動更像隔代教養家庭,儘管父親鮮少打罵,陳敬也特別早熟懂事,不曾經歷過什麼叛逆期,不過兩人之間似乎就是少了那麼點親密。
父親總是五點多就早早甦醒,簡單吃過早餐後便會出門運動。當他回家時,差不多就是陳敬該起床的時刻。陳敬相當自律,每天父親運動完打開門,便會發現陳敬早已起床準備,下樓趕校車。幾乎不需要父親擔憂。父子兩人會簡單互道「早安」,接著各自忙各自的事。這便是每個早晨的樣貌。
還沒找到志向的陳敬,去年寒假參加了文學營,暑假則去醫學營,他好像就是無法像某些學生一樣,感受到對某種領域的熱情。因此只是試著把每件事都做好,似乎這樣就沒有問題了,表現出某種「還在努力探索」的表象,便能堵住所有人的嘴。
※※※
他一如既往地上學、放學,日子似乎沒有什麼動靜。
「哇,天氣真好。」
陳敬半夢半醒,拉開窗簾,接著伸了伸懶腰,看一眼手機上的時間。
清晨五點五十八分。今天是一月七日,週日。
早晨的天空特別藍,空氣透著些微涼意,但體感舒適剛好。自從跨年開始冷了一週的寒流,終於在昨晚離開。
「厚被子可以先收起來了!」他喃喃自語。雖然今天不是上學日,但生理時鐘依然叫醒了他。
坐在床沿,陳敬從窗外看見天空,竟沒有一朵白雲,湛藍得像是海洋。
他嘴角輕輕微笑,拔去耳塞。
房門外頭空蕩蕩。爸還沒回來嗎?今天運動怎麼特別久。他心想。
不如上學時匆忙出門,陳敬比平常更從容地梳洗,一邊哼歌,一邊把房裡的棉被折疊整齊。
捷運上的乘客寥寥無幾,冬天早晨,城市還在熟睡。因為繞路,捷運比平常校車花更久時間到達學校,抵達校門口時,已經是七點半了。陳敬一手拿著課本,另一手轉動手機的音樂音量,那是他喜歡的搖滾樂團,只要聽著他們的歌,煩惱就像被靜音一樣。他不自覺哼出聲音,陶醉在重節拍的鼓聲,渾然不知背後有個人正向他走近。
那人拍了拍他的肩。
「同學,同學!」
陳敬嚇了一大跳,連耳機都被甩到地上。
「怎麼了?」
「同學!今天是週末喔,學校沒有開門喔。」
眼前站著的人,是學校的掃地阿姨。陳敬裝作看著手機日期,表情訝異。
「啊……謝謝。我是和同學有約,在學校附近。」
他尷尬地撒了個謊,好讓自己顯得不那麼狼狽。接著頭也不回地朝反方向走去。
哎啊……真的超尷尬……怎麼會呢?他心想。
要回家嗎?難得的藍天,就這樣走入地下鐵實在可惜。說來有趣,雖然這段路是他每天必經的路線,陳敬卻從沒有好好地走過、看過這段路,每天都是上課前昏昏沉沉坐在公車上,下課後又急忙搭車回家趕補習班。
「不如我慢慢走回去吧。」
三〇年代,每年的冬日只剩個位數,即使是一月,剛過去的寒流也代表著今年冬天正式結束了。臺北街頭不怎麼冷,太陽尚未躁動,是適合漫步的時間。街上行人不多,除了某些店家開始營業,只有清道夫緩緩掃著昨夜遺留的垃圾。
他很少見過這樣的臺北。比起平常的忙碌,他更喜歡這樣安靜的感覺。
一束光線照下,天光灑落,溫度又上升了一些。
陳敬往光線來自的方向望去,右手半遮瞇著的雙眼,偶然看到在那之下,有一幢正進行拆除工程的建築,不知不覺近在眼前。
「這是千歲大樓?」
曾目睹千歲大樓盛極一時的人,一定不會相信它現在的狼狽模樣。二十年前風光落成的摩登商辦大樓,是當時臺北前三高的建築,高價聘請國外得獎的「臺灣之光」建築師回臺設計,以「傑克與豌豆」裡的魔豆樹為理念,奇特的樹狀建築風格在天際線中特別突出,因此吸引許多外媒報導。霸氣名稱「千歲」特別請來知名書法家題字,烙印建築上方,是許多人對它的期許,但風光日子沒多久,進駐店面就換過一家又一家,不知為何,哪間國際品牌來此設店,幾乎都以賠錢收場,最終紛紛退出。
很快地,彷彿被詛咒的厄運讓它成為政論節目茶餘飯後的主題,有人說名字有諧音「碎」是不吉利的徵兆,有人說施工時死過工人但消息被壓下,死者怨靈不散讓它成為鬼樓,也有人說是因為一旁的高架橋造成「攔腰煞」破壞風水。
陰謀論滿天飛,經營大樓的董事長還接連爆出逃漏稅弊案,導致氣派的千歲大樓,成為人們口中戲稱的欠稅大樓。
什麼原因聽起來都有點荒唐,但假的說著說著就變成真的,人們嫌它晦氣,也逐漸不願光顧這棟樓。最終不堪營運壓力,走向不意外的退場結局,拆除日倒數計時。
千歲大樓旁矗立一幢豪宅,是有著L型特殊造型的高級別墅,中間挖空作為高空花園和游泳池,俯瞰周遭,彷彿咆哮自己的不可一世,在普遍低矮的臺北西區房舍間顯得格格不入。相形之下讓千歲大樓更淒涼了。
陳敬好奇地走進尚未成為廢墟的建築。
已經多久沒有來這裡了,什麼時候成了這模樣?他心想。
小時候每到週末,陳敬常與爸媽來到這裡。當同齡人對小螢幕聲光刺激感興趣,他卻迥然。他喜歡走出家裡,喜歡沿著河堤騎單車到家附近的公園,雖然不大,也早已充滿人工池、人工林、人工造景,但卻能讓他有種逃脫現實的放鬆感。
他真正喜歡的,是觀察人們。比起說話,他更常默默觀察、聆聽,因此大家都不怎麼知道他到底在想什麼。
尤其在千歲大樓,光顧的人各式各樣。觀光客和本地人,習慣週末早上來的和下午散步的人,都有著不一樣特徵。他喜歡猜測人與人的關係,為那些人想像他們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跨越圍籬,他張望四周,「千歲」題字夾在殘壁中顯得尤其淒涼。雖然地板布滿石礫,施工工程應該還沒開始,建築本體仍保留原本樣貌,只是和印象中的樣貌相比,這裡確實滄桑許多。
轉過頭,他看見牆壁上有個區塊明顯與周遭顏色不同。
「這是當時電影時刻表的位置吧。」他喃喃自語。
走上二樓,即使建築外觀破舊不堪,裡面樣貌仍維持體面。觀察某些店面留下未帶走的商品,大致可以猜測過去經營什麼樣的生意,而陳敬基本上對大多數的攤位都相當熟悉。
多次走過的記憶,彷彿潛意識設定,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正記憶著。
他幾乎能記得哪邊是什麼店,甚至店裡的老闆、氣味和燈光顏色,無一不記憶猶新。
低頭看,地板上貼的指引已斑駁,但依稀能看見密密麻麻寫著不同樓層的介紹文字。有些區域被多次覆蓋過,想必換過不少店家吧。不過,還是有些地方從一而終,例如眼前這間電影院。
他的記憶停留在某次與父母看完電影的盛夏。印象中後來一直在施工,有的地方漏水,有的結構不穩,似乎預示這棟大樓的未來,在那之後,好像就不曾來過這裡了。明明千歲大樓一直營業到他十六歲那年才正式歇業,中間的幾年卻像是空白一樣,許多事情改變了,他再也沒有踏進這裡。
抬頭看——週年慶,感謝祭,購物節,促銷季,出清廣告布條層層堆疊,資本主義暈頭轉向,店家張牙舞爪,遊客垂涎三尺,好個雙贏局面,如今都已是雲煙,只剩那些過度燦爛的行銷紙張,染料微粒散落一地,似乎一碰觸便會化為煙塵。行走其中,彷彿能嗅出一種由盛轉衰的蒼涼。
老實說,千歲大樓的失敗不完全能歸咎怪力亂神,大樓周邊算是比較早開發的區域,因為都市計畫重整,臺北市的商業中心逐漸轉移,再加上幾年前,陳敬家附近的重劃區,開幕了號稱全臺最大的複合式百貨商場,宛如致命一擊,年輕男女不再來到千歲大樓。這個區域於是呈現某種尷尬的過時氛圍,儘管外表壯觀大氣,還是給人怪異的老舊感。
縱使陳敬感受到曾經喧囂,如今只剩寂靜,彷彿連心跳都聽得一清二楚,只有偶爾風吹過響起的沙沙聲,才提醒著時間的流動。
※※※
他打開其中一扇門,記憶喚回,塵埃抹去,這裡就是當年和家人常來的電影院。空氣中還能聞見淡淡的爆米花氣味,這是屬於電影院的味道。然而此刻電影院瀰漫的爆米花氣味,不是溫熱的焦糖香,而是涼去的疲憊感。
陳敬往廳內走去。與過往不同,迎接他的不是剪票員,而是空蕩蕩的門口。他推了推門,似乎沒有鎖。走進漆黑影廳,開啟手機照明功能,暗紅漆皮座椅與深藍牆壁令人感覺像跨入不同世界,也似乎還能聽見隔壁大廳傳來震耳欲聾的特效音。
牆壁上的海報都還在,他欣喜。放眼望去,每幀都是影史經典作,像《日落大道》、《萬花嬉春》、《2001太空漫遊》和《八又二分之一》……巧合的是,那些電影海報都帶點紅色元素,似乎是為了與影城的紅色主視覺相互呼應。
雖然這些電影都在他出生前誕生,它們其中描寫的未來,甚至已是他的過去,陳敬卻認為它們一點都不遙遠,反倒感覺格外接近,加上修復技術日新月異,如果不是察覺到片中場景和人們的說話用字,幾乎就是一部新電影。
後來的很多電影,好像都拍不出這些經典的味道了,他心想。
其中最吸引人的海報,莫過於接近大銀幕的那張《一一》海報。紅色簾幕鋪滿底部,中間則有粉紅氣球,最前則是一個背對我們的男孩。
凝視海報,他自言自語:「離開前,為什麼沒把這些海報被帶走呢?」
出神之際,外頭突然傳來聲響,是人的聲音,而且有很多人。工人嗎?七嘴八舌地說他聽不太清楚的話。
比起聲音,飄來的味道更讓陳敬手足無措——某種藥水味,難以精準形容,又不知究竟何來,但令陳敬相當不舒服。
他一陣眩暈,心跳加速,幾乎要從胸口跳出來,陳敬伸出手想扶著座椅卻撲空,四肢震顫讓他失去重心,頓時跌坐在地。在沒有營業的戲院,原本無光的影廳變得更加漆黑,他伸手不見五指,意識到自己已汗流滿身,他找到座椅之間的一塊空地,先是趴跪而後躺下,喘息不止,最終昏了過去。
※※※
那是天空暈黃的午後,他緩緩走回家。家門外,他隱約聽見門內傳來大聲的爭執聲,「本來以為我再活一次的話,也許會有什麼不一樣。但是,我突然覺得再活一次的話,好像真的沒那個必要,真的沒那個必要。」
似是母親的聲音,陳敬將耳朵靠上門前,試圖聽得更清楚一些。
接著,他聽見父親說,「每天醒來,我都覺得對接下來的生活一點把握也沒有。有時……有時會覺得好不容易睡著了,幹嘛又要醒來,然後得去面對那些煩惱,一次又一次發生。」
父親的聲音顫抖著。
他們怎麼了?
時不時傳來母親的哭泣聲。嗚咽中,他聽見母親嘶吼著,「為什麼這個世界和我們想的都不一樣呢?」
等等……這些話語彷彿特別熟悉。不正是電影《一一》中的對白嗎?
疑惑時,陳敬同時睜開眼睛。
「原來是一場夢。不過……也太真實了。」
「天啊,我昏了多久!」
擦去額頭的汗水,讓他不適的氣味不再,四周聲音靜默。
他緩緩起身,沿著門口方向走去,確定外頭沒人後,趕緊推開大門。臨走前不禁回頭看一眼,這可能是最後一次來到這裡了,他心想。
陳敬熟門熟路地往樓梯方向走去,步下一樓,儘管身體恢復平靜,剛剛發生過的事依然讓他餘悸猶存。
人們總說逝去的事物是時代的眼淚,但如果時間會哭泣,會不會,其實人們才是時代流下的眼淚?曾經鮮豔興奮的事物,終有一天都會成為讓人提不起興致的話當年。
十七歲的陳敬第一次感受到時間的重量,如晨一般壓境,也如塵一吹即散。
走出大樓,陳敬混亂的思緒還沒來得及梳理清楚,卻發現周遭景象已經變得陌生。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