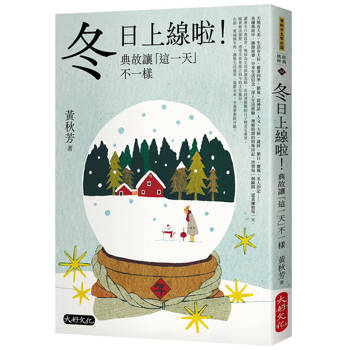十二月☆從大雪到冬至,世界靜下來慢慢滋長
◆〈一個字,唱出整個季節〉◆
十二月是一年的最後一個月,在北半球,是冬季的第一個月,在南半球,則為夏季的第一個月。身處北半球的我們,風變冷了,像收緊的線,拉住季節的倉促;一年即將結束,空氣冰冰的,繃得指尖都凍僵了,碰什麼都微微顫一下;從沒停下腳步的時間,感覺都變慢了;比平常更放緩的安靜,像在暗中醞釀著「不確定會發生甚麼」的神祕時刻,有時候像「恐怖箱」遊戲,有時又變成禮物般的「驚喜箱」,那些埋在漫長流光裡的故事,悄悄動了起來。
以典故取暖,不是為了說教,只是讓各種各樣新鮮的想法、奇幻的故事,陪伴我們度過一個又一個寒冷的日子、照亮一段又一段越來越漫長的黑夜。像圍坐在火爐旁,分享著喜歡的人、事、物,讓隱伏在遙遠歲月中的光和熱,穿過千年,在不斷翻新的講述裡,重新化作一盞盞小燈,看透此時此地,回望前塵,照亮未來,各種各樣的典故,好像讓每一個「這一天」,都變得不一樣了。
那些寫在書頁上的字,經過時間淬煉,代代薪傳,承載著整個天地的收斂與蘊藏,帶著微溫,等待著被深刻理解。有沒有發現,漢字和英文最不一樣的地方是,喜歡靜靜看見自己?所以,比起「合唱」的熱鬧氣氛,漢字更喜歡「獨唱」。英文要出動「W」、「I」、「N」、「T」、「E」、「R」六個字,才能完成「表現寒冷」的大合唱;漢字卻只簡簡單單寫出一個「冬」字,就用獨唱把對世界的觀察,表達得生動又有趣。
古代的字,多半用刀刻在獸骨或竹片上,習慣把筆畫刻成橫的或直的,這樣比較容易「施工」。在字的筆畫成熟變身成現代樣貌以前,「冬」的甲骨文是這樣的:「 」,其實就是古人在畫畫。大半的人都說,這個字是「結繩紀事」時標示出繩子兩端的終結,也就是「結束」的意思,一年終結,同時也是各種各樣考驗的總結算,撐不過的人,生命可能也會「終結」喔!後來在金文、篆文中,冬的表意,又加入「日」和「冫」(冰)等「文字零件」,逐漸演化為表示寒冬的現代字。
也有一小部分的學者認為,這是天氣寒凍前,原始初民用繩子串藏的「種子果實」,一方面可以充飢,也能在第二年春天播種,這個字就用來表示「天氣很冷,我們要先做好各種準備,儲備體力,好好度過艱難考驗,等待新的開始」。
你喜歡哪一種呢?讀典故,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沒有標準答案」,說起來,讀書之有趣,也不是為了做學問,當然也不需要標準答案。隨著四時變化,年紀和經驗慢慢增長,我們對「冬」字的感受和領略,會一層又一層地轉換與加深,無論是比較喜歡理性的「結束」,還是充滿感性想像的「種子果實」,都不會影響我們的學習和成長,天地萬物的變化,因為「沒有標準答案」而豐饒。
我們都像種子果實,在時間變慢時,不急不躁,慢慢累積滋養,並且相信,每一次結束,都會是另一個意想不到的開端。
◆〈冬天的故事:走向希望,不是魔法〉◆
福爾摩沙全島的樣貌,隨著葡萄牙人的繪製與標註,在十六世紀中期,第一次出現在世界地圖上。到了約四百年前,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東亞貿易轉運,讓台灣成為當時國際貿易多條航道必經地,全球化和現代化的腳步,伴隨著各種衝突和磨難,慢慢前行。
宛如在深沉寒冬中的試煉與累積,就在這蘊蓄著「世界流動」的時空裡,英國劇作家威廉·莎士比亞,在約一六○九至一六一一年間,發表了劇情荒誕、但又不斷被翻新詮釋的《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熱情的西西里王和溫和的波西米亞王自幼相伴,一直是無話不談的死黨,直到各自承擔起治理國家的責任而分離;多年後,波西米亞王到西西里作客,他們快樂得像重回童年,連西西里王后也和他們成為最要好的朋友。
可惜,快樂的時光太短暫,西西里王太愛王后了,竟懷疑好友和妻子有私情,連自己的孩子也認定是「別人的」,就在波西米亞王回國前,西西里王命人毒死好友、遺棄孩子,把無辜的王后關進牢裡。幸好,波西米亞王得到暗助,成功逃亡;小公主被善良的牧羊人收養;王后在悲傷中昏倒後失蹤……一切變化都太快了,等西西里王恢復理智、後悔莫及時,真相早已迷失,無從彌補,像暴雪突襲,溫暖瞬間結冰,只有時間,才能為未知的命運和選擇翻轉解凍。
十六年後,長大了的小公主和波西米亞王子相戀,他們在愛情受阻時私奔到西西里,命運在層層考驗後揭開真相。西西里王找回失散多年的公主,喜極而泣;堅毅不拔的王后,熬過長久的等待,潛入皇宮扮成雕像,神秘復活,並且選擇寬恕,造就離散重聚的「魔法時光」,終而一家團圓,朋友和好,年輕人相互珍惜,所有的慘烈都變成幸福的奇蹟。
這部藏著忌妒、傷心、後悔……等各種負面情緒的戲劇,居然被歸類成「喜劇」,也被現代學者歸為「浪漫劇」。信任、希望與堅忍,像魔法種子,凝聚著國王的悔恨、公主的勇敢、母親的堅持、朋友的寬恕,從悲傷開出花來,釀造出心碎後還願意相信溫柔的花蜜,這才是「冬天」的意義,成為四百年來反覆被運用的多重意象。
冰冷雕像重新「活起來」,不是靠魔法,而是在堅持與勇氣中召喚未來,從悲劇裡重生,才能在真實人生中活出真正的喜劇。當全球化和現代化日趨成熟,並且不斷分化,世界以我們想像不到的疾速在前進,仍然有各種文學、戲劇、影視、教育、心理療癒與創傷修復等領域,運用《冬天的故事》借喻,從裂解走向修補、從悲傷邁向重建。
四百年的文明進展,從葡萄牙航海圖到福爾摩沙衛星影像,為這座島嶼留下美麗的形影。一如莎士比亞的預言,只要放下恐懼與執念,重新擁抱彼此,就能走過全球化和現代化的各種試煉,從脆弱處萌芽,在寒冬中迎接溫暖。
◆〈世界土壤日,聽見盤古的心跳、燭龍的呼吸〉◆
冬天一到,世界就屏氣抵住寒冷,像蒙上厚厚的被子,準備做一個很長很長的夢。天地沉靜,如蜷身沉睡億萬年的盤古,吸收著萬有滋養在等待機會,直到撐開困縛,頭頂著天,腳踩著地,在天地間不斷長大。傳說,他的頭探天,天日高一丈,他的腳立地,地也日厚一丈;這樣過了一萬八千年,天高地厚,盤古用自己的基因血肉,澆灌出一個充滿生機的世界。最後,他微笑倒下,把自己的身體奉獻給大地,左眼變太陽,右眼變月亮,眼底晶瑩的淚水撒向天空,變成萬點繁星,為大地帶來光明和希望。
盤古創世的版本很多,混一點自己的想像,就成為美麗的神話旅行。他的汗珠變湖泊、血液成江河、毛髮變成草原和森林;更進一步,讓筋脈變地理、肌肉化田土、皮毛成草木、齒骨成金石、精髓化珠玉,四肢五體化成四極五嶽;為了這整片大地的生機,他呼氣變清風、吐息化雲霧,輕音如風嘯、發聲成雷鳴。我在《崑崙傳說》中,刻意讓他僅剩的最後一點點魂魄,化成「燭龍」,呼吸成風,聲息換四季,張眼是白晝、閉眼是黑夜,照亮九幽重暗,讓我們更真切地貼近土地,聽見各種夢想的心跳,咚、咚、咚、咚,鼓動這個世界,好像所有仰望的星星、賴以存活的土壤,都是神蹟般的禮物,像盤古最後的餘溫,滋養著我們的學習與成長。
二○一四年,興大附中的學生在中央大學天文營隊,透過Pan-STARRS 影像,發現一顆遠在海王星軌道外、估計約兩百公里的遙遠天體;後來由國際天文學聯合會(IAU)賦予永久編號472235,命名為「Zhulong」(燭龍)。這些仰望星辰的孩子們,取得命名權,以神話的遙遠聲息提醒我們,腳下的泥土是萬物的搖籃,更是時間行走的印記。
隨著工業化和文明過度開發,土壤面臨污染、退化、養分耗竭,影響糧食安全,導致生物多樣性驟縮、生態系統失衡。聯合國於二○一三年底通過決議,將十二月五日定為「世界土壤日」(World Soil Day),並宣布二○一五年為國際土壤年,自此世界各地持續舉行相關倡議。
無論是致力減貧、降緩氣候變化、積極參與土壤保育和水源暨生態系統永續照護的大合作;或只是支持在地農業、減少土地污染、在日常生活中友善環境的小心意,都是我們破開寒冬封閉、回應生命得以共榮的承諾。像盤古倒下時殘留的心跳,隨著大地的脈絡傳來溫熱,燭龍的呼吸,隨著四季循環,依舊在泥土深處緩緩流動,從冬日的沉睡中,喚醒春甦萌芽、豔夏繁盛和秋收的豐饒。
◆〈讓路給大夢想家,華特·迪士尼〉◆
十二月五日,大夢想家華特·迪士尼(Walt Disney,1901·12·5~1966·12·15)生日。回想起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他記得,就是搬進父親以全部家產換購的小農場,自由地游泳、閒蕩,不斷畫著在樹林、田野間一起嬉耍的小動物;愛上火車,常把耳朵貼在鐵軌上聽著遠遠駛來的火車聲,宛如遠方有夢想呼喚;直到大哥、二哥相繼離家出走,父親又因傷寒而病倒,只好賣掉農場,全家遷離。
癡迷火車的華特,在火車上打工,賣起汽水、糖果和報紙,趴在窗邊欣賞火車走過的風景,以致於商品全都被拿走,不得不向哥哥羅伊·O·迪士尼(Roy O·Disney)借錢賠給老闆。後來,他在芝加哥藝術學院註冊,繼續在課堂上畫畫、打瞌睡、作白日夢,並未完成學業。世界大戰爆發時,他加入美國紅十字救護隊負責駕駛,閒來沒事就畫救護車,把車子裡裡外外都畫成漫畫和卡通。
歷經動畫師、導演、劇作家、配音與製片人的各種角色,華特·迪士尼仍帶著孩子般的執著,用畫筆與夢想創造一個讓世界微笑的王國。他與哥哥羅伊共同創辦「迪士尼公司」,推出各種創舉:米老鼠(Mickey Mouse)第一次躍上銀幕的《威利汽船》首映日,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成為他的生日;《花與樹》(1932)是首部商業放映採用完整三色Technicolor的動畫短片並獲得奧斯卡;第一部片長符合奧斯卡獎項規定的「全長動畫電影」《白雪公主與七矮人》(1937),大受歡迎;《幻想曲》以開創性的Fantasound系統,在音響與視覺上做出大膽實驗(1940);更有不少作品,引發文化與倫理的討論,從娛樂轉向深邃的人文資產。真人動畫共演的《歡樂滿人間》,拿下五座奧斯卡;華特本人一生共獲得26座奧斯卡獎(含22座競賽獎與4座榮譽獎),至今仍保持最多個人奧斯卡紀錄;迪士尼團隊在全球亦獲得近千次榮譽,包括多座奧斯卡與艾美獎。
迪士尼王國,從動畫、電影、電視節目《迪士尼奇妙世界》,慢慢發展到串流平台,迪士尼主題樂園遍及全球,讓純真夢想多了個棲息地。「華特·迪士尼家族博物館」是舊金山的世外桃源,一樓介紹迪士尼家庭和他們的童年生活;二樓則是迪士尼在好萊塢的奮鬥。其中收藏展示的逝世致哀報刊與文物,多為以米老鼠或其作品為題的悼念圖像和文章,象徵他的事業從一隻小老鼠開始。
這隻走過一世紀的老鼠,讓我們擁有做夢的勇氣。原來,夢想並不需要一開始就很偉大,只要看見希望,找到對的人一起奮鬥,堅持到最後,世界就會為夢想讓路。
◆〈大雪到了!二十四節氣是屋簷下的魔法小鈴鐺〉◆
很久很久以前,二十四節氣是生活的口袋曆,記錄著四季天候、農耕規律,承載著天人合一的泛靈信仰,以及社會秩序的建立與傳承,保存著人與大自然相互依存的文化價值與生命活力。依循著這些「時間的記號」,人們安心地播種、灌溉、收成、休息;經過產業革命與時代變遷,單純的農耕生活分化成各種忙碌與重複,現代社會簡直像生命檔案都被「格式化」了。
幸好還有二十四節氣,像一串魔法小鈴噹,掛在一年四季的屋簷下,每隔一段時間便叮噹響起,從來不曾離開。便利商店裡限定口味的飯糰、學校午餐中出現的南瓜,還有家裡不時冒出的時令菜色與應時補湯……都在提醒我們,天地翻身了,季節也想換衣服。「立春」一早換上的淺色衣裳;「驚蟄」一響,草叢與樹蔭間的小小聯合國忙碌起來;「小滿」時,誰都想出門看看鮮綠的水田;過了「秋分」,記得帶件薄外套;入冬後,風變得厚重,樹枝輕輕蜷著,挽留不住的落葉四處飄飛,世界的腳步也慢了下來。冬季的節氣由「立冬」開場,夜裡藉湯圓找回一點圓滿;「小雪」之後,氣溫漸降;「大雪」是農曆冬季的第三個節氣,落在每年十二月六日至八日間,約在西曆北半球冬季初。
漢文化習慣以「農曆」為四季規律的依據;因準確性而成為國際通行的「公曆」,源自重新定義閏年規則的「格里曆」,讓曆法年的平均長度(365·2425日)更接近地球繞太陽公轉的回歸年(約365·2422日),也稱「西曆」、「陽曆」或「國曆」。
為了凸顯與農曆的差異,「四季有典微光」系列的曆法典故說明,統一使用「西曆」。西曆的冬天從十二月至二月;農曆以二十四節氣區別四季,除了少數的提前或延後,冬日多半在十月至十二月,換成西曆時間約為十一月至翌年一月。這種遊走在農曆和西曆間的一個月時間差,在時間縫隙中錯位交疊,讓我們在忙碌的日子裡聽見天地律動,藉著與自然同步呼吸的節奏調整,一點點鮮活的生活皺褶,都變成充滿異質情韻的美感。
古人為每個節氣找出三種訊號,稱為「三候」。大雪三候是:「鶡鴠不鳴」、「虎始交」和「荔挺出」。高緯度地區受冷空氣影響降雪,無論動物或植物,都在因應天候與地氣而改變;在台灣,烏魚每年冬季隨等溫線洄游,恰與大雪、冬至前後時序相近,成為在地的季節風物。
讀「物候」,不能當作精確的現代生物學名詞,而是更接近一種從天候、物種、四季循環延伸至生活秩序的人生意象。古籍中的「鹖鴠」(ㄏㄜˊ ㄉㄢˋ),常作為禽鳥夜鳴求旦的意象,民間傳述與近代教科書,如《國語日報》五○年代教材與早期自然課本,也曾將「鹖鴠」與某些鼯鼠類混同。傳說中,鶡鴠是「寒號鳥」,夏季長滿絢麗羽毛,樣子十分美麗;到了冬天,毛羽脫落,只剩光禿禿的翅膀,雖然有四隻腳,卻無法像一般的鳥那樣飛行,為了節省力氣儲藏過冬,再也無法鳴叫。這樣的形象,特別適合當寓言故事的主角,過了絢爛的盛夏,就得面對自己選擇的後果。
老虎是強韌的山大王,卻在入冬前求偶,藉以孕養未來。古籍所載的「荔挺」是一種香草,也有一種說法是蘭草,小小的,卻在冷冬中感受到「極陰裡,陽氣萌動」的契機,於是努力舒展,讓人想起雪萊名詩〈西風頌〉的激昂結語:「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在最冷酷的黑暗時刻,只要勇敢,就能新生出打不倒的力量。萬物自有時序,低谷不是終點。節氣是記憶的節拍器,溫柔地提醒我們,春天記得發芽,夏天要流汗,秋天學會收藏,到了冬天,好好擁抱自己,慢慢感覺、慢慢長大,在最冷的時候,勇敢地長成自己最喜歡的樣子。
◆〈一個字,唱出整個季節〉◆
十二月是一年的最後一個月,在北半球,是冬季的第一個月,在南半球,則為夏季的第一個月。身處北半球的我們,風變冷了,像收緊的線,拉住季節的倉促;一年即將結束,空氣冰冰的,繃得指尖都凍僵了,碰什麼都微微顫一下;從沒停下腳步的時間,感覺都變慢了;比平常更放緩的安靜,像在暗中醞釀著「不確定會發生甚麼」的神祕時刻,有時候像「恐怖箱」遊戲,有時又變成禮物般的「驚喜箱」,那些埋在漫長流光裡的故事,悄悄動了起來。
以典故取暖,不是為了說教,只是讓各種各樣新鮮的想法、奇幻的故事,陪伴我們度過一個又一個寒冷的日子、照亮一段又一段越來越漫長的黑夜。像圍坐在火爐旁,分享著喜歡的人、事、物,讓隱伏在遙遠歲月中的光和熱,穿過千年,在不斷翻新的講述裡,重新化作一盞盞小燈,看透此時此地,回望前塵,照亮未來,各種各樣的典故,好像讓每一個「這一天」,都變得不一樣了。
那些寫在書頁上的字,經過時間淬煉,代代薪傳,承載著整個天地的收斂與蘊藏,帶著微溫,等待著被深刻理解。有沒有發現,漢字和英文最不一樣的地方是,喜歡靜靜看見自己?所以,比起「合唱」的熱鬧氣氛,漢字更喜歡「獨唱」。英文要出動「W」、「I」、「N」、「T」、「E」、「R」六個字,才能完成「表現寒冷」的大合唱;漢字卻只簡簡單單寫出一個「冬」字,就用獨唱把對世界的觀察,表達得生動又有趣。
古代的字,多半用刀刻在獸骨或竹片上,習慣把筆畫刻成橫的或直的,這樣比較容易「施工」。在字的筆畫成熟變身成現代樣貌以前,「冬」的甲骨文是這樣的:「 」,其實就是古人在畫畫。大半的人都說,這個字是「結繩紀事」時標示出繩子兩端的終結,也就是「結束」的意思,一年終結,同時也是各種各樣考驗的總結算,撐不過的人,生命可能也會「終結」喔!後來在金文、篆文中,冬的表意,又加入「日」和「冫」(冰)等「文字零件」,逐漸演化為表示寒冬的現代字。
也有一小部分的學者認為,這是天氣寒凍前,原始初民用繩子串藏的「種子果實」,一方面可以充飢,也能在第二年春天播種,這個字就用來表示「天氣很冷,我們要先做好各種準備,儲備體力,好好度過艱難考驗,等待新的開始」。
你喜歡哪一種呢?讀典故,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沒有標準答案」,說起來,讀書之有趣,也不是為了做學問,當然也不需要標準答案。隨著四時變化,年紀和經驗慢慢增長,我們對「冬」字的感受和領略,會一層又一層地轉換與加深,無論是比較喜歡理性的「結束」,還是充滿感性想像的「種子果實」,都不會影響我們的學習和成長,天地萬物的變化,因為「沒有標準答案」而豐饒。
我們都像種子果實,在時間變慢時,不急不躁,慢慢累積滋養,並且相信,每一次結束,都會是另一個意想不到的開端。
◆〈冬天的故事:走向希望,不是魔法〉◆
福爾摩沙全島的樣貌,隨著葡萄牙人的繪製與標註,在十六世紀中期,第一次出現在世界地圖上。到了約四百年前,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東亞貿易轉運,讓台灣成為當時國際貿易多條航道必經地,全球化和現代化的腳步,伴隨著各種衝突和磨難,慢慢前行。
宛如在深沉寒冬中的試煉與累積,就在這蘊蓄著「世界流動」的時空裡,英國劇作家威廉·莎士比亞,在約一六○九至一六一一年間,發表了劇情荒誕、但又不斷被翻新詮釋的《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熱情的西西里王和溫和的波西米亞王自幼相伴,一直是無話不談的死黨,直到各自承擔起治理國家的責任而分離;多年後,波西米亞王到西西里作客,他們快樂得像重回童年,連西西里王后也和他們成為最要好的朋友。
可惜,快樂的時光太短暫,西西里王太愛王后了,竟懷疑好友和妻子有私情,連自己的孩子也認定是「別人的」,就在波西米亞王回國前,西西里王命人毒死好友、遺棄孩子,把無辜的王后關進牢裡。幸好,波西米亞王得到暗助,成功逃亡;小公主被善良的牧羊人收養;王后在悲傷中昏倒後失蹤……一切變化都太快了,等西西里王恢復理智、後悔莫及時,真相早已迷失,無從彌補,像暴雪突襲,溫暖瞬間結冰,只有時間,才能為未知的命運和選擇翻轉解凍。
十六年後,長大了的小公主和波西米亞王子相戀,他們在愛情受阻時私奔到西西里,命運在層層考驗後揭開真相。西西里王找回失散多年的公主,喜極而泣;堅毅不拔的王后,熬過長久的等待,潛入皇宮扮成雕像,神秘復活,並且選擇寬恕,造就離散重聚的「魔法時光」,終而一家團圓,朋友和好,年輕人相互珍惜,所有的慘烈都變成幸福的奇蹟。
這部藏著忌妒、傷心、後悔……等各種負面情緒的戲劇,居然被歸類成「喜劇」,也被現代學者歸為「浪漫劇」。信任、希望與堅忍,像魔法種子,凝聚著國王的悔恨、公主的勇敢、母親的堅持、朋友的寬恕,從悲傷開出花來,釀造出心碎後還願意相信溫柔的花蜜,這才是「冬天」的意義,成為四百年來反覆被運用的多重意象。
冰冷雕像重新「活起來」,不是靠魔法,而是在堅持與勇氣中召喚未來,從悲劇裡重生,才能在真實人生中活出真正的喜劇。當全球化和現代化日趨成熟,並且不斷分化,世界以我們想像不到的疾速在前進,仍然有各種文學、戲劇、影視、教育、心理療癒與創傷修復等領域,運用《冬天的故事》借喻,從裂解走向修補、從悲傷邁向重建。
四百年的文明進展,從葡萄牙航海圖到福爾摩沙衛星影像,為這座島嶼留下美麗的形影。一如莎士比亞的預言,只要放下恐懼與執念,重新擁抱彼此,就能走過全球化和現代化的各種試煉,從脆弱處萌芽,在寒冬中迎接溫暖。
◆〈世界土壤日,聽見盤古的心跳、燭龍的呼吸〉◆
冬天一到,世界就屏氣抵住寒冷,像蒙上厚厚的被子,準備做一個很長很長的夢。天地沉靜,如蜷身沉睡億萬年的盤古,吸收著萬有滋養在等待機會,直到撐開困縛,頭頂著天,腳踩著地,在天地間不斷長大。傳說,他的頭探天,天日高一丈,他的腳立地,地也日厚一丈;這樣過了一萬八千年,天高地厚,盤古用自己的基因血肉,澆灌出一個充滿生機的世界。最後,他微笑倒下,把自己的身體奉獻給大地,左眼變太陽,右眼變月亮,眼底晶瑩的淚水撒向天空,變成萬點繁星,為大地帶來光明和希望。
盤古創世的版本很多,混一點自己的想像,就成為美麗的神話旅行。他的汗珠變湖泊、血液成江河、毛髮變成草原和森林;更進一步,讓筋脈變地理、肌肉化田土、皮毛成草木、齒骨成金石、精髓化珠玉,四肢五體化成四極五嶽;為了這整片大地的生機,他呼氣變清風、吐息化雲霧,輕音如風嘯、發聲成雷鳴。我在《崑崙傳說》中,刻意讓他僅剩的最後一點點魂魄,化成「燭龍」,呼吸成風,聲息換四季,張眼是白晝、閉眼是黑夜,照亮九幽重暗,讓我們更真切地貼近土地,聽見各種夢想的心跳,咚、咚、咚、咚,鼓動這個世界,好像所有仰望的星星、賴以存活的土壤,都是神蹟般的禮物,像盤古最後的餘溫,滋養著我們的學習與成長。
二○一四年,興大附中的學生在中央大學天文營隊,透過Pan-STARRS 影像,發現一顆遠在海王星軌道外、估計約兩百公里的遙遠天體;後來由國際天文學聯合會(IAU)賦予永久編號472235,命名為「Zhulong」(燭龍)。這些仰望星辰的孩子們,取得命名權,以神話的遙遠聲息提醒我們,腳下的泥土是萬物的搖籃,更是時間行走的印記。
隨著工業化和文明過度開發,土壤面臨污染、退化、養分耗竭,影響糧食安全,導致生物多樣性驟縮、生態系統失衡。聯合國於二○一三年底通過決議,將十二月五日定為「世界土壤日」(World Soil Day),並宣布二○一五年為國際土壤年,自此世界各地持續舉行相關倡議。
無論是致力減貧、降緩氣候變化、積極參與土壤保育和水源暨生態系統永續照護的大合作;或只是支持在地農業、減少土地污染、在日常生活中友善環境的小心意,都是我們破開寒冬封閉、回應生命得以共榮的承諾。像盤古倒下時殘留的心跳,隨著大地的脈絡傳來溫熱,燭龍的呼吸,隨著四季循環,依舊在泥土深處緩緩流動,從冬日的沉睡中,喚醒春甦萌芽、豔夏繁盛和秋收的豐饒。
◆〈讓路給大夢想家,華特·迪士尼〉◆
十二月五日,大夢想家華特·迪士尼(Walt Disney,1901·12·5~1966·12·15)生日。回想起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他記得,就是搬進父親以全部家產換購的小農場,自由地游泳、閒蕩,不斷畫著在樹林、田野間一起嬉耍的小動物;愛上火車,常把耳朵貼在鐵軌上聽著遠遠駛來的火車聲,宛如遠方有夢想呼喚;直到大哥、二哥相繼離家出走,父親又因傷寒而病倒,只好賣掉農場,全家遷離。
癡迷火車的華特,在火車上打工,賣起汽水、糖果和報紙,趴在窗邊欣賞火車走過的風景,以致於商品全都被拿走,不得不向哥哥羅伊·O·迪士尼(Roy O·Disney)借錢賠給老闆。後來,他在芝加哥藝術學院註冊,繼續在課堂上畫畫、打瞌睡、作白日夢,並未完成學業。世界大戰爆發時,他加入美國紅十字救護隊負責駕駛,閒來沒事就畫救護車,把車子裡裡外外都畫成漫畫和卡通。
歷經動畫師、導演、劇作家、配音與製片人的各種角色,華特·迪士尼仍帶著孩子般的執著,用畫筆與夢想創造一個讓世界微笑的王國。他與哥哥羅伊共同創辦「迪士尼公司」,推出各種創舉:米老鼠(Mickey Mouse)第一次躍上銀幕的《威利汽船》首映日,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成為他的生日;《花與樹》(1932)是首部商業放映採用完整三色Technicolor的動畫短片並獲得奧斯卡;第一部片長符合奧斯卡獎項規定的「全長動畫電影」《白雪公主與七矮人》(1937),大受歡迎;《幻想曲》以開創性的Fantasound系統,在音響與視覺上做出大膽實驗(1940);更有不少作品,引發文化與倫理的討論,從娛樂轉向深邃的人文資產。真人動畫共演的《歡樂滿人間》,拿下五座奧斯卡;華特本人一生共獲得26座奧斯卡獎(含22座競賽獎與4座榮譽獎),至今仍保持最多個人奧斯卡紀錄;迪士尼團隊在全球亦獲得近千次榮譽,包括多座奧斯卡與艾美獎。
迪士尼王國,從動畫、電影、電視節目《迪士尼奇妙世界》,慢慢發展到串流平台,迪士尼主題樂園遍及全球,讓純真夢想多了個棲息地。「華特·迪士尼家族博物館」是舊金山的世外桃源,一樓介紹迪士尼家庭和他們的童年生活;二樓則是迪士尼在好萊塢的奮鬥。其中收藏展示的逝世致哀報刊與文物,多為以米老鼠或其作品為題的悼念圖像和文章,象徵他的事業從一隻小老鼠開始。
這隻走過一世紀的老鼠,讓我們擁有做夢的勇氣。原來,夢想並不需要一開始就很偉大,只要看見希望,找到對的人一起奮鬥,堅持到最後,世界就會為夢想讓路。
◆〈大雪到了!二十四節氣是屋簷下的魔法小鈴鐺〉◆
很久很久以前,二十四節氣是生活的口袋曆,記錄著四季天候、農耕規律,承載著天人合一的泛靈信仰,以及社會秩序的建立與傳承,保存著人與大自然相互依存的文化價值與生命活力。依循著這些「時間的記號」,人們安心地播種、灌溉、收成、休息;經過產業革命與時代變遷,單純的農耕生活分化成各種忙碌與重複,現代社會簡直像生命檔案都被「格式化」了。
幸好還有二十四節氣,像一串魔法小鈴噹,掛在一年四季的屋簷下,每隔一段時間便叮噹響起,從來不曾離開。便利商店裡限定口味的飯糰、學校午餐中出現的南瓜,還有家裡不時冒出的時令菜色與應時補湯……都在提醒我們,天地翻身了,季節也想換衣服。「立春」一早換上的淺色衣裳;「驚蟄」一響,草叢與樹蔭間的小小聯合國忙碌起來;「小滿」時,誰都想出門看看鮮綠的水田;過了「秋分」,記得帶件薄外套;入冬後,風變得厚重,樹枝輕輕蜷著,挽留不住的落葉四處飄飛,世界的腳步也慢了下來。冬季的節氣由「立冬」開場,夜裡藉湯圓找回一點圓滿;「小雪」之後,氣溫漸降;「大雪」是農曆冬季的第三個節氣,落在每年十二月六日至八日間,約在西曆北半球冬季初。
漢文化習慣以「農曆」為四季規律的依據;因準確性而成為國際通行的「公曆」,源自重新定義閏年規則的「格里曆」,讓曆法年的平均長度(365·2425日)更接近地球繞太陽公轉的回歸年(約365·2422日),也稱「西曆」、「陽曆」或「國曆」。
為了凸顯與農曆的差異,「四季有典微光」系列的曆法典故說明,統一使用「西曆」。西曆的冬天從十二月至二月;農曆以二十四節氣區別四季,除了少數的提前或延後,冬日多半在十月至十二月,換成西曆時間約為十一月至翌年一月。這種遊走在農曆和西曆間的一個月時間差,在時間縫隙中錯位交疊,讓我們在忙碌的日子裡聽見天地律動,藉著與自然同步呼吸的節奏調整,一點點鮮活的生活皺褶,都變成充滿異質情韻的美感。
古人為每個節氣找出三種訊號,稱為「三候」。大雪三候是:「鶡鴠不鳴」、「虎始交」和「荔挺出」。高緯度地區受冷空氣影響降雪,無論動物或植物,都在因應天候與地氣而改變;在台灣,烏魚每年冬季隨等溫線洄游,恰與大雪、冬至前後時序相近,成為在地的季節風物。
讀「物候」,不能當作精確的現代生物學名詞,而是更接近一種從天候、物種、四季循環延伸至生活秩序的人生意象。古籍中的「鹖鴠」(ㄏㄜˊ ㄉㄢˋ),常作為禽鳥夜鳴求旦的意象,民間傳述與近代教科書,如《國語日報》五○年代教材與早期自然課本,也曾將「鹖鴠」與某些鼯鼠類混同。傳說中,鶡鴠是「寒號鳥」,夏季長滿絢麗羽毛,樣子十分美麗;到了冬天,毛羽脫落,只剩光禿禿的翅膀,雖然有四隻腳,卻無法像一般的鳥那樣飛行,為了節省力氣儲藏過冬,再也無法鳴叫。這樣的形象,特別適合當寓言故事的主角,過了絢爛的盛夏,就得面對自己選擇的後果。
老虎是強韌的山大王,卻在入冬前求偶,藉以孕養未來。古籍所載的「荔挺」是一種香草,也有一種說法是蘭草,小小的,卻在冷冬中感受到「極陰裡,陽氣萌動」的契機,於是努力舒展,讓人想起雪萊名詩〈西風頌〉的激昂結語:「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在最冷酷的黑暗時刻,只要勇敢,就能新生出打不倒的力量。萬物自有時序,低谷不是終點。節氣是記憶的節拍器,溫柔地提醒我們,春天記得發芽,夏天要流汗,秋天學會收藏,到了冬天,好好擁抱自己,慢慢感覺、慢慢長大,在最冷的時候,勇敢地長成自己最喜歡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