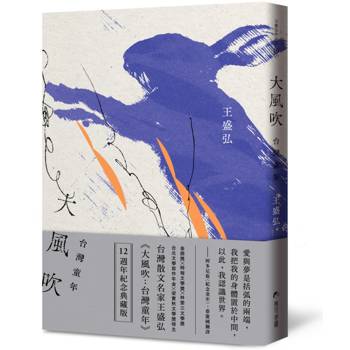台灣童年
1 一場葬禮
父親帶我參加一場遠房親戚的葬禮。
擇吉日出殯,沿途房舍門柱事先都貼有紅紙頭,隊伍經過時家家戶戶設案拜祭。
當送葬隊伍走到村子口,少部分人摘去喪服,折返;其餘登遊覽車,車隊鑼鼓喧天一路鬧到墳場。
等待吉時下葬、覆土,白花花陽光灑下,眾人各自尋陰影底立著、蹲著,小孩們或有不耐煩,但很快找到玩伴,偶爾玩過了頭,遭大人低聲制止。
儀式過後,陸續上車,日頭下折騰大半天後得以歇息,都舒了一口氣。很快地車上氣氛熱絡,自報身分、職業,聊旅遊見聞,一陣陣笑聲漸次傳開。本還壓抑著,卻隱忍不住,有了喧譁的態勢。
竟有人唱起歌來。唱的是三天兩頭電視上播放的歌曲,一樹桃花千朵紅,朵朵帶笑舞春風;有人加入合唱,桃花伴著春風舞,歡送哥哥去從戎……找到共通語言般地,興致十分高昂。
幾個小時前還哭哭啼啼的這群人,不像剛參加過一場葬禮,倒像出門遊玩,把握最後相聚時刻作樂一番。
我緊緊握住父親的手臂,睜大眼睛看著這個令人納悶的場面。彼時,死亡是生命中最大的恐懼,害怕得連開口問大人那到底是怎麼回事都不敢。
要過了很多年後,如今我才懂得,自悲痛中快速復原的能力,不是上天對死者的殘忍,而是對生者的慈悲。
2 陰陽雨
對阿媽的印象已如經久曝曬的廣告紙,顏色褪得十分淡薄了。
有個場面似乎是,有人向她敬菸,她嘴上說毋免毋免,卻伸出手去把菸接了過來。這是我最早的幾個記憶之一。我仰頭站在一旁,目睹了推辭與接受同時進行,好像大太陽天裡下起了雨,當成一樁新鮮好玩的事去告訴了母親。
當時怎麼懂得,這是人際應對的客套,類似於儀式。
另有一個場面:二期稻作收穫後,粟仔曬在稻埕,夏日午後,天空猛地烏雲四合,西北雨倒臉盆水般潑下,頃刻間稻埕積水高逾腳踝,粟仔不斷被沖進排水道。大人小孩都頂著暴雨搶救,因為一雙小腳而幫不上忙的阿媽為眼前景象所驚嚇,突然癱軟,跌坐在地。
對了──記憶真像種在地底的憨吉(han-tsû,番薯),以為只有微微露出地表的那一個,一扯卻纍纍一大串──親朋好友探望,送來五爪蘋果、克寧奶粉,阿媽都收進五斗櫃。當她好大方拿在手上問有誰要時,水果已經開始腐爛,而奶粉早過了食用期限。
關於阿媽的記憶,遂瀰漫了爛熟的甜香,雜糅灰撲撲的霉味。
母親提過,有回阿媽出門晃盪了一圈,返家後盛讚自家水田種得真好,追問之下才得知,她根本找錯了地方。母親的結論是,看恁阿媽命有好無?
母親沒說出口的,也許是對自己操勞一生的惋歎?
母親真夠辛苦的了。父親曾滿口酒氣透露,在我們三兄弟之外,母親懷第四胎,翁仔某兩人商量,自知無力扶養而偷偷去做了人工流產,又怕阿公阿媽發現,第二天母親仍舊照常操持家務,下田勞動。
父親說這些話時不當一回事的語氣,真令人討厭。
透過追憶,阿媽的形象浮水印般逐漸鮮活了起來──還記得的是,每遇陰陽雨她便要說一句諺語或歇後語一般的話:「出日閣落雨,嬰仔翻豬肚。」(註一)因為太古怪了,我格格笑著,一遍遍琅琅複述。問阿媽是什麼意思,阿媽說她也不知道,伊做囡仔時就聽大人按呢講了。
補述:
記憶中的「嬰仔翻豬肚」,因「嬰仔」與「燕子」台語同音,我一度以為,指的是天氣變化之際,燕子離巢,在空中嬉耍、遊獵,露出腹部凝脂般的白色羽毛。因自知強作解人,此事長期懸在心上。四十餘年後,上網查找,赫然發現有一首〈出日落雨〉的童謠:「出日落雨,刣豬翻豬肚。尪仔穿紅褲,乞食行無路,行去竹跤邊予狗哺。」才知「嬰仔」不是燕子,是尪仔,玩偶。另有數個相去不遠的版本。林文寶等人合著的《兒童文學》一書,對此寫道:「從字面來看,我們不容易了解它的意旨,但從社會學角度深入欣賞,才知道當時占據台灣的日本憲兵穿的是紅褲子,而這兒的『小玩偶」,指的是沒有人性的人,也就是借代日本憲兵。整首兒歌敘述日本憲兵的橫暴、喜怒無常,像邊出太陽,邊下雨,以及屠夫的翻豬肚子,翻來翻去,令人不可捉摸。」至此,懸念落實,無邪的兒時記憶卻沾染了肅殺的氛圍。
3 撲滿
扁扁圓圓的水果糖鐵盒是我的撲滿原型,一向疼愛我的大伯母幫忙收著,我把一角鎳幣、五角一元紙鈔交給她,她在我面前放進盒子,蓋嚴。有時我問,存多少錢了呢?大伯母便自衣櫥深處取出盒子,算數給我看。
將錢交給大伯母,是要比讓父親母親保管可靠多了。這世上若真有純良的好人,我心目中的大伯母要算上一個。
大伯母晚年遭逢病痛摧殘,我回竹圍仔探望,她勉強自床上坐起身來,閒聊幾句後相對無語。突然地她冒出一句話,我這世人嘛無做過啥物歹代誌,想袂曉哪會受遮的拖磨。我聽了,眼眶發酸,吶吶安慰幾句,心中感到茫然。那時候我已經略懂得人生實難的況味了。
最典型的撲滿是肥墩墩的小豬造型,全都在飽食後挨上一刀,沒能留下。倒是有個竹編大阪城撲滿,底部設有機關可以旋開,是姑姑自日本帶回的等路,肯定還遺落在家裡某個角落。
小時候常見母親將錢幣餵進大阪城,但我拎著它在空中搖晃,卻只聽見幾枚硬幣空空洞洞撞擊著。心裡納悶,便留意著動靜。
謎底很快揭曉,我撞見父親正倒拿著大阪城掏錢。父親雖不是什麼在家人面前擺派頭、端架子的人,但總是「父親」,他心虛囁嚅著,想,想買包菸。尷尬地笑了一笑。
我思量著該不該向母親通風報訊,終究還是決定說了。話頭剛起,馬上遭母親打斷。母親以彷彿自己才是被撞破了祕密的那種不讓人聲張的音量說,沒多少錢啦。一時我也就明白,父親出手大方,口袋空空如也是常有的事,拉不下臉為菸酒小錢向母親伸手,母親也不說破,只是把錢存進撲滿任父親取用。
在外飲宴也是這樣,臨付帳時母親自口袋取出幾張鈔票,桌底下偷偷交給父親,讓他作面子。
這些,我都看在眼裡。
●收入廖玉蕙、林芳妃主編,幼獅文化出版《甜蜜與憂傷》。
4 枵鬼
長輩C說過,她不吃釋迦和榴槤。我猜因為吃釋迦太過於麻煩,而榴槤氣味薰人。她說不是,只為了「釋迦和榴槤長得不太好看」,不好看的水果她不吃。
長輩C──算了,還是說出她的名字吧,她是資深藝文記者陳長華女士──是我在報社綜藝新聞中心擔任文化新聞版編輯時的老長官,一向照顧部屬。辦公室冷氣太強,一到傍晚就讓人打哆嗦,我卻常穿得單薄,有日,長華姊拿一件薄外套給我,說是她的公子出國前穿的,讓我放在辦公室,冷了可以披上。
在人生道路上,我常仰賴長輩的善意。改寫《慾望街車》裡白蘭琪的台詞,就該這麼說。
關於水果,我沒有長華姊的那些個講究,固有偏愛但並不挑食,不過,深感覺到目前連鎖超市賣的弓蕉、菝仔,都沒小時候的好吃。這應該不只是記憶為食物調味,或貧窮的日子裡格外珍惜物資。或許那時賣場不必替弓蕉預留太長銷售期,不至於過於青澀時便得採收;至於菝仔,「現挽的」,都是到鄰村果園現採現吃,自然鮮美無比。
菝仔不要連籽一起吃下肚裡去喔,大人警告,食菝仔放銃子。西瓜籽也不行,大哥看我手上拿一片西瓜,眼睛盯著盤裡另一片,猴急得連西瓜籽也囫圇吞下,恐嚇我,小心明天斗宅(tōo-tsâi ,肚臍)長出西瓜來。我扁扁嘴,回他,莫騙,我才沒這麼容易上當。
第二日醒來,一睜眼便和大哥一雙又黑又亮龍眼籽一般的眼睛對望,那是一副幸災樂禍的表情。我想起了什麼,趕緊伸手撩起上衣下襬,赫然在肚臍眼上摸到一枝西瓜苗。大哥說風涼話,就告訴你西瓜籽不能吃嘛,看你現在怎麼辦?我急了,哽咽了。還好大哥很有義氣地,說著我來吧,一把便將西瓜苗連根拔起,根部還帶著一小團黏土。
大哥告誡我,看你以後還敢不敢遮爾枵鬼!我噙著淚水,搖了搖頭。卻只見他莫名其妙地突然笑岔了氣,連平日不太表露情緒的母親,站在幾步之遙的地方,也笑出聲音來。
5 釣魚
一九八○年代,販厝一排排蓋起之前,竹圍仔處處池塘,假日裡父親找個蔭涼角落拋出釣線,足以消磨一整個午後。傍晚返家,手上提一桶魚交給母親,感覺像打了一場勝仗。儘管母親又因父親鎮日不見影跡而生一肚子悶氣,但接過這桶魚,也就認命地到井邊打水料理。
直到父親當年的年紀我才能體會,或許並非釣魚這件事吸引了父親,而是享受難能可貴的獨處時光。但在那個客廳即工廠,所有時間縫隙都填滿家庭代工的年代,不事生產不啻是個罪惡,母親常為此嘀咕,而與父親起口角。
外婆家院子裡也有一口池塘,和一般池塘不同的是,它原用來養鴨,斜斜滑進地面像個碟子。我與父親並肩,一人一支釣竿,學父親拋竿,學父親一言不發像個大人。不一會兒浮標點頭,一拉,吃力得不得了,父親見狀,急放下釣竿過來幫忙。
咬餌的顯然是條大魚,一會兒往左一會兒往右,刁鑽得很,父親自己拿釣竿大概能夠制伏,但這時他自我身後環抱,大手包著小手使力氣。父親是要我「自己」釣起這條魚。嘴上「出力出力」喊著時,腳步一踉蹌他卻跌倒了,跌倒了而仍喊著,出力,毋通放手。
我根本沒打算鬆手,但土石流般地,止不住往前滑動的步伐,我被拉進了水塘。
還是父親下水去把我救上來的,母親、外婆忙著料理一身濕淋淋的我,而父親雙腳污泥站在一旁,哈哈大笑。直說,別人釣魚,你卻被魚釣走了!哈哈哈。
我瞪著父親,就快哭出來了。
6 信邪
「你以為我是被嚇大的嗎?」電影、電視裡常見劇中人這樣向爭執的對方嗆聲。其實,仔細想想,我們還真都是被嚇大的。
早在媽媽肚裡,孕婦的禁忌便不勝枚舉,比如不能多吃醬油,否則日後會生出深膚色小孩;又比如不能釘釘子、動刀剪,不只一回聽見竹圍仔的婦人低聲嘁嗾,說誰家產下五官或肢體有缺陷的嬰孩,肯定是懷孕期間動了刀剪,並以其部位推算犯忌的月分。
語氣裡帶有一種「怎麼可以不信邪呢」的批判。
隨著嬰孩日漸長大,時時觸犯著禁忌,大人跟在後頭「不能這樣、不能那樣」地叮囑──不能拿筷子敲碗,乞丐才這麼做;筷子不能插白飯上,這是祭拜的模式;不能吃雞爪,食雞爪剺破冊;碗裡不能留飯粒,小心日後嫁娶的對象是個麻臉的。也不能騎在狗背上,要不,婚禮當天會下雨。
母親還說,不能跟姓黃的交往,因為母親姓黃。這就有優生學的根據了。
拿筷子的高低則可以預測未來對象住家的遠近,拿得越高距離越遠。
萬物有神,也有魔神仔:不能拔腳毛,一支腳毛管三隻鬼;晚上尤其容易招鬼,不能吹口哨、有人叫你不能回頭,不能行經竹林,有竹篙鬼;棄置路邊的紅包不能撿,一撿,就會有人跳出來,要你娶鬼新娘。
有些禁忌變成生活習慣──不能搗燕子築在屋簷底的巢,燕子是瑞鳥;不能踩戶橂,戶橂有神,如今若見有人大剌剌踩在戶橂上,我自然冒出「這個人真沒家教」的念頭;蠶的計量單位是「仙」,不能叫「隻」,否則養不活;不能用紅筆寫名字,會招來厄運;出殯的隊伍經過時,要遮住繡在制服上自己的名字;參加喪禮不能說再見,上醫院看病也是。
也有一些就顧不得那許多了:屋裡不能張傘,會遭賊偷;衣服不能在室外晾過夜,會沾上髒東西;不能以手指指月,耳朵會被刈去;不能拔白頭髮,拔一根長三根。
……
小時候,大人提出這些禁忌,是無可商量的,若有孩子想追根究柢,多問為什麼,阿公回他一句「囡仔人有耳無喙」,也就拍板定案。
7 野台
最初的電影並不是在電影院裡看的,而是野台。作醮酬神搬演的以大戲為主、布袋戲為輔;私人還願常放映電影,大家樂、六合彩盛行時,簽中明牌,一演五天七天,甚至長達半個月的也有。
埤仔頭、下甸尾、頂番婆,距離竹圍仔步行一兩刻鐘可到的所在如有露天電影,幾名玩伴便相約著去看。若是冬天,出門前母親會幫忙將外套釦子扣到第一顆;若是夏天,甚至隨身帶一捲蚊香。
有回不知怎麼地我落了單,獨個兒拎一張小板凳走到鄰村看電影。放映機答答響著,射出一束光,光裡有微粒懸浮,風很大,屏幕刷刷波動,喇叭響徹雲霄。這是演給神明看的,聲音也要放送到天際吧。
銀幕上成龍屌兒啷噹地,一會兒調戲婦女,一會兒吃霸王餐,一會兒又路見不平出拳相助,終於在受了胯下之辱後發憤練功,吃盡苦頭打下根基,好不容易蘇乞兒才準備將絕學醉八仙傳授予他。
我弓著背,手肘支在膝蓋上,托腮看得入神。
突然聞到濃濃一股刺鼻酒氣近身,下意識地縮起身體緊緊抱住自己。是附近翻模工廠的僱工,瘦瘦的癟癟的,年紀並不很大但一臉皺,他嘿笑兩聲,我往旁挪動,把自己像隻蛹般團得緊緊的。
當他將手伸向我的褲襠時,當時年幼的我甚至不能確知到底發生了什麼,只覺得他的身上好臭,眼神渙散發出奇異的光。
我再無心看電影,端著小板凳返家,進門時母親問我電影不好看嗎怎麼這麼早回來。我說,突然想到功課還沒寫完。有種直覺是,剛剛發生了不該開口向旁人,哪怕是自己的母親說的事。母親看我無精打采,要我先去洗澡,明天一大早再叫我起床寫功課。
也許許多小男孩小女孩,都曾遭遇過這類,事發當時不敢、事後終其一生都不願對人提起,但放在心上忘也忘不了的事。
●入選柯裕棻主編、九歌出版《102年散文選》。
1 一場葬禮
父親帶我參加一場遠房親戚的葬禮。
擇吉日出殯,沿途房舍門柱事先都貼有紅紙頭,隊伍經過時家家戶戶設案拜祭。
當送葬隊伍走到村子口,少部分人摘去喪服,折返;其餘登遊覽車,車隊鑼鼓喧天一路鬧到墳場。
等待吉時下葬、覆土,白花花陽光灑下,眾人各自尋陰影底立著、蹲著,小孩們或有不耐煩,但很快找到玩伴,偶爾玩過了頭,遭大人低聲制止。
儀式過後,陸續上車,日頭下折騰大半天後得以歇息,都舒了一口氣。很快地車上氣氛熱絡,自報身分、職業,聊旅遊見聞,一陣陣笑聲漸次傳開。本還壓抑著,卻隱忍不住,有了喧譁的態勢。
竟有人唱起歌來。唱的是三天兩頭電視上播放的歌曲,一樹桃花千朵紅,朵朵帶笑舞春風;有人加入合唱,桃花伴著春風舞,歡送哥哥去從戎……找到共通語言般地,興致十分高昂。
幾個小時前還哭哭啼啼的這群人,不像剛參加過一場葬禮,倒像出門遊玩,把握最後相聚時刻作樂一番。
我緊緊握住父親的手臂,睜大眼睛看著這個令人納悶的場面。彼時,死亡是生命中最大的恐懼,害怕得連開口問大人那到底是怎麼回事都不敢。
要過了很多年後,如今我才懂得,自悲痛中快速復原的能力,不是上天對死者的殘忍,而是對生者的慈悲。
2 陰陽雨
對阿媽的印象已如經久曝曬的廣告紙,顏色褪得十分淡薄了。
有個場面似乎是,有人向她敬菸,她嘴上說毋免毋免,卻伸出手去把菸接了過來。這是我最早的幾個記憶之一。我仰頭站在一旁,目睹了推辭與接受同時進行,好像大太陽天裡下起了雨,當成一樁新鮮好玩的事去告訴了母親。
當時怎麼懂得,這是人際應對的客套,類似於儀式。
另有一個場面:二期稻作收穫後,粟仔曬在稻埕,夏日午後,天空猛地烏雲四合,西北雨倒臉盆水般潑下,頃刻間稻埕積水高逾腳踝,粟仔不斷被沖進排水道。大人小孩都頂著暴雨搶救,因為一雙小腳而幫不上忙的阿媽為眼前景象所驚嚇,突然癱軟,跌坐在地。
對了──記憶真像種在地底的憨吉(han-tsû,番薯),以為只有微微露出地表的那一個,一扯卻纍纍一大串──親朋好友探望,送來五爪蘋果、克寧奶粉,阿媽都收進五斗櫃。當她好大方拿在手上問有誰要時,水果已經開始腐爛,而奶粉早過了食用期限。
關於阿媽的記憶,遂瀰漫了爛熟的甜香,雜糅灰撲撲的霉味。
母親提過,有回阿媽出門晃盪了一圈,返家後盛讚自家水田種得真好,追問之下才得知,她根本找錯了地方。母親的結論是,看恁阿媽命有好無?
母親沒說出口的,也許是對自己操勞一生的惋歎?
母親真夠辛苦的了。父親曾滿口酒氣透露,在我們三兄弟之外,母親懷第四胎,翁仔某兩人商量,自知無力扶養而偷偷去做了人工流產,又怕阿公阿媽發現,第二天母親仍舊照常操持家務,下田勞動。
父親說這些話時不當一回事的語氣,真令人討厭。
透過追憶,阿媽的形象浮水印般逐漸鮮活了起來──還記得的是,每遇陰陽雨她便要說一句諺語或歇後語一般的話:「出日閣落雨,嬰仔翻豬肚。」(註一)因為太古怪了,我格格笑著,一遍遍琅琅複述。問阿媽是什麼意思,阿媽說她也不知道,伊做囡仔時就聽大人按呢講了。
補述:
記憶中的「嬰仔翻豬肚」,因「嬰仔」與「燕子」台語同音,我一度以為,指的是天氣變化之際,燕子離巢,在空中嬉耍、遊獵,露出腹部凝脂般的白色羽毛。因自知強作解人,此事長期懸在心上。四十餘年後,上網查找,赫然發現有一首〈出日落雨〉的童謠:「出日落雨,刣豬翻豬肚。尪仔穿紅褲,乞食行無路,行去竹跤邊予狗哺。」才知「嬰仔」不是燕子,是尪仔,玩偶。另有數個相去不遠的版本。林文寶等人合著的《兒童文學》一書,對此寫道:「從字面來看,我們不容易了解它的意旨,但從社會學角度深入欣賞,才知道當時占據台灣的日本憲兵穿的是紅褲子,而這兒的『小玩偶」,指的是沒有人性的人,也就是借代日本憲兵。整首兒歌敘述日本憲兵的橫暴、喜怒無常,像邊出太陽,邊下雨,以及屠夫的翻豬肚子,翻來翻去,令人不可捉摸。」至此,懸念落實,無邪的兒時記憶卻沾染了肅殺的氛圍。
3 撲滿
扁扁圓圓的水果糖鐵盒是我的撲滿原型,一向疼愛我的大伯母幫忙收著,我把一角鎳幣、五角一元紙鈔交給她,她在我面前放進盒子,蓋嚴。有時我問,存多少錢了呢?大伯母便自衣櫥深處取出盒子,算數給我看。
將錢交給大伯母,是要比讓父親母親保管可靠多了。這世上若真有純良的好人,我心目中的大伯母要算上一個。
大伯母晚年遭逢病痛摧殘,我回竹圍仔探望,她勉強自床上坐起身來,閒聊幾句後相對無語。突然地她冒出一句話,我這世人嘛無做過啥物歹代誌,想袂曉哪會受遮的拖磨。我聽了,眼眶發酸,吶吶安慰幾句,心中感到茫然。那時候我已經略懂得人生實難的況味了。
最典型的撲滿是肥墩墩的小豬造型,全都在飽食後挨上一刀,沒能留下。倒是有個竹編大阪城撲滿,底部設有機關可以旋開,是姑姑自日本帶回的等路,肯定還遺落在家裡某個角落。
小時候常見母親將錢幣餵進大阪城,但我拎著它在空中搖晃,卻只聽見幾枚硬幣空空洞洞撞擊著。心裡納悶,便留意著動靜。
謎底很快揭曉,我撞見父親正倒拿著大阪城掏錢。父親雖不是什麼在家人面前擺派頭、端架子的人,但總是「父親」,他心虛囁嚅著,想,想買包菸。尷尬地笑了一笑。
我思量著該不該向母親通風報訊,終究還是決定說了。話頭剛起,馬上遭母親打斷。母親以彷彿自己才是被撞破了祕密的那種不讓人聲張的音量說,沒多少錢啦。一時我也就明白,父親出手大方,口袋空空如也是常有的事,拉不下臉為菸酒小錢向母親伸手,母親也不說破,只是把錢存進撲滿任父親取用。
在外飲宴也是這樣,臨付帳時母親自口袋取出幾張鈔票,桌底下偷偷交給父親,讓他作面子。
這些,我都看在眼裡。
●收入廖玉蕙、林芳妃主編,幼獅文化出版《甜蜜與憂傷》。
4 枵鬼
長輩C說過,她不吃釋迦和榴槤。我猜因為吃釋迦太過於麻煩,而榴槤氣味薰人。她說不是,只為了「釋迦和榴槤長得不太好看」,不好看的水果她不吃。
長輩C──算了,還是說出她的名字吧,她是資深藝文記者陳長華女士──是我在報社綜藝新聞中心擔任文化新聞版編輯時的老長官,一向照顧部屬。辦公室冷氣太強,一到傍晚就讓人打哆嗦,我卻常穿得單薄,有日,長華姊拿一件薄外套給我,說是她的公子出國前穿的,讓我放在辦公室,冷了可以披上。
在人生道路上,我常仰賴長輩的善意。改寫《慾望街車》裡白蘭琪的台詞,就該這麼說。
關於水果,我沒有長華姊的那些個講究,固有偏愛但並不挑食,不過,深感覺到目前連鎖超市賣的弓蕉、菝仔,都沒小時候的好吃。這應該不只是記憶為食物調味,或貧窮的日子裡格外珍惜物資。或許那時賣場不必替弓蕉預留太長銷售期,不至於過於青澀時便得採收;至於菝仔,「現挽的」,都是到鄰村果園現採現吃,自然鮮美無比。
菝仔不要連籽一起吃下肚裡去喔,大人警告,食菝仔放銃子。西瓜籽也不行,大哥看我手上拿一片西瓜,眼睛盯著盤裡另一片,猴急得連西瓜籽也囫圇吞下,恐嚇我,小心明天斗宅(tōo-tsâi ,肚臍)長出西瓜來。我扁扁嘴,回他,莫騙,我才沒這麼容易上當。
第二日醒來,一睜眼便和大哥一雙又黑又亮龍眼籽一般的眼睛對望,那是一副幸災樂禍的表情。我想起了什麼,趕緊伸手撩起上衣下襬,赫然在肚臍眼上摸到一枝西瓜苗。大哥說風涼話,就告訴你西瓜籽不能吃嘛,看你現在怎麼辦?我急了,哽咽了。還好大哥很有義氣地,說著我來吧,一把便將西瓜苗連根拔起,根部還帶著一小團黏土。
大哥告誡我,看你以後還敢不敢遮爾枵鬼!我噙著淚水,搖了搖頭。卻只見他莫名其妙地突然笑岔了氣,連平日不太表露情緒的母親,站在幾步之遙的地方,也笑出聲音來。
5 釣魚
一九八○年代,販厝一排排蓋起之前,竹圍仔處處池塘,假日裡父親找個蔭涼角落拋出釣線,足以消磨一整個午後。傍晚返家,手上提一桶魚交給母親,感覺像打了一場勝仗。儘管母親又因父親鎮日不見影跡而生一肚子悶氣,但接過這桶魚,也就認命地到井邊打水料理。
直到父親當年的年紀我才能體會,或許並非釣魚這件事吸引了父親,而是享受難能可貴的獨處時光。但在那個客廳即工廠,所有時間縫隙都填滿家庭代工的年代,不事生產不啻是個罪惡,母親常為此嘀咕,而與父親起口角。
外婆家院子裡也有一口池塘,和一般池塘不同的是,它原用來養鴨,斜斜滑進地面像個碟子。我與父親並肩,一人一支釣竿,學父親拋竿,學父親一言不發像個大人。不一會兒浮標點頭,一拉,吃力得不得了,父親見狀,急放下釣竿過來幫忙。
咬餌的顯然是條大魚,一會兒往左一會兒往右,刁鑽得很,父親自己拿釣竿大概能夠制伏,但這時他自我身後環抱,大手包著小手使力氣。父親是要我「自己」釣起這條魚。嘴上「出力出力」喊著時,腳步一踉蹌他卻跌倒了,跌倒了而仍喊著,出力,毋通放手。
我根本沒打算鬆手,但土石流般地,止不住往前滑動的步伐,我被拉進了水塘。
還是父親下水去把我救上來的,母親、外婆忙著料理一身濕淋淋的我,而父親雙腳污泥站在一旁,哈哈大笑。直說,別人釣魚,你卻被魚釣走了!哈哈哈。
我瞪著父親,就快哭出來了。
6 信邪
「你以為我是被嚇大的嗎?」電影、電視裡常見劇中人這樣向爭執的對方嗆聲。其實,仔細想想,我們還真都是被嚇大的。
早在媽媽肚裡,孕婦的禁忌便不勝枚舉,比如不能多吃醬油,否則日後會生出深膚色小孩;又比如不能釘釘子、動刀剪,不只一回聽見竹圍仔的婦人低聲嘁嗾,說誰家產下五官或肢體有缺陷的嬰孩,肯定是懷孕期間動了刀剪,並以其部位推算犯忌的月分。
語氣裡帶有一種「怎麼可以不信邪呢」的批判。
隨著嬰孩日漸長大,時時觸犯著禁忌,大人跟在後頭「不能這樣、不能那樣」地叮囑──不能拿筷子敲碗,乞丐才這麼做;筷子不能插白飯上,這是祭拜的模式;不能吃雞爪,食雞爪剺破冊;碗裡不能留飯粒,小心日後嫁娶的對象是個麻臉的。也不能騎在狗背上,要不,婚禮當天會下雨。
母親還說,不能跟姓黃的交往,因為母親姓黃。這就有優生學的根據了。
拿筷子的高低則可以預測未來對象住家的遠近,拿得越高距離越遠。
萬物有神,也有魔神仔:不能拔腳毛,一支腳毛管三隻鬼;晚上尤其容易招鬼,不能吹口哨、有人叫你不能回頭,不能行經竹林,有竹篙鬼;棄置路邊的紅包不能撿,一撿,就會有人跳出來,要你娶鬼新娘。
有些禁忌變成生活習慣──不能搗燕子築在屋簷底的巢,燕子是瑞鳥;不能踩戶橂,戶橂有神,如今若見有人大剌剌踩在戶橂上,我自然冒出「這個人真沒家教」的念頭;蠶的計量單位是「仙」,不能叫「隻」,否則養不活;不能用紅筆寫名字,會招來厄運;出殯的隊伍經過時,要遮住繡在制服上自己的名字;參加喪禮不能說再見,上醫院看病也是。
也有一些就顧不得那許多了:屋裡不能張傘,會遭賊偷;衣服不能在室外晾過夜,會沾上髒東西;不能以手指指月,耳朵會被刈去;不能拔白頭髮,拔一根長三根。
……
小時候,大人提出這些禁忌,是無可商量的,若有孩子想追根究柢,多問為什麼,阿公回他一句「囡仔人有耳無喙」,也就拍板定案。
7 野台
最初的電影並不是在電影院裡看的,而是野台。作醮酬神搬演的以大戲為主、布袋戲為輔;私人還願常放映電影,大家樂、六合彩盛行時,簽中明牌,一演五天七天,甚至長達半個月的也有。
埤仔頭、下甸尾、頂番婆,距離竹圍仔步行一兩刻鐘可到的所在如有露天電影,幾名玩伴便相約著去看。若是冬天,出門前母親會幫忙將外套釦子扣到第一顆;若是夏天,甚至隨身帶一捲蚊香。
有回不知怎麼地我落了單,獨個兒拎一張小板凳走到鄰村看電影。放映機答答響著,射出一束光,光裡有微粒懸浮,風很大,屏幕刷刷波動,喇叭響徹雲霄。這是演給神明看的,聲音也要放送到天際吧。
銀幕上成龍屌兒啷噹地,一會兒調戲婦女,一會兒吃霸王餐,一會兒又路見不平出拳相助,終於在受了胯下之辱後發憤練功,吃盡苦頭打下根基,好不容易蘇乞兒才準備將絕學醉八仙傳授予他。
我弓著背,手肘支在膝蓋上,托腮看得入神。
突然聞到濃濃一股刺鼻酒氣近身,下意識地縮起身體緊緊抱住自己。是附近翻模工廠的僱工,瘦瘦的癟癟的,年紀並不很大但一臉皺,他嘿笑兩聲,我往旁挪動,把自己像隻蛹般團得緊緊的。
當他將手伸向我的褲襠時,當時年幼的我甚至不能確知到底發生了什麼,只覺得他的身上好臭,眼神渙散發出奇異的光。
我再無心看電影,端著小板凳返家,進門時母親問我電影不好看嗎怎麼這麼早回來。我說,突然想到功課還沒寫完。有種直覺是,剛剛發生了不該開口向旁人,哪怕是自己的母親說的事。母親看我無精打采,要我先去洗澡,明天一大早再叫我起床寫功課。
也許許多小男孩小女孩,都曾遭遇過這類,事發當時不敢、事後終其一生都不願對人提起,但放在心上忘也忘不了的事。
●入選柯裕棻主編、九歌出版《102年散文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