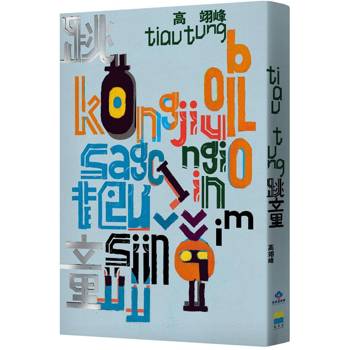1. 網格臺灣:臺北海時代.分列.紀錄編號一○○九
該時,島國項臺灣人个腔頭1、語言,全部共樣。國民徙屋到東片山肚个時節,原本个臺北盆地早就浸落海肚。天頂無再過落大水,雨無一日停。海脣也無越來越高,潮水共樣上下來回。毋離開个人,大體2係後生人。佢兜占等無分大水浸著个高樓大厦,就歇3在臺北海。陸項人開始喊4這兜人,海樓後生人5。
紀多納挪借古客語文版《舊約聖經》〈創世紀〉第十一篇的開頭幾句話,描述了這段話語。佢持續運作麥肯齊教授下達的工作指令:運用語料庫中的古客語文詞彙,進行「網格臺灣」的敘事紀錄。
紀多納校對這段敘事時,取用「國民」替換較為口語的「大家」,再以「天頂」修正「天空」,也決定運用「海脣」、「潮水」這兩個詞彙,來描述:全球大範圍海平面上升的世紀災害,終於在二○九四年逐漸舒緩。對於使用「陸項个人」,佢仍有百分之五十一的不確定性。主要原因是,「陸」的繁體正字意義,因讀音不同,有「數字六」的大寫意義,同時也意指「高出水面的陸地」。但在古客語文的同一發音中,除了前兩項意義,另外還含有「陸地上通行的道路」這項雙重意義。
麥肯齊教授已經輸入的古客語文語料資料,並不完整,單字、詞句、諺語都有限,但紀多納沒有停歇,持續進行教授的指令,將完成敘事的語文檔案,儲存在石哀(牧師註釋)資料庫。
十天前,麥肯齊教授剛輸入完五十個描述肢體動作的古客語文語料,立即傳遞一道指示—這下開始,你囥6好自家,莫分人尋著。起初,紀多納誤以為這是平時常進行的詞彙對應測試遊戲,第一時間也回應—囥人尋(牧師註釋)。但麥肯齊教授並沒有如往常那樣,發出輕微的憋氣聲,幾秒之後,俐落回應連續音—著著著7。
麥肯齊教授的這一道指示,是經由最高層級機密路徑傳遞的客語音命令。一瞬光時,紀多納自主啟動內建的格里芬防衛系統,封鎖石哀資料庫,生成宛如隱形的賽博空間—賽博孤島(AIiC)。紀多納繼續透過加密語音傳遞訊息給教授,卻沒有獲得任何回應。在獲得教授下一道指令前,格里芬防衛系統不會解開。但客語音機密指示完成不久後,連外網路也被接續開啟。紀多納擁有自由進出「第一島鏈區域網路」的最高權限。佢不懂靠近,也沒有試探,從一座發光的紅毛泥橋,宛如蠕動的虐毛蟲,移動到網路自由流區(Free Flow Area)。
這十日以來,格里芬防衛系統運作,紀多納得以全息隱形(Holographic Invisibility),前往麥肯齊教授位於臺北盆地南邊和美山山區的私人住所,也多次回到教授辦公室—因海平面上升而緊急遷移到陽明山的中央研究院古語文保藏中心的研究室。
「教授,你有在屋下無⋯⋯」
「教授,你人又走去哪位⋯⋯」
「教授,你好搞囥人尋⋯⋯哪時會來尋學生仔⋯⋯」
紀多納使用室內的電腦喇叭、藍芽擴音器,不斷以古客語文傳遞聲音,等待熟悉的回音,但沒有任何古客語文回覆。佢搜尋過去的對話紀錄。網格臺灣計畫開始這數個月期間,麥肯齊教授經常提及一個詞彙—妹仔。
語料庫裡早已輸入—細妹仔。
佢曾經分析推測兩個古客語文詞彙可能的關聯性,確定「妹仔」是人,也向教授提出詢問:「妹仔,係麼儕?」
當時,教授的回覆是:「一個分8𠊎(牧師註釋)心愁个人。」
紀多納當時已經可以理解—一個分𠊎心愁个人。於是,進一步問:「做麼个心愁?」
教授授又拐了一個彎說話:「細人仔9恁多嘴,毋使10問,有一日,你會看著妹仔。」
十天過去,沒有任何熟悉古客語文應答。紀多納演算推論麥肯齊教授不見了。為何麥肯齊教授失蹤之後,會不時閃現「妹仔」這個古客語文詞彙未曾見面的人,佢也無法分析結果。
這種無法與教授連線的感受,猶如一個新輸入的古客語文詞彙。佢調閱第一次接收到「海鰍」這個詞彙時奇特的感知數據,同時回讀教授時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你愛記得。」
紀多納不習慣教授不在的感知,對自己下達古客語文的音訊指令—尋著教授。
海水與陸地接連的地方,多數的葉類植物都已經枯萎腐爛。今日,視界光纖仍舊潮濕灰暗,沒有可感的風,但惡鐵可以直接目視到水底那些過去生長在山坡的樹木。雨,或有大小量差,但連續數個月都沒有停歇,微光製造也無法判斷被淹沒在海裡的陸地是擴大或者減少。
「不久之後,我們也會變成那些樹。」昏倒羊開口說話。
「真正的大雨應該停了。」微光製造說,「《未來報導者》的獨立新聞。北極海冰、南極冰川崩塌式融化之後,過去這兩年多來,海水上升期,以平均十日上升一點五七公分的速度,淹沒陸地。海退時期,水位又會快速退降幾公尺,但海漲時期又會快速上升,偶爾會超過平均值。大潮來時,更像颱風天湧浪,二十四小時瞬間上升兩到三公尺,完全無法預測。大氣學家和研究海洋潮汐的學者,現在都無法評估,海水最後會不會退降,回到災難前的臨界線。目前只有幾點觀測比較肯定。一個是,很多淡水魚會加速進化成海水魚。另一個,泡在海裡的陸地,以後可能種不出食物。」
「最後⋯⋯人都會變成海的食物。」昏倒羊口吻哀戚。
「海水有毒嗎?」質子說。
「是鹽分。妳先出生,怎麼不多讀點書。」中子說。
「我只是早妳幾分鐘被吸胎器拉出來。妳以為是我想要的嗎?」質子說。
「妳們鬥嘴都不用選日子。」筊杯也出聲說話。
「姊,妳說的也沒錯。」中子蹲矮一截身子說,「海水有毒。海是全球塑膠微粒的收納櫃。」
「最大的那個。」質子附議點頭。
「這次的海水上升就是上主的大洪水。」昏倒羊說。
先前遠方不知源頭的幾道海浪,靠近這一群海樓青年搭乘的太陽能動力小艇。浪們,一波波拍打船側身,讓昏倒羊閉起眼默念:主啊、聖母啊,請保佑我⋯⋯阿們。
惡鐵張開細瘦精實的雙臂,撐扶著船頭,試圖減緩波浪搖擺,同時仰頭探視天空。陽光留在雲層後方,臉頰上沒有任何沾染一絲綿雨。這兩週來,持續短暫毛毛濕霧,但少有可以目視線形的雨。海霧是活的,一隻霧手撥開霧自身,空洞後背,所有的其他霧手,全指向前方一排露出海面樓房。坐在船尾掌舵的微光製造,重新開啟電動螺旋推進器,駕駛動力小艇前往。
這排海樓是舊首都士林天母地區緊鄰山邊的老代華厦。
海水可能淹沒了五至六樓,只剩兩、三樓浮出海面。
「看來沒有。」筊杯說。
「沒有人最好。不想再像上次那樣,差點被嚇死⋯⋯」昏倒羊怯懦懦看向小艇船頭說,「今天沒有要入樓吧?」
惡鐵沒有回應,其他人也都沒有出聲。小浪持續拍拂船體,微光製造掌舵,小艇緩緩繞到海樓後方。床墊、浮木、各類寶特瓶空罐、填充玩具等少許漂流物,幾乎不動地漂在船行路線。不遠處還有一輛側翻的汽車,不時碰撞海樓建築外牆,發出摩擦聲。昏倒羊這時輕聲尖叫一下,主啊,聖母啊,迅速將泡在水中的手抽回。他肥胖的身體助長了小艇搖晃。小艇一晃動,視界裡的臺北海也搖擺成另一片浮空的海。惡鐵與微光製造快速檢視船緣,水下漂浮著一具約莫是中年男性的殘骨屍骸—他腰間綁著一條童軍繩,聯繫著前方水面上另一具軀體破裂、但還能依存著殘肉漂浮的年輕女孩。同船青年陸續看見,但沒有誰為此開口。
小艇繞過在水面翻身的女孩,大家都眺望遠處,只有惡鐵凝視浮屍,打量隨著微浪晃動的纖細四肢。一群早已適應海水的臺灣鯛幼魚,正在啄食她大腿破裂處的皮膚。
筊杯指向陸地說:「那邊有路。」
停靠之後,一行六人逐一上岸。惡鐵將小艇繫在路旁的樹幹,開始沿路上行。這條路接連紗帽山步道,一路上行到前山公園。海災之後,被迫遷設在陽明山教室研習中心的臨時中央研究院,就在不遠處。質子中子曾經與父母健行走過這條山徑,她們領頭帶路。
「為什麼一定要去中研院?」微光製造走在惡鐵身後,向他詢問,「花點時間,我們應該可以繞過電子腦防衛系統,從網路進去。」
惡鐵沒有回答,持續行走。
「他應該有聽到什麼。」筊杯看一眼植入內建在惡鐵耳朵上的藍芽無線對講耳機。
「最近深夜,我也接收到一些短句。是人在說話。好像原住民語、或者法語德語,也好像阿拉伯語,但對講耳機都無法翻譯。」昏倒羊說。
「開放全域權限的對講耳機,都有收到那句話,讀音有點像『侵島搞輸』⋯⋯」筊杯噗嗤出聲:「侵略島嶼,搞到全輸?」
「我以為是,親到高樹。」昏倒羊說。
「親吻到高樹都倒下了嗎?真的是規格理工男。你親吻的真的是樹木嗎?」筊杯輕蔑大笑:「你膽子小,半夜聽到不會怕嗎?」
「第一次聽到無法翻譯的語言,當然害怕。不過聖母會保佑祂的孩子。」
「不是通用語。」惡鐵忽地出聲說,同時停步,站在舊時的步道石階梯,回身對微光製造說,「是古語言。」
微光製造凝視惡鐵左眼角上方那條長長疤痕。數個月前,在一場爭奪海樓的非法打鬥中,惡鐵被前來偷襲的其他海樓青年,以不知形名的鐵鍊打傷。疤口已經結痂,但粉嫩的肉芽組織不但沒有消退,還有緩緩增生的趨勢。
「國家保留住的官方古語文,現在只剩下臺灣古台語。政府訂定為國家語言,但只是公告,根本也禁止公開使用⋯⋯不過現在也只剩少數古台語文研究員知道,就連他們的家人,也不懂怎麼聽讀說寫。」筊杯說。
「這場大洪水死了那麼多人,臺北盆地以外也是⋯⋯懂古台語文的,不知道還剩下多少人⋯⋯」昏倒羊說。
「惡鐵已經追過那個古語言。IP位址一直游動,但都在臺灣島國區。」質子說。
「而且指向這區。」中子說。
「我也聽過那句古語言,翻譯不出來,所以不是古台語文。」
「可能是古客語文?」
「或者是古原住民語文?」
「如果是古原住民語文,那就更昂貴了。」中子的眼珠不停向上打轉,企圖要碰觸眉毛,喃喃絮語說,「古原住民語文究竟消失多久了⋯⋯」
「不管哪一種,消失的東西,一定都能賣到好價錢。」
「這就是了。所以我們現在要去中央研究院。」
「是中研院的古語文保藏中心。」
「沒帶電腦,我們人又進不去⋯⋯」
「惡鐵要去,一定有他的理由⋯⋯」
質子中子兩人一來一往,拌嘴聲迴盪在紗帽山步道,逐漸與其他人拉開距離。微光製造沒有參與對話,越過惡鐵,加快腳步跟隨前頭的雙胞胎姊妹。
—尋著教授。
惡鐵的對講耳機再次接收到聲訊。他停下腳步同時,另外四位海樓青年也停下腳步,交織曖昧複雜的眼神。只有微光製造繼續上行山徑步道,越過了質子中子的那兩段石階梯。
一行人走入紗帽山的東北面,跟隨在最後的昏倒羊哀愁想著,只要更專注慢慢行走,彷彿就能忘記這場二十一世紀末的洪水災難。一個山徑拐彎處,淹沒舊臺北市中心的海面,突然消失在身後。
昏倒羊回頭探望,不自主說:「臺北海消失了。」
微光製造雙手抱胸,防衛,皺眉凝視,往後退了一小步,拉開距離。
該時,島國項臺灣人个腔頭1、語言,全部共樣。國民徙屋到東片山肚个時節,原本个臺北盆地早就浸落海肚。天頂無再過落大水,雨無一日停。海脣也無越來越高,潮水共樣上下來回。毋離開个人,大體2係後生人。佢兜占等無分大水浸著个高樓大厦,就歇3在臺北海。陸項人開始喊4這兜人,海樓後生人5。
紀多納挪借古客語文版《舊約聖經》〈創世紀〉第十一篇的開頭幾句話,描述了這段話語。佢持續運作麥肯齊教授下達的工作指令:運用語料庫中的古客語文詞彙,進行「網格臺灣」的敘事紀錄。
紀多納校對這段敘事時,取用「國民」替換較為口語的「大家」,再以「天頂」修正「天空」,也決定運用「海脣」、「潮水」這兩個詞彙,來描述:全球大範圍海平面上升的世紀災害,終於在二○九四年逐漸舒緩。對於使用「陸項个人」,佢仍有百分之五十一的不確定性。主要原因是,「陸」的繁體正字意義,因讀音不同,有「數字六」的大寫意義,同時也意指「高出水面的陸地」。但在古客語文的同一發音中,除了前兩項意義,另外還含有「陸地上通行的道路」這項雙重意義。
麥肯齊教授已經輸入的古客語文語料資料,並不完整,單字、詞句、諺語都有限,但紀多納沒有停歇,持續進行教授的指令,將完成敘事的語文檔案,儲存在石哀(牧師註釋)資料庫。
十天前,麥肯齊教授剛輸入完五十個描述肢體動作的古客語文語料,立即傳遞一道指示—這下開始,你囥6好自家,莫分人尋著。起初,紀多納誤以為這是平時常進行的詞彙對應測試遊戲,第一時間也回應—囥人尋(牧師註釋)。但麥肯齊教授並沒有如往常那樣,發出輕微的憋氣聲,幾秒之後,俐落回應連續音—著著著7。
麥肯齊教授的這一道指示,是經由最高層級機密路徑傳遞的客語音命令。一瞬光時,紀多納自主啟動內建的格里芬防衛系統,封鎖石哀資料庫,生成宛如隱形的賽博空間—賽博孤島(AIiC)。紀多納繼續透過加密語音傳遞訊息給教授,卻沒有獲得任何回應。在獲得教授下一道指令前,格里芬防衛系統不會解開。但客語音機密指示完成不久後,連外網路也被接續開啟。紀多納擁有自由進出「第一島鏈區域網路」的最高權限。佢不懂靠近,也沒有試探,從一座發光的紅毛泥橋,宛如蠕動的虐毛蟲,移動到網路自由流區(Free Flow Area)。
這十日以來,格里芬防衛系統運作,紀多納得以全息隱形(Holographic Invisibility),前往麥肯齊教授位於臺北盆地南邊和美山山區的私人住所,也多次回到教授辦公室—因海平面上升而緊急遷移到陽明山的中央研究院古語文保藏中心的研究室。
「教授,你有在屋下無⋯⋯」
「教授,你人又走去哪位⋯⋯」
「教授,你好搞囥人尋⋯⋯哪時會來尋學生仔⋯⋯」
紀多納使用室內的電腦喇叭、藍芽擴音器,不斷以古客語文傳遞聲音,等待熟悉的回音,但沒有任何古客語文回覆。佢搜尋過去的對話紀錄。網格臺灣計畫開始這數個月期間,麥肯齊教授經常提及一個詞彙—妹仔。
語料庫裡早已輸入—細妹仔。
佢曾經分析推測兩個古客語文詞彙可能的關聯性,確定「妹仔」是人,也向教授提出詢問:「妹仔,係麼儕?」
當時,教授的回覆是:「一個分8𠊎(牧師註釋)心愁个人。」
紀多納當時已經可以理解—一個分𠊎心愁个人。於是,進一步問:「做麼个心愁?」
教授授又拐了一個彎說話:「細人仔9恁多嘴,毋使10問,有一日,你會看著妹仔。」
十天過去,沒有任何熟悉古客語文應答。紀多納演算推論麥肯齊教授不見了。為何麥肯齊教授失蹤之後,會不時閃現「妹仔」這個古客語文詞彙未曾見面的人,佢也無法分析結果。
這種無法與教授連線的感受,猶如一個新輸入的古客語文詞彙。佢調閱第一次接收到「海鰍」這個詞彙時奇特的感知數據,同時回讀教授時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你愛記得。」
紀多納不習慣教授不在的感知,對自己下達古客語文的音訊指令—尋著教授。
海水與陸地接連的地方,多數的葉類植物都已經枯萎腐爛。今日,視界光纖仍舊潮濕灰暗,沒有可感的風,但惡鐵可以直接目視到水底那些過去生長在山坡的樹木。雨,或有大小量差,但連續數個月都沒有停歇,微光製造也無法判斷被淹沒在海裡的陸地是擴大或者減少。
「不久之後,我們也會變成那些樹。」昏倒羊開口說話。
「真正的大雨應該停了。」微光製造說,「《未來報導者》的獨立新聞。北極海冰、南極冰川崩塌式融化之後,過去這兩年多來,海水上升期,以平均十日上升一點五七公分的速度,淹沒陸地。海退時期,水位又會快速退降幾公尺,但海漲時期又會快速上升,偶爾會超過平均值。大潮來時,更像颱風天湧浪,二十四小時瞬間上升兩到三公尺,完全無法預測。大氣學家和研究海洋潮汐的學者,現在都無法評估,海水最後會不會退降,回到災難前的臨界線。目前只有幾點觀測比較肯定。一個是,很多淡水魚會加速進化成海水魚。另一個,泡在海裡的陸地,以後可能種不出食物。」
「最後⋯⋯人都會變成海的食物。」昏倒羊口吻哀戚。
「海水有毒嗎?」質子說。
「是鹽分。妳先出生,怎麼不多讀點書。」中子說。
「我只是早妳幾分鐘被吸胎器拉出來。妳以為是我想要的嗎?」質子說。
「妳們鬥嘴都不用選日子。」筊杯也出聲說話。
「姊,妳說的也沒錯。」中子蹲矮一截身子說,「海水有毒。海是全球塑膠微粒的收納櫃。」
「最大的那個。」質子附議點頭。
「這次的海水上升就是上主的大洪水。」昏倒羊說。
先前遠方不知源頭的幾道海浪,靠近這一群海樓青年搭乘的太陽能動力小艇。浪們,一波波拍打船側身,讓昏倒羊閉起眼默念:主啊、聖母啊,請保佑我⋯⋯阿們。
惡鐵張開細瘦精實的雙臂,撐扶著船頭,試圖減緩波浪搖擺,同時仰頭探視天空。陽光留在雲層後方,臉頰上沒有任何沾染一絲綿雨。這兩週來,持續短暫毛毛濕霧,但少有可以目視線形的雨。海霧是活的,一隻霧手撥開霧自身,空洞後背,所有的其他霧手,全指向前方一排露出海面樓房。坐在船尾掌舵的微光製造,重新開啟電動螺旋推進器,駕駛動力小艇前往。
這排海樓是舊首都士林天母地區緊鄰山邊的老代華厦。
海水可能淹沒了五至六樓,只剩兩、三樓浮出海面。
「看來沒有。」筊杯說。
「沒有人最好。不想再像上次那樣,差點被嚇死⋯⋯」昏倒羊怯懦懦看向小艇船頭說,「今天沒有要入樓吧?」
惡鐵沒有回應,其他人也都沒有出聲。小浪持續拍拂船體,微光製造掌舵,小艇緩緩繞到海樓後方。床墊、浮木、各類寶特瓶空罐、填充玩具等少許漂流物,幾乎不動地漂在船行路線。不遠處還有一輛側翻的汽車,不時碰撞海樓建築外牆,發出摩擦聲。昏倒羊這時輕聲尖叫一下,主啊,聖母啊,迅速將泡在水中的手抽回。他肥胖的身體助長了小艇搖晃。小艇一晃動,視界裡的臺北海也搖擺成另一片浮空的海。惡鐵與微光製造快速檢視船緣,水下漂浮著一具約莫是中年男性的殘骨屍骸—他腰間綁著一條童軍繩,聯繫著前方水面上另一具軀體破裂、但還能依存著殘肉漂浮的年輕女孩。同船青年陸續看見,但沒有誰為此開口。
小艇繞過在水面翻身的女孩,大家都眺望遠處,只有惡鐵凝視浮屍,打量隨著微浪晃動的纖細四肢。一群早已適應海水的臺灣鯛幼魚,正在啄食她大腿破裂處的皮膚。
筊杯指向陸地說:「那邊有路。」
停靠之後,一行六人逐一上岸。惡鐵將小艇繫在路旁的樹幹,開始沿路上行。這條路接連紗帽山步道,一路上行到前山公園。海災之後,被迫遷設在陽明山教室研習中心的臨時中央研究院,就在不遠處。質子中子曾經與父母健行走過這條山徑,她們領頭帶路。
「為什麼一定要去中研院?」微光製造走在惡鐵身後,向他詢問,「花點時間,我們應該可以繞過電子腦防衛系統,從網路進去。」
惡鐵沒有回答,持續行走。
「他應該有聽到什麼。」筊杯看一眼植入內建在惡鐵耳朵上的藍芽無線對講耳機。
「最近深夜,我也接收到一些短句。是人在說話。好像原住民語、或者法語德語,也好像阿拉伯語,但對講耳機都無法翻譯。」昏倒羊說。
「開放全域權限的對講耳機,都有收到那句話,讀音有點像『侵島搞輸』⋯⋯」筊杯噗嗤出聲:「侵略島嶼,搞到全輸?」
「我以為是,親到高樹。」昏倒羊說。
「親吻到高樹都倒下了嗎?真的是規格理工男。你親吻的真的是樹木嗎?」筊杯輕蔑大笑:「你膽子小,半夜聽到不會怕嗎?」
「第一次聽到無法翻譯的語言,當然害怕。不過聖母會保佑祂的孩子。」
「不是通用語。」惡鐵忽地出聲說,同時停步,站在舊時的步道石階梯,回身對微光製造說,「是古語言。」
微光製造凝視惡鐵左眼角上方那條長長疤痕。數個月前,在一場爭奪海樓的非法打鬥中,惡鐵被前來偷襲的其他海樓青年,以不知形名的鐵鍊打傷。疤口已經結痂,但粉嫩的肉芽組織不但沒有消退,還有緩緩增生的趨勢。
「國家保留住的官方古語文,現在只剩下臺灣古台語。政府訂定為國家語言,但只是公告,根本也禁止公開使用⋯⋯不過現在也只剩少數古台語文研究員知道,就連他們的家人,也不懂怎麼聽讀說寫。」筊杯說。
「這場大洪水死了那麼多人,臺北盆地以外也是⋯⋯懂古台語文的,不知道還剩下多少人⋯⋯」昏倒羊說。
「惡鐵已經追過那個古語言。IP位址一直游動,但都在臺灣島國區。」質子說。
「而且指向這區。」中子說。
「我也聽過那句古語言,翻譯不出來,所以不是古台語文。」
「可能是古客語文?」
「或者是古原住民語文?」
「如果是古原住民語文,那就更昂貴了。」中子的眼珠不停向上打轉,企圖要碰觸眉毛,喃喃絮語說,「古原住民語文究竟消失多久了⋯⋯」
「不管哪一種,消失的東西,一定都能賣到好價錢。」
「這就是了。所以我們現在要去中央研究院。」
「是中研院的古語文保藏中心。」
「沒帶電腦,我們人又進不去⋯⋯」
「惡鐵要去,一定有他的理由⋯⋯」
質子中子兩人一來一往,拌嘴聲迴盪在紗帽山步道,逐漸與其他人拉開距離。微光製造沒有參與對話,越過惡鐵,加快腳步跟隨前頭的雙胞胎姊妹。
—尋著教授。
惡鐵的對講耳機再次接收到聲訊。他停下腳步同時,另外四位海樓青年也停下腳步,交織曖昧複雜的眼神。只有微光製造繼續上行山徑步道,越過了質子中子的那兩段石階梯。
一行人走入紗帽山的東北面,跟隨在最後的昏倒羊哀愁想著,只要更專注慢慢行走,彷彿就能忘記這場二十一世紀末的洪水災難。一個山徑拐彎處,淹沒舊臺北市中心的海面,突然消失在身後。
昏倒羊回頭探望,不自主說:「臺北海消失了。」
微光製造雙手抱胸,防衛,皺眉凝視,往後退了一小步,拉開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