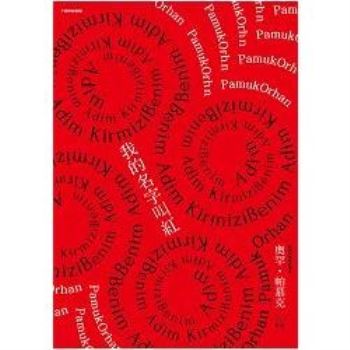1 我是一具屍體
如今我只是一具屍體,一具躺在井底的屍首。儘管我已經死了很久,心臟早已停止跳動,然而,除了那個卑鄙的殺人凶手之外,沒半個人知道我發生了什麼事。至於那個混蛋,他先摸了摸我的脈搏,傾聽我是否還有呼吸,確定我死了之後,又狠狠朝我的肚子踢了幾腳,然後才把我扛到井邊,抬起我的身體往下丟。當我跌落井底時,先前被他用石頭砸爛的腦袋摔裂開來;我的臉、我的額頭和臉頰,全部擠爛成一團;我全身的骨頭都散了,滿嘴都是鮮血。
我已經失蹤了將近四天,妻子和兒女一定到處找我。我的女兒在哭累了之後,一定正焦躁不安地瞪著庭院大門發呆。沒錯,我知道他們全都站在窗口,引頸期盼我的歸來。
不過,他們是真的在等待嗎?甚至我也不能確定。或許他們對於我的缺席早就習以為常。
真可悲呀!因為在這邊,生死線上的另一邊,讓人覺得好像自己昔日的生命仍然繼續走下去。在我出生前,已經存在著無窮的時間,而在我死後,時間更是沒有止盡。我以前從沒想過這一點:一直以來,我明晰地生活在兩團永恆的黑暗之間。
我很快樂,此時我才明白自己以前過得很快樂。在蘇丹殿下的工匠坊,我畫的書頁插畫最為精緻華麗,沒有人能夠匹敵。我私底下做的工作每個月為我賺進九百塊銀幣,這一切自然而然只讓此時此刻的情況更教人難以接受。
我的工作內容是替書本畫插畫及紋飾。我在書頁的邊緣畫上裝飾圖案,用鮮豔的色彩在它們周圍勾勒極為生動的花紋,像是葉子、枝幹、玫瑰、花朵和小鳥。我畫上中國樣式的扇形雲朵、糾結纏繞的串串藤蔓,以及隱約藏在層層色彩之下的瞪羚、遠洋帆船、蘇丹、樹木、宮殿、馬匹與獵人。當我年輕的時候,還會紋飾盤子、鏡子的背面,以及小櫃子,有時候我會畫一棟豪宅或博斯普魯斯宅邸的天花板,甚至只是一支木湯匙。然而這幾年來,我只專精於裝飾手抄本的頁面,因為蘇丹殿下願意支付高額的酬勞。我不能說這些現在都已經不再重要。就算你死了,你也知道金錢的價值。聽過我奇蹟般的聲音後,你們也許會想:「誰管你活著的時候賺多少錢,告訴我們你看見什麼。死後還有生命嗎?你的靈魂到哪去了?究竟有沒有天堂和地獄?死是什麼感覺?你很痛苦嗎?」問得沒錯,活著的人對於死後的世界總是極度好奇。或許你聽過這個故事,有一個人因為對這些問題太過好奇,以致於跑上戰場在士兵當中亂晃,於一群躺在血泊裡做生死掙扎的傷兵中,找到一個死而復生的人,心想這個人必定能告訴他另一個世界的祕密。然而一位帖木兒汗國的戰士誤以為這位追尋者是敵人,拔出彎刀俐落地把他劈成兩半,使他最後得出一個結論:在死後的世界裡人都會分成兩半。
荒唐!恰巧相反,我甚至要說,活著的時候分開的靈魂在死後融合了。那些沉淪於魔鬼召喚下的罪惡異教徒們,宣稱死後沒有生命,大錯特錯,確實有另一個世界,感謝真主。證據呢,就是我現在正從這個世界對你們說話。我已經死了,不過你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我並沒有消失。很遺憾地,我得承認,我沒有看見偉大古蘭經中描述的情景,像是從天堂的金銀色涼亭旁蜿蜒流過的河流、長著碩大果實的寬葉樹木或是美麗的處女——雖然我記得很清楚,自己以前常常在腦中熱切地想像古蘭經〈大事〉這一章描寫的大眼美女是什麼模樣。除此之外,儘管古蘭經沒有提到,但在一些想像力豐富的夢想家如伊本‧阿拉比生花妙筆的描繪中,天堂有許多河流,流滿了牛奶、醇酒、清水與蜂蜜,事實上,這裡我沒看到半條河的蹤跡。不過對於那些藉由幻想期盼來世過活的正直人士,我絲毫無意挑戰他們的信仰,因此,容我說明,我所見到的一切全來自於個人的特別處境。任何相信或稍微了解死後世界的人都會明白,處於我目前的狀況,全身被憤怒擠壓,實在也不太可能見到天堂之河。
簡言之,我,人們稱為高雅‧埃芬迪大師的這位,死了。然而我還沒有被埋葬,也因此我的靈魂尚未完全脫離軀體。儘管我的處境想當然不是史上第一宗,但滯留於此種特殊狀態,卻使我身體不滅的那部分感受到難以言喻的痛苦。雖然感覺不到自己碎裂的頭骨、傷痕累累逐漸腐敗的軀體、一身斷骨,以及一半泡在冰水裡的身體,但我確實感覺到我的靈魂正深受折磨,絕望地掙扎想逃脫塵世的枷鎖。那就像整個世界,包括我的軀體,正收縮成為緊緊一團痛苦。
唯一能與這種痛苦收縮相提並論的,是在死亡的那個駭人剎那,我感覺到一種出人意料的輕鬆感。是的,當那個混蛋猛然拿石頭砸我的頭、打破我的腦袋時,我立刻明白他想殺死我,但我並不相信他會成功。突然間,我發現自己原來是個樂觀的人,以前在工匠坊和家庭的陰影下生活時,從不曾察覺這一點。我狂熱地緊抓住生命,我的指甲、手指及牙齒陷入他的皮膚裡。關於接下來他怎麼毒打我的慘痛細節,這裡就不再多加贅述。
在這場痛楚中我知道自己難逃一死,頓時一股不可思議的輕鬆感湧上心頭。離開人世的剎那,我感受到這股輕鬆;通往死亡的過程非常平順,彷彿在夢中看著自己沉睡。我最後一件注意到的東西,是凶手那雙沾滿泥雪的鞋子。我閉上眼睛,彷彿逐漸沉入睡眠,接著慢慢地失去知覺。
此時我的焦慮不在於我的牙齒像堅果般掉進滿是鮮血的嘴裡,也不在於我的臉摔爛以至於無法辨認,更不是因為我被棄屍在一口深不見底的井裡——而是每個人都以為我還活著。我騷動的靈魂之所以痛苦不堪,是因為我的家人以及,是的,關心我的親友,可能猜想我正在伊斯坦堡某個地方處理瑣事,或甚至正在調戲另一個女人。夠了!趕快找到我的屍體,祭拜我,並把我好好埋葬。最重要的,找出殺我的凶手!因為就算你們把我葬在最富麗堂皇的陵墓,只要那個混蛋仍舊自由逍遙,我就會在墳墓裡輾轉難安,日日等待,並且夜夜騷擾你們。快找到那個婊子養的凶手,我就告訴你們死後世界的所有細節。不過記住,抓到他之後,一定要凌遲他一番,把他的骨頭一段一段拆成八塊,最好是他的肋骨;在用專為酷刑特製的尖針戳進他的頭皮前,先拿支鉗子把他噁心的油膩頭髮拔光,一根一根拔,讓他一次又一次地尖叫。
這個讓我忿恨難當的凶手究竟是誰?他為什麼用如此出其不意的手段殺我?請注意並探究這些細節。你們說世界上充滿了卑微低賤的罪犯,不是這個人幹的,就是那個人做的?如果你這麼想的話,讓我提醒你們:我死亡的背後隱藏著一個駭人的陰謀,極可能瓦解我們的宗教、傳統,以及世界觀。張大你們的眼睛,探究你們信仰並生活其中的伊斯蘭世界,存在著何種敵人,他們為什麼要除掉我?甚至試著去體認為什麼有一天他們也可能同樣對你下毒手。偉大的傳道士,艾祖隆的努索瑞教長,我曾流淚傾聽他的布道,他所預測的所有事情,將一件接著一件全部成真。讓我再這麼說,如果把我們如今陷入的處境寫進書裡,就連最精湛的細密畫家也永遠無法配以圖畫呈現。至於古蘭經——若我誤解的話,求真主責罰——這本書之所以擁有如此強大的力量,正是由於它絕不可能被描繪。我懷疑你們是否徹底明瞭這個事實。
聽我的話。我當學徒的時候,也因為害怕而忽視了隱藏的真相及上天的話語。過去我總以開玩笑的口氣談論。結果,我落得這種下場,躺在一口可悲的井底!留心了,它也可能發生在你身上。現在,我什麼都不能做了,只希望我能徹底腐爛,用我的屍臭引他們來找到我。我什麼都不能做了,只剩下一點希望,想像那個齷齪的殺人凶手被抓到後,某個善心人士會用什麼恐怖的手段凌虐他。
2 我的名字叫布拉克
離開伊斯坦堡十二年後,我像個夢遊者再度歸來。「土地召喚他回來。」他們這麼形容快死的人,就我的情況而言,是死亡引領我返回自己從小生長的城市。初抵舊地時,我以為這裡只有死亡;雖然之後,我也將遇見愛情。只不過,如同我對這個城市的記憶一樣,愛情是一段遙遠而早已忘卻的過去。十二年前,就是在伊斯坦堡,我無可救藥地愛上我的表妹。
離開伊斯坦堡的最初四年,我行遍廣袤無垠的大草原、積雪覆蓋的山脈、哀傷憂愁的波斯城市,遞送信件並收集稅款,那時,我向自己坦承,我已慢慢淡忘了遺留在身後的童年摯愛面容。在逐漸累積的驚恐中,我絕望地試圖記起她,但終究發現除了愛情之外,那張久未見面的臉孔已經褪去。待在東方的第六年,我擔任帕夏的祕書,工作或旅行,這時我明白幻想中的臉孔不再是我愛人的。之後,到了第八年,我忘記了自己在第六年時心中誤認的那張臉,於是再度編織出一張截然不同的臉孔。就這樣,到了第十二年,我以三十六歲的年紀回到這座城市時,痛苦地察覺愛人的容顏早已離我而去。
浪跡天涯十二年這段期間,我的許多朋友及親戚相繼死去。我前往俯瞰金角灣的墓園探視,為在我離開時過世的母親及叔伯們禱告。泥土的氣味混入我的回憶。母親的墳墓旁,有人打破了一只陶水罐,不知道為什麼,我凝視著地上的碎片,哭了起來。我是為死去的人流淚嗎?還是因為,很奇怪的,經過這麼多年,我仍然只是在生命的開端?或者因為,我已經來到了人生旅途的終點?雪輕柔地落下。我失神望著雪花四處飄散,腦中昏亂地想像生命的種種,以致沒有注意到墓園的陰暗角落,一隻黑狗正盯著我瞧。
淚水止息後,我擦淨鼻子。離開墓園時,我看見那隻黑狗友善地搖尾巴。稍晚,我在城中找到一個地方安頓下來,租下一間父親的親戚以前住過的房子。女房東看到我,似乎想起她在戰場上被薩非波斯王朝士兵殺死的兒子,因此同意幫我打掃房間並為我煮飯。
我出發展開漫長而滿足的散步,穿梭於街道間,彷彿現在停留的城市不是伊斯坦堡,而是暫時來到位於世界另一端的某座阿拉伯城市。馬路變得比以前窄,至少在我看來是如此。在某些區域,道路擠在緊緊相鄰的房屋之間,我得全身貼上牆壁和大門,才不會被滿載物品的馬匹撞上。城裡多了許多有錢人,至少在我看來是如此。我看見一輛裝飾華麗的馬車,如同一座堡壘,由高傲的馬匹拖著,類似的車在阿拉伯或波斯是看不到的。在「焚毀的石柱」附近,我看到幾個一身襤褸的討厭乞丐擠成一堆,四周飄散著從雞販市場傳出的內臟殘渣氣味。其中一個瞎子空瞪著落下的雪花微笑。
如果有人告訴我,伊斯坦堡以前是個較為貧窮、狹小、快樂的城市,我大概不會相信,但我的內心正是這麼對我說。儘管我摯愛的屋子仍在原處,隱藏在菩提樹和栗樹之間,但待我敲門詢問後,才知道屋子的主人已經換人了。我得知愛人的母親,我的阿姨,已經去世,而她的丈夫,我的恩尼須帖,以及他的女兒皆已搬走。從應門的陌生人口中,我得知父親及女兒淪為某種厄運的受害者。這些陌生人非常熱心地回答我的問題,卻絲毫沒有察覺自己如何殘忍地傷透了你的心,摧毀了你的夢想。我不打算將這一切描述給你們聽,但允許我這麼說:當回憶起舊日花園裡青蔥翠綠、陽光普照的溫暖夏日,我同時察覺到一根根小指粗細的冰柱垂懸在菩提枝枒上。如今這個充滿苦痛、積雪而疏於照顧的花園裡,能讓人聯想到的,只有死亡。
從我的恩尼須帖寄到大不里士給我的一封信中,我已經得知一些親戚們的遭遇。信中他邀請我回到伊斯坦堡,解釋說他正在為蘇丹殿下編纂一本祕密書籍,而他需要我的幫助。他聽說我在大不里士時,有段時間曾為鄂圖曼帕夏、地方官員及伊斯坦堡人製作書本。伊斯坦堡的客戶會付錢下訂單委託手稿編寫,我的職責是拿這筆錢到附近城市尋找細密畫家及書法家。當時許多畫師受到戰爭以及鄂圖曼士兵的壓迫,流散各處,但還沒有投靠西北部的卡茲文或其他波斯城市,我委託這些飽嘗貧窮、懷才不遇的專家,請他們書寫、繪畫並裝訂手抄本的書頁,再找人把完成的書送回伊斯坦堡。要不是年少時,我的恩尼須帖灌輸我對繪畫與精緻書本的熱愛,我絕不可能有機會從事這項職業。
街道的盡頭通往市場,在這個我的恩尼須帖曾經居住的馬路邊,我找到那位技藝精湛的理髮師,他待在同樣的小店裡,身旁圍繞著同樣的鏡子、剃刀、水罐和肥皂刷。我們目光相遇,但我不確定他是否認得我。店裡有一只連著鍊子從天花板懸垂而下的洗頭盆,我很高興看見他往裡頭倒熱水的時候,它仍然依循著舊日的拋物線,前後擺盪。
有一些我年少時往來頻繁的區域和街道已經灰飛煙滅,取而代之的是焦黑的殘骸,成為野狗聚集的場所以及瘋癲的流浪漢嚇壞當地孩童的角落。其他被大火夷為平地的區域中,富麗堂皇的房屋拔地而起,奢華的程度令我震驚不已,屋子的窗戶鑲上最昂貴的威尼斯彩繪玻璃,豪華的樓房二樓裝設著凸窗,拱出高牆之外。
和其他城市一樣,金錢在伊斯坦堡不再具有任何價值。從東方回來後,我發現以前一個銀幣可以買到一百特拉姆那麼重的麵包,如今同樣的價錢只能換得縮水成一半的麵包,而且嘗起來味道也不如我孩提時代。要是死去的母親知道如今她得花三塊銀幣買一打雞蛋,一定會說:「不能待了,再沒多久那些雞會驕傲到爬上我們頭頂大便。」但我知道金錢貶值的問題哪裡都一樣。有謠言傳說法蘭德斯和威尼斯的商船載滿一箱箱偽幣運至伊斯坦堡。過去,官方的鑄幣是用一百特拉姆的銀子鑄成五百個硬幣,然而現在,由於與波斯連年征戰,同樣的銀子卻可以鑄成八百個硬幣。當土耳其禁衛步兵發現賺來的硬幣居然可以飄浮在金角灣上,就像菜販碼頭上掉落的乾豆子一樣,群起暴動,把蘇丹殿下的宮殿當作敵人的城堡團團圍繞。
在這段道德淪喪、物價飛漲、偷竊和犯罪盛行的時期,一位在巴耶塞特清真寺傳道,並宣稱是我們榮耀的先知穆罕默德後裔的傳道士努索瑞,自封為王。這位來自艾祖隆小城的傳道士,把這十年間降臨伊斯坦堡的災難——包括巴切卡比和卡珊吉拉地區的大火、奪去上萬人性命的瘟疫、與波斯人長年不斷損失無數人命的戰爭,以及西部地方被基督教叛徒占據的鄂圖曼堡壘——歸咎於人們偏離了先知的道路、輕忽偉大古蘭經的教誨、過於縱容基督徒、公開販賣酒類,以及在苦行僧修院彈奏樂器。
賣醬菜的小販口沫橫飛說完了艾祖隆傳道士的故事,又談到偽幣,新鑄的、上面刻著獅子的假銀幣,以及含銀量逐年降低的鄂圖曼硬幣。這些錢幣充斥市場和商店,就像馬路上摩肩接踵的切爾克斯人、阿布哈茲人、明加利亞人、波士尼亞人、喬治亞人和亞美尼亞人,把我們拖往墮落的深淵,難以翻身。他告訴我,流氓和叛徒都聚集在咖啡館,密謀叛亂直到清晨;猥瑣的窮人、酗鴉片的瘋子,以及非法的卡連德里苦行教派追隨者,這群人宣稱依循阿拉的道路,徹夜在苦行僧修院裡隨著音樂跳舞,用尖針穿刺自己的身體,從事各種邪惡的行為,最後再野蠻地彼此相姦,或對任何他們找得到的男孩下手。
我不知道是因為遠方傳來一陣優美的魯特琴琴聲吸引我跟隨,或者在我混沌的記憶與慾望中,再也無法忍受這個口出穢言的醬菜小販,總之,我以樂聲為藉口,逃離和他的對話。然而,我確實知道一點:當你熱愛一座城市並且時常漫步探索其間時,你的身體,更不要說你的靈魂,會變得對這些街道極為熟悉,以致於多年之後,在一股或許因為憂傷飄落的輕雪所引起的哀愁情緒中,你會發現你的腿自動帶著你來到最喜愛的一個岬角。
我就是如此離開了蹄鐵市場,來到蘇里曼清真寺旁一個地方,望著雪片落入金角灣。清真寺面北的屋頂,以及圓頂上迎著東北風的幾個部分,已經開始積雪。一艘逐漸駛近的船隻,降下了船帆,撲拍的帆布向我招呼。金角灣的水面泛著鉛灰的霧氣,映上船帆的顏色。眼前的柏樹和梧桐樹、屋頂、淒涼的黃昏、下方住宅區傳來的聲響、小販的叫賣、清真寺庭院孩童的玩耍叫喊,這一切揉入我的腦海,決絕地宣布:從今而後,除了這裡,我將無法在其他城市定居。我莫名地感覺到,那張逃離多年的我所摯愛的臉孔,很可能驀然出現在面前。
我開始走下山丘,融入人群。晚禱過後,我在一間食堂填飽肚子。我坐在空無一人的店鋪裡,仔細聆聽老闆的談話,他慈愛地望著我一口一口進食,好像在餵貓一樣。我根據他提供的線索,轉進奴隸市場後面其中一條小巷子,找到一家咖啡館,這時街上已經暗了下來。
咖啡館內擁擠而溫暖。一個說書人,如同我在大不里士和波斯城市看到的「表演明星」,坐在燒木柴火爐旁一座架高的平台上。他展開一張圖畫,掛在觀眾正前方,粗糙的紙上有一條狗,儘管線條潦草,卻頗具架式。說書人扮演起狗的角色說故事,不時伸手指向圖畫。
如今我只是一具屍體,一具躺在井底的屍首。儘管我已經死了很久,心臟早已停止跳動,然而,除了那個卑鄙的殺人凶手之外,沒半個人知道我發生了什麼事。至於那個混蛋,他先摸了摸我的脈搏,傾聽我是否還有呼吸,確定我死了之後,又狠狠朝我的肚子踢了幾腳,然後才把我扛到井邊,抬起我的身體往下丟。當我跌落井底時,先前被他用石頭砸爛的腦袋摔裂開來;我的臉、我的額頭和臉頰,全部擠爛成一團;我全身的骨頭都散了,滿嘴都是鮮血。
我已經失蹤了將近四天,妻子和兒女一定到處找我。我的女兒在哭累了之後,一定正焦躁不安地瞪著庭院大門發呆。沒錯,我知道他們全都站在窗口,引頸期盼我的歸來。
不過,他們是真的在等待嗎?甚至我也不能確定。或許他們對於我的缺席早就習以為常。
真可悲呀!因為在這邊,生死線上的另一邊,讓人覺得好像自己昔日的生命仍然繼續走下去。在我出生前,已經存在著無窮的時間,而在我死後,時間更是沒有止盡。我以前從沒想過這一點:一直以來,我明晰地生活在兩團永恆的黑暗之間。
我很快樂,此時我才明白自己以前過得很快樂。在蘇丹殿下的工匠坊,我畫的書頁插畫最為精緻華麗,沒有人能夠匹敵。我私底下做的工作每個月為我賺進九百塊銀幣,這一切自然而然只讓此時此刻的情況更教人難以接受。
我的工作內容是替書本畫插畫及紋飾。我在書頁的邊緣畫上裝飾圖案,用鮮豔的色彩在它們周圍勾勒極為生動的花紋,像是葉子、枝幹、玫瑰、花朵和小鳥。我畫上中國樣式的扇形雲朵、糾結纏繞的串串藤蔓,以及隱約藏在層層色彩之下的瞪羚、遠洋帆船、蘇丹、樹木、宮殿、馬匹與獵人。當我年輕的時候,還會紋飾盤子、鏡子的背面,以及小櫃子,有時候我會畫一棟豪宅或博斯普魯斯宅邸的天花板,甚至只是一支木湯匙。然而這幾年來,我只專精於裝飾手抄本的頁面,因為蘇丹殿下願意支付高額的酬勞。我不能說這些現在都已經不再重要。就算你死了,你也知道金錢的價值。聽過我奇蹟般的聲音後,你們也許會想:「誰管你活著的時候賺多少錢,告訴我們你看見什麼。死後還有生命嗎?你的靈魂到哪去了?究竟有沒有天堂和地獄?死是什麼感覺?你很痛苦嗎?」問得沒錯,活著的人對於死後的世界總是極度好奇。或許你聽過這個故事,有一個人因為對這些問題太過好奇,以致於跑上戰場在士兵當中亂晃,於一群躺在血泊裡做生死掙扎的傷兵中,找到一個死而復生的人,心想這個人必定能告訴他另一個世界的祕密。然而一位帖木兒汗國的戰士誤以為這位追尋者是敵人,拔出彎刀俐落地把他劈成兩半,使他最後得出一個結論:在死後的世界裡人都會分成兩半。
荒唐!恰巧相反,我甚至要說,活著的時候分開的靈魂在死後融合了。那些沉淪於魔鬼召喚下的罪惡異教徒們,宣稱死後沒有生命,大錯特錯,確實有另一個世界,感謝真主。證據呢,就是我現在正從這個世界對你們說話。我已經死了,不過你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我並沒有消失。很遺憾地,我得承認,我沒有看見偉大古蘭經中描述的情景,像是從天堂的金銀色涼亭旁蜿蜒流過的河流、長著碩大果實的寬葉樹木或是美麗的處女——雖然我記得很清楚,自己以前常常在腦中熱切地想像古蘭經〈大事〉這一章描寫的大眼美女是什麼模樣。除此之外,儘管古蘭經沒有提到,但在一些想像力豐富的夢想家如伊本‧阿拉比生花妙筆的描繪中,天堂有許多河流,流滿了牛奶、醇酒、清水與蜂蜜,事實上,這裡我沒看到半條河的蹤跡。不過對於那些藉由幻想期盼來世過活的正直人士,我絲毫無意挑戰他們的信仰,因此,容我說明,我所見到的一切全來自於個人的特別處境。任何相信或稍微了解死後世界的人都會明白,處於我目前的狀況,全身被憤怒擠壓,實在也不太可能見到天堂之河。
簡言之,我,人們稱為高雅‧埃芬迪大師的這位,死了。然而我還沒有被埋葬,也因此我的靈魂尚未完全脫離軀體。儘管我的處境想當然不是史上第一宗,但滯留於此種特殊狀態,卻使我身體不滅的那部分感受到難以言喻的痛苦。雖然感覺不到自己碎裂的頭骨、傷痕累累逐漸腐敗的軀體、一身斷骨,以及一半泡在冰水裡的身體,但我確實感覺到我的靈魂正深受折磨,絕望地掙扎想逃脫塵世的枷鎖。那就像整個世界,包括我的軀體,正收縮成為緊緊一團痛苦。
唯一能與這種痛苦收縮相提並論的,是在死亡的那個駭人剎那,我感覺到一種出人意料的輕鬆感。是的,當那個混蛋猛然拿石頭砸我的頭、打破我的腦袋時,我立刻明白他想殺死我,但我並不相信他會成功。突然間,我發現自己原來是個樂觀的人,以前在工匠坊和家庭的陰影下生活時,從不曾察覺這一點。我狂熱地緊抓住生命,我的指甲、手指及牙齒陷入他的皮膚裡。關於接下來他怎麼毒打我的慘痛細節,這裡就不再多加贅述。
在這場痛楚中我知道自己難逃一死,頓時一股不可思議的輕鬆感湧上心頭。離開人世的剎那,我感受到這股輕鬆;通往死亡的過程非常平順,彷彿在夢中看著自己沉睡。我最後一件注意到的東西,是凶手那雙沾滿泥雪的鞋子。我閉上眼睛,彷彿逐漸沉入睡眠,接著慢慢地失去知覺。
此時我的焦慮不在於我的牙齒像堅果般掉進滿是鮮血的嘴裡,也不在於我的臉摔爛以至於無法辨認,更不是因為我被棄屍在一口深不見底的井裡——而是每個人都以為我還活著。我騷動的靈魂之所以痛苦不堪,是因為我的家人以及,是的,關心我的親友,可能猜想我正在伊斯坦堡某個地方處理瑣事,或甚至正在調戲另一個女人。夠了!趕快找到我的屍體,祭拜我,並把我好好埋葬。最重要的,找出殺我的凶手!因為就算你們把我葬在最富麗堂皇的陵墓,只要那個混蛋仍舊自由逍遙,我就會在墳墓裡輾轉難安,日日等待,並且夜夜騷擾你們。快找到那個婊子養的凶手,我就告訴你們死後世界的所有細節。不過記住,抓到他之後,一定要凌遲他一番,把他的骨頭一段一段拆成八塊,最好是他的肋骨;在用專為酷刑特製的尖針戳進他的頭皮前,先拿支鉗子把他噁心的油膩頭髮拔光,一根一根拔,讓他一次又一次地尖叫。
這個讓我忿恨難當的凶手究竟是誰?他為什麼用如此出其不意的手段殺我?請注意並探究這些細節。你們說世界上充滿了卑微低賤的罪犯,不是這個人幹的,就是那個人做的?如果你這麼想的話,讓我提醒你們:我死亡的背後隱藏著一個駭人的陰謀,極可能瓦解我們的宗教、傳統,以及世界觀。張大你們的眼睛,探究你們信仰並生活其中的伊斯蘭世界,存在著何種敵人,他們為什麼要除掉我?甚至試著去體認為什麼有一天他們也可能同樣對你下毒手。偉大的傳道士,艾祖隆的努索瑞教長,我曾流淚傾聽他的布道,他所預測的所有事情,將一件接著一件全部成真。讓我再這麼說,如果把我們如今陷入的處境寫進書裡,就連最精湛的細密畫家也永遠無法配以圖畫呈現。至於古蘭經——若我誤解的話,求真主責罰——這本書之所以擁有如此強大的力量,正是由於它絕不可能被描繪。我懷疑你們是否徹底明瞭這個事實。
聽我的話。我當學徒的時候,也因為害怕而忽視了隱藏的真相及上天的話語。過去我總以開玩笑的口氣談論。結果,我落得這種下場,躺在一口可悲的井底!留心了,它也可能發生在你身上。現在,我什麼都不能做了,只希望我能徹底腐爛,用我的屍臭引他們來找到我。我什麼都不能做了,只剩下一點希望,想像那個齷齪的殺人凶手被抓到後,某個善心人士會用什麼恐怖的手段凌虐他。
2 我的名字叫布拉克
離開伊斯坦堡十二年後,我像個夢遊者再度歸來。「土地召喚他回來。」他們這麼形容快死的人,就我的情況而言,是死亡引領我返回自己從小生長的城市。初抵舊地時,我以為這裡只有死亡;雖然之後,我也將遇見愛情。只不過,如同我對這個城市的記憶一樣,愛情是一段遙遠而早已忘卻的過去。十二年前,就是在伊斯坦堡,我無可救藥地愛上我的表妹。
離開伊斯坦堡的最初四年,我行遍廣袤無垠的大草原、積雪覆蓋的山脈、哀傷憂愁的波斯城市,遞送信件並收集稅款,那時,我向自己坦承,我已慢慢淡忘了遺留在身後的童年摯愛面容。在逐漸累積的驚恐中,我絕望地試圖記起她,但終究發現除了愛情之外,那張久未見面的臉孔已經褪去。待在東方的第六年,我擔任帕夏的祕書,工作或旅行,這時我明白幻想中的臉孔不再是我愛人的。之後,到了第八年,我忘記了自己在第六年時心中誤認的那張臉,於是再度編織出一張截然不同的臉孔。就這樣,到了第十二年,我以三十六歲的年紀回到這座城市時,痛苦地察覺愛人的容顏早已離我而去。
浪跡天涯十二年這段期間,我的許多朋友及親戚相繼死去。我前往俯瞰金角灣的墓園探視,為在我離開時過世的母親及叔伯們禱告。泥土的氣味混入我的回憶。母親的墳墓旁,有人打破了一只陶水罐,不知道為什麼,我凝視著地上的碎片,哭了起來。我是為死去的人流淚嗎?還是因為,很奇怪的,經過這麼多年,我仍然只是在生命的開端?或者因為,我已經來到了人生旅途的終點?雪輕柔地落下。我失神望著雪花四處飄散,腦中昏亂地想像生命的種種,以致沒有注意到墓園的陰暗角落,一隻黑狗正盯著我瞧。
淚水止息後,我擦淨鼻子。離開墓園時,我看見那隻黑狗友善地搖尾巴。稍晚,我在城中找到一個地方安頓下來,租下一間父親的親戚以前住過的房子。女房東看到我,似乎想起她在戰場上被薩非波斯王朝士兵殺死的兒子,因此同意幫我打掃房間並為我煮飯。
我出發展開漫長而滿足的散步,穿梭於街道間,彷彿現在停留的城市不是伊斯坦堡,而是暫時來到位於世界另一端的某座阿拉伯城市。馬路變得比以前窄,至少在我看來是如此。在某些區域,道路擠在緊緊相鄰的房屋之間,我得全身貼上牆壁和大門,才不會被滿載物品的馬匹撞上。城裡多了許多有錢人,至少在我看來是如此。我看見一輛裝飾華麗的馬車,如同一座堡壘,由高傲的馬匹拖著,類似的車在阿拉伯或波斯是看不到的。在「焚毀的石柱」附近,我看到幾個一身襤褸的討厭乞丐擠成一堆,四周飄散著從雞販市場傳出的內臟殘渣氣味。其中一個瞎子空瞪著落下的雪花微笑。
如果有人告訴我,伊斯坦堡以前是個較為貧窮、狹小、快樂的城市,我大概不會相信,但我的內心正是這麼對我說。儘管我摯愛的屋子仍在原處,隱藏在菩提樹和栗樹之間,但待我敲門詢問後,才知道屋子的主人已經換人了。我得知愛人的母親,我的阿姨,已經去世,而她的丈夫,我的恩尼須帖,以及他的女兒皆已搬走。從應門的陌生人口中,我得知父親及女兒淪為某種厄運的受害者。這些陌生人非常熱心地回答我的問題,卻絲毫沒有察覺自己如何殘忍地傷透了你的心,摧毀了你的夢想。我不打算將這一切描述給你們聽,但允許我這麼說:當回憶起舊日花園裡青蔥翠綠、陽光普照的溫暖夏日,我同時察覺到一根根小指粗細的冰柱垂懸在菩提枝枒上。如今這個充滿苦痛、積雪而疏於照顧的花園裡,能讓人聯想到的,只有死亡。
從我的恩尼須帖寄到大不里士給我的一封信中,我已經得知一些親戚們的遭遇。信中他邀請我回到伊斯坦堡,解釋說他正在為蘇丹殿下編纂一本祕密書籍,而他需要我的幫助。他聽說我在大不里士時,有段時間曾為鄂圖曼帕夏、地方官員及伊斯坦堡人製作書本。伊斯坦堡的客戶會付錢下訂單委託手稿編寫,我的職責是拿這筆錢到附近城市尋找細密畫家及書法家。當時許多畫師受到戰爭以及鄂圖曼士兵的壓迫,流散各處,但還沒有投靠西北部的卡茲文或其他波斯城市,我委託這些飽嘗貧窮、懷才不遇的專家,請他們書寫、繪畫並裝訂手抄本的書頁,再找人把完成的書送回伊斯坦堡。要不是年少時,我的恩尼須帖灌輸我對繪畫與精緻書本的熱愛,我絕不可能有機會從事這項職業。
街道的盡頭通往市場,在這個我的恩尼須帖曾經居住的馬路邊,我找到那位技藝精湛的理髮師,他待在同樣的小店裡,身旁圍繞著同樣的鏡子、剃刀、水罐和肥皂刷。我們目光相遇,但我不確定他是否認得我。店裡有一只連著鍊子從天花板懸垂而下的洗頭盆,我很高興看見他往裡頭倒熱水的時候,它仍然依循著舊日的拋物線,前後擺盪。
有一些我年少時往來頻繁的區域和街道已經灰飛煙滅,取而代之的是焦黑的殘骸,成為野狗聚集的場所以及瘋癲的流浪漢嚇壞當地孩童的角落。其他被大火夷為平地的區域中,富麗堂皇的房屋拔地而起,奢華的程度令我震驚不已,屋子的窗戶鑲上最昂貴的威尼斯彩繪玻璃,豪華的樓房二樓裝設著凸窗,拱出高牆之外。
和其他城市一樣,金錢在伊斯坦堡不再具有任何價值。從東方回來後,我發現以前一個銀幣可以買到一百特拉姆那麼重的麵包,如今同樣的價錢只能換得縮水成一半的麵包,而且嘗起來味道也不如我孩提時代。要是死去的母親知道如今她得花三塊銀幣買一打雞蛋,一定會說:「不能待了,再沒多久那些雞會驕傲到爬上我們頭頂大便。」但我知道金錢貶值的問題哪裡都一樣。有謠言傳說法蘭德斯和威尼斯的商船載滿一箱箱偽幣運至伊斯坦堡。過去,官方的鑄幣是用一百特拉姆的銀子鑄成五百個硬幣,然而現在,由於與波斯連年征戰,同樣的銀子卻可以鑄成八百個硬幣。當土耳其禁衛步兵發現賺來的硬幣居然可以飄浮在金角灣上,就像菜販碼頭上掉落的乾豆子一樣,群起暴動,把蘇丹殿下的宮殿當作敵人的城堡團團圍繞。
在這段道德淪喪、物價飛漲、偷竊和犯罪盛行的時期,一位在巴耶塞特清真寺傳道,並宣稱是我們榮耀的先知穆罕默德後裔的傳道士努索瑞,自封為王。這位來自艾祖隆小城的傳道士,把這十年間降臨伊斯坦堡的災難——包括巴切卡比和卡珊吉拉地區的大火、奪去上萬人性命的瘟疫、與波斯人長年不斷損失無數人命的戰爭,以及西部地方被基督教叛徒占據的鄂圖曼堡壘——歸咎於人們偏離了先知的道路、輕忽偉大古蘭經的教誨、過於縱容基督徒、公開販賣酒類,以及在苦行僧修院彈奏樂器。
賣醬菜的小販口沫橫飛說完了艾祖隆傳道士的故事,又談到偽幣,新鑄的、上面刻著獅子的假銀幣,以及含銀量逐年降低的鄂圖曼硬幣。這些錢幣充斥市場和商店,就像馬路上摩肩接踵的切爾克斯人、阿布哈茲人、明加利亞人、波士尼亞人、喬治亞人和亞美尼亞人,把我們拖往墮落的深淵,難以翻身。他告訴我,流氓和叛徒都聚集在咖啡館,密謀叛亂直到清晨;猥瑣的窮人、酗鴉片的瘋子,以及非法的卡連德里苦行教派追隨者,這群人宣稱依循阿拉的道路,徹夜在苦行僧修院裡隨著音樂跳舞,用尖針穿刺自己的身體,從事各種邪惡的行為,最後再野蠻地彼此相姦,或對任何他們找得到的男孩下手。
我不知道是因為遠方傳來一陣優美的魯特琴琴聲吸引我跟隨,或者在我混沌的記憶與慾望中,再也無法忍受這個口出穢言的醬菜小販,總之,我以樂聲為藉口,逃離和他的對話。然而,我確實知道一點:當你熱愛一座城市並且時常漫步探索其間時,你的身體,更不要說你的靈魂,會變得對這些街道極為熟悉,以致於多年之後,在一股或許因為憂傷飄落的輕雪所引起的哀愁情緒中,你會發現你的腿自動帶著你來到最喜愛的一個岬角。
我就是如此離開了蹄鐵市場,來到蘇里曼清真寺旁一個地方,望著雪片落入金角灣。清真寺面北的屋頂,以及圓頂上迎著東北風的幾個部分,已經開始積雪。一艘逐漸駛近的船隻,降下了船帆,撲拍的帆布向我招呼。金角灣的水面泛著鉛灰的霧氣,映上船帆的顏色。眼前的柏樹和梧桐樹、屋頂、淒涼的黃昏、下方住宅區傳來的聲響、小販的叫賣、清真寺庭院孩童的玩耍叫喊,這一切揉入我的腦海,決絕地宣布:從今而後,除了這裡,我將無法在其他城市定居。我莫名地感覺到,那張逃離多年的我所摯愛的臉孔,很可能驀然出現在面前。
我開始走下山丘,融入人群。晚禱過後,我在一間食堂填飽肚子。我坐在空無一人的店鋪裡,仔細聆聽老闆的談話,他慈愛地望著我一口一口進食,好像在餵貓一樣。我根據他提供的線索,轉進奴隸市場後面其中一條小巷子,找到一家咖啡館,這時街上已經暗了下來。
咖啡館內擁擠而溫暖。一個說書人,如同我在大不里士和波斯城市看到的「表演明星」,坐在燒木柴火爐旁一座架高的平台上。他展開一張圖畫,掛在觀眾正前方,粗糙的紙上有一條狗,儘管線條潦草,卻頗具架式。說書人扮演起狗的角色說故事,不時伸手指向圖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