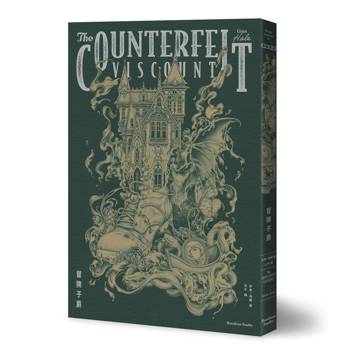第一章 冒牌子爵
貴為佛蒙子爵,亞奇柏德・雷克格斯・格蘭維,日子多半都在優雅奢侈的排場中流逝:新摘的鮮花、擦得發亮的皮靴,還有以鍍金盤盛上的晚宴。入夜後,他流連於迷人的情人之間,兜轉於牌局之中,輸贏或許有來有往,但他總是略勝一籌。
用寧布爾的話來說,這就叫「奶油配培根」—過太爽。
亞奇柏德擁有一馬廄剽悍的賽馬,名下莊園都養著大批傭人,儘管他鮮少離開典雅的連幢邸墅去造訪任何一處。偶爾,當有外國女性繼承人投入貴族圈這灘死水時,他會假裝向她們求愛,時不時也會為了寵溺俊美的藝術家或貌美的女演員而大手筆埋單。
除了胸口雪白襯衫下那一大片炮彈碎片留下的紅疤,他身上幾乎沒有半點吃過苦的痕跡。白皙的肌膚晒出一層健康的古銅色,再配上纖細的身材,即使他今年二十五歲了,依然像個天真無邪的少年。
他本可過著無憂無慮的完美生活,卻得在每三個月的那一天下到惡獄底,向他的魔鬼支付代價。
三月二十一日,他在破曉前起床,避開細心的傭人和昨夜留宿的客人,悄悄溜了出去。走在魚肚白的光線之中,路上與他同行的只有賣草藥的女孩,還有最後一班夜間巡警。城市西側,有推車小販高聲叫賣著自家咖啡有多醇香,亞奇柏德彷彿能聞到那苦澀黑液體的香氣,隨著清晨河面升起的霧氣籠罩大街小巷。
等他抵達布萊爾旅社,進入他訂的那間寒冷但乾淨的房間時,陽光已經燒穿了濃霧。他在房間換下時髦的貂皮大衣,脫下光滑亮麗的高禮帽,取出銀製懷錶,改換上一件防水油布斗篷,再壓上一頂破舊的有簷軟帽;那頂軟帽是路上許多流浪的退役軍人會戴的尋常款式,而他也曾是其中一員。他抄起粗重的鐵木手杖,將腳上的小牛皮皮鞋換成破爛的軍靴。這雙鞋當初配發給他時,對十五歲的他來說實在大得離譜。
衣櫃門上的黃銅鏡將他的身影染上一層金色調,卻已不見半點佛蒙子爵的風采。此刻的他只是平凡無奇的老亞奇,沒人會把他放在眼裡,更不在意他去哪裡,或跟誰在一起。
他從後門離開布萊爾旅社,穿過繁忙的街道,將大理石外牆和大片綠地公園構成的世界拋在身後,繼續走過幾排樸素的磚房店鋪,踏上皇冠塔橋。抵達城市中較亂的那一區後,他在窄巷左彎右拐,穿過擁擠的住宅、嘈雜的工廠和喧鬧的琴酒酒吧,酒吧裡頭早已人影竄動,坐滿買醉忘憂的人。這裡有些人認識他,只不過他們認識的,是那個賣蘋果和貓食的攤販亞奇。他們友善地寒暄幾句,交換一些街頭話題,然後分道揚鑣。
終於,他抵達那座巍峨的花崗岩拱門下,基座連著一道磨損得厲害的石階,往下直通希望之城—更為人熟知的名稱是惡獄底。亞奇緩步走進潮溼的陰影中,欣賞兩側牆面上沾了煤灰的馬賽克鑲嵌畫。儘管覆蓋了一層陳年汙垢,加上黯淡的光線,他仍可辨識出明亮的彩色碎片與唯美脫俗的人物圖像。據說,這些鑲嵌畫所記錄的是數百年前,駭人又美麗的惡獄軍團上到地面接受教會拯救、迎接救贖的榮耀時刻。畫面上還可見閃閃發亮的巨蛇、生了翅膀的猛獅,與墮落天使、魁梧戰士的金色雕像交相輝映。
薩塔內爾、利維坦、沙利葉、臨門。亞奇用指尖輕輕滑過鑲嵌著金屬與玻璃的牆磚表面,景仰那些一度主宰雷霆、怒濤與亡靈的偉大神祇。
然而,如今這片藏在地底下、與上頭的皇冠十字城同樣廣大無垠的貧民窟中,早已不見這般威儀天下的人物。他們的後代被稱為魔裔,多半在陰暗的角落從事艱苦又危險的工作,據說他們的體質天生抗毒、耐煙,同時不易疲倦。多數魔裔遠看與一般人無異,不過只要湊近一點,就能從他們的黃眼睛、黑指甲、尖牙,以及散發柑橘味的汗水嗅出端倪。然而,撇開這些表面特徵,多數魔裔與他們祖先的相似程度,就像亞奇和波坦勛爵飼養的寵物彌猴一樣,可說是相去甚遠。不過,凡事總有例外。
在牆面前略作逗留、研究上頭的馬賽克裝飾,如今已成了他的習慣。他的目光總是不由自主停在其中一個眼熟的惡魔身上。那位惡魔上身寬壯,古銅膚色,留著一頭黑髮,眼珠像檸檬糖一樣黃。即便夾雜在一群地獄公爵和墮落王子之中,那惡魔似乎仍饒富興味地盯著亞奇,甚至不可理喻地投以自信又得意的譏笑。那是一張知道自己具備稀世力量的惡魔之臉。
亞奇幾乎可以發誓,那是屬於他的寧布爾・霍布斯,彷彿正準備開口說:「你發過誓,每三個月要做我的人一天,身體和靈魂都屬於我。好啦,快把你那嬌貴的屁股拖下這骯髒的樓梯,把欠我的還來,亞奇。」
其實,還有遠比向寧布爾獻身更糟的償還方式。
亞奇拾級而下,兩步併作一步,很快便抵達蜿蜒在城市下方、廣闊的地下墓穴。隨著越來越多的下水道和煤氣管線從上方城市入侵地底,這裡似乎逐年越挖越深。教堂和商店看上去只是突出的石牆,斜睨著路過的人,而所謂的街道,不過是泥濘道路灑上一些碎石。偶爾出現的煤氣街燈忽明忽暗,透出黃色的光暈,油膩的冷凝水珠從高高的石洞頂部滴下。空氣中瀰漫葡萄柚、尿液和鞋子燒焦的味道。
趁呼吸道還沒開始出現灼燒感前,亞奇拉高方巾遮住口鼻,並戴上護目鏡,多少保護一下眼睛。他踱步走過木棧道,沿途向剛上完大夜班準備回家的礦工、染匠、製革工及帽匠點頭問候。
棧道轉角,一位白髮蒼蒼、失去雙腳的魔裔老兵朝他招手,亞奇停下腳步,聽對方話起當年勇:老兵和亞奇一樣,都參與過捍衛索倫山的那場戰役。不同的是,老兵不像他那麼走運,在那炮火隆隆、騎兵大軍壓境的最後一晚,有寧布爾守在他血跡斑斑的肉身旁,保護他活下去。
「我們還是守住了那座該死的山,對吧?」老兵的黃色眼珠看起來像褪色的舊報紙。他的視線穿過亞奇,凝視記憶的遠方。
亞奇點點頭,一滴冷凝水從洞頂滴到他的頸背,讓他打了個寒顫。「沒錯,是你們魔裔軍團為我們守下那座山,也打贏了那場仗。」他說道,事實也正是如此。諾恩人手上擁有更堅硬的鋼材、更致命的炸彈,還有聲勢浩大的騎兵隊,可是他們沒有魔裔。面對魔裔殘暴的獸性以及非人的體能極限,即便魔裔只有區區幾個部隊的兵力,他們還是被殺個措手不及。
「要是沒有你們,我們現在全都得說諾恩語,用紙片交易,餐餐只有魚乾可吃。」亞奇補充。
老兵蠟黃的臉微微泛紅。他打量亞奇。「你一定是那群被徵召去操作大炮和扛銀十字架的其中一名孩子吧?我知道乾淨的水和彈藥都是由你們這幫孩子運來的,真是多虧了你們。」
「第三兒童旅。」亞奇勉強擠出微笑,儘管往事讓他的肌膚冷得像是捏陶用的泥團。他不像多數被抽籤徵召的魔裔兒童,是從哭泣的父母身邊強行帶走的;不,是他的叔父親手把他給交了出去,連同他的弟弟一起,宛如兩枚被驕傲地丟入奉獻箱的硬幣。
「步槍手,第五師。」老兵搔了搔左腳的殘肢,扭頭瞪向一隻肥滿的黑老鼠,然後撿起一顆石子,用足以擊昏牠的力道朝老鼠扔去。
趁老兵分心,亞奇悄悄塞了一大筆錢到他乞討用的水壺裡—至少夠他活過今年。隨後,他祝老兵有個愉快的一天,便起身告辭。他繼續沿著木棧道走,越過「神賜藥酒廠」的石板屋頂,踏進瑪麗・茉莉太太寄宿所的大門。
室內溫暖明亮,只見寧布爾站在裡頭,掐著一個身穿牧師袍的矮胖男子。
貴為佛蒙子爵,亞奇柏德・雷克格斯・格蘭維,日子多半都在優雅奢侈的排場中流逝:新摘的鮮花、擦得發亮的皮靴,還有以鍍金盤盛上的晚宴。入夜後,他流連於迷人的情人之間,兜轉於牌局之中,輸贏或許有來有往,但他總是略勝一籌。
用寧布爾的話來說,這就叫「奶油配培根」—過太爽。
亞奇柏德擁有一馬廄剽悍的賽馬,名下莊園都養著大批傭人,儘管他鮮少離開典雅的連幢邸墅去造訪任何一處。偶爾,當有外國女性繼承人投入貴族圈這灘死水時,他會假裝向她們求愛,時不時也會為了寵溺俊美的藝術家或貌美的女演員而大手筆埋單。
除了胸口雪白襯衫下那一大片炮彈碎片留下的紅疤,他身上幾乎沒有半點吃過苦的痕跡。白皙的肌膚晒出一層健康的古銅色,再配上纖細的身材,即使他今年二十五歲了,依然像個天真無邪的少年。
他本可過著無憂無慮的完美生活,卻得在每三個月的那一天下到惡獄底,向他的魔鬼支付代價。
三月二十一日,他在破曉前起床,避開細心的傭人和昨夜留宿的客人,悄悄溜了出去。走在魚肚白的光線之中,路上與他同行的只有賣草藥的女孩,還有最後一班夜間巡警。城市西側,有推車小販高聲叫賣著自家咖啡有多醇香,亞奇柏德彷彿能聞到那苦澀黑液體的香氣,隨著清晨河面升起的霧氣籠罩大街小巷。
等他抵達布萊爾旅社,進入他訂的那間寒冷但乾淨的房間時,陽光已經燒穿了濃霧。他在房間換下時髦的貂皮大衣,脫下光滑亮麗的高禮帽,取出銀製懷錶,改換上一件防水油布斗篷,再壓上一頂破舊的有簷軟帽;那頂軟帽是路上許多流浪的退役軍人會戴的尋常款式,而他也曾是其中一員。他抄起粗重的鐵木手杖,將腳上的小牛皮皮鞋換成破爛的軍靴。這雙鞋當初配發給他時,對十五歲的他來說實在大得離譜。
衣櫃門上的黃銅鏡將他的身影染上一層金色調,卻已不見半點佛蒙子爵的風采。此刻的他只是平凡無奇的老亞奇,沒人會把他放在眼裡,更不在意他去哪裡,或跟誰在一起。
他從後門離開布萊爾旅社,穿過繁忙的街道,將大理石外牆和大片綠地公園構成的世界拋在身後,繼續走過幾排樸素的磚房店鋪,踏上皇冠塔橋。抵達城市中較亂的那一區後,他在窄巷左彎右拐,穿過擁擠的住宅、嘈雜的工廠和喧鬧的琴酒酒吧,酒吧裡頭早已人影竄動,坐滿買醉忘憂的人。這裡有些人認識他,只不過他們認識的,是那個賣蘋果和貓食的攤販亞奇。他們友善地寒暄幾句,交換一些街頭話題,然後分道揚鑣。
終於,他抵達那座巍峨的花崗岩拱門下,基座連著一道磨損得厲害的石階,往下直通希望之城—更為人熟知的名稱是惡獄底。亞奇緩步走進潮溼的陰影中,欣賞兩側牆面上沾了煤灰的馬賽克鑲嵌畫。儘管覆蓋了一層陳年汙垢,加上黯淡的光線,他仍可辨識出明亮的彩色碎片與唯美脫俗的人物圖像。據說,這些鑲嵌畫所記錄的是數百年前,駭人又美麗的惡獄軍團上到地面接受教會拯救、迎接救贖的榮耀時刻。畫面上還可見閃閃發亮的巨蛇、生了翅膀的猛獅,與墮落天使、魁梧戰士的金色雕像交相輝映。
薩塔內爾、利維坦、沙利葉、臨門。亞奇用指尖輕輕滑過鑲嵌著金屬與玻璃的牆磚表面,景仰那些一度主宰雷霆、怒濤與亡靈的偉大神祇。
然而,如今這片藏在地底下、與上頭的皇冠十字城同樣廣大無垠的貧民窟中,早已不見這般威儀天下的人物。他們的後代被稱為魔裔,多半在陰暗的角落從事艱苦又危險的工作,據說他們的體質天生抗毒、耐煙,同時不易疲倦。多數魔裔遠看與一般人無異,不過只要湊近一點,就能從他們的黃眼睛、黑指甲、尖牙,以及散發柑橘味的汗水嗅出端倪。然而,撇開這些表面特徵,多數魔裔與他們祖先的相似程度,就像亞奇和波坦勛爵飼養的寵物彌猴一樣,可說是相去甚遠。不過,凡事總有例外。
在牆面前略作逗留、研究上頭的馬賽克裝飾,如今已成了他的習慣。他的目光總是不由自主停在其中一個眼熟的惡魔身上。那位惡魔上身寬壯,古銅膚色,留著一頭黑髮,眼珠像檸檬糖一樣黃。即便夾雜在一群地獄公爵和墮落王子之中,那惡魔似乎仍饒富興味地盯著亞奇,甚至不可理喻地投以自信又得意的譏笑。那是一張知道自己具備稀世力量的惡魔之臉。
亞奇幾乎可以發誓,那是屬於他的寧布爾・霍布斯,彷彿正準備開口說:「你發過誓,每三個月要做我的人一天,身體和靈魂都屬於我。好啦,快把你那嬌貴的屁股拖下這骯髒的樓梯,把欠我的還來,亞奇。」
其實,還有遠比向寧布爾獻身更糟的償還方式。
亞奇拾級而下,兩步併作一步,很快便抵達蜿蜒在城市下方、廣闊的地下墓穴。隨著越來越多的下水道和煤氣管線從上方城市入侵地底,這裡似乎逐年越挖越深。教堂和商店看上去只是突出的石牆,斜睨著路過的人,而所謂的街道,不過是泥濘道路灑上一些碎石。偶爾出現的煤氣街燈忽明忽暗,透出黃色的光暈,油膩的冷凝水珠從高高的石洞頂部滴下。空氣中瀰漫葡萄柚、尿液和鞋子燒焦的味道。
趁呼吸道還沒開始出現灼燒感前,亞奇拉高方巾遮住口鼻,並戴上護目鏡,多少保護一下眼睛。他踱步走過木棧道,沿途向剛上完大夜班準備回家的礦工、染匠、製革工及帽匠點頭問候。
棧道轉角,一位白髮蒼蒼、失去雙腳的魔裔老兵朝他招手,亞奇停下腳步,聽對方話起當年勇:老兵和亞奇一樣,都參與過捍衛索倫山的那場戰役。不同的是,老兵不像他那麼走運,在那炮火隆隆、騎兵大軍壓境的最後一晚,有寧布爾守在他血跡斑斑的肉身旁,保護他活下去。
「我們還是守住了那座該死的山,對吧?」老兵的黃色眼珠看起來像褪色的舊報紙。他的視線穿過亞奇,凝視記憶的遠方。
亞奇點點頭,一滴冷凝水從洞頂滴到他的頸背,讓他打了個寒顫。「沒錯,是你們魔裔軍團為我們守下那座山,也打贏了那場仗。」他說道,事實也正是如此。諾恩人手上擁有更堅硬的鋼材、更致命的炸彈,還有聲勢浩大的騎兵隊,可是他們沒有魔裔。面對魔裔殘暴的獸性以及非人的體能極限,即便魔裔只有區區幾個部隊的兵力,他們還是被殺個措手不及。
「要是沒有你們,我們現在全都得說諾恩語,用紙片交易,餐餐只有魚乾可吃。」亞奇補充。
老兵蠟黃的臉微微泛紅。他打量亞奇。「你一定是那群被徵召去操作大炮和扛銀十字架的其中一名孩子吧?我知道乾淨的水和彈藥都是由你們這幫孩子運來的,真是多虧了你們。」
「第三兒童旅。」亞奇勉強擠出微笑,儘管往事讓他的肌膚冷得像是捏陶用的泥團。他不像多數被抽籤徵召的魔裔兒童,是從哭泣的父母身邊強行帶走的;不,是他的叔父親手把他給交了出去,連同他的弟弟一起,宛如兩枚被驕傲地丟入奉獻箱的硬幣。
「步槍手,第五師。」老兵搔了搔左腳的殘肢,扭頭瞪向一隻肥滿的黑老鼠,然後撿起一顆石子,用足以擊昏牠的力道朝老鼠扔去。
趁老兵分心,亞奇悄悄塞了一大筆錢到他乞討用的水壺裡—至少夠他活過今年。隨後,他祝老兵有個愉快的一天,便起身告辭。他繼續沿著木棧道走,越過「神賜藥酒廠」的石板屋頂,踏進瑪麗・茉莉太太寄宿所的大門。
室內溫暖明亮,只見寧布爾站在裡頭,掐著一個身穿牧師袍的矮胖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