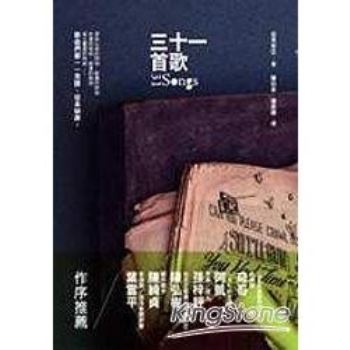01引言:「青少年俱樂部樂團」〈妳的愛是我所來之處〉,「Teenage Fanclub」〈Your Love Is the Place Where I Come From〉
我們正身處於《暈菜的天使》(Speaking With The Angel)的發行午餐會上,我將一些短篇故事集結,以此書來替小犬的學校募款。我和夥伴們、出版商以及校方,都十分緊張於以這種辦法對應來賓們是否合宜--我們不知道結合閱讀與現場音樂表演能否達到預期的效果,與會者能否感到盡興?我很早就到達會場(Hammersmith Palais),當我四處走動時,有兩件事情同時引起我的注意力,其一是表演場地看起來非常棒;前一晚,某個大公司還在這裡舉辦辦公室派對,滿地都是閃亮的裝飾碎物和金銀鋁箔之類的東西。現在,雖然它看起來稍嫌寒酸,但效果性十足,宛如魔術般地象徵性質。另一件事則是「青少年俱樂部樂團」(Teenage Fanclub),允諾在此表演一場不插電(acoustic set)的演出(也正好他們正進行歐陸巡迴演出,所以有這樣的可能與機會)。
現場正在進行器樂測試(sound check),彼時樂團演奏著《妳的愛是我所來之處》(Your Love Is The Place Where I Come From),那是我最最鍾愛的專輯之一,也是《大不列顛北方之歌》(Songs From Northern Britain)中最迷人的歌曲之一。我在一旁聽著,完美音樂型態的表述,對應於那些華而不實的金料碎飾,感覺相當地美好。那一刻,與發行會失敗與否已無關,我知道那會是很特殊的聆賞經驗。而它的確是如此--它成為了我記憶裡最難忘懷,且參與其中的表演。
如今,當我聽到〈妳的愛是我所來之處〉時,總是憶及那個晚上--當然,難不成會有其他可能?簡而言之,當我決定將我所喜愛的歌曲寫成一篇篇散文並集合成冊(這其中有著某種困難的自律,因為曾有太多的選擇而走錯了路,並不是所想得那樣地完美),我便認定這些散文應該是要與人、事、地、物有直接的緊密關聯,如同「青少年俱樂部樂團」這樣的例子。但它們並非如此,也沒有真的如此。事實上,〈妳的愛是我所來之處〉可能是唯一的一篇。我開始想,怎麼會如此呢?何以只有這麼少的歌曲能夠匯聚我的感動,並將之寫成文章?答案很清晰的浮現:當你愛上一首歌,愛到足以在人生的任何階段裡都陪伴著你,那麼任何特殊、單一關於歌曲的記憶很快地變得不是重點。
如果我是在一九七五年某個女孩的房間裡聽見〈崎嶇路〉(Thunder Road),會覺得還挺好聽的,然後可能再也沒有見過這個女孩或者去找這首歌來聽;那麼當然很可能,當我再一次聽見它時,憶及的大概就是那女孩腋下體香劑的味道。不過,實際上事情不是這樣的;事實上是我聽了〈崎嶇路〉並愛上了它,而且我聽這首歌的頻率(驚人的),多到最後我只記得關於這首歌曲本身--那時我十八歲,關於那時,實在沒什麼好說的。多說了也是白說。
我記得以前在英國國家廣播電臺(BBC)有一首很恐怖的歌叫做〈媽媽我想喝杯水〉(印象中是這樣),這首歌總在星期六早上的兒童電臺節目中撥放。我想我沒有再聽過那首歌,不過如果是這樣,大概會產生那種,當我還是個小孩時,每個週六早上超出承受地聽著那歌曲的記憶。有一首「吉普賽國王樂團」(Gypsy Kings)唱的歌曲,提醒了我曾經在里斯本(Lisbon)的某場足球賽事裡,被一個天外飛來的塑膠啤酒瓶K到的事情。有些歌曲會讓我想起關於大學時代、前女友們,或夏日的打工時光,但種種這些對我來說,跟音樂一點關聯意義也沒有,他們只是記憶的一部分,我並不想寫關乎記憶的故事。那並非重點。那只能帶出類似某人說,他們一生中最愛的唱片,令他們想起了柯西加島的蜜月旅行,或家中的吉娃娃狗,其實也沒有多麼地喜愛音樂本身。我想書寫的是這些歌曲如何令我愛上它們,而不是我的人生賦予了歌曲什麼。
我幾乎沒有拒絕聆聽的音樂類型,但並不常聽古典樂與爵士樂。當人們問及我喜愛什麼歌曲,其實有些令我困擾於該如何回答,因為他們多半要的是歌手的名字,而我多半只能給他們曲名。多數時候我所能說的,就只有我深愛的這些歌曲,總想要哼上一小段,強迫他人聽聽,然後被那些跟我喜好相差甚遠的人們給吊起來。
對以下這些歌曲沒有感覺的,本人感到相當抱歉。
包括:喬亨利(Joe Henry)的〈健身床〉(Trampoline)、「馬里斯威廉斯&圓周樂團」(Maurice Williams & the Zodiacs)的〈停留〉(Stay),或索尼男孩威廉斯(Sonny Boy Williams)的〈救我吧〉(Help),還有「流浪者合唱團」(Outkast)的〈傑克森小姐〉(Ms.Jackson),以及任何露辛達威廉斯(Lucinda Williams)、「馬拉樂團」(Marah)、史摩基.羅賓遜(Smokey Robin-son)、歐魯達拉(Olu Dara)、「佩尼斯兄弟樂團」(Pernice Brothers)、朗塞克斯史密斯(Ron Sexsmith),和上千個樂手,包括馬文蓋(Marvin Gaye)。
我的老天爺。如果你還沒聽過真的應該聽聽他們是多麼偉大的音樂人……我的意思是,我之所以能榨出一些文字,然後把這本書在正常篇幅裡處理的正正當當……但那也依然不是重點,作家總是擠榨出一堆東西好讓文章或書能有足夠的文字量。所以你現在手上這本,實際上(我指的是:自然的、沒被強迫,沒接受什麼好處的情況下)是在正常篇幅狀況的特定的書本。如果你喜歡有機的(Organic),一本不在任何置入性行銷式強迫閱讀以及類固醇的幫助下完成的書,那正是這本了。而關於有機性的事物,你多少得付出一些什麼,事情總是如此。嗯……
02 布魯斯史普林斯汀〈崎嶇路〉,Bruce Springsteen〈Thunder Road〉
我記得在一九七五年聽到這首歌,並深深愛上它。最近幾週我聽著這首歌,仍然很喜愛。(是的,是在我的車上--但大概沒真的在開車,我絕對不是奔騰在任何高速公路上,風也沒有強襲過我的髮間,因為我的髮型沒什麼好吹的,所以那並不是在下我的史普林斯汀版本故事。)我愛上這首歌已經有四分之一個世紀,聽這首歌的次數實在是聽到已經比任何……我沒蓋你,根本沒有任何歌曲可以與之相比較。不過,看吧!我現在正要做的事情是把剛剛的大言不慚試圖軟化掉,然後鑽進任何一張黑膠色或很酷的唱片裡推翻自己。﹝很可能會是〈Let’s Get It On〉,我認為史上所創造出最棒的流行歌曲,極有可能就這樣進入了我最常播放歌曲名單前二十名,但不會是第二名。老實說啦--第二名很可能是「衝擊樂團」(The Clash)的〈在漢默史密斯俱樂部發表的白人〉〈(White Man)In Hammersmith Palais〉之類的。﹞
但這種說法好像又扯遠了。這麼說吧,我曾播放過〈崎嶇路〉一千五百次(依照二十五年來每週一次左右算來,應該挺合理的,再加上頭幾年反覆不斷地聆聽);剛說到的「衝擊樂團」之類的歌曲,聆聽的數字大概是五百次吧。換句話說,還真的是沒有競爭對手的一首歌。
話說回來,〈崎嶇路〉能夠在我的生命中存活如此之久,還真是件奇怪的事情,尤其當這麼多年來不斷地出現如此之多、似乎可與之相提並論的好歌曲,比方說〈梅姬玫〉(Maggie May)、〈嘿,裘德〉(Hey Jude)、〈天佑女皇〉(God Saved The Queen)、〈喚起它吧〉(Stir It Up)、〈孤獨叫人如此厭倦〉(So Tired Of Being Alone)、〈如今妳是個女孩了〉(You Are A Girl Now)--這些歌曲在我年歲漸長後,越來越不引起我的注目了。這並非我看不見此曲的缺點,〈崎嶇路〉的確在音樂和歌詞上都太過度推敲了些,﹝正如「合成芽樂團」(Prefab Sprout)曾指出的:相較起車子和女孩,關於人生的部分才是重點。當你試著寫一首關於救贖的歌曲時--提到救贖兩字絕對是個大災難。﹞--總而言之,這四分四十五秒幾乎可說等同於吉姆史坦曼和「肉塊樂團」整個音樂生涯的總和吧。同時它也正經八百的跟史普林斯汀本人有所落差,即便一九七五年哀愁的羅曼蒂克主義音樂不是那麼地傷感,但現在絕對是如此了。
不過,有些時候,偶發性質的書、音樂、電影或繪畫完美的展現了你究竟是誰,這種表述一個人的顯現並不發生在文字或影像中,它的連結性並沒有那麼直接,而要來得複雜許多。當我開始認真投入寫作的最初,我讀了安泰勒(Anne Tyler)的《鄉愁餐廳的晚宴》(Dinner at the Homesick Restaurant),立刻知道我自己究竟是屬於哪種人,以及我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這究竟是好是壞我也說不上來。這種程序跟陷入愛河有些類似,你不會非得要去選擇最棒的、最聰明的,或是最美麗的人,還有其他的因素存在。就像相較之下,我會選擇厄普戴克(Updike)、凱魯亞克(Kerouac),或迪理羅(DeLillo)--比較陽剛氣息的作家,或至少比較晦澀一些的,而且是那種用比較多粗鄙字彙的--沒錯。儘管我在不同的時期景仰這些作家,不過這跟我要談的那種轉化是不同的事情。我所要談的是理解--或至少感覺起來,我是能夠理解的--每個關於藝術化的決心、每一種動力,在作者/作品間同時擁有的靈魂。
「這正是我」,當我在閱讀安泰勒那充滿豐沛哀傷情懷,並同時展露可人風格的作品,「我不會是其中任何一位主角,我跟作者一點也不相似,我也絕無經歷過她筆下的任何相似情境。但即便如此,我卻感同身受,在我的內心,我會使用這樣的說法,如果我有機會去闡述這般故事。」後來我終於有了機會,創造完全屬於我自己的部分,而非安泰勒的;但儘管如此,從閱讀安泰勒的這段經驗中,我感到強大的力量,關於那種認同感的連結,以致於我覺得自己還沒達到足以將自己表述完整的程度。
所以囉,即使我不是美國人、不再年輕、厭惡車子,並且可以理解有些人對於史普林斯汀的歌曲感到造作和誇大(但是為什麼他們不是發現其中充滿男子氣概的、堅定的愛國主義感,以及自身某種駑鈍沉默的特質--這種種的判斷與忽略,讓史普林斯汀的演唱生涯被災難式的誤解,這些誤解來自於那些聰明的傢伙,而事實上他們比史普林斯汀本人來得更駑鈍愚蠢許多)。〈崎嶇路〉是注定要與我對話的。這大概是因為有一部分是,嗯……甚至讓人感到羞愧的--他的歌曲在那個時期多半是關於如何功成名就,或至少是在大眾面前透過他的藝術表現方式取得樂迷/樂界的認同:當歌曲的最後一句「我將遠汲他方,並贏得勝利」,除了想到他已獲得勝利之外,還需多想什麼--這還是透過極為簡單的一種,像是美德般的效力,在一個又一個夜晚裡彈唱這樣的歌曲,然後臺下的聽眾與日俱增。﹝關於他所唱的那首〈蘿莎莉塔〉(Rosalita),一首極為深切、好笑又意外式的歡愉歌曲,除了他自己所言的「因為唱片公司主管蘿西,剛給了我一筆優渥的加薪」這樣的事情之外,我們哪還需要多想什麼--不就是唱片公司給了他一筆優渥的增額薪水嗎?﹞
這種想要成名的意圖一點也不讓人感到不爽,因為這來自一個永不自滿於現狀與無法被掌控的藝術家動力--他知道自己有什麼樣的天賦可以發光發熱,而所得理應實質的回報,在他看來像是一種純粹的儲金--高過於能夠成為一個高調宣揚的名人。主持一個電視益智問答節目,或襄助一個總統之類的。那一點也騷不到欲望的癢處。
當然--別聽信於其他人--如果你的夢想是成為作家。這裡有些黑暗的、骯髒的部分附屬於此類夢想;〈崎嶇路〉是我對每一封退稿信的回應,以及那些來自朋友與親戚們的種種懷疑表示。他們居住在那些充斥著失敗者的城鎮,我告訴自己,我將跟布魯斯一樣,要遠汲他方,並獲得勝利。﹝這些城鎮,順帶一提,乃劍橋(Cambridge)也--住著一群失敗的博士、醫生、律師以及學院人士--還有倫敦--一堆失敗者在各種領域裡取得功名--但無所謂。這就是我必須與之奮發的現實背景,而我的確也與之奮發。﹞
這首歌幫助我度過了許多時光,那些沒有什麼徵兆顯示我將要遠汲到哪裡去,或做些什麼大事業,更不是歌曲內所暗示的那般竄速。〈崎嶇路〉提及了年紀,因而包容了缺乏向前的動力。「嗯,所以你被嚇到了,且想著我們永遠不會再那般年輕了。」布魯斯這樣唱著,這一段彷彿是為我而唱的一般,每每當我在夜裡懷疑是否真的會有靈光乍現的魔術時刻:長久以來,我想著我不再那般年輕了,而且已經很長一段時光了--事實上,可說是幾十年來--甚至直至如今,我還是寧願把它解釋成一種對於中年的苦悶觀測,多於那些直逼而來的尖銳,在晚期青年時刻的恐懼。
同時它幫助了我別的事情。在八○年代的早期近中期,我開始聽這首歌的另外一個版本:史普林斯汀獨自抱著空心吉他在錄音室現場的〈未修飾草錄版〉(bootleg)﹝收錄在《戰爭與玫瑰》(War And Roses)中,此乃《生來勞碌命》的剪輯番外篇﹞,他以一種纏繞心頭、幽微倦懶的風格重現了〈崎嶇路〉,使得它像是一首向過往、向已逝之愛與失落的機會、自我稀釋、那些壞運氣與失敗的種種而述說的詩歌。同樣的那也給予我許多。事實上每當我試著憶及這首歌的最後一段,我總是想起這個空心吉他的版本。它的調子緩慢、情懷淒憂,徹底動容的說服聽者:他是一個能夠讓你信服他所唱出之真實的歌手--就兩個版本的對照來說,他則是一個有能力做出驚人分野的歌手。
有許多其他的〈未修飾草錄版〉都讓我十分喜愛且經常播放。《生來勞碌命》裡面的版本好在剛開頭的那幾段,喘息般的口琴與極其漂亮的鋼琴線,事實上聽起來像是一種,在唱片開始之前就已提到,或帶出了已經發生的什麼。一種重大且悲傷的什麼。但對於希望並未消極:〈崎嶇路〉正是《生來勞碌命》專輯的第一首歌曲。專輯一開始在效果上,已經有了歸屬的光榮謝幕。在七○年代末期,布魯斯史普林斯汀的演出中,從《在城鎮邊緣的暗闔》(the Darkness of the Edge of the Town)巡迴起,他擴大運用了這樣的效果,讓歌曲從他最知名的漂泊淒涼歌曲〈在街景的競馳〉後持續彈奏,其中口琴轉化了那兩首歌,像是一個突然間光榮閃耀的提示。那是有如漫長凋零的冬季過後,春天正欲到來的提示。在〈未修飾草錄版〉們與那些現場表演中,〈崎嶇路〉終於呈現了自己在《生來勞碌命》專輯中曾被推翻的救贖重要性。
或許這正是這首歌曲能夠常存我心的緣故吧。儘管它的能量、高音頻、快速奔馳的車子和髮型……它也可以是一首極其悲傷如輓歌般的曲子,在我年事漸長後仍舊深深吸引著我。當走到了這一步,真該說我太相信生命即是一種重大且悲傷的什麼,但對於希望仍未消極。它可能讓我陷入自我沉醉的沮喪,或讓我像個快樂的白痴。但無論是何者,〈崎嶇路〉能了解我的感覺與我是誰,而那終歸是藝術的一種慰藉吧。
後記
幾年前,我開始成為暢銷作家。首先是在英國,後來連在其他國家也是。這讓我發現(非常意圖矛盾的)我居然開始成為文學與文化主流的中堅分子之一。這不是我所預料的,更不是我有所心理準備的。雖然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讓讀者排斥我的作品--它並沒有真的很艱澀,也並非那麼實驗性--對於我自己而言,我的書似乎還是比較像古靈精怪的輕量級作品。但突然間所有人,我所不認識不知道不喜歡,或無法預知其所以然的,全都開始對我的作品有了評論。類似是一個原本充滿新鮮感與原創性的作家一夜間陳腐老調、落入俗套,而我的書卻根本一字沒動,風格也沒變。我發現自己身處在一種議論紛紛的哈哈鏡世界中,那些朝著我而來的盡是扭曲或非議,但那根本不是我。這並沒有帶給我特定感覺的困擾,我知道以及認識的許多人,經歷了更糟糕的局面。不過的確在那種種情境之下,你很難去維持住自己想要做的東西。
而同時的史普林斯汀似乎早已找到應對之道。他的名字仍舊經常性地出現在無意義的狀況中﹝一年前或大概是那時候,我在報紙一角讀到有人公開批判東尼布萊爾(Tony Blair)喜歡布魯斯史普林斯汀--非常有意圖的,顯然是指名首相無可救藥的庸俗﹞。這些人只能看見哈哈鏡世界內遭到非議的、印象中的史普林斯汀。他從搖滾樂的未來被批判成笨拙招搖、只供給搖滾樂迷現場爽快感的愚傻藝人,只是又是一次其實什麼都沒變、音樂也沒變,只有知名度更上一層。
總之,他那種對自己意圖的堅韌程度,以及面對抨擊他品味的人們,卻依舊存有著自立的毅然態度,可以說是我的模範:有時候很難去記得,當大家開始喜歡你的東西時,並不全然意味著你在做的事情就是沒有價值的。真的。有時候,事實正好相反。
我們正身處於《暈菜的天使》(Speaking With The Angel)的發行午餐會上,我將一些短篇故事集結,以此書來替小犬的學校募款。我和夥伴們、出版商以及校方,都十分緊張於以這種辦法對應來賓們是否合宜--我們不知道結合閱讀與現場音樂表演能否達到預期的效果,與會者能否感到盡興?我很早就到達會場(Hammersmith Palais),當我四處走動時,有兩件事情同時引起我的注意力,其一是表演場地看起來非常棒;前一晚,某個大公司還在這裡舉辦辦公室派對,滿地都是閃亮的裝飾碎物和金銀鋁箔之類的東西。現在,雖然它看起來稍嫌寒酸,但效果性十足,宛如魔術般地象徵性質。另一件事則是「青少年俱樂部樂團」(Teenage Fanclub),允諾在此表演一場不插電(acoustic set)的演出(也正好他們正進行歐陸巡迴演出,所以有這樣的可能與機會)。
現場正在進行器樂測試(sound check),彼時樂團演奏著《妳的愛是我所來之處》(Your Love Is The Place Where I Come From),那是我最最鍾愛的專輯之一,也是《大不列顛北方之歌》(Songs From Northern Britain)中最迷人的歌曲之一。我在一旁聽著,完美音樂型態的表述,對應於那些華而不實的金料碎飾,感覺相當地美好。那一刻,與發行會失敗與否已無關,我知道那會是很特殊的聆賞經驗。而它的確是如此--它成為了我記憶裡最難忘懷,且參與其中的表演。
如今,當我聽到〈妳的愛是我所來之處〉時,總是憶及那個晚上--當然,難不成會有其他可能?簡而言之,當我決定將我所喜愛的歌曲寫成一篇篇散文並集合成冊(這其中有著某種困難的自律,因為曾有太多的選擇而走錯了路,並不是所想得那樣地完美),我便認定這些散文應該是要與人、事、地、物有直接的緊密關聯,如同「青少年俱樂部樂團」這樣的例子。但它們並非如此,也沒有真的如此。事實上,〈妳的愛是我所來之處〉可能是唯一的一篇。我開始想,怎麼會如此呢?何以只有這麼少的歌曲能夠匯聚我的感動,並將之寫成文章?答案很清晰的浮現:當你愛上一首歌,愛到足以在人生的任何階段裡都陪伴著你,那麼任何特殊、單一關於歌曲的記憶很快地變得不是重點。
如果我是在一九七五年某個女孩的房間裡聽見〈崎嶇路〉(Thunder Road),會覺得還挺好聽的,然後可能再也沒有見過這個女孩或者去找這首歌來聽;那麼當然很可能,當我再一次聽見它時,憶及的大概就是那女孩腋下體香劑的味道。不過,實際上事情不是這樣的;事實上是我聽了〈崎嶇路〉並愛上了它,而且我聽這首歌的頻率(驚人的),多到最後我只記得關於這首歌曲本身--那時我十八歲,關於那時,實在沒什麼好說的。多說了也是白說。
我記得以前在英國國家廣播電臺(BBC)有一首很恐怖的歌叫做〈媽媽我想喝杯水〉(印象中是這樣),這首歌總在星期六早上的兒童電臺節目中撥放。我想我沒有再聽過那首歌,不過如果是這樣,大概會產生那種,當我還是個小孩時,每個週六早上超出承受地聽著那歌曲的記憶。有一首「吉普賽國王樂團」(Gypsy Kings)唱的歌曲,提醒了我曾經在里斯本(Lisbon)的某場足球賽事裡,被一個天外飛來的塑膠啤酒瓶K到的事情。有些歌曲會讓我想起關於大學時代、前女友們,或夏日的打工時光,但種種這些對我來說,跟音樂一點關聯意義也沒有,他們只是記憶的一部分,我並不想寫關乎記憶的故事。那並非重點。那只能帶出類似某人說,他們一生中最愛的唱片,令他們想起了柯西加島的蜜月旅行,或家中的吉娃娃狗,其實也沒有多麼地喜愛音樂本身。我想書寫的是這些歌曲如何令我愛上它們,而不是我的人生賦予了歌曲什麼。
我幾乎沒有拒絕聆聽的音樂類型,但並不常聽古典樂與爵士樂。當人們問及我喜愛什麼歌曲,其實有些令我困擾於該如何回答,因為他們多半要的是歌手的名字,而我多半只能給他們曲名。多數時候我所能說的,就只有我深愛的這些歌曲,總想要哼上一小段,強迫他人聽聽,然後被那些跟我喜好相差甚遠的人們給吊起來。
對以下這些歌曲沒有感覺的,本人感到相當抱歉。
包括:喬亨利(Joe Henry)的〈健身床〉(Trampoline)、「馬里斯威廉斯&圓周樂團」(Maurice Williams & the Zodiacs)的〈停留〉(Stay),或索尼男孩威廉斯(Sonny Boy Williams)的〈救我吧〉(Help),還有「流浪者合唱團」(Outkast)的〈傑克森小姐〉(Ms.Jackson),以及任何露辛達威廉斯(Lucinda Williams)、「馬拉樂團」(Marah)、史摩基.羅賓遜(Smokey Robin-son)、歐魯達拉(Olu Dara)、「佩尼斯兄弟樂團」(Pernice Brothers)、朗塞克斯史密斯(Ron Sexsmith),和上千個樂手,包括馬文蓋(Marvin Gaye)。
我的老天爺。如果你還沒聽過真的應該聽聽他們是多麼偉大的音樂人……我的意思是,我之所以能榨出一些文字,然後把這本書在正常篇幅裡處理的正正當當……但那也依然不是重點,作家總是擠榨出一堆東西好讓文章或書能有足夠的文字量。所以你現在手上這本,實際上(我指的是:自然的、沒被強迫,沒接受什麼好處的情況下)是在正常篇幅狀況的特定的書本。如果你喜歡有機的(Organic),一本不在任何置入性行銷式強迫閱讀以及類固醇的幫助下完成的書,那正是這本了。而關於有機性的事物,你多少得付出一些什麼,事情總是如此。嗯……
02 布魯斯史普林斯汀〈崎嶇路〉,Bruce Springsteen〈Thunder Road〉
我記得在一九七五年聽到這首歌,並深深愛上它。最近幾週我聽著這首歌,仍然很喜愛。(是的,是在我的車上--但大概沒真的在開車,我絕對不是奔騰在任何高速公路上,風也沒有強襲過我的髮間,因為我的髮型沒什麼好吹的,所以那並不是在下我的史普林斯汀版本故事。)我愛上這首歌已經有四分之一個世紀,聽這首歌的次數實在是聽到已經比任何……我沒蓋你,根本沒有任何歌曲可以與之相比較。不過,看吧!我現在正要做的事情是把剛剛的大言不慚試圖軟化掉,然後鑽進任何一張黑膠色或很酷的唱片裡推翻自己。﹝很可能會是〈Let’s Get It On〉,我認為史上所創造出最棒的流行歌曲,極有可能就這樣進入了我最常播放歌曲名單前二十名,但不會是第二名。老實說啦--第二名很可能是「衝擊樂團」(The Clash)的〈在漢默史密斯俱樂部發表的白人〉〈(White Man)In Hammersmith Palais〉之類的。﹞
但這種說法好像又扯遠了。這麼說吧,我曾播放過〈崎嶇路〉一千五百次(依照二十五年來每週一次左右算來,應該挺合理的,再加上頭幾年反覆不斷地聆聽);剛說到的「衝擊樂團」之類的歌曲,聆聽的數字大概是五百次吧。換句話說,還真的是沒有競爭對手的一首歌。
話說回來,〈崎嶇路〉能夠在我的生命中存活如此之久,還真是件奇怪的事情,尤其當這麼多年來不斷地出現如此之多、似乎可與之相提並論的好歌曲,比方說〈梅姬玫〉(Maggie May)、〈嘿,裘德〉(Hey Jude)、〈天佑女皇〉(God Saved The Queen)、〈喚起它吧〉(Stir It Up)、〈孤獨叫人如此厭倦〉(So Tired Of Being Alone)、〈如今妳是個女孩了〉(You Are A Girl Now)--這些歌曲在我年歲漸長後,越來越不引起我的注目了。這並非我看不見此曲的缺點,〈崎嶇路〉的確在音樂和歌詞上都太過度推敲了些,﹝正如「合成芽樂團」(Prefab Sprout)曾指出的:相較起車子和女孩,關於人生的部分才是重點。當你試著寫一首關於救贖的歌曲時--提到救贖兩字絕對是個大災難。﹞--總而言之,這四分四十五秒幾乎可說等同於吉姆史坦曼和「肉塊樂團」整個音樂生涯的總和吧。同時它也正經八百的跟史普林斯汀本人有所落差,即便一九七五年哀愁的羅曼蒂克主義音樂不是那麼地傷感,但現在絕對是如此了。
不過,有些時候,偶發性質的書、音樂、電影或繪畫完美的展現了你究竟是誰,這種表述一個人的顯現並不發生在文字或影像中,它的連結性並沒有那麼直接,而要來得複雜許多。當我開始認真投入寫作的最初,我讀了安泰勒(Anne Tyler)的《鄉愁餐廳的晚宴》(Dinner at the Homesick Restaurant),立刻知道我自己究竟是屬於哪種人,以及我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這究竟是好是壞我也說不上來。這種程序跟陷入愛河有些類似,你不會非得要去選擇最棒的、最聰明的,或是最美麗的人,還有其他的因素存在。就像相較之下,我會選擇厄普戴克(Updike)、凱魯亞克(Kerouac),或迪理羅(DeLillo)--比較陽剛氣息的作家,或至少比較晦澀一些的,而且是那種用比較多粗鄙字彙的--沒錯。儘管我在不同的時期景仰這些作家,不過這跟我要談的那種轉化是不同的事情。我所要談的是理解--或至少感覺起來,我是能夠理解的--每個關於藝術化的決心、每一種動力,在作者/作品間同時擁有的靈魂。
「這正是我」,當我在閱讀安泰勒那充滿豐沛哀傷情懷,並同時展露可人風格的作品,「我不會是其中任何一位主角,我跟作者一點也不相似,我也絕無經歷過她筆下的任何相似情境。但即便如此,我卻感同身受,在我的內心,我會使用這樣的說法,如果我有機會去闡述這般故事。」後來我終於有了機會,創造完全屬於我自己的部分,而非安泰勒的;但儘管如此,從閱讀安泰勒的這段經驗中,我感到強大的力量,關於那種認同感的連結,以致於我覺得自己還沒達到足以將自己表述完整的程度。
所以囉,即使我不是美國人、不再年輕、厭惡車子,並且可以理解有些人對於史普林斯汀的歌曲感到造作和誇大(但是為什麼他們不是發現其中充滿男子氣概的、堅定的愛國主義感,以及自身某種駑鈍沉默的特質--這種種的判斷與忽略,讓史普林斯汀的演唱生涯被災難式的誤解,這些誤解來自於那些聰明的傢伙,而事實上他們比史普林斯汀本人來得更駑鈍愚蠢許多)。〈崎嶇路〉是注定要與我對話的。這大概是因為有一部分是,嗯……甚至讓人感到羞愧的--他的歌曲在那個時期多半是關於如何功成名就,或至少是在大眾面前透過他的藝術表現方式取得樂迷/樂界的認同:當歌曲的最後一句「我將遠汲他方,並贏得勝利」,除了想到他已獲得勝利之外,還需多想什麼--這還是透過極為簡單的一種,像是美德般的效力,在一個又一個夜晚裡彈唱這樣的歌曲,然後臺下的聽眾與日俱增。﹝關於他所唱的那首〈蘿莎莉塔〉(Rosalita),一首極為深切、好笑又意外式的歡愉歌曲,除了他自己所言的「因為唱片公司主管蘿西,剛給了我一筆優渥的加薪」這樣的事情之外,我們哪還需要多想什麼--不就是唱片公司給了他一筆優渥的增額薪水嗎?﹞
這種想要成名的意圖一點也不讓人感到不爽,因為這來自一個永不自滿於現狀與無法被掌控的藝術家動力--他知道自己有什麼樣的天賦可以發光發熱,而所得理應實質的回報,在他看來像是一種純粹的儲金--高過於能夠成為一個高調宣揚的名人。主持一個電視益智問答節目,或襄助一個總統之類的。那一點也騷不到欲望的癢處。
當然--別聽信於其他人--如果你的夢想是成為作家。這裡有些黑暗的、骯髒的部分附屬於此類夢想;〈崎嶇路〉是我對每一封退稿信的回應,以及那些來自朋友與親戚們的種種懷疑表示。他們居住在那些充斥著失敗者的城鎮,我告訴自己,我將跟布魯斯一樣,要遠汲他方,並獲得勝利。﹝這些城鎮,順帶一提,乃劍橋(Cambridge)也--住著一群失敗的博士、醫生、律師以及學院人士--還有倫敦--一堆失敗者在各種領域裡取得功名--但無所謂。這就是我必須與之奮發的現實背景,而我的確也與之奮發。﹞
這首歌幫助我度過了許多時光,那些沒有什麼徵兆顯示我將要遠汲到哪裡去,或做些什麼大事業,更不是歌曲內所暗示的那般竄速。〈崎嶇路〉提及了年紀,因而包容了缺乏向前的動力。「嗯,所以你被嚇到了,且想著我們永遠不會再那般年輕了。」布魯斯這樣唱著,這一段彷彿是為我而唱的一般,每每當我在夜裡懷疑是否真的會有靈光乍現的魔術時刻:長久以來,我想著我不再那般年輕了,而且已經很長一段時光了--事實上,可說是幾十年來--甚至直至如今,我還是寧願把它解釋成一種對於中年的苦悶觀測,多於那些直逼而來的尖銳,在晚期青年時刻的恐懼。
同時它幫助了我別的事情。在八○年代的早期近中期,我開始聽這首歌的另外一個版本:史普林斯汀獨自抱著空心吉他在錄音室現場的〈未修飾草錄版〉(bootleg)﹝收錄在《戰爭與玫瑰》(War And Roses)中,此乃《生來勞碌命》的剪輯番外篇﹞,他以一種纏繞心頭、幽微倦懶的風格重現了〈崎嶇路〉,使得它像是一首向過往、向已逝之愛與失落的機會、自我稀釋、那些壞運氣與失敗的種種而述說的詩歌。同樣的那也給予我許多。事實上每當我試著憶及這首歌的最後一段,我總是想起這個空心吉他的版本。它的調子緩慢、情懷淒憂,徹底動容的說服聽者:他是一個能夠讓你信服他所唱出之真實的歌手--就兩個版本的對照來說,他則是一個有能力做出驚人分野的歌手。
有許多其他的〈未修飾草錄版〉都讓我十分喜愛且經常播放。《生來勞碌命》裡面的版本好在剛開頭的那幾段,喘息般的口琴與極其漂亮的鋼琴線,事實上聽起來像是一種,在唱片開始之前就已提到,或帶出了已經發生的什麼。一種重大且悲傷的什麼。但對於希望並未消極:〈崎嶇路〉正是《生來勞碌命》專輯的第一首歌曲。專輯一開始在效果上,已經有了歸屬的光榮謝幕。在七○年代末期,布魯斯史普林斯汀的演出中,從《在城鎮邊緣的暗闔》(the Darkness of the Edge of the Town)巡迴起,他擴大運用了這樣的效果,讓歌曲從他最知名的漂泊淒涼歌曲〈在街景的競馳〉後持續彈奏,其中口琴轉化了那兩首歌,像是一個突然間光榮閃耀的提示。那是有如漫長凋零的冬季過後,春天正欲到來的提示。在〈未修飾草錄版〉們與那些現場表演中,〈崎嶇路〉終於呈現了自己在《生來勞碌命》專輯中曾被推翻的救贖重要性。
或許這正是這首歌曲能夠常存我心的緣故吧。儘管它的能量、高音頻、快速奔馳的車子和髮型……它也可以是一首極其悲傷如輓歌般的曲子,在我年事漸長後仍舊深深吸引著我。當走到了這一步,真該說我太相信生命即是一種重大且悲傷的什麼,但對於希望仍未消極。它可能讓我陷入自我沉醉的沮喪,或讓我像個快樂的白痴。但無論是何者,〈崎嶇路〉能了解我的感覺與我是誰,而那終歸是藝術的一種慰藉吧。
後記
幾年前,我開始成為暢銷作家。首先是在英國,後來連在其他國家也是。這讓我發現(非常意圖矛盾的)我居然開始成為文學與文化主流的中堅分子之一。這不是我所預料的,更不是我有所心理準備的。雖然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讓讀者排斥我的作品--它並沒有真的很艱澀,也並非那麼實驗性--對於我自己而言,我的書似乎還是比較像古靈精怪的輕量級作品。但突然間所有人,我所不認識不知道不喜歡,或無法預知其所以然的,全都開始對我的作品有了評論。類似是一個原本充滿新鮮感與原創性的作家一夜間陳腐老調、落入俗套,而我的書卻根本一字沒動,風格也沒變。我發現自己身處在一種議論紛紛的哈哈鏡世界中,那些朝著我而來的盡是扭曲或非議,但那根本不是我。這並沒有帶給我特定感覺的困擾,我知道以及認識的許多人,經歷了更糟糕的局面。不過的確在那種種情境之下,你很難去維持住自己想要做的東西。
而同時的史普林斯汀似乎早已找到應對之道。他的名字仍舊經常性地出現在無意義的狀況中﹝一年前或大概是那時候,我在報紙一角讀到有人公開批判東尼布萊爾(Tony Blair)喜歡布魯斯史普林斯汀--非常有意圖的,顯然是指名首相無可救藥的庸俗﹞。這些人只能看見哈哈鏡世界內遭到非議的、印象中的史普林斯汀。他從搖滾樂的未來被批判成笨拙招搖、只供給搖滾樂迷現場爽快感的愚傻藝人,只是又是一次其實什麼都沒變、音樂也沒變,只有知名度更上一層。
總之,他那種對自己意圖的堅韌程度,以及面對抨擊他品味的人們,卻依舊存有著自立的毅然態度,可以說是我的模範:有時候很難去記得,當大家開始喜歡你的東西時,並不全然意味著你在做的事情就是沒有價值的。真的。有時候,事實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