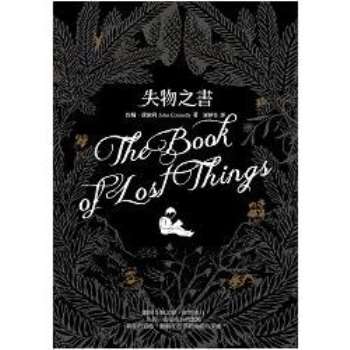【第一章 所有尋得與失落的】
很久很久以前(故事都該這樣開場),有個男孩失去了母親。
事實上,所謂「失去」的過程相當漫長。奪去他母親生命的病,像個賊兮兮、怯生生的東西,從內裡悄悄慢慢啃齧,緩緩耗盡裡頭的光亮。隨著時間一天天過去,母親的雙眼日漸黯淡,膚色愈趨蒼白。
老天一點一滴將他母親偷走,令他愈來愈怕完全失去母親的那一天。他要母親留在身邊。他沒有兄弟姊妹;雖說也愛父親,但老實講,更愛母親,實在無法想像沒有母親的日子。
這男孩名叫大衛。他做盡一切,只希望能讓母親活著。他祈禱。他盡量聽話,以免母親得為他犯的過錯受罰。他在屋裡躡手躡腳,盡力不發聲響,跟玩具兵玩戰爭遊戲時也會壓低音量。他作息固定並努力遵守,因為他相信母親的命運跟自己的行為息息相關。下床時,總讓左腳先著地,才放下右腳。刷牙時,總是數到二十,次數一滿就立刻停下不刷。碰浴室水龍頭與屋內門把時,總要固定碰滿幾次:奇數很不好,偶數就不打緊,二、四、八特別討喜,但是他不喜歡六,因為六是三的兩倍,而三又是十三的個位數。十三真的很不祥。
如果頭撞上了什麼,為了維持偶數原則,他就會多撞一回──偶爾還得反覆撞個幾次,因為頭要不是碰壁反彈,亂了次數,就是因為頭髮不如願地掃掠過牆。他撞得那麼用力,頭殼也疼了,暈眩欲吐。在母親病最重的那一整年,他每天早上起床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同樣的東西從自己的臥房搬往廚房,晚上睡前再全搬回臥房,包括:一冊小開本格林童話選集、翻得老舊折角的《磁力》漫畫集;童話集還得精確擺在漫畫本正中央。晚上,兩本書的側邊要緊靠臥房地毯一角安放;一到早上,則擺到廚房裡他最愛的那張椅子上。藉著這些方法,大衛就能出些心力,幫助母親活下去。
每天放學後,大衛便坐在母親的床沿陪伴,趁她體力夠的時候聊聊。其他時候就只能看著母親睡,數算她費勁呼吸所發出的喘吁吁的聲音,用念力要她待在自己身邊。他常隨身帶本書,母親若醒著,頭痛又不厲害,就會要他高聲朗讀。母親有她自己的書,都是些傳奇小說、推理故事、密密麻麻滿是小字的厚重黑皮小說。不過,她比較喜歡大衛唸一些老一點兒的故事聽,像是神話、傳說,或是童話。那些故事有城堡、有冒險遠征的主角、會說人話的猛獸。大衛不反對。雖然十二歲已經不算是小孩了,他依舊喜愛這些故事,更何況唸這些故事能讓母親開心,也就讓他多愛一分。
母親患病前,常告訴他「故事有生命」,但故事的生命跟人或貓狗的生命不一樣。不管留不留神,人還是活得好端端的;狗兒如果覺得乏人關注,通常就會拚命引起注意;貓咪若一時興起,還會假裝人根本不存在──這點牠們可拿手了。
故事可不一樣:人說故事,故事才會活起來。要是沒人高聲誦讀,沒人躲在毯子底下、就著手電筒光,睜大了眼專注閱讀,那麼在我們的世界裡,故事並不存在。故事好似啣在鳥喙裡的種子,等候落地入土;像樂譜上的音符,渴望樂器將其帶進世間。故事潛伏靜待,期盼現身的時機。一旦有人閱讀,故事就開始變化,在想像力中生根,讓閱讀的人改頭換面。故事渴望人來讀,大衛的母親會這樣低語。它們就是需要。所以,故事會排除萬難跳脫自己的世界,闖進我們這邊來。
這些事情是母親病倒之前告訴他的。母親常常邊說邊捧著書,指尖戀戀滑過書皮,就像他或父親偶爾說了或做了什麼,讓母親頓時想起自己多愛他們,然後以指尖輕撫他們的臉一樣。對大衛而言,母親的嗓音好似一首歌,不時即興變化,展現前所未聞的奧妙。待年歲漸長,音樂對他漸形重要(雖說分量仍不敵書本),母親的嗓音較不像歌了,更像是交響曲,能依著熟悉的主題和旋律無盡延伸變奏,隨著她的心情和興致變幻無窮。
隨著時光流逝,閱讀變成了較為孤獨的體驗,直到母親的病將他倆帶回大衛的童年時光,只不過這回角色互換。母親罹病之前,大衛常常悄悄走近正在讀書的母親,露個笑容向她致意(她也總報以微笑),在離她不遠的位置坐下,埋首自己的書中;因此,儘管兩人沈浸在各自的世界,卻共享了同樣的時光與空間。從母親閱讀的神情中,大衛能察覺書裡的故事是否在母親心裡活了起來、母親自己是否在故事中也有了生命,然後回想起母親先前說過的一切:關於故事和傳奇,以及它們在我們身上施展的威力,反之,還有我們掌控它們的力量。
大衛會永遠記得母親過世的日子。那時他正在學校,學著(或瞎混著)分析詩的格律,滿腦子全是「戴克托斯」、「磐塔米特斯」(注:Dactyls,即「揚抑抑格」。Pentameters,為「五音步」。)這些聽來就像史前天地裡那些奇異恐龍的詞句。校長推開教室的門,走向英文老師班傑明先生(學生都叫他「大笨鐘」,因為他身材壯碩,又習慣從背心褶縫掏出老懷錶,用低沈憂傷的語調,向淘氣的學生宣告時光之荏苒)。校長向班傑明先生低聲說些話,班傑明先生肅穆地點點頭,轉身面對全班,眼光與大衛相遇,說話語調比平常來得輕柔。他點了大衛的名,告訴大衛可先行離席,要大衛整理好書包跟著校長離開。大衛那時就知道發生什麼事了。校長帶他到醫護室之前,他就懂了。護士端杯茶給他喝之前,他早明白了。校長站在他面前,面容嚴峻如常,但顯然努力想對這喪親的男孩溫柔一些,而他早已明瞭。茶杯碰上嘴唇、話說出口以前,他就知道了。茶燙了他的嘴,提醒自己還活著,卻失去了母親。
縱使不斷重複例行作息,卻還是沒能保護母親。他事後回想,是不是哪一項沒做好?是不是那天早晨數錯了數?當初如果往好幾種項目再添個動作,或許就能扭轉一切?如今都已無關緊要。母親已經走了。早該待在家裡的。人在學校時,老是擔心她,因為若不在她身邊,她的存在就越出控制範圍之外。那套例行程序在學校不管用。學校有其規則和作息,自己這套就更難實施。大衛想拿學校那套來頂替,可是畢竟不同。現在母親就為這付出了代價。
因深感失敗而羞愧不已,大衛這才哭了起來。
接下來幾天,印象只是一片模糊。鄰居和親友來去紛紛,高大陌生的男士們搓搓他的頭,遞給他一先令;著黑洋裝的胖女士們哭著將大衛擁入胸懷,聞到的盡是她們的香水和樟腦丸味。他被擠進客廳角落裡跟著熬夜,大人一個個輪流談起的母親,卻是他從不認識的人、個人過往與他完全不同路的奇怪人物。例如:小時候,母親的姊姊過世時,她就是不哭,因為不肯相信對她而言那樣珍貴的人竟會永遠消失不復返。少女時期犯了小過,她爸爸一時之間失去耐性,揚言要把她交給吉普賽人,她於是逃家一天……長大後,成了身著亮紅色洋裝的美麗女郎,而大衛的爸爸從情敵面前大剌剌把她給偷了走。婚禮那天,她身穿白色婚紗,美麗動人,拇指卻讓玫瑰刺傷,在禮服上留下了眾目共睹的血斑。
大衛終於睡著,夢見自己成了這些故事的一部分,得以參與母親生命的每一階段。他不再只是耳聞過往故事的小孩,而是在場目睹了那一切。
大衛最後一次見到母親,是蓋棺之前、在葬儀社裡。看來雖有些不同,但仍是她原來的樣子──從前的她,那個受病魔侵蝕之前的她。她臉上有妝,就像上教堂做禮拜或跟爸爸出外用餐看電影那樣。她換上了最愛的那件藍洋裝,雙手交疊在肚腹上,手指交纏著玫瑰念珠,戒指都取掉了,雙唇紅通通的。大衛站著俯望她,手指碰碰她的手。摸起來好冷,也有些潮濕。
爸爸來到他身旁。只剩他倆還沒離開這房間。其他人都到外頭去了。車子在外等著載大衛和爸爸到教堂去。那車又大又黑。駕車的男人頭戴尖帽、毫無笑顏。
「大衛,你可以親親她當作道別。」大衛抬眼望著爸爸,他雙眼微濕、眼眶紅腫。母親過世第一天,爸爸就哭過了。那時大衛自學校返家,爸爸一把擁住他,向他保證一切終將好轉。在那之後,爸爸便沒再流淚,直到此刻。大衛望著望著,一顆豆大的淚湧起,緩緩地、幾乎有些彆扭地,滑落臉頰。他回身向母親,身子探進棺柩,吻了她臉頰。她身上有股化學味,還有別的;別的什麼,大衛不願多想──他在媽媽的唇上嚐到了。
「再見了,媽媽。」他輕聲說。雙眼刺痛。他想做些事情,可又不知道該做什麼。
爸爸一手搭上了大衛的肩,彎下身來輕柔吻了媽媽的唇,臉的一側貼上她的臉頰,喃喃說了些大衛聽不清的話,而後與大衛離開了房間。棺柩由禮儀師和助手抬著再度出現時,棺蓋已經闔上。唯一看得出大衛母親躺在裡頭的標示,就是棺蓋上刻著名字和生卒年月的那塊小金屬片。那晚,母親獨自留在教堂裡。如果可以,大衛情願伴著她。不知媽媽寂不寂寞?不知她是否清楚自己身在何處?不知她是否已到天堂,或者得等牧師最後祝禱、棺木入土後,才能上天堂?他實在不願想像媽媽一人孤伶伶的,讓木頭、黃銅和釘子封牢在裡面,可是他沒辦法跟爸爸開口談這事。爸爸不會懂,況且也無濟於事。既然沒辦法獨自待在教堂裡,他索性往房裡去,試著想像母親的處境。他將窗簾闔攏,把門關上,讓房裡盡可能漆黑無光,接著爬進床底。
床本身就低,床底下的空間更窄。由於位在房間角落,大衛便盡量靠邊擠,直到左手貼上牆,眼睛緊緊閉上,躺著動也不動。過了一會兒,他想抬起頭,可一抬頭就撞上支撐床墊的床板;他硬推,床板仍牢牢釘在原位。他雙手往上推,想把床抬起來,可是太重了。他聞到塵埃和尿壺的氣味,嗆咳起來,不禁流淚。他決定從床底下脫身,可把自己拖出來比挪進現在的位置還難。他打了噴嚏,頭撞上床底,又是一陣痛擊。他開始慌張,赤著腳速速踢掃,希望能在木板地上有些抓力。他朝上伸手,藉床板使力,將自己一路拉出,直到足夠靠近床緣,能再擠出身子為止。他蹣跚站起,傾靠著牆深深喘息。
原來死亡就像這樣:困身於小小空間裡,讓巨大重量給制住,直到永永遠遠。
大衛的母親在一月的某個早晨下葬。地面冷硬,弔喪者皆戴著手套、身披大衣。將棺柩往土穴裡放時,棺木看來短得過分。母親活著的時候總是顯得那麼高身,可死亡把她縮小了。
往後幾週,大衛將自己放逐在書本裡,因為他對媽媽的記憶,與書籍、閱讀交纏不分。原屬於媽媽的書,親友挑了些「適合」的傳給了大衛。他意識到自己啃著讀不懂的小說,唸著不大押韻的詩。有時他會拿去問爸爸,但是爸爸對書本似乎興趣缺缺。在家裡的時間,爸爸總一頭栽進報紙裡,執迷於現代世界的炎涼浮沈,菸斗的縷縷煙霧自報紙上方升起,好似印地安人發出的訊號。希特勒的軍隊橫掃歐陸,進擊英國本土的威脅愈來愈可能成真,讓爸爸比以往更放不下了。媽媽說過,爸爸以前閱書無數,後來卻擺脫了沈浸於故事裡的習慣。如今他偏好有長長印刷欄位的報紙,字字以手工精心編排而成,創造出某種上了報攤就幾乎頓失意義的東西;等到人閱讀時,裡頭的新聞早已成了凋零中的舊聞,早被報外世界的事件迎頭趕上。
書本裡頭的故事痛恨報紙裡的故事,大衛的媽媽會這樣說。報紙上的故事像是剛捕獲的魚,只有在新鮮期才值得一顧,保鮮期卻不持久。它們像街頭叫賣晚報的頑童,盡是大呼小叫、死纏爛打;而故事──真正的故事,正統的、出於想像的故事,好似藏書豐富的圖書館裡,那不苟言笑卻熱心助人的館員。報紙故事跟煙霧一樣虛空不實,壽命跟蜉蝣一般短;它們不會生根,反倒像野草一般沿地蔓生,從更值得青睞的故事那兒盜走陽光。爸爸的心思總讓那些競相爭鳴的尖銳聲音占據,就算將注意力轉向某個聲音讓它靜下,也隨即讓下一波喧譁取代。媽媽總是面帶微笑,悄聲跟大衛說這些話;而爸爸明知兩人正談著他,卻沈著臉咬菸斗,不願讓他們因為成功惹毛了自己而竊喜。
於是,護衛媽媽書本的重任就落在大衛身上。他把母親遺留下的書跟當初為他採買的放在一起。這些關於騎士、士兵、惡龍、海怪等傳說,或是民間傳奇、童話故事,都是母親在少女時期鍾愛的故事。疾病逐漸控制她、令她動彈不得後,換大衛唸書給她聽。病痛把她的嗓音減為呢喃低語,將她的呼息化為舊沙紙摩擦腐木的粗嘎聲,直到最後實在過於費力,便不再呼吸。母親過世後,他想避開這些老故事,因為故事跟母親之間的連結那樣深,他實在無法欣快閱讀。可是這些故事可不肯輕易被否決,開始呼喚大衛。它們似乎在大衛身上認出(或許他自己也漸漸認為)好奇、富創造力的特質。他聽到故事說話的聲音:一開始只是輕聲細語,接著便放大音量、逼人留神。
這些故事很古老,跟人一樣。就因它們威力十足,始能留存至今。就算將書本扔到一邊去,故事的情節仍會在腦裡迴盪不去。它們是由現實跳脫而出,卻也自成另一個世界,古老又怪異,令它們的存在得以獨立於書頁之外。媽媽曾告訴他,這些老故事的世界與我們的世界平行共存;偶爾,分隔這兩個世界的牆變得薄弱,兩者便開始融而為一。屆時,麻煩因之啟動。
屆時,壞事就要降臨。
屆時,駝背人開始出現在大衛周圍。
很久很久以前(故事都該這樣開場),有個男孩失去了母親。
事實上,所謂「失去」的過程相當漫長。奪去他母親生命的病,像個賊兮兮、怯生生的東西,從內裡悄悄慢慢啃齧,緩緩耗盡裡頭的光亮。隨著時間一天天過去,母親的雙眼日漸黯淡,膚色愈趨蒼白。
老天一點一滴將他母親偷走,令他愈來愈怕完全失去母親的那一天。他要母親留在身邊。他沒有兄弟姊妹;雖說也愛父親,但老實講,更愛母親,實在無法想像沒有母親的日子。
這男孩名叫大衛。他做盡一切,只希望能讓母親活著。他祈禱。他盡量聽話,以免母親得為他犯的過錯受罰。他在屋裡躡手躡腳,盡力不發聲響,跟玩具兵玩戰爭遊戲時也會壓低音量。他作息固定並努力遵守,因為他相信母親的命運跟自己的行為息息相關。下床時,總讓左腳先著地,才放下右腳。刷牙時,總是數到二十,次數一滿就立刻停下不刷。碰浴室水龍頭與屋內門把時,總要固定碰滿幾次:奇數很不好,偶數就不打緊,二、四、八特別討喜,但是他不喜歡六,因為六是三的兩倍,而三又是十三的個位數。十三真的很不祥。
如果頭撞上了什麼,為了維持偶數原則,他就會多撞一回──偶爾還得反覆撞個幾次,因為頭要不是碰壁反彈,亂了次數,就是因為頭髮不如願地掃掠過牆。他撞得那麼用力,頭殼也疼了,暈眩欲吐。在母親病最重的那一整年,他每天早上起床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同樣的東西從自己的臥房搬往廚房,晚上睡前再全搬回臥房,包括:一冊小開本格林童話選集、翻得老舊折角的《磁力》漫畫集;童話集還得精確擺在漫畫本正中央。晚上,兩本書的側邊要緊靠臥房地毯一角安放;一到早上,則擺到廚房裡他最愛的那張椅子上。藉著這些方法,大衛就能出些心力,幫助母親活下去。
每天放學後,大衛便坐在母親的床沿陪伴,趁她體力夠的時候聊聊。其他時候就只能看著母親睡,數算她費勁呼吸所發出的喘吁吁的聲音,用念力要她待在自己身邊。他常隨身帶本書,母親若醒著,頭痛又不厲害,就會要他高聲朗讀。母親有她自己的書,都是些傳奇小說、推理故事、密密麻麻滿是小字的厚重黑皮小說。不過,她比較喜歡大衛唸一些老一點兒的故事聽,像是神話、傳說,或是童話。那些故事有城堡、有冒險遠征的主角、會說人話的猛獸。大衛不反對。雖然十二歲已經不算是小孩了,他依舊喜愛這些故事,更何況唸這些故事能讓母親開心,也就讓他多愛一分。
母親患病前,常告訴他「故事有生命」,但故事的生命跟人或貓狗的生命不一樣。不管留不留神,人還是活得好端端的;狗兒如果覺得乏人關注,通常就會拚命引起注意;貓咪若一時興起,還會假裝人根本不存在──這點牠們可拿手了。
故事可不一樣:人說故事,故事才會活起來。要是沒人高聲誦讀,沒人躲在毯子底下、就著手電筒光,睜大了眼專注閱讀,那麼在我們的世界裡,故事並不存在。故事好似啣在鳥喙裡的種子,等候落地入土;像樂譜上的音符,渴望樂器將其帶進世間。故事潛伏靜待,期盼現身的時機。一旦有人閱讀,故事就開始變化,在想像力中生根,讓閱讀的人改頭換面。故事渴望人來讀,大衛的母親會這樣低語。它們就是需要。所以,故事會排除萬難跳脫自己的世界,闖進我們這邊來。
這些事情是母親病倒之前告訴他的。母親常常邊說邊捧著書,指尖戀戀滑過書皮,就像他或父親偶爾說了或做了什麼,讓母親頓時想起自己多愛他們,然後以指尖輕撫他們的臉一樣。對大衛而言,母親的嗓音好似一首歌,不時即興變化,展現前所未聞的奧妙。待年歲漸長,音樂對他漸形重要(雖說分量仍不敵書本),母親的嗓音較不像歌了,更像是交響曲,能依著熟悉的主題和旋律無盡延伸變奏,隨著她的心情和興致變幻無窮。
隨著時光流逝,閱讀變成了較為孤獨的體驗,直到母親的病將他倆帶回大衛的童年時光,只不過這回角色互換。母親罹病之前,大衛常常悄悄走近正在讀書的母親,露個笑容向她致意(她也總報以微笑),在離她不遠的位置坐下,埋首自己的書中;因此,儘管兩人沈浸在各自的世界,卻共享了同樣的時光與空間。從母親閱讀的神情中,大衛能察覺書裡的故事是否在母親心裡活了起來、母親自己是否在故事中也有了生命,然後回想起母親先前說過的一切:關於故事和傳奇,以及它們在我們身上施展的威力,反之,還有我們掌控它們的力量。
大衛會永遠記得母親過世的日子。那時他正在學校,學著(或瞎混著)分析詩的格律,滿腦子全是「戴克托斯」、「磐塔米特斯」(注:Dactyls,即「揚抑抑格」。Pentameters,為「五音步」。)這些聽來就像史前天地裡那些奇異恐龍的詞句。校長推開教室的門,走向英文老師班傑明先生(學生都叫他「大笨鐘」,因為他身材壯碩,又習慣從背心褶縫掏出老懷錶,用低沈憂傷的語調,向淘氣的學生宣告時光之荏苒)。校長向班傑明先生低聲說些話,班傑明先生肅穆地點點頭,轉身面對全班,眼光與大衛相遇,說話語調比平常來得輕柔。他點了大衛的名,告訴大衛可先行離席,要大衛整理好書包跟著校長離開。大衛那時就知道發生什麼事了。校長帶他到醫護室之前,他就懂了。護士端杯茶給他喝之前,他早明白了。校長站在他面前,面容嚴峻如常,但顯然努力想對這喪親的男孩溫柔一些,而他早已明瞭。茶杯碰上嘴唇、話說出口以前,他就知道了。茶燙了他的嘴,提醒自己還活著,卻失去了母親。
縱使不斷重複例行作息,卻還是沒能保護母親。他事後回想,是不是哪一項沒做好?是不是那天早晨數錯了數?當初如果往好幾種項目再添個動作,或許就能扭轉一切?如今都已無關緊要。母親已經走了。早該待在家裡的。人在學校時,老是擔心她,因為若不在她身邊,她的存在就越出控制範圍之外。那套例行程序在學校不管用。學校有其規則和作息,自己這套就更難實施。大衛想拿學校那套來頂替,可是畢竟不同。現在母親就為這付出了代價。
因深感失敗而羞愧不已,大衛這才哭了起來。
接下來幾天,印象只是一片模糊。鄰居和親友來去紛紛,高大陌生的男士們搓搓他的頭,遞給他一先令;著黑洋裝的胖女士們哭著將大衛擁入胸懷,聞到的盡是她們的香水和樟腦丸味。他被擠進客廳角落裡跟著熬夜,大人一個個輪流談起的母親,卻是他從不認識的人、個人過往與他完全不同路的奇怪人物。例如:小時候,母親的姊姊過世時,她就是不哭,因為不肯相信對她而言那樣珍貴的人竟會永遠消失不復返。少女時期犯了小過,她爸爸一時之間失去耐性,揚言要把她交給吉普賽人,她於是逃家一天……長大後,成了身著亮紅色洋裝的美麗女郎,而大衛的爸爸從情敵面前大剌剌把她給偷了走。婚禮那天,她身穿白色婚紗,美麗動人,拇指卻讓玫瑰刺傷,在禮服上留下了眾目共睹的血斑。
大衛終於睡著,夢見自己成了這些故事的一部分,得以參與母親生命的每一階段。他不再只是耳聞過往故事的小孩,而是在場目睹了那一切。
大衛最後一次見到母親,是蓋棺之前、在葬儀社裡。看來雖有些不同,但仍是她原來的樣子──從前的她,那個受病魔侵蝕之前的她。她臉上有妝,就像上教堂做禮拜或跟爸爸出外用餐看電影那樣。她換上了最愛的那件藍洋裝,雙手交疊在肚腹上,手指交纏著玫瑰念珠,戒指都取掉了,雙唇紅通通的。大衛站著俯望她,手指碰碰她的手。摸起來好冷,也有些潮濕。
爸爸來到他身旁。只剩他倆還沒離開這房間。其他人都到外頭去了。車子在外等著載大衛和爸爸到教堂去。那車又大又黑。駕車的男人頭戴尖帽、毫無笑顏。
「大衛,你可以親親她當作道別。」大衛抬眼望著爸爸,他雙眼微濕、眼眶紅腫。母親過世第一天,爸爸就哭過了。那時大衛自學校返家,爸爸一把擁住他,向他保證一切終將好轉。在那之後,爸爸便沒再流淚,直到此刻。大衛望著望著,一顆豆大的淚湧起,緩緩地、幾乎有些彆扭地,滑落臉頰。他回身向母親,身子探進棺柩,吻了她臉頰。她身上有股化學味,還有別的;別的什麼,大衛不願多想──他在媽媽的唇上嚐到了。
「再見了,媽媽。」他輕聲說。雙眼刺痛。他想做些事情,可又不知道該做什麼。
爸爸一手搭上了大衛的肩,彎下身來輕柔吻了媽媽的唇,臉的一側貼上她的臉頰,喃喃說了些大衛聽不清的話,而後與大衛離開了房間。棺柩由禮儀師和助手抬著再度出現時,棺蓋已經闔上。唯一看得出大衛母親躺在裡頭的標示,就是棺蓋上刻著名字和生卒年月的那塊小金屬片。那晚,母親獨自留在教堂裡。如果可以,大衛情願伴著她。不知媽媽寂不寂寞?不知她是否清楚自己身在何處?不知她是否已到天堂,或者得等牧師最後祝禱、棺木入土後,才能上天堂?他實在不願想像媽媽一人孤伶伶的,讓木頭、黃銅和釘子封牢在裡面,可是他沒辦法跟爸爸開口談這事。爸爸不會懂,況且也無濟於事。既然沒辦法獨自待在教堂裡,他索性往房裡去,試著想像母親的處境。他將窗簾闔攏,把門關上,讓房裡盡可能漆黑無光,接著爬進床底。
床本身就低,床底下的空間更窄。由於位在房間角落,大衛便盡量靠邊擠,直到左手貼上牆,眼睛緊緊閉上,躺著動也不動。過了一會兒,他想抬起頭,可一抬頭就撞上支撐床墊的床板;他硬推,床板仍牢牢釘在原位。他雙手往上推,想把床抬起來,可是太重了。他聞到塵埃和尿壺的氣味,嗆咳起來,不禁流淚。他決定從床底下脫身,可把自己拖出來比挪進現在的位置還難。他打了噴嚏,頭撞上床底,又是一陣痛擊。他開始慌張,赤著腳速速踢掃,希望能在木板地上有些抓力。他朝上伸手,藉床板使力,將自己一路拉出,直到足夠靠近床緣,能再擠出身子為止。他蹣跚站起,傾靠著牆深深喘息。
原來死亡就像這樣:困身於小小空間裡,讓巨大重量給制住,直到永永遠遠。
大衛的母親在一月的某個早晨下葬。地面冷硬,弔喪者皆戴著手套、身披大衣。將棺柩往土穴裡放時,棺木看來短得過分。母親活著的時候總是顯得那麼高身,可死亡把她縮小了。
往後幾週,大衛將自己放逐在書本裡,因為他對媽媽的記憶,與書籍、閱讀交纏不分。原屬於媽媽的書,親友挑了些「適合」的傳給了大衛。他意識到自己啃著讀不懂的小說,唸著不大押韻的詩。有時他會拿去問爸爸,但是爸爸對書本似乎興趣缺缺。在家裡的時間,爸爸總一頭栽進報紙裡,執迷於現代世界的炎涼浮沈,菸斗的縷縷煙霧自報紙上方升起,好似印地安人發出的訊號。希特勒的軍隊橫掃歐陸,進擊英國本土的威脅愈來愈可能成真,讓爸爸比以往更放不下了。媽媽說過,爸爸以前閱書無數,後來卻擺脫了沈浸於故事裡的習慣。如今他偏好有長長印刷欄位的報紙,字字以手工精心編排而成,創造出某種上了報攤就幾乎頓失意義的東西;等到人閱讀時,裡頭的新聞早已成了凋零中的舊聞,早被報外世界的事件迎頭趕上。
書本裡頭的故事痛恨報紙裡的故事,大衛的媽媽會這樣說。報紙上的故事像是剛捕獲的魚,只有在新鮮期才值得一顧,保鮮期卻不持久。它們像街頭叫賣晚報的頑童,盡是大呼小叫、死纏爛打;而故事──真正的故事,正統的、出於想像的故事,好似藏書豐富的圖書館裡,那不苟言笑卻熱心助人的館員。報紙故事跟煙霧一樣虛空不實,壽命跟蜉蝣一般短;它們不會生根,反倒像野草一般沿地蔓生,從更值得青睞的故事那兒盜走陽光。爸爸的心思總讓那些競相爭鳴的尖銳聲音占據,就算將注意力轉向某個聲音讓它靜下,也隨即讓下一波喧譁取代。媽媽總是面帶微笑,悄聲跟大衛說這些話;而爸爸明知兩人正談著他,卻沈著臉咬菸斗,不願讓他們因為成功惹毛了自己而竊喜。
於是,護衛媽媽書本的重任就落在大衛身上。他把母親遺留下的書跟當初為他採買的放在一起。這些關於騎士、士兵、惡龍、海怪等傳說,或是民間傳奇、童話故事,都是母親在少女時期鍾愛的故事。疾病逐漸控制她、令她動彈不得後,換大衛唸書給她聽。病痛把她的嗓音減為呢喃低語,將她的呼息化為舊沙紙摩擦腐木的粗嘎聲,直到最後實在過於費力,便不再呼吸。母親過世後,他想避開這些老故事,因為故事跟母親之間的連結那樣深,他實在無法欣快閱讀。可是這些故事可不肯輕易被否決,開始呼喚大衛。它們似乎在大衛身上認出(或許他自己也漸漸認為)好奇、富創造力的特質。他聽到故事說話的聲音:一開始只是輕聲細語,接著便放大音量、逼人留神。
這些故事很古老,跟人一樣。就因它們威力十足,始能留存至今。就算將書本扔到一邊去,故事的情節仍會在腦裡迴盪不去。它們是由現實跳脫而出,卻也自成另一個世界,古老又怪異,令它們的存在得以獨立於書頁之外。媽媽曾告訴他,這些老故事的世界與我們的世界平行共存;偶爾,分隔這兩個世界的牆變得薄弱,兩者便開始融而為一。屆時,麻煩因之啟動。
屆時,壞事就要降臨。
屆時,駝背人開始出現在大衛周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