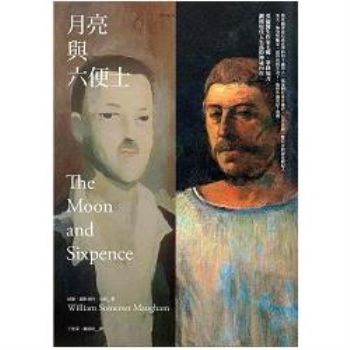第21章
我讓他領著來到一間餐館,不過我在路上買了份報紙。點好餐,我就把報紙架在一只聖‧加爾米耶酒瓶上開始看。我們沉默的吃完了飯,我可以感覺到他一次又一次的看我,但我沒理他。我就是要故意逼他跟我說話。
「報上有什麼消息嗎?」我們這頓安靜的晚餐快結束時,他終於開口。
從他的語調,我似乎已聽出微微的怒氣。
「我喜歡看劇評。」我說。
我把報紙摺好放旁邊。
「我吃飽了。」他說。
「我想我們可以在這兒喝杯咖啡,你覺得呢?」
「好。」
我們點起雪茄。我抽著雪茄,一句話也沒說。我發現他的視線不時停在我身上,眼裡帶著隱隱笑意。我耐心的繼續等待。
「自從上次我見到你之後,你都做了些什麼?」最後他問。
我也沒有太多經歷可說。我就是努力工作,沒什麼新奇的事情,這個那個都試試,將書本和人身上學到的知識慢慢積累下來。至於史崔克蘭做了什麼事,我很當心的一句話也不問,擺出對他完全不感興趣的樣子。這樣的堅持最終獲得了回報,他開始說起自己的事,但他原本就不擅表達,對自己過去的經歷只能說個大概,我得運用想像力才能補足那些片段之間的空白(沒辦法更深入了解一個這麼讓我感興趣的對象實在太作弄人了,簡直像從斷簡殘編建構出整部作品的全貌)。從他的話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一直在各式各樣的困頓中掙扎,但我發現大多數人覺得可怕的這種生活,對他卻沒有絲毫影響。史崔克蘭和大部分英國人最大的不同在於,他一點也不在乎生活舒不舒服,老住破爛房間不影響他的心情,身邊也不需要什麼漂亮擺飾。我想他從來也沒注意到,我第一次去拜訪他時,他房裡那面牆的牆紙有多髒。他不需要舒適的扶手椅,硬邦邦直挺挺的椅子他反而坐得自在。他胃口很好,但吃什麼對他都沒有差別,對他而言,他狼吞虎嚥的只是一種能吃的東西,為的是不讓肚子餓得發疼,而一旦斷了糧,他似乎也頗有挨餓的能耐。我得知他曾有半年時間,每天只靠一條麵包一瓶牛奶過日子。他是個重視身體感官的人,卻又對美食聲色這類享受全然不在意。他並不把貧窮當成苦難,他過的是一種完全精神至上的生活方式,令人印象深刻。
他從倫敦來的時候身上帶了些錢,用光之後也不沮喪。他沒賣畫(這方面我想他幾乎沒試),他開始找門路想賺點錢。他用一種面無表情的幽默口氣告訴我,他當過一陣子嚮導,專為那些想看看巴黎夜生活長什麼樣的倫敦佬帶路。就他那種凡事冷嘲熱諷的個性,這倒是個適合的工作,於是他莫名其妙的把這個城市裡最聲名狼藉的幾個區都摸熟了。他告訴我,他會在瑪德蓮大道上走來走去走很久,希望找到一些想瞧瞧違法勾當的英國人,假如是喝得爛醉的那種就更好了。如果走運,他可以賺個一小筆錢,但到最後,他已經衣衫襤褸到會嚇著遊客的地步,再也找不到人願意冒險把自己的旅行託付給他。接著,他偶然得到了一個翻譯廣告的工作,那是一家打算進軍英國醫藥界的專利藥商,而碰上公司罷工時,他就去幫別人漆房子。
拚命賺錢的同時,他從未停止畫畫,只是很快就厭倦了畫室,所以一切都自己來。他一度窮到連畫布和顏料都買不起,而這正是他最需要的東西。從他的敘述中,我發現他畫畫陷入了嚴重困境,他不願接受別人指導,只能花費大量時間獨自尋找解決技術問題的方法,然而這些技術問題早已被前幾代的畫家一個個解決了。他想把某種東西畫出來,我不知道是什麼,也許連他自己也不清楚,而我之前覺得他是被什麼東西附了身的印象,這次更強烈了。他的想法似乎都不合常理。我感覺他不願把畫拿出來,是因為他其實對畫本身沒興趣。他活在一個夢境裡面,現實生活的一切對他都沒有意義。我可以感覺到,他作畫時會將自己內心激情的那一面完全發揮出來,無視周遭的事物,竭盡全力把靈魂裡所見的事物揮灑在畫布上。然後,等到過程結束(也許這兒指的並不是把畫畫完,因為我知道他其實很少真的完成一幅畫),熱情燃燒完,他對那幅畫也就失去了興趣。他對自己的作品從沒滿意過,似乎和他心中揮之不去的景象相比,那些畫完全不值一提。
「為什麼你不把畫送去展覽呢?」我問,「我想你會願意聽聽大家的看法。」
「是你的話,你會聽?」
他灌注在這幾個字裡的鄙視意味,簡直難以形容。
「你不想成名嗎?大部分藝術家還是在意這件事的。」
「幼稚的傢伙。如果一個人的看法你都不當回事,一群人的看法幹嘛在乎?」
「不是每個人都這麼理性的。」我笑著說。
「名氣這種東西,是誰搞出來的?評論家、作家、證券經紀人,還有女人。」
「但是,想到那些你不認識、沒見過的陌生人,從你筆下的作品接收到你想傳達的感情,為此有時低迴有時激昂,難道你不覺得高興嗎?每個人都喜歡權力,能讓人們的靈魂隨自己的意思悲憫或恐慌,我實在想不出有什麼方式比這個更神奇的。」
「根本就是鬧劇。」
「那你為什麼還在乎自己畫得好還壞?」
「我一點都不在乎。我只是想把我看見的畫下來。」
「如果我在一個荒島上,很確定除了我自己,沒有人能看見我寫的東西,我不知道還能不能繼續寫下去。」
史崔克蘭好一陣子沒接話,眼睛卻奇特的亮了起來,好像看見了某種燃燒他靈魂、令他狂喜的東西。
「有時我會想像一個無垠大海中的小島,我可以住在隱密的山谷裡,安安靜靜的,四周長滿了奇特的樹。我想,我可以在那兒找到我要的東西。」
這並不是他的原話。他用了許多手勢當形容詞,而且還斷斷續續,這是我推敲他的意思後,用自己的話講出來的。
「回想這五年,你覺得值得嗎?」我問。
他看著我,我看得出他不懂我在問什麼,我解釋給他聽。
「你放棄了一個舒服的家,以及一般人都會覺得幸福的生活。以前你事業那麼成功,現在你在巴黎的生活糟到極點。如果可以重新來過,你還會做同樣的選擇嗎?」
「會。」
「你知道你完全沒問你妻子兒女的近況嗎?你從來沒想過他們嗎?」
「沒。」
「我希望你他媽的別再用一個字回答我。給他們造成這麼大的痛苦,難道你從來沒後悔過?」
他綻開嘴角笑了,搖搖頭。
「我本來以為有時你還是會不禁想起過去。我不是指過去的七八年,而是更久以前,當你第一次見到你太太,愛上她,然後和她結婚的時候。當年你第一次把她擁在懷裡,那種喜悅難道你一點都不記得了嗎?」
「我不想過去,我唯一在乎的是永恆的現在。」
他的回答讓我思考了一陣。也許說得並不清楚,但我想我稍稍懂得他的意思了。
「你快樂嗎?」我問。
「是。」
我沉默了。我看著他,陷入沉思。他也看著我,沒多久眼裡又閃起嘲諷的光芒。
「恐怕你對我很難苟同啊?」
「胡說,」我立刻回他,「我對大蟒蛇的行為沒有意見,相反的,牠的心理活動倒頗吸引我。」
「所以你對我感興趣,是出自純專業眼光考量?」
「純專業眼光。」
「你確實不該對我有意見才對,你這人個性也很卑劣。」
「也許就是這樣,所以你跟我在一起真是如沐春風啊。」我回敬他。
他乾笑幾聲,什麼也沒說。我真希望我有辦法形容他的笑容。我不覺得他的笑容吸引人,但他一笑,那張素來陰沉的臉便瞬間亮了,表情完全不同,看上去有種無害的狡獪。他笑起來很慢,從眼睛笑起,有時笑容隱去前的最後一抹痕跡也是在眼睛。那笑容非常肉慾,既不殘忍,也不善良,讓人想起森林之神薩堤兒那充滿獸性的笑。這笑容讓我問了他一個問題:
「你到巴黎後,沒談過戀愛嗎?」
「我才沒空搞那些無聊事。生命太短,要兼顧戀愛和藝術,時間不夠用。」
「你的樣子可不像個隱士。」
「談戀愛那些事都讓我想吐。」
「人性很麻煩,是吧?」我說。
「幹嘛看著我偷笑?」
「因為我不相信你。」
「那你就是個該死的笨蛋。」
我停了一下,然後用銳利的目光盯著他。
「騙我究竟對你有什麼好處?」我說。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微笑。
「讓我告訴你吧。在我的想像裡,你腦子裡好幾個月都沒想過那檔事,你幾乎可以說服自己已經一勞永逸擺脫它了。你為這份自由歡欣雀躍,你覺得終於完全掌握了自己的靈魂,你眼前繁星環繞,彷彿自己也在群星間漫步。然後,你突然忍不下去了,這才發現自己原來自始至終雙腳都陷在爛泥裡,你好想就這樣躺進泥裡翻滾。於是你找了某個粗俗、下流又淫亂的女人,全身散發出性的噁心氣味的牲畜般生物,接著你就像頭野獸一樣撲到她身上。你拚命灌酒,直到酒精矇蔽你的雙眼,再也看不見這瘋狂的一切。」
他動也不動的盯著我。我毫不畏懼的迎上他的目光,一個字一個字的說。
「接著我要告訴你的事,聽起來一定很奇怪。完事之後,你會感覺自己超乎想像的純淨。你覺得自己的精神脫離了肉體,不再受形體束縛。你彷彿可以碰觸到美,彷彿那是個確實摸得到的東西。你覺得自己和吹過的微風、新葉初綻的樹木,以及漾著彩虹波光的河流,都成了心靈至交。你覺得自己跟上帝一樣。你能跟我解釋這是為什麼嗎?」
他定定的看著我,直到我說完才移開目光。他臉上有種奇特的表情,那是一種也許只有被嚴刑拷打至死的男人臉上才會出現的神情。他什麼也沒說,我明白,我們這場對話已經結束了。
我讓他領著來到一間餐館,不過我在路上買了份報紙。點好餐,我就把報紙架在一只聖‧加爾米耶酒瓶上開始看。我們沉默的吃完了飯,我可以感覺到他一次又一次的看我,但我沒理他。我就是要故意逼他跟我說話。
「報上有什麼消息嗎?」我們這頓安靜的晚餐快結束時,他終於開口。
從他的語調,我似乎已聽出微微的怒氣。
「我喜歡看劇評。」我說。
我把報紙摺好放旁邊。
「我吃飽了。」他說。
「我想我們可以在這兒喝杯咖啡,你覺得呢?」
「好。」
我們點起雪茄。我抽著雪茄,一句話也沒說。我發現他的視線不時停在我身上,眼裡帶著隱隱笑意。我耐心的繼續等待。
「自從上次我見到你之後,你都做了些什麼?」最後他問。
我也沒有太多經歷可說。我就是努力工作,沒什麼新奇的事情,這個那個都試試,將書本和人身上學到的知識慢慢積累下來。至於史崔克蘭做了什麼事,我很當心的一句話也不問,擺出對他完全不感興趣的樣子。這樣的堅持最終獲得了回報,他開始說起自己的事,但他原本就不擅表達,對自己過去的經歷只能說個大概,我得運用想像力才能補足那些片段之間的空白(沒辦法更深入了解一個這麼讓我感興趣的對象實在太作弄人了,簡直像從斷簡殘編建構出整部作品的全貌)。從他的話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一直在各式各樣的困頓中掙扎,但我發現大多數人覺得可怕的這種生活,對他卻沒有絲毫影響。史崔克蘭和大部分英國人最大的不同在於,他一點也不在乎生活舒不舒服,老住破爛房間不影響他的心情,身邊也不需要什麼漂亮擺飾。我想他從來也沒注意到,我第一次去拜訪他時,他房裡那面牆的牆紙有多髒。他不需要舒適的扶手椅,硬邦邦直挺挺的椅子他反而坐得自在。他胃口很好,但吃什麼對他都沒有差別,對他而言,他狼吞虎嚥的只是一種能吃的東西,為的是不讓肚子餓得發疼,而一旦斷了糧,他似乎也頗有挨餓的能耐。我得知他曾有半年時間,每天只靠一條麵包一瓶牛奶過日子。他是個重視身體感官的人,卻又對美食聲色這類享受全然不在意。他並不把貧窮當成苦難,他過的是一種完全精神至上的生活方式,令人印象深刻。
他從倫敦來的時候身上帶了些錢,用光之後也不沮喪。他沒賣畫(這方面我想他幾乎沒試),他開始找門路想賺點錢。他用一種面無表情的幽默口氣告訴我,他當過一陣子嚮導,專為那些想看看巴黎夜生活長什麼樣的倫敦佬帶路。就他那種凡事冷嘲熱諷的個性,這倒是個適合的工作,於是他莫名其妙的把這個城市裡最聲名狼藉的幾個區都摸熟了。他告訴我,他會在瑪德蓮大道上走來走去走很久,希望找到一些想瞧瞧違法勾當的英國人,假如是喝得爛醉的那種就更好了。如果走運,他可以賺個一小筆錢,但到最後,他已經衣衫襤褸到會嚇著遊客的地步,再也找不到人願意冒險把自己的旅行託付給他。接著,他偶然得到了一個翻譯廣告的工作,那是一家打算進軍英國醫藥界的專利藥商,而碰上公司罷工時,他就去幫別人漆房子。
拚命賺錢的同時,他從未停止畫畫,只是很快就厭倦了畫室,所以一切都自己來。他一度窮到連畫布和顏料都買不起,而這正是他最需要的東西。從他的敘述中,我發現他畫畫陷入了嚴重困境,他不願接受別人指導,只能花費大量時間獨自尋找解決技術問題的方法,然而這些技術問題早已被前幾代的畫家一個個解決了。他想把某種東西畫出來,我不知道是什麼,也許連他自己也不清楚,而我之前覺得他是被什麼東西附了身的印象,這次更強烈了。他的想法似乎都不合常理。我感覺他不願把畫拿出來,是因為他其實對畫本身沒興趣。他活在一個夢境裡面,現實生活的一切對他都沒有意義。我可以感覺到,他作畫時會將自己內心激情的那一面完全發揮出來,無視周遭的事物,竭盡全力把靈魂裡所見的事物揮灑在畫布上。然後,等到過程結束(也許這兒指的並不是把畫畫完,因為我知道他其實很少真的完成一幅畫),熱情燃燒完,他對那幅畫也就失去了興趣。他對自己的作品從沒滿意過,似乎和他心中揮之不去的景象相比,那些畫完全不值一提。
「為什麼你不把畫送去展覽呢?」我問,「我想你會願意聽聽大家的看法。」
「是你的話,你會聽?」
他灌注在這幾個字裡的鄙視意味,簡直難以形容。
「你不想成名嗎?大部分藝術家還是在意這件事的。」
「幼稚的傢伙。如果一個人的看法你都不當回事,一群人的看法幹嘛在乎?」
「不是每個人都這麼理性的。」我笑著說。
「名氣這種東西,是誰搞出來的?評論家、作家、證券經紀人,還有女人。」
「但是,想到那些你不認識、沒見過的陌生人,從你筆下的作品接收到你想傳達的感情,為此有時低迴有時激昂,難道你不覺得高興嗎?每個人都喜歡權力,能讓人們的靈魂隨自己的意思悲憫或恐慌,我實在想不出有什麼方式比這個更神奇的。」
「根本就是鬧劇。」
「那你為什麼還在乎自己畫得好還壞?」
「我一點都不在乎。我只是想把我看見的畫下來。」
「如果我在一個荒島上,很確定除了我自己,沒有人能看見我寫的東西,我不知道還能不能繼續寫下去。」
史崔克蘭好一陣子沒接話,眼睛卻奇特的亮了起來,好像看見了某種燃燒他靈魂、令他狂喜的東西。
「有時我會想像一個無垠大海中的小島,我可以住在隱密的山谷裡,安安靜靜的,四周長滿了奇特的樹。我想,我可以在那兒找到我要的東西。」
這並不是他的原話。他用了許多手勢當形容詞,而且還斷斷續續,這是我推敲他的意思後,用自己的話講出來的。
「回想這五年,你覺得值得嗎?」我問。
他看著我,我看得出他不懂我在問什麼,我解釋給他聽。
「你放棄了一個舒服的家,以及一般人都會覺得幸福的生活。以前你事業那麼成功,現在你在巴黎的生活糟到極點。如果可以重新來過,你還會做同樣的選擇嗎?」
「會。」
「你知道你完全沒問你妻子兒女的近況嗎?你從來沒想過他們嗎?」
「沒。」
「我希望你他媽的別再用一個字回答我。給他們造成這麼大的痛苦,難道你從來沒後悔過?」
他綻開嘴角笑了,搖搖頭。
「我本來以為有時你還是會不禁想起過去。我不是指過去的七八年,而是更久以前,當你第一次見到你太太,愛上她,然後和她結婚的時候。當年你第一次把她擁在懷裡,那種喜悅難道你一點都不記得了嗎?」
「我不想過去,我唯一在乎的是永恆的現在。」
他的回答讓我思考了一陣。也許說得並不清楚,但我想我稍稍懂得他的意思了。
「你快樂嗎?」我問。
「是。」
我沉默了。我看著他,陷入沉思。他也看著我,沒多久眼裡又閃起嘲諷的光芒。
「恐怕你對我很難苟同啊?」
「胡說,」我立刻回他,「我對大蟒蛇的行為沒有意見,相反的,牠的心理活動倒頗吸引我。」
「所以你對我感興趣,是出自純專業眼光考量?」
「純專業眼光。」
「你確實不該對我有意見才對,你這人個性也很卑劣。」
「也許就是這樣,所以你跟我在一起真是如沐春風啊。」我回敬他。
他乾笑幾聲,什麼也沒說。我真希望我有辦法形容他的笑容。我不覺得他的笑容吸引人,但他一笑,那張素來陰沉的臉便瞬間亮了,表情完全不同,看上去有種無害的狡獪。他笑起來很慢,從眼睛笑起,有時笑容隱去前的最後一抹痕跡也是在眼睛。那笑容非常肉慾,既不殘忍,也不善良,讓人想起森林之神薩堤兒那充滿獸性的笑。這笑容讓我問了他一個問題:
「你到巴黎後,沒談過戀愛嗎?」
「我才沒空搞那些無聊事。生命太短,要兼顧戀愛和藝術,時間不夠用。」
「你的樣子可不像個隱士。」
「談戀愛那些事都讓我想吐。」
「人性很麻煩,是吧?」我說。
「幹嘛看著我偷笑?」
「因為我不相信你。」
「那你就是個該死的笨蛋。」
我停了一下,然後用銳利的目光盯著他。
「騙我究竟對你有什麼好處?」我說。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微笑。
「讓我告訴你吧。在我的想像裡,你腦子裡好幾個月都沒想過那檔事,你幾乎可以說服自己已經一勞永逸擺脫它了。你為這份自由歡欣雀躍,你覺得終於完全掌握了自己的靈魂,你眼前繁星環繞,彷彿自己也在群星間漫步。然後,你突然忍不下去了,這才發現自己原來自始至終雙腳都陷在爛泥裡,你好想就這樣躺進泥裡翻滾。於是你找了某個粗俗、下流又淫亂的女人,全身散發出性的噁心氣味的牲畜般生物,接著你就像頭野獸一樣撲到她身上。你拚命灌酒,直到酒精矇蔽你的雙眼,再也看不見這瘋狂的一切。」
他動也不動的盯著我。我毫不畏懼的迎上他的目光,一個字一個字的說。
「接著我要告訴你的事,聽起來一定很奇怪。完事之後,你會感覺自己超乎想像的純淨。你覺得自己的精神脫離了肉體,不再受形體束縛。你彷彿可以碰觸到美,彷彿那是個確實摸得到的東西。你覺得自己和吹過的微風、新葉初綻的樹木,以及漾著彩虹波光的河流,都成了心靈至交。你覺得自己跟上帝一樣。你能跟我解釋這是為什麼嗎?」
他定定的看著我,直到我說完才移開目光。他臉上有種奇特的表情,那是一種也許只有被嚴刑拷打至死的男人臉上才會出現的神情。他什麼也沒說,我明白,我們這場對話已經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