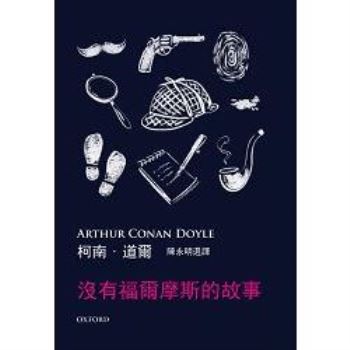那個小四方箱
「所有都上船了嗎?」船長問。
「都上船了。」大副回答。
「好。準備開船。」那是星期三早上九點鐘。停泊在波士頓碼頭的郵船「斯巴達」號,貨都進了倉,乘客都上了船,一切就緒,等候啟航。啟程的警笛響了兩次,最後的鐘聲亦已敲過,船頭轉向英國,機器噴出的蒸氣嘶嘶作響,表示為前面三千哩的旅程,一切都預備妥當了。繫船的纜索繃得緊緊,好像扯着蓄勢待發的灰犬的繮繩。
我不幸生來神經衰弱,自幼便性情孤僻,從事案牘勞形的文職工作,叫我變得更愛孤獨。站在這艘跨越大西洋的郵船後艙甲板上,我不住詛咒這個我無法迴避,將要把我帶回我祖先故鄉的旅程。水手的呼喊,船震盪的響聲,乘客的告別,群眾的歡呼,每個聲音都刺激我敏感的神經。我覺得很落寞。一種無以名狀,好像大禍臨頭的感受,把我整個人籠罩着。海面雖然風平浪靜,沒有任何東西惹起我這個喜歡陸地之人的不安,但我總覺得自己正站在一個巨大的,不能描述的危險邊緣。我知道像我這樣性格的人,往往會有特別的預感,而預感成真也並非不常見。有人說,這是因為我們有另一種感覺——精神上和未來的一種微妙的溝通。記得靈學大師饒梅爾先生說過,在他豐富的人生經驗中,我是他所遇見過,對靈界現象最敏感的人。無論怎樣,當我穿插於「斯巴達」號甲板上一堆堆有哭有笑的人群中,我的感覺絕對不是快樂。倘使當時預知以後十二小時內所要發生的情事,我一定會在這個最後的時刻,跳回岸上,逃離這艘可惡之船。
「時間到了!」船長說,「拍」的一聲關上了錶,放回口袋裏。「時間到了!」大副說。汽笛發出最後的長鳴,送船的親友紛紛趕着回岸。繫船的纜索解下了一條,吊板被推離岸邊,忽然駕駛室有人喊叫,兩個人匆匆地跑下碼頭。他們瘋狂地揮手,就像要把船停下來似的。「小心!」岸上的人群大喊。「拿穩!」船長叫道。「慢來!停下!扯起吊板!」那兩個人就在第二條纜索鬆開的時候跳上了船,在一下機器震動的響聲中船駛離了岸。甲板上,碼頭旁都響起了歡呼,在無數手帕的揮舞下,巨輪慢慢地,安詳地駛出了平靜的海灣。兩週的旅程開始了。乘客都忙着找他們的房間、行李。餐廳傳來開瓶的聲音,表示不少旅客採用這種人造的東西去消解他們的離愁。我環視船艙,試了解一下我的「旅伴」。他們都是一般的旅客,沒有任何突出的面孔。在這方面我可以說是個專家,因為人的臉容是我的專長。我對人面孔的特徵就如植物學家對花一樣,牢記不放,空閒的時候再細細分析,然後分類標記,收入我小小的人類學博物館裏面。可是這裏沒有甚麼值得記下來的。二十種不同類形,都想要看看「舊世界」的美國青年,一些和他們迥異,有體面的中年人,小撮神職人員,職業人士,年青婦女,旅行售貨員,英國特殊階級人士,和一般郵輪上常見的大雜燴。觀察完了,我回顧漸漸退逝的美國海岸線,記憶如雲升起,對這個我選擇寄居之地,心內湧生一種溫暖。船的一旁堆滿了等待運送到艙房的皮箱、行李。喜歡孤獨一人,我便走到這堆行李的後面,坐在它和船邊之間的一綑繩纜上,做起我憂鬱的白日夢來。
我被後面的輕聲說話喚醒:「這裏夠安靜了,坐下,我們可以安全地談談。」
從兩堆行李的夾縫望出去,那兩個最後趕上船的乘客就站在行李堆的另一邊。他們顯然沒有見到我,因為我是倚卧在行李堆的陰影之處。說話的是個瘦削的高個子,一把青黑色的鬍鬚,臉容蒼白,神色緊張,興奮。他的同伴是個血氣旺盛的小伙子,態度急躁、果敢,口裏咬着一支雪茄,左臂搭着一件厚厚,長長的大衣。他們左右觀望,像是要弄清楚周圍是否只有他們兩個人,我聽到另一個說:「這裏是最合適的地方了。」他們背着我坐到行李堆上。我雖然並不是有意,但卻成了他們對話的竊聽者。
「穆勒,」高個子說,「我們終於上到了船。」
「對啊,」那個叫穆勒的傢伙同意地說,「安全地上了船。」
「可是差點兒便趕不上了。」
「的確很險,范寧根。」
「如果上不到船便不曉得該怎麼辦了。」
「那我們的計劃便都泡湯了。」
「全都破壞了。」小個子一邊說,一邊拼命的吸了好幾分鐘他的雪茄。最後他說:「我把它帶來了。」
「讓我看看。」
「其他人看不到吧?」
「沒有人會看到的,他們都到下面的艙房去了。」「我們不能掉以輕心,因為事關重大。」穆勒一面說,一面展開搭在他左臂上的大衣,把裹在裏面一件深色的物體放到甲板上。只瞧了一眼,已經把我嚇得驚叫一聲,跳了起來。還好他們專注於前面的事物,沒有發覺,其實只要他們稍稍轉過頭來,便會看到,在那堆行李箱上,我那張瞪着他們滿是驚惶的面孔了。
從他們對話的開始,我已感到恐懼不安。看到面前的那件東西,更為我的感受提供了確據。那是一個方形,以深色木料製成的小箱,用銅片,一條條像肋骨一樣地綑着加固。箱子大概是一立方呎大小,像個載手槍的箱子,不過高很多。還有一個裝置,吸引了我的注意:箱蓋上,安有一個像手槍扳機一樣的東西,以彈簧和箱蓋連接。這個裝設,把原來看似載槍的箱子,變成了好像可以發射東西的槍枝。這個裝設的旁邊,有個方形的小洞。叫范寧根的那個傢伙把眼睛湊到洞上窺看了好幾分鐘,神色凝重,滿臉憂慮。最後說:「一切看來都似乎很正常。」
「我盡量沒有搖動它。」他的同伴說。
「這樣容易受損害的東西,要非常小心看待。穆勒,把需要的東西放些進去吧。」
小個子在口袋裏掏了好一陣子,拿出來一個小紙包,倒出半掬白色的晶體粒,傾注入那些方形小孔裏面。箱內發出卡咯卡咯的怪聲,兩個人都展露滿意的微笑。
「沒有甚麼大問題。」范寧根說。
「一切穩如泰出。」他的同伴回答說。
「小心!人來了。把它拿回我們的艙位。不要讓人懷疑我們在幹些甚麼,如果給他們誤觸開關,無意間啟動了整件事,那就糟糕了。」
「其實,無論誰觸發開關,都是一樣結果的。」穆勒說。
「觸動開關的人定必要大吃一驚,」高個子陰森地笑着說。「哈,哈!真想瞧瞧他們屆時的面色!我得讚讚我自己,我的工藝還不錯吧。」
「很不錯,」穆勒說。「聽說設計也是你的,對嗎?」
「是的,彈簧和活栓都是我想出來的。」
「你應該把它註冊專利。」
兩人又再發出一聲冷笑,然後拿起那件包銅的物體,用穆勒特大的大衣掩蓋起來。「下去吧,我們把他藏在床上,」范寧根說。「今晚之前還用不着它,放在那裏應該是很安全的。」他的同伴表示同意,兩人手牽手,攜着那神秘的小箱,沿着甲板走過通往下艙的閘門,便再看不到他們了。最後聽到的是范寧根:「小心,不要讓它撞到船上的欄墻」的反覆叮嚀。
也不曉得在那綑繩纜上坐了多久。暈船的感覺更增加了我聽到那番對話的恐懼。大西洋的波濤開始向郵船和其上的旅客展示它的威力了。我感到身心交瘁,快要崩潰,二副的聲音把我喚回來。「先生,可否從這裏移開,」他說。「我們要把這些木材挪走。」
他不客氣的率直,紅光滿面的健康臉容,就像是在嘲諷我當時的境況。如果我有勇氣,或者身強力壯,就真想揍他一頓。但以我當下的情況,我只能向這位老實的水手發出令他十分詫異惡狠狠的哼聲,然後從他身旁走到甲板的另一邊。我需要獨自一人,好好地想想正在我眼前醞釀的可怕罪行。一隻小艇正低低地懸掛在吊架上。我有了個主意,攀過船欄,鑽進那隻空艇,躺在艇底,把身體伸直。我上方就只看到蔚藍色的天空,偶然,因為船隨波低昂,還可以見到船的後桅。伴着我的就只有我的思想和暈船的不適。
我重溫所聽到那番可怕的對話。看看是否可以找到,和那明顯展示在我面前的,另一種不同的解釋。我不能不承認,似乎找不到。我努力把所有推論的表面證據臚列出來,看看推論可有甚麼地方出錯。沒有,毫無漏洞。他們最後一刻才跳上船,這樣,便逃過了行李驗查。「范寧根」〔一個常見的愛爾蘭姓氏〕這個名字,把他和愛爾蘭恐怖組織扯上了關係,而「穆勒」*,叫人想起社會主義和謀殺。加上他們鬼鬼祟祟的態度,認為如果趕不上船計劃便要泡湯,害怕被別人見到,還有那個裝有機關的神秘方形小箱——他們開玩笑地說要看看錯誤觸發機關的人的臉容,更是確鑿的證據。所有一切都只能帶到唯一的結論:他們是某種政治,或其他組織派來的亡命之徒,存心犧牲他們自己、船上的旅客、這艘郵輪,製造一件轟天大屠殺。他們傾進箱子裏面的白色晶粒應該是引爆的藥引,那些卡咯、卡咯的聲音大概是箱內精巧機器所發出來的。他們提到今晚,那是甚麼意思呢?是不是他們準備在旅程的第一個晚上便進行甚麼恐怖行動呢?越想越害怕,冷汗直冒,汗毛倒豎,連暈船也再感覺不到了。已經說過,在具體行動上我是個懦夫,在對錯的判斷上也是同樣的懦弱。像我這樣,兩方面都如此怯懦的人不曾多見。我認識很多人雖然很害怕身體上的傷害,但對自己內心的想法卻是十分自信、堅定。說來慚愧,我愛靜又內向的習性,任何可能引起他人注意的行為,我都異常地害怕,比諸身體受到損傷更甚。一般人在我現在的處境,都會把疑懼告訴船長,讓他處理。然而,對我來說,想到將會受到眾多人的關注、陌生人的盤查、以控訴人身份和那兩個陰謀者對質、就覺得討厭,難以接受的難堪。萬一我的推想是錯誤的,控訴被證實毫無根據,那將會是何等地尷尬呢?不,我還是拖延一下。先留心監察這兩個亡命之徒每一步的行動。無論做甚麼都比可能被證明出錯要好得多。
我忽然省悟此刻他們的陰謀可能已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這種緊張亢奮驅走了我的不適,我站起來,爬出小艇,一點暈眩的感覺都沒有了。我在甲板上蹌蹌踉踉地走,準備到下面的船艙,看看今早才見到的那兩個人在幹些甚麼。就在我抓着梯級扶手的當兒,忽然有人在我背上熱情地一拍,差點兒叫我狼狽地滾下梯級。「是你?哈門德?」一個似乎認識的聲音說。
「老天爺,」我回頭一望,說,「是你?迪克.梅頓!好傢伙,你好嗎?」
面對當前的困惑,這實在是意想不到的好運氣。迪克正是我所需要的人:心腸好,果斷,能幹。我可以把疑慮告訴他,曉得他一定能夠給我明智的指引,告訴我下一步應該怎樣走。從哈羅中學二年級開始,他便是我的顧問和保護人。他立刻便看出我有點兒不對勁了。「哈囉!」他和藹地說,「沒事兒吧?哈門德。看你面色白得像塊紙。暈船?」
「不,不是這回事,」我說。「扶我來回走一陣子吧,迪克,我有話想要跟你說。」靠着迪克魁梧的身軀走了一段時間,我才尋回足夠說話的勇氣。
「來支雪茄吧,」他說,打破了沉默。
「不,謝謝,」我說。「迪克,我們今天晚上都要變成死屍了。」
「這可不是現在不抽雪茄的理由啊,」迪克從他的濃眉下盯着我,冷靜地說。顯而易見,他是認為我有點兒神智不清。「不,」我繼續說。「我不是開玩笑;所說保證都是清醒、誠實的。我發現了一個可怕的陰謀,迪克,有人要摧毀這條船和她所有的搭客,」我把找到的證據一件一件,有系統地陳述出來。總結地說,「看,迪克,你怎樣想?更重要的是你認為我該怎樣做?」
我十分訝異,他竟然大笑起來。「如果不是你,而是其他的人告訴我這番話,我一定十分震驚。哈門德,你經常都是杯弓蛇影,覺得危機處處。我看你又故態復萌了。可還記得,中學時你矢言在學校的長房見到鬼魅,原來只不過是你自己在鏡子裏面的影像?嘿,」他繼續,「有甚麼理由有人要摧毀這條船?船上沒有重要的政治人物,乘客大半是美國人*。況且在今日這個理性的十九世紀,就是最狠毒的批發謀殺者,都不會把自己也變成受害人的。我想你一定攪錯了,把一部照相機,或同樣普通的物品,誤會為邪惡的機器。」
「絕不是這樣,先生,」我憤懣地說。「如果你不信,這是你的損失。我沒有誤會,也沒有誇張所聽到的。至於那個箱子,我從未見過像它一樣的東西。從他們的對話,對它那樣的小心,我確信裏面一定藏有件精巧的機器。」
「按你的推理,船上所有容易破碎的貨品都可以被看成水雷了。」
「那個人的名字是范寧根啊,」我繼續說。
「在法庭上,這證明不了甚麼,」迪克說,「不過,我已抽完雪茄。讓我們一起到下面去,喝瓶紅酒。你指給我看看誰是那兩個恐怖份子,如果他們在那裏的話。」
「好的,」我回答說;「今天無論如何,我都不會讓他們離開視線的了。不過可千萬別定睛望着他們,讓他們知道自己正在被監視。」
「相信我,」迪克說;「我會表現得如羊羔一樣的無知,溫馴。」說着,我們通過艙門,走進了船的餐廳。
不少乘客坐在中央那張大桌子的周圍,有忙着處理大大小小的行李箱的,有在吃午餐的,有在閱讀的,或以其他方法自娛的。但卻沒看到我們的目的物。我們沿着大廳走,察看旁邊的艙房,都沒有看到他們的影踪。「糟糕!」我想,「他們會不會,就在這一刻,在我們腳底下的機倉進行他們的勾當呢?」就算發現真的是這個最壞的可能,也要比處身當時的懸疑更好過。「部長,」迪克問,「還有其他乘客在甚麼地方嗎?」
「還有兩位在吸菸室,先生,」部長回答說。吸菸室是所漂亮舒適,毗鄰餐具室的房間。推門進去,我馬上鬆了口氣。首先映入眼簾的是范寧根那張血色全無的臉面,倔強的嘴巴,眨也不一眨的眼睛。他的同伴坐在他的對面。他們正喝着酒,前面桌子堆着一堆紙牌。我們進去的時候,他們正專注地在玩牌。我碰碰迪克表示他們便是我所說的那兩個人了,我們像是不經意地坐到他們的旁邊。這兩個陰謀者似乎沒有注意到我們的存在。我留心監視他們。他們正在玩一種叫「拿破崙」的牌戲*。兩個都是老手。我不得不佩服他們的鎮定。心內藏着這樣重大的秘密,竟然還是如此難得的「高章」。銀錢轉手很快;高個子的手氣不太好。最後他爆了一聲粗話,把牌摔到桌面,拒絕再玩下去了。
「所有都上船了嗎?」船長問。
「都上船了。」大副回答。
「好。準備開船。」那是星期三早上九點鐘。停泊在波士頓碼頭的郵船「斯巴達」號,貨都進了倉,乘客都上了船,一切就緒,等候啟航。啟程的警笛響了兩次,最後的鐘聲亦已敲過,船頭轉向英國,機器噴出的蒸氣嘶嘶作響,表示為前面三千哩的旅程,一切都預備妥當了。繫船的纜索繃得緊緊,好像扯着蓄勢待發的灰犬的繮繩。
我不幸生來神經衰弱,自幼便性情孤僻,從事案牘勞形的文職工作,叫我變得更愛孤獨。站在這艘跨越大西洋的郵船後艙甲板上,我不住詛咒這個我無法迴避,將要把我帶回我祖先故鄉的旅程。水手的呼喊,船震盪的響聲,乘客的告別,群眾的歡呼,每個聲音都刺激我敏感的神經。我覺得很落寞。一種無以名狀,好像大禍臨頭的感受,把我整個人籠罩着。海面雖然風平浪靜,沒有任何東西惹起我這個喜歡陸地之人的不安,但我總覺得自己正站在一個巨大的,不能描述的危險邊緣。我知道像我這樣性格的人,往往會有特別的預感,而預感成真也並非不常見。有人說,這是因為我們有另一種感覺——精神上和未來的一種微妙的溝通。記得靈學大師饒梅爾先生說過,在他豐富的人生經驗中,我是他所遇見過,對靈界現象最敏感的人。無論怎樣,當我穿插於「斯巴達」號甲板上一堆堆有哭有笑的人群中,我的感覺絕對不是快樂。倘使當時預知以後十二小時內所要發生的情事,我一定會在這個最後的時刻,跳回岸上,逃離這艘可惡之船。
「時間到了!」船長說,「拍」的一聲關上了錶,放回口袋裏。「時間到了!」大副說。汽笛發出最後的長鳴,送船的親友紛紛趕着回岸。繫船的纜索解下了一條,吊板被推離岸邊,忽然駕駛室有人喊叫,兩個人匆匆地跑下碼頭。他們瘋狂地揮手,就像要把船停下來似的。「小心!」岸上的人群大喊。「拿穩!」船長叫道。「慢來!停下!扯起吊板!」那兩個人就在第二條纜索鬆開的時候跳上了船,在一下機器震動的響聲中船駛離了岸。甲板上,碼頭旁都響起了歡呼,在無數手帕的揮舞下,巨輪慢慢地,安詳地駛出了平靜的海灣。兩週的旅程開始了。乘客都忙着找他們的房間、行李。餐廳傳來開瓶的聲音,表示不少旅客採用這種人造的東西去消解他們的離愁。我環視船艙,試了解一下我的「旅伴」。他們都是一般的旅客,沒有任何突出的面孔。在這方面我可以說是個專家,因為人的臉容是我的專長。我對人面孔的特徵就如植物學家對花一樣,牢記不放,空閒的時候再細細分析,然後分類標記,收入我小小的人類學博物館裏面。可是這裏沒有甚麼值得記下來的。二十種不同類形,都想要看看「舊世界」的美國青年,一些和他們迥異,有體面的中年人,小撮神職人員,職業人士,年青婦女,旅行售貨員,英國特殊階級人士,和一般郵輪上常見的大雜燴。觀察完了,我回顧漸漸退逝的美國海岸線,記憶如雲升起,對這個我選擇寄居之地,心內湧生一種溫暖。船的一旁堆滿了等待運送到艙房的皮箱、行李。喜歡孤獨一人,我便走到這堆行李的後面,坐在它和船邊之間的一綑繩纜上,做起我憂鬱的白日夢來。
我被後面的輕聲說話喚醒:「這裏夠安靜了,坐下,我們可以安全地談談。」
從兩堆行李的夾縫望出去,那兩個最後趕上船的乘客就站在行李堆的另一邊。他們顯然沒有見到我,因為我是倚卧在行李堆的陰影之處。說話的是個瘦削的高個子,一把青黑色的鬍鬚,臉容蒼白,神色緊張,興奮。他的同伴是個血氣旺盛的小伙子,態度急躁、果敢,口裏咬着一支雪茄,左臂搭着一件厚厚,長長的大衣。他們左右觀望,像是要弄清楚周圍是否只有他們兩個人,我聽到另一個說:「這裏是最合適的地方了。」他們背着我坐到行李堆上。我雖然並不是有意,但卻成了他們對話的竊聽者。
「穆勒,」高個子說,「我們終於上到了船。」
「對啊,」那個叫穆勒的傢伙同意地說,「安全地上了船。」
「可是差點兒便趕不上了。」
「的確很險,范寧根。」
「如果上不到船便不曉得該怎麼辦了。」
「那我們的計劃便都泡湯了。」
「全都破壞了。」小個子一邊說,一邊拼命的吸了好幾分鐘他的雪茄。最後他說:「我把它帶來了。」
「讓我看看。」
「其他人看不到吧?」
「沒有人會看到的,他們都到下面的艙房去了。」「我們不能掉以輕心,因為事關重大。」穆勒一面說,一面展開搭在他左臂上的大衣,把裹在裏面一件深色的物體放到甲板上。只瞧了一眼,已經把我嚇得驚叫一聲,跳了起來。還好他們專注於前面的事物,沒有發覺,其實只要他們稍稍轉過頭來,便會看到,在那堆行李箱上,我那張瞪着他們滿是驚惶的面孔了。
從他們對話的開始,我已感到恐懼不安。看到面前的那件東西,更為我的感受提供了確據。那是一個方形,以深色木料製成的小箱,用銅片,一條條像肋骨一樣地綑着加固。箱子大概是一立方呎大小,像個載手槍的箱子,不過高很多。還有一個裝置,吸引了我的注意:箱蓋上,安有一個像手槍扳機一樣的東西,以彈簧和箱蓋連接。這個裝設,把原來看似載槍的箱子,變成了好像可以發射東西的槍枝。這個裝設的旁邊,有個方形的小洞。叫范寧根的那個傢伙把眼睛湊到洞上窺看了好幾分鐘,神色凝重,滿臉憂慮。最後說:「一切看來都似乎很正常。」
「我盡量沒有搖動它。」他的同伴說。
「這樣容易受損害的東西,要非常小心看待。穆勒,把需要的東西放些進去吧。」
小個子在口袋裏掏了好一陣子,拿出來一個小紙包,倒出半掬白色的晶體粒,傾注入那些方形小孔裏面。箱內發出卡咯卡咯的怪聲,兩個人都展露滿意的微笑。
「沒有甚麼大問題。」范寧根說。
「一切穩如泰出。」他的同伴回答說。
「小心!人來了。把它拿回我們的艙位。不要讓人懷疑我們在幹些甚麼,如果給他們誤觸開關,無意間啟動了整件事,那就糟糕了。」
「其實,無論誰觸發開關,都是一樣結果的。」穆勒說。
「觸動開關的人定必要大吃一驚,」高個子陰森地笑着說。「哈,哈!真想瞧瞧他們屆時的面色!我得讚讚我自己,我的工藝還不錯吧。」
「很不錯,」穆勒說。「聽說設計也是你的,對嗎?」
「是的,彈簧和活栓都是我想出來的。」
「你應該把它註冊專利。」
兩人又再發出一聲冷笑,然後拿起那件包銅的物體,用穆勒特大的大衣掩蓋起來。「下去吧,我們把他藏在床上,」范寧根說。「今晚之前還用不着它,放在那裏應該是很安全的。」他的同伴表示同意,兩人手牽手,攜着那神秘的小箱,沿着甲板走過通往下艙的閘門,便再看不到他們了。最後聽到的是范寧根:「小心,不要讓它撞到船上的欄墻」的反覆叮嚀。
也不曉得在那綑繩纜上坐了多久。暈船的感覺更增加了我聽到那番對話的恐懼。大西洋的波濤開始向郵船和其上的旅客展示它的威力了。我感到身心交瘁,快要崩潰,二副的聲音把我喚回來。「先生,可否從這裏移開,」他說。「我們要把這些木材挪走。」
他不客氣的率直,紅光滿面的健康臉容,就像是在嘲諷我當時的境況。如果我有勇氣,或者身強力壯,就真想揍他一頓。但以我當下的情況,我只能向這位老實的水手發出令他十分詫異惡狠狠的哼聲,然後從他身旁走到甲板的另一邊。我需要獨自一人,好好地想想正在我眼前醞釀的可怕罪行。一隻小艇正低低地懸掛在吊架上。我有了個主意,攀過船欄,鑽進那隻空艇,躺在艇底,把身體伸直。我上方就只看到蔚藍色的天空,偶然,因為船隨波低昂,還可以見到船的後桅。伴着我的就只有我的思想和暈船的不適。
我重溫所聽到那番可怕的對話。看看是否可以找到,和那明顯展示在我面前的,另一種不同的解釋。我不能不承認,似乎找不到。我努力把所有推論的表面證據臚列出來,看看推論可有甚麼地方出錯。沒有,毫無漏洞。他們最後一刻才跳上船,這樣,便逃過了行李驗查。「范寧根」〔一個常見的愛爾蘭姓氏〕這個名字,把他和愛爾蘭恐怖組織扯上了關係,而「穆勒」*,叫人想起社會主義和謀殺。加上他們鬼鬼祟祟的態度,認為如果趕不上船計劃便要泡湯,害怕被別人見到,還有那個裝有機關的神秘方形小箱——他們開玩笑地說要看看錯誤觸發機關的人的臉容,更是確鑿的證據。所有一切都只能帶到唯一的結論:他們是某種政治,或其他組織派來的亡命之徒,存心犧牲他們自己、船上的旅客、這艘郵輪,製造一件轟天大屠殺。他們傾進箱子裏面的白色晶粒應該是引爆的藥引,那些卡咯、卡咯的聲音大概是箱內精巧機器所發出來的。他們提到今晚,那是甚麼意思呢?是不是他們準備在旅程的第一個晚上便進行甚麼恐怖行動呢?越想越害怕,冷汗直冒,汗毛倒豎,連暈船也再感覺不到了。已經說過,在具體行動上我是個懦夫,在對錯的判斷上也是同樣的懦弱。像我這樣,兩方面都如此怯懦的人不曾多見。我認識很多人雖然很害怕身體上的傷害,但對自己內心的想法卻是十分自信、堅定。說來慚愧,我愛靜又內向的習性,任何可能引起他人注意的行為,我都異常地害怕,比諸身體受到損傷更甚。一般人在我現在的處境,都會把疑懼告訴船長,讓他處理。然而,對我來說,想到將會受到眾多人的關注、陌生人的盤查、以控訴人身份和那兩個陰謀者對質、就覺得討厭,難以接受的難堪。萬一我的推想是錯誤的,控訴被證實毫無根據,那將會是何等地尷尬呢?不,我還是拖延一下。先留心監察這兩個亡命之徒每一步的行動。無論做甚麼都比可能被證明出錯要好得多。
我忽然省悟此刻他們的陰謀可能已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這種緊張亢奮驅走了我的不適,我站起來,爬出小艇,一點暈眩的感覺都沒有了。我在甲板上蹌蹌踉踉地走,準備到下面的船艙,看看今早才見到的那兩個人在幹些甚麼。就在我抓着梯級扶手的當兒,忽然有人在我背上熱情地一拍,差點兒叫我狼狽地滾下梯級。「是你?哈門德?」一個似乎認識的聲音說。
「老天爺,」我回頭一望,說,「是你?迪克.梅頓!好傢伙,你好嗎?」
面對當前的困惑,這實在是意想不到的好運氣。迪克正是我所需要的人:心腸好,果斷,能幹。我可以把疑慮告訴他,曉得他一定能夠給我明智的指引,告訴我下一步應該怎樣走。從哈羅中學二年級開始,他便是我的顧問和保護人。他立刻便看出我有點兒不對勁了。「哈囉!」他和藹地說,「沒事兒吧?哈門德。看你面色白得像塊紙。暈船?」
「不,不是這回事,」我說。「扶我來回走一陣子吧,迪克,我有話想要跟你說。」靠着迪克魁梧的身軀走了一段時間,我才尋回足夠說話的勇氣。
「來支雪茄吧,」他說,打破了沉默。
「不,謝謝,」我說。「迪克,我們今天晚上都要變成死屍了。」
「這可不是現在不抽雪茄的理由啊,」迪克從他的濃眉下盯着我,冷靜地說。顯而易見,他是認為我有點兒神智不清。「不,」我繼續說。「我不是開玩笑;所說保證都是清醒、誠實的。我發現了一個可怕的陰謀,迪克,有人要摧毀這條船和她所有的搭客,」我把找到的證據一件一件,有系統地陳述出來。總結地說,「看,迪克,你怎樣想?更重要的是你認為我該怎樣做?」
我十分訝異,他竟然大笑起來。「如果不是你,而是其他的人告訴我這番話,我一定十分震驚。哈門德,你經常都是杯弓蛇影,覺得危機處處。我看你又故態復萌了。可還記得,中學時你矢言在學校的長房見到鬼魅,原來只不過是你自己在鏡子裏面的影像?嘿,」他繼續,「有甚麼理由有人要摧毀這條船?船上沒有重要的政治人物,乘客大半是美國人*。況且在今日這個理性的十九世紀,就是最狠毒的批發謀殺者,都不會把自己也變成受害人的。我想你一定攪錯了,把一部照相機,或同樣普通的物品,誤會為邪惡的機器。」
「絕不是這樣,先生,」我憤懣地說。「如果你不信,這是你的損失。我沒有誤會,也沒有誇張所聽到的。至於那個箱子,我從未見過像它一樣的東西。從他們的對話,對它那樣的小心,我確信裏面一定藏有件精巧的機器。」
「按你的推理,船上所有容易破碎的貨品都可以被看成水雷了。」
「那個人的名字是范寧根啊,」我繼續說。
「在法庭上,這證明不了甚麼,」迪克說,「不過,我已抽完雪茄。讓我們一起到下面去,喝瓶紅酒。你指給我看看誰是那兩個恐怖份子,如果他們在那裏的話。」
「好的,」我回答說;「今天無論如何,我都不會讓他們離開視線的了。不過可千萬別定睛望着他們,讓他們知道自己正在被監視。」
「相信我,」迪克說;「我會表現得如羊羔一樣的無知,溫馴。」說着,我們通過艙門,走進了船的餐廳。
不少乘客坐在中央那張大桌子的周圍,有忙着處理大大小小的行李箱的,有在吃午餐的,有在閱讀的,或以其他方法自娛的。但卻沒看到我們的目的物。我們沿着大廳走,察看旁邊的艙房,都沒有看到他們的影踪。「糟糕!」我想,「他們會不會,就在這一刻,在我們腳底下的機倉進行他們的勾當呢?」就算發現真的是這個最壞的可能,也要比處身當時的懸疑更好過。「部長,」迪克問,「還有其他乘客在甚麼地方嗎?」
「還有兩位在吸菸室,先生,」部長回答說。吸菸室是所漂亮舒適,毗鄰餐具室的房間。推門進去,我馬上鬆了口氣。首先映入眼簾的是范寧根那張血色全無的臉面,倔強的嘴巴,眨也不一眨的眼睛。他的同伴坐在他的對面。他們正喝着酒,前面桌子堆着一堆紙牌。我們進去的時候,他們正專注地在玩牌。我碰碰迪克表示他們便是我所說的那兩個人了,我們像是不經意地坐到他們的旁邊。這兩個陰謀者似乎沒有注意到我們的存在。我留心監視他們。他們正在玩一種叫「拿破崙」的牌戲*。兩個都是老手。我不得不佩服他們的鎮定。心內藏着這樣重大的秘密,竟然還是如此難得的「高章」。銀錢轉手很快;高個子的手氣不太好。最後他爆了一聲粗話,把牌摔到桌面,拒絕再玩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