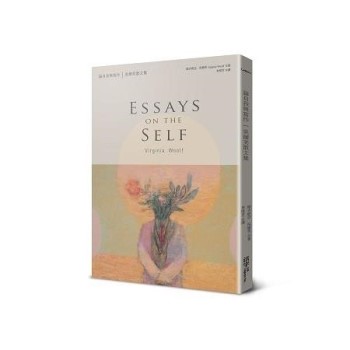現代小說
即使是以最鬆散自由的形式,要對現代小說提出任何的考察,難免都會有個先入為主的觀念,認為當代的藝術呈現和舊有的比起來多少都是種進步。或許可以這樣說,在只有簡單的技巧和古老原始素材可運用的情況下,菲爾丁(Fielding)寫得不錯,珍.奧斯婷(Jane Austen)更好,但他們的機遇和我們是不可同日而語的!而他們的傑作當然也就顯得有點太過簡單了。若是舉個例子,把文學和汽車製造過程做類比,雖然第一眼看起來有趣,但之後就再沒什麼可說了。雖然幾百年來我們對於製造機器了解不少,但是對於生產文學有多少認識倒是十分可議的。我們並沒有寫得比較好,只能說我們持續在做,一會兒往這個方向,一會兒往那個方向,如果從一個夠高的山頂來看,恐怕這整個軌跡不過是在轉圈兒罷了。就算連短暫地站上制高點都談不上。在平地上,人群之中,有半數都蒙了沙土而看不清,我們回首望向那些比較快樂的戰士,心裡不免有些嫉羨,他們可是打贏了仗,而且他們的成就是如此祥如自在,以至於我們忍不住想低聲地說他們打的仗可沒有我們這麼激烈。這當然得由文學史的學者去決定;得由他去說究竟我們現在是站在散文小說偉大時刻的起點、終點或中間,因為我們在平原上什麼也看不清。我們只知道有些善意和惡意刺激著我們,某些路徑似乎迎向了肥沃土壤,有些則走入塵土和沙漠;關於這一點或許不妨來討論一番。
我們只要稍稍審視一個普通人平常的一天,其心靈會接收到無數的印象——細瑣的、精彩的、稍縱即逝的,或是鋼鐵般堅利的刻骨銘心。這些印象來自四面八方,無數原子不斷湧向我們;這些原子變成了我們星期一或星期二的生活,重點總是跟之前不一樣;重要的時刻不是在這兒,而是在那兒;所以,如果一個作家是個自由人而不是奴隸,如果他可以選擇他寫什麼,而不是他必須寫什麼,如果他可以根據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傳統來寫作,那麼就不會有固定接受風格的情節、喜劇、悲劇、愛情或災難,或許也不會有人像龐德街裁縫師傅縫扣子那樣地來寫作了。人生並不是一系列對稱安排的眼鏡;人生是燦爛的光輝,從意識的開始到結束,半透明的封套包圍著我們。無論呈現出怎樣的脫離常軌或錯綜複雜,小說家的任務不正是要儘可能避免把怪異和外在混合在一起,去傳達這種變化的、未知的、不受限的精神嗎?我們祈求的不僅是勇氣和誠懇,我們要求的是,小說的題材如果要有說服力,總得和傳統有些不一樣。
――寫於1919年,收錄於《普通讀者》(1925)。
致年輕詩人的一封信
……拜託你行行好,在你未滿三十歲前,不要出版任何作品。
我很確定,這是非常重要的。我認為,我讀的這些詩絕大部分的缺點就在於,這些詩人太過年輕,一旦暴露在強烈的公開亮相之下,他們無法承受這樣的壓力。這把他們縮小到最緊縮的骨架,無論是在情感上或文字上,但這不應該是年輕人的特質。詩人寫得非常好;他是為了嚴格且聰明的大眾之眼而寫;如果再過十年,他不為了任何人而是為自己的眼睛而寫,那麼他不是可以寫得更好嗎!畢竟,從二十歲到三十歲(讓我再提到你的信),經歷的是情感最激烈的時刻。雨滴落下、翅膀飛馳、有人經過——我依稀記得,即使是最尋常的聲音和視野,都有能力讓一個人從狂喜的高度墜落到絕望的深淵。如果真實生命是如此極端,想像的生命應該能夠自由地跟隨。那麼就寫吧,你現在正年輕,可以盡情揮霍。無拘無束、感懷傷情,模仿雪萊、模仿塞謬爾.史邁爾斯 ;讓你每個衝動都能自由發揮;犯下所有風格、文法、品味和句法的錯誤;傾囊而出;盡情翻滾;釋放你的怒氣、愛、諷刺,用所有你想得到的文字,強迫也好創造也好,用所有可能的格律、散文、詩 ,或是順手拈來的胡言亂語。這樣你就學會了寫作。但是一旦你出版了,你的自由就會受到限制;你會想到人們會說些什麼;你應該為自己而寫,但是你卻會為別人而寫。限制你此時狂野的隨機無聊思緒有什麼好處呢,因為你也只有幾年可以這麼做,為了出版拘謹的實驗詩作選,浪費了你神聖的天賦?賺錢嗎?我們都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得到批評家的評語嗎?但是你的朋友所給予你的意見遠比那些評論家的看法要來得認真而有建設性。至於名聲,我求你看看那些名人;看看他們走進來濺起了多麼無趣的水花;觀察他們的虛張聲勢;他們故作先知的姿態;想像最偉大的詩人都是匿名的;想像莎士比亞對名聲如何不屑一顧;鄧恩如何把詩作丟進字紙簍裡;寫一篇散文,只要舉出一個例子是現代英國作家經歷過學徒和崇拜者、索取簽名者和要求訪問者、晚宴和午宴、讓歌手能夠立刻閉嘴停止歌唱的慶典和紀念會,而竟能倖存的。
――寫於 1931年,收錄於《蛾之死與其他散文》(1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