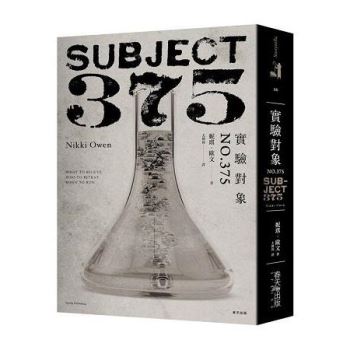1
坐在我對面的那名男子不動。他面朝前方,忍著沒咳嗽。太陽曬著這個房間,但即使我把襯衫拉鬆透風時,還是覺得熱氣刺人。我看著他。我不喜歡這樣:他,我,這裡,這個房間,這個……這個牢籠。我好想扯自己的頭髮,朝他、朝他們、朝全世界尖叫。然而我什麼都沒做,只是坐在那裡。牆上的時鐘發出滴答聲。
那男子把錄音筆放在桌上,然後毫無預兆地,忽然朝我露出大大的笑容。
「別忘了,」他說。「我來這裡是要幫助你的。」
我張嘴要說話,但腦中忽然靈光一閃,有個聲音悄悄說,開始!我不想理會那聲音。為了撫平心中高漲的情緒,我轉而試圖把注意力集中在別的事物上頭,任何事物都行。他的身高。他對那張椅子來說太高了。他駝著背,腹部下陷,雙腳交叉。以他一八八公分的身高和七十四公斤的體重,可以輕鬆跑一公里,也不會喘不過氣來。
那男人清了清嗓子,雙眼看著我。我艱難地吞嚥著。
「瑪麗亞,」他開口了。「我可以……」他結巴著,然後稍微湊近一點。「我可以喊你瑪麗亞嗎?」
我出自本能地用西班牙語回答。
「麻煩請說英語。」他說。
我咳了一聲。「可以。我叫瑪麗亞沒錯。」我的聲音有點顫抖,他聽得出來嗎?我得慢下來,心裡想著各種事實。他的指甲。很乾淨,認真洗刷過。他穿的襯衫是白色的,領口敞開。他的西裝是黑色的。布料很昂貴。羊毛的?除此之外,他穿著絲質襪子和真皮的平底便鞋。沒有磨損的痕跡。他整個人簇新得就像是從一本雜誌裡走出來似的。
他拿起一支筆,我大著膽子伸手去拿水杯。我緊握著玻璃杯,但還是有幾滴水不聽使喚,濺出了杯緣。我停住。雙手顫抖。
「你還好吧?」那男子問,但我沒回答。有個什麼不對勁。
我眨眨眼,視線模糊起來,一層薄薄的白色罩住我的雙眼,像一件斗篷,或是一個面具。我的眼皮開始顫動,心臟狂跳,腎上腺素不斷分泌。或許是因為跟他待在這個房間裡,或許是想到要跟一個陌生人講我的感覺,總之觸發了我內心深處的一段記憶,很可怕的記憶。
這種狀況之前發生過很多次。一開始那記憶搖晃著,不慌不忙。然後,才幾秒鐘,它就匆忙加速,完全形成了一個影像,彷彿一齣舞台劇在我面前出現。布幕升起,我在一間診療室裡。白色的牆,不鏽鋼,漿過的床單。天花板上排列著一根根長條燈管,發著亮光,照得我無可遁逃。然後,在前方,就像煙霧中出現的魔術師,那個有著黑色眼珠的醫師從遠處的門走進來。他戴著面具,手裡拿著一根注射針。
「哈囉,瑪麗亞。」
恐慌從我心底冒出來,像火山爆發的熔岩,快得我都擔心自己要爆炸了。那黑眼男走近了些,我開始發抖,想逃走,但我四肢被皮帶綁著。他的嘴唇往上翹,他在房間裡了,逼近我,他的氣息——菸草、大蒜、薄荷——吹在我臉上,我看得到他的鼻孔,而且我開始聽到自己尖叫著。另外還有別的,一個耳語:「他不是真實的。他不是真實的。」那耳語,盤旋在我腦海,拍著翅膀,逗留不去,然後就像一陣微風吹過般,在我的皮膚上留下一道雞皮疙瘩。這是正常的嗎?我環視周圍:玻璃小藥瓶、注射針、掛圖。我看著自己的雙手:年輕,沒有皺紋。我碰觸自己的臉:青春痘。不是我,不是現在的我。所以表示這一切都不存在。
就像蠟燭被吹熄般,那影像消失了,布幕落下。我的雙眼趕緊往下看,發現自己的每個指節都因為緊握玻璃杯而發白。我抬起眼睛,對面的人正盯著我看。
「怎麼了?」他說。
我吸了口氣,檢查自己所在的位置。我的鼻孔內、口腔裡仍有黑眼男的氣息,彷彿他真的來過。我設法拋開恐懼,然後緩緩放下玻璃杯,雙手扭絞在一起,緊握兩次。「我想起了一些事。」我停了一下說。
「真實的事情?」
「我不曉得。」
「這樣的狀況常常發生嗎?」
我猶豫了。他已經知道了嗎?我決定告訴他實話。「對。」
那男子看了我的雙手,然後轉頭打開一些影印檔案。
我雙眼瀏覽著他膝上的那些紙頁。資料,資訊。事實,真正的事實,全都是黑白的,清楚,沒有灰色地帶,沒有模稜兩可或隱藏的意義。我一定是專注在這個想法上,因為不知不覺間,我腦袋裡的資訊就脫口而出。
「影印機源起於一四四○年,」我說,雙眼看著他手裡的那些紙頁。
他抬頭看我。「你說什麼?」
「影印機——是古騰堡在一四四○年發明印刷術的時候開始萌芽的。」我吸了口氣。我的腦袋實在裝了太多資訊了,有時候就是會滿得溢出來。「古騰堡聖經,」我繼續說,「是第一種大量印刷的書。」我停下,等著,但那男人沒有反應。他又盯著我,雙眼瞇起來,成了兩道藍色的縫隙。我開始一腳輕敲地板,胸口一股熟悉的緊繃感擴散開來。為了紓解,我開始算。一、二、三、四……算到五,我看向窗子。平紋細布的窗簾鼓起。窗玻璃外有鐵窗格柵。窗子下方,三輛巴士經過,發出呼呼聲,吐出噪音、廢氣。我轉頭摸摸後頸的髮際線。汗水流過我的衣領。
「這裡好熱,」我說。「有電扇嗎?」
那男子放下紙頁。「據我所知,你記住資訊的能力是頂尖。」他瞇起眼睛。「你的智商很高。」他看看手上的紙,目光又回到我身上。「一百八十一。」
我沒動。這些資訊不是一般人會知道的。
「我的職責是研究病人,」他繼續說,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他身體前傾。「我知道很多關於你的事情。」他暫停一下。「比方說,你很喜歡在你的筆記本上記錄資訊。」
我目光忽然轉向掛在我椅子上的一個布製袋子。
「你怎麼知道我筆記本的事情?」
看到我在椅子上挪動著坐立不安,他只是眨著眼睛,往後坐回去。我的脈搏加速。
「因為你的檔案上有寫啊,」最後他終於說。朝我微笑,然後目光又回到手上的檔案。
我動也不動,時鐘滴答走著,窗簾飄動。他跟我說的是實話嗎?他身上有薄荷的香氣,混合了他皮膚上的汗水,聞起來像牙膏。我胃裡開始打結,發現這個人讓我想到黑眼男。這個想法再度點燃我心底那個沉默的火花,再度警告我趕緊逃離這裡,逃得遠遠的。但如果我現在離開,如果我拒絕開口、拒絕合作,那麼對誰有好處?我?他?我對這個人一無所知。沒有細節,沒有事實。我開始好奇自己是不是犯錯了。
那男子放下筆,開始把一個檔案夾底下的筆記往左翻,一張照片掉出來。我往下看著它墜落,差點呼吸停止。
是那個神父的頭部。
在他被謀殺之前。
那男子蹲下去撿起照片,神父的頭部影像從他的手指間垂下。我們兩人旁觀著那影像,一陣微風從窗外吹進來,吹得那個頭前後搖晃。我們什麼都沒說。在外頭,車聲喧囂,巴士吐出廢氣。照片還在搖晃。腦袋、骨頭、血肉。那位神父,還活著。沒有死。沒有噴濺的血和流出來的肚腸。沒有呆滯不動、冰冷睜大的眼睛。但活著,在呼吸,身體還是溫暖的。我打了個哆嗦,但那男子絲毫不動。過了一會兒,他把照片放回檔案夾,我吐出一口長氣,順了一下自己的頭髮,看著那男子的手指。長長的、曬黑的手指。於是我想到:他是哪裡來的?他為什麼會在這裡,在這個國家?當初安排這場會面時,我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至今我還是不確定。
「看到他的臉,你有什麼感覺?」
聽到他忽然開口發出聲音,讓我驚跳一下。「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看到奧唐諾神父。」
我往後靠坐,雙掌壓在大腿上。「他就是那個神父。」
那男子歪著頭。「不然你以為是其他人嗎?」
「不。」我把一綹頭髮塞到耳後。他雙眼還是注視著我。我真希望他不要再盯著我看了。
我摸摸自己的後頸。溼溼黏黏的。
「接下來,我想正式開始訪談了。」他說,伸手去拿錄音筆。我來不及反對了。「一開始,請你先告訴我,拜託講英文,說出你的全名、職業、年齡,還有出生地。另外也要你說出你原先被定罪的罪名。」
紅色的錄音燈閃爍著。那顏色害我眨眼,害我想緊緊閉上眼睛,再也不要睜開。我看了這個房間一圈,想找些細節讓自己的大腦冷靜下來。房間四面是愛德華時代風格的紅磚牆,兩扇垂直拉窗,一面落地玻璃窗,還有一扇門。我暫停下來。一個出口,只有一個。玻璃窗不算出口——我們在三樓。倫敦市中心。如果我往下跳,以那個速度和軌跡,我很可能會摔斷一條腿、兩邊肩膀和一邊腳踝。我的目光又回到那名男子身上。我是高個子,體格健壯。我很會跑。但無論他是誰,無論這名男子宣稱他是什麼身分,他可能有種種答案。而我需要答案。因為我發生了那麼多事,這一切都必須停止了。
我在窗玻璃上看到自己的鏡影:深色短髮,長長的脖子,褐色眼珠。回看著我的是另一個人,忽然變得蒼老些、皺紋多些,被過往摧殘得憔悴。窗簾飄起來,蓋住玻璃和那個影像,我的鏡影消失了,有如沙漠中的海市蜃樓。我閉上眼睛一會兒,然後睜開來,此時碰巧有一束陽光透進窗內,讓我覺得異樣地清醒而蓄勢待發。該是談一談的時候了。
「我名叫瑪麗亞.馬汀尼茲.維亞努艾瓦醫師,我是——曾經是——整容外科顧問醫師。我三十三歲。出生地:西班牙薩拉曼卡。」我暫停,吸了口氣。「我之前被定罪的罪名,是謀殺一位天主教神父。」
旁邊一個女人拽著我的袖子。
「喂,」她說。「你聽到我講的話嗎?」我無法回答。我的腦袋裡面迴旋著叫聲、氣味、亮藍光和一道道鐵柵,無論我多麼努力,無論我怎麼告訴自己呼吸、算數字、專心,都沒辦法冷靜下來,無法甩掉那個滲入腦中的混亂夢魘。
我是搭乘一輛警方廂型車抵達監獄的。車上有十個座位,兩名警衛,三名乘客。整趟路我都沒動、沒講話,幾乎難以呼吸。現在來到這裡了,我告訴自己冷靜下來。我瀏覽著這個區域,目光停留在那些瓷磚上頭。每塊瓷磚都跟門的顏色一樣黑,牆壁是髒灰色。我嗅了嗅,空氣中有尿臊味和馬桶清潔劑的氣味。一名警衛站在離我一公尺處,她後方是戈德茅斯監獄的主要監區,也就是我的新家。
又有人扯我的衣袖。我往下看,那女人現在抓著我,手指像蟹爪似的緊緊鉗著我的外套。她的指甲咬短了,她的皮膚龜裂得像樹皮,透出底下土灰色細細的血管。
「喂。你。我說,你叫什麼名字啊?」她看著我。「你是外國人還什麼的?」
「我是西班牙人。我是瑪麗亞.馬汀尼茲醫師。」她還是緊抓著我。我不曉得該怎麼辦,她抓著我外套是應該的嗎?無可奈何之下,我開始尋找警衛的蹤影。
那女人大笑一聲。「醫師?哈!」她放開我的衣袖,朝我拋了個飛吻。我皺起臉,她呼出的氣息有糞便味。我抽回手,撫平袖子的縐褶,也撫掉她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跡。正當我以為她可能要放棄時,她又開口了。
「一個當醫師的是做了什麼,才會被關進來啊?」
我張開嘴想問她是誰——聽說一般人都是這麼做的——但是有個警衛叫我們往前走,於是我們照辦了。我腦袋裡有好多問題,但眼前有太多新的聲音、形狀、顏色,以及人。對我來說,這一切都太多了。
「我叫蜜凱拉,」那女人說,此時我們往前走著。她想看我的眼睛,我別開臉。「蜜凱拉.克洛夫特。」她繼續說。「朋友都喊我蜜琪。」她拉高她的T恤。
「蜜卡拉(Michaela)是希伯來文,原意是喜歡天主的人。米迦勒(Michael)是猶太教和基督教聖經中的天使長。」我說,沒辦法阻止自己,那些話從我口中直衝出來。
我以為她會嘲笑我,就像一般人那樣,但她沒有,於是我偷看她一眼。她正微笑看著自己肚子上的刺青,刺著一條蛇環繞著肚臍。她發現我在看,趕緊放下T恤張開嘴巴。她的舌頭吐出來,上頭有三個銀舌釘。她又把舌頭往外吐更多。我別開眼睛。走到下一個區域後,警衛命令我們停下。周圍還是沒窗子,也看不見有什麼出路。無處可逃。天花板的長條燈管照著走廊,我數著燈的數目,沉湎在無意義的計算中。
「我想你得前進了。」
我驚跳起來。一個中年男子站在兩公尺外。他的頭歪向一旁,嘴唇張開。他是誰?他跟我四目相對好一會兒;然後,他抬起一手梳過頭髮,同時大步離開。我不好意思盯著他看,正要轉頭,此時他忽然停住腳步,又看著我。他的雙眼。褐色的,深邃得我無法別開眼睛。
「馬汀尼茲?」那個警衛說。「你又沒跟上了,快點。」
我伸著脖子想看那男人是不是還在,但他忽然不見了。就好像他從來不曾存在過。
監獄中心的這棟建築物很吵。我雙臂緊緊交抱在胸前,始終低著頭,希望可以掩飾自己的不知所措。我們跟著警衛往前走,一路沉默無聲。我試圖保持冷靜,試圖告訴自己,說我有辦法面對這個狀況,說我可以應付這個新環境,就跟其他人沒有兩樣;但在監獄中,一切都太陌生了。持續不斷的體臭味、叫喊聲,偶爾還有尖叫。我得花時間消化、處理。這一切對我都不是例行常規。
蜜凱拉拍拍我的肩膀,我本能地往後瑟縮。
「所以你看到他了?」她說。
「誰?」
「戈德茅斯的典獄長。剛剛那個眼神和氣、曬得一身昂貴古銅色的傢伙。」她咧嘴笑了。「小心點,曉得嗎?」她的手掌貼在我的右臀上。「我以前在這裡蹲過,小美人。我們的典獄長哪,他是……出了名的。」
她的手掌還是沒拿開,我希望她拿開手,不要煩我。我正要把她的手拍開,警衛就大吼著要她放開我。
蜜凱拉舔舔牙齒,然後手移開了。我的身體放鬆下來。蜜凱拉沒說話,只是嗅了嗅,用手掌擦了下鼻子,然後走開了。
我再度低下頭,好確保自己離她遠一點。
坐在我對面的那名男子不動。他面朝前方,忍著沒咳嗽。太陽曬著這個房間,但即使我把襯衫拉鬆透風時,還是覺得熱氣刺人。我看著他。我不喜歡這樣:他,我,這裡,這個房間,這個……這個牢籠。我好想扯自己的頭髮,朝他、朝他們、朝全世界尖叫。然而我什麼都沒做,只是坐在那裡。牆上的時鐘發出滴答聲。
那男子把錄音筆放在桌上,然後毫無預兆地,忽然朝我露出大大的笑容。
「別忘了,」他說。「我來這裡是要幫助你的。」
我張嘴要說話,但腦中忽然靈光一閃,有個聲音悄悄說,開始!我不想理會那聲音。為了撫平心中高漲的情緒,我轉而試圖把注意力集中在別的事物上頭,任何事物都行。他的身高。他對那張椅子來說太高了。他駝著背,腹部下陷,雙腳交叉。以他一八八公分的身高和七十四公斤的體重,可以輕鬆跑一公里,也不會喘不過氣來。
那男人清了清嗓子,雙眼看著我。我艱難地吞嚥著。
「瑪麗亞,」他開口了。「我可以……」他結巴著,然後稍微湊近一點。「我可以喊你瑪麗亞嗎?」
我出自本能地用西班牙語回答。
「麻煩請說英語。」他說。
我咳了一聲。「可以。我叫瑪麗亞沒錯。」我的聲音有點顫抖,他聽得出來嗎?我得慢下來,心裡想著各種事實。他的指甲。很乾淨,認真洗刷過。他穿的襯衫是白色的,領口敞開。他的西裝是黑色的。布料很昂貴。羊毛的?除此之外,他穿著絲質襪子和真皮的平底便鞋。沒有磨損的痕跡。他整個人簇新得就像是從一本雜誌裡走出來似的。
他拿起一支筆,我大著膽子伸手去拿水杯。我緊握著玻璃杯,但還是有幾滴水不聽使喚,濺出了杯緣。我停住。雙手顫抖。
「你還好吧?」那男子問,但我沒回答。有個什麼不對勁。
我眨眨眼,視線模糊起來,一層薄薄的白色罩住我的雙眼,像一件斗篷,或是一個面具。我的眼皮開始顫動,心臟狂跳,腎上腺素不斷分泌。或許是因為跟他待在這個房間裡,或許是想到要跟一個陌生人講我的感覺,總之觸發了我內心深處的一段記憶,很可怕的記憶。
這種狀況之前發生過很多次。一開始那記憶搖晃著,不慌不忙。然後,才幾秒鐘,它就匆忙加速,完全形成了一個影像,彷彿一齣舞台劇在我面前出現。布幕升起,我在一間診療室裡。白色的牆,不鏽鋼,漿過的床單。天花板上排列著一根根長條燈管,發著亮光,照得我無可遁逃。然後,在前方,就像煙霧中出現的魔術師,那個有著黑色眼珠的醫師從遠處的門走進來。他戴著面具,手裡拿著一根注射針。
「哈囉,瑪麗亞。」
恐慌從我心底冒出來,像火山爆發的熔岩,快得我都擔心自己要爆炸了。那黑眼男走近了些,我開始發抖,想逃走,但我四肢被皮帶綁著。他的嘴唇往上翹,他在房間裡了,逼近我,他的氣息——菸草、大蒜、薄荷——吹在我臉上,我看得到他的鼻孔,而且我開始聽到自己尖叫著。另外還有別的,一個耳語:「他不是真實的。他不是真實的。」那耳語,盤旋在我腦海,拍著翅膀,逗留不去,然後就像一陣微風吹過般,在我的皮膚上留下一道雞皮疙瘩。這是正常的嗎?我環視周圍:玻璃小藥瓶、注射針、掛圖。我看著自己的雙手:年輕,沒有皺紋。我碰觸自己的臉:青春痘。不是我,不是現在的我。所以表示這一切都不存在。
就像蠟燭被吹熄般,那影像消失了,布幕落下。我的雙眼趕緊往下看,發現自己的每個指節都因為緊握玻璃杯而發白。我抬起眼睛,對面的人正盯著我看。
「怎麼了?」他說。
我吸了口氣,檢查自己所在的位置。我的鼻孔內、口腔裡仍有黑眼男的氣息,彷彿他真的來過。我設法拋開恐懼,然後緩緩放下玻璃杯,雙手扭絞在一起,緊握兩次。「我想起了一些事。」我停了一下說。
「真實的事情?」
「我不曉得。」
「這樣的狀況常常發生嗎?」
我猶豫了。他已經知道了嗎?我決定告訴他實話。「對。」
那男子看了我的雙手,然後轉頭打開一些影印檔案。
我雙眼瀏覽著他膝上的那些紙頁。資料,資訊。事實,真正的事實,全都是黑白的,清楚,沒有灰色地帶,沒有模稜兩可或隱藏的意義。我一定是專注在這個想法上,因為不知不覺間,我腦袋裡的資訊就脫口而出。
「影印機源起於一四四○年,」我說,雙眼看著他手裡的那些紙頁。
他抬頭看我。「你說什麼?」
「影印機——是古騰堡在一四四○年發明印刷術的時候開始萌芽的。」我吸了口氣。我的腦袋實在裝了太多資訊了,有時候就是會滿得溢出來。「古騰堡聖經,」我繼續說,「是第一種大量印刷的書。」我停下,等著,但那男人沒有反應。他又盯著我,雙眼瞇起來,成了兩道藍色的縫隙。我開始一腳輕敲地板,胸口一股熟悉的緊繃感擴散開來。為了紓解,我開始算。一、二、三、四……算到五,我看向窗子。平紋細布的窗簾鼓起。窗玻璃外有鐵窗格柵。窗子下方,三輛巴士經過,發出呼呼聲,吐出噪音、廢氣。我轉頭摸摸後頸的髮際線。汗水流過我的衣領。
「這裡好熱,」我說。「有電扇嗎?」
那男子放下紙頁。「據我所知,你記住資訊的能力是頂尖。」他瞇起眼睛。「你的智商很高。」他看看手上的紙,目光又回到我身上。「一百八十一。」
我沒動。這些資訊不是一般人會知道的。
「我的職責是研究病人,」他繼續說,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他身體前傾。「我知道很多關於你的事情。」他暫停一下。「比方說,你很喜歡在你的筆記本上記錄資訊。」
我目光忽然轉向掛在我椅子上的一個布製袋子。
「你怎麼知道我筆記本的事情?」
看到我在椅子上挪動著坐立不安,他只是眨著眼睛,往後坐回去。我的脈搏加速。
「因為你的檔案上有寫啊,」最後他終於說。朝我微笑,然後目光又回到手上的檔案。
我動也不動,時鐘滴答走著,窗簾飄動。他跟我說的是實話嗎?他身上有薄荷的香氣,混合了他皮膚上的汗水,聞起來像牙膏。我胃裡開始打結,發現這個人讓我想到黑眼男。這個想法再度點燃我心底那個沉默的火花,再度警告我趕緊逃離這裡,逃得遠遠的。但如果我現在離開,如果我拒絕開口、拒絕合作,那麼對誰有好處?我?他?我對這個人一無所知。沒有細節,沒有事實。我開始好奇自己是不是犯錯了。
那男子放下筆,開始把一個檔案夾底下的筆記往左翻,一張照片掉出來。我往下看著它墜落,差點呼吸停止。
是那個神父的頭部。
在他被謀殺之前。
那男子蹲下去撿起照片,神父的頭部影像從他的手指間垂下。我們兩人旁觀著那影像,一陣微風從窗外吹進來,吹得那個頭前後搖晃。我們什麼都沒說。在外頭,車聲喧囂,巴士吐出廢氣。照片還在搖晃。腦袋、骨頭、血肉。那位神父,還活著。沒有死。沒有噴濺的血和流出來的肚腸。沒有呆滯不動、冰冷睜大的眼睛。但活著,在呼吸,身體還是溫暖的。我打了個哆嗦,但那男子絲毫不動。過了一會兒,他把照片放回檔案夾,我吐出一口長氣,順了一下自己的頭髮,看著那男子的手指。長長的、曬黑的手指。於是我想到:他是哪裡來的?他為什麼會在這裡,在這個國家?當初安排這場會面時,我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至今我還是不確定。
「看到他的臉,你有什麼感覺?」
聽到他忽然開口發出聲音,讓我驚跳一下。「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看到奧唐諾神父。」
我往後靠坐,雙掌壓在大腿上。「他就是那個神父。」
那男子歪著頭。「不然你以為是其他人嗎?」
「不。」我把一綹頭髮塞到耳後。他雙眼還是注視著我。我真希望他不要再盯著我看了。
我摸摸自己的後頸。溼溼黏黏的。
「接下來,我想正式開始訪談了。」他說,伸手去拿錄音筆。我來不及反對了。「一開始,請你先告訴我,拜託講英文,說出你的全名、職業、年齡,還有出生地。另外也要你說出你原先被定罪的罪名。」
紅色的錄音燈閃爍著。那顏色害我眨眼,害我想緊緊閉上眼睛,再也不要睜開。我看了這個房間一圈,想找些細節讓自己的大腦冷靜下來。房間四面是愛德華時代風格的紅磚牆,兩扇垂直拉窗,一面落地玻璃窗,還有一扇門。我暫停下來。一個出口,只有一個。玻璃窗不算出口——我們在三樓。倫敦市中心。如果我往下跳,以那個速度和軌跡,我很可能會摔斷一條腿、兩邊肩膀和一邊腳踝。我的目光又回到那名男子身上。我是高個子,體格健壯。我很會跑。但無論他是誰,無論這名男子宣稱他是什麼身分,他可能有種種答案。而我需要答案。因為我發生了那麼多事,這一切都必須停止了。
我在窗玻璃上看到自己的鏡影:深色短髮,長長的脖子,褐色眼珠。回看著我的是另一個人,忽然變得蒼老些、皺紋多些,被過往摧殘得憔悴。窗簾飄起來,蓋住玻璃和那個影像,我的鏡影消失了,有如沙漠中的海市蜃樓。我閉上眼睛一會兒,然後睜開來,此時碰巧有一束陽光透進窗內,讓我覺得異樣地清醒而蓄勢待發。該是談一談的時候了。
「我名叫瑪麗亞.馬汀尼茲.維亞努艾瓦醫師,我是——曾經是——整容外科顧問醫師。我三十三歲。出生地:西班牙薩拉曼卡。」我暫停,吸了口氣。「我之前被定罪的罪名,是謀殺一位天主教神父。」
旁邊一個女人拽著我的袖子。
「喂,」她說。「你聽到我講的話嗎?」我無法回答。我的腦袋裡面迴旋著叫聲、氣味、亮藍光和一道道鐵柵,無論我多麼努力,無論我怎麼告訴自己呼吸、算數字、專心,都沒辦法冷靜下來,無法甩掉那個滲入腦中的混亂夢魘。
我是搭乘一輛警方廂型車抵達監獄的。車上有十個座位,兩名警衛,三名乘客。整趟路我都沒動、沒講話,幾乎難以呼吸。現在來到這裡了,我告訴自己冷靜下來。我瀏覽著這個區域,目光停留在那些瓷磚上頭。每塊瓷磚都跟門的顏色一樣黑,牆壁是髒灰色。我嗅了嗅,空氣中有尿臊味和馬桶清潔劑的氣味。一名警衛站在離我一公尺處,她後方是戈德茅斯監獄的主要監區,也就是我的新家。
又有人扯我的衣袖。我往下看,那女人現在抓著我,手指像蟹爪似的緊緊鉗著我的外套。她的指甲咬短了,她的皮膚龜裂得像樹皮,透出底下土灰色細細的血管。
「喂。你。我說,你叫什麼名字啊?」她看著我。「你是外國人還什麼的?」
「我是西班牙人。我是瑪麗亞.馬汀尼茲醫師。」她還是緊抓著我。我不曉得該怎麼辦,她抓著我外套是應該的嗎?無可奈何之下,我開始尋找警衛的蹤影。
那女人大笑一聲。「醫師?哈!」她放開我的衣袖,朝我拋了個飛吻。我皺起臉,她呼出的氣息有糞便味。我抽回手,撫平袖子的縐褶,也撫掉她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跡。正當我以為她可能要放棄時,她又開口了。
「一個當醫師的是做了什麼,才會被關進來啊?」
我張開嘴想問她是誰——聽說一般人都是這麼做的——但是有個警衛叫我們往前走,於是我們照辦了。我腦袋裡有好多問題,但眼前有太多新的聲音、形狀、顏色,以及人。對我來說,這一切都太多了。
「我叫蜜凱拉,」那女人說,此時我們往前走著。她想看我的眼睛,我別開臉。「蜜凱拉.克洛夫特。」她繼續說。「朋友都喊我蜜琪。」她拉高她的T恤。
「蜜卡拉(Michaela)是希伯來文,原意是喜歡天主的人。米迦勒(Michael)是猶太教和基督教聖經中的天使長。」我說,沒辦法阻止自己,那些話從我口中直衝出來。
我以為她會嘲笑我,就像一般人那樣,但她沒有,於是我偷看她一眼。她正微笑看著自己肚子上的刺青,刺著一條蛇環繞著肚臍。她發現我在看,趕緊放下T恤張開嘴巴。她的舌頭吐出來,上頭有三個銀舌釘。她又把舌頭往外吐更多。我別開眼睛。走到下一個區域後,警衛命令我們停下。周圍還是沒窗子,也看不見有什麼出路。無處可逃。天花板的長條燈管照著走廊,我數著燈的數目,沉湎在無意義的計算中。
「我想你得前進了。」
我驚跳起來。一個中年男子站在兩公尺外。他的頭歪向一旁,嘴唇張開。他是誰?他跟我四目相對好一會兒;然後,他抬起一手梳過頭髮,同時大步離開。我不好意思盯著他看,正要轉頭,此時他忽然停住腳步,又看著我。他的雙眼。褐色的,深邃得我無法別開眼睛。
「馬汀尼茲?」那個警衛說。「你又沒跟上了,快點。」
我伸著脖子想看那男人是不是還在,但他忽然不見了。就好像他從來不曾存在過。
監獄中心的這棟建築物很吵。我雙臂緊緊交抱在胸前,始終低著頭,希望可以掩飾自己的不知所措。我們跟著警衛往前走,一路沉默無聲。我試圖保持冷靜,試圖告訴自己,說我有辦法面對這個狀況,說我可以應付這個新環境,就跟其他人沒有兩樣;但在監獄中,一切都太陌生了。持續不斷的體臭味、叫喊聲,偶爾還有尖叫。我得花時間消化、處理。這一切對我都不是例行常規。
蜜凱拉拍拍我的肩膀,我本能地往後瑟縮。
「所以你看到他了?」她說。
「誰?」
「戈德茅斯的典獄長。剛剛那個眼神和氣、曬得一身昂貴古銅色的傢伙。」她咧嘴笑了。「小心點,曉得嗎?」她的手掌貼在我的右臀上。「我以前在這裡蹲過,小美人。我們的典獄長哪,他是……出了名的。」
她的手掌還是沒拿開,我希望她拿開手,不要煩我。我正要把她的手拍開,警衛就大吼著要她放開我。
蜜凱拉舔舔牙齒,然後手移開了。我的身體放鬆下來。蜜凱拉沒說話,只是嗅了嗅,用手掌擦了下鼻子,然後走開了。
我再度低下頭,好確保自己離她遠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