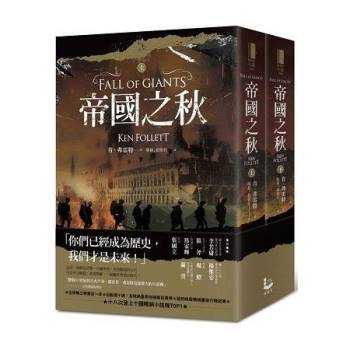第一章
一九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英王喬治五世在倫敦西敏寺加冕的那一天,比利.威廉斯在南威爾斯阿伯羅溫鎮下了礦井。
一九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這一天是比利十三歲的生日。他還在睡夢中大(在威爾斯和蘇格蘭地區,稱呼父親為「大」[Da))就把他弄醒了。大弄醒人的辦法很不溫柔,但非常有效。他搧比利的臉頰,以穩定有力的節奏,不把他弄醒不甘休。比利本來睡得正香,一開始他還以為忍忍就算了,但耳光一直搧個不停。他本想發火,但想起自己應該起床。他睜開眼睛,猛地坐起身。
「四點了。」大說了一句,然後走出房間,下樓的時候腳上的靴子把木樓梯弄得震天價響。今天比利就要開始工作了,當礦工學徒,鎮上的人在他這個年紀都幹這個。他希望自己能像個真正的礦工,決心不要讓自己出醜。大衛.克蘭普頓第一天下礦井的時候嚇得又哭又鬧,現在他們還叫他「戴哭包」,儘管他已經二十五歲了,是鎮上橄欖球隊的明星。
眼下是仲夏時節,小小的窗戶外透進一抹明亮的晨光。比利看著躺在身邊的外公。格蘭帕睜著眼睛,只要比利一醒,他也就跟著醒。他總是說老人家睡得不多。
比利下了床,身上只穿著內褲。如果天氣冷,他會穿襯衫睡覺,但現在英國正值明媚的夏天,晚上很暖和。他從床底拉出尿壺,揭開壺蓋。
他的陰莖尺寸還是那樣(他叫它「小弟弟」),一直都是那麼孩子氣的一小根。他原本以為在生日前夕這一夜會長大一些,或者能長出一根黑毛也好,但結果令他很失望。他最好的朋友湯米.格里菲斯和他同一天出生,但湯米的發育要快得多:他已經開始變聲,嘴脣上方長出了黑色的絨毛,小弟弟也像成年人一樣雄壯。比利覺得很丟臉。
往尿壺撒尿的時候,比利看了看窗外,只看見一個煤渣場,上面堆積著石頭、殘渣和煤礦裡運出來的垃圾,都是些瓦礫和沙土。比利心想,上帝創造世界後第二天大概就是這幅光景吧,那時候神還沒說「地要發生青草」。一陣輕風吹過,黑色的沙塵從煤渣上飄起來,飄進一排排的房屋裡。
房間裡沒什麼可看的。這裡是小臥室,狹窄得只能放下一張單人床、一個斗櫃和格蘭帕的舊箱子,牆上掛著一幅刺繡,上面寫著: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第一章
一九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英王喬治五世在倫敦西敏寺加冕的那一天,比利.威廉斯在南威爾斯阿伯羅溫鎮下了礦井。
一九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這一天是比利十三歲的生日。他還在睡夢中大(在威爾斯和蘇格蘭地區,稱呼父親為「大」[Da))就把他弄醒了。大弄醒人的辦法很不溫柔,但非常有效。他搧比利的臉頰,以穩定有力的節奏,不把他弄醒不甘休。比利本來睡得正香,一開始他還以為忍忍就算了,但耳光一直搧個不停。他本想發火,但想起自己應該起床。他睜開眼睛,猛地坐起身。
「四點了。」大說了一句,然後走出房間,下樓的時候腳上的靴子把木樓梯弄得震天價響。今天比利就要開始工作了,當礦工學徒,鎮上的人在他這個年紀都幹這個。他希望自己能像個真正的礦工,決心不要讓自己出醜。大衛.克蘭普頓第一天下礦井的時候嚇得又哭又鬧,現在他們還叫他「戴哭包」,儘管他已經二十五歲了,是鎮上橄欖球隊的明星。
眼下是仲夏時節,小小的窗戶外透進一抹明亮的晨光。比利看著躺在身邊的外公。格蘭帕睜著眼睛,只要比利一醒,他也就跟著醒。他總是說老人家睡得不多。
比利下了床,身上只穿著內褲。如果天氣冷,他會穿襯衫睡覺,但現在英國正值明媚的夏天,晚上很暖和。他從床底拉出尿壺,揭開壺蓋。
他的陰莖尺寸還是那樣(他叫它「小弟弟」),一直都是那麼孩子氣的一小根。他原本以為在生日前夕這一夜會長大一些,或者能長出一根黑毛也好,但結果令他很失望。他最好的朋友湯米.格里菲斯和他同一天出生,但湯米的發育要快得多:他已經開始變聲,嘴脣上方長出了黑色的絨毛,小弟弟也像成年人一樣雄壯。比利覺得很丟臉。
往尿壺撒尿的時候,比利看了看窗外,只看見一個煤渣場,上面堆積著石頭、殘渣和煤礦裡運出來的垃圾,都是些瓦礫和沙土。比利心想,上帝創造世界後第二天大概就是這幅光景吧,那時候神還沒說「地要發生青草」。一陣輕風吹過,黑色的沙塵從煤渣上飄起來,飄進一排排的房屋裡。
房間裡沒什麼可看的。這裡是小臥室,狹窄得只能放下一張單人床、一個斗櫃和格蘭帕的舊箱子,牆上掛著一幅刺繡,上面寫著: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屋裡連鏡子也沒有。
房間的一扇門通往樓梯,另一扇門通往主臥室,只有從這扇門才能進去那裡。主臥室要寬敞一些,放得下兩張床。大和媽在這間房睡覺,幾年前比利的幾個姊姊也在這裡睡覺。大姊艾瑟爾已經離家工作,而另外三個姊姊都早夭了,一個死於麻疹,一個死於百日咳,一個死於白喉。比利還有過一個哥哥,在格蘭帕來之前和比利一塊睡。他的名字叫威斯利,在一次礦車脫軌事故中喪生。
比利穿上他唯一的襯衫。昨天他才穿去上學,今天是星期四,只有到了星期天他才會換洗襯衫。不過,他有一條新褲子,生平第一條,料子是厚厚的防水斜紋棉布。這條褲子象徵著他進入了男人的世界,他驕傲地穿上新褲子,感受布料那種厚重陽剛的感覺,覺得滿心歡喜。他穿上威斯利遺留下來的厚皮革腰帶和靴子,然後走下樓去。
樓下那一層主要是客廳,有十五平方呎大,中間擺了張桌子,一側是壁爐,地板上鋪著一張自家織的毯子。大正坐在桌旁讀著過期的《每日郵報》,長而尖的鼻子上架著一副眼鏡。媽媽正在泡茶。她放下冒著熱氣的水壺,親了親比利的額頭,說:「我的小男子漢,今天你生日,覺得怎麼樣啊?」
比利沒有回答。「小」這個字讓他有點受傷,因為他的確還小,而「男子漢」也刺痛了他,因為他還不是真正的男子漢。他走進屋後的洗滌室,用一個錫碗從水桶裡盛水洗了臉和手,然後把水倒進淺淺的石頭水槽裡。洗滌室有一個燒水的大銅壺,下頭有爐篦,但只有洗澡的時候才會用,也就是星期六。
政府答應他們很快會有自來水,一些礦工的屋子裡已經接通了。在比利看來,只要輕輕轉開水龍頭就有一杯涼快清冽的水喝,不用挑著水桶到街上的水塔去接水,實在是個奇蹟。不過威廉斯一家住的威靈頓街這一帶還沒有接通管道。
他回到客廳,坐在桌子旁邊。媽媽在他面前擺了一大杯奶茶,裡面加好了糖。她從自家做的麵包塊上切了兩片厚實的麵包,從樓梯底下的餐具櫃那裡拿出了一大片牛脂。比利雙手合十,閉上眼睛,祈禱道:「感謝主賜予我們食物,阿門。」然後喝了幾口奶茶,把牛脂塗在麵包片上。
大的灰藍色眼睛從報紙上方望出。「麵包上加點鹽,在礦井下你會流汗。」比利的父親是礦工的代表,受雇於南威爾斯礦工聯盟,他一有機會總是說這個聯盟是英國最強大的工會組織。大家都叫他戴工會。許多名叫大衛或達維德的人會把自己的名字簡稱為「戴」,這是威爾斯的習慣。比利在學校裡得知大衛這個名字在威爾斯很流行,因為這是這片土地的守護聖徒之名,就像在愛爾蘭,很多人以那裡的守護聖徒派崔克為名。所有名字都叫「戴」的人並不靠姓氏來區分彼此,因為鎮裡的人無非就是姓瓊斯、威廉斯、伊文斯或摩根。他們靠綽號來區分,有了好玩的綽號,本名也就很少用了。比利的本名是威廉.威廉斯,大家都叫他比利雙雙。女人通常冠上丈夫的綽號,所以他們稱呼媽媽為戴工會太太。
比利吃著第二片麵包的時候,格蘭帕下來了。儘管天氣很暖和,他還是穿著夾克和背心。他洗完手後坐在比利對面。「別那麼緊張,」他說,「我十歲就下礦了。我父親五歲就被我爺爺扛在肩膀上跟著下礦,從早上六點一直幹到晚上七點。從十月到隔年三月,他都沒見過太陽。」
「我可不緊張。」比利說道。其實他在說謊,心裡慌著呢。
幸好格蘭帕沒有就這個問題窮追不捨。比利喜歡格蘭帕。媽媽把他當成了小寶寶,大總是很嚴厲,而且老是嘲笑他,但格蘭帕很有耐心,和比利說話的時候當他是個大人。
「聽聽這條新聞。」大說道。他從不買右翼的《郵報》,但有時他會把別人的報紙帶回家,用譏諷的語氣讀報紙給大家聽,嘲笑統治階級的愚蠢和虛偽。「戴安娜.曼那斯夫人因穿同一件服裝出席兩場舞會而飽受批評。這位拉特蘭郡公爵的小女兒在薩伏伊舞會上贏得了『最佳著裝獎』,得到兩百五十基尼獎金。她當時穿的是一件露肩緊身馬甲上衣和帶裙襯的長裙。」他放下報紙,說道:「那至少是你五年的工資,小比利。」他繼續讀報:「但服裝界批評她以同樣的裝扮參加了溫特頓勳爵和F.E.史密斯爵士在克拉里奇酒店舉行的舞會。常言道:再好的東西多了也令人厭倦。」他抬起頭。「妳那身衣服得換一下了,媽媽,」他說,「不然的話服裝界會批評妳的。」
媽媽並不覺得好笑。她穿著破舊的棕色羊毛洋裝,肘處打著補丁,腋下有兩團汙漬。「假如我有兩百五十基尼,我會比那個戴安娜.馬拉屎更美麗動人。」她說道,語氣不無苦澀。「對啊。」格蘭帕說,「卡拉一直都是個美人,長得像她媽媽。」卡拉是媽媽的名字。格蘭帕轉向比利。「你外婆是義大利人,名字叫瑪麗亞.費羅內。」比利知道外婆的名字,但格蘭帕就是喜歡翻來覆去講一樣的事情。「你媽媽繼承了她柔順的黑髮和動人的黑眸,你姊姊也是。你外婆是卡地夫最漂亮的女孩,而我娶了她。」他突然一臉傷感。「這些都已經是往事了。」他輕聲說道。
大皺了皺眉頭——外公的這番話似乎暗示了肉體的歡娛——但媽媽聽到外公的讚美心裡喜孜孜的,面帶微笑把早餐擺在他的面前。她說:「噢,欸,我和姊妹以前可都稱得上是美女。假如買得起綢緞和蕾絲的話,我們會讓那些貴族老爺看看美女到底長什麼樣。」
比利有點驚訝,他可從來沒想過媽媽漂不漂亮,儘管星期六晚上她打扮一番去禮拜堂的時候,看上去也挺動人的,尤其是戴著帽子的時候。他猜想或許媽媽以前真的漂亮過,但實在挺難想像。
「提醒你一句,」格蘭帕說,「你外婆的家族還很聰明。我的大舅子原本是個礦工,後來他不幹這行了,在騰比開了間咖啡廳,現在過上好日子了,整天享受海風,什麼也不用幹,只要煮咖啡和數錢。」
大又讀了一則新聞。「為籌備加冕大典,白金漢宮專門撰寫了一本長達二百一十二頁的手冊。」他抬起視線,「告訴下面的人這則新聞,比利,他們會覺得放心的,所有的事情王室都安排得很周全。」
比利對王室的事情並不感興趣。他喜歡的是《郵報》上刊登的冒險故事,裡面講述中學裡那些玩橄欖球的猛男怎麼逮到狡猾的德國間諜。根據報紙上所說,德國在英國每個鎮裡都安插了間諜,不過,阿伯羅溫這裡似乎一個也沒有,真叫人失望。
比利站起身,宣布道:「我上街一趟。」他從前門走出了屋子。「上街一趟」是家裡的委婉說法,意思是上廁所,要走過威靈頓街的一半才到。廁所是一間低矮的磚房,屋頂鋪了波浪鐵皮,就在地上挖一個深坑做地基建起來的。磚房隔成兩間,一間是男廁,一間是女廁。每一間都有兩個廁位,所以可以兩兩結伴同行。沒有人知道為什麼建造者會這麼安排,但大家都將就著用。男人通常都是目視前方,一言不發,但比利總是聽到隔壁傳來女人聊天的聲音。廁所裡臭氣熏天,即使你每天都到裡面如廁也感覺受不了。比利在裡面時總是盡可能不呼吸,出來後再大口大口地喘氣。有個叫「戴倒屎」的人會定期用鏟子把糞便鏟出來。比利回到家裡時,欣喜地看到姊姊艾瑟爾正坐在桌旁。「生日快樂,比利!」她叫嚷著,「我過來看你,在你下礦井之前親你一下。」
艾瑟爾十八歲了,比利覺得姊姊是個大美人。她有一頭濃密的紅褐色鬈髮,黑色的雙眸閃爍著調皮的光芒。或許,媽媽以前也有這般的美貌。艾瑟爾穿著簡樸的黑洋裝,戴著一頂家庭女僕的白棉帽,她很喜歡這身裝扮。
比利很崇拜姊姊。她不但美麗動人,而且聰明伶俐又詼諧勇敢,有時甚至敢頂撞大。她告訴比利別人根本不會講的事情,像是婦女稱之為「詛咒」的月經,還有讓本地的聖公會牧師匆忙離開小鎮的公然猥褻罪指的是什麼。上學的時候她一直在班裡名列前茅。在《南威爾斯之聲報》舉辦的作文比賽中,她的作文〈我的家鄉〉獲得了一等獎,獎品是一本《卡塞爾世界地圖冊》。
她親了親比利的臉頰。「我跟管家傑文茲太太說鞋油用完了,得到鎮裡買一些。」艾瑟爾在菲茨伯特伯爵的白公館裡工作,也住在那兒,那是一間位於半山的豪宅,離小鎮有一哩遠。她遞給比利一塊乾淨的棉布,裡面包著東西。「我偷了塊蛋糕給你。」
「噢,謝謝妳,艾絲。」比利說道。他喜歡吃蛋糕。
媽媽說:「我把蛋糕放飯盒裡好嗎?」
「欸,好啊。」
媽媽從碗櫥裡拿出一個馬口鐵盒子,把蛋糕放進去。然後切了兩片麵包,往上面淋上牛脂,撒了點鹽,也放進盒子裡。所有的礦工都自帶飯盒,如果把食物包在布裡帶下礦井,沒到上午休息的時候就會讓老鼠偷吃光了。媽媽說:「等你掙了工資回家,我就給你加一片燻肉。」
比利一開始的工資不會很多,但多多少少能貼補一下家計。他不知道媽媽會給自己多少零用錢,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攢夠錢買一輛單車,這是他最想要的東西。
艾瑟爾坐在桌旁,大問她:「妳在大宅那邊過得還好嗎?」
「挺好,安靜得很。」她說道,「伯爵和公主會去倫敦參加加冕大典。」她看了看壁爐架上的時鐘,「他們快起床了——他們得一早就趕到大教堂。公主不喜歡早起,但她不能在國王面前遲到。」伯爵的妻子貝婭是俄羅斯的公主,地位非常顯赫。
大說道:「他們是要占個前排的位置,讓自己能看得清楚些吧。」
「噢,不是的。你不能想坐哪就坐哪。」艾瑟爾說,「他們特別訂做了六千張桃花心木椅子,背後用金字寫上客人的名字。」
格蘭帕說:「嗯,這可真浪費!典禮後他們會怎麼處理這些椅子?」「我不知道,可能他們會把椅子帶回家做紀念品吧。」
大冷冷地說:「告訴他們留張椅子給咱們家。咱們家只有五口人,但妳媽已經得站著了。」
當大揶揄別人的時候,心中可能是在生氣。艾瑟爾跳了起來。「噢,對不起,媽媽。我剛才不知道妳沒地方坐。」
「妳坐,我忙得沒工夫坐下。」媽媽說道。
時鐘敲了五下,大說道:「小比利,早點去比較好,打起精神來,該出發了。」
比利很不情願地站起身,拿起他的飯盒。
艾瑟爾又親吻了他一下,格蘭帕和他握了握手。大給了他兩根六吋長的釘子,已經鏽跡斑斑,有點彎曲。「把釘子放你褲子口袋裡。」
「幹嘛用的?」比利問道。
「你會知道的。」大微笑著回答。
媽媽給了比利一個帶旋塞的夸脫瓶,裡面裝滿了加牛奶和方糖的茶水。她說道:「好了,比利,記得耶穌總是與你同在,下了礦也一樣。」
「欸,媽媽。」
他看到媽媽眼裡噙著淚花,馬上轉過身去,因為覺得自己也有點想哭了。他從牆釘上取下帽子。「大家再見。」他跟家裡人道別,好像只是去上學一樣,然後走出了前門。
這個夏天一直很晴朗炎熱,但今天是個陰天,而且看起來似乎要下雨。湯米靠在屋子的牆上,正等著他。「欸,欸,比利。」他打了個招呼。
「欸,欸,湯米。」
兩人並肩走在街上。
阿伯羅溫曾經是個小小的集鎮,供山裡的農民過來趕集,比利是在學校學到的。從威靈頓街最上方望下去,可以看到以前的集市中心,那裡有牲畜市場的畜欄、羊毛買賣處和聖公會教堂,都在歐文河的一側(其實這河只是條小溪)。如今一條鐵路像傷口似的橫穿小鎮,一直通往礦口。礦工的房子延伸到山谷的斜坡上,有好幾百間,都是灰石修築的,屋頂鋪著深灰色的威爾斯石板。一排排的房屋順著山勢蜿蜒排列,越過較短的街道一直延伸到山谷下。
「你知道會和誰一起幹活嗎?」湯米問道。
比利聳了聳肩。新的學徒會由礦場經理的副手安排工作。「我怎麼知道。」
「我希望他們能安排我去馬廄。」湯米喜歡馬,礦場裡養了五十匹矮種馬。礦工把礦車填滿後,這些馬就沿著鐵軌把礦車拉上來。「你希望做什麼樣的工作?」
比利希望以自己瘦弱的體格可以不用幹太重的活兒,但他不想承認這一點。「給礦車上油。」他說。
「為什麼?」
「似乎挺簡單的。」他們走過學校,昨天兩人還是裡面的學生。學校是一座維多利亞式的建築,帶有尖尖的窗戶,看上去像座教堂。學校是菲茨伯特家族出資修建的,校長總是不厭其煩提醒學生這件事。伯爵可以任命教師和決定課程。牆上貼滿了講述英勇軍事勝利的圖畫,大英帝國的偉大是永恆的主題。每天的第一堂課是聖經課,灌輸學生嚴苛的英國國教教義,儘管幾乎所有的學生都來自不從國教者的家庭。學校有一個管理委員會,大也是裡面的成員,但委員會只有提建議的權力。大認為伯爵把學校看成是自家私有的財產了。
學校在最後一年教男生關於採礦的知識,教女生如何縫紉做飯。比利覺得很驚訝,原來自己腳下的土地是由不同的土層堆積而成的,就像三明治一樣。煤層——這個詞他一直聽到,但從來沒有真正明白它的意思——就是其中一個土層。學校還教他煤是由爛葉和其他植物沉積在一起,經過數千年上面泥土重壓而形成的。湯米的父親是個無神論者,他說這證明了《聖經》的謬誤,但比利的大認為這只是解釋之一。
這個時候學校裡沒人,操場上空蕩蕩的。比利覺得很驕傲,他已經畢業了,不過,他內心深處還是挺想繼續上學,而不是下礦井去。
隨著礦口越來越近,街上多了許多礦工,每個人都帶著飯盒和茶瓶。他們都穿著舊衣服,一到工作的地方就會脫下來。有的煤礦很冷,不過阿伯羅溫的礦坑挺暖和,所以礦工穿著內衣褲和靴子或粗布短褲在下面工作,還會一直戴著舊帽子,因為礦道很矮,容易碰到頭。
越過房子比利可以看到升降機,那是一座高塔,頂上有兩個往反方向旋轉的大輪子,控制著纜繩把籠子吊上吊下。南威爾斯山谷大部分的城鎮都可以看到類似這樣的礦場,就像在農村可以見到教堂的尖頂一樣。
在礦口周圍環繞著雜亂無章的建築:礦燈房、礦工辦公室、鐵匠鋪和倉庫,鐵軌就在建築群中蜿蜒。在一塊荒地上堆著破損的礦車、開裂的舊枕木、飼料袋和幾堆報廢的機器,上面都覆蓋著一層煤灰。大經常說如果礦工能把東西放得整齊點,事故就會少一些。
一九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英王喬治五世在倫敦西敏寺加冕的那一天,比利.威廉斯在南威爾斯阿伯羅溫鎮下了礦井。
一九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這一天是比利十三歲的生日。他還在睡夢中大(在威爾斯和蘇格蘭地區,稱呼父親為「大」[Da))就把他弄醒了。大弄醒人的辦法很不溫柔,但非常有效。他搧比利的臉頰,以穩定有力的節奏,不把他弄醒不甘休。比利本來睡得正香,一開始他還以為忍忍就算了,但耳光一直搧個不停。他本想發火,但想起自己應該起床。他睜開眼睛,猛地坐起身。
「四點了。」大說了一句,然後走出房間,下樓的時候腳上的靴子把木樓梯弄得震天價響。今天比利就要開始工作了,當礦工學徒,鎮上的人在他這個年紀都幹這個。他希望自己能像個真正的礦工,決心不要讓自己出醜。大衛.克蘭普頓第一天下礦井的時候嚇得又哭又鬧,現在他們還叫他「戴哭包」,儘管他已經二十五歲了,是鎮上橄欖球隊的明星。
眼下是仲夏時節,小小的窗戶外透進一抹明亮的晨光。比利看著躺在身邊的外公。格蘭帕睜著眼睛,只要比利一醒,他也就跟著醒。他總是說老人家睡得不多。
比利下了床,身上只穿著內褲。如果天氣冷,他會穿襯衫睡覺,但現在英國正值明媚的夏天,晚上很暖和。他從床底拉出尿壺,揭開壺蓋。
他的陰莖尺寸還是那樣(他叫它「小弟弟」),一直都是那麼孩子氣的一小根。他原本以為在生日前夕這一夜會長大一些,或者能長出一根黑毛也好,但結果令他很失望。他最好的朋友湯米.格里菲斯和他同一天出生,但湯米的發育要快得多:他已經開始變聲,嘴脣上方長出了黑色的絨毛,小弟弟也像成年人一樣雄壯。比利覺得很丟臉。
往尿壺撒尿的時候,比利看了看窗外,只看見一個煤渣場,上面堆積著石頭、殘渣和煤礦裡運出來的垃圾,都是些瓦礫和沙土。比利心想,上帝創造世界後第二天大概就是這幅光景吧,那時候神還沒說「地要發生青草」。一陣輕風吹過,黑色的沙塵從煤渣上飄起來,飄進一排排的房屋裡。
房間裡沒什麼可看的。這裡是小臥室,狹窄得只能放下一張單人床、一個斗櫃和格蘭帕的舊箱子,牆上掛著一幅刺繡,上面寫著: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第一章
一九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英王喬治五世在倫敦西敏寺加冕的那一天,比利.威廉斯在南威爾斯阿伯羅溫鎮下了礦井。
一九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這一天是比利十三歲的生日。他還在睡夢中大(在威爾斯和蘇格蘭地區,稱呼父親為「大」[Da))就把他弄醒了。大弄醒人的辦法很不溫柔,但非常有效。他搧比利的臉頰,以穩定有力的節奏,不把他弄醒不甘休。比利本來睡得正香,一開始他還以為忍忍就算了,但耳光一直搧個不停。他本想發火,但想起自己應該起床。他睜開眼睛,猛地坐起身。
「四點了。」大說了一句,然後走出房間,下樓的時候腳上的靴子把木樓梯弄得震天價響。今天比利就要開始工作了,當礦工學徒,鎮上的人在他這個年紀都幹這個。他希望自己能像個真正的礦工,決心不要讓自己出醜。大衛.克蘭普頓第一天下礦井的時候嚇得又哭又鬧,現在他們還叫他「戴哭包」,儘管他已經二十五歲了,是鎮上橄欖球隊的明星。
眼下是仲夏時節,小小的窗戶外透進一抹明亮的晨光。比利看著躺在身邊的外公。格蘭帕睜著眼睛,只要比利一醒,他也就跟著醒。他總是說老人家睡得不多。
比利下了床,身上只穿著內褲。如果天氣冷,他會穿襯衫睡覺,但現在英國正值明媚的夏天,晚上很暖和。他從床底拉出尿壺,揭開壺蓋。
他的陰莖尺寸還是那樣(他叫它「小弟弟」),一直都是那麼孩子氣的一小根。他原本以為在生日前夕這一夜會長大一些,或者能長出一根黑毛也好,但結果令他很失望。他最好的朋友湯米.格里菲斯和他同一天出生,但湯米的發育要快得多:他已經開始變聲,嘴脣上方長出了黑色的絨毛,小弟弟也像成年人一樣雄壯。比利覺得很丟臉。
往尿壺撒尿的時候,比利看了看窗外,只看見一個煤渣場,上面堆積著石頭、殘渣和煤礦裡運出來的垃圾,都是些瓦礫和沙土。比利心想,上帝創造世界後第二天大概就是這幅光景吧,那時候神還沒說「地要發生青草」。一陣輕風吹過,黑色的沙塵從煤渣上飄起來,飄進一排排的房屋裡。
房間裡沒什麼可看的。這裡是小臥室,狹窄得只能放下一張單人床、一個斗櫃和格蘭帕的舊箱子,牆上掛著一幅刺繡,上面寫著: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屋裡連鏡子也沒有。
房間的一扇門通往樓梯,另一扇門通往主臥室,只有從這扇門才能進去那裡。主臥室要寬敞一些,放得下兩張床。大和媽在這間房睡覺,幾年前比利的幾個姊姊也在這裡睡覺。大姊艾瑟爾已經離家工作,而另外三個姊姊都早夭了,一個死於麻疹,一個死於百日咳,一個死於白喉。比利還有過一個哥哥,在格蘭帕來之前和比利一塊睡。他的名字叫威斯利,在一次礦車脫軌事故中喪生。
比利穿上他唯一的襯衫。昨天他才穿去上學,今天是星期四,只有到了星期天他才會換洗襯衫。不過,他有一條新褲子,生平第一條,料子是厚厚的防水斜紋棉布。這條褲子象徵著他進入了男人的世界,他驕傲地穿上新褲子,感受布料那種厚重陽剛的感覺,覺得滿心歡喜。他穿上威斯利遺留下來的厚皮革腰帶和靴子,然後走下樓去。
樓下那一層主要是客廳,有十五平方呎大,中間擺了張桌子,一側是壁爐,地板上鋪著一張自家織的毯子。大正坐在桌旁讀著過期的《每日郵報》,長而尖的鼻子上架著一副眼鏡。媽媽正在泡茶。她放下冒著熱氣的水壺,親了親比利的額頭,說:「我的小男子漢,今天你生日,覺得怎麼樣啊?」
比利沒有回答。「小」這個字讓他有點受傷,因為他的確還小,而「男子漢」也刺痛了他,因為他還不是真正的男子漢。他走進屋後的洗滌室,用一個錫碗從水桶裡盛水洗了臉和手,然後把水倒進淺淺的石頭水槽裡。洗滌室有一個燒水的大銅壺,下頭有爐篦,但只有洗澡的時候才會用,也就是星期六。
政府答應他們很快會有自來水,一些礦工的屋子裡已經接通了。在比利看來,只要輕輕轉開水龍頭就有一杯涼快清冽的水喝,不用挑著水桶到街上的水塔去接水,實在是個奇蹟。不過威廉斯一家住的威靈頓街這一帶還沒有接通管道。
他回到客廳,坐在桌子旁邊。媽媽在他面前擺了一大杯奶茶,裡面加好了糖。她從自家做的麵包塊上切了兩片厚實的麵包,從樓梯底下的餐具櫃那裡拿出了一大片牛脂。比利雙手合十,閉上眼睛,祈禱道:「感謝主賜予我們食物,阿門。」然後喝了幾口奶茶,把牛脂塗在麵包片上。
大的灰藍色眼睛從報紙上方望出。「麵包上加點鹽,在礦井下你會流汗。」比利的父親是礦工的代表,受雇於南威爾斯礦工聯盟,他一有機會總是說這個聯盟是英國最強大的工會組織。大家都叫他戴工會。許多名叫大衛或達維德的人會把自己的名字簡稱為「戴」,這是威爾斯的習慣。比利在學校裡得知大衛這個名字在威爾斯很流行,因為這是這片土地的守護聖徒之名,就像在愛爾蘭,很多人以那裡的守護聖徒派崔克為名。所有名字都叫「戴」的人並不靠姓氏來區分彼此,因為鎮裡的人無非就是姓瓊斯、威廉斯、伊文斯或摩根。他們靠綽號來區分,有了好玩的綽號,本名也就很少用了。比利的本名是威廉.威廉斯,大家都叫他比利雙雙。女人通常冠上丈夫的綽號,所以他們稱呼媽媽為戴工會太太。
比利吃著第二片麵包的時候,格蘭帕下來了。儘管天氣很暖和,他還是穿著夾克和背心。他洗完手後坐在比利對面。「別那麼緊張,」他說,「我十歲就下礦了。我父親五歲就被我爺爺扛在肩膀上跟著下礦,從早上六點一直幹到晚上七點。從十月到隔年三月,他都沒見過太陽。」
「我可不緊張。」比利說道。其實他在說謊,心裡慌著呢。
幸好格蘭帕沒有就這個問題窮追不捨。比利喜歡格蘭帕。媽媽把他當成了小寶寶,大總是很嚴厲,而且老是嘲笑他,但格蘭帕很有耐心,和比利說話的時候當他是個大人。
「聽聽這條新聞。」大說道。他從不買右翼的《郵報》,但有時他會把別人的報紙帶回家,用譏諷的語氣讀報紙給大家聽,嘲笑統治階級的愚蠢和虛偽。「戴安娜.曼那斯夫人因穿同一件服裝出席兩場舞會而飽受批評。這位拉特蘭郡公爵的小女兒在薩伏伊舞會上贏得了『最佳著裝獎』,得到兩百五十基尼獎金。她當時穿的是一件露肩緊身馬甲上衣和帶裙襯的長裙。」他放下報紙,說道:「那至少是你五年的工資,小比利。」他繼續讀報:「但服裝界批評她以同樣的裝扮參加了溫特頓勳爵和F.E.史密斯爵士在克拉里奇酒店舉行的舞會。常言道:再好的東西多了也令人厭倦。」他抬起頭。「妳那身衣服得換一下了,媽媽,」他說,「不然的話服裝界會批評妳的。」
媽媽並不覺得好笑。她穿著破舊的棕色羊毛洋裝,肘處打著補丁,腋下有兩團汙漬。「假如我有兩百五十基尼,我會比那個戴安娜.馬拉屎更美麗動人。」她說道,語氣不無苦澀。「對啊。」格蘭帕說,「卡拉一直都是個美人,長得像她媽媽。」卡拉是媽媽的名字。格蘭帕轉向比利。「你外婆是義大利人,名字叫瑪麗亞.費羅內。」比利知道外婆的名字,但格蘭帕就是喜歡翻來覆去講一樣的事情。「你媽媽繼承了她柔順的黑髮和動人的黑眸,你姊姊也是。你外婆是卡地夫最漂亮的女孩,而我娶了她。」他突然一臉傷感。「這些都已經是往事了。」他輕聲說道。
大皺了皺眉頭——外公的這番話似乎暗示了肉體的歡娛——但媽媽聽到外公的讚美心裡喜孜孜的,面帶微笑把早餐擺在他的面前。她說:「噢,欸,我和姊妹以前可都稱得上是美女。假如買得起綢緞和蕾絲的話,我們會讓那些貴族老爺看看美女到底長什麼樣。」
比利有點驚訝,他可從來沒想過媽媽漂不漂亮,儘管星期六晚上她打扮一番去禮拜堂的時候,看上去也挺動人的,尤其是戴著帽子的時候。他猜想或許媽媽以前真的漂亮過,但實在挺難想像。
「提醒你一句,」格蘭帕說,「你外婆的家族還很聰明。我的大舅子原本是個礦工,後來他不幹這行了,在騰比開了間咖啡廳,現在過上好日子了,整天享受海風,什麼也不用幹,只要煮咖啡和數錢。」
大又讀了一則新聞。「為籌備加冕大典,白金漢宮專門撰寫了一本長達二百一十二頁的手冊。」他抬起視線,「告訴下面的人這則新聞,比利,他們會覺得放心的,所有的事情王室都安排得很周全。」
比利對王室的事情並不感興趣。他喜歡的是《郵報》上刊登的冒險故事,裡面講述中學裡那些玩橄欖球的猛男怎麼逮到狡猾的德國間諜。根據報紙上所說,德國在英國每個鎮裡都安插了間諜,不過,阿伯羅溫這裡似乎一個也沒有,真叫人失望。
比利站起身,宣布道:「我上街一趟。」他從前門走出了屋子。「上街一趟」是家裡的委婉說法,意思是上廁所,要走過威靈頓街的一半才到。廁所是一間低矮的磚房,屋頂鋪了波浪鐵皮,就在地上挖一個深坑做地基建起來的。磚房隔成兩間,一間是男廁,一間是女廁。每一間都有兩個廁位,所以可以兩兩結伴同行。沒有人知道為什麼建造者會這麼安排,但大家都將就著用。男人通常都是目視前方,一言不發,但比利總是聽到隔壁傳來女人聊天的聲音。廁所裡臭氣熏天,即使你每天都到裡面如廁也感覺受不了。比利在裡面時總是盡可能不呼吸,出來後再大口大口地喘氣。有個叫「戴倒屎」的人會定期用鏟子把糞便鏟出來。比利回到家裡時,欣喜地看到姊姊艾瑟爾正坐在桌旁。「生日快樂,比利!」她叫嚷著,「我過來看你,在你下礦井之前親你一下。」
艾瑟爾十八歲了,比利覺得姊姊是個大美人。她有一頭濃密的紅褐色鬈髮,黑色的雙眸閃爍著調皮的光芒。或許,媽媽以前也有這般的美貌。艾瑟爾穿著簡樸的黑洋裝,戴著一頂家庭女僕的白棉帽,她很喜歡這身裝扮。
比利很崇拜姊姊。她不但美麗動人,而且聰明伶俐又詼諧勇敢,有時甚至敢頂撞大。她告訴比利別人根本不會講的事情,像是婦女稱之為「詛咒」的月經,還有讓本地的聖公會牧師匆忙離開小鎮的公然猥褻罪指的是什麼。上學的時候她一直在班裡名列前茅。在《南威爾斯之聲報》舉辦的作文比賽中,她的作文〈我的家鄉〉獲得了一等獎,獎品是一本《卡塞爾世界地圖冊》。
她親了親比利的臉頰。「我跟管家傑文茲太太說鞋油用完了,得到鎮裡買一些。」艾瑟爾在菲茨伯特伯爵的白公館裡工作,也住在那兒,那是一間位於半山的豪宅,離小鎮有一哩遠。她遞給比利一塊乾淨的棉布,裡面包著東西。「我偷了塊蛋糕給你。」
「噢,謝謝妳,艾絲。」比利說道。他喜歡吃蛋糕。
媽媽說:「我把蛋糕放飯盒裡好嗎?」
「欸,好啊。」
媽媽從碗櫥裡拿出一個馬口鐵盒子,把蛋糕放進去。然後切了兩片麵包,往上面淋上牛脂,撒了點鹽,也放進盒子裡。所有的礦工都自帶飯盒,如果把食物包在布裡帶下礦井,沒到上午休息的時候就會讓老鼠偷吃光了。媽媽說:「等你掙了工資回家,我就給你加一片燻肉。」
比利一開始的工資不會很多,但多多少少能貼補一下家計。他不知道媽媽會給自己多少零用錢,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攢夠錢買一輛單車,這是他最想要的東西。
艾瑟爾坐在桌旁,大問她:「妳在大宅那邊過得還好嗎?」
「挺好,安靜得很。」她說道,「伯爵和公主會去倫敦參加加冕大典。」她看了看壁爐架上的時鐘,「他們快起床了——他們得一早就趕到大教堂。公主不喜歡早起,但她不能在國王面前遲到。」伯爵的妻子貝婭是俄羅斯的公主,地位非常顯赫。
大說道:「他們是要占個前排的位置,讓自己能看得清楚些吧。」
「噢,不是的。你不能想坐哪就坐哪。」艾瑟爾說,「他們特別訂做了六千張桃花心木椅子,背後用金字寫上客人的名字。」
格蘭帕說:「嗯,這可真浪費!典禮後他們會怎麼處理這些椅子?」「我不知道,可能他們會把椅子帶回家做紀念品吧。」
大冷冷地說:「告訴他們留張椅子給咱們家。咱們家只有五口人,但妳媽已經得站著了。」
當大揶揄別人的時候,心中可能是在生氣。艾瑟爾跳了起來。「噢,對不起,媽媽。我剛才不知道妳沒地方坐。」
「妳坐,我忙得沒工夫坐下。」媽媽說道。
時鐘敲了五下,大說道:「小比利,早點去比較好,打起精神來,該出發了。」
比利很不情願地站起身,拿起他的飯盒。
艾瑟爾又親吻了他一下,格蘭帕和他握了握手。大給了他兩根六吋長的釘子,已經鏽跡斑斑,有點彎曲。「把釘子放你褲子口袋裡。」
「幹嘛用的?」比利問道。
「你會知道的。」大微笑著回答。
媽媽給了比利一個帶旋塞的夸脫瓶,裡面裝滿了加牛奶和方糖的茶水。她說道:「好了,比利,記得耶穌總是與你同在,下了礦也一樣。」
「欸,媽媽。」
他看到媽媽眼裡噙著淚花,馬上轉過身去,因為覺得自己也有點想哭了。他從牆釘上取下帽子。「大家再見。」他跟家裡人道別,好像只是去上學一樣,然後走出了前門。
這個夏天一直很晴朗炎熱,但今天是個陰天,而且看起來似乎要下雨。湯米靠在屋子的牆上,正等著他。「欸,欸,比利。」他打了個招呼。
「欸,欸,湯米。」
兩人並肩走在街上。
阿伯羅溫曾經是個小小的集鎮,供山裡的農民過來趕集,比利是在學校學到的。從威靈頓街最上方望下去,可以看到以前的集市中心,那裡有牲畜市場的畜欄、羊毛買賣處和聖公會教堂,都在歐文河的一側(其實這河只是條小溪)。如今一條鐵路像傷口似的橫穿小鎮,一直通往礦口。礦工的房子延伸到山谷的斜坡上,有好幾百間,都是灰石修築的,屋頂鋪著深灰色的威爾斯石板。一排排的房屋順著山勢蜿蜒排列,越過較短的街道一直延伸到山谷下。
「你知道會和誰一起幹活嗎?」湯米問道。
比利聳了聳肩。新的學徒會由礦場經理的副手安排工作。「我怎麼知道。」
「我希望他們能安排我去馬廄。」湯米喜歡馬,礦場裡養了五十匹矮種馬。礦工把礦車填滿後,這些馬就沿著鐵軌把礦車拉上來。「你希望做什麼樣的工作?」
比利希望以自己瘦弱的體格可以不用幹太重的活兒,但他不想承認這一點。「給礦車上油。」他說。
「為什麼?」
「似乎挺簡單的。」他們走過學校,昨天兩人還是裡面的學生。學校是一座維多利亞式的建築,帶有尖尖的窗戶,看上去像座教堂。學校是菲茨伯特家族出資修建的,校長總是不厭其煩提醒學生這件事。伯爵可以任命教師和決定課程。牆上貼滿了講述英勇軍事勝利的圖畫,大英帝國的偉大是永恆的主題。每天的第一堂課是聖經課,灌輸學生嚴苛的英國國教教義,儘管幾乎所有的學生都來自不從國教者的家庭。學校有一個管理委員會,大也是裡面的成員,但委員會只有提建議的權力。大認為伯爵把學校看成是自家私有的財產了。
學校在最後一年教男生關於採礦的知識,教女生如何縫紉做飯。比利覺得很驚訝,原來自己腳下的土地是由不同的土層堆積而成的,就像三明治一樣。煤層——這個詞他一直聽到,但從來沒有真正明白它的意思——就是其中一個土層。學校還教他煤是由爛葉和其他植物沉積在一起,經過數千年上面泥土重壓而形成的。湯米的父親是個無神論者,他說這證明了《聖經》的謬誤,但比利的大認為這只是解釋之一。
這個時候學校裡沒人,操場上空蕩蕩的。比利覺得很驕傲,他已經畢業了,不過,他內心深處還是挺想繼續上學,而不是下礦井去。
隨著礦口越來越近,街上多了許多礦工,每個人都帶著飯盒和茶瓶。他們都穿著舊衣服,一到工作的地方就會脫下來。有的煤礦很冷,不過阿伯羅溫的礦坑挺暖和,所以礦工穿著內衣褲和靴子或粗布短褲在下面工作,還會一直戴著舊帽子,因為礦道很矮,容易碰到頭。
越過房子比利可以看到升降機,那是一座高塔,頂上有兩個往反方向旋轉的大輪子,控制著纜繩把籠子吊上吊下。南威爾斯山谷大部分的城鎮都可以看到類似這樣的礦場,就像在農村可以見到教堂的尖頂一樣。
在礦口周圍環繞著雜亂無章的建築:礦燈房、礦工辦公室、鐵匠鋪和倉庫,鐵軌就在建築群中蜿蜒。在一塊荒地上堆著破損的礦車、開裂的舊枕木、飼料袋和幾堆報廢的機器,上面都覆蓋著一層煤灰。大經常說如果礦工能把東西放得整齊點,事故就會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