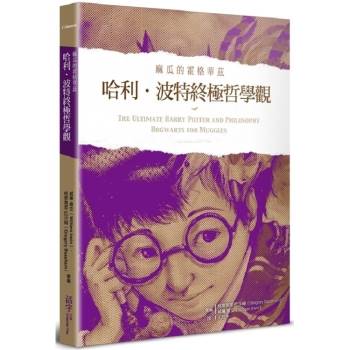9. 鄧不利多、柏拉圖、和權力的慾望
大衛.賴.威廉斯(David Lay Williams)和亞倫.J.凱爾納(Alan J. Kellner)
最適合擁有權力的人,是那些從不曾追逐權力的人。――阿不思.鄧不利多
一個城市中即將成為統治者的是最沒有統治慾望的人,那必定是最好的城市。――柏拉圖
阿克頓男爵有句常被引述的話,說道「權力會使人腐化,而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這句話俐落地道出了許多人公認的日常智慧。然而,這世界卻從來都不缺權力遭濫用的例子。統治者一直在發掘更新更有創意的方式來中飽私囊、賦予朋友特權、鞏固甚至更強化自身的威權。羅列出來的罪刑,甚至會讓許多食死人吃驚――或者可能讓他們很羨慕。
在一個因科技進展、甚至是道德提升而自豪的年代裡,為什麼我們在保護自己免於領導者侵占篡奪的方面會沒什麼長進?或許是因為我們還沒學會第一位西方政治哲學家柏拉圖(Plato,西元前約428-348年)教導我們的事。柏拉圖對此事的解決方案明確又簡單:權力絕對不應落入那些渴望權力的人手中。相反地,權力應該只賦予那些寧願去忙別的事情的人。很矛盾地,那些對權力不感興趣的人,反而會是最好的領導人。這個教訓,碰巧是哈利.波特系列整個結尾高潮中的重要元素。柏拉圖和鄧不利多:失散的兄弟?
阿不思.鄧不利多生活在一個風風雨雨的年代。他見到了黑魔法巫師蓋瑞.葛林戴華德(Gellert Grindelwald)的崛起和殞落,也經歷了佛地魔的恐怖統治。他見過交戰衝突,有他帶著魔杖親身參與戰鬥的,也有較微妙型態的交鋒,像是集結盟友或是收集情資。他和整個系列中幾個最重要的角色有私人交情。葛林戴華德是他童年的好友,而佛地魔則是霍格華茲最傑出的學生之一。這些經驗讓鄧不利多了解到,和平有多麼不穩定,以及擁有真正耿直的領導者有多重要。
柏拉圖也是生長在一個政治異常動盪的時代。他整個青年時期都在長達數十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中渡過,那是他的家鄉雅典城與強大城邦斯巴達之間的戰爭。這場戰爭和其餘波提供了很好的機會,可以觀察到人性最好以及最糟的一面。和鄧不利多一樣,柏拉圖見證了才華洋溢卻又對權力飢渴的同學阿爾西比亞德斯(Alcibiades)崛起,性格狂暴的阿爾西比亞德斯掌握了軍事和政治權位,後來又背叛了雅典,與敵人斯巴達為伍。雅典最後輸了戰爭,被迫接受暴政統治而蒙羞,統治者是斯巴達的「三十人僭主集團」(the Thirty),以令人畏懼的克里提亞斯(Critias)為首。克里提亞斯是個兇殘嗜血的暴君,碰巧又是柏拉圖母親的堂表親。數年後,柏拉圖受邀前往敘拉古(Syracuse),協助訓練大狄奧尼西奧斯(Dionysius I)的任性兒子。和鄧不利多一樣,柏拉圖也曾認真考慮從政――考量到其才能、家世和個人經驗,這算是個合乎常理的選擇。因此,儘管柏拉圖有時候會被認為是個不食人間煙火的哲學家,但這和真實情況相差了十萬八千里。他對政客以及他們與權力關係的觀察,是根據真實經歷而來的。
柏拉圖在與政治權勢的接觸中學到了什麼?他對於自身經歷最詳細的回應,記錄在他的「第七封信」(Seventh Letter)裡,是寫給敘拉古(Syracuse)統治者的。信中提及他自身在政治權力中打滾的經歷,包括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後曾有機會加入三十人僭主集團。起初,他深受吸引想加入他們,以打造新的社會,或許也能創造「更偉大的利益」,就如同年輕時的鄧不利多和葛林戴華德所渴望的。但他很快就發現自己無法加入這個新的政體,這新政體「相較之下讓前政府看起來像黃金一樣珍貴。」暴君擁有無限度的權力,也因此被權力沖昏了頭,展開了報復仇殺、清算舊帳、充公私人財富、而且最後在存續的民主下,不義地處死了柏拉圖摯愛的老師蘇格拉底。這已足以讓柏拉圖「厭惡地退出」政治生活,最終全職奉獻於哲學,就如同和葛林戴華德的決鬥造成鄧不利多的妹妹死亡,因而改變了鄧不利多對政治生命的想法。
和鄧不利多一樣,柏拉圖放棄政治,轉投入教育。對政治的不滿,引領他創設了學院(the Academy),這是西方文明中的第一所大學,而學院也是現代英文學者(academic)一詞的根源。柏拉圖也在學院裡體驗到一些人生最大的勝利。柏拉圖學院著名的校友包括哲學家西塞羅(Cicero)以及柏拉圖自己的門生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柏拉圖在學院教學期間,也寫下許多個人最著名的著作,涵蓋的主題相當廣泛,包括藝術、倫理學、科學、數學、哲學、甚至還有愛。因此,鄧不利多和柏拉圖兩人都是放下政治的重擔和誘惑,並在教導年輕學子中找到了慰藉。
然而,柏拉圖雖然退出了政治圈,但卻沒有放棄關於政治的系統性思考――這點也很類似鄧不利多,他在霍格華茲擔任教授期間仍參與了關於魔法政策的事物。柏拉圖發現學院是用來反思政治世界,並把自身經歷提升為智慧的最佳地點。他的政治哲學完整且巧妙地呈現在他的著作《理想國》裡。書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提議,或許是一個由哲學家統治的城邦。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描繪的理想社會,包含三個階層――勞動階層、軍人、和領導者。最後這個階層擁有所有的政策制訂權力,並且要管理日常國家事務。柏拉圖的哲學家領導者擁有巨大的權力,因此很重要的是他們一定要是最優秀且最有資格領導的人。尤其是,他們必須擁有全部四種「基本德行」(cardinal virtues):正義、勇氣、智慧、和自制。為了確保唯有最具智慧且最正直的人才能成為領導者,柏拉圖提出了嚴苛且長期的教育過程,目的是要從眾人中篩選出菁英。這教育過程一直持續到三十五歲,而且需要在公職擔任十五年的實習生。這整個過程會讓霍格華茲感到汗顏。最後,柏拉圖希望,如此我們應該就能夠分辨出波特和馬份。
當然,柏拉圖認為領導者最重要的特質是智識(intelligence)。他一再表明,領導者必須要學習能力強,而且擁有不凡的好記性。想當然柏拉圖經常被稱作是第一位公開提倡將政治權力與智識相結合的哲學家。確實,這也是為什麼他堅稱唯一合格的領導人是哲人領導人(philosopher ruler)――因為哲人在大腦智力方面超越他人。
雖說這或許是柏拉圖認定領導人特質中最知名的元素,但單有智力並不足夠。從大眾文化中,我們看到許多傑出的罪犯都把自身的天賦用到了狡詐的意圖上――《超人》裡的雷克斯.路瑟(Lex Luther)、《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裡的漢尼拔.萊克特(Hannibal Lecter)、《星際大戰》(Star Wars)裡的安納金.天行者(Anakin Skywalker)、以及《王牌大賤諜》(Austin Powers)裡的邪惡博士(Dr. Evil)。智能或許是擔任領導人的首要條件,但柏拉圖要求的不只是顆超級聰明的腦袋。領導人除了有腦袋外,也要有德行。問題在於――不管對柏拉圖或對波特系列來說――要如何辨別哪些有天賦才華的人會運用自身的能力來做好事,哪些人會把天賦用於自私的目的上。特別是,那些過度愛自己的人並不適合當領導人。他們通常是最有聰明才智的學生,但很難抗拒自身的衝動,也招架不住拍他們馬屁的人。和佛地魔一樣,他們認為政治權力是滿足個人慾望的管道,因此他們渴望權力。他們貪求權力,並且使出渾身解數來取得權力。但正是這種對權力的渴求,暗示了他們並不適合行使權力,根據柏拉圖表示:「當統治權是爭鬥而來的……內戰摧毀了這些人,也毀了城市其餘的部分。」像克里提亞斯這樣的暴君通常很短命,而且會帶著整個國家一起陪葬。回想一下佛地魔的例子,他的人生――實際肉身存在的時間――也是相當短暫。在《神秘的魔法石》裡,他必須引用獨角獸的血才能恢復氣力;他必須吸取他人的生命,才能再次恢復實體的型態。儘管柏拉圖認為魔法無法用來拯救一個人,但他對於暴君的分析,仍然適用於哈利的世界。因此,我們應該要去找出對於掌握政治權力沒有興趣的人:「一個城市中即將成為統治者的是最沒有統治慾望的人,那必定是最好的城市。」
柏拉圖提供了一個有用的測試,幫助讀者辨別哪些人可能會屈服於權力的誘惑,以及哪些人可以抵抗權力的誘惑;那是一個題為「蓋吉斯的隱形戒指」(Ring of Gyges)的故事,而J.K.羅琳也在《死神的聖物》裡透過哈利的隱形斗篷(稍後會再討論)來致敬重現這則故事。柏拉圖的這則故事,是由《理想國》中的角色葛勞康(Glaucon)來述說,而葛勞康實際上在真實世界中是柏拉圖的兄弟。根據該故事,一個牧羊人在地震後找到一只神奇的戒指,並且發現只要把戒指轉向自己,他就能隱形。著迷於這項新的能力下,原本謙虛的牧羊人立即設計引誘國王的妻子,在她的協助下攻擊並殺死了國王,奪下王位,這一連串事件是在很短的期間內發生。葛勞康指出,「當能夠在市場上任意拿取想要的東西而不會被懲罰、能夠走進他人的屋裡跟任何自己想要的人發生性關係、能夠殺害任何想殺的人、能夠從牢裡釋放任何想釋放的犯人、能夠做所有使自己在人群中看起來像是神一樣的事情時,沒有人……會如此地不被腐化,以至於堅持遵循正義,或讓自己遠離他人的財物,不去觸碰。」
柏拉圖暗示的回應是,葛勞康的結論只適用於那些渴求權力的人。那些真正良善和正義的人――也就是那些適合掌政權的人――不管自己是不是能隱形,行為舉止都不會改變。對那些少數合格的人來說,他們並沒有野心想要踏過友人或同胞的利益,來滿足自己的私慾。因此,隱形也不會給他們帶來政治利益。說到底,柏拉圖希望政治權力落在那些有智慧也有道德的人手中。這些特質,最可能出現在那些對權力的誘惑絲毫不感興趣的極少數人身上。蓋吉斯的隱形戒指,是用來分辨哪些人能被信任授予這類權力的最佳測試之一。的確,這個關於誰能抵抗權力誘惑的問題,是哈利.波特系列中值得探索的一個核心問題,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那個問題。
大衛.賴.威廉斯(David Lay Williams)和亞倫.J.凱爾納(Alan J. Kellner)
最適合擁有權力的人,是那些從不曾追逐權力的人。――阿不思.鄧不利多
一個城市中即將成為統治者的是最沒有統治慾望的人,那必定是最好的城市。――柏拉圖
阿克頓男爵有句常被引述的話,說道「權力會使人腐化,而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這句話俐落地道出了許多人公認的日常智慧。然而,這世界卻從來都不缺權力遭濫用的例子。統治者一直在發掘更新更有創意的方式來中飽私囊、賦予朋友特權、鞏固甚至更強化自身的威權。羅列出來的罪刑,甚至會讓許多食死人吃驚――或者可能讓他們很羨慕。
在一個因科技進展、甚至是道德提升而自豪的年代裡,為什麼我們在保護自己免於領導者侵占篡奪的方面會沒什麼長進?或許是因為我們還沒學會第一位西方政治哲學家柏拉圖(Plato,西元前約428-348年)教導我們的事。柏拉圖對此事的解決方案明確又簡單:權力絕對不應落入那些渴望權力的人手中。相反地,權力應該只賦予那些寧願去忙別的事情的人。很矛盾地,那些對權力不感興趣的人,反而會是最好的領導人。這個教訓,碰巧是哈利.波特系列整個結尾高潮中的重要元素。柏拉圖和鄧不利多:失散的兄弟?
阿不思.鄧不利多生活在一個風風雨雨的年代。他見到了黑魔法巫師蓋瑞.葛林戴華德(Gellert Grindelwald)的崛起和殞落,也經歷了佛地魔的恐怖統治。他見過交戰衝突,有他帶著魔杖親身參與戰鬥的,也有較微妙型態的交鋒,像是集結盟友或是收集情資。他和整個系列中幾個最重要的角色有私人交情。葛林戴華德是他童年的好友,而佛地魔則是霍格華茲最傑出的學生之一。這些經驗讓鄧不利多了解到,和平有多麼不穩定,以及擁有真正耿直的領導者有多重要。
柏拉圖也是生長在一個政治異常動盪的時代。他整個青年時期都在長達數十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中渡過,那是他的家鄉雅典城與強大城邦斯巴達之間的戰爭。這場戰爭和其餘波提供了很好的機會,可以觀察到人性最好以及最糟的一面。和鄧不利多一樣,柏拉圖見證了才華洋溢卻又對權力飢渴的同學阿爾西比亞德斯(Alcibiades)崛起,性格狂暴的阿爾西比亞德斯掌握了軍事和政治權位,後來又背叛了雅典,與敵人斯巴達為伍。雅典最後輸了戰爭,被迫接受暴政統治而蒙羞,統治者是斯巴達的「三十人僭主集團」(the Thirty),以令人畏懼的克里提亞斯(Critias)為首。克里提亞斯是個兇殘嗜血的暴君,碰巧又是柏拉圖母親的堂表親。數年後,柏拉圖受邀前往敘拉古(Syracuse),協助訓練大狄奧尼西奧斯(Dionysius I)的任性兒子。和鄧不利多一樣,柏拉圖也曾認真考慮從政――考量到其才能、家世和個人經驗,這算是個合乎常理的選擇。因此,儘管柏拉圖有時候會被認為是個不食人間煙火的哲學家,但這和真實情況相差了十萬八千里。他對政客以及他們與權力關係的觀察,是根據真實經歷而來的。
柏拉圖在與政治權勢的接觸中學到了什麼?他對於自身經歷最詳細的回應,記錄在他的「第七封信」(Seventh Letter)裡,是寫給敘拉古(Syracuse)統治者的。信中提及他自身在政治權力中打滾的經歷,包括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後曾有機會加入三十人僭主集團。起初,他深受吸引想加入他們,以打造新的社會,或許也能創造「更偉大的利益」,就如同年輕時的鄧不利多和葛林戴華德所渴望的。但他很快就發現自己無法加入這個新的政體,這新政體「相較之下讓前政府看起來像黃金一樣珍貴。」暴君擁有無限度的權力,也因此被權力沖昏了頭,展開了報復仇殺、清算舊帳、充公私人財富、而且最後在存續的民主下,不義地處死了柏拉圖摯愛的老師蘇格拉底。這已足以讓柏拉圖「厭惡地退出」政治生活,最終全職奉獻於哲學,就如同和葛林戴華德的決鬥造成鄧不利多的妹妹死亡,因而改變了鄧不利多對政治生命的想法。
和鄧不利多一樣,柏拉圖放棄政治,轉投入教育。對政治的不滿,引領他創設了學院(the Academy),這是西方文明中的第一所大學,而學院也是現代英文學者(academic)一詞的根源。柏拉圖也在學院裡體驗到一些人生最大的勝利。柏拉圖學院著名的校友包括哲學家西塞羅(Cicero)以及柏拉圖自己的門生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柏拉圖在學院教學期間,也寫下許多個人最著名的著作,涵蓋的主題相當廣泛,包括藝術、倫理學、科學、數學、哲學、甚至還有愛。因此,鄧不利多和柏拉圖兩人都是放下政治的重擔和誘惑,並在教導年輕學子中找到了慰藉。
然而,柏拉圖雖然退出了政治圈,但卻沒有放棄關於政治的系統性思考――這點也很類似鄧不利多,他在霍格華茲擔任教授期間仍參與了關於魔法政策的事物。柏拉圖發現學院是用來反思政治世界,並把自身經歷提升為智慧的最佳地點。他的政治哲學完整且巧妙地呈現在他的著作《理想國》裡。書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提議,或許是一個由哲學家統治的城邦。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描繪的理想社會,包含三個階層――勞動階層、軍人、和領導者。最後這個階層擁有所有的政策制訂權力,並且要管理日常國家事務。柏拉圖的哲學家領導者擁有巨大的權力,因此很重要的是他們一定要是最優秀且最有資格領導的人。尤其是,他們必須擁有全部四種「基本德行」(cardinal virtues):正義、勇氣、智慧、和自制。為了確保唯有最具智慧且最正直的人才能成為領導者,柏拉圖提出了嚴苛且長期的教育過程,目的是要從眾人中篩選出菁英。這教育過程一直持續到三十五歲,而且需要在公職擔任十五年的實習生。這整個過程會讓霍格華茲感到汗顏。最後,柏拉圖希望,如此我們應該就能夠分辨出波特和馬份。
當然,柏拉圖認為領導者最重要的特質是智識(intelligence)。他一再表明,領導者必須要學習能力強,而且擁有不凡的好記性。想當然柏拉圖經常被稱作是第一位公開提倡將政治權力與智識相結合的哲學家。確實,這也是為什麼他堅稱唯一合格的領導人是哲人領導人(philosopher ruler)――因為哲人在大腦智力方面超越他人。
雖說這或許是柏拉圖認定領導人特質中最知名的元素,但單有智力並不足夠。從大眾文化中,我們看到許多傑出的罪犯都把自身的天賦用到了狡詐的意圖上――《超人》裡的雷克斯.路瑟(Lex Luther)、《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裡的漢尼拔.萊克特(Hannibal Lecter)、《星際大戰》(Star Wars)裡的安納金.天行者(Anakin Skywalker)、以及《王牌大賤諜》(Austin Powers)裡的邪惡博士(Dr. Evil)。智能或許是擔任領導人的首要條件,但柏拉圖要求的不只是顆超級聰明的腦袋。領導人除了有腦袋外,也要有德行。問題在於――不管對柏拉圖或對波特系列來說――要如何辨別哪些有天賦才華的人會運用自身的能力來做好事,哪些人會把天賦用於自私的目的上。特別是,那些過度愛自己的人並不適合當領導人。他們通常是最有聰明才智的學生,但很難抗拒自身的衝動,也招架不住拍他們馬屁的人。和佛地魔一樣,他們認為政治權力是滿足個人慾望的管道,因此他們渴望權力。他們貪求權力,並且使出渾身解數來取得權力。但正是這種對權力的渴求,暗示了他們並不適合行使權力,根據柏拉圖表示:「當統治權是爭鬥而來的……內戰摧毀了這些人,也毀了城市其餘的部分。」像克里提亞斯這樣的暴君通常很短命,而且會帶著整個國家一起陪葬。回想一下佛地魔的例子,他的人生――實際肉身存在的時間――也是相當短暫。在《神秘的魔法石》裡,他必須引用獨角獸的血才能恢復氣力;他必須吸取他人的生命,才能再次恢復實體的型態。儘管柏拉圖認為魔法無法用來拯救一個人,但他對於暴君的分析,仍然適用於哈利的世界。因此,我們應該要去找出對於掌握政治權力沒有興趣的人:「一個城市中即將成為統治者的是最沒有統治慾望的人,那必定是最好的城市。」
柏拉圖提供了一個有用的測試,幫助讀者辨別哪些人可能會屈服於權力的誘惑,以及哪些人可以抵抗權力的誘惑;那是一個題為「蓋吉斯的隱形戒指」(Ring of Gyges)的故事,而J.K.羅琳也在《死神的聖物》裡透過哈利的隱形斗篷(稍後會再討論)來致敬重現這則故事。柏拉圖的這則故事,是由《理想國》中的角色葛勞康(Glaucon)來述說,而葛勞康實際上在真實世界中是柏拉圖的兄弟。根據該故事,一個牧羊人在地震後找到一只神奇的戒指,並且發現只要把戒指轉向自己,他就能隱形。著迷於這項新的能力下,原本謙虛的牧羊人立即設計引誘國王的妻子,在她的協助下攻擊並殺死了國王,奪下王位,這一連串事件是在很短的期間內發生。葛勞康指出,「當能夠在市場上任意拿取想要的東西而不會被懲罰、能夠走進他人的屋裡跟任何自己想要的人發生性關係、能夠殺害任何想殺的人、能夠從牢裡釋放任何想釋放的犯人、能夠做所有使自己在人群中看起來像是神一樣的事情時,沒有人……會如此地不被腐化,以至於堅持遵循正義,或讓自己遠離他人的財物,不去觸碰。」
柏拉圖暗示的回應是,葛勞康的結論只適用於那些渴求權力的人。那些真正良善和正義的人――也就是那些適合掌政權的人――不管自己是不是能隱形,行為舉止都不會改變。對那些少數合格的人來說,他們並沒有野心想要踏過友人或同胞的利益,來滿足自己的私慾。因此,隱形也不會給他們帶來政治利益。說到底,柏拉圖希望政治權力落在那些有智慧也有道德的人手中。這些特質,最可能出現在那些對權力的誘惑絲毫不感興趣的極少數人身上。蓋吉斯的隱形戒指,是用來分辨哪些人能被信任授予這類權力的最佳測試之一。的確,這個關於誰能抵抗權力誘惑的問題,是哈利.波特系列中值得探索的一個核心問題,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那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