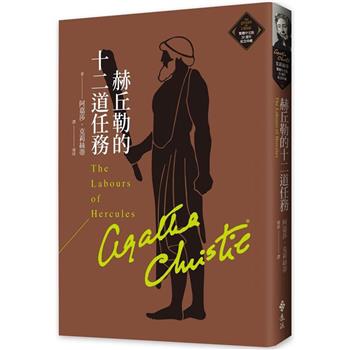01涅墨亞獅子
涅墨亞獅子是巨人杜篷和巨蛇厄喀德娜之子。牠蹂躪阿爾戈利斯的原野,任何人間的武器都不能傷害牠。赫丘勒斯在涅墨亞森林用手把牠掐死,剝下牠的皮做了自己的衣服。這是大力士赫丘勒斯的第一件任務。
「萊蒙小姐,今天早晨有什麼趣事嗎?」次日早晨他走進辦公室問道。
他相當依賴萊蒙小姐。雖說她是個沒有想像力的女人,但她具有天生的直覺,只要建議什麼事情可以考慮,通常那件事就值得考慮。她生來就是當祕書的料。
「沒有什麼特別的,白羅先生。只有一封信我想你可能會感興趣,我把它放在卷宗最上面了。」
「是什麼啊?」他頗感興趣地向前跨了一步。
「有個男人寫信來,請你幫他調查他妻子那隻走失的北京狗。」
白羅的腳步停在半空中,不滿地朝萊蒙小姐瞥了一眼。但她沒留意,逕自在一旁打起字來,她打字的速度簡直和掃射的機關槍一樣快。
白羅氣得火冒三丈,他又生氣又懊惱。這位盡職的女祕書萊蒙小姐實在太令他失望了!一隻北京狗,一隻北京狗!這事竟緊接在他昨夜做的那場好夢之後。昨夜夢中,他正在白金漢宮接受皇室的褒獎─就在此時,他的好夢被無情地打斷了:他的男僕端著他每早必喝的熱可可走了進來!
一些惡毒挖苦的話已顫到了嘴邊,但他終究沒說出口,因為萊蒙小姐正迅速而有效率地打字,想必是無法聽見。
他不高興地嘟囔一聲,拿起那封放在寫字檯卷宗上的信。
正如萊蒙小姐所說,信是從城裡寄來的,對方的要求簡短而粗俗──調查一隻被綁架的北京狗,那種眼突腿短、備受闊太太嬌寵的小狗。赫丘勒邊看信,邊輕蔑地噘著嘴唇。
這種事既不特別,又不奇怪,或者──但是,對,對,萊蒙小姐是對的,是有一處小地方令人起疑,是有個小地方不大對勁。
赫丘勒.白羅坐了下來,慢慢地仔細看了一遍那封信。其內容既不是他平時偵辦的那種類型,更不是他期望承辦的案子。從任何角度來看,這都不是什麼重大案件,簡直可以說它根本是不值一提。他不喜歡這案子的關鍵在於,如果偵破了,它也不能和大力士赫丘勒斯所達成的任務相提並論。
他卻感到好奇,是的,他感到相當好奇……
他提高音量,蓋過萊蒙小姐打字機的聲音,好讓她聽見。
「打個電話給這位約瑟夫.霍金爵士,」他吩咐道,「約好時間,我去他的辦公室和他談談。」
一如往常,萊蒙小姐的判斷總是正確的。
「我是個平凡的人,白羅先生。」約瑟夫.霍金爵士說。
赫丘勒.白羅用手稍微致意,表示(也許可以這樣理解)讚賞約瑟夫爵士儘管事業有成卻還能如此謙虛;但你也可以說是不贊成爵士太過自謙。其實在赫丘勒.白羅那高深莫測的頭腦裡,最主要的想法是約瑟夫爵士確實(用口語的話來說)──是一個很不起眼的人。赫丘勒.白羅挑剔地望著他那過長的下巴,凹陷的小眼睛,球狀的圓鼻頭和緊閉的嘴巴。這初步印象讓他想起某人或某件事,但一時又不確定是何人、何事。他腦中浮現模糊的記憶,彷彿許久以前,在比利時,好像和肥皂有關……
約瑟夫爵士繼續說著。
「我不打官腔,說話也從不拐彎抹角。白羅先生,大多數的人都不會計較這點小事,只會將它當成一筆爛帳,花錢了事。但這不是約瑟夫.霍金的一貫作風。我是個有錢人,事實上,兩百英鎊對我來說根本不算什麼──」
白羅插嘴說了聲:「那我得恭喜你了!」
「啊?」約瑟夫爵士頓了頓,那雙小眼睛瞇得更細了。他強調道:「但這並不是說我不把錢看在眼裡。該付的錢,我照付──不過我照市價付,絕不會多給。」
「您知道我的費用很高吧?」
「哦,知道。呃,不過嘛,」約瑟夫爵士狡黠地望著他。「這倒是小事一樁。」
赫丘勒.白羅聳聳肩,說道:「我從不讓人討價還價。我是個專家,對專家所做的服務,你必須付出高價。」
約瑟夫爵士坦白地說:「我知道在這行你是個頂尖人物,有許多人都向我推薦你。我絕對要把這事調查個水落石出不可,不在乎花多少錢,所以我才找你來。」
「你很幸運。」赫丘勒.白羅說。
約瑟夫爵士又「啊?」了一聲。
「你非常幸運,」赫丘勒.白羅面不改色地說,「我就不客氣地說吧,目前正是我事業的巔峰,不過再過些時日,我就打算退休,屆時我要住在鄉下,偶爾出遊,到世界各處去看看;也或許就在菜園裡耕種,致力改良櫛瓜,櫛瓜是個很營養的蔬菜,但不夠美味。然而這不是重點。我主要是想說明,我在退休之前已經給自己訂了一個目標──就是我將接辦十二個案子,不多也不少。我將它形容為自發性的『赫丘勒的十二道任務』。約瑟夫爵士,你這個案子將是十二道任務裡的頭一件。」他感嘆道,「因為它看起來那麼不值得重視,反倒把我給吸引住了。」
「值得重視?」約瑟夫爵士問道。
「我是說不值得重視。我偵破過各式各樣的案子,謀殺、離奇死亡、盜竊、偷竊財寶等等,這還是第一次被要求運用我的智慧才能,來偵辦一隻北京狗的綁架案呢。」
約瑟夫爵士嘟囔一聲,說道:「你真叫人吃驚!你一定不曾遇過女人拿著心愛寵物的事不停地煩你吧!」
「那倒是事實。不過,這可是我頭一回遇到做丈夫的請我承辦這類案子。」
約瑟夫爵士感激地瞇著小眼睛,說道:「現在我明白人家為什麼把你推薦給我了。你是個十分精明能幹的人,白羅先生。」
「那就說說案情吧。那隻狗是什麼時候不見的?」白羅問。
「整整一個星期前。」
「我想尊夫人現在一定急得都快瘋了吧?」
約瑟夫爵士瞪起雙眼,說道:「你不知道,那狗已經被送回來了。」
「送回來了?容我問一聲,那你請我來做什麼?」
約瑟夫爵士滿臉脹得通紅。
「因為有人在暗地裡想辦法欺騙我!白羅先生,我現在就把事情的經過講給你聽。一星期前,小狗被人偷走了──那是在我太太雇用的侍伴帶牠到肯辛頓公園散步的時候。有人剪斷狗鏈把牠帶走。第二天我太太就接到勒索兩百英鎊的通知。請注意──是兩百英鎊!就為贖回整天圍繞在你身旁汪汪叫的一隻小狗!」
「那你並不同意支付那筆款子囉?」
「當然不同意──或者說,我要是事先知情,就一定不會付錢。但我太太深知我的個性,什麼也沒說就把錢──對方要求全是面額一鎊的鈔票──寄到指定地址去了。」
「之後狗就被送回來了?」
「對。那天傍晚,有人按了門鈴,開門一看,那隻狗就蹲在門前的石階上,但屋外半個人影也沒看見。」
「很好,接著往下說。」
「隨後,米麗只好坦承自己做的蠢事,我便發了頓脾氣。但是沒一會兒,我就心平氣和了。反正這件事都已經做了,你根本無法要求一個女人做什麼理智的事──要不是在俱樂部碰到薩姆森,我敢說自己也會就此作罷。」
「怎麼回事?」
「真要命,這純粹是個敲詐的騙局!他也遇到了相同的事,有人敲了他太太三百英鎊!說真的,這真是太過分了!我決定要制止這種事再發生,便請你來了。」
「可是,約瑟夫爵士,最恰當、也最省錢的辦法,應該是報警啊。」
約瑟夫爵士揉揉鼻子,問道:「你結婚了嗎,白羅先生?」
「唉,」白羅答道,「我沒有那種福氣。」
「這就難怪了。」約瑟夫爵士說,「我不知那叫不叫福氣,不過,你要是結了婚,就知道女人是種奇怪的生物。只要一提起報警,我太太就會歇斯底里──她認定如果我去報警,她的寶貝山山就會受到傷害。她堅決反對那樣做,甚至我可以告訴你,她並不同意請你來調查此案。但我在這點上非常堅持,她也就讓步了。不過,你知道她並不喜歡我這樣做。」
「我看這事有點棘手,也許我最好先去見見尊夫人,從她那裡獲得一些詳細情況,同時也向她保證這樣一來,日後她的狗將安全無虞。」赫丘勒.白羅輕聲說。
約瑟夫爵士點點頭,起身說:「那我現在就開車帶你去。」
兩個女人正坐在一間寬敞卻悶熱、裝飾過於華麗的客廳裡。
約瑟夫爵士和赫丘勒.白羅走進去,一隻北京狗立刻狂吠,衝過來繞著白羅的腳打轉。
「山山,過來,到媽媽這邊來,小寶貝兒。噢,卡娜比小姐,去把牠抱過來。」
另外那個女人急忙跑過去抱牠。
赫丘勒.白羅小聲說道:「這隻狗凶猛得還真像頭獅子咧!」
那個抱著山山的女人氣喘吁吁地附和道:「是啊,說真的,牠是一隻很好的看門狗。什麼都不怕,誰也不怕。好,小乖乖!」
經過簡要的介紹之後,約瑟夫爵士說:「白羅先生,那就請你接手吧。」
他點了點頭,便離開了客廳。
霍金夫人看起來脾氣不佳,個子矮小,體型稍胖,染著一頭紅髮。她那焦慮不安的侍伴卡娜比小姐是個和藹可親、體態豐滿的女人,年紀大約在四十到五十之間。她不只尊敬霍金夫人,而且顯然對她十分畏懼。
「現在,霍金夫人,就請把這樁可惡的罪行從頭說給我聽聽吧。」白羅說。
霍金夫人滿臉通紅。
「我很高興你這麼說,白羅先生。因為這確實是樁犯罪行為。北京狗是很敏感的,就和孩子一樣敏感。可憐的山山,一定被嚇壞了。」
卡娜比小姐喘著氣附和道:「是啊,真惡毒,太惡毒了!」
「請描述實際情況。」
「嗯,是這樣的,山山那天跟著卡娜比小姐到公園散步──」
「唉,是啊,都是我的錯。」那位侍伴又插嘴道,「我怎麼會那麼笨,又那麼粗心大意……」
霍金夫人尖刻地說:「我不怪你,卡娜比小姐,但我的確認為你應該更警覺才對。」
白羅把目光移向那位侍伴身上。
「出了什麼事?」
卡娜比小姐一下子滔滔不絕且有點激動地說:「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我們正沿著那條花徑往前走,山山當然是跑在前頭,牠開心地在草地上跑著。之後我準備轉身,忽然旁邊一輛嬰兒車裡的小嬰兒把我吸引住了──好可愛的娃娃,對著我笑,有著粉紅小臉蛋,一頭漂亮的鬈髮。我忍不住就和那位保母聊了起來,問她孩子有多大,她說十七個月……我可以確定我只和她說了一兩分鐘的話;後來回頭一看,山山不見了,那條狗鏈已經被人割斷。」
霍金夫人接著說:「如果你有把心思放在工作上的話,就不會有人偷偷靠近、割斷鏈子了。」
卡娜比小姐似乎就要放聲大哭了,白羅連忙插嘴道:「後來又怎麼樣了?」
「嗯,我當然就到處去找,放開喉嚨叫喊!我還問公園管理員是否見到有人帶走一隻北京狗,可是他什麼也沒注意到……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便繼續四處尋找,最後只好垂頭喪氣地回家──」
卡娜比小姐突然頓住,不過白羅卻可以清楚地想像後來發生的情景。他問道:「接著你們就收到了一封信?」
霍金夫人說:「是的,是第二天早晨第一班郵件送來的。信上說,如果我們想見到山山活著回來,就必須用非掛號的信封,將面額一鎊共兩百英鎊現款寄到布魯姆斯貝利廣場三十八號給柯蒂茲上尉。信上還說,如果在錢上做記號或是報了警,山山的耳朵和尾巴就會被割掉!」
卡娜比小姐開始大聲抽泣。
「太可怕了,」她低聲說,「怎麼會有人這樣狠毒!」
霍金夫人接著說:「信上說,如果立刻把錢送去,山山當天傍晚就會好好地被送回來。可是如果─如果我事後去報警,今後山山可得為此付出相當代價──」
卡娜比小姐眼淚汪汪地嘟囔道:「哦,我的天,直到現在我還很害怕呢──當然,白羅先生不算是警察──」
霍金夫人焦慮地說:「所以,白羅先生,你調查這事時得十分小心謹慎。」
赫丘勒.白羅馬上就減輕她的顧慮。
「我不是警方的人。我當然會十分小心謹慎,而且會悄悄地偵查。你只管放心,霍金夫人,山山會很安全,不會再出事。這一點我可以向你『保證』。」
兩個女人似乎都由於這個神奇的字眼而感到放心了。
「你還留著那封信嗎?」白羅問。
霍金夫人搖搖頭。
「沒有,信中告知在付錢時必須把它一併寄回。」
「你照辦了?」
「是的。」
「嗯,真可惜。」
卡娜比小姐馬上說:「我還留著那根斷了的鏈子呢,我去把它拿來好嗎?」
接著她便走出客廳。白羅趁她不在場問了幾個問題。霍金夫人答道:「艾美.卡娜比嗎?哦,她還可以。心地不錯,就是有點糊塗。我先後雇用過好幾位侍伴,全都是些愚蠢的人。不過艾美挺喜歡山山的,她對這次的不幸事件感到很自責。說不定是她散步時只顧和人聊天,完全忽視了我的小寶貝。這種老處女全都一個樣,酷愛逗弄小嬰兒!不過,我可以確定她和這事一點牽連都沒有。」
「看起來也確實不像。」白羅同意道,「不過,畢竟小狗是在她負責照顧時丟失的,所以得弄清楚她是否忠誠。她在你這兒工作多久?」
「快一年了。我有她品行優良的推薦函。她曾在哈婷菲老夫人那裡工作十年,直到老太太去世。之後她照顧一位生病的修女好一陣子。她真的是個挺好的人──只不過正如我所說的,她也是個愚蠢的人。」
這時艾美回來了,呼吸有些急促,非常慎重地把那根被割斷的狗鏈交給白羅,滿心期待地望著他。白羅仔細檢查一番,說道:「沒錯,是被利器割斷的。」
那兩個女人等著白羅指示。他又說:「那我就先留下這個。」
他鄭重其事地把它放進口袋裡,兩個女人深深鬆了一口氣,因為白羅的舉動使她們終於放心了。
赫丘勒.白羅向來凡事都會仔細驗證,一點也不遺漏。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卡娜比小姐只是個態度可親、算不上精明能幹的女人,白羅還是去拜訪那位不苟言笑、已故哈婷菲夫人的侄女。
「艾美.卡娜比?」拉弗絲小姐說,「我當然記得她。她心地善良,和尤麗亞姑姑十分投合。她疼愛狗,而且擅長朗讀。她做事得體,從來不和人起衝突。她出了什麼事?我希望不是什麼不幸吧。一年前我曾經把她推薦給一位夫人,姓霍什麼的──」
白羅連忙說明卡娜比小姐目前還在那兒工作,只是最近為著一隻走失的狗傷透腦筋。
「艾美.卡娜比很愛小狗的。我姑姑曾養過一隻北京狗,她去世後就把牠送給卡娜比小姐了,卡娜比小姐十分寵愛牠。後來那狗兒死了,讓她傷心極了。哦,是的,她是個好人,當然,是沒有那麼能幹啦。」
赫丘勒.白羅同意這種看法:大概沒有人會認為卡娜比小姐既能幹又有智慧。
接下來,他去拜訪出事那天下午,曾和卡娜比小姐談話的那個公園管理員。還好事情發生不久,那人仍記憶猶新。
「是個中年婦女,胖胖的沒什麼特別,就是她的北京狗走丟了。我認得她,每天下午她多半會來遛狗。那天我看見她帶著狗走進來了;之後狗不見了,她看起來很慌亂,跑到我這兒來問我是否看見有人帶走一隻北京狗。我真想反問一句,公園裡到處都是狗,有各類品種,狼狗、北京狗、德國短腿獵狗甚至還有俄羅斯狼狗,也可以說我們這兒什麼樣的狗都有。我根本不可能特別注意一隻北京狗吧?」
赫丘勒.白羅沉思地點點頭。
接著他去了布魯姆斯貝利廣場三十八號。
三十八號、三十九號和四十號是巴拉克旅館。白羅步上台階推開門走了進去。裡面很暗,有股燉白菜和燻鮭魚混雜的味道。左邊一張紅木桌上放著一盆快要凋零的菊花,上方還有一個頗大的郵件架,用綠色的布蓋著,上面插著不少信件。白羅沉思地朝那架上的分隔板望了片刻後,推開右邊一扇門,走進休息室,裡面有幾張小桌子和幾把安樂椅,椅上鋪蓋著相當沉悶的印花裝飾布。有三位老太太和一位相貌凶惡的老先生抬起頭來,不友善地望著此時闖進來的不速之客。赫丘勒.白羅只好窘迫地退了出來。
他順著走道走下去,來到樓梯口。在它右邊另有個小走道可以通到餐廳。
走進那條通道,沒多少路就有一扇門,門上寫著「辦公室」的字樣。
白羅輕叩那扇門,無人回應。他便推開門,朝裡面望了一眼。這房裡有張大寫字檯,上面擺滿了文件,卻不見半個人影。他又退出來,關上門,朝前走進餐廳。
裡面有個圍著髒圍裙、神態憂鬱的女孩,正從一個餐具箱裡掏出刀叉來擺放。
「對不起,我想見一下你們的女經理,可以嗎?」赫丘勒.白羅不好意思地說。
女孩兩眼無神地望了他一下,說道:「我不知道她在哪兒,真的不知道。」
「辦公室裡沒人。」白羅說。
「那我也不知道她現在在哪兒。」
「可否,」赫丘勒.白羅堅持道,「請你幫我找一下,好嗎?」
女孩嘆了口氣。她的日子已經夠枯燥乏味了,現在又加上這個新負擔。她陰沉地說:「唉,那我找找看吧。」
白羅向她致謝後,又退回走道裡,也不敢再去休息室面對裡頭那幾雙不友善的眼睛。他抬頭凝視著那個郵件架,忽然傳來一陣衣裙的摩擦聲和一股濃烈的紫羅蘭香水味,女經理走過來了。哈特太太彬彬有禮地說:「對不起,我剛才不在辦公室。你要訂房嗎?」
「不是。我是來打聽我的一個朋友柯蒂茲上尉,他最近是不是曾來你這裡住過?」赫丘勒.白羅輕聲問。
「柯蒂茲?」哈特太太詫異道,「柯蒂茲上尉?讓我想想看,好像在哪裡聽過這名字?」
白羅不發一語。她搖搖頭。
「那就是說,沒有一位柯蒂茲上尉曾在這裡住過了?」
「對,至少最近沒有。但是你知道,這個姓聽起來相當耳熟,你能不能簡單地形容一下這位朋友?」
「哦,」赫丘勒.白羅答道,「這倒有點困難。」接著他又問道:「我猜想有時某些信會寄到你們這裡來,但事實上,收信人不住在這裡吧?」
「是的,確實有這種情況。」
「那你都怎麼處理這種信件呢?」
「我們一般會把它們保留一段時間。因為,你知道,收信人有時過幾天會來。當然,如果這些信件或包裹長期無人領取,我們就退回給郵局。」
赫丘勒.白羅理解地點點頭。
「我明白了。」接著他補充道:「之前我給一個朋友寫了封信寄到這兒。」
哈特太太的表情顯得豁然開朗起來了。
「這就對了。我一定是在信封上見過柯蒂茲這個姓。可是,有許多退役的將官常在我們這兒下榻──讓我查查看。」
她抬頭盯著牆上那個郵件架。
「沒有那封信。」白羅說。
「那我應該已經把它退給郵差了。太對不起了,但願不是什麼急事吧?」
「沒關係,沒關係,不是急事。」
他轉身朝大門走去,哈特太太渾身散發著一股刺鼻的紫羅蘭香水味追了上來。
「你的朋友如果真的來──」「大概不會來了,我想必定是弄錯了……」
「我們的住宿費很公道,」哈特太太說,「飯後飲料咖啡不另外收費。我想請你參觀一下我們幾間有客廳的客房……」
赫丘勒.白羅費了不少勁兒才得以脫身。
涅墨亞獅子是巨人杜篷和巨蛇厄喀德娜之子。牠蹂躪阿爾戈利斯的原野,任何人間的武器都不能傷害牠。赫丘勒斯在涅墨亞森林用手把牠掐死,剝下牠的皮做了自己的衣服。這是大力士赫丘勒斯的第一件任務。
「萊蒙小姐,今天早晨有什麼趣事嗎?」次日早晨他走進辦公室問道。
他相當依賴萊蒙小姐。雖說她是個沒有想像力的女人,但她具有天生的直覺,只要建議什麼事情可以考慮,通常那件事就值得考慮。她生來就是當祕書的料。
「沒有什麼特別的,白羅先生。只有一封信我想你可能會感興趣,我把它放在卷宗最上面了。」
「是什麼啊?」他頗感興趣地向前跨了一步。
「有個男人寫信來,請你幫他調查他妻子那隻走失的北京狗。」
白羅的腳步停在半空中,不滿地朝萊蒙小姐瞥了一眼。但她沒留意,逕自在一旁打起字來,她打字的速度簡直和掃射的機關槍一樣快。
白羅氣得火冒三丈,他又生氣又懊惱。這位盡職的女祕書萊蒙小姐實在太令他失望了!一隻北京狗,一隻北京狗!這事竟緊接在他昨夜做的那場好夢之後。昨夜夢中,他正在白金漢宮接受皇室的褒獎─就在此時,他的好夢被無情地打斷了:他的男僕端著他每早必喝的熱可可走了進來!
一些惡毒挖苦的話已顫到了嘴邊,但他終究沒說出口,因為萊蒙小姐正迅速而有效率地打字,想必是無法聽見。
他不高興地嘟囔一聲,拿起那封放在寫字檯卷宗上的信。
正如萊蒙小姐所說,信是從城裡寄來的,對方的要求簡短而粗俗──調查一隻被綁架的北京狗,那種眼突腿短、備受闊太太嬌寵的小狗。赫丘勒邊看信,邊輕蔑地噘著嘴唇。
這種事既不特別,又不奇怪,或者──但是,對,對,萊蒙小姐是對的,是有一處小地方令人起疑,是有個小地方不大對勁。
赫丘勒.白羅坐了下來,慢慢地仔細看了一遍那封信。其內容既不是他平時偵辦的那種類型,更不是他期望承辦的案子。從任何角度來看,這都不是什麼重大案件,簡直可以說它根本是不值一提。他不喜歡這案子的關鍵在於,如果偵破了,它也不能和大力士赫丘勒斯所達成的任務相提並論。
他卻感到好奇,是的,他感到相當好奇……
他提高音量,蓋過萊蒙小姐打字機的聲音,好讓她聽見。
「打個電話給這位約瑟夫.霍金爵士,」他吩咐道,「約好時間,我去他的辦公室和他談談。」
一如往常,萊蒙小姐的判斷總是正確的。
「我是個平凡的人,白羅先生。」約瑟夫.霍金爵士說。
赫丘勒.白羅用手稍微致意,表示(也許可以這樣理解)讚賞約瑟夫爵士儘管事業有成卻還能如此謙虛;但你也可以說是不贊成爵士太過自謙。其實在赫丘勒.白羅那高深莫測的頭腦裡,最主要的想法是約瑟夫爵士確實(用口語的話來說)──是一個很不起眼的人。赫丘勒.白羅挑剔地望著他那過長的下巴,凹陷的小眼睛,球狀的圓鼻頭和緊閉的嘴巴。這初步印象讓他想起某人或某件事,但一時又不確定是何人、何事。他腦中浮現模糊的記憶,彷彿許久以前,在比利時,好像和肥皂有關……
約瑟夫爵士繼續說著。
「我不打官腔,說話也從不拐彎抹角。白羅先生,大多數的人都不會計較這點小事,只會將它當成一筆爛帳,花錢了事。但這不是約瑟夫.霍金的一貫作風。我是個有錢人,事實上,兩百英鎊對我來說根本不算什麼──」
白羅插嘴說了聲:「那我得恭喜你了!」
「啊?」約瑟夫爵士頓了頓,那雙小眼睛瞇得更細了。他強調道:「但這並不是說我不把錢看在眼裡。該付的錢,我照付──不過我照市價付,絕不會多給。」
「您知道我的費用很高吧?」
「哦,知道。呃,不過嘛,」約瑟夫爵士狡黠地望著他。「這倒是小事一樁。」
赫丘勒.白羅聳聳肩,說道:「我從不讓人討價還價。我是個專家,對專家所做的服務,你必須付出高價。」
約瑟夫爵士坦白地說:「我知道在這行你是個頂尖人物,有許多人都向我推薦你。我絕對要把這事調查個水落石出不可,不在乎花多少錢,所以我才找你來。」
「你很幸運。」赫丘勒.白羅說。
約瑟夫爵士又「啊?」了一聲。
「你非常幸運,」赫丘勒.白羅面不改色地說,「我就不客氣地說吧,目前正是我事業的巔峰,不過再過些時日,我就打算退休,屆時我要住在鄉下,偶爾出遊,到世界各處去看看;也或許就在菜園裡耕種,致力改良櫛瓜,櫛瓜是個很營養的蔬菜,但不夠美味。然而這不是重點。我主要是想說明,我在退休之前已經給自己訂了一個目標──就是我將接辦十二個案子,不多也不少。我將它形容為自發性的『赫丘勒的十二道任務』。約瑟夫爵士,你這個案子將是十二道任務裡的頭一件。」他感嘆道,「因為它看起來那麼不值得重視,反倒把我給吸引住了。」
「值得重視?」約瑟夫爵士問道。
「我是說不值得重視。我偵破過各式各樣的案子,謀殺、離奇死亡、盜竊、偷竊財寶等等,這還是第一次被要求運用我的智慧才能,來偵辦一隻北京狗的綁架案呢。」
約瑟夫爵士嘟囔一聲,說道:「你真叫人吃驚!你一定不曾遇過女人拿著心愛寵物的事不停地煩你吧!」
「那倒是事實。不過,這可是我頭一回遇到做丈夫的請我承辦這類案子。」
約瑟夫爵士感激地瞇著小眼睛,說道:「現在我明白人家為什麼把你推薦給我了。你是個十分精明能幹的人,白羅先生。」
「那就說說案情吧。那隻狗是什麼時候不見的?」白羅問。
「整整一個星期前。」
「我想尊夫人現在一定急得都快瘋了吧?」
約瑟夫爵士瞪起雙眼,說道:「你不知道,那狗已經被送回來了。」
「送回來了?容我問一聲,那你請我來做什麼?」
約瑟夫爵士滿臉脹得通紅。
「因為有人在暗地裡想辦法欺騙我!白羅先生,我現在就把事情的經過講給你聽。一星期前,小狗被人偷走了──那是在我太太雇用的侍伴帶牠到肯辛頓公園散步的時候。有人剪斷狗鏈把牠帶走。第二天我太太就接到勒索兩百英鎊的通知。請注意──是兩百英鎊!就為贖回整天圍繞在你身旁汪汪叫的一隻小狗!」
「那你並不同意支付那筆款子囉?」
「當然不同意──或者說,我要是事先知情,就一定不會付錢。但我太太深知我的個性,什麼也沒說就把錢──對方要求全是面額一鎊的鈔票──寄到指定地址去了。」
「之後狗就被送回來了?」
「對。那天傍晚,有人按了門鈴,開門一看,那隻狗就蹲在門前的石階上,但屋外半個人影也沒看見。」
「很好,接著往下說。」
「隨後,米麗只好坦承自己做的蠢事,我便發了頓脾氣。但是沒一會兒,我就心平氣和了。反正這件事都已經做了,你根本無法要求一個女人做什麼理智的事──要不是在俱樂部碰到薩姆森,我敢說自己也會就此作罷。」
「怎麼回事?」
「真要命,這純粹是個敲詐的騙局!他也遇到了相同的事,有人敲了他太太三百英鎊!說真的,這真是太過分了!我決定要制止這種事再發生,便請你來了。」
「可是,約瑟夫爵士,最恰當、也最省錢的辦法,應該是報警啊。」
約瑟夫爵士揉揉鼻子,問道:「你結婚了嗎,白羅先生?」
「唉,」白羅答道,「我沒有那種福氣。」
「這就難怪了。」約瑟夫爵士說,「我不知那叫不叫福氣,不過,你要是結了婚,就知道女人是種奇怪的生物。只要一提起報警,我太太就會歇斯底里──她認定如果我去報警,她的寶貝山山就會受到傷害。她堅決反對那樣做,甚至我可以告訴你,她並不同意請你來調查此案。但我在這點上非常堅持,她也就讓步了。不過,你知道她並不喜歡我這樣做。」
「我看這事有點棘手,也許我最好先去見見尊夫人,從她那裡獲得一些詳細情況,同時也向她保證這樣一來,日後她的狗將安全無虞。」赫丘勒.白羅輕聲說。
約瑟夫爵士點點頭,起身說:「那我現在就開車帶你去。」
兩個女人正坐在一間寬敞卻悶熱、裝飾過於華麗的客廳裡。
約瑟夫爵士和赫丘勒.白羅走進去,一隻北京狗立刻狂吠,衝過來繞著白羅的腳打轉。
「山山,過來,到媽媽這邊來,小寶貝兒。噢,卡娜比小姐,去把牠抱過來。」
另外那個女人急忙跑過去抱牠。
赫丘勒.白羅小聲說道:「這隻狗凶猛得還真像頭獅子咧!」
那個抱著山山的女人氣喘吁吁地附和道:「是啊,說真的,牠是一隻很好的看門狗。什麼都不怕,誰也不怕。好,小乖乖!」
經過簡要的介紹之後,約瑟夫爵士說:「白羅先生,那就請你接手吧。」
他點了點頭,便離開了客廳。
霍金夫人看起來脾氣不佳,個子矮小,體型稍胖,染著一頭紅髮。她那焦慮不安的侍伴卡娜比小姐是個和藹可親、體態豐滿的女人,年紀大約在四十到五十之間。她不只尊敬霍金夫人,而且顯然對她十分畏懼。
「現在,霍金夫人,就請把這樁可惡的罪行從頭說給我聽聽吧。」白羅說。
霍金夫人滿臉通紅。
「我很高興你這麼說,白羅先生。因為這確實是樁犯罪行為。北京狗是很敏感的,就和孩子一樣敏感。可憐的山山,一定被嚇壞了。」
卡娜比小姐喘著氣附和道:「是啊,真惡毒,太惡毒了!」
「請描述實際情況。」
「嗯,是這樣的,山山那天跟著卡娜比小姐到公園散步──」
「唉,是啊,都是我的錯。」那位侍伴又插嘴道,「我怎麼會那麼笨,又那麼粗心大意……」
霍金夫人尖刻地說:「我不怪你,卡娜比小姐,但我的確認為你應該更警覺才對。」
白羅把目光移向那位侍伴身上。
「出了什麼事?」
卡娜比小姐一下子滔滔不絕且有點激動地說:「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我們正沿著那條花徑往前走,山山當然是跑在前頭,牠開心地在草地上跑著。之後我準備轉身,忽然旁邊一輛嬰兒車裡的小嬰兒把我吸引住了──好可愛的娃娃,對著我笑,有著粉紅小臉蛋,一頭漂亮的鬈髮。我忍不住就和那位保母聊了起來,問她孩子有多大,她說十七個月……我可以確定我只和她說了一兩分鐘的話;後來回頭一看,山山不見了,那條狗鏈已經被人割斷。」
霍金夫人接著說:「如果你有把心思放在工作上的話,就不會有人偷偷靠近、割斷鏈子了。」
卡娜比小姐似乎就要放聲大哭了,白羅連忙插嘴道:「後來又怎麼樣了?」
「嗯,我當然就到處去找,放開喉嚨叫喊!我還問公園管理員是否見到有人帶走一隻北京狗,可是他什麼也沒注意到……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便繼續四處尋找,最後只好垂頭喪氣地回家──」
卡娜比小姐突然頓住,不過白羅卻可以清楚地想像後來發生的情景。他問道:「接著你們就收到了一封信?」
霍金夫人說:「是的,是第二天早晨第一班郵件送來的。信上說,如果我們想見到山山活著回來,就必須用非掛號的信封,將面額一鎊共兩百英鎊現款寄到布魯姆斯貝利廣場三十八號給柯蒂茲上尉。信上還說,如果在錢上做記號或是報了警,山山的耳朵和尾巴就會被割掉!」
卡娜比小姐開始大聲抽泣。
「太可怕了,」她低聲說,「怎麼會有人這樣狠毒!」
霍金夫人接著說:「信上說,如果立刻把錢送去,山山當天傍晚就會好好地被送回來。可是如果─如果我事後去報警,今後山山可得為此付出相當代價──」
卡娜比小姐眼淚汪汪地嘟囔道:「哦,我的天,直到現在我還很害怕呢──當然,白羅先生不算是警察──」
霍金夫人焦慮地說:「所以,白羅先生,你調查這事時得十分小心謹慎。」
赫丘勒.白羅馬上就減輕她的顧慮。
「我不是警方的人。我當然會十分小心謹慎,而且會悄悄地偵查。你只管放心,霍金夫人,山山會很安全,不會再出事。這一點我可以向你『保證』。」
兩個女人似乎都由於這個神奇的字眼而感到放心了。
「你還留著那封信嗎?」白羅問。
霍金夫人搖搖頭。
「沒有,信中告知在付錢時必須把它一併寄回。」
「你照辦了?」
「是的。」
「嗯,真可惜。」
卡娜比小姐馬上說:「我還留著那根斷了的鏈子呢,我去把它拿來好嗎?」
接著她便走出客廳。白羅趁她不在場問了幾個問題。霍金夫人答道:「艾美.卡娜比嗎?哦,她還可以。心地不錯,就是有點糊塗。我先後雇用過好幾位侍伴,全都是些愚蠢的人。不過艾美挺喜歡山山的,她對這次的不幸事件感到很自責。說不定是她散步時只顧和人聊天,完全忽視了我的小寶貝。這種老處女全都一個樣,酷愛逗弄小嬰兒!不過,我可以確定她和這事一點牽連都沒有。」
「看起來也確實不像。」白羅同意道,「不過,畢竟小狗是在她負責照顧時丟失的,所以得弄清楚她是否忠誠。她在你這兒工作多久?」
「快一年了。我有她品行優良的推薦函。她曾在哈婷菲老夫人那裡工作十年,直到老太太去世。之後她照顧一位生病的修女好一陣子。她真的是個挺好的人──只不過正如我所說的,她也是個愚蠢的人。」
這時艾美回來了,呼吸有些急促,非常慎重地把那根被割斷的狗鏈交給白羅,滿心期待地望著他。白羅仔細檢查一番,說道:「沒錯,是被利器割斷的。」
那兩個女人等著白羅指示。他又說:「那我就先留下這個。」
他鄭重其事地把它放進口袋裡,兩個女人深深鬆了一口氣,因為白羅的舉動使她們終於放心了。
赫丘勒.白羅向來凡事都會仔細驗證,一點也不遺漏。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卡娜比小姐只是個態度可親、算不上精明能幹的女人,白羅還是去拜訪那位不苟言笑、已故哈婷菲夫人的侄女。
「艾美.卡娜比?」拉弗絲小姐說,「我當然記得她。她心地善良,和尤麗亞姑姑十分投合。她疼愛狗,而且擅長朗讀。她做事得體,從來不和人起衝突。她出了什麼事?我希望不是什麼不幸吧。一年前我曾經把她推薦給一位夫人,姓霍什麼的──」
白羅連忙說明卡娜比小姐目前還在那兒工作,只是最近為著一隻走失的狗傷透腦筋。
「艾美.卡娜比很愛小狗的。我姑姑曾養過一隻北京狗,她去世後就把牠送給卡娜比小姐了,卡娜比小姐十分寵愛牠。後來那狗兒死了,讓她傷心極了。哦,是的,她是個好人,當然,是沒有那麼能幹啦。」
赫丘勒.白羅同意這種看法:大概沒有人會認為卡娜比小姐既能幹又有智慧。
接下來,他去拜訪出事那天下午,曾和卡娜比小姐談話的那個公園管理員。還好事情發生不久,那人仍記憶猶新。
「是個中年婦女,胖胖的沒什麼特別,就是她的北京狗走丟了。我認得她,每天下午她多半會來遛狗。那天我看見她帶著狗走進來了;之後狗不見了,她看起來很慌亂,跑到我這兒來問我是否看見有人帶走一隻北京狗。我真想反問一句,公園裡到處都是狗,有各類品種,狼狗、北京狗、德國短腿獵狗甚至還有俄羅斯狼狗,也可以說我們這兒什麼樣的狗都有。我根本不可能特別注意一隻北京狗吧?」
赫丘勒.白羅沉思地點點頭。
接著他去了布魯姆斯貝利廣場三十八號。
三十八號、三十九號和四十號是巴拉克旅館。白羅步上台階推開門走了進去。裡面很暗,有股燉白菜和燻鮭魚混雜的味道。左邊一張紅木桌上放著一盆快要凋零的菊花,上方還有一個頗大的郵件架,用綠色的布蓋著,上面插著不少信件。白羅沉思地朝那架上的分隔板望了片刻後,推開右邊一扇門,走進休息室,裡面有幾張小桌子和幾把安樂椅,椅上鋪蓋著相當沉悶的印花裝飾布。有三位老太太和一位相貌凶惡的老先生抬起頭來,不友善地望著此時闖進來的不速之客。赫丘勒.白羅只好窘迫地退了出來。
他順著走道走下去,來到樓梯口。在它右邊另有個小走道可以通到餐廳。
走進那條通道,沒多少路就有一扇門,門上寫著「辦公室」的字樣。
白羅輕叩那扇門,無人回應。他便推開門,朝裡面望了一眼。這房裡有張大寫字檯,上面擺滿了文件,卻不見半個人影。他又退出來,關上門,朝前走進餐廳。
裡面有個圍著髒圍裙、神態憂鬱的女孩,正從一個餐具箱裡掏出刀叉來擺放。
「對不起,我想見一下你們的女經理,可以嗎?」赫丘勒.白羅不好意思地說。
女孩兩眼無神地望了他一下,說道:「我不知道她在哪兒,真的不知道。」
「辦公室裡沒人。」白羅說。
「那我也不知道她現在在哪兒。」
「可否,」赫丘勒.白羅堅持道,「請你幫我找一下,好嗎?」
女孩嘆了口氣。她的日子已經夠枯燥乏味了,現在又加上這個新負擔。她陰沉地說:「唉,那我找找看吧。」
白羅向她致謝後,又退回走道裡,也不敢再去休息室面對裡頭那幾雙不友善的眼睛。他抬頭凝視著那個郵件架,忽然傳來一陣衣裙的摩擦聲和一股濃烈的紫羅蘭香水味,女經理走過來了。哈特太太彬彬有禮地說:「對不起,我剛才不在辦公室。你要訂房嗎?」
「不是。我是來打聽我的一個朋友柯蒂茲上尉,他最近是不是曾來你這裡住過?」赫丘勒.白羅輕聲問。
「柯蒂茲?」哈特太太詫異道,「柯蒂茲上尉?讓我想想看,好像在哪裡聽過這名字?」
白羅不發一語。她搖搖頭。
「那就是說,沒有一位柯蒂茲上尉曾在這裡住過了?」
「對,至少最近沒有。但是你知道,這個姓聽起來相當耳熟,你能不能簡單地形容一下這位朋友?」
「哦,」赫丘勒.白羅答道,「這倒有點困難。」接著他又問道:「我猜想有時某些信會寄到你們這裡來,但事實上,收信人不住在這裡吧?」
「是的,確實有這種情況。」
「那你都怎麼處理這種信件呢?」
「我們一般會把它們保留一段時間。因為,你知道,收信人有時過幾天會來。當然,如果這些信件或包裹長期無人領取,我們就退回給郵局。」
赫丘勒.白羅理解地點點頭。
「我明白了。」接著他補充道:「之前我給一個朋友寫了封信寄到這兒。」
哈特太太的表情顯得豁然開朗起來了。
「這就對了。我一定是在信封上見過柯蒂茲這個姓。可是,有許多退役的將官常在我們這兒下榻──讓我查查看。」
她抬頭盯著牆上那個郵件架。
「沒有那封信。」白羅說。
「那我應該已經把它退給郵差了。太對不起了,但願不是什麼急事吧?」
「沒關係,沒關係,不是急事。」
他轉身朝大門走去,哈特太太渾身散發著一股刺鼻的紫羅蘭香水味追了上來。
「你的朋友如果真的來──」「大概不會來了,我想必定是弄錯了……」
「我們的住宿費很公道,」哈特太太說,「飯後飲料咖啡不另外收費。我想請你參觀一下我們幾間有客廳的客房……」
赫丘勒.白羅費了不少勁兒才得以脫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