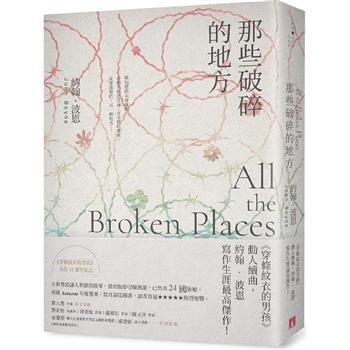第一部
惡魔的女兒
倫敦2022/巴黎1946
1
如果每個人因為自己沒做的善事而有罪,有如伏爾泰提議的,那麼我這輩子都在想辦法說服自己,說起所有的惡行,我都是無辜的。這一直是個方便門,讓我得以承受幾十年來遠離過往的自我放逐,視自己為歷史失憶的受害者,卸除共犯的罪名,並且免於受到責難。
不過,我最終的故事始於也終於開箱刀這個微不足道的小東西。我的開箱刀幾天前壞掉了,我發現廚房抽屜非得放一把這種實用的工具不可,於是前往當地的五金行買把新的。我回來的時候,仲介留了封信給我,冬市苑的每個住戶都收到了類似的信件,客客氣氣通知我們每個人,我樓下的公寓即將出售。前任居民李察森先生住在一號公寓三十年之久,但聖誕節以前不久過世了,住處於是騰了出來。他女兒是語言治療師,住在紐約,就我所知,她並不打算回倫敦。於是我只好接受不久之後就會被迫在大廳跟陌生人互動,甚至必須假裝對對方的生活有興趣,或是不得不吐露一點關於自己的小細節。
我和李察森先生向來維持著完美的鄰居關係,因為我們從二○○八年起就不曾交換過隻字片語,他入住的早年歲月,我們一度關係友好,他偶爾會上樓來跟我先夫艾德格下盤棋,但我跟他素來只是相敬如賓。他總是稱呼我為「芬斯比太太」,我則稱他為「李察森先生」。我最後一次踏進他的公寓,是在艾德格過世四個月之後,他邀請我共進晚餐,我接受了邀約,然後婉拒了對方發動的愛情攻勢。他對我的拒絕反應激烈,後來我們幾乎形同陌路,成了兩個同住一棟樓房的陌生人。
我位於梅費爾區的住處登記為公寓,但這有點類似將溫莎城堡形容為女王週末的避居處。我們這棟樓房的每戶公寓──總共有五戶,一戶在地面樓層,上面兩層則各有兩戶──占地一千五百平方英尺,在倫敦地產的黃金地段,每戶都有三間臥房、兩間半浴室,加上海德公園的景色,按照可靠的資訊來源,每戶價值介於兩百至三百萬英鎊之間。艾德格在我們婚後幾年拿到了一筆豐厚的財產,是終身未婚的姑姑所遺贈,他更想搬到倫敦市中心外更寧靜的地方,但我事先做了點研究,打定主意不只要住在梅費爾區,如果有可能的話,更要住進這棟建築。財務上來說,原本看似毫無可能,但是有一天,彷彿有如神助,柏琳達姑姑過世了,一切都改變了。我一直計畫要向艾德格解釋,我這麼急著住進這裡的原因,可是從來不曾說過,我現在還滿後悔的。
我丈夫非常喜歡孩子,但我只同意生養一個,並在一九六一年生下我們的兒子卡登。近年來房地產增值,卡登鼓勵我賣掉這戶公寓,在城裡房價較低的地區買個坪數小點的單位,但我想那是因為他擔心我可能會活到一百歲,急著趁年輕還能享受的時候,拿到他的那份遺產。他結婚過三次,現在第四次訂婚;我已經放棄認識他生命中的女性。我發現每每才認識她們,她們就被送走,然後新的款式就會進駐,我還得花時間學習她們的特性,就像新型洗衣機或電視機。孩提時代,他就用類似的無情方式對待朋友。我們經常通電話,他每兩週就會過來吃一次晚飯,不過我們的關係複雜,部分因為我在他九歲時從他生活中缺席整整一年。事實是,我跟小孩相處就是不自在,而我發現小男孩特別難相處。
我對新鄰居的顧慮不是他或她可能發出不必要的噪音──這些公寓隔音效果很好,即使在這裡那裡有幾個瑕疵,經年以來,我已經習慣透過李察森先生天花板傳上來的各種奇特聲響──但我痛恨自己井井有條的世界可能會被顛覆。我希望進駐的人不會有興趣認識住樓上的婦人。也許來個病弱殘疾的老人家,鮮少離開家門,每天早上有家務幫手來探訪。或者是年輕專業人士,星期五下午消失,返回自己週末的家,然後星期天深夜才回來,其餘的時間都在辦公室或健身房。有個謠言傳遍了這棟樓,說有個事業在一九八○年代到達顛峰的知名流行樂手考慮把那戶當成退休以後的住家,但令人高興的是,這件事並無下文。
只要房仲把車停在外面,護送客戶參觀那戶公寓,我的窗簾就會跟著掀動:我針對每個潛在的鄰居都做了點筆記。有個前景看好七十出頭的夫婦,說話輕聲細語,手牽手,問這棟樓能否養寵物──我在樓梯井上側聽──被告知不行時,似乎相當失望。一對三十幾歲的同志伴侶,從他們刻意仿舊的服飾、帶有凌亂感的外觀看來,口袋肯定頗深,但他們說這個「場域」對他們來說可能有點小,覺得自己不大能跟它的「敘事」起共鳴。一個長相不起眼的年輕女子說,有個叫史提芬的人會很愛這裡的挑高天花板,除此之外並未洩漏自己的意願。想也知道,我希望是同志──他們很適合當鄰居,而且不大有機會生兒育女──但他們似乎興趣最低。
然後,幾個星期過後,仲介不再帶人來參觀,待售訊息從網路上消失了,我猜交易已經談定。不管我喜不喜歡,總有一天醒過來就會發現搬家貨車停在外頭,有個人或幾個人正把鑰匙插進前門,住進我樓下。
噢,我真害怕!
2
我和母親在一九四六年初期逃離德國,當時戰爭結束才幾個月,我們從殘破的柏林搭火車前往殘破的巴黎。我當年十五歲,對人生所知不多,但還是逐漸接受了軸心國被打敗的事實。父親曾經充滿信心說著我們種族在基因上多麼優越,以及元首身為軍事策略家有無以倫比的技巧,勝利指日可待。但是我們卻戰敗了。
橫越大陸將近七百英里的行程,不大能讓人對未來懷抱樂觀。我們行經的城市呈現近年來飽受摧殘的模樣,而我在車站和車廂裡看到的人臉並不因為戰爭結束而開心,而是因為戰爭的影響而受創。到處都彌漫著筋疲力竭的感覺;眾人逐漸領悟到,歐洲無法回到一九三八年的模樣,而必須整個重建,居民的心靈也是。
我出生的城市現在幾乎整個夷為平地,征服我們的四個勢力瓜分了戰利品。有少數堅定信徒的屋舍從戰火倖存下來,我們為了得到庇護,在取得偽造文件、確保可以安全離開德國以前,一直躲在他們家的地下室裡。現在,我們護照上的姓氏是蓋馬爾。為了確定聽起來很逼真,我反覆練習發音,母親現在要改名為娜塔莉──我祖母的名字──我則維持原名葛蕾朵。
關於集中營裡發生的事情,每天都有新的細節曝光,父親的名字成了天理不容罪行的代名詞。雖然沒人暗示我們跟他一樣有罪,但母親相信,要是我們向當局揭露自己的身分,肯定會招來災禍。我有同感,因為我跟她一樣害怕,雖然想到有人會認為我是暴行的共犯,震撼了我。確實,從我十歲生日以來,我一直是「少女聯盟」的成員,但德國的每個年輕女生都是,畢竟那是強制的,就像十歲男孩非得加入「德意志少年團」不可。可是,比起黨的意識形態,我更有興趣的是跟朋友參加定期的運動賽事。我們到了另一地方時,我只越過那道圍籬一次,當時父親帶我進營區觀察他的工作實況。我試圖告訴自己,我只是旁觀者,如此而已,告訴自己我的良心清白,但我已經開始質疑自己參與了我目睹的事件。
不過,我們的火車駛入法國時,我擔心口音會洩漏我們的身分。當然了,我推想,最近解放的巴黎公民因為一九四○年的立即投降感到羞愧,對於講話方式跟我們一樣的人都很不客氣。我的憂慮證實是對的,儘管強調我們身上帶的錢要長期住宿綽綽有餘,卻一連遭到五家民宿的拒絕。最後凡登廣場那裡有個婦人同情我們,給我們附近一家民宿的地址,說那個女房東不會多問,我們才找到落腳的地方。要不是因為她,我們可能會成為有錢卻浪跡街頭的可憐人。
我們租用的房間在西堤島東側,早先那些日子,我只在住處附近活動,將步行距離限制在從蘇利橋到新橋,然後再回來,永無止盡的迴圈,如果要過橋進入陌生區域就會備感焦慮。有時候我會想起弟弟,他一直渴望成為探險家,如果能夠辨識這些陌生街道,他該有多高興,但在這樣的時刻裡,我總是快快揮開對他的記憶。
我和母親住在島上兩個月之後,我才鼓起勇氣前往盧森堡公園,那裡綠意盎然,讓我覺得彷彿無意間遇見了天堂。我們初初抵達另一地方時,迎面就是光禿荒蕪的自然景象,跟這裡的對比起來好強烈,我想。在這裡,可以吸進生命的芬芳;在那裡,會因死亡的臭氣而嗆噎。我從盧森堡宮遊蕩到梅迪奇噴泉,彷彿陷入恍惚狀態,然後從那裡走往水池,看到一群小男孩將木船放進水裡,輕風將他們的小船帶到另一側的玩伴那裡,我便轉身離開。我無聲地苦惱著──這成了我日漸熟悉的情緒──苦思不解,為何一片大陸可以同時容納如此極端的美麗與醜陋,而他們的笑聲和興奮的對話提供了令人難受的背景音樂。
某天下午,我在滾球場附近的板凳上躲避陽光,發現自己被悲慟和內疚吞噬,淚水簌簌淌下我的臉。有個俊美的男孩,也許比我大兩歲,一臉擔憂走過來問我怎麼了。我抬起頭,湧上一絲慾望,渴望他能攬住我,或是讓我將頭靠在他肩上。但當我一開口,就落入了舊有的說話模式,德國口音壓過了我的法文,他往後退開一步瞪著我,神情不掩輕蔑,然後召喚起他對我族類所感到的怒火,當著我的面暴烈地啐了一口,然後大步走開。怪的是,他的舉止並未削減我對他撫觸的慾望,反倒增加了。我抹乾臉頰,追了過去並揪住他的手臂,邀請他帶我進樹林裡,並且告訴他,在隱密的空間裡他可以對我為所欲為。
「如果想要,你可以傷害我。」我輕聲說,閉起眼睛,心想他可能會用力摑我耳光,用拳頭揍我肚子,打斷我的鼻梁。
「妳為什麼想要那樣?」他問我,語氣洩漏出天真,與他的俊美互為牴觸。
「這樣我就會知道自己還活著。」
他似乎起了性慾同時又覺得反感,環顧四周看看是否有人旁觀,然後望向我指的小樹林。他舔舔嘴唇,觀察我起伏的胸脯,但是當我握住他的手,我的碰觸侮辱了他,他連忙將手抽開,用法文罵我妓女,然後拔腿就跑,消失在吉梅荷路上。
天氣好的時候,我從清晨開始在街頭遊蕩,回到租處時母親往往已經爛醉如泥,不會問我都怎麼打發時間。現在,她先前生活的雅致漸漸消散無蹤,但她依然是個外貌姣好的女子,我忖度她會不會再找個丈夫,找個可以照顧我們的人,可是她似乎不想要陪伴或愛情,寧可與自己的思緒獨處,在酒吧跟酒吧之間遊走。她買醉的時候很安靜,會坐在幽暗的角落裡慢慢啜飲一瓶瓶的酒,在木頭桌面上刮著隱形的刻痕,絕對不會鬧事,免得被趕到街上。有一次,太陽消失在布洛涅森林上方時,我們湊巧碰上了,母親搖搖晃晃走過來,勾住我的手臂,問我幾點了。她似乎不知道講話的對象是自己的女兒。我回答之後,她露出如釋重負的笑容──天色越來越暗,但酒吧還會營業好幾個小時──她持續朝著西堤島上燦亮誘人的點點燈火走去。我納悶,如果我完全消失,她是不是會忘記我曾經存在過?
我們共睡一張床,我很討厭在母親身邊醒來,吸進毒化她呼吸、注滿睡意的酒精臭氣。她睜開眼睛的時候,會困惑地坐起身,然後回憶就會一股腦兒湧回來,她便會合起雙眼,試圖回到不省人事的狀態。當她終於接受日光的無禮攪擾,勉強將自己從被單底下拖出來,就會到水槽那裡做基本的清洗,然後換上洋裝走到外頭去,高高興興重複昨天的時時刻刻,前天的,以及大前天的。
她將我們的錢和貴重物品收在衣櫥後方的一個小舊背包裡,我看著我們那筆小小的財富開始漸漸縮水。相對來說,我們過得還算舒適──堅定的信徒確保了這點──但母親拒絕投資更多在我們的住所上,只要我提議到城裡更便宜的區域租個小公寓,她就搖頭拒絕。看來她對自己的生活只有個簡單的規劃,就是藉酒驅逐夢魘,只要有床可睡、有瓶酒可飲盡,其他一概無關痛癢。跟過去簡直有著天壤之別,我曾在這女人的懷抱裡度過早年歲月,她曾經是個舉止神態有如電影明星,風情萬種的名媛嬌妻,頂著最新潮的髮型、身穿最細緻的禮服。
這兩個女人天差地別,肯定會互相鄙視。
惡魔的女兒
倫敦2022/巴黎1946
1
如果每個人因為自己沒做的善事而有罪,有如伏爾泰提議的,那麼我這輩子都在想辦法說服自己,說起所有的惡行,我都是無辜的。這一直是個方便門,讓我得以承受幾十年來遠離過往的自我放逐,視自己為歷史失憶的受害者,卸除共犯的罪名,並且免於受到責難。
不過,我最終的故事始於也終於開箱刀這個微不足道的小東西。我的開箱刀幾天前壞掉了,我發現廚房抽屜非得放一把這種實用的工具不可,於是前往當地的五金行買把新的。我回來的時候,仲介留了封信給我,冬市苑的每個住戶都收到了類似的信件,客客氣氣通知我們每個人,我樓下的公寓即將出售。前任居民李察森先生住在一號公寓三十年之久,但聖誕節以前不久過世了,住處於是騰了出來。他女兒是語言治療師,住在紐約,就我所知,她並不打算回倫敦。於是我只好接受不久之後就會被迫在大廳跟陌生人互動,甚至必須假裝對對方的生活有興趣,或是不得不吐露一點關於自己的小細節。
我和李察森先生向來維持著完美的鄰居關係,因為我們從二○○八年起就不曾交換過隻字片語,他入住的早年歲月,我們一度關係友好,他偶爾會上樓來跟我先夫艾德格下盤棋,但我跟他素來只是相敬如賓。他總是稱呼我為「芬斯比太太」,我則稱他為「李察森先生」。我最後一次踏進他的公寓,是在艾德格過世四個月之後,他邀請我共進晚餐,我接受了邀約,然後婉拒了對方發動的愛情攻勢。他對我的拒絕反應激烈,後來我們幾乎形同陌路,成了兩個同住一棟樓房的陌生人。
我位於梅費爾區的住處登記為公寓,但這有點類似將溫莎城堡形容為女王週末的避居處。我們這棟樓房的每戶公寓──總共有五戶,一戶在地面樓層,上面兩層則各有兩戶──占地一千五百平方英尺,在倫敦地產的黃金地段,每戶都有三間臥房、兩間半浴室,加上海德公園的景色,按照可靠的資訊來源,每戶價值介於兩百至三百萬英鎊之間。艾德格在我們婚後幾年拿到了一筆豐厚的財產,是終身未婚的姑姑所遺贈,他更想搬到倫敦市中心外更寧靜的地方,但我事先做了點研究,打定主意不只要住在梅費爾區,如果有可能的話,更要住進這棟建築。財務上來說,原本看似毫無可能,但是有一天,彷彿有如神助,柏琳達姑姑過世了,一切都改變了。我一直計畫要向艾德格解釋,我這麼急著住進這裡的原因,可是從來不曾說過,我現在還滿後悔的。
我丈夫非常喜歡孩子,但我只同意生養一個,並在一九六一年生下我們的兒子卡登。近年來房地產增值,卡登鼓勵我賣掉這戶公寓,在城裡房價較低的地區買個坪數小點的單位,但我想那是因為他擔心我可能會活到一百歲,急著趁年輕還能享受的時候,拿到他的那份遺產。他結婚過三次,現在第四次訂婚;我已經放棄認識他生命中的女性。我發現每每才認識她們,她們就被送走,然後新的款式就會進駐,我還得花時間學習她們的特性,就像新型洗衣機或電視機。孩提時代,他就用類似的無情方式對待朋友。我們經常通電話,他每兩週就會過來吃一次晚飯,不過我們的關係複雜,部分因為我在他九歲時從他生活中缺席整整一年。事實是,我跟小孩相處就是不自在,而我發現小男孩特別難相處。
我對新鄰居的顧慮不是他或她可能發出不必要的噪音──這些公寓隔音效果很好,即使在這裡那裡有幾個瑕疵,經年以來,我已經習慣透過李察森先生天花板傳上來的各種奇特聲響──但我痛恨自己井井有條的世界可能會被顛覆。我希望進駐的人不會有興趣認識住樓上的婦人。也許來個病弱殘疾的老人家,鮮少離開家門,每天早上有家務幫手來探訪。或者是年輕專業人士,星期五下午消失,返回自己週末的家,然後星期天深夜才回來,其餘的時間都在辦公室或健身房。有個謠言傳遍了這棟樓,說有個事業在一九八○年代到達顛峰的知名流行樂手考慮把那戶當成退休以後的住家,但令人高興的是,這件事並無下文。
只要房仲把車停在外面,護送客戶參觀那戶公寓,我的窗簾就會跟著掀動:我針對每個潛在的鄰居都做了點筆記。有個前景看好七十出頭的夫婦,說話輕聲細語,手牽手,問這棟樓能否養寵物──我在樓梯井上側聽──被告知不行時,似乎相當失望。一對三十幾歲的同志伴侶,從他們刻意仿舊的服飾、帶有凌亂感的外觀看來,口袋肯定頗深,但他們說這個「場域」對他們來說可能有點小,覺得自己不大能跟它的「敘事」起共鳴。一個長相不起眼的年輕女子說,有個叫史提芬的人會很愛這裡的挑高天花板,除此之外並未洩漏自己的意願。想也知道,我希望是同志──他們很適合當鄰居,而且不大有機會生兒育女──但他們似乎興趣最低。
然後,幾個星期過後,仲介不再帶人來參觀,待售訊息從網路上消失了,我猜交易已經談定。不管我喜不喜歡,總有一天醒過來就會發現搬家貨車停在外頭,有個人或幾個人正把鑰匙插進前門,住進我樓下。
噢,我真害怕!
2
我和母親在一九四六年初期逃離德國,當時戰爭結束才幾個月,我們從殘破的柏林搭火車前往殘破的巴黎。我當年十五歲,對人生所知不多,但還是逐漸接受了軸心國被打敗的事實。父親曾經充滿信心說著我們種族在基因上多麼優越,以及元首身為軍事策略家有無以倫比的技巧,勝利指日可待。但是我們卻戰敗了。
橫越大陸將近七百英里的行程,不大能讓人對未來懷抱樂觀。我們行經的城市呈現近年來飽受摧殘的模樣,而我在車站和車廂裡看到的人臉並不因為戰爭結束而開心,而是因為戰爭的影響而受創。到處都彌漫著筋疲力竭的感覺;眾人逐漸領悟到,歐洲無法回到一九三八年的模樣,而必須整個重建,居民的心靈也是。
我出生的城市現在幾乎整個夷為平地,征服我們的四個勢力瓜分了戰利品。有少數堅定信徒的屋舍從戰火倖存下來,我們為了得到庇護,在取得偽造文件、確保可以安全離開德國以前,一直躲在他們家的地下室裡。現在,我們護照上的姓氏是蓋馬爾。為了確定聽起來很逼真,我反覆練習發音,母親現在要改名為娜塔莉──我祖母的名字──我則維持原名葛蕾朵。
關於集中營裡發生的事情,每天都有新的細節曝光,父親的名字成了天理不容罪行的代名詞。雖然沒人暗示我們跟他一樣有罪,但母親相信,要是我們向當局揭露自己的身分,肯定會招來災禍。我有同感,因為我跟她一樣害怕,雖然想到有人會認為我是暴行的共犯,震撼了我。確實,從我十歲生日以來,我一直是「少女聯盟」的成員,但德國的每個年輕女生都是,畢竟那是強制的,就像十歲男孩非得加入「德意志少年團」不可。可是,比起黨的意識形態,我更有興趣的是跟朋友參加定期的運動賽事。我們到了另一地方時,我只越過那道圍籬一次,當時父親帶我進營區觀察他的工作實況。我試圖告訴自己,我只是旁觀者,如此而已,告訴自己我的良心清白,但我已經開始質疑自己參與了我目睹的事件。
不過,我們的火車駛入法國時,我擔心口音會洩漏我們的身分。當然了,我推想,最近解放的巴黎公民因為一九四○年的立即投降感到羞愧,對於講話方式跟我們一樣的人都很不客氣。我的憂慮證實是對的,儘管強調我們身上帶的錢要長期住宿綽綽有餘,卻一連遭到五家民宿的拒絕。最後凡登廣場那裡有個婦人同情我們,給我們附近一家民宿的地址,說那個女房東不會多問,我們才找到落腳的地方。要不是因為她,我們可能會成為有錢卻浪跡街頭的可憐人。
我們租用的房間在西堤島東側,早先那些日子,我只在住處附近活動,將步行距離限制在從蘇利橋到新橋,然後再回來,永無止盡的迴圈,如果要過橋進入陌生區域就會備感焦慮。有時候我會想起弟弟,他一直渴望成為探險家,如果能夠辨識這些陌生街道,他該有多高興,但在這樣的時刻裡,我總是快快揮開對他的記憶。
我和母親住在島上兩個月之後,我才鼓起勇氣前往盧森堡公園,那裡綠意盎然,讓我覺得彷彿無意間遇見了天堂。我們初初抵達另一地方時,迎面就是光禿荒蕪的自然景象,跟這裡的對比起來好強烈,我想。在這裡,可以吸進生命的芬芳;在那裡,會因死亡的臭氣而嗆噎。我從盧森堡宮遊蕩到梅迪奇噴泉,彷彿陷入恍惚狀態,然後從那裡走往水池,看到一群小男孩將木船放進水裡,輕風將他們的小船帶到另一側的玩伴那裡,我便轉身離開。我無聲地苦惱著──這成了我日漸熟悉的情緒──苦思不解,為何一片大陸可以同時容納如此極端的美麗與醜陋,而他們的笑聲和興奮的對話提供了令人難受的背景音樂。
某天下午,我在滾球場附近的板凳上躲避陽光,發現自己被悲慟和內疚吞噬,淚水簌簌淌下我的臉。有個俊美的男孩,也許比我大兩歲,一臉擔憂走過來問我怎麼了。我抬起頭,湧上一絲慾望,渴望他能攬住我,或是讓我將頭靠在他肩上。但當我一開口,就落入了舊有的說話模式,德國口音壓過了我的法文,他往後退開一步瞪著我,神情不掩輕蔑,然後召喚起他對我族類所感到的怒火,當著我的面暴烈地啐了一口,然後大步走開。怪的是,他的舉止並未削減我對他撫觸的慾望,反倒增加了。我抹乾臉頰,追了過去並揪住他的手臂,邀請他帶我進樹林裡,並且告訴他,在隱密的空間裡他可以對我為所欲為。
「如果想要,你可以傷害我。」我輕聲說,閉起眼睛,心想他可能會用力摑我耳光,用拳頭揍我肚子,打斷我的鼻梁。
「妳為什麼想要那樣?」他問我,語氣洩漏出天真,與他的俊美互為牴觸。
「這樣我就會知道自己還活著。」
他似乎起了性慾同時又覺得反感,環顧四周看看是否有人旁觀,然後望向我指的小樹林。他舔舔嘴唇,觀察我起伏的胸脯,但是當我握住他的手,我的碰觸侮辱了他,他連忙將手抽開,用法文罵我妓女,然後拔腿就跑,消失在吉梅荷路上。
天氣好的時候,我從清晨開始在街頭遊蕩,回到租處時母親往往已經爛醉如泥,不會問我都怎麼打發時間。現在,她先前生活的雅致漸漸消散無蹤,但她依然是個外貌姣好的女子,我忖度她會不會再找個丈夫,找個可以照顧我們的人,可是她似乎不想要陪伴或愛情,寧可與自己的思緒獨處,在酒吧跟酒吧之間遊走。她買醉的時候很安靜,會坐在幽暗的角落裡慢慢啜飲一瓶瓶的酒,在木頭桌面上刮著隱形的刻痕,絕對不會鬧事,免得被趕到街上。有一次,太陽消失在布洛涅森林上方時,我們湊巧碰上了,母親搖搖晃晃走過來,勾住我的手臂,問我幾點了。她似乎不知道講話的對象是自己的女兒。我回答之後,她露出如釋重負的笑容──天色越來越暗,但酒吧還會營業好幾個小時──她持續朝著西堤島上燦亮誘人的點點燈火走去。我納悶,如果我完全消失,她是不是會忘記我曾經存在過?
我們共睡一張床,我很討厭在母親身邊醒來,吸進毒化她呼吸、注滿睡意的酒精臭氣。她睜開眼睛的時候,會困惑地坐起身,然後回憶就會一股腦兒湧回來,她便會合起雙眼,試圖回到不省人事的狀態。當她終於接受日光的無禮攪擾,勉強將自己從被單底下拖出來,就會到水槽那裡做基本的清洗,然後換上洋裝走到外頭去,高高興興重複昨天的時時刻刻,前天的,以及大前天的。
她將我們的錢和貴重物品收在衣櫥後方的一個小舊背包裡,我看著我們那筆小小的財富開始漸漸縮水。相對來說,我們過得還算舒適──堅定的信徒確保了這點──但母親拒絕投資更多在我們的住所上,只要我提議到城裡更便宜的區域租個小公寓,她就搖頭拒絕。看來她對自己的生活只有個簡單的規劃,就是藉酒驅逐夢魘,只要有床可睡、有瓶酒可飲盡,其他一概無關痛癢。跟過去簡直有著天壤之別,我曾在這女人的懷抱裡度過早年歲月,她曾經是個舉止神態有如電影明星,風情萬種的名媛嬌妻,頂著最新潮的髮型、身穿最細緻的禮服。
這兩個女人天差地別,肯定會互相鄙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