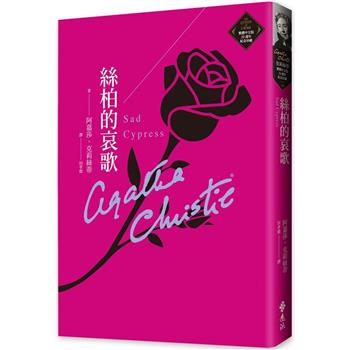序幕
「奧莉隆.凱瑟琳.克里修,你被指控於今年七月二十七日殺害了瑪麗.傑勒德。你是否承認自己有罪?」
奧莉隆.克里修筆直且昂首站立著,她那有如時裝模特兒般輪廓分明的面容上,有一雙靈巧湛藍的眼睛,兩道追隨時尚修剪的細眉,一頭烏黑亮麗的頭髮,使整個人散發著一股優雅的氣質。
法庭正籠罩在一片沉悶而緊張的寂靜中。
辯護律師艾德溫.布默先生心中沮喪而不安。
「我的天哪,她該不會是要承認自己有罪……恐怕她是支持不住了……」
奧莉隆開口了。
「我沒罪。」
辯護律師如釋重負地坐了下來,用手帕擦著額頭的汗水,心裡很清楚這件案子差點就將以悲劇收場。
檢察官山姆.艾頓博先生站起來說道:「敬愛的法官先生和各位陪審團員,今年七月二十七日下午三時三十分,瑪麗.傑勒德在曼登佛德的杭特伯利莊中死去……」
檢察官說話時提高分貝,響亮且悅耳的聲音直達每人耳中。他單調的敘述著事件經過,聽得奧莉隆神志恍惚,幾乎忘了周圍的一切,能進入她心中的只有一些零星片段。
「就其本質而言,該事件可以說是出人意料地簡單……原告方面的責任是證明被告犯罪的動機和可能性……
「從所有證據上來看,除被告之外,再也沒有第二個人存有殺害這不幸女孩瑪麗.傑勒德的動機了。她年輕善良,人緣甚佳,我可以斷言,在這個世界上,她不曾有任何仇敵。」
瑪麗,瑪麗.傑勒德!這一切是那麼地遙遠,猶如一場夢似的不真實……
「我認為本人有責任提醒諸位注意以下幾點:第一,被告曾有過哪些致死者於非命的機會?第二,她是因著什麼動機而做案?我會秉職責所在而盡可能提供證人,以幫助諸位做出正確的結論……
「對於瑪麗.傑勒德被害這一事實,我將盡力證明只有被告才有做案的動機和可能性……」
奧莉隆覺得自己好像在濃霧中迷了路,一個個不相關的獨立字眼在迷霧中無意義地飄浮著。
「……三明治……魚肉餡……空屋……」
這幾個字刺穿了奧莉隆沉重的思緒,戳破那重重包覆著的黑暗面紗……
法庭內一排排陌生的臉孔,其中有一張臉特別引人注意,那上面嵌著一雙清澈明亮的眼睛、兩撇烏黑濃密的鬍子。赫丘勒.白羅,他微微歪著頭,正若有所思地打量著她。
奧莉隆心想:他想了解我為什麼要下毒……他想看穿我的心思,想知道我有什麼樣的感覺……
感覺?一片模糊,一點驚恐……羅迪的面孔……多麼可愛而親切的面孔啊!修長的鼻子,柔軟的嘴唇……羅迪,全是羅迪!從她懂事的時候開始,從在杭特伯利莊的木莓園、養兔場、小河邊……羅迪,羅迪,羅迪……
接著是一些別的面孔,奧布萊護士正微張著嘴,長著雀斑、氣色良好的臉專注地向前傾。荷普金護士一副得意而冷酷的神情。彼得.洛德的臉……彼得.洛德總是那麼親切、感性,那麼……溫暖!可是他現在看來,卻是一臉──怎麼說呢,失落嗎?對,就是失落!一副憂心如焚的樣子。然而身為當事人的自己,這齣戲的主角,對眼前的這一切,卻已無動於衷了。
她只是異常冷靜地站著,站在被指控為殺人犯的被告席。
此時好像有什麼在奧莉隆的心中甦醒了;那纏繞在她腦海內的烏雲逐漸消散。她在法庭之中!四周都是人……
人們都專注地向前傾,嘴巴微張,瞪大眼睛,幸災樂禍地打量著她,並一派稱心如意地聆聽身材高大、有著猶太人豐鼻的檢察官在說話。
「本案的事實既簡單又無可置辯。接下來,我將就事實向諸位簡略地陳述。本案從一開始……」
一開始……一開始?就是接到那封可怕匿名信的那一天!這就是開始……
01
一封匿名信!
奧莉隆.克里修手裡拿著一封拆開的信,不知所措地看著。她從來未遇過這種事。這封信真令人不舒服,字跡醜陋,文法錯誤百出,寫在一張廉價的粉紅色信紙上。
寫這封匿名信是為了提醒你如下的事情:我就不提姓名,總之,有一個人已盯上你的姑媽,你若不留意將會失去所有。現在的年輕女孩太狡猾,而上了年紀的女士們則耳根子太軟,只要有人拍馬逢迎就言聽計從。你最好親自來這裡了解實際狀況吧。你和你的未婚夫若因此失去這份家產,那就太可惜了。這女孩手段高明,而你姑媽的身體隨時可能突然辭世。
善心人士
奧莉隆眉頭緊蹙,厭惡地看著這封信,就在這時候,女僕開門來通報說:「韋爾曼先生來了。」
羅迪走進房內。
羅迪!奧莉隆每一次見到羅迪,心中都有一絲迷亂的感覺、一陣喜悅的悸動,但她總是壓抑著不顯露出自己的情感。因為顯而易見的是,羅迪雖然也愛她,卻遠遠不及她愛他那樣強烈。第一次見到他,奧莉隆的心就像被攪動了似的,糾結得幾至心痛。說不出究竟是為什麼,一個長相如此普通的年輕男子,居然能如此吸引她,他的一個眼神能使人目眩神迷,他的聲音會讓你有種想哭的感覺。愛情的感覺應該是快樂喜悅的,但是如果愛得太深而竟至痛楚……
有一點她心裡是很明白的─她必須更加小心掩飾自己的感情,因為男人並不喜歡女人對他過度癡心和崇拜。尤其是對羅迪而言。
奧莉隆愉快地向羅迪打著招呼。
「哈囉,羅迪!」
「哈囉,親愛的!你看起來好像有心事,這是帳單嗎?」
奧莉隆搖搖頭,羅迪說:「我以為是帳單。仲夏時節嘛,小精靈漫天飛舞的同時,帳單也蹦蹦跳跳尾隨而至。」
奧莉隆搖著頭說道:「這個更糟,你看,這是一封匿名信。」
羅迪的眉毛向上一揚,他那冷傲的面容一瞬間僵住了。他不悅地厲聲說道:「不會吧!」
「真的很討厭。」奧莉隆向寫字檯走去,邊走邊說道,「我最好把它撕掉……」
她可以這樣做……而且差點就這麼做了。這事和羅迪八竿子打不著關係,她盡可以把信丟了,不再想它。羅迪絕不會阻止她,因為他對這類事情的厭惡程度遠勝過他的好奇心。
可是,此時奧莉隆卻改變了主意,她說道:「也許,先讓你看看,然後我再燒掉它。這信上所寫的事與蘿拉姑媽有關。」
羅迪的眉毛揚得更高了,他問道:「與蘿拉嬸嬸有關?」
他接過信,看了一遍,不快地皺皺眉頭,又把信還給了奧莉隆。
「對,」他說,「一定要把它燒掉!這世上竟有這樣的怪人!」
「你認為這會不會是哪個僕人寫的?」奧莉隆問道。
「很有可能。」他沒有把握地說道,「我很好奇信裡提到的女孩到底是誰呢?」
奧莉隆想了想。「一定是指瑪麗.傑勒德。」
羅迪皺起眉頭,極力回想:「瑪麗.傑勒德?她是誰?」
「就是門房的女兒。你應該記得她小時候的樣子?蘿拉姑媽一向喜歡這個女孩,對她十分寵愛,甚至還替她支付各種費用,包括音樂課和法語課等等的學費。」
「噢,我記起來了,就是那個長著一頭濃密金髮、全身瘦巴巴的小女孩吧?」
奧莉隆點點頭。
「自從你爸媽都選擇到國外去度暑假後,你大概沒有再見過她了。而且,你去杭特伯利莊的次數比我少,再加上之前一段時間她又去德國當人家的女伴。小時候我們經常找她一塊兒玩。」
「她現在長什麼樣子?」羅迪頗感興趣地問道。
「也許是受過教育的關係,她變得非常漂亮,看起來很有氣質,舉止得體。誰都看不出她是門房的女兒呢!」
「照你這麼說,那不是像一位名門淑女囉?」
「是呀。正因為這樣,我看她現在大概不願意再住在門房的僕人房裡了。她母親傑勒德太太死了好幾年,而她和父親處得並不好,老傑勒德老愛嘲弄女兒那身知書達禮的教養。」
羅迪氣憤地說道:「人們從來不知道,『教育』一個人會帶來什麼樣的傷害!那不是仁慈,相反的,是一種殘忍。」
奧莉隆說:「她在那裡的地位愈來愈重要……我知道在姑媽得了腦溢血以後,她經常為姑媽朗讀書報。」
「為什麼護士不讀給她聽呢?」
「奧布萊護士?」奧莉隆微笑著說道,「她一口愛爾蘭腔,聽了可是會使人發瘋的!這就難怪姑媽會比較喜歡瑪麗了。」
羅迪神經質地在房間裡來回踱步,走了約有一兩分鐘,然後說道:「奧莉隆,我認為我們有必要到杭特伯利莊走一趟。」
奧莉隆不悅地反問道:「就因為這封……」
「不,不,和這事無關。噢,該死……我還是老實說吧!沒錯,雖然這是一封卑鄙的匿名信,然而其中所說的事有可能成真,我指的是,老太太已經病入膏肓,而……」
「是的,羅迪。」
他帶著迷人的微笑看了奧莉隆一眼,像是承認人本性中有自私的一面,然後把自己的話說完:「這筆財產無論對你還是對我都很重要,奧莉隆。」
「噢,是的。」奧莉隆馬上回答表示支持。
羅迪又認真地說:「請不要認為我自私貪心,蘿拉嬸嬸自己不是經常說,我們是她唯一的親屬嗎?你是她弟弟的女兒,是她的親侄女,而我是她丈夫的侄子。她經常告訴我們說,她死後的一切財產不是歸你就是歸我,或是歸我們兩個所有。而那可是一筆巨額財產哪,奧莉隆。」
「是的,沒錯。」奧莉隆沉思地附和著。
「要維持杭特伯利莊可不是件開玩笑的事,」他說,「亨利叔父認識蘿拉嬸嬸時,就已經生活得相當富裕,而蘿拉嬸嬸本身也是個富有的遺產繼承人。她和你的父親都繼承了一筆為數可觀的遺產。只可惜,後來你父親去做投機生意,大部分的財產都賠進去了。」
奧莉隆嘆口氣說道:「可憐的爸爸,他實在沒有生意頭腦。直到他死前,還為著錢的事而不得安寧呢。」
「是呀,你的蘿拉姑媽倒是比你父親精明多了。她嫁給亨利叔父之後,他們就買下了杭特伯利莊。有一次她對我說,她的投資運一向非常好,從沒有損失慘重的情形發生。」
「亨利姑父把所有的家產都遺留給她了,是嗎?」
羅迪點頭說道:「是的,令人遺憾的是,他去世得太早,而她也一直沒有再婚。說起來她真是個傳統保守的女人,她對我們是呵護備至,待我就像對待自己的親侄子一樣。當我有需要的時候,她總是伸出援手幫我脫離困境,還好我沒有經常麻煩她。」
「她對我也是相當慷慨。」奧莉隆感激地補了一句。
「蘿拉嬸嬸真是個好人!」羅迪說道,「但是奧莉隆,你知道,以我們現在的財力,我們的生活可以說是過分揮霍了,雖然我們也不是故意的。」
「這話說得沒錯,我們的消費都太昂貴了,衣著啦、化妝品啦,還有一些諸如看電影、喝雞尾酒等沒必要的支出,甚至還買了一堆唱片。」
羅迪繼續說:「親愛的,你是那麼純潔,實在沒有必要工作,甚至和那些人周旋!」
「你這樣想嗎,羅迪?」奧莉隆問。
羅迪搖了搖頭。
「我之所以喜歡你,就是因為你優雅、孤高而且不同流俗。我不喜歡你正經八百的。我的意思是,如果不是蘿拉嬸嬸,你可能必須從事一些討厭的工作來養活自己。」他繼續說,「就像我,我有一份工作……算是吧。我在『路易斯和休姆公司』的工作還算輕鬆,那個地方很適合我。我工作是為了維持尊嚴,但我要聲明,我對未來是一點也不擔憂,因為我把希望全寄託在蘿拉嬸嬸身上。」
奧莉隆嘆息了一聲。
「說的好像我們是寄生蟲一樣。」
「胡說八道!我們只是事先得知自己將來會得到一筆遺產,這當然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活態度。」
奧莉隆思索著。
「可是,姑媽從未具體談過她要如何分配自己的財產。」
「這有什麼關係?我們不是已經準備結婚了嗎?所以,不論她的財產是平分給我們兩個人,或是因血緣關係全留給了你,或是為了使我負起韋爾曼家族的責任而留給了我,不管是留給我們當中的誰都可以,反正結果都一樣。」他迷人地微笑著,又補充道:「幸運的是,我們彼此相愛。你是愛我的吧,奧莉隆?」
「是呀。」她冷漠地回答著,不帶情緒。
「是呀。」羅迪模仿著她的口吻說道,「你太迷人了,奧莉隆。你是白雪公主,冰冷得難以靠近,我想也許正因為這樣,我才如此愛你。」
奧莉隆感到一陣窒息。她說道:「是嗎?」
「是的,」羅迪皺著眉頭說道,「有些女人實在是……呃,該怎麼說……占有欲太強,太……太做賤自己,無所保留,感情一發便不可收拾。但是和你在一起……我無法掌握,從不確定,你彷彿隨時會轉變心情,換上那副淡漠、疏離的姿態,告訴我你改變心意了,說時你可以冷若冰霜,甚至連眼睛都不眨一下!你真特別,奧莉隆,彷彿是一件精心雕琢的藝術珍品,是如此、如此地完美!」他繼續說,「我想我們的婚姻將會非常幸福。我們彼此相愛,但又不是那種過分的激情。我們也是很好的朋友,有很多共同的興趣。我們相知相惜,擁有表親屬間的親密溝通,卻無血親間的利益衝突。你永遠不會使我感到厭倦,因為你是這樣的難以捉摸。也許你會厭煩我,因為我是個平庸無奇的凡夫俗子……」
奧莉隆搖著頭說道:「我永遠不會對你厭煩,羅迪,永遠不會!」
「親愛的!」羅迪親吻了她,又接著說道:「蘿拉嬸嬸是個心細的人,她大概猜到我們兩人現在已經到了什麼程度,雖然我們自從決定婚事之後一直沒去過她那兒。看來,這倒是我們去看她的一個好理由呢!」
「是的,我曾經想過……」
羅迪替她說完了這句話。
「我也這麼認為,我們去她那裡的次數太少了。當她第一次中風時,我們幾乎每個週末都去看她,但現在已經將近兩個月沒去探望她了……」
「如果她叫我們去,我們一定會立即趕去的。」奧莉隆說。
「是的,那當然。因為我們知道奧布萊護士很中她的意,對她也照顧得很周到,所以比較放心。可是不管怎麼說,我們對她的關心還是不夠。我不是為了錢的關係才這麼說,這是身為晚輩該做的事。」
奧莉隆點一下頭說:「我知道。」
「所以,這封可惡的信倒也做了件好事。我們到她那兒去,一方面是保障自己的利益,除此之外,也因為我們確實喜歡這位令人敬愛的老太太!」
他從奧莉隆手中拿了那封信,劃了一根火柴燒了信,思索著說道:「到底是誰寫的呢?是否就像我們小時候常說的,有人和我們是『同一國』?或許有人特別關心我們。像吉姆.帕廷頓的母親,她到里維拉生活,在那兒愛上一個年輕的義大利醫生,她對他一片癡情,甚至到後來把自己所有的積蓄都給了他,儘管吉姆和他幾個姐妹對這份遺囑提出異議,但也無濟於事……」
奧莉隆笑了。
「蘿拉姑媽很喜歡那位新來的醫生──他是接替蘭塞姆醫生的──可是也不至於到那種地步啊!總之,這封討厭的信提到一個女孩,我想他指的一定就是瑪麗了。」
「等我們去了那裡,就會明白一切……」
奧布萊護士從韋爾曼夫人的臥室裡出來到浴室去,轉頭說道:「我來燒水,我想你也想喝杯茶了吧?」
荷普金護士欣然同意。
「親愛的,我隨時都可以來杯茶,再沒有比喝一杯好茶要更享受的了,濃茶尤其是我的最愛!」
奧布萊盛滿一壺水,放到爐子上說道:「我所有的用具都放在這個櫥櫃裡,茶壺、茶杯、糖,艾娜每天還送來兩次新鮮牛奶。真是沒必要按鈴麻煩那些僕人裝熱水,這個爐子很好,一壺水一下子就燒開了。」
奧布萊護士是個身材修長的紅髮女子,年約三十,有著一口潔白的牙齒,長著雀斑的臉總是笑咪咪的,她很爽朗、熱情,病人都喜歡她。荷普金護士則是個外表溫和的中年婦女,動作敏捷,活潑開朗。她是區公所護士,每天早上都會到村裡幫那些臥病的老太太如廁、整理房間。
荷普金護士稱讚地說道:「這房子的設備真是不錯。」
奧布萊點頭表示同意。
「是呀,雖然有些地方的設計已經跟不上潮流了,像是沒有暖氣設備。不過還有很多壁爐可以使用。在這裡工作的女孩都很聽話,碧夏太太把她們教得很好。」
荷普金說道:「現在的女孩子啊,真令我受不了,大都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工作表現更是令人不敢恭維。」
「瑪麗.傑勒德倒是個好女孩,」奧布萊辯解地說,「我無法想像要是沒有她,韋爾曼夫人該怎麼辦?你聽見韋爾曼夫人今天是怎樣叮囑她的嗎?總之,這小女孩確實是溫順可愛,她很有自己的作風。」
荷普金說:「我實在為瑪麗感到難過,她父親那個老頑固就知道想盡辦法折磨她。」
「就是嘛,從這個壞脾氣的老頭嘴裡,你是聽不到任何一句好話。」奧布萊表示深有同感。「水開了,等水一煮沸我馬上倒入茶中。」
不一會兒,茶已經沏好。兩位護士圍坐在韋爾曼夫人臥室隔壁的一間房間裡,這是奧布萊護士的房間。
「韋爾曼先生和克里修小姐今天會來。」奧布萊告訴對方。「今天早晨來了封電報。」
「這就對了,親愛的,」荷普金開心地說,「我才想,韋爾曼夫人今天看起來好像特別興奮。他們已經好久沒來了,不是嗎?」
「至少有兩個多月了吧!韋爾曼先生是個很不錯的年輕人,就是態度有些傲慢。」
荷普金說道:「我前些時候在《閒話東西》上看到『她』的一張照片,是她和朋友在馬克鎮照的。」
「她在社交界很紅,對吧?」奧布萊感興趣地說道,「而且總是穿得十分得體又出眾脫俗,你認為她長得美嗎?」
「這些女孩大半上了妝,很難知道她們真正的長相。就我個人認為,在外表上她不及瑪麗漂亮。」荷普金說。
奧布萊把嘴唇一嘟,歪著頭說道:「也許你說得沒錯,但瑪麗缺乏她的那種氣質。」
荷普金不以為然地說道:「有好的環境,自然可以塑造好的氣質。」
「你還要一杯嗎?」
「謝謝,我不介意再來一杯。」
兩個女人品茗著芳香的茶汁,親密地聊著。
奧布萊說道:「昨天夜裡有件事令我很不解。我和往常一樣,兩點鐘走進韋爾曼夫人的房間,想讓她躺得舒服一點,當時老太太已經醒了。但她一定還在作夢,因為她一看見我就說:『相片,拿相片給我。』
「我回答說:『好的,韋爾曼夫人。但可不可以等到明天早晨再拿?』她堅持說:『不,我現在就要看。』於是我問:『那好吧,相片在哪兒?你是不是想看羅迪先生的相片?』然後她說:『羅迪?不,我要路易斯的照片。』說完,她吃力地想撐起身子,我扶著她坐起來,她從靠近床旁邊的一個小匣子取出鑰匙,要我用鑰匙打開那個高腳櫃的第二個抽屜。裡面果真有一張鑲著銀框的大照片。照片裡是一位英俊的紳士,角落上橫寫著『路易斯』這個名字。相片是舊式的,一定是好多年前照的。我把相片遞給了她,她仔細端詳其中人物,看了好長一段時間,口裡低語地喚著:『路易斯,路易斯!』然後嘆了口氣把照片還給我,要我放回去。你相信嗎?當我放好相片回過頭來一看,她已經睡著了,睡得像個嬰兒一樣的香甜。」
「你認為這是她丈夫嗎?」荷普金好奇地問道。
「當然不是!今天早晨我不經意地問了一下碧夏太太說,已故韋爾曼先生的名字是什麼,她說是亨利。」
這兩個女人互看對方一眼。荷普金的鼻子很長,此時她的鼻尖因著興奮而微微震動著。她凝神思索著說道:「路易斯……路易斯,我不曾在這裡聽說過這個名字。」
「或許是許多年前的事了,親愛的。」奧布萊提醒她說。
「你說得對,我來到這裡的時間也不過幾年,可是我想……」
奧布萊說道:「那真是一個英俊的男人,看起來像是一個英挺的騎兵軍官。」
荷普金啜飲了一口茶說道:「這真的很有意思。」
奧布萊浪漫地說道:「也許他們年輕的時候曾在一起,卻被一個殘忍的父親硬生生地給分開了……」
「或許他最後死在戰場上。」荷普金深深嘆了口氣。
「奧莉隆.凱瑟琳.克里修,你被指控於今年七月二十七日殺害了瑪麗.傑勒德。你是否承認自己有罪?」
奧莉隆.克里修筆直且昂首站立著,她那有如時裝模特兒般輪廓分明的面容上,有一雙靈巧湛藍的眼睛,兩道追隨時尚修剪的細眉,一頭烏黑亮麗的頭髮,使整個人散發著一股優雅的氣質。
法庭正籠罩在一片沉悶而緊張的寂靜中。
辯護律師艾德溫.布默先生心中沮喪而不安。
「我的天哪,她該不會是要承認自己有罪……恐怕她是支持不住了……」
奧莉隆開口了。
「我沒罪。」
辯護律師如釋重負地坐了下來,用手帕擦著額頭的汗水,心裡很清楚這件案子差點就將以悲劇收場。
檢察官山姆.艾頓博先生站起來說道:「敬愛的法官先生和各位陪審團員,今年七月二十七日下午三時三十分,瑪麗.傑勒德在曼登佛德的杭特伯利莊中死去……」
檢察官說話時提高分貝,響亮且悅耳的聲音直達每人耳中。他單調的敘述著事件經過,聽得奧莉隆神志恍惚,幾乎忘了周圍的一切,能進入她心中的只有一些零星片段。
「就其本質而言,該事件可以說是出人意料地簡單……原告方面的責任是證明被告犯罪的動機和可能性……
「從所有證據上來看,除被告之外,再也沒有第二個人存有殺害這不幸女孩瑪麗.傑勒德的動機了。她年輕善良,人緣甚佳,我可以斷言,在這個世界上,她不曾有任何仇敵。」
瑪麗,瑪麗.傑勒德!這一切是那麼地遙遠,猶如一場夢似的不真實……
「我認為本人有責任提醒諸位注意以下幾點:第一,被告曾有過哪些致死者於非命的機會?第二,她是因著什麼動機而做案?我會秉職責所在而盡可能提供證人,以幫助諸位做出正確的結論……
「對於瑪麗.傑勒德被害這一事實,我將盡力證明只有被告才有做案的動機和可能性……」
奧莉隆覺得自己好像在濃霧中迷了路,一個個不相關的獨立字眼在迷霧中無意義地飄浮著。
「……三明治……魚肉餡……空屋……」
這幾個字刺穿了奧莉隆沉重的思緒,戳破那重重包覆著的黑暗面紗……
法庭內一排排陌生的臉孔,其中有一張臉特別引人注意,那上面嵌著一雙清澈明亮的眼睛、兩撇烏黑濃密的鬍子。赫丘勒.白羅,他微微歪著頭,正若有所思地打量著她。
奧莉隆心想:他想了解我為什麼要下毒……他想看穿我的心思,想知道我有什麼樣的感覺……
感覺?一片模糊,一點驚恐……羅迪的面孔……多麼可愛而親切的面孔啊!修長的鼻子,柔軟的嘴唇……羅迪,全是羅迪!從她懂事的時候開始,從在杭特伯利莊的木莓園、養兔場、小河邊……羅迪,羅迪,羅迪……
接著是一些別的面孔,奧布萊護士正微張著嘴,長著雀斑、氣色良好的臉專注地向前傾。荷普金護士一副得意而冷酷的神情。彼得.洛德的臉……彼得.洛德總是那麼親切、感性,那麼……溫暖!可是他現在看來,卻是一臉──怎麼說呢,失落嗎?對,就是失落!一副憂心如焚的樣子。然而身為當事人的自己,這齣戲的主角,對眼前的這一切,卻已無動於衷了。
她只是異常冷靜地站著,站在被指控為殺人犯的被告席。
此時好像有什麼在奧莉隆的心中甦醒了;那纏繞在她腦海內的烏雲逐漸消散。她在法庭之中!四周都是人……
人們都專注地向前傾,嘴巴微張,瞪大眼睛,幸災樂禍地打量著她,並一派稱心如意地聆聽身材高大、有著猶太人豐鼻的檢察官在說話。
「本案的事實既簡單又無可置辯。接下來,我將就事實向諸位簡略地陳述。本案從一開始……」
一開始……一開始?就是接到那封可怕匿名信的那一天!這就是開始……
01
一封匿名信!
奧莉隆.克里修手裡拿著一封拆開的信,不知所措地看著。她從來未遇過這種事。這封信真令人不舒服,字跡醜陋,文法錯誤百出,寫在一張廉價的粉紅色信紙上。
寫這封匿名信是為了提醒你如下的事情:我就不提姓名,總之,有一個人已盯上你的姑媽,你若不留意將會失去所有。現在的年輕女孩太狡猾,而上了年紀的女士們則耳根子太軟,只要有人拍馬逢迎就言聽計從。你最好親自來這裡了解實際狀況吧。你和你的未婚夫若因此失去這份家產,那就太可惜了。這女孩手段高明,而你姑媽的身體隨時可能突然辭世。
善心人士
奧莉隆眉頭緊蹙,厭惡地看著這封信,就在這時候,女僕開門來通報說:「韋爾曼先生來了。」
羅迪走進房內。
羅迪!奧莉隆每一次見到羅迪,心中都有一絲迷亂的感覺、一陣喜悅的悸動,但她總是壓抑著不顯露出自己的情感。因為顯而易見的是,羅迪雖然也愛她,卻遠遠不及她愛他那樣強烈。第一次見到他,奧莉隆的心就像被攪動了似的,糾結得幾至心痛。說不出究竟是為什麼,一個長相如此普通的年輕男子,居然能如此吸引她,他的一個眼神能使人目眩神迷,他的聲音會讓你有種想哭的感覺。愛情的感覺應該是快樂喜悅的,但是如果愛得太深而竟至痛楚……
有一點她心裡是很明白的─她必須更加小心掩飾自己的感情,因為男人並不喜歡女人對他過度癡心和崇拜。尤其是對羅迪而言。
奧莉隆愉快地向羅迪打著招呼。
「哈囉,羅迪!」
「哈囉,親愛的!你看起來好像有心事,這是帳單嗎?」
奧莉隆搖搖頭,羅迪說:「我以為是帳單。仲夏時節嘛,小精靈漫天飛舞的同時,帳單也蹦蹦跳跳尾隨而至。」
奧莉隆搖著頭說道:「這個更糟,你看,這是一封匿名信。」
羅迪的眉毛向上一揚,他那冷傲的面容一瞬間僵住了。他不悅地厲聲說道:「不會吧!」
「真的很討厭。」奧莉隆向寫字檯走去,邊走邊說道,「我最好把它撕掉……」
她可以這樣做……而且差點就這麼做了。這事和羅迪八竿子打不著關係,她盡可以把信丟了,不再想它。羅迪絕不會阻止她,因為他對這類事情的厭惡程度遠勝過他的好奇心。
可是,此時奧莉隆卻改變了主意,她說道:「也許,先讓你看看,然後我再燒掉它。這信上所寫的事與蘿拉姑媽有關。」
羅迪的眉毛揚得更高了,他問道:「與蘿拉嬸嬸有關?」
他接過信,看了一遍,不快地皺皺眉頭,又把信還給了奧莉隆。
「對,」他說,「一定要把它燒掉!這世上竟有這樣的怪人!」
「你認為這會不會是哪個僕人寫的?」奧莉隆問道。
「很有可能。」他沒有把握地說道,「我很好奇信裡提到的女孩到底是誰呢?」
奧莉隆想了想。「一定是指瑪麗.傑勒德。」
羅迪皺起眉頭,極力回想:「瑪麗.傑勒德?她是誰?」
「就是門房的女兒。你應該記得她小時候的樣子?蘿拉姑媽一向喜歡這個女孩,對她十分寵愛,甚至還替她支付各種費用,包括音樂課和法語課等等的學費。」
「噢,我記起來了,就是那個長著一頭濃密金髮、全身瘦巴巴的小女孩吧?」
奧莉隆點點頭。
「自從你爸媽都選擇到國外去度暑假後,你大概沒有再見過她了。而且,你去杭特伯利莊的次數比我少,再加上之前一段時間她又去德國當人家的女伴。小時候我們經常找她一塊兒玩。」
「她現在長什麼樣子?」羅迪頗感興趣地問道。
「也許是受過教育的關係,她變得非常漂亮,看起來很有氣質,舉止得體。誰都看不出她是門房的女兒呢!」
「照你這麼說,那不是像一位名門淑女囉?」
「是呀。正因為這樣,我看她現在大概不願意再住在門房的僕人房裡了。她母親傑勒德太太死了好幾年,而她和父親處得並不好,老傑勒德老愛嘲弄女兒那身知書達禮的教養。」
羅迪氣憤地說道:「人們從來不知道,『教育』一個人會帶來什麼樣的傷害!那不是仁慈,相反的,是一種殘忍。」
奧莉隆說:「她在那裡的地位愈來愈重要……我知道在姑媽得了腦溢血以後,她經常為姑媽朗讀書報。」
「為什麼護士不讀給她聽呢?」
「奧布萊護士?」奧莉隆微笑著說道,「她一口愛爾蘭腔,聽了可是會使人發瘋的!這就難怪姑媽會比較喜歡瑪麗了。」
羅迪神經質地在房間裡來回踱步,走了約有一兩分鐘,然後說道:「奧莉隆,我認為我們有必要到杭特伯利莊走一趟。」
奧莉隆不悅地反問道:「就因為這封……」
「不,不,和這事無關。噢,該死……我還是老實說吧!沒錯,雖然這是一封卑鄙的匿名信,然而其中所說的事有可能成真,我指的是,老太太已經病入膏肓,而……」
「是的,羅迪。」
他帶著迷人的微笑看了奧莉隆一眼,像是承認人本性中有自私的一面,然後把自己的話說完:「這筆財產無論對你還是對我都很重要,奧莉隆。」
「噢,是的。」奧莉隆馬上回答表示支持。
羅迪又認真地說:「請不要認為我自私貪心,蘿拉嬸嬸自己不是經常說,我們是她唯一的親屬嗎?你是她弟弟的女兒,是她的親侄女,而我是她丈夫的侄子。她經常告訴我們說,她死後的一切財產不是歸你就是歸我,或是歸我們兩個所有。而那可是一筆巨額財產哪,奧莉隆。」
「是的,沒錯。」奧莉隆沉思地附和著。
「要維持杭特伯利莊可不是件開玩笑的事,」他說,「亨利叔父認識蘿拉嬸嬸時,就已經生活得相當富裕,而蘿拉嬸嬸本身也是個富有的遺產繼承人。她和你的父親都繼承了一筆為數可觀的遺產。只可惜,後來你父親去做投機生意,大部分的財產都賠進去了。」
奧莉隆嘆口氣說道:「可憐的爸爸,他實在沒有生意頭腦。直到他死前,還為著錢的事而不得安寧呢。」
「是呀,你的蘿拉姑媽倒是比你父親精明多了。她嫁給亨利叔父之後,他們就買下了杭特伯利莊。有一次她對我說,她的投資運一向非常好,從沒有損失慘重的情形發生。」
「亨利姑父把所有的家產都遺留給她了,是嗎?」
羅迪點頭說道:「是的,令人遺憾的是,他去世得太早,而她也一直沒有再婚。說起來她真是個傳統保守的女人,她對我們是呵護備至,待我就像對待自己的親侄子一樣。當我有需要的時候,她總是伸出援手幫我脫離困境,還好我沒有經常麻煩她。」
「她對我也是相當慷慨。」奧莉隆感激地補了一句。
「蘿拉嬸嬸真是個好人!」羅迪說道,「但是奧莉隆,你知道,以我們現在的財力,我們的生活可以說是過分揮霍了,雖然我們也不是故意的。」
「這話說得沒錯,我們的消費都太昂貴了,衣著啦、化妝品啦,還有一些諸如看電影、喝雞尾酒等沒必要的支出,甚至還買了一堆唱片。」
羅迪繼續說:「親愛的,你是那麼純潔,實在沒有必要工作,甚至和那些人周旋!」
「你這樣想嗎,羅迪?」奧莉隆問。
羅迪搖了搖頭。
「我之所以喜歡你,就是因為你優雅、孤高而且不同流俗。我不喜歡你正經八百的。我的意思是,如果不是蘿拉嬸嬸,你可能必須從事一些討厭的工作來養活自己。」他繼續說,「就像我,我有一份工作……算是吧。我在『路易斯和休姆公司』的工作還算輕鬆,那個地方很適合我。我工作是為了維持尊嚴,但我要聲明,我對未來是一點也不擔憂,因為我把希望全寄託在蘿拉嬸嬸身上。」
奧莉隆嘆息了一聲。
「說的好像我們是寄生蟲一樣。」
「胡說八道!我們只是事先得知自己將來會得到一筆遺產,這當然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活態度。」
奧莉隆思索著。
「可是,姑媽從未具體談過她要如何分配自己的財產。」
「這有什麼關係?我們不是已經準備結婚了嗎?所以,不論她的財產是平分給我們兩個人,或是因血緣關係全留給了你,或是為了使我負起韋爾曼家族的責任而留給了我,不管是留給我們當中的誰都可以,反正結果都一樣。」他迷人地微笑著,又補充道:「幸運的是,我們彼此相愛。你是愛我的吧,奧莉隆?」
「是呀。」她冷漠地回答著,不帶情緒。
「是呀。」羅迪模仿著她的口吻說道,「你太迷人了,奧莉隆。你是白雪公主,冰冷得難以靠近,我想也許正因為這樣,我才如此愛你。」
奧莉隆感到一陣窒息。她說道:「是嗎?」
「是的,」羅迪皺著眉頭說道,「有些女人實在是……呃,該怎麼說……占有欲太強,太……太做賤自己,無所保留,感情一發便不可收拾。但是和你在一起……我無法掌握,從不確定,你彷彿隨時會轉變心情,換上那副淡漠、疏離的姿態,告訴我你改變心意了,說時你可以冷若冰霜,甚至連眼睛都不眨一下!你真特別,奧莉隆,彷彿是一件精心雕琢的藝術珍品,是如此、如此地完美!」他繼續說,「我想我們的婚姻將會非常幸福。我們彼此相愛,但又不是那種過分的激情。我們也是很好的朋友,有很多共同的興趣。我們相知相惜,擁有表親屬間的親密溝通,卻無血親間的利益衝突。你永遠不會使我感到厭倦,因為你是這樣的難以捉摸。也許你會厭煩我,因為我是個平庸無奇的凡夫俗子……」
奧莉隆搖著頭說道:「我永遠不會對你厭煩,羅迪,永遠不會!」
「親愛的!」羅迪親吻了她,又接著說道:「蘿拉嬸嬸是個心細的人,她大概猜到我們兩人現在已經到了什麼程度,雖然我們自從決定婚事之後一直沒去過她那兒。看來,這倒是我們去看她的一個好理由呢!」
「是的,我曾經想過……」
羅迪替她說完了這句話。
「我也這麼認為,我們去她那裡的次數太少了。當她第一次中風時,我們幾乎每個週末都去看她,但現在已經將近兩個月沒去探望她了……」
「如果她叫我們去,我們一定會立即趕去的。」奧莉隆說。
「是的,那當然。因為我們知道奧布萊護士很中她的意,對她也照顧得很周到,所以比較放心。可是不管怎麼說,我們對她的關心還是不夠。我不是為了錢的關係才這麼說,這是身為晚輩該做的事。」
奧莉隆點一下頭說:「我知道。」
「所以,這封可惡的信倒也做了件好事。我們到她那兒去,一方面是保障自己的利益,除此之外,也因為我們確實喜歡這位令人敬愛的老太太!」
他從奧莉隆手中拿了那封信,劃了一根火柴燒了信,思索著說道:「到底是誰寫的呢?是否就像我們小時候常說的,有人和我們是『同一國』?或許有人特別關心我們。像吉姆.帕廷頓的母親,她到里維拉生活,在那兒愛上一個年輕的義大利醫生,她對他一片癡情,甚至到後來把自己所有的積蓄都給了他,儘管吉姆和他幾個姐妹對這份遺囑提出異議,但也無濟於事……」
奧莉隆笑了。
「蘿拉姑媽很喜歡那位新來的醫生──他是接替蘭塞姆醫生的──可是也不至於到那種地步啊!總之,這封討厭的信提到一個女孩,我想他指的一定就是瑪麗了。」
「等我們去了那裡,就會明白一切……」
奧布萊護士從韋爾曼夫人的臥室裡出來到浴室去,轉頭說道:「我來燒水,我想你也想喝杯茶了吧?」
荷普金護士欣然同意。
「親愛的,我隨時都可以來杯茶,再沒有比喝一杯好茶要更享受的了,濃茶尤其是我的最愛!」
奧布萊盛滿一壺水,放到爐子上說道:「我所有的用具都放在這個櫥櫃裡,茶壺、茶杯、糖,艾娜每天還送來兩次新鮮牛奶。真是沒必要按鈴麻煩那些僕人裝熱水,這個爐子很好,一壺水一下子就燒開了。」
奧布萊護士是個身材修長的紅髮女子,年約三十,有著一口潔白的牙齒,長著雀斑的臉總是笑咪咪的,她很爽朗、熱情,病人都喜歡她。荷普金護士則是個外表溫和的中年婦女,動作敏捷,活潑開朗。她是區公所護士,每天早上都會到村裡幫那些臥病的老太太如廁、整理房間。
荷普金護士稱讚地說道:「這房子的設備真是不錯。」
奧布萊點頭表示同意。
「是呀,雖然有些地方的設計已經跟不上潮流了,像是沒有暖氣設備。不過還有很多壁爐可以使用。在這裡工作的女孩都很聽話,碧夏太太把她們教得很好。」
荷普金說道:「現在的女孩子啊,真令我受不了,大都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工作表現更是令人不敢恭維。」
「瑪麗.傑勒德倒是個好女孩,」奧布萊辯解地說,「我無法想像要是沒有她,韋爾曼夫人該怎麼辦?你聽見韋爾曼夫人今天是怎樣叮囑她的嗎?總之,這小女孩確實是溫順可愛,她很有自己的作風。」
荷普金說:「我實在為瑪麗感到難過,她父親那個老頑固就知道想盡辦法折磨她。」
「就是嘛,從這個壞脾氣的老頭嘴裡,你是聽不到任何一句好話。」奧布萊表示深有同感。「水開了,等水一煮沸我馬上倒入茶中。」
不一會兒,茶已經沏好。兩位護士圍坐在韋爾曼夫人臥室隔壁的一間房間裡,這是奧布萊護士的房間。
「韋爾曼先生和克里修小姐今天會來。」奧布萊告訴對方。「今天早晨來了封電報。」
「這就對了,親愛的,」荷普金開心地說,「我才想,韋爾曼夫人今天看起來好像特別興奮。他們已經好久沒來了,不是嗎?」
「至少有兩個多月了吧!韋爾曼先生是個很不錯的年輕人,就是態度有些傲慢。」
荷普金說道:「我前些時候在《閒話東西》上看到『她』的一張照片,是她和朋友在馬克鎮照的。」
「她在社交界很紅,對吧?」奧布萊感興趣地說道,「而且總是穿得十分得體又出眾脫俗,你認為她長得美嗎?」
「這些女孩大半上了妝,很難知道她們真正的長相。就我個人認為,在外表上她不及瑪麗漂亮。」荷普金說。
奧布萊把嘴唇一嘟,歪著頭說道:「也許你說得沒錯,但瑪麗缺乏她的那種氣質。」
荷普金不以為然地說道:「有好的環境,自然可以塑造好的氣質。」
「你還要一杯嗎?」
「謝謝,我不介意再來一杯。」
兩個女人品茗著芳香的茶汁,親密地聊著。
奧布萊說道:「昨天夜裡有件事令我很不解。我和往常一樣,兩點鐘走進韋爾曼夫人的房間,想讓她躺得舒服一點,當時老太太已經醒了。但她一定還在作夢,因為她一看見我就說:『相片,拿相片給我。』
「我回答說:『好的,韋爾曼夫人。但可不可以等到明天早晨再拿?』她堅持說:『不,我現在就要看。』於是我問:『那好吧,相片在哪兒?你是不是想看羅迪先生的相片?』然後她說:『羅迪?不,我要路易斯的照片。』說完,她吃力地想撐起身子,我扶著她坐起來,她從靠近床旁邊的一個小匣子取出鑰匙,要我用鑰匙打開那個高腳櫃的第二個抽屜。裡面果真有一張鑲著銀框的大照片。照片裡是一位英俊的紳士,角落上橫寫著『路易斯』這個名字。相片是舊式的,一定是好多年前照的。我把相片遞給了她,她仔細端詳其中人物,看了好長一段時間,口裡低語地喚著:『路易斯,路易斯!』然後嘆了口氣把照片還給我,要我放回去。你相信嗎?當我放好相片回過頭來一看,她已經睡著了,睡得像個嬰兒一樣的香甜。」
「你認為這是她丈夫嗎?」荷普金好奇地問道。
「當然不是!今天早晨我不經意地問了一下碧夏太太說,已故韋爾曼先生的名字是什麼,她說是亨利。」
這兩個女人互看對方一眼。荷普金的鼻子很長,此時她的鼻尖因著興奮而微微震動著。她凝神思索著說道:「路易斯……路易斯,我不曾在這裡聽說過這個名字。」
「或許是許多年前的事了,親愛的。」奧布萊提醒她說。
「你說得對,我來到這裡的時間也不過幾年,可是我想……」
奧布萊說道:「那真是一個英俊的男人,看起來像是一個英挺的騎兵軍官。」
荷普金啜飲了一口茶說道:「這真的很有意思。」
奧布萊浪漫地說道:「也許他們年輕的時候曾在一起,卻被一個殘忍的父親硬生生地給分開了……」
「或許他最後死在戰場上。」荷普金深深嘆了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