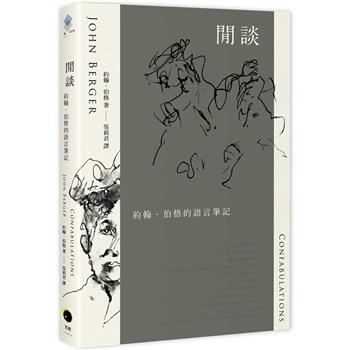自畫像
Self-Portrait
我已經寫了約莫八十年。起先是書信,接著是詩歌與講演,後來是故事、文章與書籍,如今是筆記。
一直以來,書寫行為對我至關緊要;它幫助我理解事物,延續人生。不過,書寫其實是分支,衍生自某個更深刻、更普遍的事物──我們和語言本身的關係。而這幾則筆記的主題,正是語言。
讓我們從不同語言之間的翻譯行為開始檢視。今日大多數的翻譯都是技術方面的,而我要談的是文學翻譯。也就是說,翻譯的文本內容與個人經驗有關。
傳統上對翻譯的看法,涉及到研究某一頁面上以某種語言書寫的字詞,然後將它們轉化成另一頁面上的另一種語言。這過程首先要進行所謂的逐字翻譯;接著要做出適當調整,以尊重並融入第二種語言的傳統和規則;最後要再下番苦功,重新創造出可等同於原始文本的「聲音」(voice)。許多翻譯,或說大多數的翻譯是遵循這樣的程序,得到的成果也頗具價值,但終究是二流翻譯。
何以這麼說?因為真正的翻譯並非兩種語言之間的二元關係,而是一種三角關係。這個三角形的第三點,是隱藏在原始文本書寫之前的字詞背後。真正的翻譯要求你回歸到言詞之前。
我們反覆閱讀、一再咀嚼原始文本,希望能穿透字詞,觸及到當初激發出這些字詞的景象或經驗。接著,我們採集在字詞背後發現之物,拿起那個顫顫巍巍、近乎無言的「東西」,把它放置在需要將它翻譯出來的主方語言(host language)背後。接下來的首要任務,就是說服主方語言接納並歡迎那個等著被言說出來的「東西」。
這種做法提醒我們,語言無法簡化成字典或詞庫。語言也無法減縮成以該語言書寫的作品庫。
口語是身體,是活物,它的外形容貌來自言詞,它的臟腑功能涉及語言學。而這個生物的家不只是那些可以言說的,更是那些不可言說的。
想想「母語」(Mother Tongue,字義是「母親的舌頭」)一詞。俄文的母語是Rodnoi-yazyk,意思是「最接近或最親近的舌頭」(Nearest or Dearest Tongue)。必要時,你可以稱它為「親愛的舌頭」(Darling Tongue)。
母語是我們的第一語言,是嬰兒時期最早從母親嘴裡聽到的。「母語」一詞就是這樣來的。
之所以提及這點,是因為我正在描述的語言生物毫無疑問是女性。我想像,那個語言生物的核心部位是語音子宮。
一種母語裡包含了所有母語。或者,換個說法:每一種母語都是共通的。
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曾做出精彩論述,證明所有語言都擁有某些共同的結構和程序,不僅限於說寫語言。也就是說,母語和非說寫式的語言也有關聯(也能押韻?),例如符號語言,行為語言,空間語言。
畫畫時,我就是在試圖解開並謄抄一份由形貌構成的文本,我知道,這份文本在我的母語裡已經有一個無法言喻但肯定無疑的位置。
單字、詞彙和短句,可以脫離它們所屬的語言生物,僅當成標籤使用。但如此一來,它們會變得呆板空洞。重複使用首字母縮寫就是一個顯而易見的範例。今日大多數的主流政治論述,都是由這類脫離了語言生物、無趣死氣的字詞所構成。而這類死氣沉沉的「浮言夸語」會抹除記憶,滋長無情的自滿。
多年來,促使我寫作的驅力,是我預感到有些事情需要被講述,如果我不試著講述它,它可能永遠沒機會被講述。所以,我不太會把自己想像成具有影響力的專業作家,更像是臨時上來救場的人。
書寫時,完成幾行之後,我會讓那些字詞溜回去,溜回它們所屬的語言生物。在那裡,它們馬上就被其他一堆字詞認出來,並熱烈歡迎,它們和那些字詞有一種意義的或對立的或隱喻的或頭韻的或節奏的親近性。我聽著他們交談議論。它們聚在一起,針對我挑選的字詞,爭辯我的用法。它們質疑我分派給它們的角色。
於是我調整文句,修改一兩個字,再次提交出去。另一陣交談議論接著展開。
如此這般循環往復,直到出現暫時達成共識的喃喃低語。我接著朝下一段推進。
另一陣交談議論再次展開……
其他人可以隨自己高興,把我定位成一名作家。但對我而言,我是惡女之子(the son of a bitch)──你們應該能猜出那個惡女是誰,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