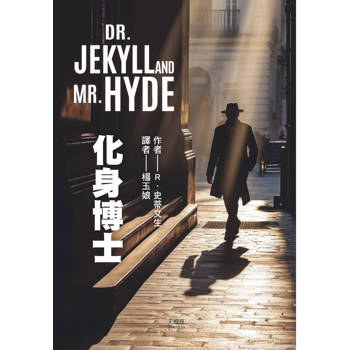第一章 門的故事
1.律師歐特森先生
律師歐特森先生長著一張其貌不揚的面孔,佈滿皺紋的臉上從來不曾因為微笑而容光煥發;言語枯燥,沈靜寡言,明明簡單的事情到了他的口中總會變得越說越複雜,而且非常不善於表達自己的情感或觀點;手長腳長,老是一副猥瑣落寞的陰沈相。
可是話說回來,卻也還是有他受人喜愛的地方。在氣氛和善的聚會裡,當口中的美酒投合脾胃之際,他的眼中自然迸射出兩道閃耀異常的人性光彩;那是在他言語應對之間從來不曾展現的東西,但在飽餐之後的臉龐上,一個個默默無言的表徵裡,卻不聲不響地自動流露出來,而在日常生活舉止中,更是頻頻明顯地出現。
他的為人律己甚嚴,刻苦自持;在獨處之時只喝以杜松子釀造而成的琴酒,至於個人雅好的葡萄美酒卻是絕口不沾;儘管喜歡戲院,距離最後一次跨進其中任何一家的大門也已有足足二十來年了。
相對地,他待人之寬、容忍的氣度之大,則值得廣受稱揚。
偶而,他也會懷著幾近羨慕的心態,亟欲體會包藏於人們惡行當中的高度精神壓力。
此外,相較於譴責,他百分之一百二十傾向於選擇協助。
「我樂意相信該隱的異端邪說;」他常三天兩頭莫名其妙地說:「我聽任我的兄弟肆無忌憚地沾染惡習。」
正由於具備這樣的一種性格,歐特森先生每每有機會成為墮落沈淪之輩一生中結識的最後一位高尚人士,同時也是最後一個好影響。
只要他們正好走進自己的辦事處裡來,他對待這些人的言行態度絕不會有一絲一毫不同於平常。
無疑的,這樣的表面演出對於律師歐特森先生根本就是輕輕鬆鬆的小事一樁,因為他原本就是一個喜怒完全不形於色的人;就連友誼也似乎建立在同樣的寬大為懷、溫厚性情基礎上。
從機會之神手中手中接下現成的友好圈子,對於個性靦蜆的謙沖之士而言乃是常情,而發生在律師身上的正是這種狀況。
他的朋友若非是自己的血親,就是不知已經相識多少年的人。他的情感猶如長春藤一般,與時俱增,瞧不出什麼特定的攀附對象。
是以,聯繫住他和理查 英費爾德先生的無疑正是這一條繫帶;對方是他一表八千里的一名遠親,也是城裡城外無人不曉的名人。這兩名男人彼此可以從對對方身上看到不少相似處,或者發現許多共通性話題。
根據那些在他倆的禮拜日散步途中與之邂逅的人們傳言,當他或他乍見自己的好友身影出現眼前之際,兩人的反應都是一語不發,滿臉呆滯的遲頓表情,隨即如釋重負般地開口大聲招呼對方。
最重要的,他們兩人極端重視這一趟固定的漫遊,把它們視為一週裡面最值得珍視的大事,不僅謝絕出席娛樂場合,甚至不肯接受職業上的召喚,以便在不受打擾的情況下充分享受彼此的共遊之樂。
就在其中一次漫步裡,他俩偶然走到倫敦市內某個繁忙區域的一條支道上。那是一條人們所謂寧靜的小街,不過在平常非週日的日子裡,卻也是人來人往,生意十分活絡。
街道兩旁的居民日子看來都過得不錯,而且全都競相期望能過更好的生活,甚至賣弄似地將自家盈溢的穀物盡情展示出來;於是一家家店舖的門面便宛如兩排笑意盈盈的女店員,帶著殷勤招攬的姿態,整整齊齊羅列在街道的兩側。
即使到了禮拜天,小街鮮麗的容貌已蒙上一層面紗,走廊也在相形之下顯得空空盪盪後,只要與骯髒昏暗的鄰近地區互相做個對照,仍然覺得有如一把森林中的烽火,閃閃發出奪目的光芒。
它那一扇扇剛粉刷過的遮門與窗板,磨得光可鑑人的黃銅門牌,以及清新潔淨、鮮艷明亮的整體風格,瞬間擄獲過往行人的注意,令他們倍添賞心悅目之情。
在左手往東行進的方向上,自某個轉角算起的兩戶大門外,整排行列被一座庭院的入口給打斷;就在同一個地點,一棟外觀予人凶險印象的建築阻擋住此去的視線,臨街一側的山形牆並向前突伸出來。
那棟建築共計上下兩層樓,整個正面不見一扇窗戶,只在樓下那層存在一扇大門;至於上層則不僅門窗均無,就連一個孔洞也不見,只是一片褪了顏色、髒兮兮的牆;無論是從哪一個角度看去,都顯現出多年荒廢、無人照管,污穢不潔的跡象。既無門鈴又沒扣環的大門不僅已經變了色,更在日曬雨淋之中冒出一塊塊浮泡。
流浪漢們垂頭喪氣踅進它的壁凹裡,就著門板便劃起火柴;不少小孩在它的臺階上面擺攤做買賣;小學生利用它的嵌線來磨刀;將近整整三十年的時間裡,從未有人現身趕走這些隨意來去的過客,或者修復慘遭他們破壞的地方。
2.邪惡的神情
英費爾德先生與律師行走的路線是在街道另一側,但當兩人來到入口對面時,前者卻舉起他的手杖指指點點地詢問:「你可曾注意到那一扇大門?」
等到獲得同伴的肯定回答後,他又緊接著說道:「在我心中,它與某個十分詭異的故事間有著相當密切的結合。」
「真的?」歐特森先生語氣微微一變:「是什麼故事?」
「唔,是這樣的……」英費爾德先生作了以下的回答——
時間是某個星月無光的冬天凌晨,大約在三點鐘左右,我正從遙遠世界盡頭的某處返回家中,途中必須經過城市的某一地帶,除了燈光,眼裡真的什麼也看不見。
一條街道走過另一條街道,所有的人們都已經睡著——一條街又過另一條街,家家戶戶都燈火通明,彷彿是在迎接某個遊行的隊伍,偏又全都空盪盪的有如教堂一般。
直到最後,我終於陷入與那種不時豎起雙耳全神貫注聆聽,並開始渴望能夠見到一名警察之人同樣的心理狀態。
忽然間,我猛看見兩條身影:其一是名身材瘦小的男子,他正著僵直的步伐大步朝東行走;另外一人則是個大約八到十歲之間的小女孩,正拼了命似的邁動飛快的腳步狂奔過街。
噢,先生,這兩個人自然而然在街道的轉角處撞成了一團;然後——恐怖的情況發生了;
因為那名男子竟若無其事地從那個孩子身上踩過去,任由她倒在地上哀哀叫個不停。也許您光聽這樣說並不覺得很稀奇,可是親眼看到那幅畫面可真是慘不忍睹。
就好像踏過那個女孩身上的不是個男人,而是印度教的傳說裡頭那位專門送人升天的護持神。
1.律師歐特森先生
律師歐特森先生長著一張其貌不揚的面孔,佈滿皺紋的臉上從來不曾因為微笑而容光煥發;言語枯燥,沈靜寡言,明明簡單的事情到了他的口中總會變得越說越複雜,而且非常不善於表達自己的情感或觀點;手長腳長,老是一副猥瑣落寞的陰沈相。
可是話說回來,卻也還是有他受人喜愛的地方。在氣氛和善的聚會裡,當口中的美酒投合脾胃之際,他的眼中自然迸射出兩道閃耀異常的人性光彩;那是在他言語應對之間從來不曾展現的東西,但在飽餐之後的臉龐上,一個個默默無言的表徵裡,卻不聲不響地自動流露出來,而在日常生活舉止中,更是頻頻明顯地出現。
他的為人律己甚嚴,刻苦自持;在獨處之時只喝以杜松子釀造而成的琴酒,至於個人雅好的葡萄美酒卻是絕口不沾;儘管喜歡戲院,距離最後一次跨進其中任何一家的大門也已有足足二十來年了。
相對地,他待人之寬、容忍的氣度之大,則值得廣受稱揚。
偶而,他也會懷著幾近羨慕的心態,亟欲體會包藏於人們惡行當中的高度精神壓力。
此外,相較於譴責,他百分之一百二十傾向於選擇協助。
「我樂意相信該隱的異端邪說;」他常三天兩頭莫名其妙地說:「我聽任我的兄弟肆無忌憚地沾染惡習。」
正由於具備這樣的一種性格,歐特森先生每每有機會成為墮落沈淪之輩一生中結識的最後一位高尚人士,同時也是最後一個好影響。
只要他們正好走進自己的辦事處裡來,他對待這些人的言行態度絕不會有一絲一毫不同於平常。
無疑的,這樣的表面演出對於律師歐特森先生根本就是輕輕鬆鬆的小事一樁,因為他原本就是一個喜怒完全不形於色的人;就連友誼也似乎建立在同樣的寬大為懷、溫厚性情基礎上。
從機會之神手中手中接下現成的友好圈子,對於個性靦蜆的謙沖之士而言乃是常情,而發生在律師身上的正是這種狀況。
他的朋友若非是自己的血親,就是不知已經相識多少年的人。他的情感猶如長春藤一般,與時俱增,瞧不出什麼特定的攀附對象。
是以,聯繫住他和理查 英費爾德先生的無疑正是這一條繫帶;對方是他一表八千里的一名遠親,也是城裡城外無人不曉的名人。這兩名男人彼此可以從對對方身上看到不少相似處,或者發現許多共通性話題。
根據那些在他倆的禮拜日散步途中與之邂逅的人們傳言,當他或他乍見自己的好友身影出現眼前之際,兩人的反應都是一語不發,滿臉呆滯的遲頓表情,隨即如釋重負般地開口大聲招呼對方。
最重要的,他們兩人極端重視這一趟固定的漫遊,把它們視為一週裡面最值得珍視的大事,不僅謝絕出席娛樂場合,甚至不肯接受職業上的召喚,以便在不受打擾的情況下充分享受彼此的共遊之樂。
就在其中一次漫步裡,他俩偶然走到倫敦市內某個繁忙區域的一條支道上。那是一條人們所謂寧靜的小街,不過在平常非週日的日子裡,卻也是人來人往,生意十分活絡。
街道兩旁的居民日子看來都過得不錯,而且全都競相期望能過更好的生活,甚至賣弄似地將自家盈溢的穀物盡情展示出來;於是一家家店舖的門面便宛如兩排笑意盈盈的女店員,帶著殷勤招攬的姿態,整整齊齊羅列在街道的兩側。
即使到了禮拜天,小街鮮麗的容貌已蒙上一層面紗,走廊也在相形之下顯得空空盪盪後,只要與骯髒昏暗的鄰近地區互相做個對照,仍然覺得有如一把森林中的烽火,閃閃發出奪目的光芒。
它那一扇扇剛粉刷過的遮門與窗板,磨得光可鑑人的黃銅門牌,以及清新潔淨、鮮艷明亮的整體風格,瞬間擄獲過往行人的注意,令他們倍添賞心悅目之情。
在左手往東行進的方向上,自某個轉角算起的兩戶大門外,整排行列被一座庭院的入口給打斷;就在同一個地點,一棟外觀予人凶險印象的建築阻擋住此去的視線,臨街一側的山形牆並向前突伸出來。
那棟建築共計上下兩層樓,整個正面不見一扇窗戶,只在樓下那層存在一扇大門;至於上層則不僅門窗均無,就連一個孔洞也不見,只是一片褪了顏色、髒兮兮的牆;無論是從哪一個角度看去,都顯現出多年荒廢、無人照管,污穢不潔的跡象。既無門鈴又沒扣環的大門不僅已經變了色,更在日曬雨淋之中冒出一塊塊浮泡。
流浪漢們垂頭喪氣踅進它的壁凹裡,就著門板便劃起火柴;不少小孩在它的臺階上面擺攤做買賣;小學生利用它的嵌線來磨刀;將近整整三十年的時間裡,從未有人現身趕走這些隨意來去的過客,或者修復慘遭他們破壞的地方。
2.邪惡的神情
英費爾德先生與律師行走的路線是在街道另一側,但當兩人來到入口對面時,前者卻舉起他的手杖指指點點地詢問:「你可曾注意到那一扇大門?」
等到獲得同伴的肯定回答後,他又緊接著說道:「在我心中,它與某個十分詭異的故事間有著相當密切的結合。」
「真的?」歐特森先生語氣微微一變:「是什麼故事?」
「唔,是這樣的……」英費爾德先生作了以下的回答——
時間是某個星月無光的冬天凌晨,大約在三點鐘左右,我正從遙遠世界盡頭的某處返回家中,途中必須經過城市的某一地帶,除了燈光,眼裡真的什麼也看不見。
一條街道走過另一條街道,所有的人們都已經睡著——一條街又過另一條街,家家戶戶都燈火通明,彷彿是在迎接某個遊行的隊伍,偏又全都空盪盪的有如教堂一般。
直到最後,我終於陷入與那種不時豎起雙耳全神貫注聆聽,並開始渴望能夠見到一名警察之人同樣的心理狀態。
忽然間,我猛看見兩條身影:其一是名身材瘦小的男子,他正著僵直的步伐大步朝東行走;另外一人則是個大約八到十歲之間的小女孩,正拼了命似的邁動飛快的腳步狂奔過街。
噢,先生,這兩個人自然而然在街道的轉角處撞成了一團;然後——恐怖的情況發生了;
因為那名男子竟若無其事地從那個孩子身上踩過去,任由她倒在地上哀哀叫個不停。也許您光聽這樣說並不覺得很稀奇,可是親眼看到那幅畫面可真是慘不忍睹。
就好像踏過那個女孩身上的不是個男人,而是印度教的傳說裡頭那位專門送人升天的護持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