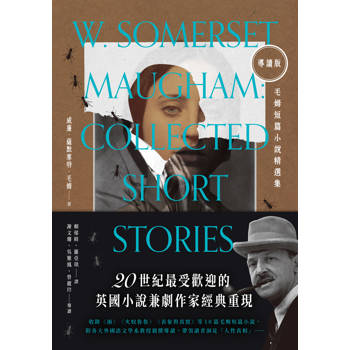導讀簡介
謝文珊 副教授
英國薩賽克斯大學英語文學博士。現任實踐大學應用外語學系副教授。研究領域包括現當代英語文學、英語短篇小說及醫療人文研究。相關論文發表於 Tamkang Review 和 Katherine Mansfield Studies 等國內外期刊,並收錄於《文學、視覺文化與醫學》和《再探醫學與文學》兩本論文集中。其論文曾入圍二○二二年曼殊斐兒學會論文獎(Katherine Mansfield Society Essay Prize)決選名單。
吳雅鳳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教授,於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取得英國文學博士,英國牛津大學英國文學碩士,主要研究英國浪漫主義、藝術史、自然史、東西物質與敘事交流、志異文學、哥德復興建築文化、環境人文等。
曾麗玲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含喬伊斯小說、貝克特小說、二十世紀英國小說。
推薦序
學界幾乎要遺忘他的今日,毛姆小說至今仍有廣大讀者群。
在他的時代,現代主義正值高峰,文學形式的實驗百花齊放,新技巧前衛而多元;而毛姆則謹守寫實筆法,以簡單的文句描摹人性之百態,故事娛樂性高,作品在商業上頗為成功。
現代主義巨擘勞倫斯(D. H. Lawrence)認為毛姆只是迎合都會讀者群的品味,談不上藝術;毛姆則以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等寫實主義者為寫作導師,認為詹姆斯(Henry James)、康拉德(Joseph Conrad)等人迂迴百轉的新文風,有害於誠摯切實的表達原則。然而,在現代主義眾星的巨大光芒掩蓋下,毛姆常被文學史貶為次流,像是一個生錯時代的寫實主義遺孤,只能在其讀者群中避免遭歷史遺忘。
即便如此,毛姆仍留下不少文學遺產,如間諜小說。毛姆與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有私交,一戰與二戰期間都做過政府特務,近距離觀察過俄國革命和納粹德軍占領巴黎等事件。以這些經驗為背景,毛姆創立了間諜小說這個新類型文學,影響了新一代的作家如格林(Graham Greene)、勒卡雷(John Le Carré)等。
除了小說,毛姆也寫戲劇、散文、評論,其戲劇尤其受歡迎,不過流傳於世的卻是小說。
觀毛姆其人,有其複雜面。他的言行舉止像個典型英國紳士,在文人圈中人脈極廣,有頭有臉的人物幾乎都認識。可是他也與很多人不合,有人甚至覺得他高傲、冷漠。
但這或許非性格使然,而是因為毛姆有口吃、具政府特務背景,還是未出櫃的同志。有鑑於同志前輩王爾德(Oscar Wilde)的下場,毛姆對此終身戒慎恐懼,生前不願讓私生活的任何方面見光,使他充滿神祕。毛姆在文化圈之活躍,猶如一位不沾俗塵的文人;而他與政府的關係,又使人感覺他像是大英帝國在文化圈的宣傳人。
不管真相如何,大英帝國在毛姆的時代實已逐漸衰敗,從毛姆故事常有的悲劇、反諷中,也能聞到一絲帝國沒落的氣息。
毛姆善用且好用反諷,故事人物的想法、期待、信念常與結果相反而行為反覆,故事也常以反轉或反高潮作結。其行文的語調從容、節奏穩定,讀其小說像在高遠處靜靜地俯視人世間的各種怪誕與謎團,觀察人生這匹善惡絲線交織的布。
《人性枷鎖》中,毛姆曾說「正常是這世界上最稀有的事」。評論界常認為大量反諷是展現其冷眼觀世、不信任人性,甚至厭世的性格。
一方面來說,這個說法勉強有些道理,因為反諷讓人不敢輕易相信世間的人事物,因此得以對所見所聞保持距離,不輕易入戲動情;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毛姆是繼承了自《唐吉軻德》(The Ingenious Gentleman Don Quixote of La Mancha)以來的小說傳統,著重描寫表象與真相、理想與現實的差距。
唐吉軻德的幻想在很多英國人眼裡是警世寓言,勸人不要過於執著投入,懷有高遠的理想。傳統上,英國文化對普世價值抱持懷疑,對理論、形而上、宏遠的大問題缺乏興趣。因此,毛姆沒有處理這些大問題的野心,只是從經驗中的種種細節觀察難以捉摸的人與事,以反諷方式,不願為其輕易下定論。
讀毛姆的小說,我們是否會懷疑故事中發人省思的人物與事件,不是那些經世濟民、使人夜不成眠的憂思,而只是文人墨客社交時閒談的話題?這就讓讀者們自行判斷吧。
──國立嘉義大學 外國語言學系暨研究所 專案助理教授 陳麒方
自序
這本書是這部短篇小說選集的第一卷(編註:本書僅收錄其中的前十篇)。我年少時曾寫過幾篇短篇小說,有一些被收錄在早已絕版的書中,另一些則分散刊載於各種雜誌裡,但是當時我的寫作還不夠成熟,因此並沒有將那些作品收錄於選集中。最好讓那些故事就這樣被遺忘吧。這部選集中的第一篇故事〈雨〉是我於一九二○年在香港時所寫,靈感來自一九一六年冬季的一場南太平洋旅行;選集中的最後一篇小說於一九四五年的紐約完成,源自當時我偶然在文件推中找到、寫於一九○一年的簡短筆記。往後我預計不會再寫其他短篇作品了。
當一位作者要將數量繁多的故事彙集成冊時,最困難的事情之一莫過於決定故事的先後順序。若這些故事的篇幅相似或地點(local)相同,作品的排列順序和編排格式就相對簡單了(我本來想用「場景〔locale〕」,不過牛津詞典說這個字雖然常用,但其實是誤用)。對作者來說,若能將故事編排得巧妙,讓書本在最終呈現給讀者時有一定的邏輯脈絡,那麼即便讀者沒有察覺,也是件令人心滿意足的事情。小說的結構簡單明瞭,有開頭、過程和結尾,而一篇架構良好的故事亦是如此。
然而,我所寫的故事篇幅不一,有些短至一千六百字,有些則長達一萬六千字,其中一篇甚至超過二萬字。我曾漂泊於世界各地,寫作時總會在各個棲身之地獲取一兩篇故事的素材。我寫過悲劇性的故事,也寫過幽默詼諧的故事。要將寫作篇幅、故事場景、題材性質如此相異且數量眾多的故事集結成冊,同時又要盡可能地讓讀者能輕鬆閱讀,著實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儘管讓故事被閱讀並非作者寫作的動機,但作品一旦完成,作者還是會抱有希望讀者看見的渴望,而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就必須盡量提升故事的易讀性。
基於這個目的,我盡可能地將一系列的短篇故事接在篇幅較長的故事之後;這些故事有的非常短,有的則有五、六千字之長,如此一來,讀者在閱讀時就無需突然從中國跳到祕魯,然後再跳回來。同時,我也盡量將發生地點(local)或場景(locale)在同一國家的故事排在一起,這樣編排就輕鬆多了。我希望透過這樣的安排,讓讀者在我的帶領下前往遙遠國度時,都能明確地找到自己的所在位置。
謝文珊 副教授
英國薩賽克斯大學英語文學博士。現任實踐大學應用外語學系副教授。研究領域包括現當代英語文學、英語短篇小說及醫療人文研究。相關論文發表於 Tamkang Review 和 Katherine Mansfield Studies 等國內外期刊,並收錄於《文學、視覺文化與醫學》和《再探醫學與文學》兩本論文集中。其論文曾入圍二○二二年曼殊斐兒學會論文獎(Katherine Mansfield Society Essay Prize)決選名單。
吳雅鳳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教授,於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取得英國文學博士,英國牛津大學英國文學碩士,主要研究英國浪漫主義、藝術史、自然史、東西物質與敘事交流、志異文學、哥德復興建築文化、環境人文等。
曾麗玲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含喬伊斯小說、貝克特小說、二十世紀英國小說。
推薦序
學界幾乎要遺忘他的今日,毛姆小說至今仍有廣大讀者群。
在他的時代,現代主義正值高峰,文學形式的實驗百花齊放,新技巧前衛而多元;而毛姆則謹守寫實筆法,以簡單的文句描摹人性之百態,故事娛樂性高,作品在商業上頗為成功。
現代主義巨擘勞倫斯(D. H. Lawrence)認為毛姆只是迎合都會讀者群的品味,談不上藝術;毛姆則以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等寫實主義者為寫作導師,認為詹姆斯(Henry James)、康拉德(Joseph Conrad)等人迂迴百轉的新文風,有害於誠摯切實的表達原則。然而,在現代主義眾星的巨大光芒掩蓋下,毛姆常被文學史貶為次流,像是一個生錯時代的寫實主義遺孤,只能在其讀者群中避免遭歷史遺忘。
即便如此,毛姆仍留下不少文學遺產,如間諜小說。毛姆與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有私交,一戰與二戰期間都做過政府特務,近距離觀察過俄國革命和納粹德軍占領巴黎等事件。以這些經驗為背景,毛姆創立了間諜小說這個新類型文學,影響了新一代的作家如格林(Graham Greene)、勒卡雷(John Le Carré)等。
除了小說,毛姆也寫戲劇、散文、評論,其戲劇尤其受歡迎,不過流傳於世的卻是小說。
觀毛姆其人,有其複雜面。他的言行舉止像個典型英國紳士,在文人圈中人脈極廣,有頭有臉的人物幾乎都認識。可是他也與很多人不合,有人甚至覺得他高傲、冷漠。
但這或許非性格使然,而是因為毛姆有口吃、具政府特務背景,還是未出櫃的同志。有鑑於同志前輩王爾德(Oscar Wilde)的下場,毛姆對此終身戒慎恐懼,生前不願讓私生活的任何方面見光,使他充滿神祕。毛姆在文化圈之活躍,猶如一位不沾俗塵的文人;而他與政府的關係,又使人感覺他像是大英帝國在文化圈的宣傳人。
不管真相如何,大英帝國在毛姆的時代實已逐漸衰敗,從毛姆故事常有的悲劇、反諷中,也能聞到一絲帝國沒落的氣息。
毛姆善用且好用反諷,故事人物的想法、期待、信念常與結果相反而行為反覆,故事也常以反轉或反高潮作結。其行文的語調從容、節奏穩定,讀其小說像在高遠處靜靜地俯視人世間的各種怪誕與謎團,觀察人生這匹善惡絲線交織的布。
《人性枷鎖》中,毛姆曾說「正常是這世界上最稀有的事」。評論界常認為大量反諷是展現其冷眼觀世、不信任人性,甚至厭世的性格。
一方面來說,這個說法勉強有些道理,因為反諷讓人不敢輕易相信世間的人事物,因此得以對所見所聞保持距離,不輕易入戲動情;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毛姆是繼承了自《唐吉軻德》(The Ingenious Gentleman Don Quixote of La Mancha)以來的小說傳統,著重描寫表象與真相、理想與現實的差距。
唐吉軻德的幻想在很多英國人眼裡是警世寓言,勸人不要過於執著投入,懷有高遠的理想。傳統上,英國文化對普世價值抱持懷疑,對理論、形而上、宏遠的大問題缺乏興趣。因此,毛姆沒有處理這些大問題的野心,只是從經驗中的種種細節觀察難以捉摸的人與事,以反諷方式,不願為其輕易下定論。
讀毛姆的小說,我們是否會懷疑故事中發人省思的人物與事件,不是那些經世濟民、使人夜不成眠的憂思,而只是文人墨客社交時閒談的話題?這就讓讀者們自行判斷吧。
──國立嘉義大學 外國語言學系暨研究所 專案助理教授 陳麒方
自序
這本書是這部短篇小說選集的第一卷(編註:本書僅收錄其中的前十篇)。我年少時曾寫過幾篇短篇小說,有一些被收錄在早已絕版的書中,另一些則分散刊載於各種雜誌裡,但是當時我的寫作還不夠成熟,因此並沒有將那些作品收錄於選集中。最好讓那些故事就這樣被遺忘吧。這部選集中的第一篇故事〈雨〉是我於一九二○年在香港時所寫,靈感來自一九一六年冬季的一場南太平洋旅行;選集中的最後一篇小說於一九四五年的紐約完成,源自當時我偶然在文件推中找到、寫於一九○一年的簡短筆記。往後我預計不會再寫其他短篇作品了。
當一位作者要將數量繁多的故事彙集成冊時,最困難的事情之一莫過於決定故事的先後順序。若這些故事的篇幅相似或地點(local)相同,作品的排列順序和編排格式就相對簡單了(我本來想用「場景〔locale〕」,不過牛津詞典說這個字雖然常用,但其實是誤用)。對作者來說,若能將故事編排得巧妙,讓書本在最終呈現給讀者時有一定的邏輯脈絡,那麼即便讀者沒有察覺,也是件令人心滿意足的事情。小說的結構簡單明瞭,有開頭、過程和結尾,而一篇架構良好的故事亦是如此。
然而,我所寫的故事篇幅不一,有些短至一千六百字,有些則長達一萬六千字,其中一篇甚至超過二萬字。我曾漂泊於世界各地,寫作時總會在各個棲身之地獲取一兩篇故事的素材。我寫過悲劇性的故事,也寫過幽默詼諧的故事。要將寫作篇幅、故事場景、題材性質如此相異且數量眾多的故事集結成冊,同時又要盡可能地讓讀者能輕鬆閱讀,著實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儘管讓故事被閱讀並非作者寫作的動機,但作品一旦完成,作者還是會抱有希望讀者看見的渴望,而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就必須盡量提升故事的易讀性。
基於這個目的,我盡可能地將一系列的短篇故事接在篇幅較長的故事之後;這些故事有的非常短,有的則有五、六千字之長,如此一來,讀者在閱讀時就無需突然從中國跳到祕魯,然後再跳回來。同時,我也盡量將發生地點(local)或場景(locale)在同一國家的故事排在一起,這樣編排就輕鬆多了。我希望透過這樣的安排,讓讀者在我的帶領下前往遙遠國度時,都能明確地找到自己的所在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