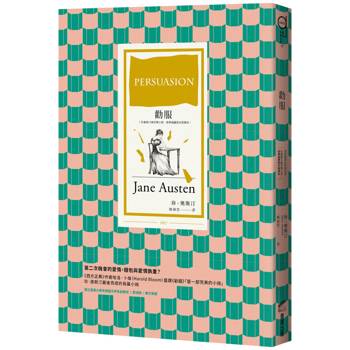第十二章
隔天早上安妮和亨莉埃塔最早起床,決定趁早餐前到海邊走走。她們走到沙灘,欣賞輕柔的東南風在這麼平坦的海岸所能掀起的最大波濤。她們讚嘆美好的晨光,稱頌壯闊的海洋,享受清新海風吹拂的歡快,而後靜默無語。最後亨莉埃塔突然說,「啊,沒錯,除了少數例外,海邊的空氣通常有益健康。雪利博士去年春天生病,海邊的空氣對他一定有好處。他自己也說,在萊姆鎮住一個月,比他吃的任何藥都有效。另外,住在海邊也讓他覺得自己變年輕。他沒有搬來海邊定居實在可惜。我真心覺得他最好搬到萊姆鎮定居,別繼續住在厄普克勞斯。安妮,你不這樣認為嗎?你不覺得這對他和他太太都是最好的選擇嗎?他太太有親戚住在這裡,還有很多朋友,她一定能過得更開心。我相信她也會希望住家附近就有醫療人員,以防他再次發病。雪利博士和他太太都是善良的人,一輩子都在做好事,想到他們要在厄普克勞斯這樣的地方度過晚年,我就覺得傷心。他們在那裡好像跟整個世界隔絕,除了我們一家,沒有可以往來的人。真希望他朋友能勸勸他,我真的這麼認為。還有申請退休的事,以他的年紀和聲譽,絕不會有困難。我只是擔心,可能沒有任何事能讓他離開自己的教區。他個性非常嚴謹,一絲不苟。我必須說他顧慮太多。安妮,你不覺得他那是顧慮太多嗎?神職人員為了工作犧牲健康,你不覺得那是對道義良心的誤解嗎?明明其他人也能把那份工作做好。何況只是搬到萊姆,離厄普克勞斯不到三十公里,如果教區的人有任何不滿,他也能聽得到。」
安妮聆聽這番話的過程中,內心幾度莞爾。但她也專注傾聽,就像面對另一位年輕男士時一樣,設身處地去理解對方的心情,也隨時準備好提供她的協助。只是這次難度比較低,畢竟除了一般性的附和,她還能做什麼?她針對這件事說了些合理又恰當的話:她也覺得雪利博士應該好好休養,應該聘個勤奮又正派的年輕人擔任駐堂助理牧師。甚至體貼地暗示,這位駐堂助理牧師最好已婚。
亨莉埃塔對同伴的表現十分滿意。「但願洛瑟夫人住在厄普克勞斯,而且跟雪利博士關係密切。我聽說她對任何人都很有影響力!我向來覺得她能說服別人做任何事!我有點怕她,這點我以前告訴過你。我相當怕她,因為她非常聰明。不過我特別尊敬她,也希望我們在厄普克勞斯有這樣的鄰居。」
安妮覺得,亨莉埃塔感恩雪利博士的方式很有意思。另外,由於事情的發展,也因為亨莉埃塔對未來的關切,馬斯葛洛福家竟然有人對洛瑟夫人產生好感,這也挺有趣。然而,她只來得及簡單回應,說她也希望厄普克勞斯有這樣一位女士,她們的談話就結束了,因為露易莎和費德里克已經朝她們走來。他們同樣是利用早餐前這段時間出來散步,不過露易莎馬上想起她還得去一家店鋪買點東西,邀請大家跟她一起回鎮上。他們都聽從她的安排。
他們走到從海灘往上的台階時,有位男士正好要走下台階,見到他們便彬彬有禮地後退,停下腳步讓他們先走。他們踏上台階,從他身旁經過。那人看見安妮的臉,眼神裡有真心的讚賞,安妮不可能察覺不到。她容光煥發,清新的海風讓她端正嬌美的五官恢復年輕時的紅潤與鮮麗,也讓她的眼眸更為靈動有神。那位男士顯然非常欣賞她,而他本人的舉止也十足紳士。費德里克立刻回頭看她,那表情顯示他注意到那男人的表現。他迅速瞄了她一眼,那明亮的眼神彷彿在說,「那男人為你驚豔,在這一刻,我好像也看見了曾經的安妮.艾略特。」
眾人陪露易莎買好東西,又閒逛一陣子,就回到旅館。之後安妮快步從她的房間趕往餐廳時,差點撞上那位男士,因為對方剛好從隔壁房間出來。先前她猜他跟他們一樣是外地人,另外,他們回來時在看見有個帥氣馬伕在兩家旅館之間走來走去,她猜那是他的僕人,因為主人和僕人都在服喪。原來他跟他們住同一家旅館。這第二次偶遇儘管短暫,那位男士的表情卻再次證實,他認為她美麗動人。另外,他迅速又得體地向她致歉,也顯示他非常謙恭有禮。他看起來大約三十歲,稱不上英俊,但還算好看。安妮覺得她會想知道他的身分。
他們快吃完早餐時,外面傳來馬車聲,吸引半數的人跑到窗子邊查看。這幾乎是他們來到萊姆鎮後第一次聽到馬車聲。「是紳士的馬車,雙駕,剛從馬廄來到旅館前門。一定有人要離開,駕車的僕人在服喪。」
查爾斯聽見「雙駕」立刻跳起來,他想跟自己的馬車做個比較。服喪的僕人引起安妮的好奇,於是六個人都走到窗口觀看。這時馬車的主人從旅館大門走出去,在旅館老闆一家人鞠躬哈腰歡送下,坐上馬車揚長而去。
費德里克用眼角餘光覷了安妮一眼,說道,「啊!那是我們剛才遇見的男人。」
兩位馬斯葛洛福小姐贊同他的話,所有人都親切地目送那人的馬車消失在山坡上,才回到早餐桌。不久後侍者走進餐廳。
費德里克馬上開口,「請問,你知道剛才離開那位男士姓什麼嗎?」
「知道,先生。他姓艾略特,是個有錢紳士,昨晚從錫德茅斯過來。先生,那會兒你們在吃晚餐,一定聽到馬車聲了。他下一站是克魯肯,之後要去巴斯和倫敦。」
「艾略特!」侍者答得夠快,但在他說完以前,已經有人交換了視線,有人重複了這個姓氏。
瑪麗嚷嚷說,「我的天!一定是我們堂哥,一定是我們的艾略特先生,絕對錯不了!查爾斯,安妮,你們說呢?他在服喪,我們的艾略特先生也是。實在太神奇了!跟我們住同一家旅館!安妮,那是我們的艾略特先生吧?是父親的繼承人吧?」她轉頭問侍者,「我請問你,你有沒有聽到……他的僕人有沒有提到他屬於凱林奇的艾略特家族?」
「沒有,女士。他沒有提到那個家族。不過他說他家主人是個非常有錢的紳士,以後會是從男爵。」
瑪麗欣喜若狂,「你們聽!我說得沒錯吧!是我父親的繼承人!我早就知道,如果真是他,我們一定會聽說。錯不了的,這種事僕人一定會走到哪宣傳到哪。可是安妮,這實在太神奇了!早知道當時把他看仔細點。真希望我們早點知道他的身分,這樣就可以跟他認識。錯過這個互相介紹的機會,真可惜!你覺得他有沒有遺傳到艾略特家族的長相?當時我在看他的馬,幾乎一眼都沒看他。不過我覺得他長得像艾略特家族的人。我竟然沒注意到馬車上的紋章!哎呀,他的大衣掛在車門面板上,把紋章擋住了。是這樣沒錯,不然我一定會看到。還有僕人的制服,僕人在服喪,不然從制服也能看得出來。」
費德里克說,「這麼多非常神奇的事湊在一起,你竟然沒能認識你的堂哥,我們不得不認為這是神的旨意。」
安妮好不容易吸引瑪麗的注意力,連忙悄悄提醒她,多年來她們父親和艾略特先生關係不算太好,對方未必樂意認識她們。
不過,見到堂哥後安妮暗自慶幸,因為凱林奇未來的主人顯然是個紳士,而且看起來相當明事理。只是,她無論如何都不會告訴瑪麗她後來又遇見他一次。幸好瑪麗不太關注他們早上散步時跟他偶遇的事,但如果她知道安妮在走廊差點撞上他,對方還謙恭有禮地致歉,而她自己完全錯過接近他的機會,一定會覺得太不公平。沒錯,遇見堂哥那件事必須守口如瓶。
瑪麗說,「對了,你下次寫信去巴斯,別忘了說我們遇見艾略特先生。這件事應該讓父親知道,一定要說仔細。」
安妮沒有直接回應。她覺得這種事不但沒必要提,甚至要瞞下來。她知道多年前對方嚴重冒犯過父親,也猜測那件事跟伊莉莎白有關。她甚至篤定,只要提起艾略特先生,父親和伊莉莎白都會很生氣。瑪麗自己從來不寫信去巴斯,跟伊莉莎白之間稀疏又敷衍的通信這種苦差事,向來由安妮承擔。
早餐過後不久,哈維爾夫婦和班威克就來了,大家約好來一趟萊姆鎮最後巡禮。他們預定一點鐘出發返回厄普克勞斯,在那之前大家都要聚在一起,盡量在戶外活動。
一行人走到街上後,安妮發現班威克來到她身邊。他並沒有因為前一天晚上的談話疏遠她。他們同行一段路,跟先前一樣討論司各特和拜倫。但如同先前,也如同天底下任何兩名讀者,他們還是無法對兩位詩人的優點達成共識。後來眾人的組合發生了變化,走在她身邊的不再是班威克,而是哈維爾上校。
他壓低聲音說,「安妮小姐你做了好事,讓那可憐的傢伙說了那麼多話。我希望他能更常遇見這樣的同伴。他在這裡跟外界隔離,對他很不好,可是我們能怎麼辦?我們不能分開。」
安妮說,「確實,我相信你們現在離不開彼此,也許日子一久會有所改變。我們都知道時間能治癒所有傷痛。哈維爾上校,你別忘了,班威克先生哀悼的時間不算久,據我所知是今年夏天的事。」
哈維爾上校深深嘆息,「唉,確實沒錯,六月的事。」
「而他得知消息的時間可能更晚。」
「那是在八月的第一週,他剛升任搏鬥號艦長,從好望角回來。那時我在普利茅斯,害怕聽到他的消息。後來他寫信告訴我搏鬥號奉命前往樸茨茅斯。必須有人去通知他,但是由誰去?我做不到,我寧可吊死在帆桁上。誰也沒辦法去做,除了那個好心人。」他指著費德里克。「當時拉科尼亞號剛抵達普利茅斯一星期,暫時不會再奉命出海。他冒了一點風險,寫信向上級請假,沒有等批准,直接日夜兼程趕到樸茨茅斯,到了以後立刻划船去到搏鬥號,留在那裡陪那可憐的傢伙一星期。他做了這麼多。除了他,誰也救不了可憐的班威克。安妮小姐,你說說,他是不是我們的好夥伴!」
安妮完全認同,也盡可能表達內心的想法,既要顧慮自己的心情,也要考慮對方的感受,因為重提這件事,哈維爾上校好像也深受影響。不過,等他再次開口,已經轉換截然不同的話題。
當時哈維爾太太說她丈夫最好現在往回走,以免累著了。於是這最後巡禮的路線就這麼敲定,大家決定一起走到他們家門口,再回旅館,之後出發回家。根據估算,回到旅館時間剛好。只是,他們走到防波堤附近時,又覺得不妨再去逛逛,大家都十分意動,露易莎更是非去不可。經過考量,晚一刻鐘出發差別不大。到了哈維爾家門口,雙方依依不捨地道別,交換許多邀請與承諾,他們就繼續往前走,去和防波堤道別。班威克好像決定陪他們到最後,繼續跟他們走。
安妮發現班威克又走到她身邊。看著眼前的景色,他們不可能不提起拜倫的「暗藍色大海」。她也願意專心跟他說話,只要她能保持注意力。然而,不久後她的注意力就被引到另一邊。
這天風勢不弱,不太適合女士們在新建的防波堤上步行,所以大家決定走下台階到底下那層。所有人都平靜又小心地沿著陡峭的台階往下走,但不包括露易莎。她非得往下跳,要費德里克在底下接住她。在散步的過程中,他總是要等在台階旁接住她,她喜歡冒險的感覺。防波堤地面太硬,他不太願意這麼做,卻還是讓步了。她安全落地,因為太開心,又跑上台階想再跳一次。他覺得台階太高,勸她別這麼做。可是沒用,不管他怎麼動之以情、曉之以理,都是白費唇舌。她笑著說,「我就要跳。」他張開雙臂,但她提早了半秒,摔在下層堤防上,被抱起來時已經不省人事!
沒有傷口,沒有流血,沒有明顯瘀青,但她雙目緊閉,沒有呼吸,看上去像個死人,站在旁邊的人無不驚恐萬分!
費德里克將她從地上抱起來後,直接跪在原地呆呆看著她,一張臉跟她一樣毫無血色,沉浸在無聲的痛苦中。瑪麗驚聲尖叫,「她死了!她死了!」她緊緊抓住丈夫,原本滿心驚駭的查爾斯因此動彈不得。緊接著亨莉埃塔也嚇暈了,幸虧班威克和安妮及時扶住她,否則她也會摔倒在台階上。
費德里克突然大聲問,「沒有人能幫幫我嗎?」那聲音裡滿滿的絕望,彷彿他全身的力量都流失了。
安妮大聲說,「去幫他,去幫他。我的天,去幫幫他。我自己扶她就行。去吧,你去幫他。按摩她的雙手,揉她的太陽穴。這裡有嗅鹽,拿去,趕緊拿去。」
班威克聽從她的安排,這時查爾斯也掙脫瑪麗的抓攫,兩人一起過去幫忙。三人合力把露易莎抬起來,穩穩托住。他們照安妮的話做,可惜沒有一點效果。費德里克踉蹌地靠在牆邊撐住身子,悲痛欲絕地吶喊,「天啊!快通知她父母!」
安妮喊道,「找醫生!」
他聽見她的話,好像立刻打起精神,「對,對,馬上找醫生。」說著快步往外衝。安妮急忙建議,「班威克先生,讓班威克先生去是不是比較合適?他知道哪裡能找到醫生。」
只要還有思考能力,都明白這個建議的好處。這一切都發生在電光石火之間,不一會兒班威克已經把死屍般的露易莎交給她哥哥照顧,用最快的速度往鎮上趕去。
至於留下來的人,目前還神智清醒的費德里克、安妮和查爾斯之中,很難說哪個比較痛苦。查爾斯是真心疼愛妹妹,這時俯身對著露易莎哀傷啜泣,偶爾把視線轉向同樣昏迷的亨莉埃塔,或愛莫能助地看著情緒失控、向他求助的妻子。
安妮拿出所有的力量和熱忱,體貼地協助亨莉埃塔,還抽空安慰其他人,努力讓瑪麗冷靜下來。她鼓舞查爾斯,安撫費德里克,他們兩個好像都期望她的指引。
查爾斯吶喊著,「安妮,安妮,接下來怎麼做?天吶,接下來該做點什麼?」
費德里克的視線也轉向她。
「把她送回旅館是不是比較好?對,沒錯,輕輕地把她送回旅館。」
費德里克附和,「對,去旅館。」他鎮定了些,急著想做點什麼。「我一個人抱她,查爾斯,你照顧其他人。」
到這時,防波堤附近的工人和船工都已經聽說這起意外,很多人聚攏過來,必要時可以幫點忙,至少可以欣賞一個昏迷不醒的女士。不,是兩個昏迷不醒的女士,這可比最初聽到的消息有趣一倍。亨莉埃塔雖然已經稍微清醒,還是軟弱無力,於是他們請幾個看起來最正派的人看著她。安妮陪在她身邊,查爾斯照顧瑪麗,一行人就這樣往回走,懷著難以言喻的心情,踏上片刻前才優遊自在走過的那條路。
隔天早上安妮和亨莉埃塔最早起床,決定趁早餐前到海邊走走。她們走到沙灘,欣賞輕柔的東南風在這麼平坦的海岸所能掀起的最大波濤。她們讚嘆美好的晨光,稱頌壯闊的海洋,享受清新海風吹拂的歡快,而後靜默無語。最後亨莉埃塔突然說,「啊,沒錯,除了少數例外,海邊的空氣通常有益健康。雪利博士去年春天生病,海邊的空氣對他一定有好處。他自己也說,在萊姆鎮住一個月,比他吃的任何藥都有效。另外,住在海邊也讓他覺得自己變年輕。他沒有搬來海邊定居實在可惜。我真心覺得他最好搬到萊姆鎮定居,別繼續住在厄普克勞斯。安妮,你不這樣認為嗎?你不覺得這對他和他太太都是最好的選擇嗎?他太太有親戚住在這裡,還有很多朋友,她一定能過得更開心。我相信她也會希望住家附近就有醫療人員,以防他再次發病。雪利博士和他太太都是善良的人,一輩子都在做好事,想到他們要在厄普克勞斯這樣的地方度過晚年,我就覺得傷心。他們在那裡好像跟整個世界隔絕,除了我們一家,沒有可以往來的人。真希望他朋友能勸勸他,我真的這麼認為。還有申請退休的事,以他的年紀和聲譽,絕不會有困難。我只是擔心,可能沒有任何事能讓他離開自己的教區。他個性非常嚴謹,一絲不苟。我必須說他顧慮太多。安妮,你不覺得他那是顧慮太多嗎?神職人員為了工作犧牲健康,你不覺得那是對道義良心的誤解嗎?明明其他人也能把那份工作做好。何況只是搬到萊姆,離厄普克勞斯不到三十公里,如果教區的人有任何不滿,他也能聽得到。」
安妮聆聽這番話的過程中,內心幾度莞爾。但她也專注傾聽,就像面對另一位年輕男士時一樣,設身處地去理解對方的心情,也隨時準備好提供她的協助。只是這次難度比較低,畢竟除了一般性的附和,她還能做什麼?她針對這件事說了些合理又恰當的話:她也覺得雪利博士應該好好休養,應該聘個勤奮又正派的年輕人擔任駐堂助理牧師。甚至體貼地暗示,這位駐堂助理牧師最好已婚。
亨莉埃塔對同伴的表現十分滿意。「但願洛瑟夫人住在厄普克勞斯,而且跟雪利博士關係密切。我聽說她對任何人都很有影響力!我向來覺得她能說服別人做任何事!我有點怕她,這點我以前告訴過你。我相當怕她,因為她非常聰明。不過我特別尊敬她,也希望我們在厄普克勞斯有這樣的鄰居。」
安妮覺得,亨莉埃塔感恩雪利博士的方式很有意思。另外,由於事情的發展,也因為亨莉埃塔對未來的關切,馬斯葛洛福家竟然有人對洛瑟夫人產生好感,這也挺有趣。然而,她只來得及簡單回應,說她也希望厄普克勞斯有這樣一位女士,她們的談話就結束了,因為露易莎和費德里克已經朝她們走來。他們同樣是利用早餐前這段時間出來散步,不過露易莎馬上想起她還得去一家店鋪買點東西,邀請大家跟她一起回鎮上。他們都聽從她的安排。
他們走到從海灘往上的台階時,有位男士正好要走下台階,見到他們便彬彬有禮地後退,停下腳步讓他們先走。他們踏上台階,從他身旁經過。那人看見安妮的臉,眼神裡有真心的讚賞,安妮不可能察覺不到。她容光煥發,清新的海風讓她端正嬌美的五官恢復年輕時的紅潤與鮮麗,也讓她的眼眸更為靈動有神。那位男士顯然非常欣賞她,而他本人的舉止也十足紳士。費德里克立刻回頭看她,那表情顯示他注意到那男人的表現。他迅速瞄了她一眼,那明亮的眼神彷彿在說,「那男人為你驚豔,在這一刻,我好像也看見了曾經的安妮.艾略特。」
眾人陪露易莎買好東西,又閒逛一陣子,就回到旅館。之後安妮快步從她的房間趕往餐廳時,差點撞上那位男士,因為對方剛好從隔壁房間出來。先前她猜他跟他們一樣是外地人,另外,他們回來時在看見有個帥氣馬伕在兩家旅館之間走來走去,她猜那是他的僕人,因為主人和僕人都在服喪。原來他跟他們住同一家旅館。這第二次偶遇儘管短暫,那位男士的表情卻再次證實,他認為她美麗動人。另外,他迅速又得體地向她致歉,也顯示他非常謙恭有禮。他看起來大約三十歲,稱不上英俊,但還算好看。安妮覺得她會想知道他的身分。
他們快吃完早餐時,外面傳來馬車聲,吸引半數的人跑到窗子邊查看。這幾乎是他們來到萊姆鎮後第一次聽到馬車聲。「是紳士的馬車,雙駕,剛從馬廄來到旅館前門。一定有人要離開,駕車的僕人在服喪。」
查爾斯聽見「雙駕」立刻跳起來,他想跟自己的馬車做個比較。服喪的僕人引起安妮的好奇,於是六個人都走到窗口觀看。這時馬車的主人從旅館大門走出去,在旅館老闆一家人鞠躬哈腰歡送下,坐上馬車揚長而去。
費德里克用眼角餘光覷了安妮一眼,說道,「啊!那是我們剛才遇見的男人。」
兩位馬斯葛洛福小姐贊同他的話,所有人都親切地目送那人的馬車消失在山坡上,才回到早餐桌。不久後侍者走進餐廳。
費德里克馬上開口,「請問,你知道剛才離開那位男士姓什麼嗎?」
「知道,先生。他姓艾略特,是個有錢紳士,昨晚從錫德茅斯過來。先生,那會兒你們在吃晚餐,一定聽到馬車聲了。他下一站是克魯肯,之後要去巴斯和倫敦。」
「艾略特!」侍者答得夠快,但在他說完以前,已經有人交換了視線,有人重複了這個姓氏。
瑪麗嚷嚷說,「我的天!一定是我們堂哥,一定是我們的艾略特先生,絕對錯不了!查爾斯,安妮,你們說呢?他在服喪,我們的艾略特先生也是。實在太神奇了!跟我們住同一家旅館!安妮,那是我們的艾略特先生吧?是父親的繼承人吧?」她轉頭問侍者,「我請問你,你有沒有聽到……他的僕人有沒有提到他屬於凱林奇的艾略特家族?」
「沒有,女士。他沒有提到那個家族。不過他說他家主人是個非常有錢的紳士,以後會是從男爵。」
瑪麗欣喜若狂,「你們聽!我說得沒錯吧!是我父親的繼承人!我早就知道,如果真是他,我們一定會聽說。錯不了的,這種事僕人一定會走到哪宣傳到哪。可是安妮,這實在太神奇了!早知道當時把他看仔細點。真希望我們早點知道他的身分,這樣就可以跟他認識。錯過這個互相介紹的機會,真可惜!你覺得他有沒有遺傳到艾略特家族的長相?當時我在看他的馬,幾乎一眼都沒看他。不過我覺得他長得像艾略特家族的人。我竟然沒注意到馬車上的紋章!哎呀,他的大衣掛在車門面板上,把紋章擋住了。是這樣沒錯,不然我一定會看到。還有僕人的制服,僕人在服喪,不然從制服也能看得出來。」
費德里克說,「這麼多非常神奇的事湊在一起,你竟然沒能認識你的堂哥,我們不得不認為這是神的旨意。」
安妮好不容易吸引瑪麗的注意力,連忙悄悄提醒她,多年來她們父親和艾略特先生關係不算太好,對方未必樂意認識她們。
不過,見到堂哥後安妮暗自慶幸,因為凱林奇未來的主人顯然是個紳士,而且看起來相當明事理。只是,她無論如何都不會告訴瑪麗她後來又遇見他一次。幸好瑪麗不太關注他們早上散步時跟他偶遇的事,但如果她知道安妮在走廊差點撞上他,對方還謙恭有禮地致歉,而她自己完全錯過接近他的機會,一定會覺得太不公平。沒錯,遇見堂哥那件事必須守口如瓶。
瑪麗說,「對了,你下次寫信去巴斯,別忘了說我們遇見艾略特先生。這件事應該讓父親知道,一定要說仔細。」
安妮沒有直接回應。她覺得這種事不但沒必要提,甚至要瞞下來。她知道多年前對方嚴重冒犯過父親,也猜測那件事跟伊莉莎白有關。她甚至篤定,只要提起艾略特先生,父親和伊莉莎白都會很生氣。瑪麗自己從來不寫信去巴斯,跟伊莉莎白之間稀疏又敷衍的通信這種苦差事,向來由安妮承擔。
早餐過後不久,哈維爾夫婦和班威克就來了,大家約好來一趟萊姆鎮最後巡禮。他們預定一點鐘出發返回厄普克勞斯,在那之前大家都要聚在一起,盡量在戶外活動。
一行人走到街上後,安妮發現班威克來到她身邊。他並沒有因為前一天晚上的談話疏遠她。他們同行一段路,跟先前一樣討論司各特和拜倫。但如同先前,也如同天底下任何兩名讀者,他們還是無法對兩位詩人的優點達成共識。後來眾人的組合發生了變化,走在她身邊的不再是班威克,而是哈維爾上校。
他壓低聲音說,「安妮小姐你做了好事,讓那可憐的傢伙說了那麼多話。我希望他能更常遇見這樣的同伴。他在這裡跟外界隔離,對他很不好,可是我們能怎麼辦?我們不能分開。」
安妮說,「確實,我相信你們現在離不開彼此,也許日子一久會有所改變。我們都知道時間能治癒所有傷痛。哈維爾上校,你別忘了,班威克先生哀悼的時間不算久,據我所知是今年夏天的事。」
哈維爾上校深深嘆息,「唉,確實沒錯,六月的事。」
「而他得知消息的時間可能更晚。」
「那是在八月的第一週,他剛升任搏鬥號艦長,從好望角回來。那時我在普利茅斯,害怕聽到他的消息。後來他寫信告訴我搏鬥號奉命前往樸茨茅斯。必須有人去通知他,但是由誰去?我做不到,我寧可吊死在帆桁上。誰也沒辦法去做,除了那個好心人。」他指著費德里克。「當時拉科尼亞號剛抵達普利茅斯一星期,暫時不會再奉命出海。他冒了一點風險,寫信向上級請假,沒有等批准,直接日夜兼程趕到樸茨茅斯,到了以後立刻划船去到搏鬥號,留在那裡陪那可憐的傢伙一星期。他做了這麼多。除了他,誰也救不了可憐的班威克。安妮小姐,你說說,他是不是我們的好夥伴!」
安妮完全認同,也盡可能表達內心的想法,既要顧慮自己的心情,也要考慮對方的感受,因為重提這件事,哈維爾上校好像也深受影響。不過,等他再次開口,已經轉換截然不同的話題。
當時哈維爾太太說她丈夫最好現在往回走,以免累著了。於是這最後巡禮的路線就這麼敲定,大家決定一起走到他們家門口,再回旅館,之後出發回家。根據估算,回到旅館時間剛好。只是,他們走到防波堤附近時,又覺得不妨再去逛逛,大家都十分意動,露易莎更是非去不可。經過考量,晚一刻鐘出發差別不大。到了哈維爾家門口,雙方依依不捨地道別,交換許多邀請與承諾,他們就繼續往前走,去和防波堤道別。班威克好像決定陪他們到最後,繼續跟他們走。
安妮發現班威克又走到她身邊。看著眼前的景色,他們不可能不提起拜倫的「暗藍色大海」。她也願意專心跟他說話,只要她能保持注意力。然而,不久後她的注意力就被引到另一邊。
這天風勢不弱,不太適合女士們在新建的防波堤上步行,所以大家決定走下台階到底下那層。所有人都平靜又小心地沿著陡峭的台階往下走,但不包括露易莎。她非得往下跳,要費德里克在底下接住她。在散步的過程中,他總是要等在台階旁接住她,她喜歡冒險的感覺。防波堤地面太硬,他不太願意這麼做,卻還是讓步了。她安全落地,因為太開心,又跑上台階想再跳一次。他覺得台階太高,勸她別這麼做。可是沒用,不管他怎麼動之以情、曉之以理,都是白費唇舌。她笑著說,「我就要跳。」他張開雙臂,但她提早了半秒,摔在下層堤防上,被抱起來時已經不省人事!
沒有傷口,沒有流血,沒有明顯瘀青,但她雙目緊閉,沒有呼吸,看上去像個死人,站在旁邊的人無不驚恐萬分!
費德里克將她從地上抱起來後,直接跪在原地呆呆看著她,一張臉跟她一樣毫無血色,沉浸在無聲的痛苦中。瑪麗驚聲尖叫,「她死了!她死了!」她緊緊抓住丈夫,原本滿心驚駭的查爾斯因此動彈不得。緊接著亨莉埃塔也嚇暈了,幸虧班威克和安妮及時扶住她,否則她也會摔倒在台階上。
費德里克突然大聲問,「沒有人能幫幫我嗎?」那聲音裡滿滿的絕望,彷彿他全身的力量都流失了。
安妮大聲說,「去幫他,去幫他。我的天,去幫幫他。我自己扶她就行。去吧,你去幫他。按摩她的雙手,揉她的太陽穴。這裡有嗅鹽,拿去,趕緊拿去。」
班威克聽從她的安排,這時查爾斯也掙脫瑪麗的抓攫,兩人一起過去幫忙。三人合力把露易莎抬起來,穩穩托住。他們照安妮的話做,可惜沒有一點效果。費德里克踉蹌地靠在牆邊撐住身子,悲痛欲絕地吶喊,「天啊!快通知她父母!」
安妮喊道,「找醫生!」
他聽見她的話,好像立刻打起精神,「對,對,馬上找醫生。」說著快步往外衝。安妮急忙建議,「班威克先生,讓班威克先生去是不是比較合適?他知道哪裡能找到醫生。」
只要還有思考能力,都明白這個建議的好處。這一切都發生在電光石火之間,不一會兒班威克已經把死屍般的露易莎交給她哥哥照顧,用最快的速度往鎮上趕去。
至於留下來的人,目前還神智清醒的費德里克、安妮和查爾斯之中,很難說哪個比較痛苦。查爾斯是真心疼愛妹妹,這時俯身對著露易莎哀傷啜泣,偶爾把視線轉向同樣昏迷的亨莉埃塔,或愛莫能助地看著情緒失控、向他求助的妻子。
安妮拿出所有的力量和熱忱,體貼地協助亨莉埃塔,還抽空安慰其他人,努力讓瑪麗冷靜下來。她鼓舞查爾斯,安撫費德里克,他們兩個好像都期望她的指引。
查爾斯吶喊著,「安妮,安妮,接下來怎麼做?天吶,接下來該做點什麼?」
費德里克的視線也轉向她。
「把她送回旅館是不是比較好?對,沒錯,輕輕地把她送回旅館。」
費德里克附和,「對,去旅館。」他鎮定了些,急著想做點什麼。「我一個人抱她,查爾斯,你照顧其他人。」
到這時,防波堤附近的工人和船工都已經聽說這起意外,很多人聚攏過來,必要時可以幫點忙,至少可以欣賞一個昏迷不醒的女士。不,是兩個昏迷不醒的女士,這可比最初聽到的消息有趣一倍。亨莉埃塔雖然已經稍微清醒,還是軟弱無力,於是他們請幾個看起來最正派的人看著她。安妮陪在她身邊,查爾斯照顧瑪麗,一行人就這樣往回走,懷著難以言喻的心情,踏上片刻前才優遊自在走過的那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