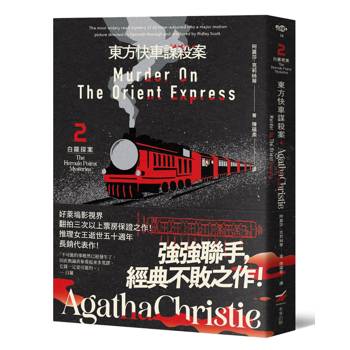Part1——事實
Chapter1 托魯斯快車上的重要乘客
敘利亞,冬日早上五點。阿勒坡車站的月台上停靠著一列火車,根據鐵路指南的精心介紹,這列火車是托魯斯快車,附廚房和餐車廂,另外還有一節臥鋪車廂和兩節區域列車車廂。
通往臥鋪車廂的登車梯旁,站著一位年輕的法國中尉,他身穿耀眼華麗的制服,正在和一個矮小的男人交談,那個男人把自己包得相當嚴實,一路遮到耳朵,除了粉紅色的尖鼻子和八字鬍上翹的鬍鬚尾之外,完全看不見他的樣子。
天氣極為寒冷,幫這位尊貴的陌生人送行,可算得上是一件苦差事,但杜伯斯克中尉仍盡責地完成任務。優美的法語從他嘴裡流淌而出,每一個字都經過精心雕琢。他不曉得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當然,是有各種傳言,總是這樣子。那位將軍——也就是他的上司——脾氣愈來愈差。接著,這位陌生的比利時人來了——他似乎是從英國遠道而來。那一整週充滿著詭異緊張的氣氛。然後,發生了一些事件。一位傑出的軍官自殺,另一位又突然辭職……不久,一張張焦慮的臉龐突然放鬆了下來,特定的軍事防範部署也解除了。杜伯斯克中尉所效忠的那位將軍看上去瞬間年輕了十歲。
杜伯斯克無意間聽到將軍跟這位陌生人之間的部分對話。「我親愛的,是你救了我們,」將軍激動地說道,他說話時,濃密的白鬍子顫動著。「你救了法國軍隊的榮譽……阻止了流血事件發生!你居然願意答應我的請求,我該如何報答你?你這樣遠道而來……」
那位陌生人(名叫赫丘勒・白羅先生)回答得十分客氣,他講的其中一句話是:「我記得很清楚,你不是也曾救過我一命嗎?」對此,將軍再次客氣地做出回應,否認自己在那次行動有任何功勞;接著他又提到法國、比利時、榮譽等之類的話題,兩人最後熱情地擁抱,結束了談話。
至於一切究竟是怎麼回事,杜伯斯克中尉還是搞不清楚,但此時他尚有任務在身,要送白羅先生搭乘托魯斯快車,他以前途無量的年輕軍官應有的熱情與幹勁執行這項任務。
「今天是星期天,」杜伯斯克中尉說道。「明天,也就是星期一晚上,您就在伊斯坦堡了吧。」
這不是他第一次做出這樣的推斷。在火車出發前的月台上可以交談的主題往往就是那幾種。
「的確如此,」白羅先生附和道。
「我想,您打算在那裡待上幾天,對吧?」
「是呀。我從沒去過伊斯坦堡。如果就這樣路過,未免太可惜了。」他彈了彈指比劃著。「若沒什麼要緊的事,我會在那邊當幾天觀光客。」
「聖索菲亞大教堂實在非常壯觀,」杜伯斯克中尉這樣說,但他其實沒看過那間教堂。
一陣寒風吹過月台。兩個男人都打著冷顫。杜伯斯克中尉快速瞥了一眼手表。再過五分鐘就五點了……只剩下五分鐘!
他怕對方發現他偷看手表,連忙繼續往下說道。
「每年的這個時候,遊客不太多,」他邊說邊抬頭看了看上方臥鋪車廂的窗戶。
「的確如此,」白羅先生附和道。
「希望您不會因為大雪被困在托魯斯快車裡!」
「有這種事啊?」
「是呀,發生過。但不是今年,今年還沒有。」
「那希望不會,」白羅先生說道。「歐洲那邊的氣象預報說天氣很糟。」
「非常糟。巴爾幹地區下了很多雪。」
「聽說德國也是。」
「那麼,」杜伯斯克中尉急忙接著說道,他怕雙方再次陷入沉默。「您明天晚上七點四十分就會抵達君士坦丁堡。」
「是的,」白羅先生說道,他也在拚命接話,「我聽說聖索菲亞大教堂非常宏偉。」
「我想一定非常壯觀。」
在他們的正上方,有人拉開了臥鋪包廂的窗簾,一名年輕女子向外張望。
瑪麗・德本漢姆自從上星期四離開巴格達之後,幾乎沒有好好睡過一覺。
無論是開往基爾庫克的火車、摩蘇爾的休息站,還是昨晚在火車上,她都沒有睡好。此刻,她已經厭倦在又熱又悶的包廂裡失眠,於是起身向外探看。這裡應該就是阿勒坡了。當然,外面沒什麼好看的。只有長長的月台,燈光昏暗,某處傳來阿拉伯語激烈憤怒的爭吵聲。她的窗戶下方有兩個男人正在用法語交談。一位是法國中尉,另一位是蓄著八字鬍的矮小男人。她露出淺淺的微笑。沒看過有人把自己全身裹得那麼緊,外面一定很冷,難怪車廂內的溫度調得那麼高。她使力想把車窗往下拉一點,但是拉不動。
臥鋪車廂的列車員走到那兩個男人面前。火車就要開了,他說。先生最好現在就上車。矮小男人摘下帽子。他的頭型多像一顆蛋啊!瑪麗・德本漢姆儘管心事重重,還是笑了。這個長相逗趣的小個子。這類型的矮小男人,實在讓人無法嚴肅看待。
杜伯斯克中尉正在說些離別的贈言。他已經事先想好,但直到最後一刻才講出來。他的贈言十分優美、措辭精煉。
白羅先生也不甘示弱,以同樣的方式回應對方。
「請上車,先生,」臥鋪車廂的列車員說道。白羅先生一副十分不情願的模樣,勉強上了火車。列車員跟在他後面。白羅先生揮了揮手。杜伯斯克中尉行了一個軍禮。火車猛烈一震,緩緩向前移動。
「終於啊!」赫丘勒・白羅先生喃喃自語。
「呼唔唔唔,」杜伯斯克中尉發出聲音,現在才注意到自己有多冷⋯⋯
「先生,您看看。」列車員用誇張的手勢向白羅展示美麗的包廂以及整齊擺放的行李。「先生的小手提箱,我就放在這裡了。」
他伸出來的手是一種暗示。赫丘勒・白羅在他手裡放了一張摺好的紙鈔。
「先生,謝謝您。」列車員的態度轉為果斷且公事公辦。「我已經拿到先生的車票了。請您把護照也給我。先生中途會在伊斯坦堡停留嗎?」
白羅先生點點頭表示沒錯。
「我想,現在旅客不多吧?」他說道。
「的確不多,先生。車上另外只有兩位乘客,都是英國人。一位是從印度來的上校,另一位是從巴格達來的年輕英國女士。先生有需要什麼嗎?」
白羅要了一瓶沛綠雅礦泉水。
清晨五點搭火車實在很早,還有兩個小時才天亮。白羅意識到自己昨晚沒睡好,而且已經順利處理好一項棘手的任務,於是便蜷縮在角落睡著了。
他醒來時已是早上九點半,於是前去餐車廂找熱咖啡喝。
此刻,那裡只有一個人,顯然是列車員提到的那位年輕英國女士。她身材高䠷,頭髮烏黑——看起來大約二十八歲。她吃早餐和召喚服務生續咖啡的方式都表現出一種從容俐落的感覺,顯示她見過世面且旅行經驗豐富。她穿著深色旅行便服,布料輕薄,在高溫悶熱的車廂內很適合這樣穿。
赫丘勒・白羅先生沒什麼事好做,便暗自觀察起這位女士,打發時間。
依照他的判斷,這樣的年輕女性,無論去哪裡都能從容處理好自己的事。個性沉穩且做事俐落。白羅相當喜歡她五官端正的面貌,細緻白皙的皮膚;也喜歡她充滿光澤、波浪整齊的烏黑秀髮,以及她那雙沉著、冷漠的灰色眼眸。但他評斷,她看起來太過精明幹練,因而稱不上所謂「迷人的女士」。
不一會兒,又有另一個人進入餐車廂。是一個高個子男人,年紀介於四十至五十歲之間,身材瘦削,棕色皮膚,兩鬢有些許灰白。
「印度來的上校,」白羅心想。
這位新到的乘客向那個女孩微微點了點頭。
「早安,德本漢姆小姐。」
「早安,阿布斯諾上校。」
上校站著,一隻手搭在她對面的椅子上。
「介意我坐這嗎?」他問。
「當然不介意。坐吧。」
「嗯,我知道,早餐時刻不一定適合閒聊。」
「我也是這樣想。但別擔心,我不會咬你。」
上校坐了下來。
「夥計,」他不客氣地喊道。
接著,他點了蛋和咖啡。
他的目光在赫丘勒・白羅的身上短暫停留了一下,接著又淡漠地移開了視線。白羅已經讀懂這個英國人的心態,知道對方心裡想的是:「不過就是個討厭的外國人。」
這兩個英國人都不太說話,十分符合他們的民族性。僅簡短地交談了幾句之後,女孩就起身回到自己的包廂。
午餐時段,那兩人再次同桌,且一樣對第三名乘客視若無睹。他們聊得比早餐時熱絡一點。阿布斯諾上校談起旁遮普,並時不時向女孩問起一些關於巴格達的問題,很顯然,她在巴格達當過家庭教師。他們在交談的過程中,發現彼此有一些共同朋友,這立刻讓他們熟了起來,談話也不再那麼拘謹。他們聊起某某湯米和那個什麼傑瑞。上校問她是否直接回英國,或者會在伊斯坦堡停留。
「不,我直接回英國。」
「這樣不是很可惜嗎?」
「我兩年前走過這條路,那時在伊斯坦堡待了三天。」
「喔!了解。我得說,很高興你要直接回英國,因為我也是。」
他笨拙地微微點了頭,臉上泛起一陣紅暈。
「這位上校很容易動情嘛,」赫丘勒・白羅心裡覺得頗有意思。「這趟火車之旅,危險程度堪比海上航行!」
德本漢姆小姐平靜地說那真是太好了。她的態度略顯壓抑。
赫丘勒・白羅注意到,上校陪她走回包廂。不久,那兩人經過窗外托魯斯山區壯麗的景色。當他們並肩站在走道上,眺望著奇里乞亞山口,那個女孩突然嘆了一口氣。白羅就站在他們旁邊,他聽見女孩低聲說:
「這真是太美了!我希望⋯⋯希望⋯⋯」
「希望什麼?」
「我多希望好好享受這片景致。」
阿布斯諾沒有回應。他那寬正的下巴線條變得有些緊繃。
「我希望上天能讓你擺脫這一切,」他說道。
「噓,拜託。別說了。」
「噢!沒關係。」他往白羅的方向看去,略顯不悅。然後,他接著說:「我不喜歡看你當什麼家庭教師,對那些專橫的母親和討厭的小鬼言聽計從。」
她笑了,聲音透露了一點真性情。
「啊,你可千萬別這樣想。家庭教師受壓迫這種迷思早就被推翻了。我可以向你保證,那些父母才怕被我欺負呢。」
他們沒再繼續交談。也許阿布斯諾正在為自己的衝動感到不好意思。
「我還真是看了一齣頗為怪異的小鬧劇」,白羅心想。
他之後還會再次回想起這時的想法。
那天晚上十一點半左右,他們抵達科尼亞。那兩名英國遊客下車活動筋骨,在積雪的月台上走來走去。
白羅先生光是透過玻璃窗欣賞車站熙熙攘攘的風景,就已經感到十分滿意。然而,過了約十分鐘,他覺得出去透透氣也不是什麼壞事。於是仔細做好準備,裹上幾件外套,圍上圍巾,並用防水鞋套套住乾淨的靴子。穿戴好之後,他就小心翼翼地走下車廂,沿著月台走到了火車頭的前方。
他循著交談的聲音走去,發現兩個模糊的身影,正站在一輛運輸車廂的陰影中。阿布斯諾正在說話。
「瑪麗……」
女孩打斷了他。
「現在不行。不是現在。等到一切結束。等到一切都過去了……然後……」
白羅先生低調地轉過身去。他很納悶。
他幾乎沒認出德本漢姆小姐那冷靜、從容的聲音⋯⋯
「真奇怪,」他心想。
隔天,他猜測他們也許起了口角。那兩人很少交談。他覺得那個女孩看起來非常焦慮,臉上有了黑眼圈。
差不多下午兩點半左右,火車停了下來。人們把頭探出窗外。一小群男子聚集在鐵軌旁邊,指著餐車廂底下的某個東西。
白羅探出頭,跟匆匆走過的列車員說話。列車員回應之後,白羅把頭縮回來,一轉身,差點和站在他後方的德本漢姆小姐撞在一起。
「發生什麼事?」她上氣不接下氣地用法語問。「我們為什麼停下來?」
「沒什麼,小姐。只是餐車廂下面有什麼東西著火了。不嚴重。火已經撲滅了。他們現在要修復損壞的地方。我向您保證,這裡沒有危險。」
她突然做了一個手勢,像是在驅散危險這個想法,好像這種想法完全不重要。
「對,我了解。可是時間呢!」
「時間?」
「是呀,這樣會耽誤我們的時間。」
「是呀……的確有這可能,」白羅附和道。
「可是這班火車不能誤點!它應該要在六點五十五分到站,然後我們還得橫渡博斯普魯斯海峽,去另一邊搭九點整出發的辛普朗東方快車。如果誤點一兩個小時,我們就會趕不上。」
「是呀,的確有可能,」他承認。
他好奇地看著她。她抓著窗欄的手有點不穩;嘴唇也在顫抖。
「這對您來說非常重要嗎,小姐?」他問。
「是的,非常重要。我……我一定要搭上那班火車。」
她轉身離去,沿著走道去找阿布斯諾上校。
不過,她白擔心了。十分鐘後,火車又開了。因為在中途追回了時間,火車抵達海達爾帕夏車站的時候才誤點了五分鐘。
博斯普魯斯海峽的風大浪高,白羅先生不太喜歡這段渡海的航程。他在船上和那兩位旅伴失散了,之後再也沒見到他們。
抵達加拉塔大橋後,他就直接搭車前往托卡特利安飯店。
Chapter1 托魯斯快車上的重要乘客
敘利亞,冬日早上五點。阿勒坡車站的月台上停靠著一列火車,根據鐵路指南的精心介紹,這列火車是托魯斯快車,附廚房和餐車廂,另外還有一節臥鋪車廂和兩節區域列車車廂。
通往臥鋪車廂的登車梯旁,站著一位年輕的法國中尉,他身穿耀眼華麗的制服,正在和一個矮小的男人交談,那個男人把自己包得相當嚴實,一路遮到耳朵,除了粉紅色的尖鼻子和八字鬍上翹的鬍鬚尾之外,完全看不見他的樣子。
天氣極為寒冷,幫這位尊貴的陌生人送行,可算得上是一件苦差事,但杜伯斯克中尉仍盡責地完成任務。優美的法語從他嘴裡流淌而出,每一個字都經過精心雕琢。他不曉得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當然,是有各種傳言,總是這樣子。那位將軍——也就是他的上司——脾氣愈來愈差。接著,這位陌生的比利時人來了——他似乎是從英國遠道而來。那一整週充滿著詭異緊張的氣氛。然後,發生了一些事件。一位傑出的軍官自殺,另一位又突然辭職……不久,一張張焦慮的臉龐突然放鬆了下來,特定的軍事防範部署也解除了。杜伯斯克中尉所效忠的那位將軍看上去瞬間年輕了十歲。
杜伯斯克無意間聽到將軍跟這位陌生人之間的部分對話。「我親愛的,是你救了我們,」將軍激動地說道,他說話時,濃密的白鬍子顫動著。「你救了法國軍隊的榮譽……阻止了流血事件發生!你居然願意答應我的請求,我該如何報答你?你這樣遠道而來……」
那位陌生人(名叫赫丘勒・白羅先生)回答得十分客氣,他講的其中一句話是:「我記得很清楚,你不是也曾救過我一命嗎?」對此,將軍再次客氣地做出回應,否認自己在那次行動有任何功勞;接著他又提到法國、比利時、榮譽等之類的話題,兩人最後熱情地擁抱,結束了談話。
至於一切究竟是怎麼回事,杜伯斯克中尉還是搞不清楚,但此時他尚有任務在身,要送白羅先生搭乘托魯斯快車,他以前途無量的年輕軍官應有的熱情與幹勁執行這項任務。
「今天是星期天,」杜伯斯克中尉說道。「明天,也就是星期一晚上,您就在伊斯坦堡了吧。」
這不是他第一次做出這樣的推斷。在火車出發前的月台上可以交談的主題往往就是那幾種。
「的確如此,」白羅先生附和道。
「我想,您打算在那裡待上幾天,對吧?」
「是呀。我從沒去過伊斯坦堡。如果就這樣路過,未免太可惜了。」他彈了彈指比劃著。「若沒什麼要緊的事,我會在那邊當幾天觀光客。」
「聖索菲亞大教堂實在非常壯觀,」杜伯斯克中尉這樣說,但他其實沒看過那間教堂。
一陣寒風吹過月台。兩個男人都打著冷顫。杜伯斯克中尉快速瞥了一眼手表。再過五分鐘就五點了……只剩下五分鐘!
他怕對方發現他偷看手表,連忙繼續往下說道。
「每年的這個時候,遊客不太多,」他邊說邊抬頭看了看上方臥鋪車廂的窗戶。
「的確如此,」白羅先生附和道。
「希望您不會因為大雪被困在托魯斯快車裡!」
「有這種事啊?」
「是呀,發生過。但不是今年,今年還沒有。」
「那希望不會,」白羅先生說道。「歐洲那邊的氣象預報說天氣很糟。」
「非常糟。巴爾幹地區下了很多雪。」
「聽說德國也是。」
「那麼,」杜伯斯克中尉急忙接著說道,他怕雙方再次陷入沉默。「您明天晚上七點四十分就會抵達君士坦丁堡。」
「是的,」白羅先生說道,他也在拚命接話,「我聽說聖索菲亞大教堂非常宏偉。」
「我想一定非常壯觀。」
在他們的正上方,有人拉開了臥鋪包廂的窗簾,一名年輕女子向外張望。
瑪麗・德本漢姆自從上星期四離開巴格達之後,幾乎沒有好好睡過一覺。
無論是開往基爾庫克的火車、摩蘇爾的休息站,還是昨晚在火車上,她都沒有睡好。此刻,她已經厭倦在又熱又悶的包廂裡失眠,於是起身向外探看。這裡應該就是阿勒坡了。當然,外面沒什麼好看的。只有長長的月台,燈光昏暗,某處傳來阿拉伯語激烈憤怒的爭吵聲。她的窗戶下方有兩個男人正在用法語交談。一位是法國中尉,另一位是蓄著八字鬍的矮小男人。她露出淺淺的微笑。沒看過有人把自己全身裹得那麼緊,外面一定很冷,難怪車廂內的溫度調得那麼高。她使力想把車窗往下拉一點,但是拉不動。
臥鋪車廂的列車員走到那兩個男人面前。火車就要開了,他說。先生最好現在就上車。矮小男人摘下帽子。他的頭型多像一顆蛋啊!瑪麗・德本漢姆儘管心事重重,還是笑了。這個長相逗趣的小個子。這類型的矮小男人,實在讓人無法嚴肅看待。
杜伯斯克中尉正在說些離別的贈言。他已經事先想好,但直到最後一刻才講出來。他的贈言十分優美、措辭精煉。
白羅先生也不甘示弱,以同樣的方式回應對方。
「請上車,先生,」臥鋪車廂的列車員說道。白羅先生一副十分不情願的模樣,勉強上了火車。列車員跟在他後面。白羅先生揮了揮手。杜伯斯克中尉行了一個軍禮。火車猛烈一震,緩緩向前移動。
「終於啊!」赫丘勒・白羅先生喃喃自語。
「呼唔唔唔,」杜伯斯克中尉發出聲音,現在才注意到自己有多冷⋯⋯
「先生,您看看。」列車員用誇張的手勢向白羅展示美麗的包廂以及整齊擺放的行李。「先生的小手提箱,我就放在這裡了。」
他伸出來的手是一種暗示。赫丘勒・白羅在他手裡放了一張摺好的紙鈔。
「先生,謝謝您。」列車員的態度轉為果斷且公事公辦。「我已經拿到先生的車票了。請您把護照也給我。先生中途會在伊斯坦堡停留嗎?」
白羅先生點點頭表示沒錯。
「我想,現在旅客不多吧?」他說道。
「的確不多,先生。車上另外只有兩位乘客,都是英國人。一位是從印度來的上校,另一位是從巴格達來的年輕英國女士。先生有需要什麼嗎?」
白羅要了一瓶沛綠雅礦泉水。
清晨五點搭火車實在很早,還有兩個小時才天亮。白羅意識到自己昨晚沒睡好,而且已經順利處理好一項棘手的任務,於是便蜷縮在角落睡著了。
他醒來時已是早上九點半,於是前去餐車廂找熱咖啡喝。
此刻,那裡只有一個人,顯然是列車員提到的那位年輕英國女士。她身材高䠷,頭髮烏黑——看起來大約二十八歲。她吃早餐和召喚服務生續咖啡的方式都表現出一種從容俐落的感覺,顯示她見過世面且旅行經驗豐富。她穿著深色旅行便服,布料輕薄,在高溫悶熱的車廂內很適合這樣穿。
赫丘勒・白羅先生沒什麼事好做,便暗自觀察起這位女士,打發時間。
依照他的判斷,這樣的年輕女性,無論去哪裡都能從容處理好自己的事。個性沉穩且做事俐落。白羅相當喜歡她五官端正的面貌,細緻白皙的皮膚;也喜歡她充滿光澤、波浪整齊的烏黑秀髮,以及她那雙沉著、冷漠的灰色眼眸。但他評斷,她看起來太過精明幹練,因而稱不上所謂「迷人的女士」。
不一會兒,又有另一個人進入餐車廂。是一個高個子男人,年紀介於四十至五十歲之間,身材瘦削,棕色皮膚,兩鬢有些許灰白。
「印度來的上校,」白羅心想。
這位新到的乘客向那個女孩微微點了點頭。
「早安,德本漢姆小姐。」
「早安,阿布斯諾上校。」
上校站著,一隻手搭在她對面的椅子上。
「介意我坐這嗎?」他問。
「當然不介意。坐吧。」
「嗯,我知道,早餐時刻不一定適合閒聊。」
「我也是這樣想。但別擔心,我不會咬你。」
上校坐了下來。
「夥計,」他不客氣地喊道。
接著,他點了蛋和咖啡。
他的目光在赫丘勒・白羅的身上短暫停留了一下,接著又淡漠地移開了視線。白羅已經讀懂這個英國人的心態,知道對方心裡想的是:「不過就是個討厭的外國人。」
這兩個英國人都不太說話,十分符合他們的民族性。僅簡短地交談了幾句之後,女孩就起身回到自己的包廂。
午餐時段,那兩人再次同桌,且一樣對第三名乘客視若無睹。他們聊得比早餐時熱絡一點。阿布斯諾上校談起旁遮普,並時不時向女孩問起一些關於巴格達的問題,很顯然,她在巴格達當過家庭教師。他們在交談的過程中,發現彼此有一些共同朋友,這立刻讓他們熟了起來,談話也不再那麼拘謹。他們聊起某某湯米和那個什麼傑瑞。上校問她是否直接回英國,或者會在伊斯坦堡停留。
「不,我直接回英國。」
「這樣不是很可惜嗎?」
「我兩年前走過這條路,那時在伊斯坦堡待了三天。」
「喔!了解。我得說,很高興你要直接回英國,因為我也是。」
他笨拙地微微點了頭,臉上泛起一陣紅暈。
「這位上校很容易動情嘛,」赫丘勒・白羅心裡覺得頗有意思。「這趟火車之旅,危險程度堪比海上航行!」
德本漢姆小姐平靜地說那真是太好了。她的態度略顯壓抑。
赫丘勒・白羅注意到,上校陪她走回包廂。不久,那兩人經過窗外托魯斯山區壯麗的景色。當他們並肩站在走道上,眺望著奇里乞亞山口,那個女孩突然嘆了一口氣。白羅就站在他們旁邊,他聽見女孩低聲說:
「這真是太美了!我希望⋯⋯希望⋯⋯」
「希望什麼?」
「我多希望好好享受這片景致。」
阿布斯諾沒有回應。他那寬正的下巴線條變得有些緊繃。
「我希望上天能讓你擺脫這一切,」他說道。
「噓,拜託。別說了。」
「噢!沒關係。」他往白羅的方向看去,略顯不悅。然後,他接著說:「我不喜歡看你當什麼家庭教師,對那些專橫的母親和討厭的小鬼言聽計從。」
她笑了,聲音透露了一點真性情。
「啊,你可千萬別這樣想。家庭教師受壓迫這種迷思早就被推翻了。我可以向你保證,那些父母才怕被我欺負呢。」
他們沒再繼續交談。也許阿布斯諾正在為自己的衝動感到不好意思。
「我還真是看了一齣頗為怪異的小鬧劇」,白羅心想。
他之後還會再次回想起這時的想法。
那天晚上十一點半左右,他們抵達科尼亞。那兩名英國遊客下車活動筋骨,在積雪的月台上走來走去。
白羅先生光是透過玻璃窗欣賞車站熙熙攘攘的風景,就已經感到十分滿意。然而,過了約十分鐘,他覺得出去透透氣也不是什麼壞事。於是仔細做好準備,裹上幾件外套,圍上圍巾,並用防水鞋套套住乾淨的靴子。穿戴好之後,他就小心翼翼地走下車廂,沿著月台走到了火車頭的前方。
他循著交談的聲音走去,發現兩個模糊的身影,正站在一輛運輸車廂的陰影中。阿布斯諾正在說話。
「瑪麗……」
女孩打斷了他。
「現在不行。不是現在。等到一切結束。等到一切都過去了……然後……」
白羅先生低調地轉過身去。他很納悶。
他幾乎沒認出德本漢姆小姐那冷靜、從容的聲音⋯⋯
「真奇怪,」他心想。
隔天,他猜測他們也許起了口角。那兩人很少交談。他覺得那個女孩看起來非常焦慮,臉上有了黑眼圈。
差不多下午兩點半左右,火車停了下來。人們把頭探出窗外。一小群男子聚集在鐵軌旁邊,指著餐車廂底下的某個東西。
白羅探出頭,跟匆匆走過的列車員說話。列車員回應之後,白羅把頭縮回來,一轉身,差點和站在他後方的德本漢姆小姐撞在一起。
「發生什麼事?」她上氣不接下氣地用法語問。「我們為什麼停下來?」
「沒什麼,小姐。只是餐車廂下面有什麼東西著火了。不嚴重。火已經撲滅了。他們現在要修復損壞的地方。我向您保證,這裡沒有危險。」
她突然做了一個手勢,像是在驅散危險這個想法,好像這種想法完全不重要。
「對,我了解。可是時間呢!」
「時間?」
「是呀,這樣會耽誤我們的時間。」
「是呀……的確有這可能,」白羅附和道。
「可是這班火車不能誤點!它應該要在六點五十五分到站,然後我們還得橫渡博斯普魯斯海峽,去另一邊搭九點整出發的辛普朗東方快車。如果誤點一兩個小時,我們就會趕不上。」
「是呀,的確有可能,」他承認。
他好奇地看著她。她抓著窗欄的手有點不穩;嘴唇也在顫抖。
「這對您來說非常重要嗎,小姐?」他問。
「是的,非常重要。我……我一定要搭上那班火車。」
她轉身離去,沿著走道去找阿布斯諾上校。
不過,她白擔心了。十分鐘後,火車又開了。因為在中途追回了時間,火車抵達海達爾帕夏車站的時候才誤點了五分鐘。
博斯普魯斯海峽的風大浪高,白羅先生不太喜歡這段渡海的航程。他在船上和那兩位旅伴失散了,之後再也沒見到他們。
抵達加拉塔大橋後,他就直接搭車前往托卡特利安飯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