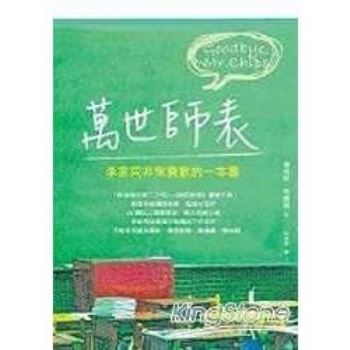【內文轉載】
03
威基特太太租給他的房間雖小,可是相當舒服,陽光充足。房子本身難看又太矯飾,但那無所謂;住處距離學校近、很方便,那才重要。
如果天氣夠溫暖,他喜歡下午漫步經過操場,觀看學生們打球。當他們觸帽向他致意,他會微笑著和他們閒聊幾句。
齊普斯有個很特別的本事,就是能夠認識所有的新學生,因為在他們剛入學的第一學期,他會分別邀請他們一道喝茶。
他總是向村子裡的瑞達威麵包店,訂一個有粉紅色糖霜的胡桃蛋糕,冬季的學期還多了些煎餅——一小堆放在壁爐前,並浸在奶油裡,所以最下面的一塊會像是躺在一個小淺池裡。
客人看著他小心地從不同的茶葉罐裡,各取出滿滿一匙茶葉來混合,覺得看他泡茶很有趣。他會問新同學們住在哪裡,家人是否和布魯克菲德有某種關係。他留心他們的盤子,不時為他們添放餅乾。
待五點鐘一到,茶會已經進行了一個鐘頭後,他會瞄向時鐘說:「喔,很高興能和你們這樣聊聊天,可惜我不能再留你們,你們該回學校了……」然後他會微笑著,站在門廊上和他們一一握手,讓他們賽跑著過馬路回學校。
學生們會在他背後評論:「齊普斯是個親切的老傢伙。他會給你喝很好喝的茶,也會讓你知道他要你告辭了……」
在威基特太太進來收拾桌上的殘局時,齊普斯也會對她發表評論:「威基特太太,真是—嗯哼—有趣啊。小布藍克珊告訴我—嗯哼—他舅舅是寇林伍德市長,就是來念過我們學校的寇林伍德—嗯哼—我以為他不會有什麼成就。啊,我清楚地記得寇林伍德。我曾經打他—嗯哼—因為他為了要撿回掉到體育館導水槽的球,而爬到體育館的屋頂上。他可能—嗯哼—摔斷脖子,那個小笨蛋。威基特太太,妳還記得他嗎?他應該是在妳還在學校時就學的。」
威基特太太在她存夠錢之前,在學校的洗衣房工作。
「是的,我記得他,先生。他常對我太放肆,不過我們也不曾惡言相向。他就是那樣的人,從來沒有惡意。那種大剌剌的人不會是壞人,先生。他不是有得到獎章嗎?」
「是的,優等服務獎章。」
「你還要些什麼嗎?先生。」
「現在不需要—嗯哼—等到教堂時間妳再送我的晚餐來。我想……他戰死了,死在埃及……」
「好的,先生。」
齊普斯在威基特太太家過的是愉悅寧靜的生活。他沒有煩惱,退休金夠他用,他自己也另外有點積蓄。他付得起他想買的任何東西。
他的房間擺設簡單,有老師的味道——幾個書架和幾個運動獎盃;一個壁爐台上堆擠著一些比賽或公演等的通知卡,還有男孩及男人們的簽名照片;一條陳舊的土耳其地毯;大搖椅;牆上是雅典的衛城(Acropolis)和古羅馬廣場的照片。幾乎每一件東西都是從學校的宿舍、他的舊舍監房間搬出來的。
他的書大部分是經典書籍,因為他教的是經典文學學科。不過,他上課時會添加一些歷史和純文學。下層書架上有一些廉價版的偵探小說。齊普斯喜歡看那些書。他有時候會拿古羅馬詩人威吉爾(Vergil),或希臘歷史學家齊諾風(Xenophon)的書起來看一會兒,可是他很快就會把它放回去,換成偵探小說《宋戴克醫生》(Doctor Thorndyke)或《法蘭奇探長》(Inspector French)。
雖然他多年來孜孜不倦地教授經典文學,但他其實並不是個經典文學造詣很深的學者。
事實上,他認為拉丁文或古希臘文並非給活著的人說的活語言,而比較像是死的語言,只有少數英國紳士會在掉書袋的時候引用幾句。他喜歡「泰晤士報」上那些出色的短文,它會介紹幾個他熟悉的引句。了解古文學的人口遞減,這對身為其中一員的他而言,是一種沒人可分享的祕密與可貴的惺惺相惜。他感覺,那代表著經典教育的主要好處之一被剝奪了。
他住在威基特太太家,安靜地享受閱讀、談話和回憶。他是個只有一點禿頭的白髮老人,以他的年紀來說還相當活躍,喝茶、接待訪客、忙著更正下一版的布魯克菲德通訊錄,還有偶爾用細長、但能夠清楚辨認的筆跡寫信。
他不只請新學生,也會請新老師來喝茶。秋季的學期有兩位新老師來喝茶,他們在拜訪過他、離開之後,其中一位說:「老先生很性格,是不是?講究混合茶葉那一套,典型的單身漢代表性人物。」
這麼說完全不正確,因為齊普斯根本就不是單身漢——他結過婚,雖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現在布魯克菲德的教職員沒有一個人記得他太太。
04
在溫暖的壁爐前,淡淡的茶香中,齊普斯回憶起往昔。
那是一八九六年春天的事了。他四十八歲,到了那個年紀一些習慣都固定了,幾乎一成不變。他剛被指派擔任舍監,教授古典語文兼做舍監,使得他人生的這個階段充實又忙碌。
暑假期間,他和一位同事羅登去湖區(Lake District)玩,他們去那裡健行、爬山一個禮拜,直到羅登家裡突然有事必須先走。齊普斯獨自一人留在韋斯戴爾(Wasdale),住在那裡的一間小農莊裡。
有一天,他去爬大蓋布爾山(Great Gable),注意到有個女孩從一塊看起來很危險的突出岩石上興奮地揮手。他以為她遇到什麼困難,匆忙接近間,自己卻滑倒了,還扭傷腳踝。而那個女孩其實根本沒有遭遇什麼困難,只是在和山下遠方的朋友打招呼。她是個爬山高手,比自認是好手的齊普斯還行。就這樣,他發現自己變成待救者,而不是救援者。這兩種認知對他而言都相當陌生。
他以前很少去注意女人,跟女人在一起總是覺得不自在或不安。一八九○年代新女性的言論開始風起雲湧,那種可怕的女人令他覺得恐懼。他是個內向傳統的男人,一向從布魯克菲德這個避風港來看世界,對他來說,一些革新看起來都很討厭。有個叫蕭伯納的奇怪傢伙居然倡導女性運動,他的主張非常不當,應該受譴責;另一個叫易卜生的也在他惱人的劇本裡宣揚女權主義。
還有新發明的瘋狂腳踏車,讓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樣平等地騎著跑。齊普斯對這些摩登的新玩意,以及女性自由的新觀念,都無法苟同。
他有個模糊的想法,如果由他規劃,好女人應該是軟弱、羞怯、嬌柔的,好男人則會殷勤體貼、彬彬有禮地對待她們。
因此,他沒有預期會在大蓋布爾山發現女人,更沒料到會遇見一個看起來似乎需要男性幫助的女人,竟反過來幫助他,這令他震驚得不得了。她真的幫了大忙,他幾乎不能走路,於是她和她朋友必須幫助他。想要把他弄下陡峭的山路回韋斯戴爾,是一件困難的工作。
她叫凱薩琳‧布里吉,二十五歲,年輕得可以做齊普斯的女兒。她有一雙閃亮的藍眸,長了雀斑的臉頰,和柔順的麥稈色秀髮。她跟一位女性朋友來度假,也住在一家農莊民宿。她認為自己應該負起齊普斯發生意外的責任,於是經常沿湖騎著腳踏車,到他住的那家農莊,去看那位躺在床上休養的中年男子,他看起來安靜又嚴肅。
一開始她對他的印象就是那樣。而他,因為她騎腳踏車,不怕單獨到農莊的客廳拜訪一個男人,隱隱覺得這個世界到底是怎麼了。他的腳扭傷,使得他只好任由她擺布,但他很快就明白自己有多麼需要她的好心照顧。
她拋頭露面在當家庭教師,存了一點錢;她崇拜易卜生,閱讀他的著作;她認為大學應該允許女人就讀;她甚至覺得女人應該有投票權。在政治上,她是個激進派,傾向擁護蕭伯納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觀點。在韋斯戴爾的那些個夏日午后,她把她的想法和意見全部傾倒給齊普斯,而由於他的口才不是很好,一開始他不認為那值得他們爭辯。
直到她的朋友走了,可是她留了下來。齊普斯想,你能拿這樣的女人怎麼辦?那時候他用手杖沿著鄉間小路跛行到小教堂,那裡的圍牆上有個石頭平板,坐起來很舒服,面對著陽光和綠褐色雄偉的蓋布爾山,聽著身旁女孩的喋喋不休。是的,齊普斯必須承認,她非常漂亮。
他從來沒見過像她這樣的人。他以前一直認為,這種所謂「現代新女性」類型的女人會令他反感。然而她在這裡,令他熱切地引頸企盼,看著她微晃地沿著湖邊的路,安全地騎著腳踏車過來。
而她也從來沒見過像他這樣的男人。她一直以為會看「泰晤士報」,而且不贊同新時代東西的中年男子,肯定無聊透頂。可是他在這裡,引起她的興趣和注意,比起那些和她同年齡的年輕人還多得多。
她喜歡他,起初是因為他很難了解,因為他溫文儒雅的態度,因為他陳腐的思想完全停留在一八七○和八○年代,甚至更早。儘管如此,他非常地誠實,還有——因為他的眼睛是棕色的,當他微笑的時候十分迷人。當她知道他在學校的綽號叫齊普斯時,她說:「我當然也要叫你齊普斯。」
不到一個禮拜,他們就陷入熱戀。在齊普斯能放開手杖走路之前,他們就自認他們訂婚了。秋季學期開學前的一個禮拜,他們在倫敦結婚。
06
接著是一段非常幸福的日子,令齊普斯多年來懷念不已,幾乎無法置信世界上會有那麼甜蜜的美好人生。不只他的婚姻是那麼凱旋似地成功,凱薩琳也征服了布魯克菲德,如同她征服齊普斯一般。她受到學生們的熱烈歡迎,教師們也是。儘管老師們的太太一開始嫉妒她那麼年輕可愛,但沒過多久,就傾倒在她的魅力之下。
最了不起的是,她完全改變了齊普斯。結婚前他是個乏味、相當平庸的老師,儘管在布魯克菲德的風評還不錯,卻也不是特別受歡迎、或有特殊表現的老師。那個時候他已經在布魯克菲德服務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了,久得足以讓他建立起勤奮優秀的名聲,可是長久以來沒人相信他有能力做什麼值得令人尊敬的事。
事實上,他已經開始墜入枯燥墮落的刻板教學法,那是這個職業做久了最容易犯的毛病,年復一年教授同樣的課程,會形成教學上的僵化與老套;他生命中其他的事情,也會在不知不覺中調整為——用最輕鬆省事的方法去做。他可以做好份內的工作,也頗為認真;他固定做某些事情,也能令人滿意信任;可是他做任何事情都沒有幹勁。
然後,任誰都沒料到,至少齊普斯自己怎麼都想不到,他娶來這位令人耳目一新的年輕太太。她使他整個人改觀,變成一個嶄新的人。雖然大部分所謂的新,其實是因為生命中有了溫暖,而將舊的、受到桎梏的、和未曾開發的潛能發揮出來。
他的眼睛綻出光芒,本來就充足的愛心此刻更加湧現,並逐漸勇於冒險。他一向具備的幽默感,突然像開花般地豐美繁盛起來,使他自信地展現成熟男人的魅力。他感到生活更踏實,連自己的學問好像都有了長足的進步,彷彿開竅一般地可以靈活教學,不再那麼僵硬死板了。他變成一個最受歡迎的人。
當他剛到布魯克菲德時,他期許自己成為一個受學生喜愛、尊敬、樂意服從的老師。教書幾年下來,學生會服從他、尊敬他,可是現在,他們愛他。學生們突然愛上這位慈祥但不軟弱的老師,他了解他們,不會管教過度;他個人的幸福好像也成了他們的幸福。他會輕鬆地開開小玩笑,那種學生喜歡的玩笑,像順口溜和雙關語,引發他們的笑聲,同時學生們也將他們該學的東西深印在腦海裡。
有個笑話一向能取悅學生,而它只是許多笑話中的一個樣本。每次他上古羅馬的歷史課,談到卡努勒亞法(Lex Canuleia),那是個允許貴族與平民通婚的法律,齊普斯常會補充說明:「所以,你瞧,如果平民小姐要貴族先生娶她,而他說不行,她可能回答:『喔,你行的,我知道你行,你這個騙子!』」結果引起哄堂大笑。
凱薩琳拓展了他的視野和見解,也讓他往外越過布魯克菲德的屋頂和塔樓望去,他因此能深入、寬容地去看他的國家;布魯克菲德只不過是許多條供水河中的一條。她比他還聰明,即使他不同意,他也無法駁倒她的看法。
舉例來說,儘管聽過她所有的激進社會主義理論的談話,在政治上他依然是個保守黨。雖然他無法接受那些想法,倒也能理解。她年輕的理想主義融進他中年的成熟練達,產生非常溫和與聰明的混合物。
有時候她能完全說服他。舉例來說,布魯克菲德每年舉辦一個濟助東倫敦貧民窟的活動,學生和家長們大方地捐錢,可是向來幾乎沒有人際之間的接觸。凱薩琳建議這個活動可以擴大為——接受贊助的東區孩子組成一個十一人足球隊,來跟布魯克菲德的球隊之一比賽。這個想法非常具革命性,如果不是凱薩琳、而是別人提出來的話,馬上會被嚴詞否決。要讓一隊貧民窟男孩闖入平靜愉快、家庭經濟較優裕的布魯克菲德學生的生活,猶如無端吹皺一池春水。
一開始,所有的老師都反對這個狂放的想法,校方如果有正式的官方意見的話,可能也是反對的。大家都相信東區的少年是小流氓,要不然也會令他們感到不安。反正大家都覺得可能會發生「意外」,每個人都會慌亂、苦惱,那又何必貿然惹是生非?然而凱薩琳十分堅持。
「齊普斯,」她說,「他們錯了,你知道我是對的。我是往前看未來,他們和你則是往後看過去。英國的百姓不會永遠存在如同軍官與士兵的等級之分。那些波普拉區(Poplar)的窮男孩對英國而言,和布魯克菲德的男孩一樣重要。齊普斯,你必須請他們來。只開一張支票或給他們幾個基尼(註:英國舊金幣),跟他們保持距離,你的良心怎能過意得去?再說,他們會跟你一樣,為布魯克菲德感到驕傲。許多年後,或許他們的兒子會到這裡來就讀,至少可能有少數幾個。這麼做有何不可呢?為什麼不能這麼做?齊普斯,親愛的,請你記住現在是一八九七年,不是一八六七年你剛進劍橋念書的時候。你的思想一直停留在那個年代,我相信其中有很多是很好的想法,可是一小部分,只有一小部分,齊普斯,應該跟著時代進步……」
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他讓步了,而且突然變得積極鼓吹這個提議。他這一百八十度大轉變是如此的堅決,因而使得校方沒提防地發現,他們同意了這個危險的實驗。
一個禮拜六的下午,波普拉區的男孩抵達布魯克菲德,和學校第二強的足球隊比賽,以七比五落敗,雖敗猶榮。稍後,客隊與地主隊在學校的餐廳裡一起喝傳統的下午茶,然後一起和校長見面,參觀學校。
傍晚時分,齊普斯送他們到火車站。這個事件過去了,沒有出一點點差錯,訪客們顯然帶著對布魯克菲德的良好印象離開,他們留下來的印象也一樣。
此外,他們也帶回對一個迷人女士的記憶,她親切和藹地招呼他們,跟他們聊天。許多年後,有一次,在戰爭期間,一個駐紮在靠近布魯克菲德附近大軍營的士兵來拜訪齊普斯,他說他是第一次到他們學校比賽的客隊成員之一。
齊普斯請他喝茶,和他閒聊,最後兩人握過手,那個男人預備離開。他說:「你太太好嗎?先生,我還記得她人很和善。」
「是嗎?」齊普斯急切地反問,「你記得她?」
「我記得很清楚。我想,任何見過她的人都會記得她。」
齊普斯黯然回答:「他們不記得了,至少這裡的人都不記得了。學生來來去去,總是有些新面孔,記憶不會持續太久。即使老師也不會永遠待在這裡。自從去年總務主任老葛立波退休後,這裡就沒有任何人見過我太太。她死了,就在你們來訪後不到一年……一八九八年。」
「我真的很遺憾,先生。雖然我們只見過尊夫人一面,但我的兩、三個隊友都和我一樣牢記著她。是的,我們都記得她,而且記得很清楚。」
「我很高興……那是我們的大日子,同時也是一場很精彩的比賽。」
「那是我人生中最快樂的日子之一。我好希望時間還停留在那時候,而不是現在。我們明天就要開拔去法國了。」
大約一個月後,齊普斯聽說他戰死在帕斯尚戴爾(Passchendaele)戰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