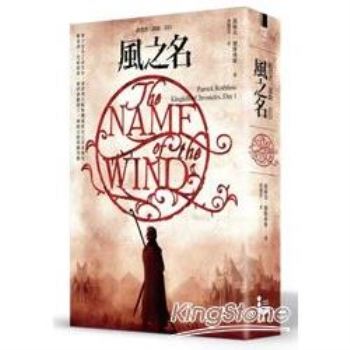寇特坐在吧台後方翻著書,「啊,我們的意外訪客,頭還好嗎?」
編史家舉起手摸摸後腦杓,「動太快時會有點抽痛,但還行。」
「那不錯。」寇特說。
「這是……」編史家遲疑了一下,環顧四周。「這裡是紐沃爾嗎?」
寇特點頭,「事實上,你就在紐沃爾的中心。」他大手一揮說,「蓬勃的府城,眾人的家園。」
編史家凝視著吧台後方的紅髮男子,他倚靠著桌子以便撐住身體。「老天!」他屏息問:「真的是你,沒錯吧?」
旅店老闆一臉疑惑:「抱歉,你說什麼?」
「我知道你會否認。」編史家說:「但根據我昨天看到的……」
旅店老闆舉起一隻手,請他靜一靜。「在我們討論你可能撞壞腦袋以前,先告訴我,到提努耶的路況如何?」
「什麼?」編史家問,他生氣地說:「我不是要去提努耶,我是……噢,即使不看昨晚的事,路況也滿糟的,我在修院長淺灘外被搶,之後就一直是靠雙腳步行。不過既然你在這裡,這一切都值得了。」編史家瞥見掛在吧台上的劍,深深吸了一口氣,表情變得有點不安。「請聽清楚,我不是來這裡惹麻煩的,我不是為了緝拿你的懸賞金而來的。」他勉強一笑,「我也不是你的對手……」
「很好。」旅店老闆打斷他的話,抽出一塊白色的亞麻布,開始擦拭吧台,「你又是誰?」
「你可以叫我編史家。」
「我不是問我可以叫你什麼。」寇特說:「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德凡,德凡.洛奇斯。」
寇特停止擦拭,抬起頭。「洛奇斯?你是不是與公爵有關……」寇特聲音漸弱,自顧自點頭。「沒錯,你一定是。你不是隨便哪個編史家,而是那個編史家。」他緊盯著那個禿頭男子,上下打量著他。「我這樣說對不對?大名鼎鼎的本尊。」
編史家稍微放鬆了一些,顯然對於自己稍具名氣很高興。「我之前不是故意不報名字,我已經好幾年沒把自己當成德凡,老早就把那名字忘了。」他意味深長地看著旅店老闆,「我想你也知道一些箇中原因……」
寇特不理那暗示。「幾年前我讀過你的書:《龍蜥的交配習慣》。對滿腦子充滿想像力的年輕人來說,那本書真是令人大開眼界。」他低頭,又用白布沿著吧台的紋理擦拭,「我承認,後來得知那種龍不存在時,我滿失望的,那對男孩來說是個沉痛的啟示。」
編史家微笑,「坦白說,我自己也有點失望,我去尋找傳奇,結果卻發現是隻蜥蜴,牠是很吸引人,但畢竟還是蜥蜴。」
「而如今你在這裡。」寇特說:「你是來證明我不存在嗎?」
編史家緊張地笑:「不,不是,我們聽到一個謠傳……」
「『我們?』」寇特打斷他的話。
「我一直和你的老友史卡皮周遊各地。」
「他收你為徒了?」寇特自言自語:「當史卡皮的徒弟,感覺如何?」
「其實比較像是同事。」
寇特點頭,依舊面無表情。「我原本猜他會是第一個找到我的人。造謠者,你倆都是。」
編史家的笑容變僵,忍住原本快講出來的那些話,努力恢復沉穩的態度。
「所以我能為你效勞嗎?」寇特把乾淨的亞麻布擱在一旁,露出他當旅店老闆的最佳笑容。「要不要吃點什麼或喝點東西?住個一晚?」
編史家遲疑了一下。
「我這裡什麼都有。」寇特揮手泛指吧台的後方。「老酒,順口白酒?蜂蜜酒?黑麥啤酒?還是來點水果甜酒!梅子酒?櫻桃酒?綠蘋果酒?黑莓酒?」寇特依次指著酒瓶。「別客氣,你一定想喝點什麼吧?」他一邊說,嘴巴笑得愈開,牙齒露出太多,愈看愈不像和善的旅店老闆。在此同時,他的眼神也愈變愈凶惡。
編史家目光下移,「我原本想……」
「你想!」寇特不以為然地嘲諷他,收起偽裝的笑容。「我很懷疑你真的想過,不然你早想到……」他停了一會,「你來這裡是陷我於多大的危險。」
編史家臉紅了,「我聽說克沃思天不怕地不怕。」他激動地說。
旅店老闆聳聳肩。「只有祭司和傻瓜才是天不怕地不怕,我向來跟老天的關係不是挺好。」
編史家皺眉,知道這其中有陷阱,他得繼續保持冷靜,「我格外小心,除了史卡皮外,沒人知道我要來。我也沒跟任何人提到你,沒想到真的會找到你。」
「這真是讓我十分安慰。」寇特諷刺地說。(待續)
編史家顯然很沮喪:「我得先承認,我來這裡可能是一個錯誤。」他停了一下,給寇特反駁的機會,但寇特不發一語。編史家小小嘆了一聲,繼續說:「但木已成舟,你難道不考慮……」
寇特搖頭說:「那是很早以前……」
「還不到兩年。」編史家提出異議。
「而且我也不是過去的我了。」寇特沒停下來,繼續說。
「過去的你究竟是什麼?」
「克沃思。」他簡單地說,不願再多做解釋。「現在我是寇特,經營旅店,那表示啤酒是三鐵幣,住宿一晚是一銅幣。」他又開始用力地擦拭吧台。「就像你說的,『木已成舟』,謠傳會自己發展下去。」
「但是……」
寇特抬起頭,編史家瞬間看穿他眼神表面的憤怒,看到背後的痛苦,血肉交織,彷彿傷口太深、難以癒合。接著寇特移開目光,但怒氣仍在:「你能用什麼補償我憶起往事的代價?」
「大家都以為你死了。」
「你還是不懂,對不對?」寇特搖頭,覺得又好氣又可笑。「那正是重點所在。你死了,大家就不會再找你了,宿敵不會想要一清宿怨,也不會有人來找你說個明白。」他尖酸地說。
編史家不肯就此罷休,「有些人說你是虛構人物。」
「我是虛構人物。」寇特從容地說,做出誇張的手勢。「我是很特別的虛構人物,還會自創故事。關於我的最佳謊言,都是我自己編的。」
「他們說你從來沒存在過。」編史家客氣地更正。
寇特無所謂地聳聳肩,他的笑容在不知不覺中逐漸消失。
編史家察覺到他的弱點,繼續說:「有些故事還說,你不過是個沾滿鮮血的殺手。」
「那也是我。」寇特轉身擦拭吧台後方的櫃臺。他再次聳肩,不過沒像之前那麼泰然自若了。「我殺過人,也殺過比人還可怕的東西,他們個個都是罪有應得。」
編史家緩緩搖頭,「傳聞說的是『刺客』,而非『英雄』。祕法克沃思和弒君者克沃思是兩個很不一樣的人。」
寇特停止擦拭吧台,轉身面對牆壁,他點了一下頭,沒有往上看。
「有些人甚至說有新的祁德林人,一種新的暗夜恐怖力量,髮色如血般鮮紅。」
「重要人物就會知道差異在哪了。」寇特這麼說,彷彿想要說服自己,但他的語氣聽來疲倦而絕望,毫無說服力。
編史家輕笑,「當然,目前是如此。但你們應該都知道,真相與幾可亂真的謊言之間、歷史與引人入勝的故事之間,差異有多麼細微。」編史家停了一會兒,讓寇特聽進他的話。「你知道在歲月荏苒下,哪個會勝出。」
寇特面對牆壁,雙手平放在櫃臺上,頭略低垂,彷彿扛了千斤重,不發一語。
編史家知道自己贏了,急切地往前一步,「有些人說有個女人……」
「他們知道什麼?」寇特的語氣就像骨鋸般銳利,「他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講得很小聲,小聲到編史家得屏息聆聽。
「他們說她……」屋裡變得異常寧靜,編史家的喉嚨突然發乾,講不出話來。寇特面牆站著,身軀僵硬,咬牙切齒沉默不語,拿著乾淨白布的右手緩緩握拳。
離他八吋遠的一個瓶子就這樣碎了,空氣中瀰漫著草莓的味道,還有玻璃的碎裂聲。強大的寂靜中參雜了小雜音,但這已足以把寂靜化為尖銳的細片。編史家發現自己全身發冷,他突然意識到自己正在玩的遊戲有多麼危險。他茫然地想到,所以這就是說故事和身處在故事裡的差別:恐懼。
寇特轉身,「他們能知道什麼關於她的事?」他輕聲問。編史家看到寇特的臉時,不由屏住了呼吸。旅店老闆平靜的表情,就像是碎掉的面具,藏在面具底下的臉彷彿備受折磨,眼神一半在這個世界裡,一半在其他地方,回憶著。
編史家想起他聽過的一個故事,眾多傳聞中的一個。那個故事提到克沃思如何去追尋他內心的渴望。他必須騙過一個惡魔才能找到。但是當他找到時,卻得打敗天使才能保有那份渴望。我相信那個故事,編史家心想。之前那只是一個故事,但現在我相信了,這就是殺了天使的人才有的臉龐。
「他們能知道什麼關於我的事?」寇特質問,語氣中帶著冷冷的怒氣。「他們能知道什麼關於這件事的任何資訊?」他做了一個簡短激動的動作,那動作似乎涵蓋了一切東西,破酒瓶,吧台,整個世界。
編史家為發乾的喉嚨嚥下口水,「那都只是他們聽說的。」
啪嗒,啪嗒,破瓶子裡的酒開始以不規則的韻律,啪嗒啪嗒地流到地面。「啊──」寇特發出長嘆。啪嗒,啪嗒。「你很聰明,用我最擅長的技巧來對付我,扣押我的故事,就像押制人質一樣。」
「我會說出真相。」
「除了真相,沒什麼制得了我。世上有什麼東西比真相更嚴苛?」他臉上閃過一絲苦笑。有好一會兒,只有酒滴落地板的細微聲響,打破整個屋子的寂靜。
最後寇特走進吧台後方的門,編史家尷尬地站在空房間裡,不知道他是不是該走了。(待續)
幾分鐘後,寇特拿著一桶肥皂水回來,看也不看編史家,開始有條不紊地小心清洗酒瓶。寇特洗掉瓶底的草莓酒,把酒瓶一一放在他和編史家之間的吧台上,彷彿那些酒瓶可以保護他一樣。
「所以你尋找一個虛構人物,卻找到了真人。」他語調平淡地說,頭也沒抬。「你聽過故事,現在你想要事情的真相。」
編史家大大鬆了一口氣,把背包放在桌上,對於自己的手微微顫抖感到訝異。「不久前我們聽到你的消息,就只是一些謠傳,我其實沒料到……」編史家暫停了一下,突然覺得尷尬,「我以為你比較老。」
「我是比較老。」寇特說,編史家一臉疑惑,但他還沒來得及說話,旅店老闆就繼續說:「什麼原因讓你來到這世上的偏僻角落?」
「我和貝登布萊特伯爵有約。」編史家說,稍微自我吹捧一下。「三天後,約在特雷亞。」
旅店老闆擦拭到一半停下來,「你預期四天內抵達伯爵的領地?」他悄悄地問。
「我進度落後了。」編史家坦承,「我的馬在修院長淺灘附近被劫。」他望向窗外陰暗的天空,「但我願意犧牲一些睡眠,我明早就走,不打擾你了。」
「我也不想耽誤你的睡眠。」寇特諷刺地說,他的眼神又變冷酷了,「我可以一口氣說完整件事。他清清喉嚨,「『我巡迴表演,周遊各地,談情說愛,迷失方向,信賴別人,反遭背叛。』把這句話寫下來,若是覺得對你沒用,就把它燒了。」
「你不需要這樣。」編史家馬上說,「如果你願意,我們可以用一整晚的時間,還有早上的幾個小時,說個清楚。」
「你還真有心。」寇特喝斥,「你要我在一個晚上說完我的故事?沒時間讓我平心靜氣下來?沒時間準備?」他抿著嘴,「你還是去見你的伯爵吧,我才不甩你。」
編史家連忙說:「如果你確定你需要……」
「對,我確定。」寇特猛力把一瓶酒放到吧台上,「我肯定我會需要比那還長的時間,你今晚也不會聽到,真正的故事需要時間準備。」
編史家緊張地皺眉,用手梳弄頭髮。「我可以利用明天聽你的故事……」他看到寇特搖頭,聲音漸弱。他停頓了一下,又開始說,彷彿是對自己說的一樣。「如果我在貝登買到馬,明天我整個白天都可以聽你說,還有大半個晚上和後天的一點時間。」他揉著額頭,「我討厭夜晚趕路,但……」
「我需要三天。」寇特說:「我很確定。」
編史家臉色發白:「但……伯爵。」
寇特輕蔑地揮手。
「沒人需要講三天。」編史家肯定的說,「我訪問過歐倫.威爾西特。注意喔,是歐倫.威爾西特。他八十歲,但人生有如活了兩百年般精采,如果再算進謊言,可能相當於五百年,他找上我。」編史家特別強調,「他才講兩天而已。」
「那是我的提議。」旅店老闆簡短的說,「我要做,就會把它做好,否則乾脆別做。」
「等等!」編史家突然喜形於色,「我剛剛一直倒著思考這件事。」他說,為自己的不知變通搖頭,「我其實可以先去拜訪伯爵再回來,到時你要多少時間都沒問題了。我甚至可以帶史卡皮一起來。」
寇特以極其不屑的表情看著編史家:「你憑什麼以為你回來時我還會在這裡?」他不敢置信地問,「而且,你怎麼會以為自己可以在獲知一切之後,還隨心所欲地踏出這間旅店?」
編史家整個人僵住了,「你……」他嚥了一下口水說:「你是說……」
「故事要講三天。」寇特打斷他的話:「從明天開始,那就是我要說的!」
編史家閉上眼,用手抓臉,伯爵一定會很生氣,不知道要怎麼做才能再次博得他的歡心,但是……「如果那是聽到故事的唯一方法,我願意接受。」
「很高興聽你這麼說。」旅店老闆稍微露出了一點笑容,「拜託,講三天真的那麼不尋常嗎?」
編史家恢復正經的表情,「三天真的很不尋常,但話說回來……」他做了一個手勢,彷彿要顯示那些話很多餘,「你是克沃思。」
那個自稱寇特的男子原本低頭擦拭著瓶子,他抬起頭來,臉上露出滿意的笑容,眼裡亮起光芒,他看起來更高大了。
「是的,我想我是。」克沃思說,語帶堅定。(待續)
陽光灑進道石旅店,清爽的光線,正適合一切初始。磨坊主人一早啟動水車之際,陽光穿過了磨坊;鐵匠做了四天的冷鐵加工,今日再次開爐,陽光也照亮了冶爐。那陽光照著拴在馬車上的馱馬,以及利光閃閃的鐮刀,在秋日一早,準備好展開新的一天。
在道石旅店裡,陽光落在編史家的臉上,觸及那兒的開端,一張空白的頁面正等著他寫下故事的初章。那陽光也穿過吧台,在有色玻璃瓶上映照出成千上百道七彩光芒,又照向牆上的那把劍,彷彿在搜尋決定性的起點。
但是陽光觸及那把劍時,卻看不到開端。事實上,劍只反射出老早以前打磨的隱約光澤。編史家看著那把劍,想起這雖然是一日之始,卻已入晚秋,氣溫日降。那劍散發著智識,意義深長:相較於季節之末與一年終了,拂曉不過是個小小初始罷了。
編史家聽到克沃思說話,但沒聽清楚,他把目光移開那把劍,問道:「抱歉,你剛說了什麼?」
「大家講故事時,一般是怎麼開頭的?」克沃思問。
編史家聳聳肩說:「大多是直接對我說他們記得什麼,之後我再按順序記錄事件,篩除不必要的枝節,釐清與簡化內容。」
克沃思皺眉:「我覺得那樣不可行。」
編史家尷尬地笑,「說故事的人各不相同,他們比較希望自己的故事保留原狀,也比較希望聽眾能聚精會神地聆聽,所以我通常是先聽,事後再做記錄,我幾乎可以一字不忘。」
「幾乎一字不忘還不適合我。」克沃思把一根手指壓在唇上,「你寫字能有多快?」
編史家會意地微笑,「比人說話還快。」
克沃思頗為驚訝:「我倒想見識見識。」
編史家打開背包,取出一疊精緻的白紙和一瓶墨水。他小心擺好這些東西後,用筆沾好墨,一臉期待地看著克沃思。
克沃思坐在椅子上,身子向前移,劈哩啪啦說了一串:「我是,我們是,她是,他是,他們會是。」編史家舞動墨筆,當著克沃思的面,迅速在紙上書寫,「我,編史家,以此聲明,我既不會閱讀,也不會書寫。仰臥,不敬,寒鴉,石英,漆器,艾哥里昂,林達盧索蘭喜亞:『有個來自費頓的年輕寡婦,堅守婦道,她入告解室,透露迷念……』」克沃思又把身子往前傾了一些,以便觀看編史家書寫,「有意思……噢,你可以停筆了。」
編史家再次微笑,用一塊布擦筆。他的紙上寫了一行難以理解的符號。「那是密碼之類的?」克沃思說出內心的疑惑,「你寫得很工整,想必不會浪費很多紙張。」他把那張紙轉向自己,更仔細觀察上面寫的東西。
「我從來不浪費紙。」編史家自豪地說。
克沃思點頭,沒有抬頭看。
「『艾哥里昂』是什麼意思?」編史家問。
「啥?喔,沒什麼意思,我掰的,只是想看不熟悉的字會不會減緩你的速度。」他舒展身子,把椅子拉近編史家。「你教我怎麼讀這些字以後,我們就可以開始了。」
編史家一臉疑惑,「這很複雜……」他看到克沃思皺眉,嘆口氣說:「好吧,我試試看。」
編史家深深吸了一口氣,開始寫一行符號,一邊說:「我們說話約用五十個音,我為每個音設計了一個符號,由一兩個筆劃組成,這些都是代表聲音,所以我也可以抄寫我完全不懂的語言。」他指出,「這些是不同的母音。」
「全都是垂直線。」克沃思凝視著紙說。
編史家停了一下,不太高興。「嗯……沒錯。」
「那子音就是水平線囉?然後母音和子音會像這樣結合起來。」克沃思拿起筆,在紙上寫下幾個自創的符號。「聰明,這樣一來,你一個字就不必寫兩三劃以上了。」
編史家靜靜看著克沃思。
克沃思沒注意到他,他一直注意著紙。「如果這是發『盎』音,那這些一定是發啊音。」他指著編史家寫下的一群字母。「啊、耶、唉,凹。那這些就是喔了。」克沃思自顧自點頭,把筆塞回編史家的手中。「讓我看看子音長什麼樣子。」
編史家漠然地寫下子音,一邊寫一邊唸出聲音。過了一會兒,克沃思拿起筆,自己寫完子音清單,請錯愕的編史家看到錯誤就幫他更正。
克沃思寫子音清單時,編史家看著他邊寫邊念,從頭到尾大約花十五分鐘,都沒有出錯。(待續)
「這系統超有效率!」克沃思讚嘆,「非常有邏輯,你自己設計的嗎?」
編史家停了很久都沒說話,他凝視著克沃思面前寫的幾行字,最後他不理會克沃思的問題,問道:「你真的一天就學會泰瑪語嗎?」
克沃思淺淺一笑,低頭看著桌子。「那是很久以前的故事,我差點忘了,其實是花了一天半的時間,一天半不眠不休。你怎麼會問這個?」
「我在大學院聽到的,原本一直不太相信。」他低頭看克沃思在他的密碼紙上寫的工整筆跡,「全部嗎?」
克沃思一臉狐疑:「什麼?」
「你學會整套語言了?」
「當然沒有。」克沃思不耐地說:「只有一部分,的確是大部分,但我覺得你不可能完全學會任何東西,語言就更不用說了。」
克沃思搓揉著雙手:「現在你準備好了嗎?」
書記官甩甩頭,彷彿在清理腦袋一樣,他擺好一張新的紙,點頭。
克沃思伸手先阻止書記官動筆,他說:「我以前從來沒講過這個故事,我猜以後也不會再說一次了。」克沃思把身體前傾,「在我們開始之前,你必須先記得,我是艾迪瑪盧族,我們是講卡路提納燒毀前的故事,在沒有書籍記載,也沒有音樂可演奏之前。第一把火點燃時,我們盧族正在閃爍的光圈裡編造故事。」
克沃思對編史家點頭說:「我知道你以收集故事與記錄事件聞名。」克沃思的眼神轉趨冷酷,如碎玻璃般銳利,「即便如此,也不要擅自更改我說的一字一句。如果我看似迷失,看似偏離,切記,真實的故事鮮少直線到底。」
編史家嚴肅地點頭,試著想像一小時就破解他自創密碼的頭腦,那頭腦可以一天學一種語言。
克沃思溫和地微笑,環視屋內,彷彿要記住一切。編史家用筆沾墨,克沃思低頭看著合掌的雙手,緩緩做了三次深呼吸。
接著他就開始說了。
「就某種意義來說,一切是從我聽到她唱歌開始的。她的聲音與我的成雙交揉,彷彿描繪著她的靈魂:如火焰般狂野,如碎玻璃般尖銳,如苜蓿般甜美潔淨。」
克沃思搖頭,「不,一切是從大學院開始的。我去那裡學故事中常提到的魔法,像至尊塔柏林的魔法,我想學風之名,我想掌控火與閃電,我想得知成千上萬種問題的答案,讀取他們的檔案。但我在大學院裡發現的,卻和故事裡描述的截然不同,讓我深感失望。」
「但我想,真正的開始在於促使我踏入大學院的原因;黃昏時突然出現的火,眼睛如井底之冰的男人,血與燃燒毛髮的味道,祁德林人。」他兀自點頭,「對,我想,那是一切的開端,從很多方面來說,這是一個關於祁德林人的故事。」
克沃思甩頭,彷彿想擺脫某種晦暗的想法,「但我想,我得回顧更早之前的事,如果這是類似個人傳記的東西,我可以騰出時間好好的說。如果大家因此記得我,即使不是讚譽,至少內容還有些精確。」
「但是,萬一我父親聽到我用這種方式講述故事,他會怎麼說呢?『從頭開始。』很好,既然要說,就好好的說。」
克沃思把身子往前傾。
「一開始,就我所知,世界是阿列夫從無名虛無中幻化出來的,他為萬物命名。又或者,有些版本的故事是說,他找到萬物早已擁有的名字。」
編史家小聲地噗哧一笑,但他沒有抬頭,也沒停止書寫。
克沃思自己也笑了,他繼續說:「我看到你笑了,很好,為了簡單起見,我們就假設我是創始的中心。這麼一來,我們就可以略過無數沉悶的故事:帝國興衰、英勇傳奇、悲慘情歌。我們就直接跳到唯一真正重要的故事。」他笑開了嘴,「我的故事。」(待續)
我名叫克沃思,聲音近似「闊特」。名字很重要,因為他們透露出許多攸關該人的訊息,我用過的名字比任何人都多。
阿頓人叫我梅卓,這字在不同語言中各有不同的意義,可以是「火焰」、「雷」或「殘木」。
如果你看過我,「火焰」之名顯而易見,我有一頭火紅的頭髮。如果是在兩百年前出生,我可能會被當成惡魔燒死。我蓄短髮,但頭髮總是散亂難理。放著不管,頭髮就會豎起,彷彿頭頂著火焰一般。
至於「雷」,我想是因為我有宏亮的中低音,兒時受過許多舞台訓練。
我從沒把「殘木」當回事,不過如今回想起來,我想那名稱至少有些預言的意味。
第一位導師叫我穎兒,因為我天資聰穎而且自知甚詳。初戀情人叫我杜拉托,因為她喜歡那名字的發音。有人叫我沙地卡、巧指、六弦。也有人叫我無血克沃思、祕法克沃思、弒君者克沃思。那些都是我付出代價所贏得的稱號。
但我的成長過程中,家人叫我克沃思。父親曾告訴我,那有「去理解」的意思。
當然,我還有過許多別的稱呼,這些名字大多粗鄙,但多數名符其實。
我曾從沉睡的古塚諸王身旁劫走公主;曾焚燬特雷邦城;和菲露芮安共處一晚,仍神智清楚、全身而退;我被大學院退學時,年紀比多數人入學時還小;我夜半走在連白天都沒人敢提起的路上;我曾和眾神交談;與女子相戀;寫過讓吟遊詩人流淚的歌曲。
你可能也聽過我的三兩事。
*************************
如果這是類似個人傳記的東西,我們就得從頭開始說起,從我的本質,看真正的我是什麼模樣。為此,你必須記得,我在成為任何人之前,我是艾迪瑪盧族。
一般認為,所有的巡迴表演者都是盧族,其實不然。我的劇團不是那種在聚會中心耍寶賺小錢,為了裹腹而載歌載舞的窮困劇團。相反的,我們是宮廷表演者,是灰綠大人的御用劇團。我們下鄉表演比較像是當地的大事,而不是和冬至慶典與索林納德慶典一起舉辦的活動。我們的劇團通常至少有八輛旅行車,遠超過二十幾人以上的表演者:有演員、體操表演者、樂師、魔術師、雜耍者、小丑。他們都是我的家人。
我從小就充滿好奇心,愛問問題,學習欲旺盛。在雜技表演者與演員的教導下,這也難怪我從小到大並不像多數孩子那樣畏懼學習。
當時的路況比較安全,但謹慎的旅人還是會為了安全起見,跟著我們劇團一起上路,他們為我提供了補充教育。有一位跟我們同行的訴訟士,他大概是醉得厲害或過於自大,沒發現他是在對一個八歲小孩說教,我從他身上學到聯邦法律的一些入門知識。還有一位獵人名叫拉克里斯,他和我們同行了近一季,我從他身上學到了山林野外的知識。
我從高官顯貴的娼妓口中,得知莫代格宮廷裡的齷齪勾當。就像父親說的:「實話實說,直言不諱,但是見到娼妓,都要以淑女稱呼,她們的日子已經夠苦了,客氣待人錯不了。」
赫特拉散發著淡淡的肉桂香,我九歲時,覺得她好迷人,但不太清楚為什麼。她教我不該私下做我不願公開談論的事,告誡我不要說夢話。
另外還有阿本希,我第一位真正的老師,他教我的東西比其他人教我的加起來還多。要不是他,就不會有今天的我。
我請你們不要對他有成見,他是好意的。
阿本希是我第一個碰到的祕術士。對小男孩來說,他是個既奇怪又有意思的人物。他博學多聞,植物學、天文學、解剖學、鍊金術、地質學、化學等各類科學,無所不通。
他體格壯碩,眼睛閃閃發亮,目光敏捷。他的後腦杓有一束深黑色的頭髮,卻沒有眉毛(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其實他有眉毛,卻因為一直練鍊金術而燒掉了,眉毛永遠處於再生狀態,所以看起來總是一臉又驚訝又滑稽的樣子。
他語氣溫和,常笑臉迎人,從來不會為了突顯自己的智慧而貶抑別人。他咒罵時就像瘸腿的酒醉水手一樣,但他只會咒罵他的驢子。那兩隻驢子分別叫阿法與貝塔。阿本希趁人不注意時,會餵牠們吃蘿蔔與糖塊。他特別喜愛化學,我父親說,他從來沒認識比阿本希更會用蒸餾器的人。
他加入我們劇團的第二天,我就習慣去搭他的貨車。我問他問題,他就回答我。接著他會點歌,我就用從父親車上借來的魯特琴彈給他聽。
他偶爾也會跟著哼唱,他有宏亮的男高音,卻總是唱著唱著就走音了。每次走音後,他常停下來取笑自己。他人品不錯,一點都不自大。
阿本希加入劇團不久,我就問他當祕術士是什麼感覺。
他若有所思地看著我,「你認識過祕術士嗎?」
「我們曾付錢請過一位,請他在路上幫我們修故障的車軸。」我停下來思考,「他載著一車魚往內地走。」
阿本希比了一個不以為然的手勢,「不對不對,孩子,我是指祕術士,不是在旅道上來來回回、幫肉品保鮮的冷凍術士。」
「那有什麼差別?」我問,察覺他似乎希望我提問。
「嗯,」他說:「那可能要解釋很久……」
「我多的是時間。」
阿本希打量著我,我一直在等那個神情,那神情好像在說:「你聽起來不像你外表那麼小。」我希望他很快就了解這點,被當成小孩看待的感覺很煩,即便你就是小孩。
他深深吸了一口氣,「某人懂一兩樣把戲,並不表示他就是祕術士,他們可能知道如何接骨或解讀古維塔語,甚至懂一點共感術,但……」
「共感術?」我盡可能客氣地打斷他的話。
「你可能會稱它為魔法。」阿本希勉強地說,「其實不是。」他聳聳肩,「即使你懂共感術,也稱不上是祕術士。真正的祕術士得經過大學院奧祕所的洗禮。」
他一提到奧祕所,我腦中又湧現二十幾個新的問題。你可能覺得問題還不算多,但是加上我腦中一直念念不忘的五十幾個問題,我整個腦子都快爆炸了。我得靠很大的意志力才能保持沉默,等候阿本希繼續說下去。
不過,阿本希也注意到我的反應,「所以你聽過奧祕所囉?」他似乎覺得很有意思,「告訴我,你聽到了什麼。」
我正需要這種小小鼓勵讓我借題發揮,「我聽一位怒火谷的男孩說,萬一你的手臂斷了,大學院可以把它縫回去,這是真的嗎?有些故事是說,至尊塔柏林到那裡學萬物之名。那裡有個藏書室,藏書千冊,真的有那麼多嗎?」
他回答了最後那個問題,其他問題講得太快,他來不及回應。「其實不止千冊,十萬冊,比那還多,多到你永遠都讀不完。」阿本希的語氣顯得有些傷感。
書多到我讀不完?不知怎的,我不太相信。
阿本希繼續說:「你看到和旅隊同行的人,那些幫食物保鮮的術士、探礦者、算命師、江湖郎中,都不是真的祕術士,就好像旅行表演者並不一定都是艾迪瑪盧族一樣。他們可能懂一點鍊金術、一點共感術、一點醫術。」他搖頭,「但他們不是祕術士。」
「很多人假裝他們是,穿起長袍,裝腔作勢,欺騙無知、容易上當的人。但是我教你怎麼判斷真的祕術士。」
阿本希從頭上抽出一片東西,交給我。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奧祕繫德,看起來很不起眼,只是個扁平的鉛片,上面印有陌生的字跡。
「那是真正的『繫斯』,你也可以稱它為繫德。」阿本希有點得意地解釋,「這是唯一確認某人是不是祕術士的方法,你父親請我先出示繫德,才答應讓我跟著劇團同行,那表示他閱歷豐富,見聞廣博。」他故意若無其事地看著我,「不舒服,對不對?」
我咬著牙點點頭,我一接觸到那東西,手就麻了。我好奇地端詳它正反面的記號,但沒隔幾秒,我整隻手已經麻到肩膀,好像我整晚壓在手上睡一樣。我心想,再拿久一點,會不會全身都麻了。
我沒機會知道,因為貨車剛好撞上路面凸起,我因為手麻,差點就讓阿本希的繫德滑落到貨車的踏板上。他快手接了起來,塞回頭上,咯咯地笑。
「你怎麼受得了?」我問,一邊揉著手,想讓手恢復一點知覺。
「只有其他人才會感到麻痺。」他解釋,「對它的主人來說,只會覺得暖暖的。這就是用來區分祕術士,以及有探找水源或預測氣候天賦者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