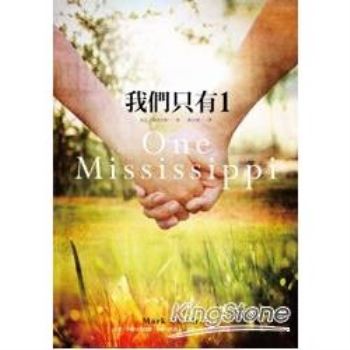「有感覺了嗎?」
「還沒。」
「那你最好再多吸一點。」
印地安納州的夏天。再過一個禮拜,我就要滿十六歲了。整個下午,我都和那夥哥兒們在一起,騎著腳踏車跟在噴灑殺蟲劑的卡車後面,猛吸DDT的霧氣。那種味道聞起來香香甜甜的,聽說吸多了會長高。
經過我家門口的時候,忽然瞥見老爸的車停在車道上。那是一輛藍色的Oldsmobile Delta 88型全家福大房車。禮拜四下午,家門口竟然會看到老爸的車,那種玩樂的好心情剎那間就無影無蹤了。於是,我跟那些哥兒們揮揮手,讓他們自己去玩了。
老爸是個好人──經過這麼多年的風風雨雨之後,我可以給他這麼一個整體評價──不過,如果你每天跟他生活在一起,你可能會覺得他的幽默感跟希特勒不相上下。我模模糊糊還記得,小時候,他也曾經像別人的爸爸一樣,把我們高高舉起來,抱在懷裡,逗我們玩,不過,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我已經快想不起來了。我只記得,當我們漸漸長大以後,他總是對我們板著一張臉。他說,要是不對我們嚴厲一點,我們長大以後恐怕會變成軟腳蝦。
他的名字叫做李.雷.莫斯葛羅夫,出身於阿拉巴馬州一個窮苦人家。一九三○年代的「大蕭條」時期,他家裡徹底破產了。後來,對於自己的窮苦出身,老爸始終耿耿於懷。「大蕭條」彷彿一朵暴風雨的烏雲,始終籠罩在我們家上空,彷彿某種註定的厄運正從遙遠的地平線外席捲而來。
每個星期一,老爸都是一大早四點就起床,一個人默默吃早餐片,邊吃邊看潛在客戶名單。又一個星期開始了,他又要繼續拜訪客戶,繼續搏鬥,以免全家被「大蕭條」的烏雲吞沒。從禮拜一到禮拜五,他到處奔波,馬不停蹄的拜訪客戶。他連續三年榮獲「鐵力士公司」年度模範地區業務經理,是全公司最拚命的業務員,態度也最和善。他永遠面帶微笑,說起話來禮貌周到。只不過,一整個禮拜下來,他心裡壓抑了太多的憤怒、挫折、失望和沮喪,一等到禮拜五晚上,他回到家,那些情緒就會全部發洩在我們身上。
可是,今天才禮拜四,他竟然回家了。這實在很異乎尋常。在我們這個家庭裡,異乎尋常的事鐵定不是好事。
我偷偷摸摸把腳踏車放進車庫裡,儘量不弄出聲音,但沒想到打開後門的時候,門忽然嘎吱一聲,壞了我的大事。這時候,我聽到客廳裡傳來他的怒吼聲:「你跑到哪裡去鬼混了?給我進來!」
每次爸用那種口氣講話的時候,你是不需要回答的。我囁囁嚅嚅的走進客廳,看到全家人都圍在電視機前面,只不過,電視並沒有開。恐怕真的大事不妙了。
我走到沙發前面,輕輕坐下來,坐在巴德和珍妮中間。他們個個臉色凝重。看他們那副模樣,我心裡想,會不會是有誰死了。
「嗯,全家人都到齊了。」老爸說。「那好,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宣布。我要調職了,我們又要搬家了。」
那一剎那,我立刻全身發麻,彷彿身體突然失去了知覺。調職。「鐵力士公司」每隔一兩年就會把業務員調到別的地區,以免他們鬆懈。這十年來,老爸已經調職了六次,而最後一次,我們來到了目前居住的印地安那州。在所有住過的地方當中,這裡是我最喜歡的,只可惜,鐵力士才不會管我喜不喜歡。不久之前,我心裡還暗暗希望,但願我們能夠在這裡安家落戶。我愛印地安那州。我在這裡交到很多好朋友,而且這裡地勢很平坦,可以隨心所欲的騎腳踏車到處跑,想去哪裡就去哪裡。而且,一到冬天,這裡就大雪紛飛,天寒地凍,你可以整天窩在家裡看電視。
好一會兒,大家都沒說話,客廳裡陷入一片沉寂。接著,我突然開口問:「我們要搬去哪裡?」
「密西西比州。」老爸說。「噢,對了,你最好閉嘴,我不想聽你發表意見。」
「喂,李,你怎麼這樣講話呢?」媽媽突然插嘴了。老爸站在那扇橫推式的玻璃門旁邊,我們坐在沙發上,而老媽則站在老爸和我們中間。「好了,你們幾個,對爸爸來說,這可是一件大事──事實上,不光是對爸爸,對我們全家人也一樣。你們都知道,我一直都很希望能夠住在外婆和傑克家附近……而且,你們也知道,我很受不了這裡的冬天。」
那倒是真的。老媽是南方姑娘一朵花,當年第一次搬家,老爸要帶她離開阿拉巴馬州的時候,她就已經嚇得六神無主了。(待續)「妳瘋了嗎?」巴德說。「媽,我們現在怎麼可以搬家呢?我最近好不容易才被大學代表隊相中。」巴德是摔角選手。他摔角簡直像在拚命,每次比賽結束,他都會吐得七葷八素。這一點,老爸倒是感到十分光榮。
「好了,巴德,別這樣。搬到那邊去,爸爸會比較好開發業務。」媽說。「更何況,我們已經別無選擇了,既然如此,我們何不坦然接受,高高興興的去面對呢?」
「要搬就搬,你們全都搬走沒關係。我自己留在這裡。」巴德說。「媽,秋天一開學,我就升高三了,我們怎麼可以搬去—妳剛剛說哪裡?密西西比嗎?這輩子我還沒碰過這麼荒唐的事!」
聽巴德這樣說話,我嚇了一大跳。要是我說出這種話,恐怕會被老爸甩一巴掌,然後關在房間裡不准出來。這時候,老爸臉色一沉,好像快要發作了,不過,他還是按捺住了,沒有出聲。巴德的模樣看起來很像老爸,所以,老爸總是對他另眼相看。
「好,巴德,你說你要留下來。」媽忽然露出一種陰森詭異的笑容。「那我問你,誰煮飯給你吃?衣服髒了誰幫你洗?」
「如果巴德要留下來,那我也要留下來。」珍妮說。
「誰都不准留下來。」媽媽說。「搬家沒什麼大不了的,我們不是已經搬過很多次了嗎?搬家公司的人禮拜一一大早就會過來裝貨了。」
這時候,巴德忽然站起來,劈哩啪啦的跺著腳跑向走廊,跑回房間去,然後砰的一聲把門用力一甩!
「老天。」爸大叫起來。「我的老天,看看妳兒子……」
「好了,李。」媽說。「你別給我找麻煩。」
「找麻煩?妳才別給我找麻煩。」
「親愛的,我不是告訴過你嗎?他們需要多一點時間適應的。想也知道,一開始他們當然會不高興—在這裡,他們已經有一群朋友了,而現在卻不得不和朋友分開。」說著,她轉頭看看珍妮和我,眼神有點不安。「我跟你們保證,你們一定會喜歡密西西比的。你們一定會交上新的朋友。老爸已經找到一棟鄉下的房子,很漂亮,而且,那裡的學校一定很棒。」
我不由自主的冷笑了一聲。「密西西比?嘿嘿,想也知道,一定棒得不得了。」我從來沒去過密西西比,不過,我在電視新聞裡已經看得夠多了。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密西西比都是全美國最爛的。那裡別的沒有,就是凶神惡煞的警長特別多,遊行抗爭的黑鬼特別多,死於非命的人權鬥士特別多。
「密西西比有什麼不好?」媽說。「那裡很漂亮,天氣很暖和,而且,最重要的一點是,我講話有人聽得懂。」
「要是我們不想去呢?」我問。「為什麼我們非去不可?」
「因為爸爸要調職了。就這樣。」她伸出一根指頭,把垂在眼睛前面那根金黃色的頭髮撥開。「而且,這次的業務轄區比較小,所以,他就不用整天在外面跑了。」說到這裡,她臉上露出笑容,可是爸卻開始皺起眉頭死盯著我,那副模樣彷彿認定我會說出什麼大逆不道的話,所以,他已經準備要撲上來掐死我了。
「密西西比州又稱木蘭之州。」珍妮翻開《世界百科全書》,邊看邊唸。「首府是傑克森市。物產是棉花、木材、家禽,和牛隻。」
「太棒了,珍妮。」老媽說。「我早說過,有了這些書,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
老媽拚命想讓我們以為,老爸這次調職是升官了,不過我心裡有數,根本不是這麼回事。我已經快十六歲了,什麼都瞞不了我的。我看過他們的信,翻過他們的檔案櫃。我看到他們買的保單,嚇了一大跳,因為,要是他們死了,我們這幾個孩子可就要發財了。有好幾天晚上,我聽到老爸在咒罵賴瑞.森普。他是區經理,老爸的頂頭上司。我心裡明白,目前印地安那州總部的業務轄區橫跨三個州,而調到密西西比之後,業務轄區只剩下一個州,說穿了,這根本就是降職。而我就是不知好歹,偏偏要在傷口上撒鹽。「為什麼爸爸的業務轄區變小了呢?」
這時候,空氣中彷彿起了一陣隱隱的顫動。那是從爸爸站的地方發出來的。(待續)珍妮這個人對表演時機的拿捏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彷彿有一具無形的攝影機隨時跟著她。這時候,她忽然開口了。「哇,終於要搬家了,我好開心哦。」她大聲說。「媽,我也好討厭這個地方耶。而且,我也好希望可以和外婆住近一點。」
「乖孩子。」老媽說。「凡事往好的方面想,人生才會美好。」
這時候,我用手掩住嘴巴,假裝咳了一下,嘴裡罵了一聲「馬屁精」。
「媽!他罵我馬屁精!」
「才沒呢。我是咳嗽。難不成連咳嗽都要妳批准嗎?」
於是,到了禮拜一,搬家公司來了,把我們家的東西裝上車。那是一節橘紅色的巨無霸拖掛貨廂,外殼有「聯合貨運公司」的字樣。
禮拜二,我們出發上路,沿著那條嶄新的州際公路向前奔馳,迎向未來。我們開了一整天的車,一直開到太陽都快下山了。抵達孟斐斯市南區的時候,車子壓到路面上的一塊凸起,我震了一下,臉頰撞到車窗玻璃。這時候,四線道的公路突然縮小成兩線道,路邊有一面標示牌,上面寫著:
歡迎蒞臨密西西比
這時候,眼前忽然豁然開朗,出現一片平野。乍看第一眼,那種感覺彷彿我們又回到了印地安那州:一望無際的平疇綠野一路連綿到地平線,遠處蔚藍的天際有一道道綿延不盡的圍欄,矗立著一座座的穀物升降機。不過,這裡的房子看起來可就有點不太一樣了。中西部到處都是整齊美觀的農舍,可是這裡的房子卻是那種貼著防水紙的小木屋,而坐在門廊上的都是黑人:小孩子個個骨瘦嶙峋,衣服破破爛爛,而老人則是彎腰駝背,頭上戴著草帽。不過,偶爾車子從高大的橡樹林旁邊經過時,我們會瞥見一兩棟莊園大宅在樹林後若隱若現—巨大的白色柱子看起來很像希臘神殿,感覺很隱密。
老媽說:「你能想像住在那種房子裡是什麼感覺嗎?要是我,我一定會覺得自己就像『亂世佳人』裡的郝思嘉。」
「媽,妳看,」珍妮說。「那個女孩子沒穿襯衫。」
「珍妮,不要盯著人家看。不是每個人日子都能過得像我們這麼好。」
「哎呀。」老爸搔搔脖子。「這年頭只要肯拚,日子都還過得去。想當年大蕭條的時候,那種日子才真叫苦咧。」
「她家的人怎麼會讓她這樣,沒穿襯衫光溜溜的在外面跑呢?」珍妮往後一仰,靠到椅背上。車窗外那個女孩越來越遠了。「她看起來好像和我差不多大。」
「呃,親愛的,我相信她平常穿的襯衫一定是很不錯的。」老媽說。「不過,大概是因為這裡天氣比較熱吧,所以今天沒穿。」
車子裡冷氣很強,吹得我們涼颼颼的,可是,你依然感覺得到車窗外的熱浪。你可以看得到,路面上,田野上,一波波的熱氣蒸騰而上。雖然車子以將近一百公里的時速向前飛馳,但你依然看得到外面的人臉上的汗水。
「噢,今天真是太美好了。」老媽說。「回到家鄉的感覺真是太棒了。我們把車窗打開吧,好好感覺一下。」說著,她把車窗搖下來,那一剎那,涼爽的空氣彷彿瞬間被吸乾了,車子裡忽然灌滿了夏日滾燙的熱氣──我忽然感覺一陣燠熱潮濕迎面撲來。我們全都哀聲慘叫起來,後來,老媽終於又把車窗搖了上來。
她咧開嘴笑得好開心。「熱!我就是喜歡這種熱天。」我們又回到南方了,這時候,老媽那種南方腔又開始蠢蠢欲動了──你一定聽過那種濃濃的、甜甜的阿拉巴馬南方腔。我就是喜歡這種熱天!
「這種天氣,我絕對不到外面去—絕不。」巴德說。「老天保佑,屋子裡的冷氣最好夠冷。」
「噢,我保證你們一定會成天在外面的。」老爸很堅定地告訴他。「屋子外面有一大片草坪,除草的工作,你們這幾個男生很有得忙的。」
「孩子們,這裡是鄉下地方。」老媽說。「這裡遠離了城市的喧囂,那種寧靜安詳是你們難以想像的,而且,房子後面有一大片庭院。我已經有點迫不及待了,好想趕快把整片庭院都種滿杜鵑花。印地安那州還在冰天雪地的時候,我們這裡的花已經開了滿庭院了。」(待續)「天曉得,那間爛學校不知道有沒有摔角隊。」巴德嘀咕著。
「就算他們沒有摔角隊,我相信學校裡一定有跟摔角一樣好玩的運動。」老媽說。「事實上,這裡就是美式足球的發源地。」
「我恨死了美式足球。」巴德說。
「千萬別讓這裡的人聽到這種話,那是很傷感情的。」老爸說。「巴德,我是說正經的,你嘴巴小心點。」
「媽,我肚子餓了。」珍妮說。
「呃,二十分鐘之前我們吃午飯的時候,妳不是說妳還不餓嗎?」老媽把那個Kroger便利商店的袋子拿起來晃了兩下。「親愛的,妳想吃哪一個?花生醬口味的好不好?噢,有了,這裡還剩一個火腿乳酪口味的。」
「我要花生醬的,不過,麵包皮拿掉,我不要吃。」
「麵包皮才是最好吃的地方。」老爸說。
老爸並不是因為想哄珍妮吃掉麵包皮才這樣說的。老爸真的就是這調調:對老爸來說,麵包皮不光是好吃而已,而是最好吃的。此外,他還喜歡在禮拜天啃雞脖子。他喜歡把吃剩的玉米餅和脆豬皮混在一起,再配上蕪菁甘藍,冷冷的吃,當早餐吃。他喜歡吃這種東西,因為這種東西會讓他回想起當年窮苦的滋味。
他瞇起眼睛,看著前面的車道上那長長的一排車陣—前面好像有什麼地方堵住了,整條車陣從前面那個彎道一路延伸過來。「老天,你們看看這個。」他嘆了一口氣,彷彿那些車停住不動,只是為了要跟他過不去。他兩隻手按在脖子後面,扭動肩膀關節,喀嚓作響。「幫幫忙,老兄。」他的手指頭輪流在方向盤上敲打著。「我們還有好幾英里的路要開呢。」
我們前面是一輛旅行車,肯塔基州的車牌,裡頭擠滿了小孩子,有的吐舌頭跟我們做鬼臉,有的把髒兮兮的腳踩在窗玻璃上。你彷彿聞得到孩子們那種不耐煩的氣息從那輛車子裡飄出來。想像得到,坐在前座那兩個爸媽一定是拚命裝聾作啞,裝作沒聽到。
「謝天謝地,還好我們只生了三個。」老爸說。
老媽微微一笑。「老天保佑。」
「嘿,你們兩位。」巴德叫了一聲。「這是什麼話。」
「你們幾個小鬼,看到前面那輛車沒有?」老爸說。「為什麼要節育,前面那輛車就是活生生的理由。」
「李。」
珍妮問:「什麼叫節育?」
「都是你,哪壺不開提哪壺。」
「所謂節育,就是要掂掂自己有幾兩重,不要不自量力。」說著,老爸伸手去按喇叭。整條路上喇叭聲此起彼落,好像在大合唱。
放眼望去,我看到前面的田野上有一排松樹,樹後面升起一股濃濃的黑煙。「嘿,爸,那邊好像在燒東西。」
這時候,爸爸看向我手指的方向。「嗯,你好像沒看走眼,那裡有一棟鬼房子燒起來了。難怪路上車子都不動了,大家都在看熱鬧。」說著,他又拚命按喇叭。「趕快開車吧!沒看過火燒房子嗎?」這時候,前面那輛擠滿了小孩的車也在按喇叭,開車的人把手伸出窗外,猛揮拳頭。
那東西很大,而且正在起火燃燒,濃濃的黑煙衝上雲霄,彷彿一團烏雲,而且濃煙裡不時竄出火舌。這時候,前面有些車子忽然開始進一下退一下,設法在車陣裡掉頭,然後從我們旁邊往反方向開過去。
老媽說:「大家都想繞路了。」
老爸往前慢慢開了一個車身長的距離。「繞路得繞一大圈,搞不好得花上兩倍時間。」說著,他開始去調收音機的頻率,沒多久,收音機接收到一個播放農業新聞的頻道。播報員的聲音聽起來平平板板的。
「大豆又漲啦,棉花的行情還是老樣子。」那個人說。「今天要灑農藥,各位鄉親別忘了哦。以上的報導是由熱心公益的『鐵力士化學』所提供。害蟲在哪裡,我們都知道。」
這時候,老爸忽然叫了一聲:「嘿嘿!」然後他把音量調大。「你們聽到他說什麼嗎?才剛到密西西比,沒想到收音機裡就已經聽得到我們公司的新聞了。」
「這是個好兆頭。」老媽說。「就像他們用這種方式在歡迎你。告訴你,李,未來一定是一片大好。」(待續)這時候,前面又有更多人投降了。又有好幾部車掉頭開走了。
我們的車慢慢繞過那個彎道之後,赫然發現原來那不是房子失火,而是路上有東西著火了。正前方是上坡道,擋住了我們的視線,看不到是什麼東西。州警的巡邏車閃著藍燈。戴著寬邊牛仔帽的警察比著手勢,指揮車子開下高速公路。
「看起來像是大車禍。」老爸說。「看那種火勢,鐵定是油罐車燒起來了。」
「太酷了。」巴德說。
「酷?巴德,你怎麼這樣說話呢?」老媽說。「說不定有人受傷了。」
「我不是那個意思。我是說,那麼大的火,看起來很酷。」巴德說。
「爸,車子不要開太近好不好?我不想看到有人被火燒的樣子。」
「不用怕,珍妮。我也不想看。」
後來,車子慢慢靠近,我們終於看到了。原來是一輛拖掛式的貨車翻倒了,橫躺在路面上,車頭和後面的車廂彎成了V字形。一群消防隊員和州警站得遠遠的看火燒—看起來很像一輛巨大的橘色玩具車,支離破碎,火舌從車頭裡竄出來,從貨廂敞開的門口竄出來。
兩個穿著灰色制服的人遠遠站在旁邊,其中一個彎著腰,手撐在膝蓋上,看起來好像快要吐了。
好一會兒,我才猛然想到,嘿,我認得那傢伙,而且,我也想到自己在哪裡看過他了。那一剎那,我腦海中忽然浮現出一幕畫面:就在昨天,在印地安那州,在我們家門口,那傢伙站在「聯合貨運公司」的車廂後面,把門關起來。
「嘿,爸。」我說。「你看那個人。昨天幫我們把東西裝上貨車的,不就是他嗎?」
「你說什麼?」
「那個人。在那邊!他不就是『聯合貨運公司』的人嗎?」
為什麼幫我們搬家的司機會和那些州警站在一起?為什麼他們會站在那輛燒得一塌糊塗的貨車旁邊?接著,我猛然想通了。因為燒毀的就是他的貨車,也就是,我們的貨車。
這時候,老爸猛轉方向盤,把車子開到路肩的草坪上,關掉引擎,把車窗搖下來,兩手搭在方向盤上。車窗一開,熾熱的空氣立刻灌進車子裡。我們聽到陣陣劈哩啪啦的爆裂聲。那是噴霧罐爆炸的聲音,一種低沉的、悶悶的巨響,彷彿一頭龐然巨獸在吸氣。
珍妮說:「幹嘛要停車?」
「妳這個白痴!」我大叫了一聲。「還搞不清楚嗎?那是我們的東西!」
「我們的東西?什麼意思?」
「你們兩個。」老媽忽然開口了。她的聲音聽起來異乎尋常的冷。後來,每當我回想起她當時說話的腔調,還是會不由自主的打個哆嗦。「不要再讓我聽到你們兩個講話。」
這時候,有個O型腿的警察從坡道上面走下來,朝我們的方向走過來。「老兄,」他說,「你們不可以在這裡逗留,趕快走吧。」
老爸的脖子忽然變得好紅好紅,彷彿瞬間被太陽曬傷了。我雖然看不到他的臉,不過,我相信,要是那個警察看到他的表情,一定會嚇得倒退好幾步。
「好了,可以了。」他說。「熱鬧也看夠了吧。趕快把車子開走吧。」
老爸悶不吭聲,眼睛死盯著那個警察。
「這位先生,你沒聽到我講話嗎?」
這時候,老媽忽然伸長了身體,湊近駕駛座的車窗。「警官,那輛貨車是不是『聯合貨運公司』的貨廂?」
「是的,女士,沒有錯。可是,妳為什麼問這個?」
「呃,我叫珮姬,這位是我先生,李.莫斯葛羅夫。事情是這樣的,那節貨廂裡的東西是我們的。」
「嗯。」那位警察臉上的表情看不出有什麼反應。「你們是要搬家到這裡來嗎?」
「是的,警官,沒錯。」老媽說。也許那個警察會覺得老媽說話的口氣聽起來很有活力,不過我心裡有數,那種口氣和哀聲慘叫只有一線之隔了。
「呃,我實在很不想當烏鴉,不過,女士,貨廂裡的東西已經差不多燒光,剩沒什麼了。」說著,他朝那堆火焰揮揮手,那副模樣彷彿我們全家都是瞎子。
「能不能麻煩妳先生上來一下?我們要跟他說幾句話。」
「呃,我想現在他恐怕沒辦法。」老媽說。「我可以代替他嗎?」
這時候,巴德忽然打開車門。「媽,我跟妳一起去。」
「我也去。」我說。
「巴德,你跟我來。丹尼爾,你和珍妮留在車子裡陪爸爸。」說著,她瞄了後照鏡一眼,看看自己的頭髮,然後就開門下車,伸手拉拉裙子,把裙子撫平。(待續)從前,我看過好幾次老媽那種臨機應變面不改色的本事,不過,這天下午,她那種從容不迫的模樣,是我這輩子從來沒見過的。她邁開大步,和巴德走上坡道,走到那群警察前面。警察問了她一些問題,她一一回答了,那種從容老練的神態,彷彿她事先排練過好幾次。
我們楞楞地看著那輛被火焰吞沒的貨車。老爸兩手緊緊抓住方向盤。
那個貨運公司的司機坐在一棵樹下,頭靠在膝蓋上。另外那個傢伙蹲在他旁邊,嘴巴湊在他耳朵旁邊,好像在嘀咕些什麼。
貨廂的門敞開著,裡頭竄出熊熊火舌。火光中,我隱隱約約看到老媽那座古董衣帽架著火了。此外,衣櫃、抽屜,還有那一堆凌亂的廚房餐桌椅,也被火焰吞噬了。鉻鋼桌腳被火燒得整個垂彎下來,彷彿一朵朵枯萎的花。我們所有的家當全部付之一炬。那幾個消防隊員站在那裡看火燒,眼神中露出一種興奮。我心裡想,他們一定是打算等東西全部燒光之後,再打開水管噴水。這時候,我忽然聽到一陣劈啪聲,還有轟隆一聲巨響,接著,我看到我們家的電視機忽然從那團地獄之火中飛出來,在半空中劃出一道弧線,然後螢幕朝下,正好砸在我面前的地上。
電視一落地,立刻竄出一團火球。這時候,旁邊有幾輛看熱鬧的車子開始猛按喇叭,彷彿在為這場精采的煙火秀大聲喝采。
過了好久,巴德和老媽終於回到車上了。老爸發動引擎,車子迅如閃電地從路邊飛竄到車道上,地面上的細砂礫被輪胎甩起來,四散飛濺。
一路上沒人吭聲,車子裡一片死寂。後來,足足開了一公里之後,車子裡好不容易有聲音了—喀嚓一聲。那是老媽的Zippo打火機。「李。」她吸了滿滿一口煙,說話的口氣小心翼翼。「我知道你心情一定很惡劣,可能不想說話。沒關係,不說也好。不過,親愛的,也許你可以換個角度想,好歹我們全家人都在一起,大家都平安。所以,不管那些東西有沒有燒掉,對我們都不會有影響。李,那只不過是一些身外之物。更何況,我們有買保險。那不是我們的錯—不是你的錯,也不是我的錯。錯的是那個司機。那個王八蛋喝醉了。」
「媽,妳怎麼可以說髒話!」珍妮大叫了一聲。
「珍妮,妳給我閉嘴。李,我告訴你,他喝醉了,我隔著好幾公尺都還聞得到他身上那股威士忌的味道。而且,那些警察也聞到了。」
「我沒有買保險。」老爸說。
老媽立刻轉頭看著他。「你說什麼?」
「家裡的東西一上了車,就不在保險的理賠範圍內了。搬家公司要收額外的保險費,可是我們公司卻不肯補貼。所以,我拒絕加保。搬家公司要我簽署一份具結書,聲明是我拒絕加保。」
「你真的簽了?」老媽問。
「妳知道光是那三天要追加多少保費嗎?」他說。
「呃」她終於把那口憋了很久的氣吐出來了。「這下子好玩了。」在我們家裡,唯一一種比「異乎尋常」更糟糕的情況,就是「好玩」。
想像一下,五個人擠在一輛車子裡,卻沒有人說話,這種狀況能撐多久?告訴你,久到超乎你的想像。我們就這樣默默坐在車子裡,而車子就這樣一直開,一直開,一直開到天黑。我敢打賭,就算車子繼續再開三個鐘頭,還是不會有人說話。
後來,老媽終於試探性地咳了一聲。「李,傑克森市不是應該快到了嗎?」
老爸根本連看都不看她一眼。他眼睛死盯著前面的車道。
老媽說:「親愛的,我剛剛看到路邊的標誌,上面寫說,再過十九公里就到哈帝斯堡了。可是,哈帝斯堡不是在傑克森市南邊嗎?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在南邊沒錯。我想,我們車子可能開過頭了,傑克森市已經過了。巴德,麻煩你把地圖拿給我好嗎?」
老爸還是一樣悶不吭聲,一直往前開。老媽打開車頂上的小燈,核對地圖,發現我們真的開過頭了。我們已經跑到傑克森市東南方一百一十公里的地方了。如果我們繼續往前開,就會距離傑克森市更遠。這時候,老爸還是不吭聲。
後來,車子開到哈帝斯堡的外圍了。這時候,老媽說:「李,看你這樣,我開始覺得害怕了。把車子停下來好不好?我們先找一家汽車旅館將就一晚。我相信只要我們好好睡一覺,明天心情就會好多了。」
老爸還是不吭聲。過了一會兒,車子經過「雷貝葉爾汽車旅館」門口,這時候,老爸忽然猛一轉彎,開進汽車旅館的停車場,然後一個緊急煞車,停在辦公室門口。接著,他走進辦公室,出來的時候,手上多了一支鑰匙。
這時候,我忽然不知道哪來的一股衝動很想開口說話。那種感覺很像小時候玩躲迷藏—我明明發現一個很棒的地方可以躲,絕對沒人找得到,可是我偏偏就是沒辦法乖乖躲好,搞到後來總是會暴露行蹤。
我跪到椅墊上,探頭到車窗外。「爸。」我說。「你瘋了嗎?這裡的游泳池連滑水道都沒有。」
還好法律有明文規定,殺自己的孩子是犯法的。我們下車走向房間的時候,他竟然有辦法悶不吭聲的揍了我一拳。真不知道他是怎麼辦到的,我想,我是永遠猜不透了。
「還沒。」
「那你最好再多吸一點。」
印地安納州的夏天。再過一個禮拜,我就要滿十六歲了。整個下午,我都和那夥哥兒們在一起,騎著腳踏車跟在噴灑殺蟲劑的卡車後面,猛吸DDT的霧氣。那種味道聞起來香香甜甜的,聽說吸多了會長高。
經過我家門口的時候,忽然瞥見老爸的車停在車道上。那是一輛藍色的Oldsmobile Delta 88型全家福大房車。禮拜四下午,家門口竟然會看到老爸的車,那種玩樂的好心情剎那間就無影無蹤了。於是,我跟那些哥兒們揮揮手,讓他們自己去玩了。
老爸是個好人──經過這麼多年的風風雨雨之後,我可以給他這麼一個整體評價──不過,如果你每天跟他生活在一起,你可能會覺得他的幽默感跟希特勒不相上下。我模模糊糊還記得,小時候,他也曾經像別人的爸爸一樣,把我們高高舉起來,抱在懷裡,逗我們玩,不過,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我已經快想不起來了。我只記得,當我們漸漸長大以後,他總是對我們板著一張臉。他說,要是不對我們嚴厲一點,我們長大以後恐怕會變成軟腳蝦。
他的名字叫做李.雷.莫斯葛羅夫,出身於阿拉巴馬州一個窮苦人家。一九三○年代的「大蕭條」時期,他家裡徹底破產了。後來,對於自己的窮苦出身,老爸始終耿耿於懷。「大蕭條」彷彿一朵暴風雨的烏雲,始終籠罩在我們家上空,彷彿某種註定的厄運正從遙遠的地平線外席捲而來。
每個星期一,老爸都是一大早四點就起床,一個人默默吃早餐片,邊吃邊看潛在客戶名單。又一個星期開始了,他又要繼續拜訪客戶,繼續搏鬥,以免全家被「大蕭條」的烏雲吞沒。從禮拜一到禮拜五,他到處奔波,馬不停蹄的拜訪客戶。他連續三年榮獲「鐵力士公司」年度模範地區業務經理,是全公司最拚命的業務員,態度也最和善。他永遠面帶微笑,說起話來禮貌周到。只不過,一整個禮拜下來,他心裡壓抑了太多的憤怒、挫折、失望和沮喪,一等到禮拜五晚上,他回到家,那些情緒就會全部發洩在我們身上。
可是,今天才禮拜四,他竟然回家了。這實在很異乎尋常。在我們這個家庭裡,異乎尋常的事鐵定不是好事。
我偷偷摸摸把腳踏車放進車庫裡,儘量不弄出聲音,但沒想到打開後門的時候,門忽然嘎吱一聲,壞了我的大事。這時候,我聽到客廳裡傳來他的怒吼聲:「你跑到哪裡去鬼混了?給我進來!」
每次爸用那種口氣講話的時候,你是不需要回答的。我囁囁嚅嚅的走進客廳,看到全家人都圍在電視機前面,只不過,電視並沒有開。恐怕真的大事不妙了。
我走到沙發前面,輕輕坐下來,坐在巴德和珍妮中間。他們個個臉色凝重。看他們那副模樣,我心裡想,會不會是有誰死了。
「嗯,全家人都到齊了。」老爸說。「那好,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宣布。我要調職了,我們又要搬家了。」
那一剎那,我立刻全身發麻,彷彿身體突然失去了知覺。調職。「鐵力士公司」每隔一兩年就會把業務員調到別的地區,以免他們鬆懈。這十年來,老爸已經調職了六次,而最後一次,我們來到了目前居住的印地安那州。在所有住過的地方當中,這裡是我最喜歡的,只可惜,鐵力士才不會管我喜不喜歡。不久之前,我心裡還暗暗希望,但願我們能夠在這裡安家落戶。我愛印地安那州。我在這裡交到很多好朋友,而且這裡地勢很平坦,可以隨心所欲的騎腳踏車到處跑,想去哪裡就去哪裡。而且,一到冬天,這裡就大雪紛飛,天寒地凍,你可以整天窩在家裡看電視。
好一會兒,大家都沒說話,客廳裡陷入一片沉寂。接著,我突然開口問:「我們要搬去哪裡?」
「密西西比州。」老爸說。「噢,對了,你最好閉嘴,我不想聽你發表意見。」
「喂,李,你怎麼這樣講話呢?」媽媽突然插嘴了。老爸站在那扇橫推式的玻璃門旁邊,我們坐在沙發上,而老媽則站在老爸和我們中間。「好了,你們幾個,對爸爸來說,這可是一件大事──事實上,不光是對爸爸,對我們全家人也一樣。你們都知道,我一直都很希望能夠住在外婆和傑克家附近……而且,你們也知道,我很受不了這裡的冬天。」
那倒是真的。老媽是南方姑娘一朵花,當年第一次搬家,老爸要帶她離開阿拉巴馬州的時候,她就已經嚇得六神無主了。(待續)「妳瘋了嗎?」巴德說。「媽,我們現在怎麼可以搬家呢?我最近好不容易才被大學代表隊相中。」巴德是摔角選手。他摔角簡直像在拚命,每次比賽結束,他都會吐得七葷八素。這一點,老爸倒是感到十分光榮。
「好了,巴德,別這樣。搬到那邊去,爸爸會比較好開發業務。」媽說。「更何況,我們已經別無選擇了,既然如此,我們何不坦然接受,高高興興的去面對呢?」
「要搬就搬,你們全都搬走沒關係。我自己留在這裡。」巴德說。「媽,秋天一開學,我就升高三了,我們怎麼可以搬去—妳剛剛說哪裡?密西西比嗎?這輩子我還沒碰過這麼荒唐的事!」
聽巴德這樣說話,我嚇了一大跳。要是我說出這種話,恐怕會被老爸甩一巴掌,然後關在房間裡不准出來。這時候,老爸臉色一沉,好像快要發作了,不過,他還是按捺住了,沒有出聲。巴德的模樣看起來很像老爸,所以,老爸總是對他另眼相看。
「好,巴德,你說你要留下來。」媽忽然露出一種陰森詭異的笑容。「那我問你,誰煮飯給你吃?衣服髒了誰幫你洗?」
「如果巴德要留下來,那我也要留下來。」珍妮說。
「誰都不准留下來。」媽媽說。「搬家沒什麼大不了的,我們不是已經搬過很多次了嗎?搬家公司的人禮拜一一大早就會過來裝貨了。」
這時候,巴德忽然站起來,劈哩啪啦的跺著腳跑向走廊,跑回房間去,然後砰的一聲把門用力一甩!
「老天。」爸大叫起來。「我的老天,看看妳兒子……」
「好了,李。」媽說。「你別給我找麻煩。」
「找麻煩?妳才別給我找麻煩。」
「親愛的,我不是告訴過你嗎?他們需要多一點時間適應的。想也知道,一開始他們當然會不高興—在這裡,他們已經有一群朋友了,而現在卻不得不和朋友分開。」說著,她轉頭看看珍妮和我,眼神有點不安。「我跟你們保證,你們一定會喜歡密西西比的。你們一定會交上新的朋友。老爸已經找到一棟鄉下的房子,很漂亮,而且,那裡的學校一定很棒。」
我不由自主的冷笑了一聲。「密西西比?嘿嘿,想也知道,一定棒得不得了。」我從來沒去過密西西比,不過,我在電視新聞裡已經看得夠多了。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密西西比都是全美國最爛的。那裡別的沒有,就是凶神惡煞的警長特別多,遊行抗爭的黑鬼特別多,死於非命的人權鬥士特別多。
「密西西比有什麼不好?」媽說。「那裡很漂亮,天氣很暖和,而且,最重要的一點是,我講話有人聽得懂。」
「要是我們不想去呢?」我問。「為什麼我們非去不可?」
「因為爸爸要調職了。就這樣。」她伸出一根指頭,把垂在眼睛前面那根金黃色的頭髮撥開。「而且,這次的業務轄區比較小,所以,他就不用整天在外面跑了。」說到這裡,她臉上露出笑容,可是爸卻開始皺起眉頭死盯著我,那副模樣彷彿認定我會說出什麼大逆不道的話,所以,他已經準備要撲上來掐死我了。
「密西西比州又稱木蘭之州。」珍妮翻開《世界百科全書》,邊看邊唸。「首府是傑克森市。物產是棉花、木材、家禽,和牛隻。」
「太棒了,珍妮。」老媽說。「我早說過,有了這些書,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
老媽拚命想讓我們以為,老爸這次調職是升官了,不過我心裡有數,根本不是這麼回事。我已經快十六歲了,什麼都瞞不了我的。我看過他們的信,翻過他們的檔案櫃。我看到他們買的保單,嚇了一大跳,因為,要是他們死了,我們這幾個孩子可就要發財了。有好幾天晚上,我聽到老爸在咒罵賴瑞.森普。他是區經理,老爸的頂頭上司。我心裡明白,目前印地安那州總部的業務轄區橫跨三個州,而調到密西西比之後,業務轄區只剩下一個州,說穿了,這根本就是降職。而我就是不知好歹,偏偏要在傷口上撒鹽。「為什麼爸爸的業務轄區變小了呢?」
這時候,空氣中彷彿起了一陣隱隱的顫動。那是從爸爸站的地方發出來的。(待續)珍妮這個人對表演時機的拿捏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彷彿有一具無形的攝影機隨時跟著她。這時候,她忽然開口了。「哇,終於要搬家了,我好開心哦。」她大聲說。「媽,我也好討厭這個地方耶。而且,我也好希望可以和外婆住近一點。」
「乖孩子。」老媽說。「凡事往好的方面想,人生才會美好。」
這時候,我用手掩住嘴巴,假裝咳了一下,嘴裡罵了一聲「馬屁精」。
「媽!他罵我馬屁精!」
「才沒呢。我是咳嗽。難不成連咳嗽都要妳批准嗎?」
於是,到了禮拜一,搬家公司來了,把我們家的東西裝上車。那是一節橘紅色的巨無霸拖掛貨廂,外殼有「聯合貨運公司」的字樣。
禮拜二,我們出發上路,沿著那條嶄新的州際公路向前奔馳,迎向未來。我們開了一整天的車,一直開到太陽都快下山了。抵達孟斐斯市南區的時候,車子壓到路面上的一塊凸起,我震了一下,臉頰撞到車窗玻璃。這時候,四線道的公路突然縮小成兩線道,路邊有一面標示牌,上面寫著:
歡迎蒞臨密西西比
這時候,眼前忽然豁然開朗,出現一片平野。乍看第一眼,那種感覺彷彿我們又回到了印地安那州:一望無際的平疇綠野一路連綿到地平線,遠處蔚藍的天際有一道道綿延不盡的圍欄,矗立著一座座的穀物升降機。不過,這裡的房子看起來可就有點不太一樣了。中西部到處都是整齊美觀的農舍,可是這裡的房子卻是那種貼著防水紙的小木屋,而坐在門廊上的都是黑人:小孩子個個骨瘦嶙峋,衣服破破爛爛,而老人則是彎腰駝背,頭上戴著草帽。不過,偶爾車子從高大的橡樹林旁邊經過時,我們會瞥見一兩棟莊園大宅在樹林後若隱若現—巨大的白色柱子看起來很像希臘神殿,感覺很隱密。
老媽說:「你能想像住在那種房子裡是什麼感覺嗎?要是我,我一定會覺得自己就像『亂世佳人』裡的郝思嘉。」
「媽,妳看,」珍妮說。「那個女孩子沒穿襯衫。」
「珍妮,不要盯著人家看。不是每個人日子都能過得像我們這麼好。」
「哎呀。」老爸搔搔脖子。「這年頭只要肯拚,日子都還過得去。想當年大蕭條的時候,那種日子才真叫苦咧。」
「她家的人怎麼會讓她這樣,沒穿襯衫光溜溜的在外面跑呢?」珍妮往後一仰,靠到椅背上。車窗外那個女孩越來越遠了。「她看起來好像和我差不多大。」
「呃,親愛的,我相信她平常穿的襯衫一定是很不錯的。」老媽說。「不過,大概是因為這裡天氣比較熱吧,所以今天沒穿。」
車子裡冷氣很強,吹得我們涼颼颼的,可是,你依然感覺得到車窗外的熱浪。你可以看得到,路面上,田野上,一波波的熱氣蒸騰而上。雖然車子以將近一百公里的時速向前飛馳,但你依然看得到外面的人臉上的汗水。
「噢,今天真是太美好了。」老媽說。「回到家鄉的感覺真是太棒了。我們把車窗打開吧,好好感覺一下。」說著,她把車窗搖下來,那一剎那,涼爽的空氣彷彿瞬間被吸乾了,車子裡忽然灌滿了夏日滾燙的熱氣──我忽然感覺一陣燠熱潮濕迎面撲來。我們全都哀聲慘叫起來,後來,老媽終於又把車窗搖了上來。
她咧開嘴笑得好開心。「熱!我就是喜歡這種熱天。」我們又回到南方了,這時候,老媽那種南方腔又開始蠢蠢欲動了──你一定聽過那種濃濃的、甜甜的阿拉巴馬南方腔。我就是喜歡這種熱天!
「這種天氣,我絕對不到外面去—絕不。」巴德說。「老天保佑,屋子裡的冷氣最好夠冷。」
「噢,我保證你們一定會成天在外面的。」老爸很堅定地告訴他。「屋子外面有一大片草坪,除草的工作,你們這幾個男生很有得忙的。」
「孩子們,這裡是鄉下地方。」老媽說。「這裡遠離了城市的喧囂,那種寧靜安詳是你們難以想像的,而且,房子後面有一大片庭院。我已經有點迫不及待了,好想趕快把整片庭院都種滿杜鵑花。印地安那州還在冰天雪地的時候,我們這裡的花已經開了滿庭院了。」(待續)「天曉得,那間爛學校不知道有沒有摔角隊。」巴德嘀咕著。
「就算他們沒有摔角隊,我相信學校裡一定有跟摔角一樣好玩的運動。」老媽說。「事實上,這裡就是美式足球的發源地。」
「我恨死了美式足球。」巴德說。
「千萬別讓這裡的人聽到這種話,那是很傷感情的。」老爸說。「巴德,我是說正經的,你嘴巴小心點。」
「媽,我肚子餓了。」珍妮說。
「呃,二十分鐘之前我們吃午飯的時候,妳不是說妳還不餓嗎?」老媽把那個Kroger便利商店的袋子拿起來晃了兩下。「親愛的,妳想吃哪一個?花生醬口味的好不好?噢,有了,這裡還剩一個火腿乳酪口味的。」
「我要花生醬的,不過,麵包皮拿掉,我不要吃。」
「麵包皮才是最好吃的地方。」老爸說。
老爸並不是因為想哄珍妮吃掉麵包皮才這樣說的。老爸真的就是這調調:對老爸來說,麵包皮不光是好吃而已,而是最好吃的。此外,他還喜歡在禮拜天啃雞脖子。他喜歡把吃剩的玉米餅和脆豬皮混在一起,再配上蕪菁甘藍,冷冷的吃,當早餐吃。他喜歡吃這種東西,因為這種東西會讓他回想起當年窮苦的滋味。
他瞇起眼睛,看著前面的車道上那長長的一排車陣—前面好像有什麼地方堵住了,整條車陣從前面那個彎道一路延伸過來。「老天,你們看看這個。」他嘆了一口氣,彷彿那些車停住不動,只是為了要跟他過不去。他兩隻手按在脖子後面,扭動肩膀關節,喀嚓作響。「幫幫忙,老兄。」他的手指頭輪流在方向盤上敲打著。「我們還有好幾英里的路要開呢。」
我們前面是一輛旅行車,肯塔基州的車牌,裡頭擠滿了小孩子,有的吐舌頭跟我們做鬼臉,有的把髒兮兮的腳踩在窗玻璃上。你彷彿聞得到孩子們那種不耐煩的氣息從那輛車子裡飄出來。想像得到,坐在前座那兩個爸媽一定是拚命裝聾作啞,裝作沒聽到。
「謝天謝地,還好我們只生了三個。」老爸說。
老媽微微一笑。「老天保佑。」
「嘿,你們兩位。」巴德叫了一聲。「這是什麼話。」
「你們幾個小鬼,看到前面那輛車沒有?」老爸說。「為什麼要節育,前面那輛車就是活生生的理由。」
「李。」
珍妮問:「什麼叫節育?」
「都是你,哪壺不開提哪壺。」
「所謂節育,就是要掂掂自己有幾兩重,不要不自量力。」說著,老爸伸手去按喇叭。整條路上喇叭聲此起彼落,好像在大合唱。
放眼望去,我看到前面的田野上有一排松樹,樹後面升起一股濃濃的黑煙。「嘿,爸,那邊好像在燒東西。」
這時候,爸爸看向我手指的方向。「嗯,你好像沒看走眼,那裡有一棟鬼房子燒起來了。難怪路上車子都不動了,大家都在看熱鬧。」說著,他又拚命按喇叭。「趕快開車吧!沒看過火燒房子嗎?」這時候,前面那輛擠滿了小孩的車也在按喇叭,開車的人把手伸出窗外,猛揮拳頭。
那東西很大,而且正在起火燃燒,濃濃的黑煙衝上雲霄,彷彿一團烏雲,而且濃煙裡不時竄出火舌。這時候,前面有些車子忽然開始進一下退一下,設法在車陣裡掉頭,然後從我們旁邊往反方向開過去。
老媽說:「大家都想繞路了。」
老爸往前慢慢開了一個車身長的距離。「繞路得繞一大圈,搞不好得花上兩倍時間。」說著,他開始去調收音機的頻率,沒多久,收音機接收到一個播放農業新聞的頻道。播報員的聲音聽起來平平板板的。
「大豆又漲啦,棉花的行情還是老樣子。」那個人說。「今天要灑農藥,各位鄉親別忘了哦。以上的報導是由熱心公益的『鐵力士化學』所提供。害蟲在哪裡,我們都知道。」
這時候,老爸忽然叫了一聲:「嘿嘿!」然後他把音量調大。「你們聽到他說什麼嗎?才剛到密西西比,沒想到收音機裡就已經聽得到我們公司的新聞了。」
「這是個好兆頭。」老媽說。「就像他們用這種方式在歡迎你。告訴你,李,未來一定是一片大好。」(待續)這時候,前面又有更多人投降了。又有好幾部車掉頭開走了。
我們的車慢慢繞過那個彎道之後,赫然發現原來那不是房子失火,而是路上有東西著火了。正前方是上坡道,擋住了我們的視線,看不到是什麼東西。州警的巡邏車閃著藍燈。戴著寬邊牛仔帽的警察比著手勢,指揮車子開下高速公路。
「看起來像是大車禍。」老爸說。「看那種火勢,鐵定是油罐車燒起來了。」
「太酷了。」巴德說。
「酷?巴德,你怎麼這樣說話呢?」老媽說。「說不定有人受傷了。」
「我不是那個意思。我是說,那麼大的火,看起來很酷。」巴德說。
「爸,車子不要開太近好不好?我不想看到有人被火燒的樣子。」
「不用怕,珍妮。我也不想看。」
後來,車子慢慢靠近,我們終於看到了。原來是一輛拖掛式的貨車翻倒了,橫躺在路面上,車頭和後面的車廂彎成了V字形。一群消防隊員和州警站得遠遠的看火燒—看起來很像一輛巨大的橘色玩具車,支離破碎,火舌從車頭裡竄出來,從貨廂敞開的門口竄出來。
兩個穿著灰色制服的人遠遠站在旁邊,其中一個彎著腰,手撐在膝蓋上,看起來好像快要吐了。
好一會兒,我才猛然想到,嘿,我認得那傢伙,而且,我也想到自己在哪裡看過他了。那一剎那,我腦海中忽然浮現出一幕畫面:就在昨天,在印地安那州,在我們家門口,那傢伙站在「聯合貨運公司」的車廂後面,把門關起來。
「嘿,爸。」我說。「你看那個人。昨天幫我們把東西裝上貨車的,不就是他嗎?」
「你說什麼?」
「那個人。在那邊!他不就是『聯合貨運公司』的人嗎?」
為什麼幫我們搬家的司機會和那些州警站在一起?為什麼他們會站在那輛燒得一塌糊塗的貨車旁邊?接著,我猛然想通了。因為燒毀的就是他的貨車,也就是,我們的貨車。
這時候,老爸猛轉方向盤,把車子開到路肩的草坪上,關掉引擎,把車窗搖下來,兩手搭在方向盤上。車窗一開,熾熱的空氣立刻灌進車子裡。我們聽到陣陣劈哩啪啦的爆裂聲。那是噴霧罐爆炸的聲音,一種低沉的、悶悶的巨響,彷彿一頭龐然巨獸在吸氣。
珍妮說:「幹嘛要停車?」
「妳這個白痴!」我大叫了一聲。「還搞不清楚嗎?那是我們的東西!」
「我們的東西?什麼意思?」
「你們兩個。」老媽忽然開口了。她的聲音聽起來異乎尋常的冷。後來,每當我回想起她當時說話的腔調,還是會不由自主的打個哆嗦。「不要再讓我聽到你們兩個講話。」
這時候,有個O型腿的警察從坡道上面走下來,朝我們的方向走過來。「老兄,」他說,「你們不可以在這裡逗留,趕快走吧。」
老爸的脖子忽然變得好紅好紅,彷彿瞬間被太陽曬傷了。我雖然看不到他的臉,不過,我相信,要是那個警察看到他的表情,一定會嚇得倒退好幾步。
「好了,可以了。」他說。「熱鬧也看夠了吧。趕快把車子開走吧。」
老爸悶不吭聲,眼睛死盯著那個警察。
「這位先生,你沒聽到我講話嗎?」
這時候,老媽忽然伸長了身體,湊近駕駛座的車窗。「警官,那輛貨車是不是『聯合貨運公司』的貨廂?」
「是的,女士,沒有錯。可是,妳為什麼問這個?」
「呃,我叫珮姬,這位是我先生,李.莫斯葛羅夫。事情是這樣的,那節貨廂裡的東西是我們的。」
「嗯。」那位警察臉上的表情看不出有什麼反應。「你們是要搬家到這裡來嗎?」
「是的,警官,沒錯。」老媽說。也許那個警察會覺得老媽說話的口氣聽起來很有活力,不過我心裡有數,那種口氣和哀聲慘叫只有一線之隔了。
「呃,我實在很不想當烏鴉,不過,女士,貨廂裡的東西已經差不多燒光,剩沒什麼了。」說著,他朝那堆火焰揮揮手,那副模樣彷彿我們全家都是瞎子。
「能不能麻煩妳先生上來一下?我們要跟他說幾句話。」
「呃,我想現在他恐怕沒辦法。」老媽說。「我可以代替他嗎?」
這時候,巴德忽然打開車門。「媽,我跟妳一起去。」
「我也去。」我說。
「巴德,你跟我來。丹尼爾,你和珍妮留在車子裡陪爸爸。」說著,她瞄了後照鏡一眼,看看自己的頭髮,然後就開門下車,伸手拉拉裙子,把裙子撫平。(待續)從前,我看過好幾次老媽那種臨機應變面不改色的本事,不過,這天下午,她那種從容不迫的模樣,是我這輩子從來沒見過的。她邁開大步,和巴德走上坡道,走到那群警察前面。警察問了她一些問題,她一一回答了,那種從容老練的神態,彷彿她事先排練過好幾次。
我們楞楞地看著那輛被火焰吞沒的貨車。老爸兩手緊緊抓住方向盤。
那個貨運公司的司機坐在一棵樹下,頭靠在膝蓋上。另外那個傢伙蹲在他旁邊,嘴巴湊在他耳朵旁邊,好像在嘀咕些什麼。
貨廂的門敞開著,裡頭竄出熊熊火舌。火光中,我隱隱約約看到老媽那座古董衣帽架著火了。此外,衣櫃、抽屜,還有那一堆凌亂的廚房餐桌椅,也被火焰吞噬了。鉻鋼桌腳被火燒得整個垂彎下來,彷彿一朵朵枯萎的花。我們所有的家當全部付之一炬。那幾個消防隊員站在那裡看火燒,眼神中露出一種興奮。我心裡想,他們一定是打算等東西全部燒光之後,再打開水管噴水。這時候,我忽然聽到一陣劈啪聲,還有轟隆一聲巨響,接著,我看到我們家的電視機忽然從那團地獄之火中飛出來,在半空中劃出一道弧線,然後螢幕朝下,正好砸在我面前的地上。
電視一落地,立刻竄出一團火球。這時候,旁邊有幾輛看熱鬧的車子開始猛按喇叭,彷彿在為這場精采的煙火秀大聲喝采。
過了好久,巴德和老媽終於回到車上了。老爸發動引擎,車子迅如閃電地從路邊飛竄到車道上,地面上的細砂礫被輪胎甩起來,四散飛濺。
一路上沒人吭聲,車子裡一片死寂。後來,足足開了一公里之後,車子裡好不容易有聲音了—喀嚓一聲。那是老媽的Zippo打火機。「李。」她吸了滿滿一口煙,說話的口氣小心翼翼。「我知道你心情一定很惡劣,可能不想說話。沒關係,不說也好。不過,親愛的,也許你可以換個角度想,好歹我們全家人都在一起,大家都平安。所以,不管那些東西有沒有燒掉,對我們都不會有影響。李,那只不過是一些身外之物。更何況,我們有買保險。那不是我們的錯—不是你的錯,也不是我的錯。錯的是那個司機。那個王八蛋喝醉了。」
「媽,妳怎麼可以說髒話!」珍妮大叫了一聲。
「珍妮,妳給我閉嘴。李,我告訴你,他喝醉了,我隔著好幾公尺都還聞得到他身上那股威士忌的味道。而且,那些警察也聞到了。」
「我沒有買保險。」老爸說。
老媽立刻轉頭看著他。「你說什麼?」
「家裡的東西一上了車,就不在保險的理賠範圍內了。搬家公司要收額外的保險費,可是我們公司卻不肯補貼。所以,我拒絕加保。搬家公司要我簽署一份具結書,聲明是我拒絕加保。」
「你真的簽了?」老媽問。
「妳知道光是那三天要追加多少保費嗎?」他說。
「呃」她終於把那口憋了很久的氣吐出來了。「這下子好玩了。」在我們家裡,唯一一種比「異乎尋常」更糟糕的情況,就是「好玩」。
想像一下,五個人擠在一輛車子裡,卻沒有人說話,這種狀況能撐多久?告訴你,久到超乎你的想像。我們就這樣默默坐在車子裡,而車子就這樣一直開,一直開,一直開到天黑。我敢打賭,就算車子繼續再開三個鐘頭,還是不會有人說話。
後來,老媽終於試探性地咳了一聲。「李,傑克森市不是應該快到了嗎?」
老爸根本連看都不看她一眼。他眼睛死盯著前面的車道。
老媽說:「親愛的,我剛剛看到路邊的標誌,上面寫說,再過十九公里就到哈帝斯堡了。可是,哈帝斯堡不是在傑克森市南邊嗎?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在南邊沒錯。我想,我們車子可能開過頭了,傑克森市已經過了。巴德,麻煩你把地圖拿給我好嗎?」
老爸還是一樣悶不吭聲,一直往前開。老媽打開車頂上的小燈,核對地圖,發現我們真的開過頭了。我們已經跑到傑克森市東南方一百一十公里的地方了。如果我們繼續往前開,就會距離傑克森市更遠。這時候,老爸還是不吭聲。
後來,車子開到哈帝斯堡的外圍了。這時候,老媽說:「李,看你這樣,我開始覺得害怕了。把車子停下來好不好?我們先找一家汽車旅館將就一晚。我相信只要我們好好睡一覺,明天心情就會好多了。」
老爸還是不吭聲。過了一會兒,車子經過「雷貝葉爾汽車旅館」門口,這時候,老爸忽然猛一轉彎,開進汽車旅館的停車場,然後一個緊急煞車,停在辦公室門口。接著,他走進辦公室,出來的時候,手上多了一支鑰匙。
這時候,我忽然不知道哪來的一股衝動很想開口說話。那種感覺很像小時候玩躲迷藏—我明明發現一個很棒的地方可以躲,絕對沒人找得到,可是我偏偏就是沒辦法乖乖躲好,搞到後來總是會暴露行蹤。
我跪到椅墊上,探頭到車窗外。「爸。」我說。「你瘋了嗎?這裡的游泳池連滑水道都沒有。」
還好法律有明文規定,殺自己的孩子是犯法的。我們下車走向房間的時候,他竟然有辦法悶不吭聲的揍了我一拳。真不知道他是怎麼辦到的,我想,我是永遠猜不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