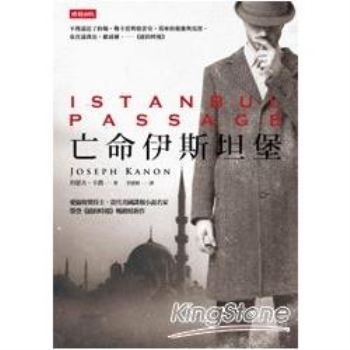第一部 貝貝克區
第一次行動被迫取消。花了好幾天安排船隻和庇護所,然後就在接應之前幾小時,起風了,一陣從東北方呼嘯而下的強風,掃過黑海時掀起巨浪。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波浪,抵達防護齊全的沿岸別墅時通常比船隻的尾浪高不了多少,這時卻洶湧拍打著登岸碼頭。從碼頭上,里昂幾乎看不清亞洲那邊,只有幾串昏暗的燈光藏在滂沱的雨幕後面。誰會冒險呢?連堅固耐操的渡輪都會誤點,更別說被收買的漁船了。他想像著漁夫計算他的機會:驚濤駭浪,視野模糊,指望四十米外突然冒出來的輪廓不是根本無法閃躲的木材貨輪。或者留在安全的碼頭上,綁好繩索在鑄鐵火爐邊喝喝梅子白蘭地。誰能苛責他呢?只有傻子才在暴風雨天出海。乘客可以等等。籌備好幾天都泡湯了。天公不作美啊。
「還要多久?」米海拉緊他的外套說。
他們停車在魯梅利碉堡底下,看著停泊的船隻隨浪翻騰,拉扯著纜繩。
「再等半小時。如果他遲到了而我不在這兒-」
「他不是遲到,」米海反駁說。他瞄了一眼。「他有這麼重要?」
「我不曉得,我只是送貨的。」
「冷死人了,」米海說,發動引擎。「這種季節。」
里昂露出微笑。在伊斯坦堡的自我想像中,四季如夏,女士們在花園涼亭裡吃果汁雪泥,旁邊有小船漂過。這座城市的人顫抖著靠火爐與毛衣撐過冬天,似乎有點驚訝天氣竟然也會變冷。
米海讓暖氣開了幾分鐘再關掉,像烏龜似的瑟縮在他的外套裡。「那就跟我來,但是不准發問。」
里昂伸手抹過窗戶上凝結的水珠,把它清除。「對你沒有危險。」
「太好了。新任務。你沒辦法自己做嗎?」
「他剛從康斯坦夏出來。就我所知,他只會說羅馬尼亞語。還有呢?手語?可是你-」
米海揮手打發。「你的新朋友之一。一定是德國人。」
「你不必這麼委屈。」
「小事一樁。我會討回來的。」
他點了根菸,有一瞬間里昂可以看見他灰白的臉孔和頭上僵硬斑白的頭髮。快要全白了。他們剛認識時,原本是黑色捲髮,打理得就像布加勒斯特時髦客的樣子,勝利大道上所有咖啡館都認識他。
「況且,看到鼠輩們離開-」 他鬱悶地說,「他們不肯讓我們出來。現在看他們的下場。」
「你已經盡力了。」巴勒斯坦護照,自由進出布加勒斯特,乞求資金,租賃老舊船隻,最後的生命線,直到這些也被剝奪。
米海吸一口菸,凝視擋風玻璃上淌落的水滴。「你最近怎麼樣?」他終於說。「你看起來很累。」
里昂聳肩,沒有回答。
「你為什麼接這差事?」米海轉頭面對他,「戰爭已經結束了。」
「是嗎?沒人告訴我。」
「才怪,他們打算展開另一場戰爭。」
「沒有我認識的人。」
「小心別喜歡上這檔事。一旦開始喜歡-」他的聲音漸低,因抽菸而沙啞,即使到現在仍維持著東歐口音。「那就不再有任何意義了。變成習慣。像這個,」他舉起他的菸說,「只是喜歡它的味道。」
里昂看著他,「那你呢?」
「對我們沒什麼改變。我們還在拯救猶太人。」他作個苦笑表情。「現在是逃離盟友。弄不到巴勒斯坦簽證,他們能去哪裡,波蘭嗎?我還在幫你跟納粹聯絡。真是美好世界。」
「為什麼找納粹?」
「為什麼做這些事?為了可憐的難民?不,我想一定是有人認識俄國佬。但是誰曉得呢?」
「你只是猜測。」
「你運送什麼東西,對你不重要嗎?」
里昂別開目光,再回來看錶。「呃,今晚他不會來了。無論他是誰。我最好打個電話。確認一下。那邊有咖啡館。」
米海俯身再次發動引擎。「我會停在附近。」
「不,留在這兒。我不希望車子-」
「了解。你在雨中跑步過馬路。淋濕。然後跑回來。又淋濕。回到等候的車子上。這樣就比較不可疑嗎。如果有人監視的話。」他把車子打到一檔。
「這是你的車,」里昂說,「如此而已。」
「你認為他們迄今還沒監視過?」
「有嗎?你會知道的,」他說,這是發問。
「永遠要假設有。」他橫過路面轉彎,停在咖啡館門前。「就照預定的做吧。避免淋濕。先告訴我。如果他來了,你的包裹,我要開車送他去-─他住宿的任何地方嗎?」
「不用。」
米海點頭。「這才像話。」他往側窗歪歪頭,「打電話吧。趁他們還沒起疑。」
有四名男子在玩骨牌、用鬱金香杯喝茶。當他們抬頭看,里昂瞬間變成希望他們看到的人─-被雨困住的外國人(ferengi原指《星艦迷航記》虛擬的外星人種族),正甩掉帽子上的水,需要電話-─他臉紅了,脈搏有點興奮加快。喜歡這感覺。或許米海看穿了,這種感覺,就像逍遙法外。
規劃,逃脫。今晚他會搭纜車到貝貝克區(Bebek,博斯普魯斯海峽歐洲岸位於兩座大橋之間的高級住宅區)的最後一站,再走到診所。這趟路他走過無數次了。如果被人跟蹤,他們會停車在診所門口一條街外等候,慶幸可以保暖,不用淋雨,又知道他在哪裡。但是剛經過一大叢夾竹桃,他就前往花園側門,折返米海在等候的博斯普魯斯路,突然感覺自由,有點狂喜。黑暗中不會有人看到他。如果他們在場,他們會抽菸,很無聊,以為他在裡面。這另一面生活,走到車上,只有他自己知道。
第一次行動被迫取消。花了好幾天安排船隻和庇護所,然後就在接應之前幾小時,起風了,一陣從東北方呼嘯而下的強風,掃過黑海時掀起巨浪。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波浪,抵達防護齊全的沿岸別墅時通常比船隻的尾浪高不了多少,這時卻洶湧拍打著登岸碼頭。從碼頭上,里昂幾乎看不清亞洲那邊,只有幾串昏暗的燈光藏在滂沱的雨幕後面。誰會冒險呢?連堅固耐操的渡輪都會誤點,更別說被收買的漁船了。他想像著漁夫計算他的機會:驚濤駭浪,視野模糊,指望四十米外突然冒出來的輪廓不是根本無法閃躲的木材貨輪。或者留在安全的碼頭上,綁好繩索在鑄鐵火爐邊喝喝梅子白蘭地。誰能苛責他呢?只有傻子才在暴風雨天出海。乘客可以等等。籌備好幾天都泡湯了。天公不作美啊。
「還要多久?」米海拉緊他的外套說。
他們停車在魯梅利碉堡底下,看著停泊的船隻隨浪翻騰,拉扯著纜繩。
「再等半小時。如果他遲到了而我不在這兒-」
「他不是遲到,」米海反駁說。他瞄了一眼。「他有這麼重要?」
「我不曉得,我只是送貨的。」
「冷死人了,」米海說,發動引擎。「這種季節。」
里昂露出微笑。在伊斯坦堡的自我想像中,四季如夏,女士們在花園涼亭裡吃果汁雪泥,旁邊有小船漂過。這座城市的人顫抖著靠火爐與毛衣撐過冬天,似乎有點驚訝天氣竟然也會變冷。
米海讓暖氣開了幾分鐘再關掉,像烏龜似的瑟縮在他的外套裡。「那就跟我來,但是不准發問。」
里昂伸手抹過窗戶上凝結的水珠,把它清除。「對你沒有危險。」
「太好了。新任務。你沒辦法自己做嗎?」
「他剛從康斯坦夏出來。就我所知,他只會說羅馬尼亞語。還有呢?手語?可是你-」
米海揮手打發。「你的新朋友之一。一定是德國人。」
「你不必這麼委屈。」
「小事一樁。我會討回來的。」
他點了根菸,有一瞬間里昂可以看見他灰白的臉孔和頭上僵硬斑白的頭髮。快要全白了。他們剛認識時,原本是黑色捲髮,打理得就像布加勒斯特時髦客的樣子,勝利大道上所有咖啡館都認識他。
「況且,看到鼠輩們離開-」 他鬱悶地說,「他們不肯讓我們出來。現在看他們的下場。」
「你已經盡力了。」巴勒斯坦護照,自由進出布加勒斯特,乞求資金,租賃老舊船隻,最後的生命線,直到這些也被剝奪。
米海吸一口菸,凝視擋風玻璃上淌落的水滴。「你最近怎麼樣?」他終於說。「你看起來很累。」
里昂聳肩,沒有回答。
「你為什麼接這差事?」米海轉頭面對他,「戰爭已經結束了。」
「是嗎?沒人告訴我。」
「才怪,他們打算展開另一場戰爭。」
「沒有我認識的人。」
「小心別喜歡上這檔事。一旦開始喜歡-」他的聲音漸低,因抽菸而沙啞,即使到現在仍維持著東歐口音。「那就不再有任何意義了。變成習慣。像這個,」他舉起他的菸說,「只是喜歡它的味道。」
里昂看著他,「那你呢?」
「對我們沒什麼改變。我們還在拯救猶太人。」他作個苦笑表情。「現在是逃離盟友。弄不到巴勒斯坦簽證,他們能去哪裡,波蘭嗎?我還在幫你跟納粹聯絡。真是美好世界。」
「為什麼找納粹?」
「為什麼做這些事?為了可憐的難民?不,我想一定是有人認識俄國佬。但是誰曉得呢?」
「你只是猜測。」
「你運送什麼東西,對你不重要嗎?」
里昂別開目光,再回來看錶。「呃,今晚他不會來了。無論他是誰。我最好打個電話。確認一下。那邊有咖啡館。」
米海俯身再次發動引擎。「我會停在附近。」
「不,留在這兒。我不希望車子-」
「了解。你在雨中跑步過馬路。淋濕。然後跑回來。又淋濕。回到等候的車子上。這樣就比較不可疑嗎。如果有人監視的話。」他把車子打到一檔。
「這是你的車,」里昂說,「如此而已。」
「你認為他們迄今還沒監視過?」
「有嗎?你會知道的,」他說,這是發問。
「永遠要假設有。」他橫過路面轉彎,停在咖啡館門前。「就照預定的做吧。避免淋濕。先告訴我。如果他來了,你的包裹,我要開車送他去-─他住宿的任何地方嗎?」
「不用。」
米海點頭。「這才像話。」他往側窗歪歪頭,「打電話吧。趁他們還沒起疑。」
有四名男子在玩骨牌、用鬱金香杯喝茶。當他們抬頭看,里昂瞬間變成希望他們看到的人─-被雨困住的外國人(ferengi原指《星艦迷航記》虛擬的外星人種族),正甩掉帽子上的水,需要電話-─他臉紅了,脈搏有點興奮加快。喜歡這感覺。或許米海看穿了,這種感覺,就像逍遙法外。
規劃,逃脫。今晚他會搭纜車到貝貝克區(Bebek,博斯普魯斯海峽歐洲岸位於兩座大橋之間的高級住宅區)的最後一站,再走到診所。這趟路他走過無數次了。如果被人跟蹤,他們會停車在診所門口一條街外等候,慶幸可以保暖,不用淋雨,又知道他在哪裡。但是剛經過一大叢夾竹桃,他就前往花園側門,折返米海在等候的博斯普魯斯路,突然感覺自由,有點狂喜。黑暗中不會有人看到他。如果他們在場,他們會抽菸,很無聊,以為他在裡面。這另一面生活,走到車上,只有他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