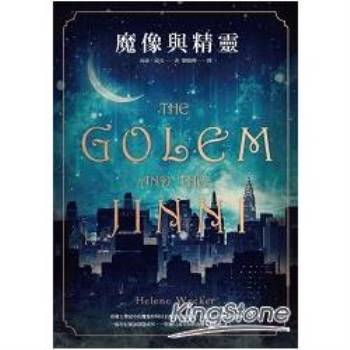1
魔像的生命始於一艘輪船的船艙之中。時間是一八九九年,船名為波羅的海號,自但澤啟航前往紐約。魔像的主人是一名叫奧圖.羅特費爾德的男子,他悄悄將裝著魔像的貨箱偷渡上船,藏在眾多乘客的行李之間。
羅特費爾德出發前往但澤碼頭的前一晚,任務終於完成。他駕著一輛馬車,載著一只大木箱、一件端莊的棕色洋裝和一雙女鞋,最後一次來到術士夏滿的小屋。
夏滿似乎已經多日無眠,眼眶發黑,臉色蒼白,彷彿精力被榨乾了。他點亮工作檯上的燈,羅特費爾德終於得以仔細端詳他要求的成品。
女子身材高䠷,幾乎和羅特費爾德自己一樣高,比例勻稱、軀幹纖長、雙乳小巧而堅挺,腰枝結實。臀部或許有些過於方正,但在她身上顯得很是合稱,甚至誘人。藉著昏暗的燈光,他偷偷瞄向她雙腿間的陰影,但一察覺夏滿譏諷的目光與自己奔騰的血液,又立刻轉開視線,表現出興趣缺缺的模樣。
她有著一張心型的寬闊臉孔,眼距甚開的雙眼緊閉,看不出眼珠顏色。鼻梁小巧玲瓏,鼻尖在豐潤的雙脣上方微微下彎,一頭微捲的褐髮被剪到約莫及肩的長度。
他試探地伸出手,半信半疑地摸向她冰涼的肩頭:「看起來好像是真的皮膚;摸起來也是。」
「是泥土。」老人說。
「你是怎麼辦到的?」
老人只是笑而不答。
「還有她的頭髮、眼珠?她的指甲呢?也都是用泥土做的?」
「不,那些全是如假包換的真貨。」夏滿若無其事地回答。羅特費爾德想起自己交給老人的那箱錢,猜想他都拿去買了什麼樣的材料。他打了個哆嗦,決定從此還是別再琢磨這事比較好。
兩人替泥像穿好衣服,小心翼翼地將她沉重的身軀搬進木箱。放置時,泥像的頭髮散落臉前,羅特費爾德等到老人轉過身後,才溫柔地幫她撥開髮絲,撥理整齊。
夏滿找到一小張紙片,在上頭寫下兩個重要的指令──一個喚醒她,一個摧毀她。他將紙片對摺再對摺,放進一枚油布信封,並在信封上寫下「魔像控制咒語」六個字,交給羅特費爾德。他的委託人急於喚醒魔像,但老人勸阻他:「她需要時間適應。」他說,「但船上過於擁擠,假若給旁人發現她真正的身分,你們兩個都會被扔下船。」聽了老人這麼說,羅特費爾德也只能不情不願地答應等抵達美國後再喚醒魔像。最後兩人釘上箱蓋,將她密密嚴嚴藏在箱中。
老人拿出一只蒙塵的酒瓶,替兩人各倒了一指高的烈酒:「敬魔像。」他說,舉起酒杯。
「敬魔像。」羅特費爾德跟著說,接著一口喝乾。這確實是個值得慶祝的勝利時刻,唯一掃興的是這段時間以來一直跟他苦苦糾纏的腹痛。他的身體向來敏感,而過去幾週來的壓力徹底擾亂了他的消化系統。他無視腹中的疼痛,協助老人將木箱搬上馬車,絕塵而去。老人揮手送別羅特費爾德遠去的背影,彷彿目送一對新婚燕爾的夫婦離去。「祝你們小倆口幸福快樂。」他高聲呼喚,笑聲兀自在樹林間迴盪。
輪船自但澤啟航,一帆風順地抵達中途的停靠站:漢堡。兩晚後,羅特費爾德躺在他狹窄的床位上,那枚寫著「魔像控制咒語」的油布信封塞在口袋深處。他覺得自己就像個收到禮物,卻又被叮囑不准打開的小孩。如果他睡得著,或許就不會如此心癢難耐,但他的腹痛已經轉變成為右腹裡的痛苦折磨。他覺得自己有點發燒,四周又緊緊環繞著下等艙的吵鬧:各種形形色色的鼾聲、小嬰兒抽抽搭搭的嗚咽,還有偶爾伴隨輪船劇烈顛簸而來的嘔吐聲。
他輾轉反側,痛得在床上打滾,心忖:不用說,那老頭肯定是謹慎過頭。如果她真如承諾中的順從,那純粹喚醒她又會有什麼危險?喚醒後,他大可命令她躺在木箱,直到輪船抵達美國後再現身。
但如果有問題怎麼辦?如果她根本無法喚醒怎麼辦?只是動也不動躺在那兒,一座徒具女人樣貌的泥像?這是他第一次醒悟,自己從沒見過任何能證明夏滿能如實履約的證據。驚慌之下,他匆匆從口袋掏出信封,拿出那張紙片,卻赫然驚見一堆胡言亂語、毫無意義的希伯來文!他太愚蠢了!
他猛然起身,從掛釘上拿下油燈,一手壓著右腹,匆匆穿過迷宮般的床鋪,沿著舷梯來到底艙。
將近兩個鐘頭後,他終於找到木箱。兩個小時以來,他在堆積如山的行李箱和用麻繩綑綁的箱子間鑽進鑽出,肚子裡彷彿有火在燒,大顆大顆的冷汗滲進眼裡。終於,他搬開一捆捲起的地毯,找到了:他的木箱,他的新娘。
他找到一把鐵撬,撬開箱上的釘子,粗魯推開箱蓋。他的心臟噗通狂跳,拿出口袋中的紙片,小心翼翼唸出喚醒魔像的咒語。
然後屏息以待。
緩緩地,魔像甦醒。
最先甦醒的是她的感官。她可以感到指尖下粗糙的木頭與肌膚上冰冷潮濕的空氣,感到輪船行進時的移動,聞到霉味和刺鼻的海水味。
她又甦醒了些,明白自己有個身體。那摸著木頭的指尖是她的指尖,感到冰涼空氣的肌膚是她的肌膚。她動了動手指,想知道自己做不做得到。
她聽見身旁傳來男人的氣息。她知道他的名字,也知道他是誰。他是她的主人、她存在的目的。她是他的魔像,一舉一動都受他的意志所操控,而現在,他想要她睜開雙眼。
魔像睜開雙眼。
昏暗的燈光中,她看見主人跪在身旁,臉孔與頭髮都被汗水浸濕了。他一手撐在木箱邊緣,另一手緊緊壓在腹部。
「哈囉,」羅特費爾德輕聲說,一陣荒謬的羞赧扼緊了他的喉頭,「妳知道我是誰嗎?」
「您是我的主人,名字叫做奧圖.羅特費爾德。」她的聲音清晰而自然,只是有點低沉。
「沒錯。」他說,彷彿在跟小孩說話,「那妳知道妳是誰嗎?」
「我是一個魔像。」她頓了會,尋思片刻,「我沒有名字。」
「暫時沒有。」羅特費爾德說,微微一笑,「我會替妳取個名字。」
這時,他身子猛然一縮,魔像不必問,因為她也能感到自己腹中傳來同樣的悶痛。「您很痛苦。」她憂心忡忡地說。
「沒什麼。」羅特費爾德說,「妳先坐起來。」
她在木箱中坐了起來,環顧四周。油燈投出微弱的光影,隨著輪船的顛簸輕柔搖曳,長長的黑影在堆積如山的行李與箱子上吞吐伸縮。「我們在哪兒?」她問。
「船艙裡。我們現在正航行於海上。」羅特費爾德回答,「在前往美國的途中。但妳一定要非常小心,船上有許多人,如果發現妳的來歷,他們會非常恐懼,甚至可能會傷害妳。在我們上岸前,妳必須靜靜待在這箱子裡,不能發出一點聲音。」
這時候,船身劇烈傾斜,魔像緊緊抓住木箱邊緣。
「沒事的。」羅特費爾德輕聲安慰,顫巍巍地舉起手,撫摸她的髮絲,「和我在一起,妳很安全。」他說,「我的魔像。」
他陡然倒抽了口氣,頭一低,大口嘔吐。魔像焦急地看著。「您痛得更厲害了。」她說。
羅特費爾德咳了幾聲,用手背抹了抹嘴。「我說過了,」他說,「沒什麼,不打緊。」他試著站起,但搖晃一陣又跪倒在地。驚恐席捲而至,他開始領悟事情非常不對勁。
「幫幫我。」他低聲求助。
命令如離弦之箭射中魔像。她迅速在箱中起身,俯身抱起羅特費爾德,彷彿他不比一個小男孩重。她將主人抱在臂彎,穿過重重行李,爬上狹窄的階梯,離開底艙。
下等艙的盡頭起了一陣騷動,喧鬧向外蔓延,驚醒睡夢中的乘客。他們咕噥抱怨了幾聲,在床鋪上翻起身來。人群開始在艙門附近的一個床位聚集,一名男子癱倒床上,在油燈的映照下,面色如土。呼喊聲在一排又一排的床位間傳開:附近有沒有醫生?
不多久,一名醫生穿著睡衣和外套現身了。人群自動分開,讓他走到小床前。一名褐色洋裝的高䠷女子在病人身旁徘徊不去,睜大了眼,看著醫生解開年輕人的襯衫鈕釦,替他褪去上衣。醫生小心翼翼地觸診羅特費爾德腹部,病患發出淒厲的慘叫。
魔像立刻猛撲上前,扯開醫生的手臂。醫生駭然後退。
「不要緊。」床上的男人氣若游絲地說,「他是醫生,是來幫忙的。」他伸出手,覆在她手上。
醫生戰戰兢兢地再次摸向羅特費爾德腹部,一隻眼睛不忘緊盯那名女子。「是盲腸炎。」他宣布,「我們得立刻把他送去船醫那兒,現在。」
醫生抬起羅特費爾德的一隻胳膊,攙扶他站起。其他人趕緊上前幫忙,一群人就這麼架著半昏半醒的羅特費爾德穿過艙門,女子緊跟在後。
船醫不是那種喜歡三更半夜被吵醒的人,特別是要為了替下等艙某個不知名的鄉巴佬開膛破肚。他瞄了在手術檯上虛弱掙扎的男子一眼,思忖自己究竟該不該大費周章替他動手術。從病人病入膏肓的盲腸炎晚期症狀和高燒看來,他那根發炎的盲腸八成已經爆裂,帶著致命的毒素在腹腔內流竄。光是開腔手術八成就會要了他的命。放下病人後,將男子送來醫務室的異國群眾在艙門附近徘徊不去,不知所措,最後一句英文也沒留下便鳥獸散去。
好吧,不管怎樣,反正他非動手術不可。他大聲呼喚,叫醒助手,要他備妥手術器材。就在他尋找乙醚罐時,身後的艙門猛然打開。是個女人,一名身材高䠷的黑髮女子,在寒冷的大西洋上只穿著一件薄薄的褐色洋裝。她匆匆跑到手術檯邊,神情幾近驚恐。大概是他的妻子或情人,醫生心想。
「我想,要妳說英文大概太貪心了。」他說。想當然爾,對方只是瞪大了眼,一個字都不明白。「很抱歉,但妳不能待在這,手術過程禁止女性旁觀,恐怕妳必須離開。」他指向艙門。
這手勢起碼起了作用。她激烈搖頭,嘴裡吐出連珠砲似的意第緒語。「妳看看這裡。」醫生開口,搭在她手肘上,要領她出去。但他覺得自己彷彿抓到一根燈柱,女人不動如山,只是巍然站在他面前,猶如一面銅牆鐵壁,而且突然間顯得巨大無比,彷彿女武神顯靈。
他像摸到什麼燙手山芋般,急急放開她手臂。「隨便妳吧。」他尷尬地喃喃咕噥,忙著尋找那罐乙醚,試圖無視身後古怪的身影。
艙門再度打開,一名年輕人睡眼惺忪、跌跌撞撞地走了進來。「醫生,我──老天!」
「別管她。」醫生說,「她不肯離開,到時昏倒更好。動作快,否則等不及我們動手術,病人就要嚥氣了。」語畢,兩人協力麻醉患者,著手正事。
如果兩人知道身後那名女子的內心交戰有多激烈,肯定會立刻拋下手術,落荒而逃。換作其他沒有思考能力的魔像,只要看到手術刀劃開羅特費爾德的皮膚,一定會立刻撲上前,扼住他們脖子。但這尊魔像想起船艙中的醫生與主人的安慰,說他是來幫忙的,而且是醫生將主人帶來這裡。儘管如此,看見他們剝開羅特費爾德的皮膚,在他肚子裡東翻西找,垂在身旁兩側的雙手仍忍不住用力擰絞,捏緊了拳頭。她在腦中尋找,卻找不到任何主人的意識,感受不到任何需要或願望。她正一點一滴地失去他。
醫生從羅特費爾德體內拿出某樣東西,扔在托盤上。「好,這該死的玩意兒取出來了。」他說,回頭望向身後,「還站著?好女孩。」
「說不定是個白癡。」助手喃喃嘟噥。
「不見得,這些鄉巴佬的胃可都是鐵打的。賽門,鉗子夾好!」
「對不起。」
但手術檯上的病人已在垂死掙扎。他吸了口氣,又是一口,然後伴隨一聲粗嘎的長嘆,奧圖.羅特費爾德吐出最後一口氣息。
魔像感到自己與主人間的最後一絲連結猛然斷裂,消失不見,身子不由搖搖欲墜。
船醫低頭貼在羅特費爾德胸口,舉起患者手腕,量了一下脈搏,然後輕輕放下。「請宣布死亡時間。」他說。
助手嚥了口口水,看向航海鐘。「凌晨兩點四十八分。」
醫生記下死亡時間,臉上流露真誠的遺憾:「回天乏術,我們也無能為力。」他說,語調苦澀,「他拖太久了,之前一定痛苦了好多天。」
魔像無法將視線轉離手術檯上那具動也不動的軀體。不久前,他還是她的主人,她存在的理由,但現在,他卻什麼也不剩。她只覺得天旋地轉,彷彿無根的浮萍,恍恍惚惚地踏前一步,伸手觸摸他的面孔、鬆弛的下顎和垂掩的眼皮。她可以感覺他肌膚上的溫度已在消退。
求求你停止。
魔像收回她的手,望向身旁兩名駭然失色,一臉嫌惡的旁觀男子。他們誰也沒開口。
「我很遺憾。」船醫終於打破沉默,希望她聽得懂他的語調,「我們盡力了。」
「我知道。」魔像說,一開口,她才驚覺自己原來聽得懂男人的話,並用同樣的語言回答。
醫生皺起眉頭,和助手交換了個眼色。「這位女士,抱歉,請問尊夫貴姓大名?」
「羅特費爾德。」魔像回答,「奧圖.羅特費爾德。」
「羅特費爾德太太,節哀順變,或許──」
「你希望我離開。」她說。這並非出於猜測,也不是她突然領悟自己的逗留有多失禮與唐突。她就是知道,就像她能看見手術檯上的主人遺體,聞到乙醚刺鼻的氣味一般,清清楚楚,不會有錯。醫生的心願、希望她能離開這裡的期盼,她在腦中聽得再明白不過。
「嗯,是的,或許這樣比較好。」他說,「賽門,請帶羅特費爾德太太回下等艙。」
她任由年輕人挽住手臂,帶她離開手術室。她在發抖,有部分的她仍不停搜探,尋找羅特費爾德的意識。同時間,這名年輕助手的尷尬困窘、想要盡快擺脫她的心聲卻如烏雲般籠罩她的思緒。她是怎麼了?
到了下等艙門口,年輕人愧疚地捏了捏她的手,轉身離開。她該怎麼辦?回到船艙,面對那些乘客?她一手按在門閂,躊躇片刻,然後用力推開。
艙內五百名乘客的心聲和恐懼如猛烈的漩渦般襲來。
能睡著該有多好啊。拜託她不要再吐了。那個男人可以不要再打呼了嗎?我需要一杯水。我們還要多久才會到達紐約?船沉了怎麼辦?如果這裡只有我們兩個,就可以好好溫存一番。喔,老天爺啊,我好想回家。
魔像放開門閂,轉身就跑。
她回到上頭空無一人的主甲板,找到一張長椅,就這麼靜靜坐到天明。冰冷的雨滴開始灑落,打濕身上的洋裝,但她恍若未覺。除了腦中混亂的喧囂外,魔像完全無法集中思緒。彷彿少了羅特費爾德的命令指引,她的頭腦就不停到處尋找替代品,底下所有乘客的思緒因而一下蜂擁而入。缺少主人與魔像間的連結和制約,這些人的願望和恐懼並沒有指揮的效力──但她依舊能夠聽見、感受各種不同的焦急,而她的四肢也因想要回應的衝動陣陣抽搐。每一個念頭都彷彿一隻拉扯她衣袖的小手,哀求著:求求妳幫我。
翌晨,迎接輪船的是溫暖的天氣與歡欣鼓舞的景致:海天之間出現了一道細細的灰線。乘客紛紛走上甲板,凝視西方那條愈來愈粗、向著地平線延伸的灰線。這代表他們的願望全都得到了允諾,恐懼拋諸腦後,即便只是暫時的。底艙內,魔像感到一陣突如其來的安心喜悅。
推進器日以繼夜的隆隆運轉聲逐漸安靜下來,船速減慢,遠方傳來聲聲吶喊與歡呼。魔像按捺不了好奇,終於離開木箱,來到前甲板,走進正午的陽光下。
甲板上擠滿了人,起初,魔像不知道他們在對什麼瘋狂揮手。然後,她看見了:一名灰綠色的女子佇立海水中央,一手抱著書,一手高舉火炬。她雙眼眨也不眨,動也不動地站立原地。她也是魔像嗎?然後,視野清晰了,她這才察覺那名女子距離他們有多遠,而且身材有多高大。她沒有生命,但那雙空白而平滑的眼珠卻仍彷彿透著一抹理解。甲板上的人群興高采烈地對著她揮手吶喊,甚至又哭又笑。魔像心想,她也是人類創造出來的女人。無論她在其他人心中具有什麼樣的意義,都深受愛戴與尊敬。自從羅特費爾德死後,這是魔像心底首度湧現一種幾近希望的感受。
輪船的喇叭轟然大作,空氣也為之撼動。魔像轉身,準備回去底艙,但就在這時,她瞥見前方的城市。它巍峨矗立在島嶼邊緣,隨著輪船靠近,那些方方正正的高大建築似乎也不停移動交錯,一排又一排地隨著韻律起舞。她看見樹,看見碼頭,看見港灣內生氣蓬勃,小船、拖船與帆船如昆蟲般在水上飛掠而過。一座灰色的長橋懸浮於各種線條交織出來的巨網中央,往東延伸而去,通往海岸另一側。不曉得船會不會從橋下經過?魔像心想。但這艘巨大的輪船轉向西行,逐漸朝碼頭靠近。大海變成了一條窄河。
幾名制服男子在前甲板上來回逡巡,高聲呼喊著什麼。拿好隨身物品。他們說,我們很快就要停靠紐約,會有渡輪載你們前往埃利斯島。底艙的行李將直接到島上。直到訊息重複五、六遍後,魔像才發覺他們用了好幾種不同的語言宣布,而每一種她都聽得懂。
不出幾分鐘,甲板上便走得一個人也不剩。她退至舵手室的陰影下,試著集中思緒思考。除了別人給的那件外套外,她沒有任何行李。那件深色的羊毛外套在陽光下逐漸暖和,她摸向口袋,找到那只小皮囊。起碼她還有它。
稀疏的幾名乘客再度浮現舷梯,然後愈來愈多。每個人都換上旅行的裝束,手上提著包袱與行李。制服男子再度扯開嗓子高喊:排好隊,準備報上自己的姓名與國籍。不要推擠,不要擠成一團。看好自己的小孩。魔像遠遠站在一旁,不知所措。她該加入隊伍嗎?還是找個地方躲起來?眾人的思緒對她高聲疾呼,全都只想著趕快通過埃利斯島和檢查,拿到合格的健康證明書。
其中一名制服男子看見魔像獨自站在一旁,遲疑不決,便上前朝她走來。有名乘客攔下他,按住他肩頭,附在他耳邊說話。是下等艙的那位醫生。船員手上拿著一疊紙,翻了起來,似乎在尋找什麼,然後皺起眉頭,離開醫生。醫生的身影消失在隊伍後方。
「夫人。」那名船員呼喊,目光直視魔像的方向。「請來這裡一下。」魔像上前,周遭的人群靜了下來。「您就是那位丈夫病逝的遺孀,對嗎?」
「對。」
「節哀順變。但可能是我一時疏忽看漏了,名單上似乎沒有您的名字。我可以看看您的船票嗎?」
她的船票?不用說,她當然是沒什麼船票。她可以撒謊,說票不小心弄丟了,但她從來沒有說過謊,怕自己破綻百出。她知道自己只有兩條路可走,不是保持沉默,就是據實以告。
「我沒有船票。」她說,面帶微笑,希望會有幫助。
船員疲憊地嘆了口氣,按住魔像手臂,彷彿要防止她逃跑。「夫人,您必須和我來一趟。」
「你要帶我去哪?」
「您得先在警衛室稍坐片刻,等我們檢查完所有乘客後,有些問題必須請教您。」
她該怎麼做?只要回答他們的問題,她的來歷一定會曝光。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已集中在她身上。她提高戒備,在男人堅定的箍握下轉身,尋找逃脫的方向。輪船尚未靠岸,仍在河中央涉水前進,較小的船隻在兩側飛掠而過。繁忙的碼頭之後,城市閃耀著誘人的光芒。
船員加重手上的力道說:「夫人,別逼我動粗。」
但他不想動粗,她看得出來。他只想擺脫她;更有甚者,他希望她能自己消失。
魔像的嘴角揚起一抹微笑。終於,有個她能幫忙實現的願望。
她手肘一擰,掙開桎梏,留下震驚的船員,跑向欄杆。在任何人來得及出聲前,她便已躍過船緣,投向波光粼粼的哈德遜河,如石塊般沒入水中。
幾個鐘頭後,一名窩在西街與甘斯沃特街轉角抽菸的碼頭工人看見一名女子自河岸走來。她渾身濕透,穿著一件男人的羊毛外套和一件褐色洋裝。洋裝濕答答地貼在身上,曲線畢露,髮絲也一束束地黏在頸間。但最驚人的還是那厚厚一層透著鹹味、覆蓋在她裙襬與鞋子上的泥土。
「嘿,這位女士!」他高喊,「妳是去游泳了嗎?」
女人經過時,給了他一個古怪的微笑。「不。」她說,「我是用走的。」
2
在魔像上岸不遠處的曼哈頓下城,有個叫做小敘利亞的社區。那兒住著一名叫做布特羅斯.阿比利的錫匠。
阿比利的亡父來自一個擁有五名兄弟手足的家庭,一代代過去,土地也一次次分產,直到每個兄弟繼承的地小到不值得費力耕種。做為錫匠的學徒,阿比利只能給自己掙得微薄的收入。儘管母親與姊妹也養蠶貼補家用,但仍入不敷出。在這股移民潮中,阿比利看見了自己的機會。他揮別家人,登上一艘前往紐約的蒸汽船,很快就在日漸興盛的小敘利亞中央的華盛頓街上租了間小小的打鐵舖。
阿比利是個善良勤勉、老實無欺的錫匠,即便在紐約如此飽和的市場中,他的東西仍是物超所值。他的製品包括各種杯碗瓢盆、家庭工具、裁縫頂針、燭臺等等,有時鄰居還會帶東西來請他修理,像是壞掉的鍋子或扭曲變形的門栓和鉸鍊,而經過他的巧手修復後,東西甚至會變得比新的還好。
這年夏天,阿比利接了件有趣的單子。一名叫做瑪莉安.法度的少婦帶著一只古老破舊,但外觀精美的銅壺來到鋪子。打從瑪莉安有記憶以來,這只銅壺就在自己家裡了。在她準備遠渡重洋,出發前往美國時,母親將這只用來裝橄欖油的銅壺送給了她。「讓妳身邊永遠有家鄉相伴。」她母親這麼說。
瑪莉安與丈夫薩伊一起在華盛頓街上開了家咖啡館,那兒很快就變成小敘利亞繁忙熱鬧的核心樞紐。某天午後,就在瑪莉安打量忙碌的廚房時,心裡突然決定,那只銅壺美歸美,但實在太過坑坑疤疤,而且磨損嚴重。她問阿比利是不是有可能把銅壺上的凹陷修補得平整些?或許再讓它恢復往日的光澤?
阿比利獨自坐在店裡,仔細檢查那銅壺。銅壺約莫九吋高,圓球般的壺身愈往上愈窄縮,最後化為細長的壺頸。打造它的工匠用精巧異常的渦漩紋飾裝飾壺身,不同於一般常見的重複花紋,那些盤旋彎曲的線條似乎是隨意交纏,最後又頭尾相連。
阿比利將手中的銅壺翻來覆去,看入了迷。銅壺顯然十分古老,歷史甚至可能比瑪莉安與她母親所知的還要久遠。由於質地柔軟,現在已經鮮少有人單獨使用紅銅製作器皿,黃銅和錫都比較耐用,而且便於鍛造。事實上,依據銅壺可能的年紀來看,它可說是保存得相當良好,沒有應有的陳舊。他沒有任何線索可判斷銅壺的出處,底部沒有鑄造者的印記,也找不到任何可辨識的記號。
他仔細察看渦紋上的嚴重凹陷,發現若要修補,一定會在新工與舊工的交界處留下明顯的接痕。所以他決定先將表面磨平,修補好壺身後再重新鑄刻渦紋。
他在壺底四周包上一層薄薄的牛皮紙,找到一截炭筆,拓下渦紋的圖樣,仔細捕捉工匠的鬼斧神工。然後用虎頭鉗牢牢固定好銅壺,從爐火中抄來一把最小的烙鐵頭。
就在他佇立原地,烙鐵穩穩地停在銅壺上方時,心底突然湧現一股古怪的預感,雞皮疙瘩爬滿雙臂和背心。阿比利顫巍巍地放下烙鐵,深呼吸了口氣。他有什麼好煩心的呢?天氣和煦,他享用了一頓豐盛的早餐,而且身強體壯,生意興隆。他搖了搖頭,再度拿起烙鐵,壓在壺身的花紋上,抹去其中一道渦紋。
一股強烈的戰慄將他震開了去,阿比利覺得自己像被雷劈中一般,凌空飛起,摔在工作檯旁的一堆器具上。他嚇得腦筋一片空白,耳鳴大作,翻身環顧四周。
一名渾身赤裸的男子躺在他店裡的地板上。
正當阿比利瞠目結舌,傻傻愣在原地時,那名男子坐了起來,雙掌掩面,但隨後又垂下手臂,環顧四周,雙眼圓睜,彷彿燒著熊熊烈火。他看起來就像是長年囚禁在天底下最深、最暗的地牢,此刻被粗暴地拖進陽光底下。
男人搖搖晃晃地踉蹌站起,他身材高䠷,強壯結實,五官英挺;實際上,是英俊過了頭──他的面孔完美到給人一種異樣感,彷彿是從畫裡走出的翩翩美男。他理著一頭短短的黑髮,似乎對自己的赤裸毫無所覺。
男人的右手腕上銬著一只粗寬的金屬手銬,他和阿比利同時發現它的存在,他立刻舉起右手,駭然瞪著手銬。「是鐵!」他驚呼,隨後又說,「但這不可能啊。」
終於,男人的視線落到阿比利身上,他仍伏在工作檯旁,嚇得連大氣都不敢喘上一口。
男人身影陡然一晃,勢若猛禽地朝阿比利直撲而下,一把揪住他脖子,將他高高拎在空中。一股深紅色的霧靄遮蔽阿比利的視線,他感覺自己的腦袋頂到天花板。
「他在哪?」男人怒吼。
「誰?」阿比利大口喘息著問。
「那個巫師!」
阿比利想要回答,但只能發出模糊難辨的咕噥。裸身男子又是一聲咆哮,將阿比利摔回地上。阿比利大口喘息,左右張望,想要尋找武器──任何可以防身的東西都好。然後他看見那把躺在舊布上、仍兀自冒著裊裊輕煙的烙鐵,立刻抄起握把,朝男子撲去。
眼前一花──阿比利又仆倒地上。這一次,烙鐵彎曲的握把抵在他喉前的凹陷處。男子單膝跪在他身前,手裡握著通紅熾熱的烙鐵尖端,但阿比利沒有聞到任何燒焦的皮肉味,男人甚至連眉頭也沒皺一下。阿比利魂飛魄散地瞪著眼前這張過分完美的面孔,感到喉前冰冷的握把開始有了溫度,而且愈來愈熱、愈來愈燙──好像那男子不知正用什麼方法燒熱那柄烙鐵般。
阿比利心想:這實在是……實在是不可能啊!
「告訴我巫師在哪。」男人說,「我要去宰了他。」
阿比利目瞪口呆地看著他。
「他把我困在人類的軀體裡!告訴我他在哪!」
錫匠心念電轉,他垂眼看向那只仍騰騰冒煙的烙鐵,想起自己要將它按上銅壺前感到的那股詭異預感。他想起祖母說過的故事,只要有關壺瓶與油燈,裡頭一定有生靈囚禁在內。
不,這太荒謬了。那些都只是神話傳說。若非如此,唯一的可能就是他瘋了。
「這位大爺,」他低聲問,「請問你是精靈嗎?」
男人緊抿雙脣,眼裡多了防備,但並沒有奚落阿比利,或開口斥責他腦袋有問題。
「你是。」阿比利說,「天啊,你真的是。」他嚥了口口水,感到烙鐵抵在喉間的壓力,不由微微一縮。「求求你,無論那巫師究竟是誰,我真的不認識他。老實說,我懷疑這世上還有沒有巫師。」他頓了會兒,又說,「你可能已經在那壺裡待很久了。」
男人似乎聽了進去,烙鐵緩緩離開錫匠的喉頭。他佇立原地,轉身四顧,彷彿首次察覺這間店鋪的存在。街上的擾攘從高窗傳了進來:馬車的車轆聲、報童的叫賣聲,還有哈德遜河上輪船悠長低沉的汽笛聲。
「這裡是什麼地方?」男人問。
「我的打鐵鋪。」阿比利回答,「位於紐約。」他努力保持冷靜的語調,「在一個叫做美國的國家。」
男人走到阿比利的工作檯前,拿起其中一根又長又細的烙鐵,抓在手裡,臉上流露驚恐又著迷的神色。
「這是真的,」男人說,「這一切都是真的。」
「是的,」阿比利回答,「恐怕是。」
男人放下烙鐵,下頷肌肉陣陣抽搐,彷彿準備迎接最糟的情況。
「帶我四處看看。」他最後終於開口。
魔像的生命始於一艘輪船的船艙之中。時間是一八九九年,船名為波羅的海號,自但澤啟航前往紐約。魔像的主人是一名叫奧圖.羅特費爾德的男子,他悄悄將裝著魔像的貨箱偷渡上船,藏在眾多乘客的行李之間。
羅特費爾德出發前往但澤碼頭的前一晚,任務終於完成。他駕著一輛馬車,載著一只大木箱、一件端莊的棕色洋裝和一雙女鞋,最後一次來到術士夏滿的小屋。
夏滿似乎已經多日無眠,眼眶發黑,臉色蒼白,彷彿精力被榨乾了。他點亮工作檯上的燈,羅特費爾德終於得以仔細端詳他要求的成品。
女子身材高䠷,幾乎和羅特費爾德自己一樣高,比例勻稱、軀幹纖長、雙乳小巧而堅挺,腰枝結實。臀部或許有些過於方正,但在她身上顯得很是合稱,甚至誘人。藉著昏暗的燈光,他偷偷瞄向她雙腿間的陰影,但一察覺夏滿譏諷的目光與自己奔騰的血液,又立刻轉開視線,表現出興趣缺缺的模樣。
她有著一張心型的寬闊臉孔,眼距甚開的雙眼緊閉,看不出眼珠顏色。鼻梁小巧玲瓏,鼻尖在豐潤的雙脣上方微微下彎,一頭微捲的褐髮被剪到約莫及肩的長度。
他試探地伸出手,半信半疑地摸向她冰涼的肩頭:「看起來好像是真的皮膚;摸起來也是。」
「是泥土。」老人說。
「你是怎麼辦到的?」
老人只是笑而不答。
「還有她的頭髮、眼珠?她的指甲呢?也都是用泥土做的?」
「不,那些全是如假包換的真貨。」夏滿若無其事地回答。羅特費爾德想起自己交給老人的那箱錢,猜想他都拿去買了什麼樣的材料。他打了個哆嗦,決定從此還是別再琢磨這事比較好。
兩人替泥像穿好衣服,小心翼翼地將她沉重的身軀搬進木箱。放置時,泥像的頭髮散落臉前,羅特費爾德等到老人轉過身後,才溫柔地幫她撥開髮絲,撥理整齊。
夏滿找到一小張紙片,在上頭寫下兩個重要的指令──一個喚醒她,一個摧毀她。他將紙片對摺再對摺,放進一枚油布信封,並在信封上寫下「魔像控制咒語」六個字,交給羅特費爾德。他的委託人急於喚醒魔像,但老人勸阻他:「她需要時間適應。」他說,「但船上過於擁擠,假若給旁人發現她真正的身分,你們兩個都會被扔下船。」聽了老人這麼說,羅特費爾德也只能不情不願地答應等抵達美國後再喚醒魔像。最後兩人釘上箱蓋,將她密密嚴嚴藏在箱中。
老人拿出一只蒙塵的酒瓶,替兩人各倒了一指高的烈酒:「敬魔像。」他說,舉起酒杯。
「敬魔像。」羅特費爾德跟著說,接著一口喝乾。這確實是個值得慶祝的勝利時刻,唯一掃興的是這段時間以來一直跟他苦苦糾纏的腹痛。他的身體向來敏感,而過去幾週來的壓力徹底擾亂了他的消化系統。他無視腹中的疼痛,協助老人將木箱搬上馬車,絕塵而去。老人揮手送別羅特費爾德遠去的背影,彷彿目送一對新婚燕爾的夫婦離去。「祝你們小倆口幸福快樂。」他高聲呼喚,笑聲兀自在樹林間迴盪。
輪船自但澤啟航,一帆風順地抵達中途的停靠站:漢堡。兩晚後,羅特費爾德躺在他狹窄的床位上,那枚寫著「魔像控制咒語」的油布信封塞在口袋深處。他覺得自己就像個收到禮物,卻又被叮囑不准打開的小孩。如果他睡得著,或許就不會如此心癢難耐,但他的腹痛已經轉變成為右腹裡的痛苦折磨。他覺得自己有點發燒,四周又緊緊環繞著下等艙的吵鬧:各種形形色色的鼾聲、小嬰兒抽抽搭搭的嗚咽,還有偶爾伴隨輪船劇烈顛簸而來的嘔吐聲。
他輾轉反側,痛得在床上打滾,心忖:不用說,那老頭肯定是謹慎過頭。如果她真如承諾中的順從,那純粹喚醒她又會有什麼危險?喚醒後,他大可命令她躺在木箱,直到輪船抵達美國後再現身。
但如果有問題怎麼辦?如果她根本無法喚醒怎麼辦?只是動也不動躺在那兒,一座徒具女人樣貌的泥像?這是他第一次醒悟,自己從沒見過任何能證明夏滿能如實履約的證據。驚慌之下,他匆匆從口袋掏出信封,拿出那張紙片,卻赫然驚見一堆胡言亂語、毫無意義的希伯來文!他太愚蠢了!
他猛然起身,從掛釘上拿下油燈,一手壓著右腹,匆匆穿過迷宮般的床鋪,沿著舷梯來到底艙。
將近兩個鐘頭後,他終於找到木箱。兩個小時以來,他在堆積如山的行李箱和用麻繩綑綁的箱子間鑽進鑽出,肚子裡彷彿有火在燒,大顆大顆的冷汗滲進眼裡。終於,他搬開一捆捲起的地毯,找到了:他的木箱,他的新娘。
他找到一把鐵撬,撬開箱上的釘子,粗魯推開箱蓋。他的心臟噗通狂跳,拿出口袋中的紙片,小心翼翼唸出喚醒魔像的咒語。
然後屏息以待。
緩緩地,魔像甦醒。
最先甦醒的是她的感官。她可以感到指尖下粗糙的木頭與肌膚上冰冷潮濕的空氣,感到輪船行進時的移動,聞到霉味和刺鼻的海水味。
她又甦醒了些,明白自己有個身體。那摸著木頭的指尖是她的指尖,感到冰涼空氣的肌膚是她的肌膚。她動了動手指,想知道自己做不做得到。
她聽見身旁傳來男人的氣息。她知道他的名字,也知道他是誰。他是她的主人、她存在的目的。她是他的魔像,一舉一動都受他的意志所操控,而現在,他想要她睜開雙眼。
魔像睜開雙眼。
昏暗的燈光中,她看見主人跪在身旁,臉孔與頭髮都被汗水浸濕了。他一手撐在木箱邊緣,另一手緊緊壓在腹部。
「哈囉,」羅特費爾德輕聲說,一陣荒謬的羞赧扼緊了他的喉頭,「妳知道我是誰嗎?」
「您是我的主人,名字叫做奧圖.羅特費爾德。」她的聲音清晰而自然,只是有點低沉。
「沒錯。」他說,彷彿在跟小孩說話,「那妳知道妳是誰嗎?」
「我是一個魔像。」她頓了會,尋思片刻,「我沒有名字。」
「暫時沒有。」羅特費爾德說,微微一笑,「我會替妳取個名字。」
這時,他身子猛然一縮,魔像不必問,因為她也能感到自己腹中傳來同樣的悶痛。「您很痛苦。」她憂心忡忡地說。
「沒什麼。」羅特費爾德說,「妳先坐起來。」
她在木箱中坐了起來,環顧四周。油燈投出微弱的光影,隨著輪船的顛簸輕柔搖曳,長長的黑影在堆積如山的行李與箱子上吞吐伸縮。「我們在哪兒?」她問。
「船艙裡。我們現在正航行於海上。」羅特費爾德回答,「在前往美國的途中。但妳一定要非常小心,船上有許多人,如果發現妳的來歷,他們會非常恐懼,甚至可能會傷害妳。在我們上岸前,妳必須靜靜待在這箱子裡,不能發出一點聲音。」
這時候,船身劇烈傾斜,魔像緊緊抓住木箱邊緣。
「沒事的。」羅特費爾德輕聲安慰,顫巍巍地舉起手,撫摸她的髮絲,「和我在一起,妳很安全。」他說,「我的魔像。」
他陡然倒抽了口氣,頭一低,大口嘔吐。魔像焦急地看著。「您痛得更厲害了。」她說。
羅特費爾德咳了幾聲,用手背抹了抹嘴。「我說過了,」他說,「沒什麼,不打緊。」他試著站起,但搖晃一陣又跪倒在地。驚恐席捲而至,他開始領悟事情非常不對勁。
「幫幫我。」他低聲求助。
命令如離弦之箭射中魔像。她迅速在箱中起身,俯身抱起羅特費爾德,彷彿他不比一個小男孩重。她將主人抱在臂彎,穿過重重行李,爬上狹窄的階梯,離開底艙。
下等艙的盡頭起了一陣騷動,喧鬧向外蔓延,驚醒睡夢中的乘客。他們咕噥抱怨了幾聲,在床鋪上翻起身來。人群開始在艙門附近的一個床位聚集,一名男子癱倒床上,在油燈的映照下,面色如土。呼喊聲在一排又一排的床位間傳開:附近有沒有醫生?
不多久,一名醫生穿著睡衣和外套現身了。人群自動分開,讓他走到小床前。一名褐色洋裝的高䠷女子在病人身旁徘徊不去,睜大了眼,看著醫生解開年輕人的襯衫鈕釦,替他褪去上衣。醫生小心翼翼地觸診羅特費爾德腹部,病患發出淒厲的慘叫。
魔像立刻猛撲上前,扯開醫生的手臂。醫生駭然後退。
「不要緊。」床上的男人氣若游絲地說,「他是醫生,是來幫忙的。」他伸出手,覆在她手上。
醫生戰戰兢兢地再次摸向羅特費爾德腹部,一隻眼睛不忘緊盯那名女子。「是盲腸炎。」他宣布,「我們得立刻把他送去船醫那兒,現在。」
醫生抬起羅特費爾德的一隻胳膊,攙扶他站起。其他人趕緊上前幫忙,一群人就這麼架著半昏半醒的羅特費爾德穿過艙門,女子緊跟在後。
船醫不是那種喜歡三更半夜被吵醒的人,特別是要為了替下等艙某個不知名的鄉巴佬開膛破肚。他瞄了在手術檯上虛弱掙扎的男子一眼,思忖自己究竟該不該大費周章替他動手術。從病人病入膏肓的盲腸炎晚期症狀和高燒看來,他那根發炎的盲腸八成已經爆裂,帶著致命的毒素在腹腔內流竄。光是開腔手術八成就會要了他的命。放下病人後,將男子送來醫務室的異國群眾在艙門附近徘徊不去,不知所措,最後一句英文也沒留下便鳥獸散去。
好吧,不管怎樣,反正他非動手術不可。他大聲呼喚,叫醒助手,要他備妥手術器材。就在他尋找乙醚罐時,身後的艙門猛然打開。是個女人,一名身材高䠷的黑髮女子,在寒冷的大西洋上只穿著一件薄薄的褐色洋裝。她匆匆跑到手術檯邊,神情幾近驚恐。大概是他的妻子或情人,醫生心想。
「我想,要妳說英文大概太貪心了。」他說。想當然爾,對方只是瞪大了眼,一個字都不明白。「很抱歉,但妳不能待在這,手術過程禁止女性旁觀,恐怕妳必須離開。」他指向艙門。
這手勢起碼起了作用。她激烈搖頭,嘴裡吐出連珠砲似的意第緒語。「妳看看這裡。」醫生開口,搭在她手肘上,要領她出去。但他覺得自己彷彿抓到一根燈柱,女人不動如山,只是巍然站在他面前,猶如一面銅牆鐵壁,而且突然間顯得巨大無比,彷彿女武神顯靈。
他像摸到什麼燙手山芋般,急急放開她手臂。「隨便妳吧。」他尷尬地喃喃咕噥,忙著尋找那罐乙醚,試圖無視身後古怪的身影。
艙門再度打開,一名年輕人睡眼惺忪、跌跌撞撞地走了進來。「醫生,我──老天!」
「別管她。」醫生說,「她不肯離開,到時昏倒更好。動作快,否則等不及我們動手術,病人就要嚥氣了。」語畢,兩人協力麻醉患者,著手正事。
如果兩人知道身後那名女子的內心交戰有多激烈,肯定會立刻拋下手術,落荒而逃。換作其他沒有思考能力的魔像,只要看到手術刀劃開羅特費爾德的皮膚,一定會立刻撲上前,扼住他們脖子。但這尊魔像想起船艙中的醫生與主人的安慰,說他是來幫忙的,而且是醫生將主人帶來這裡。儘管如此,看見他們剝開羅特費爾德的皮膚,在他肚子裡東翻西找,垂在身旁兩側的雙手仍忍不住用力擰絞,捏緊了拳頭。她在腦中尋找,卻找不到任何主人的意識,感受不到任何需要或願望。她正一點一滴地失去他。
醫生從羅特費爾德體內拿出某樣東西,扔在托盤上。「好,這該死的玩意兒取出來了。」他說,回頭望向身後,「還站著?好女孩。」
「說不定是個白癡。」助手喃喃嘟噥。
「不見得,這些鄉巴佬的胃可都是鐵打的。賽門,鉗子夾好!」
「對不起。」
但手術檯上的病人已在垂死掙扎。他吸了口氣,又是一口,然後伴隨一聲粗嘎的長嘆,奧圖.羅特費爾德吐出最後一口氣息。
魔像感到自己與主人間的最後一絲連結猛然斷裂,消失不見,身子不由搖搖欲墜。
船醫低頭貼在羅特費爾德胸口,舉起患者手腕,量了一下脈搏,然後輕輕放下。「請宣布死亡時間。」他說。
助手嚥了口口水,看向航海鐘。「凌晨兩點四十八分。」
醫生記下死亡時間,臉上流露真誠的遺憾:「回天乏術,我們也無能為力。」他說,語調苦澀,「他拖太久了,之前一定痛苦了好多天。」
魔像無法將視線轉離手術檯上那具動也不動的軀體。不久前,他還是她的主人,她存在的理由,但現在,他卻什麼也不剩。她只覺得天旋地轉,彷彿無根的浮萍,恍恍惚惚地踏前一步,伸手觸摸他的面孔、鬆弛的下顎和垂掩的眼皮。她可以感覺他肌膚上的溫度已在消退。
求求你停止。
魔像收回她的手,望向身旁兩名駭然失色,一臉嫌惡的旁觀男子。他們誰也沒開口。
「我很遺憾。」船醫終於打破沉默,希望她聽得懂他的語調,「我們盡力了。」
「我知道。」魔像說,一開口,她才驚覺自己原來聽得懂男人的話,並用同樣的語言回答。
醫生皺起眉頭,和助手交換了個眼色。「這位女士,抱歉,請問尊夫貴姓大名?」
「羅特費爾德。」魔像回答,「奧圖.羅特費爾德。」
「羅特費爾德太太,節哀順變,或許──」
「你希望我離開。」她說。這並非出於猜測,也不是她突然領悟自己的逗留有多失禮與唐突。她就是知道,就像她能看見手術檯上的主人遺體,聞到乙醚刺鼻的氣味一般,清清楚楚,不會有錯。醫生的心願、希望她能離開這裡的期盼,她在腦中聽得再明白不過。
「嗯,是的,或許這樣比較好。」他說,「賽門,請帶羅特費爾德太太回下等艙。」
她任由年輕人挽住手臂,帶她離開手術室。她在發抖,有部分的她仍不停搜探,尋找羅特費爾德的意識。同時間,這名年輕助手的尷尬困窘、想要盡快擺脫她的心聲卻如烏雲般籠罩她的思緒。她是怎麼了?
到了下等艙門口,年輕人愧疚地捏了捏她的手,轉身離開。她該怎麼辦?回到船艙,面對那些乘客?她一手按在門閂,躊躇片刻,然後用力推開。
艙內五百名乘客的心聲和恐懼如猛烈的漩渦般襲來。
能睡著該有多好啊。拜託她不要再吐了。那個男人可以不要再打呼了嗎?我需要一杯水。我們還要多久才會到達紐約?船沉了怎麼辦?如果這裡只有我們兩個,就可以好好溫存一番。喔,老天爺啊,我好想回家。
魔像放開門閂,轉身就跑。
她回到上頭空無一人的主甲板,找到一張長椅,就這麼靜靜坐到天明。冰冷的雨滴開始灑落,打濕身上的洋裝,但她恍若未覺。除了腦中混亂的喧囂外,魔像完全無法集中思緒。彷彿少了羅特費爾德的命令指引,她的頭腦就不停到處尋找替代品,底下所有乘客的思緒因而一下蜂擁而入。缺少主人與魔像間的連結和制約,這些人的願望和恐懼並沒有指揮的效力──但她依舊能夠聽見、感受各種不同的焦急,而她的四肢也因想要回應的衝動陣陣抽搐。每一個念頭都彷彿一隻拉扯她衣袖的小手,哀求著:求求妳幫我。
翌晨,迎接輪船的是溫暖的天氣與歡欣鼓舞的景致:海天之間出現了一道細細的灰線。乘客紛紛走上甲板,凝視西方那條愈來愈粗、向著地平線延伸的灰線。這代表他們的願望全都得到了允諾,恐懼拋諸腦後,即便只是暫時的。底艙內,魔像感到一陣突如其來的安心喜悅。
推進器日以繼夜的隆隆運轉聲逐漸安靜下來,船速減慢,遠方傳來聲聲吶喊與歡呼。魔像按捺不了好奇,終於離開木箱,來到前甲板,走進正午的陽光下。
甲板上擠滿了人,起初,魔像不知道他們在對什麼瘋狂揮手。然後,她看見了:一名灰綠色的女子佇立海水中央,一手抱著書,一手高舉火炬。她雙眼眨也不眨,動也不動地站立原地。她也是魔像嗎?然後,視野清晰了,她這才察覺那名女子距離他們有多遠,而且身材有多高大。她沒有生命,但那雙空白而平滑的眼珠卻仍彷彿透著一抹理解。甲板上的人群興高采烈地對著她揮手吶喊,甚至又哭又笑。魔像心想,她也是人類創造出來的女人。無論她在其他人心中具有什麼樣的意義,都深受愛戴與尊敬。自從羅特費爾德死後,這是魔像心底首度湧現一種幾近希望的感受。
輪船的喇叭轟然大作,空氣也為之撼動。魔像轉身,準備回去底艙,但就在這時,她瞥見前方的城市。它巍峨矗立在島嶼邊緣,隨著輪船靠近,那些方方正正的高大建築似乎也不停移動交錯,一排又一排地隨著韻律起舞。她看見樹,看見碼頭,看見港灣內生氣蓬勃,小船、拖船與帆船如昆蟲般在水上飛掠而過。一座灰色的長橋懸浮於各種線條交織出來的巨網中央,往東延伸而去,通往海岸另一側。不曉得船會不會從橋下經過?魔像心想。但這艘巨大的輪船轉向西行,逐漸朝碼頭靠近。大海變成了一條窄河。
幾名制服男子在前甲板上來回逡巡,高聲呼喊著什麼。拿好隨身物品。他們說,我們很快就要停靠紐約,會有渡輪載你們前往埃利斯島。底艙的行李將直接到島上。直到訊息重複五、六遍後,魔像才發覺他們用了好幾種不同的語言宣布,而每一種她都聽得懂。
不出幾分鐘,甲板上便走得一個人也不剩。她退至舵手室的陰影下,試著集中思緒思考。除了別人給的那件外套外,她沒有任何行李。那件深色的羊毛外套在陽光下逐漸暖和,她摸向口袋,找到那只小皮囊。起碼她還有它。
稀疏的幾名乘客再度浮現舷梯,然後愈來愈多。每個人都換上旅行的裝束,手上提著包袱與行李。制服男子再度扯開嗓子高喊:排好隊,準備報上自己的姓名與國籍。不要推擠,不要擠成一團。看好自己的小孩。魔像遠遠站在一旁,不知所措。她該加入隊伍嗎?還是找個地方躲起來?眾人的思緒對她高聲疾呼,全都只想著趕快通過埃利斯島和檢查,拿到合格的健康證明書。
其中一名制服男子看見魔像獨自站在一旁,遲疑不決,便上前朝她走來。有名乘客攔下他,按住他肩頭,附在他耳邊說話。是下等艙的那位醫生。船員手上拿著一疊紙,翻了起來,似乎在尋找什麼,然後皺起眉頭,離開醫生。醫生的身影消失在隊伍後方。
「夫人。」那名船員呼喊,目光直視魔像的方向。「請來這裡一下。」魔像上前,周遭的人群靜了下來。「您就是那位丈夫病逝的遺孀,對嗎?」
「對。」
「節哀順變。但可能是我一時疏忽看漏了,名單上似乎沒有您的名字。我可以看看您的船票嗎?」
她的船票?不用說,她當然是沒什麼船票。她可以撒謊,說票不小心弄丟了,但她從來沒有說過謊,怕自己破綻百出。她知道自己只有兩條路可走,不是保持沉默,就是據實以告。
「我沒有船票。」她說,面帶微笑,希望會有幫助。
船員疲憊地嘆了口氣,按住魔像手臂,彷彿要防止她逃跑。「夫人,您必須和我來一趟。」
「你要帶我去哪?」
「您得先在警衛室稍坐片刻,等我們檢查完所有乘客後,有些問題必須請教您。」
她該怎麼做?只要回答他們的問題,她的來歷一定會曝光。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已集中在她身上。她提高戒備,在男人堅定的箍握下轉身,尋找逃脫的方向。輪船尚未靠岸,仍在河中央涉水前進,較小的船隻在兩側飛掠而過。繁忙的碼頭之後,城市閃耀著誘人的光芒。
船員加重手上的力道說:「夫人,別逼我動粗。」
但他不想動粗,她看得出來。他只想擺脫她;更有甚者,他希望她能自己消失。
魔像的嘴角揚起一抹微笑。終於,有個她能幫忙實現的願望。
她手肘一擰,掙開桎梏,留下震驚的船員,跑向欄杆。在任何人來得及出聲前,她便已躍過船緣,投向波光粼粼的哈德遜河,如石塊般沒入水中。
幾個鐘頭後,一名窩在西街與甘斯沃特街轉角抽菸的碼頭工人看見一名女子自河岸走來。她渾身濕透,穿著一件男人的羊毛外套和一件褐色洋裝。洋裝濕答答地貼在身上,曲線畢露,髮絲也一束束地黏在頸間。但最驚人的還是那厚厚一層透著鹹味、覆蓋在她裙襬與鞋子上的泥土。
「嘿,這位女士!」他高喊,「妳是去游泳了嗎?」
女人經過時,給了他一個古怪的微笑。「不。」她說,「我是用走的。」
2
在魔像上岸不遠處的曼哈頓下城,有個叫做小敘利亞的社區。那兒住著一名叫做布特羅斯.阿比利的錫匠。
阿比利的亡父來自一個擁有五名兄弟手足的家庭,一代代過去,土地也一次次分產,直到每個兄弟繼承的地小到不值得費力耕種。做為錫匠的學徒,阿比利只能給自己掙得微薄的收入。儘管母親與姊妹也養蠶貼補家用,但仍入不敷出。在這股移民潮中,阿比利看見了自己的機會。他揮別家人,登上一艘前往紐約的蒸汽船,很快就在日漸興盛的小敘利亞中央的華盛頓街上租了間小小的打鐵舖。
阿比利是個善良勤勉、老實無欺的錫匠,即便在紐約如此飽和的市場中,他的東西仍是物超所值。他的製品包括各種杯碗瓢盆、家庭工具、裁縫頂針、燭臺等等,有時鄰居還會帶東西來請他修理,像是壞掉的鍋子或扭曲變形的門栓和鉸鍊,而經過他的巧手修復後,東西甚至會變得比新的還好。
這年夏天,阿比利接了件有趣的單子。一名叫做瑪莉安.法度的少婦帶著一只古老破舊,但外觀精美的銅壺來到鋪子。打從瑪莉安有記憶以來,這只銅壺就在自己家裡了。在她準備遠渡重洋,出發前往美國時,母親將這只用來裝橄欖油的銅壺送給了她。「讓妳身邊永遠有家鄉相伴。」她母親這麼說。
瑪莉安與丈夫薩伊一起在華盛頓街上開了家咖啡館,那兒很快就變成小敘利亞繁忙熱鬧的核心樞紐。某天午後,就在瑪莉安打量忙碌的廚房時,心裡突然決定,那只銅壺美歸美,但實在太過坑坑疤疤,而且磨損嚴重。她問阿比利是不是有可能把銅壺上的凹陷修補得平整些?或許再讓它恢復往日的光澤?
阿比利獨自坐在店裡,仔細檢查那銅壺。銅壺約莫九吋高,圓球般的壺身愈往上愈窄縮,最後化為細長的壺頸。打造它的工匠用精巧異常的渦漩紋飾裝飾壺身,不同於一般常見的重複花紋,那些盤旋彎曲的線條似乎是隨意交纏,最後又頭尾相連。
阿比利將手中的銅壺翻來覆去,看入了迷。銅壺顯然十分古老,歷史甚至可能比瑪莉安與她母親所知的還要久遠。由於質地柔軟,現在已經鮮少有人單獨使用紅銅製作器皿,黃銅和錫都比較耐用,而且便於鍛造。事實上,依據銅壺可能的年紀來看,它可說是保存得相當良好,沒有應有的陳舊。他沒有任何線索可判斷銅壺的出處,底部沒有鑄造者的印記,也找不到任何可辨識的記號。
他仔細察看渦紋上的嚴重凹陷,發現若要修補,一定會在新工與舊工的交界處留下明顯的接痕。所以他決定先將表面磨平,修補好壺身後再重新鑄刻渦紋。
他在壺底四周包上一層薄薄的牛皮紙,找到一截炭筆,拓下渦紋的圖樣,仔細捕捉工匠的鬼斧神工。然後用虎頭鉗牢牢固定好銅壺,從爐火中抄來一把最小的烙鐵頭。
就在他佇立原地,烙鐵穩穩地停在銅壺上方時,心底突然湧現一股古怪的預感,雞皮疙瘩爬滿雙臂和背心。阿比利顫巍巍地放下烙鐵,深呼吸了口氣。他有什麼好煩心的呢?天氣和煦,他享用了一頓豐盛的早餐,而且身強體壯,生意興隆。他搖了搖頭,再度拿起烙鐵,壓在壺身的花紋上,抹去其中一道渦紋。
一股強烈的戰慄將他震開了去,阿比利覺得自己像被雷劈中一般,凌空飛起,摔在工作檯旁的一堆器具上。他嚇得腦筋一片空白,耳鳴大作,翻身環顧四周。
一名渾身赤裸的男子躺在他店裡的地板上。
正當阿比利瞠目結舌,傻傻愣在原地時,那名男子坐了起來,雙掌掩面,但隨後又垂下手臂,環顧四周,雙眼圓睜,彷彿燒著熊熊烈火。他看起來就像是長年囚禁在天底下最深、最暗的地牢,此刻被粗暴地拖進陽光底下。
男人搖搖晃晃地踉蹌站起,他身材高䠷,強壯結實,五官英挺;實際上,是英俊過了頭──他的面孔完美到給人一種異樣感,彷彿是從畫裡走出的翩翩美男。他理著一頭短短的黑髮,似乎對自己的赤裸毫無所覺。
男人的右手腕上銬著一只粗寬的金屬手銬,他和阿比利同時發現它的存在,他立刻舉起右手,駭然瞪著手銬。「是鐵!」他驚呼,隨後又說,「但這不可能啊。」
終於,男人的視線落到阿比利身上,他仍伏在工作檯旁,嚇得連大氣都不敢喘上一口。
男人身影陡然一晃,勢若猛禽地朝阿比利直撲而下,一把揪住他脖子,將他高高拎在空中。一股深紅色的霧靄遮蔽阿比利的視線,他感覺自己的腦袋頂到天花板。
「他在哪?」男人怒吼。
「誰?」阿比利大口喘息著問。
「那個巫師!」
阿比利想要回答,但只能發出模糊難辨的咕噥。裸身男子又是一聲咆哮,將阿比利摔回地上。阿比利大口喘息,左右張望,想要尋找武器──任何可以防身的東西都好。然後他看見那把躺在舊布上、仍兀自冒著裊裊輕煙的烙鐵,立刻抄起握把,朝男子撲去。
眼前一花──阿比利又仆倒地上。這一次,烙鐵彎曲的握把抵在他喉前的凹陷處。男子單膝跪在他身前,手裡握著通紅熾熱的烙鐵尖端,但阿比利沒有聞到任何燒焦的皮肉味,男人甚至連眉頭也沒皺一下。阿比利魂飛魄散地瞪著眼前這張過分完美的面孔,感到喉前冰冷的握把開始有了溫度,而且愈來愈熱、愈來愈燙──好像那男子不知正用什麼方法燒熱那柄烙鐵般。
阿比利心想:這實在是……實在是不可能啊!
「告訴我巫師在哪。」男人說,「我要去宰了他。」
阿比利目瞪口呆地看著他。
「他把我困在人類的軀體裡!告訴我他在哪!」
錫匠心念電轉,他垂眼看向那只仍騰騰冒煙的烙鐵,想起自己要將它按上銅壺前感到的那股詭異預感。他想起祖母說過的故事,只要有關壺瓶與油燈,裡頭一定有生靈囚禁在內。
不,這太荒謬了。那些都只是神話傳說。若非如此,唯一的可能就是他瘋了。
「這位大爺,」他低聲問,「請問你是精靈嗎?」
男人緊抿雙脣,眼裡多了防備,但並沒有奚落阿比利,或開口斥責他腦袋有問題。
「你是。」阿比利說,「天啊,你真的是。」他嚥了口口水,感到烙鐵抵在喉間的壓力,不由微微一縮。「求求你,無論那巫師究竟是誰,我真的不認識他。老實說,我懷疑這世上還有沒有巫師。」他頓了會兒,又說,「你可能已經在那壺裡待很久了。」
男人似乎聽了進去,烙鐵緩緩離開錫匠的喉頭。他佇立原地,轉身四顧,彷彿首次察覺這間店鋪的存在。街上的擾攘從高窗傳了進來:馬車的車轆聲、報童的叫賣聲,還有哈德遜河上輪船悠長低沉的汽笛聲。
「這裡是什麼地方?」男人問。
「我的打鐵鋪。」阿比利回答,「位於紐約。」他努力保持冷靜的語調,「在一個叫做美國的國家。」
男人走到阿比利的工作檯前,拿起其中一根又長又細的烙鐵,抓在手裡,臉上流露驚恐又著迷的神色。
「這是真的,」男人說,「這一切都是真的。」
「是的,」阿比利回答,「恐怕是。」
男人放下烙鐵,下頷肌肉陣陣抽搐,彷彿準備迎接最糟的情況。
「帶我四處看看。」他最後終於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