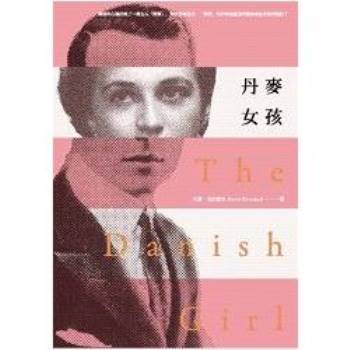第一部
1925年,哥本哈根
第一章
最早知道的是他妻子。「能幫我一個忙嗎?」那個下午葛蕾塔從臥室朝外喊,「過來幫我弄一下?」
「沒問題,」埃恩納眼睛盯著畫布,說:「做什麼都行。」
天氣沁爽,波羅的海吹來勁風,平添一股寒意。兩人在名為「寡婦之家」的公寓中作畫。個頭矮小的埃恩納還不滿三十五歲,正在畫他印象中的卡特加特海峽冬景。那一片黑水白浪滔滔,毫不留情,曾取走數百條性命,都是在海上大有斬獲、準備返回哥本哈根的漁人。樓下鄰居是個頭形如子彈的水手,老是咒罵老婆。埃恩納仔細描摹每一道海浪的灰色線條,想像水手溺斃時,絕望地舉高一隻手,灌飽伏特加的嗓子依舊罵老婆是「港口的婊子」。埃恩納靠這種方式掌握顏料調和的深淺,色調必須夠灰,足以吞沒這種男人,一層層塗抹上去,彷彿要與逐漸沉沒的咆哮聲對抗。
「我等一下要出門,」葛蕾塔說,她比丈夫年輕,臉龐扁平,五官生得俊俏。「等我回來就可以開始了。」
這一點埃恩納也跟他妻子不同——他畫陸地與海洋,由小長方形組成,有時明亮,是六月某個角度的光線;有時昏暗,是一月遲遲的日光。葛蕾塔畫人像,泰半是替略有名氣的達官要人畫全身肖像,纖毫畢現,光澤奪目,配上粉紅嘴唇。其中包括葛拉克斯達特,哥本哈根自由港口背後的金主;達爾佳德,國王的御用毛皮商;克努森,數一數二的B&W造船公司的董事會成員。當然了,還得加上安娜‧方思瑪,如今是丹麥皇家歌劇院次女高音。公司主管與企業鉅子會找葛蕾塔畫肖像,懸在辦公室檔案櫃的上方,有時掛在走廊上,好擋住小推車磕碰掉一角的牆壁。
葛蕾塔站在門框下方,問道:「你真的可以先停下來幫我嗎?」她頭髮攏到耳後,「如果不重要,我也不會求你幫忙。只是安娜原本說要來,又取消了。可以麻煩你穿上她的連身絲襪跟鞋子嗎?」
葛蕾塔一隻手略顯無力地拿著絲襪,四月陽光的光線從背後照射,穿透絲襪纖維。埃恩納看到窗外的哥本哈根圓塔,如同巨大的煙囪,上方有一架德意志勞埃德航空飛機悠然盤旋,正打算飛回柏林。
「葛蕾塔,」他說,「我不明白妳的意思。」刷子上的顏料滴了下來,滴到靴子上。愛德華四世開始吠叫,轉動白色頭顱,瞧瞧埃恩納,再瞧瞧葛蕾塔。
「安娜又不來了,」葛蕾塔說,「她說《卡門》多加了一場彩排。她的肖像只剩腿沒畫,我需要一雙腿,要不然永遠無法完成。然後我就想,你的腿或許可以。」
葛蕾塔朝他走去,另一隻手拿著芥末黃色的淑女鞋,上面有白鑞鞋扣。她穿著大罩衫充當工作服,上面有一排鈕扣,外加好幾個口袋,藏著她不想讓埃恩納看到的東西。
「可是安娜的鞋我穿不下。」埃恩納說,看著面前這雙小尺寸的鞋,前方弓起,鞋跟有軟墊。他不禁想或許真的合腳。他腳趾纖長,趾節上有幾根極細的黑毛。他想像自己套上這雙微皺的長絲襪,覆蓋潔白的腳踝,從小腿肚拉上來,繫緊吊襪帶的絆扣。埃恩納閉上眼睛,不願再想下去。
他們上禮拜在豐尼斯貝赫百貨公司便看到一雙這樣的鞋,櫥窗裡的假人模特兒身上是夜空藍洋裝,配上這雙鞋。他們倆駐足欣賞,櫥窗上綴飾著一整圈黃水仙花,葛蕾塔說:「漂亮噢?」他沒回話,厚玻璃反映出他雙眼圓睜的表情。葛蕾塔不得不拉他離開,推擠之間走過一條街,經過菸斗店,嘴裡說:「埃恩納,你還好吧?」
公寓最前面一間房間是工作室,天花板上架著好幾節細樑,中央拱起,像一艘船底翻轉的小漁船。許是因為海霧過濃,屋頂上的天窗均已變形,地板略略往西側,但不仔細看其實看不出來。下午時分,日頭無情地照進「寡婦之家」,牆壁滲出淡淡的鯡魚氣味。到了冬天,關不嚴的天窗飄進冷冷的雨絲,牆壁上的油漆浮突。埃恩納和葛蕾塔把畫架放在兩扇天窗下方,旁邊放著幾箱跟慕尼黑的赫薩拉多夫公司訂購的油彩,以及滿架子的空白畫布。埃恩納和葛蕾塔不作畫的時候,會拿幾張綠色防水布——樓下的水手丟在樓梯間,他們撿了回來——小心蓋好。
「妳為什麼要我穿她的鞋?」埃恩納坐在繩索椅上,是從他祖母農場後方的小屋搬來的。愛德華四世跳到他大腿上,狗看到畫布下方的水手狀似狂吼,不斷地發抖。
「為了安娜那張畫啊。」她說,「我要用你當模特兒。」她臉上顴骨突出的部位有一個淺疤,是先前得水痘留下的。她手指輕掠過痘瘢,埃恩納知道她現在心情焦慮。
葛蕾塔蹲下身替埃恩納解開靴子的鞋帶。埃恩納低頭看她黃色長髮,比他更像丹麥人的髮色。她打算動手做事時,會把頭髮撥到耳後,但她頭髮在臉龐上披散,只顧著替埃恩納解開鞋上的結。她身上有橘色精油的味道,她母親每年都透過船運寄來一大箱,棕色瓶身標籤上寫著「純玫瑰萃取精油,來自帕薩迪那 」。她媽還以為她用這個烘焙茶蛋糕,但葛蕾塔常沾在耳後當香水。
埃恩納雙腳放在盆中,葛蕾塔開始清洗,非常輕柔卻很有效率,手上的海綿快速搓過每道趾縫,埃恩納捲高褲管,赫然發現小腿肚很有型。他的腳側成一個角度,愛德華四世過來舔乾他的小趾,狀似鐵鎚,而且生來就沒有腳趾甲。
「葛蕾塔,不許對別人說。」埃恩納附在她耳邊細語,「妳不會告訴別人吧?」他既恐懼又興奮,覺得小孩拳頭般大的心臟正勃勃跳動,快要跳出喉頭。
「我要告訴誰?」
「安娜。」
「安娜不需要知道。」葛蕾塔說。話雖如此,埃恩納心想,安娜是歌劇演員,早已習慣男扮女裝,或女扮男裝,也就是角色反串。這是世上最大的謊言,但在歌劇舞臺上,根本算不了什麼,只是顛倒混亂,必須等到最後一幕,紛亂的謎團才會解開。
「沒人需要知道任何事。」葛蕾塔說,埃恩納原本覺得舞臺的慘白燈光打在他身上,這時稍稍放鬆,開始將絲襪套上小腿。
「你這樣穿不對,」葛蕾塔說,替他調整絲襪接縫的部分,「慢慢套上。」
第二隻絲襪綻了個洞,埃恩納問:「妳還有另外一雙嗎?」
葛蕾塔的臉瞬間僵住,彷彿這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接著她走去拉開褐灰色衣櫥的抽屜。最上方附一個活動櫃,櫃門上掛了面橢圓形鏡子,另有三個抽屜,拉動黃銅環把手就能打開。最上面那扇抽屜鎖上,葛蕾塔用小鑰匙開啟。
「這雙比較厚。」她遞給埃恩納。棕色絲襪摺得甚是齊整,四四方方。埃恩納想,就像一坨肉,是葛蕾塔夏天到法國蒙頓度完假回來的膚色。「請小心一點,」她說,「我明天還要穿。」
葛蕾塔露出銀白色髮線,他不禁想,不知她的頭皮底下在想什麼。她眼睛往上斜瞟,嘴巴抿緊,似乎正在轉著什麼念頭。埃恩納想問但問不出口,嘴巴像是被人用一塊髒布綁起來似的。因此他只默默忖度,光滑如白桃般的臉上露出一絲憎厭。他想起多年前兩人第一次獨處,她說:「你真是好看的男人。」
葛蕾塔一定是發現到他內心不快,因為她伸手捧住他的臉,說:「這不代表什麼。」又加上一句:「為什麼你老是這麼在意別人怎麼說?」
埃恩納喜歡聽她說這一類的話,雙手在空中大力比劃,信心滿滿地宣告她的信念,全世界都該這麼想。他覺得她這一點最像美國人,哦還有她喜愛銀飾珠寶的品味。
「幸好你腿上的毛很少。」葛蕾塔說,彷彿直到現在才發現。她拿著專用瓷碗,正在調顏料。葛蕾塔已經畫好安娜的上半身,小腹上有贅肉(多年來吃的奶油鮭魚都化成身上多餘的肉)。葛蕾塔畫她雙手捧著一日百合的花束,埃恩納心想畫得好極了。手指部分的處理相當細緻,指關節上方的皺縮和指甲均一一畫出,採用不透明畫法。百合花是美好的月白色,綴以暗紅色花粉。葛蕾塔的畫法經常出現矛盾,但他從來不說;相反地,他盡可能給予讚美,或許有時略嫌誇張。他盡可能幫她,把她不懂的技法傳授給她,尤其是光線和距離。埃恩納相信,只要葛蕾塔找到適合發揮的主題,她會成為優秀的畫家。「寡婦之家」窗外飄過一朵雲,陽光照在安娜的半身畫像上面。
葛蕾塔拿出一只烤漆皮箱,充當模特兒站立的平臺,皮箱是跟來自中國廣東的洗衣婦買的,她每隔一天出現,不是拉開嗓子喊,而是敲響手指上綁著的幾面小金鈸,沿街叫賣。
埃恩納站在皮箱上,覺得頭暈發熱。他低下頭看自己的小腿,柔滑如絲緞,只長出幾根腿毛,如同豆莢上的細絨毛。黃皮鞋顯得太秀氣,彷彿不足以支撐他,然而他的腳背自然朝上弓起,像是在伸展許久未用的肌肉。埃恩納閃過一絲念頭,覺得自己像追逐田鼠的狐狸,正用細長的紅鼻子掘生機勃勃的土地,一層又一層,只想找出獵物。
「站著別動。」葛蕾塔說。埃恩納望向窗外,看到皇家劇院最上方的圓形屋頂,其上有一圈圈凹槽。有時他會替歌劇公司畫布景,掛在劇院外面。此刻安娜正在裡面排練《卡門》,對著他畫的賽維利亞鬥牛場布景,挑釁似地舉高柔軟的雙臂。有幾次埃恩納在劇院裡畫畫,安娜的歌聲在禮堂裡節節升高,如同一排銅管,他往往因此發抖,畫刷一不小心弄髒了背景。他只好握拳揉揉眼睛。安娜的聲音並不圓潤,聲線粗糙,聽起來飽含悲傷,充滿滄桑,既像男聲又似女聲。但這把聲音極其高亢嘹亮,不像丹麥大多數歌劇演員那麼纖薄、明淨,儘管動聽,卻無法令觀眾顫慄。安娜的聲音有南國的熱度,給他溫暖,難道她喉嚨裡藏著煤炭?他會從後臺的梯子上爬下來,走到側翼包廂,注視著安娜,一襲潔白的羊毛長袍,張開闊嘴,跟指揮戴維克一起排練。她唱的時候身體往前傾,常對人說音樂有股吸引力,讓她的下巴不得不朝管弦樂團的席位靠近。她指指下巴上那顆黑痣,說:「這個就像一條銀鏈子,一端繫在樂隊指揮的指揮棒上,一端扣住我的下巴。要是沒有鏈子,我簡直手足無措,不曉得如何做自己了。」
葛蕾塔動筆作畫的時候,會拿玳瑁色的扁梳往後攏住頭髮,臉看起來比較大,埃恩納覺得像是透過一碗水看她的臉。他所認識的女子當中,當屬葛蕾塔最高,她比家裡的窗簾還高。本地一樓住家臨街的窗戶往往掛上蕾絲窗簾。埃恩納站在她旁邊,老覺得矮一截,如同兒子抬起頭,先看到母親的下巴跟眼睛,只想找吊環拉住。那件綴滿口袋的大罩衫是她找街角的裁縫師訂製的。腦後白髮梳成髻的女裁縫師拿著黃色皮尺,替她量胸圍和手臂,滿臉讚嘆,彷彿在說:這麼高大健康的女人居然不是丹麥人,實在不可思議。
葛蕾塔作畫時有種輕鬆的專注,埃恩納十分欣賞。她能夠在畫好左眼瞳孔光線時,先去開門,收下巴斯克牛奶公司送來的東西,再回來處理右眼瞳孔,使其更加靈動。她一面作畫,一面哼著篝火歌,跟對面的作畫對象聊天,聊到她在加州的童年生活,孔雀如何躲進她爸的柳橙果樹樹叢裡憩息。如果對象是個女性,她連他們夫妻間越來越少親熱的事也會說(埃恩納有次回家,站在黑漆漆的樓梯間準備開門,不小心聽到):「他非常介意這件事,但我從沒怪過他。」埃恩納想像她此時伸手把頭髮撥到耳後。
「滑下來了。」葛蕾塔說,用畫刷指著他的絲襪,「拉上去。」
「真的有必要嗎?」
樓下的水手摔上門,屋子裡靜悄悄的,只有他妻子吃吃的笑聲。
「噢埃恩納,」她說,「你可以放輕鬆嗎?」她臉上的微笑逐漸消失,愛德華四世晃進他們的房間,開始在床單棉被間鑽來鑽去,然後嘆息,如同嬰孩吃飽後滿足的聲音。牠是隻老狗了,在日德蘭半島的一處沼地出生,當年牠媽跟一窩剛出生的幼犬全淹死在沼澤裡。
目前的公寓是上個世紀政府開放給漁民的寡婦居住的。她們住在閣樓。不像哥本哈根大多數別墅,這棟樓房北、南、西三個方向都有窗戶,空間夠寬敞,光線也充足,適合作畫。他們差一點就要住進克里斯蒂安港的市民住宅,在內港的另一頭,是藝術家、妓女、嗜賭酒鬼聚集的地方,當地還有混合水泥公司跟進口貿易商。葛蕾塔說她哪兒都能住,在她眼中沒有骯髒下流這回事;但埃恩納直到十五歲都被保護得好好的,堅決反對,於是在「寡婦之家」找到地方棲身。
公寓外觀髹漆成紅色,離新港運河只有一個街口。陶土瓦蓋成的直立屋頂上開了幾扇天窗,屋頂上面覆滿多年苔蘚,顯得黑暗。同一條街上其他樓房都以石灰水粉刷,由八個鑲板組成的大門漆成海藻綠。街對面住的是一名醫生,叫作穆勒,常在夜裡接到緊急電話,趕去替女人接生。不過極少聽到汽車疾馳而過,因為這條街是內港的盡頭,靜到能聽見害羞女孩躲起來哭泣的聲音。
「我得回去工作了。」埃恩納最後說,不願意再穿這種鞋子站著,白鑞鞋扣扣得腳好痛。
「意思是你不想試穿她的洋裝了?」
當她說出「洋裝」二字,他感到胃裡一陣燥熱,羞恥感油然而生。「不,不要。」他說。
「幾分鐘都不行嗎?」她說,「我得畫裙襬邊緣垂在膝蓋上。」葛蕾塔坐在繩索椅上,隔著絲襪撫摸埃恩納的小腿,她的手有催眠的魔力,彷彿告訴他閉上雙眼。他只聽見她指甲刮著絲襪,發出細微的摩擦聲響,其他什麼都聽不到。
然後葛蕾塔停下手,說:「很抱歉,我不該這麼問。」
現在埃恩納看到褐灰色衣櫥的門開著,裡頭掛了一件安娜的白色洋裝,袖口和裙襬邊緣綴上珠子。有扇窗敞開,掛在衣架上的洋裝輕輕晃動。洋裝有種說不出來的什麼——是絲綢濃沉的閃光、緊身馬甲兩側的蕾絲、抑或是袖口沒扣上的鈎狀鈕扣,如同一張張小嘴巴——埃恩納覺得好想摸一摸。
「你喜歡這件衣服嗎?」她問。
埃恩納想說不喜歡,但這樣等於撒謊。他喜歡這件洋裝,幾乎可以感到皮膚底下的肉在生長、成熟。
「那就穿上吧,幾分鐘就好。」葛蕾塔拿給他,推到他胸前。
「葛蕾塔,要是我……」他說不下去。
「把身上襯衫脫掉。」她說。
他照做了。
「要是我……」
「閉上眼睛。」她說。
他照做了。
即使眼睛閉上,沒穿襯衫站在妻子前面,也有種淫穢的感覺,好像被她當場抓包——不是偷情那種事,比較像偷偷犯戒,比如在克里斯蒂安港的運河酒吧喝阿夸維特烈酒,在床上吃炸肉丸,或者拿出一副女孩子玩的麂皮撲克牌,隨便玩玩。撲克牌是他在一個孤單的午後買的。
「還有褲子。」她說,伸手遞給他,同時禮貌地轉過頭去。臥室的窗戶開著,帶有魚腥味的爽冽空氣吹了進來,讓他全身起雞皮疙瘩。
埃恩納很快從頭上套進洋裝,調整及膝的裙襬。他的胳肢窩跟腰際都在流汗。身上的熱度讓他忍不住希望,若能閉上眼睛重新變回小男孩就好了,那時腿間晃動的某物還像顆小白蘿蔔,小而無用。
葛蕾塔只說:「不錯。」舉起畫刷開始作畫,瞇著藍色眼睛,像是在審視鼻尖上的什麼東西。
埃恩納站在烤漆皮箱上,日光逐漸偏移,照在他身上不同部位,空氣中有鯡魚的氣味,他有種奇異的水淋淋的感覺。洋裝的袖子比較緊,其他部位都很寬鬆,一陣暖潮淹沒了他,如同徜徉在夏日海洋中。狐狸追逐著田鼠,腦海中隱約傳來聲音,是受驚小女孩在低聲啜泣。
埃恩納覺得無法再睜開眼,繼續看著妻子的手如同一尾敏捷的魚,在畫布上快速移動。銀製手鐲和戒指不斷晃動,閃耀如一群白鰱魚。他也無法再想安娜在皇家劇院唱歌,身體往前傾,下巴正對臺下的指揮棒。埃恩納只能專心感受身上的絲綢,如同裹著繃帶。沒錯,第一次穿上身就是這種感覺,絲如此細軟、輕盈,像紗布一般;塗上藥膏的紗布輕柔包覆正在癒合的皮膚。方才站在妻子面前覺得尷尬,也變得不再重要,因為她正忙著作畫,那份專注是他從不曾見過的。埃恩納彷彿走進迷離的夢土,在那裡,安娜的洋裝誰都可以穿,包括他自己。
他開始覺得眼皮沉重,畫室光線變得晦暗,於是嘆了口氣,垂下肩膀,愛德華四世在房間打起鼾來,就在這時,傳來安娜銅管般響亮的聲音:「看看埃恩納!」
他張開眼睛,葛蕾塔和安娜嘴唇微分,滿臉喜悅,伸手指著他,愛德華四世站在他面前吠叫。埃恩納‧維金納全身動彈不得。
葛蕾塔從安娜手上拿過百合花,是一名常去後臺的粉絲送的,然後一把塞給埃恩納。愛德華四世像個小喇叭手那樣抬起頭,繞著埃恩納轉圈子,一心想保護主人。兩個女人又笑了一會,埃恩納覺得累到睜不開眼,儘管他雙眼蓄滿淚水,笑聲和白色花束的香氣刺得他難受,花朵的紅色雌蕊在絲襪、洋裝下襬、隆起的鼠蹊部位、和張開的濕潤手掌上,一一留下印漬。
「妳真騷。」傳來樓下水手溫柔的呼喊,「真要命的騷貨啊妳。」
樓下恢復寂靜,想是兩人在親吻,言歸於好。此時葛蕾塔和安娜笑得更響了,埃恩納正想開口請她們離開畫室,好讓他脫下這身洋裝,葛蕾塔用一種陌生而小心翼翼的語調,悄聲說:「何不叫你莉莉呢?」
1925年,哥本哈根
第一章
最早知道的是他妻子。「能幫我一個忙嗎?」那個下午葛蕾塔從臥室朝外喊,「過來幫我弄一下?」
「沒問題,」埃恩納眼睛盯著畫布,說:「做什麼都行。」
天氣沁爽,波羅的海吹來勁風,平添一股寒意。兩人在名為「寡婦之家」的公寓中作畫。個頭矮小的埃恩納還不滿三十五歲,正在畫他印象中的卡特加特海峽冬景。那一片黑水白浪滔滔,毫不留情,曾取走數百條性命,都是在海上大有斬獲、準備返回哥本哈根的漁人。樓下鄰居是個頭形如子彈的水手,老是咒罵老婆。埃恩納仔細描摹每一道海浪的灰色線條,想像水手溺斃時,絕望地舉高一隻手,灌飽伏特加的嗓子依舊罵老婆是「港口的婊子」。埃恩納靠這種方式掌握顏料調和的深淺,色調必須夠灰,足以吞沒這種男人,一層層塗抹上去,彷彿要與逐漸沉沒的咆哮聲對抗。
「我等一下要出門,」葛蕾塔說,她比丈夫年輕,臉龐扁平,五官生得俊俏。「等我回來就可以開始了。」
這一點埃恩納也跟他妻子不同——他畫陸地與海洋,由小長方形組成,有時明亮,是六月某個角度的光線;有時昏暗,是一月遲遲的日光。葛蕾塔畫人像,泰半是替略有名氣的達官要人畫全身肖像,纖毫畢現,光澤奪目,配上粉紅嘴唇。其中包括葛拉克斯達特,哥本哈根自由港口背後的金主;達爾佳德,國王的御用毛皮商;克努森,數一數二的B&W造船公司的董事會成員。當然了,還得加上安娜‧方思瑪,如今是丹麥皇家歌劇院次女高音。公司主管與企業鉅子會找葛蕾塔畫肖像,懸在辦公室檔案櫃的上方,有時掛在走廊上,好擋住小推車磕碰掉一角的牆壁。
葛蕾塔站在門框下方,問道:「你真的可以先停下來幫我嗎?」她頭髮攏到耳後,「如果不重要,我也不會求你幫忙。只是安娜原本說要來,又取消了。可以麻煩你穿上她的連身絲襪跟鞋子嗎?」
葛蕾塔一隻手略顯無力地拿著絲襪,四月陽光的光線從背後照射,穿透絲襪纖維。埃恩納看到窗外的哥本哈根圓塔,如同巨大的煙囪,上方有一架德意志勞埃德航空飛機悠然盤旋,正打算飛回柏林。
「葛蕾塔,」他說,「我不明白妳的意思。」刷子上的顏料滴了下來,滴到靴子上。愛德華四世開始吠叫,轉動白色頭顱,瞧瞧埃恩納,再瞧瞧葛蕾塔。
「安娜又不來了,」葛蕾塔說,「她說《卡門》多加了一場彩排。她的肖像只剩腿沒畫,我需要一雙腿,要不然永遠無法完成。然後我就想,你的腿或許可以。」
葛蕾塔朝他走去,另一隻手拿著芥末黃色的淑女鞋,上面有白鑞鞋扣。她穿著大罩衫充當工作服,上面有一排鈕扣,外加好幾個口袋,藏著她不想讓埃恩納看到的東西。
「可是安娜的鞋我穿不下。」埃恩納說,看著面前這雙小尺寸的鞋,前方弓起,鞋跟有軟墊。他不禁想或許真的合腳。他腳趾纖長,趾節上有幾根極細的黑毛。他想像自己套上這雙微皺的長絲襪,覆蓋潔白的腳踝,從小腿肚拉上來,繫緊吊襪帶的絆扣。埃恩納閉上眼睛,不願再想下去。
他們上禮拜在豐尼斯貝赫百貨公司便看到一雙這樣的鞋,櫥窗裡的假人模特兒身上是夜空藍洋裝,配上這雙鞋。他們倆駐足欣賞,櫥窗上綴飾著一整圈黃水仙花,葛蕾塔說:「漂亮噢?」他沒回話,厚玻璃反映出他雙眼圓睜的表情。葛蕾塔不得不拉他離開,推擠之間走過一條街,經過菸斗店,嘴裡說:「埃恩納,你還好吧?」
公寓最前面一間房間是工作室,天花板上架著好幾節細樑,中央拱起,像一艘船底翻轉的小漁船。許是因為海霧過濃,屋頂上的天窗均已變形,地板略略往西側,但不仔細看其實看不出來。下午時分,日頭無情地照進「寡婦之家」,牆壁滲出淡淡的鯡魚氣味。到了冬天,關不嚴的天窗飄進冷冷的雨絲,牆壁上的油漆浮突。埃恩納和葛蕾塔把畫架放在兩扇天窗下方,旁邊放著幾箱跟慕尼黑的赫薩拉多夫公司訂購的油彩,以及滿架子的空白畫布。埃恩納和葛蕾塔不作畫的時候,會拿幾張綠色防水布——樓下的水手丟在樓梯間,他們撿了回來——小心蓋好。
「妳為什麼要我穿她的鞋?」埃恩納坐在繩索椅上,是從他祖母農場後方的小屋搬來的。愛德華四世跳到他大腿上,狗看到畫布下方的水手狀似狂吼,不斷地發抖。
「為了安娜那張畫啊。」她說,「我要用你當模特兒。」她臉上顴骨突出的部位有一個淺疤,是先前得水痘留下的。她手指輕掠過痘瘢,埃恩納知道她現在心情焦慮。
葛蕾塔蹲下身替埃恩納解開靴子的鞋帶。埃恩納低頭看她黃色長髮,比他更像丹麥人的髮色。她打算動手做事時,會把頭髮撥到耳後,但她頭髮在臉龐上披散,只顧著替埃恩納解開鞋上的結。她身上有橘色精油的味道,她母親每年都透過船運寄來一大箱,棕色瓶身標籤上寫著「純玫瑰萃取精油,來自帕薩迪那 」。她媽還以為她用這個烘焙茶蛋糕,但葛蕾塔常沾在耳後當香水。
埃恩納雙腳放在盆中,葛蕾塔開始清洗,非常輕柔卻很有效率,手上的海綿快速搓過每道趾縫,埃恩納捲高褲管,赫然發現小腿肚很有型。他的腳側成一個角度,愛德華四世過來舔乾他的小趾,狀似鐵鎚,而且生來就沒有腳趾甲。
「葛蕾塔,不許對別人說。」埃恩納附在她耳邊細語,「妳不會告訴別人吧?」他既恐懼又興奮,覺得小孩拳頭般大的心臟正勃勃跳動,快要跳出喉頭。
「我要告訴誰?」
「安娜。」
「安娜不需要知道。」葛蕾塔說。話雖如此,埃恩納心想,安娜是歌劇演員,早已習慣男扮女裝,或女扮男裝,也就是角色反串。這是世上最大的謊言,但在歌劇舞臺上,根本算不了什麼,只是顛倒混亂,必須等到最後一幕,紛亂的謎團才會解開。
「沒人需要知道任何事。」葛蕾塔說,埃恩納原本覺得舞臺的慘白燈光打在他身上,這時稍稍放鬆,開始將絲襪套上小腿。
「你這樣穿不對,」葛蕾塔說,替他調整絲襪接縫的部分,「慢慢套上。」
第二隻絲襪綻了個洞,埃恩納問:「妳還有另外一雙嗎?」
葛蕾塔的臉瞬間僵住,彷彿這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接著她走去拉開褐灰色衣櫥的抽屜。最上方附一個活動櫃,櫃門上掛了面橢圓形鏡子,另有三個抽屜,拉動黃銅環把手就能打開。最上面那扇抽屜鎖上,葛蕾塔用小鑰匙開啟。
「這雙比較厚。」她遞給埃恩納。棕色絲襪摺得甚是齊整,四四方方。埃恩納想,就像一坨肉,是葛蕾塔夏天到法國蒙頓度完假回來的膚色。「請小心一點,」她說,「我明天還要穿。」
葛蕾塔露出銀白色髮線,他不禁想,不知她的頭皮底下在想什麼。她眼睛往上斜瞟,嘴巴抿緊,似乎正在轉著什麼念頭。埃恩納想問但問不出口,嘴巴像是被人用一塊髒布綁起來似的。因此他只默默忖度,光滑如白桃般的臉上露出一絲憎厭。他想起多年前兩人第一次獨處,她說:「你真是好看的男人。」
葛蕾塔一定是發現到他內心不快,因為她伸手捧住他的臉,說:「這不代表什麼。」又加上一句:「為什麼你老是這麼在意別人怎麼說?」
埃恩納喜歡聽她說這一類的話,雙手在空中大力比劃,信心滿滿地宣告她的信念,全世界都該這麼想。他覺得她這一點最像美國人,哦還有她喜愛銀飾珠寶的品味。
「幸好你腿上的毛很少。」葛蕾塔說,彷彿直到現在才發現。她拿著專用瓷碗,正在調顏料。葛蕾塔已經畫好安娜的上半身,小腹上有贅肉(多年來吃的奶油鮭魚都化成身上多餘的肉)。葛蕾塔畫她雙手捧著一日百合的花束,埃恩納心想畫得好極了。手指部分的處理相當細緻,指關節上方的皺縮和指甲均一一畫出,採用不透明畫法。百合花是美好的月白色,綴以暗紅色花粉。葛蕾塔的畫法經常出現矛盾,但他從來不說;相反地,他盡可能給予讚美,或許有時略嫌誇張。他盡可能幫她,把她不懂的技法傳授給她,尤其是光線和距離。埃恩納相信,只要葛蕾塔找到適合發揮的主題,她會成為優秀的畫家。「寡婦之家」窗外飄過一朵雲,陽光照在安娜的半身畫像上面。
葛蕾塔拿出一只烤漆皮箱,充當模特兒站立的平臺,皮箱是跟來自中國廣東的洗衣婦買的,她每隔一天出現,不是拉開嗓子喊,而是敲響手指上綁著的幾面小金鈸,沿街叫賣。
埃恩納站在皮箱上,覺得頭暈發熱。他低下頭看自己的小腿,柔滑如絲緞,只長出幾根腿毛,如同豆莢上的細絨毛。黃皮鞋顯得太秀氣,彷彿不足以支撐他,然而他的腳背自然朝上弓起,像是在伸展許久未用的肌肉。埃恩納閃過一絲念頭,覺得自己像追逐田鼠的狐狸,正用細長的紅鼻子掘生機勃勃的土地,一層又一層,只想找出獵物。
「站著別動。」葛蕾塔說。埃恩納望向窗外,看到皇家劇院最上方的圓形屋頂,其上有一圈圈凹槽。有時他會替歌劇公司畫布景,掛在劇院外面。此刻安娜正在裡面排練《卡門》,對著他畫的賽維利亞鬥牛場布景,挑釁似地舉高柔軟的雙臂。有幾次埃恩納在劇院裡畫畫,安娜的歌聲在禮堂裡節節升高,如同一排銅管,他往往因此發抖,畫刷一不小心弄髒了背景。他只好握拳揉揉眼睛。安娜的聲音並不圓潤,聲線粗糙,聽起來飽含悲傷,充滿滄桑,既像男聲又似女聲。但這把聲音極其高亢嘹亮,不像丹麥大多數歌劇演員那麼纖薄、明淨,儘管動聽,卻無法令觀眾顫慄。安娜的聲音有南國的熱度,給他溫暖,難道她喉嚨裡藏著煤炭?他會從後臺的梯子上爬下來,走到側翼包廂,注視著安娜,一襲潔白的羊毛長袍,張開闊嘴,跟指揮戴維克一起排練。她唱的時候身體往前傾,常對人說音樂有股吸引力,讓她的下巴不得不朝管弦樂團的席位靠近。她指指下巴上那顆黑痣,說:「這個就像一條銀鏈子,一端繫在樂隊指揮的指揮棒上,一端扣住我的下巴。要是沒有鏈子,我簡直手足無措,不曉得如何做自己了。」
葛蕾塔動筆作畫的時候,會拿玳瑁色的扁梳往後攏住頭髮,臉看起來比較大,埃恩納覺得像是透過一碗水看她的臉。他所認識的女子當中,當屬葛蕾塔最高,她比家裡的窗簾還高。本地一樓住家臨街的窗戶往往掛上蕾絲窗簾。埃恩納站在她旁邊,老覺得矮一截,如同兒子抬起頭,先看到母親的下巴跟眼睛,只想找吊環拉住。那件綴滿口袋的大罩衫是她找街角的裁縫師訂製的。腦後白髮梳成髻的女裁縫師拿著黃色皮尺,替她量胸圍和手臂,滿臉讚嘆,彷彿在說:這麼高大健康的女人居然不是丹麥人,實在不可思議。
葛蕾塔作畫時有種輕鬆的專注,埃恩納十分欣賞。她能夠在畫好左眼瞳孔光線時,先去開門,收下巴斯克牛奶公司送來的東西,再回來處理右眼瞳孔,使其更加靈動。她一面作畫,一面哼著篝火歌,跟對面的作畫對象聊天,聊到她在加州的童年生活,孔雀如何躲進她爸的柳橙果樹樹叢裡憩息。如果對象是個女性,她連他們夫妻間越來越少親熱的事也會說(埃恩納有次回家,站在黑漆漆的樓梯間準備開門,不小心聽到):「他非常介意這件事,但我從沒怪過他。」埃恩納想像她此時伸手把頭髮撥到耳後。
「滑下來了。」葛蕾塔說,用畫刷指著他的絲襪,「拉上去。」
「真的有必要嗎?」
樓下的水手摔上門,屋子裡靜悄悄的,只有他妻子吃吃的笑聲。
「噢埃恩納,」她說,「你可以放輕鬆嗎?」她臉上的微笑逐漸消失,愛德華四世晃進他們的房間,開始在床單棉被間鑽來鑽去,然後嘆息,如同嬰孩吃飽後滿足的聲音。牠是隻老狗了,在日德蘭半島的一處沼地出生,當年牠媽跟一窩剛出生的幼犬全淹死在沼澤裡。
目前的公寓是上個世紀政府開放給漁民的寡婦居住的。她們住在閣樓。不像哥本哈根大多數別墅,這棟樓房北、南、西三個方向都有窗戶,空間夠寬敞,光線也充足,適合作畫。他們差一點就要住進克里斯蒂安港的市民住宅,在內港的另一頭,是藝術家、妓女、嗜賭酒鬼聚集的地方,當地還有混合水泥公司跟進口貿易商。葛蕾塔說她哪兒都能住,在她眼中沒有骯髒下流這回事;但埃恩納直到十五歲都被保護得好好的,堅決反對,於是在「寡婦之家」找到地方棲身。
公寓外觀髹漆成紅色,離新港運河只有一個街口。陶土瓦蓋成的直立屋頂上開了幾扇天窗,屋頂上面覆滿多年苔蘚,顯得黑暗。同一條街上其他樓房都以石灰水粉刷,由八個鑲板組成的大門漆成海藻綠。街對面住的是一名醫生,叫作穆勒,常在夜裡接到緊急電話,趕去替女人接生。不過極少聽到汽車疾馳而過,因為這條街是內港的盡頭,靜到能聽見害羞女孩躲起來哭泣的聲音。
「我得回去工作了。」埃恩納最後說,不願意再穿這種鞋子站著,白鑞鞋扣扣得腳好痛。
「意思是你不想試穿她的洋裝了?」
當她說出「洋裝」二字,他感到胃裡一陣燥熱,羞恥感油然而生。「不,不要。」他說。
「幾分鐘都不行嗎?」她說,「我得畫裙襬邊緣垂在膝蓋上。」葛蕾塔坐在繩索椅上,隔著絲襪撫摸埃恩納的小腿,她的手有催眠的魔力,彷彿告訴他閉上雙眼。他只聽見她指甲刮著絲襪,發出細微的摩擦聲響,其他什麼都聽不到。
然後葛蕾塔停下手,說:「很抱歉,我不該這麼問。」
現在埃恩納看到褐灰色衣櫥的門開著,裡頭掛了一件安娜的白色洋裝,袖口和裙襬邊緣綴上珠子。有扇窗敞開,掛在衣架上的洋裝輕輕晃動。洋裝有種說不出來的什麼——是絲綢濃沉的閃光、緊身馬甲兩側的蕾絲、抑或是袖口沒扣上的鈎狀鈕扣,如同一張張小嘴巴——埃恩納覺得好想摸一摸。
「你喜歡這件衣服嗎?」她問。
埃恩納想說不喜歡,但這樣等於撒謊。他喜歡這件洋裝,幾乎可以感到皮膚底下的肉在生長、成熟。
「那就穿上吧,幾分鐘就好。」葛蕾塔拿給他,推到他胸前。
「葛蕾塔,要是我……」他說不下去。
「把身上襯衫脫掉。」她說。
他照做了。
「要是我……」
「閉上眼睛。」她說。
他照做了。
即使眼睛閉上,沒穿襯衫站在妻子前面,也有種淫穢的感覺,好像被她當場抓包——不是偷情那種事,比較像偷偷犯戒,比如在克里斯蒂安港的運河酒吧喝阿夸維特烈酒,在床上吃炸肉丸,或者拿出一副女孩子玩的麂皮撲克牌,隨便玩玩。撲克牌是他在一個孤單的午後買的。
「還有褲子。」她說,伸手遞給他,同時禮貌地轉過頭去。臥室的窗戶開著,帶有魚腥味的爽冽空氣吹了進來,讓他全身起雞皮疙瘩。
埃恩納很快從頭上套進洋裝,調整及膝的裙襬。他的胳肢窩跟腰際都在流汗。身上的熱度讓他忍不住希望,若能閉上眼睛重新變回小男孩就好了,那時腿間晃動的某物還像顆小白蘿蔔,小而無用。
葛蕾塔只說:「不錯。」舉起畫刷開始作畫,瞇著藍色眼睛,像是在審視鼻尖上的什麼東西。
埃恩納站在烤漆皮箱上,日光逐漸偏移,照在他身上不同部位,空氣中有鯡魚的氣味,他有種奇異的水淋淋的感覺。洋裝的袖子比較緊,其他部位都很寬鬆,一陣暖潮淹沒了他,如同徜徉在夏日海洋中。狐狸追逐著田鼠,腦海中隱約傳來聲音,是受驚小女孩在低聲啜泣。
埃恩納覺得無法再睜開眼,繼續看著妻子的手如同一尾敏捷的魚,在畫布上快速移動。銀製手鐲和戒指不斷晃動,閃耀如一群白鰱魚。他也無法再想安娜在皇家劇院唱歌,身體往前傾,下巴正對臺下的指揮棒。埃恩納只能專心感受身上的絲綢,如同裹著繃帶。沒錯,第一次穿上身就是這種感覺,絲如此細軟、輕盈,像紗布一般;塗上藥膏的紗布輕柔包覆正在癒合的皮膚。方才站在妻子面前覺得尷尬,也變得不再重要,因為她正忙著作畫,那份專注是他從不曾見過的。埃恩納彷彿走進迷離的夢土,在那裡,安娜的洋裝誰都可以穿,包括他自己。
他開始覺得眼皮沉重,畫室光線變得晦暗,於是嘆了口氣,垂下肩膀,愛德華四世在房間打起鼾來,就在這時,傳來安娜銅管般響亮的聲音:「看看埃恩納!」
他張開眼睛,葛蕾塔和安娜嘴唇微分,滿臉喜悅,伸手指著他,愛德華四世站在他面前吠叫。埃恩納‧維金納全身動彈不得。
葛蕾塔從安娜手上拿過百合花,是一名常去後臺的粉絲送的,然後一把塞給埃恩納。愛德華四世像個小喇叭手那樣抬起頭,繞著埃恩納轉圈子,一心想保護主人。兩個女人又笑了一會,埃恩納覺得累到睜不開眼,儘管他雙眼蓄滿淚水,笑聲和白色花束的香氣刺得他難受,花朵的紅色雌蕊在絲襪、洋裝下襬、隆起的鼠蹊部位、和張開的濕潤手掌上,一一留下印漬。
「妳真騷。」傳來樓下水手溫柔的呼喊,「真要命的騷貨啊妳。」
樓下恢復寂靜,想是兩人在親吻,言歸於好。此時葛蕾塔和安娜笑得更響了,埃恩納正想開口請她們離開畫室,好讓他脫下這身洋裝,葛蕾塔用一種陌生而小心翼翼的語調,悄聲說:「何不叫你莉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