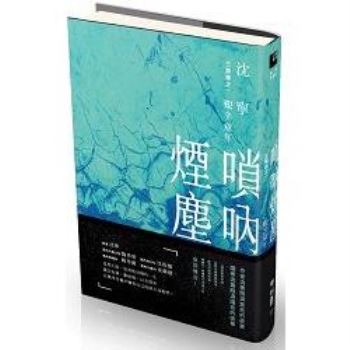過了一年,春天時候,家婆要生第一個孩子了。
三月中旬,日子到了,家婆一直躺在床上,好幾天了。全家大小女人們每天在家婆的屋門口等候。陶家的男人們呢,都還是不在家。太家公仍在河南任上。伯公和家公仍然在北京大學念書。自古至今,中國從來沒有女人生孩子要男人在身邊守著的規矩。太家婆派人到倉阜鎮上找了幾位看相算命的先生來診過脈,看過星相,都說一定生個男丫。
湖北人把孩童叫做丫。所以從太家婆開始,一家主僕都歡天喜地的等著,整日談論即將出生的小少爺。接生婆早請來了,在家婆屋裡忙。外面,陶家人手裡拿著鮮亮的虎頭小帽,或者繡著龍的小兜肚,還有幾張印著一個光屁股胖小子的彩畫,在門外等消息。
大姑婆二姑婆不高興。家婆生了兒子,在家裡的地位就提高了,太家婆喜歡,對家婆就會好起來,大姑婆二姑婆便不能隨意欺侮她了。可是眼下,太家婆期盼一個孫子,樂得合不上口,大姑婆二姑婆也只好悶在自己屋裡生氣,不敢到家婆房前生事。
除了兩個姑婆,陶家大院裡所有的人都聚在家婆屋門口,大小內外奴僕也一個不少,從早等到午,腿疼了,腰酸了,頸扭了,眼裂了。廚房裡喊吃飯,也沒人離開。誰第一個把喜訊報告給太家婆,就領得一份賞,或許明年會長工錢呢。
接生婆的話傳出屋門:生的是個女丫。
門外的人都愣了。這簡直不可能。
有人問:「真的嗎?算命先生掐過的呀,怎麼會錯。」
又有人建議:「再看看,細看看,小丫的雞雞太小,看不清。」
但是真的,家婆生的是一個女丫,我的大姨。家婆叫她驪珠。
所有在門外等了許久的人都嘆一口氣,搖著頭,走開了。沒有人敢去向太家婆報告這消息。虎頭小帽,繡龍兜肚,還有印著光屁股胖小子的彩畫,都丟在門口地上,再沒有用了。當然,太家婆到底聽說了,回屋把把房門鎖住,一整天都沒有出來。從家婆過門到陶家,一切都不按規矩來。家公沒有按時回家拜天地,家婆過門在轎上不哭,還沒成親家公就跑到新房去會新娘子,如今世道簡直的不成體統。現在,本來好好算過會生個兒子,卻又居然變成了個女娃。顯然,家婆命不濟,說不定前世惹了觀音菩薩,現在來懲罰她,不許她生兒。可是求老天開眼,陶家人可從來沒有得罪過哪位神仙,莫要給陶家降禍水呀。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外家婆心裡最怕的就是陶家沒有男兒後代。這是她在陶家做老太太的最大的責任。只要她活著主持陶家祖業的時候,看見兩個兒子生四五個孫子。孫子長大又生了兒子出來,她對陶家便算建立了豐功偉績,這一輩子可以完完全全滿足,對得起陶家祖先。死了以後,埋進陶家祖墳,理直氣壯。眼下,因為這倒楣的二媳婦進門,她得孫兒的夢想或許算是破滅了。
大姑婆二姑婆開門出了院子,大聲說話大聲笑,前院當中,抱作一團,打架哭鬧。
倉阜鎮上只有一個接生婆,週圍村落有人生孩子,只有找她。這接生婆從她自己母親那裡學了這套手藝,從來沒進過一天學校。也許是屋子不大乾淨,也許是別的原因,反正小女丫出生了,家婆受了感染,馬上就病倒了。
家婆躺在床上,剛出生的嬰兒靜靜地睡在旁邊。接生婆曉得生了女丫,拿不到賞錢,早早溜掉了。家婆獨自一人躺著,身上一陣冷,一陣熱,打著抖,沒人理會。
幾天下來,家婆的舌頭腫得半寸厚,不能吃東西,喉嚨乾得像要裂開,可是她不能喝水。床邊一個小小的奶瓶裡有一點水,家婆不能喝。她得留著水,給她的女兒,我的驪珠姨。因為產後就生病,家婆沒有奶,餵不成孩子。驪珠姨餓了,大哭,家婆只有忍著渾身疼,欠身舉臂,顫動著手,用一個小棉花球,蘸蘸那瓶中的水,然後取出,移過,滴在女兒的嘴裡。驪珠姨咂著水滴,便稍稍停住一會兒哭泣。
聽到有人從窗外石子路上走過。家婆用盡力氣叫:「水,給我一點水,求求你,水……」
可是沒有人答應。也許家婆聲音太弱,窗外的人聽不到。也許窗外的人聽到了,不搭理。沒有水送進來。這家裡前前後後三十多男女主僕,沒有人理會這母女倆。太家婆一連幾天鎖住屋門生氣。大姑婆二姑婆天天幸災樂禍,前院後院尋事打架。男僕人們不能進月子女人住的屋子,樂得躲開遠遠的。女僕人們都不敢進家婆屋去伺候,怕惹太家婆不高興。只有一個六十歲的老女僕,每天送三頓飯給家婆。家婆求她多帶些水,她答應了又忘記。
「水,哪位好心人,給點水……」家婆叫著,沒有了力氣,停下了,眼睛半睜半閉,望著窗外。她好像沉陷在一個巨大的泥潭中,越來越深地向下陷,周圍溼糊糊滑膩膩的骯髒泥水裹住她,壓迫她,窒息她。她除了疼痛,昏旋,悲哀,什麼也聽不到,什麼也看不到,什麼也說不出。
忽然,她似乎感覺到一個身影閃動。家婆鼓足所有剩餘的力氣睜開眼,終於恍恍惚惚看見一個年輕女人,穿著一身藍色長衣裙,輕輕地從門口走進屋來。家婆來到陶家一年多了,從來沒見過這人,但是她真高興。
這藍衣女人走到床邊,側著身子坐下來,把一隻手放在家婆的額頭上。那手涼涼的,好舒服。
「已經好幾天了,我一直想來看你……」藍衣女人開口說話,聲音柔和又溫暖,從家婆的耳朵裡聽進去,像一道清清的泉水,緩緩地一節一節,流過家婆喉嚨,流過家婆前胸,流過家婆心口,流過家婆肺腑,流向家婆全身。家婆的每一根血管和神經都在這柔美的話音裡震動通暢了。
藍衣女人接著說:「……可是家裡僱了好多木匠,在前院裡做活,我走不過來。今天木匠們都走了,我才來了。」
家婆想問問她是誰,可是嘴張不開,發不出聲,急得她出了一身汗,可還是說不出話來。「你會好起來,」那藍衣女人接著說,「你會好。丫不能沒有娘。你會好起來,你會好,你一定會好。」
藍衣女人的聲音繼續地震動著家婆的血脈,每說一次「你會好」,家婆就感到自己的身體從那裹住她壓迫她的泥濘中上升一截,她的身體輕鬆一些,呼吸寬暢一些,她那已經正在逝去的生命,漸漸地回覆到她的身軀裡來了。
藍衣女人說完了這番話,又用手最後在家婆額上輕輕壓了一壓,就站起身,朝門口走去。
家婆著急了,驚叫起來。可是藍衣女人沒有停,一直走出門去。
「莫走,莫走…」家婆拼命喊叫。
喊聲把家婆自己從昏睡中驚醒了。但是,她不肯相信那只是一個夢,她要相信那是真的,那是現實,那是她的生命力量。家婆忍著疼,從床上滾下床,用兩隻手,在地上爬,爬到門口。驪珠姨在床裡面大聲哭,家婆不管,只是往門口爬,她一定得找到那女人,把那女人找回來。她必須活下去,驪珠姨需要她活下去。
一個老女僕碰巧路過家婆房門,看見家婆半截身子在門外,橫在門坎上,張著兩手喊叫,嚇了一跳,忙顛著小腳過來扶她,嘴裡說:「呀,二少奶奶,你這是做麼什。你在月子裡呢,這樣招風,你不要命啦。」
家婆忽然覺得強壯起來。她抬起上半身,在空中揮舞著兩手,大聲叫:「快,快,把她叫回來,把她叫回來。」
那老女僕扶起家婆,問:「二少奶奶,你說的是誰?」
「那女人,穿藍衣裙。」家婆揮著手說。
老女僕問:「朝哪邊走了?」
家婆仍然揮著手喊:「那邊,那邊,快把她找回來。」
老女僕說:「我從那邊來,沒看見有人過去。那女人長什麼樣子?」
「長臉,」家婆喘著氣喊,「脖子左邊有一塊圓痣。」
老女僕聽了,想了一想,突然眼睛睜大起來,臉發白,抖著聲音說,」你說的是三小姐嗎?我的天老爺,藍長裙,脖子下有塊圓痣,就是她,三小姐。她原住這屋裡。四年前死了。我的天老爺,你怎麼會看見她,鬧鬼了。二少奶奶,你……」
「三姐麼?」家婆放下兩手,垂下頭問。
「二少奶奶,我得走了。你趕緊回屋到床上去吧。」老女僕不敢再逗留,也不敢再扶著家婆,搖著雙手,顛著小腳,打著抖走了。走三步回頭看一眼家婆,看過一眼更加快了步子跑。
家婆安靜了,坐在門口,靠在門框上,兩手擺在腿上,一動不動。屋裡,驪珠姨哭累了,睡著了,一聲不響。家婆睜大著眼睛,向天上望,什麼也看不見,只有一片藍色在閃耀,發著光亮。
這天之後,家婆的身體漸漸好起來。
過兩個月,家婆終於可以自己下地走路的時候,北京大學放暑假,家公回了家,剛好是驪珠姨過百天。這次家裡沒有人到碼頭去迎他。家公自己雇了一輛馬車坐回到陶盛樓。
年輕的父親在黑漆大門外下了馬車,揚起頭來深吸幾口氣。他還是穿著一件洗舊的灰布長衫,卷著兩圈寬寬的白袖口,下穿西裝褲,頭上戴了一頂黑禮帽,腳下穿了一雙黑皮鞋。他摘下來禮帽,在面前搧著,仰臉張望。一隻黃色的小鳥正從頭上飛過,很舒展的樣子。天空很藍,很深遠,好像一跳進去就會融化掉。
「誰說他可以回來?」
太家婆一聲吼叫從門裡衝出來,打散了寂靜的天空和大地。家公打了一個抖,趕緊提起書箱行李,走進門去。
「你好大膽,你敢私自回家。」太家婆站在堂屋門前的高台階上,兩手扠著腰,臉色烏黑,叫罵道,「你不知道我陶家的規矩麼?陶家人把功業看得重。你父親絕不會為一點家裡的小事放了學業,跑回家來……」
「母親……」家公低著頭,小聲地說。他手裡還提著書箱和行李,不敢放到地上。
「我曉得,我曉得。你媳婦會寫個把字,去了信,說她病了,好可憐。什麼大不了的事。家裡幾十人,不能看護她嗎?我們會看著她死嗎?為了老婆丟下學業,你羞死陶家的人了。」太家婆一口氣不停,叫了半個時辰。
家公答說:「母親,沒有人給我寫信。」
太家婆聽了,更加生氣,喊叫:「那麼,你這個時候回來做什麼?想老婆了?羞不羞。你是不是大男人。你怎麼敢為了看老婆跑出學堂?好,好,你不用去學堂了,住在家裡好了,守著你老婆好了,一天到晚睡在床上好了。書也不要念了,功業也不求了,沒出息的東西。陶家怎麼會出你這個不爭氣的兒。」
太家婆一邊說,轉身邁進堂屋門坎,一邊在身後揮著一隻手。
家公提著書箱衣箱,低著頭在後面跟著。進了堂屋門,看見太家婆在當中太師椅上坐下,才開口答:「母親,我大哥早回來了,快一個月了。」
「你敢還嘴,是麼?」太家婆咆嘯起來,一個手指指到天上,口裡連珠炮地罵,」你嫂嫂難產,住了武漢的醫院。兩個兒子,都不爭氣。什麼了不得的要命事,老時候,多麼難,還不是都在村裡生了。你們兩個,一個老婆生丫,要住醫院,還要去武漢,男人回來守在邊上。一個老婆生病,男人便要請假回家。學堂裡有規矩麼?什麼世道呀。以往男人在外頭舉業求功名,家裡老婆死了也不回家。現在好了,老大回來守著老婆生孩子,老二回來看老婆生病。老祖宗的規矩都壞了,都壞了。」
家公等太家婆吼完,說:「母親,學校現在放假。」
太家婆又喊:「放麼什假,學堂自古一年念書三百六十天,哪裡放那麼多假。」
家公說:「母親,北京大學是新式學校,一年有兩個假,一個寒假,一個暑假。現在是暑假,要一個半月呢。」
「什麼學堂,號稱全國最高學府,三天打魚,兩天晒網。念什麼書。」太家婆聲音雖然低下一些,還是氣哼哼,「你是陶家的男人,你該自己用功。他們放假,你不放,你自己念書。你爹爹,你父親,都是自己苦讀,成了功名。」
家公說:「母親,學校放假,就關門了。圖書館,教室,實驗室,都關了,教授也都回家了。放了假,學校裡沒有人了。」
「好,好,你有理,你有理。你住在家裡,吃,喝,看老婆。羞死人了。」太家婆一頭說,一頭站起轉身,走回旁側自己屋裡,順手一甩,砰一聲,把門摔得天響,又聽在裡面鎖住。整個前院後院,滿家裡的人,都躲在各自屋裡,廚房裡,工棚裡,從窗帘後頭,牆角後頭,偷偷地看,沒人敢出來。連大姑婆二姑婆也沒敢露面。她們懂得,她們可以在家裡隨心所欲,欺侮別的女人和佣人。但是她們到底只是女兒,碰上伯公家公兩兄弟的事情,她們最好躲開遠遠的。陶家裡,男人才是頂頂要緊。太家婆可以罵,可以訓,旁人可一點也碰不得。
家公等太家婆鎖住門,又在堂屋站了半晌,才提著書箱和行李轉身朝外走。剛邁出堂屋,走下台階,要轉身朝自己屋子去,又聽見太家婆從她屋裡叫:
「箱子放下,二福拿堂屋去。」
家公停下來,彎腰把書箱和行李放在堂屋門前當院地上。然後直起身,空著兩手,慢慢朝自己屋走。他不回頭,低著眼,走路。他知道身後有幾十雙眼睛盯著他,幾十個指頭在指他的後脊樑。
屋門在家公身後輕輕關住,他們相見面了,家公,家婆和驪珠姨。
家婆一直抱著驪珠姨站在門邊,聽外面堂屋前太家婆罵家公。驪珠姨好像也懂事,不吭一聲,望著家婆。
家公家婆都低著頭,垂著眼,不看對方。驪珠姨在家婆手臂裡,直著身子,睜著圓圓的眼睛,看著家公。三個多月了,她沒出過這個屋門,只有一個老女僕進來出去。這是第一個生人在跟前。
家公說:「我不曉得你生病。」
家婆說:「現在好了。」
家公問:「珠丫好麼?」
家婆說:「她會笑了。」
一陣小小的沉默。
家公說:「你辛苦了。」
家婆突然覺得眼裡澀澀的,淚好像要湧出來。
內文選摘二
法庭上官司一場一場過去,秋天已經到了,官司還沒有打完,書局案子一個星期一個星期拖。王雲五已經很久不再到法庭去。每次只是趙律師和家公去點個卯,每次都是英國律師說一聲沒有準備好,就算了。英國領事也不再露面。
家公雖然心裡憤憤的,卻倒是覺得不壞。每個星期,他總有一天出公差,早上八點進書局,不用打時間卡片,在辦公室坐一坐,看看材料,這一天不編稿子。十點鐘前後,王雲五總經理到了,派他的車子送家公去法庭,就算全天上工。
到法庭坐在那裡,看西洋景一般,一個案子一個案子的聽。中午又到街上吃一頓飯,或者北四川路上的新雅,或者武昌路上的廣州酒樓,都是趙律師一起去吃,由趙律師付賬,算在編譯所頭上。兩三個月下來,法律和法庭漸漸在家公的心裡減弱了原有的那般神聖光彩。
忽然今天,也沒有什麼辯論之類,英國律師提出要罰商務印書館六千大洋。趙律師不置可否,既不表同意,也不表反對,根本沒有掀起辨論的打算。
關法官轉頭,看看英國律師,又看看家公和趙律師,想了一想,說一聲:「本庭判罰上海商務印書館向英國領館賠款四千大洋。結案。」
一場英國領事狀告中國商務書局小職員陶希聖的官司,就這般結束了。兩位律師握握手,約好晚上一起到日租界的札榥酒家去吃日本壽司。英國律師走出法庭,向英國領事報功去了。書局要向領館賠款,自然是英國領事勝了這場官司。
趙律師連皮包都沒有打開,順手拎起來,對家公說:「今天很早,不到午飯時間,我們不去吃中飯了吧。我現在回辦公室,下午再給王先生打電話。你願意的話,可以回家,或者回編譯所。」
兩個人一起向門外走。
家公問:「就這麼完結了麼?」
趙律師說:「當然,還要怎樣呢?四千大洋,大事一樁,誰也沒輸,誰也沒贏,就算公
平。」
家公說:「怎麼說沒輸沒贏。書局要付賠款,英國人贏了。」
趙律師說:「英國人本來要三條判罰,一要關你坐牢,二要書局登報道歉,三要書局賠款兩萬銀元。現在都沒有做到,怎麼算贏。」
家公說:「為什麼要罰我們編譯所?我們沒有作錯事情,他們根本沒理由告我們,完全是誣告。」
趙律師停了一步,轉身看了家公一眼,又邁步走起來,邊說:「看你寫的文章,好像蠻有學問,原來是個書呆子。年輕人,你冒犯了政府,曉得麼?政府,中國政府,英國政府,都是政府。」
家公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沒有官民之分。」
趙律師搖搖頭說:「哈,果然是個書呆子。」
他們走出了門,站在高高的台階上,身上披著秋天的陽光。
趙律師拍拍家公的肩膀,接著說,」我勸你老弟,以後還是在書上作學問為好。寫寫書,可以生活在夢想裡面。作個教授,也可以在課堂上大講真理,義正詞嚴。如果沒什麼耐心的話別下來吃律師這碗飯,自欺欺人。中國法庭內外,沒有法律,全是骯髒的政治和權力,還有金錢的神通。好了,我走了,老弟好自為之。」
趙律師握握家公的手,揚長而去,把家公丟在那法庭房前台階上的燦爛陽光裡。
家公站在那裡發愣,好久好久。好幾個月時間,這麼一樁國際案子,中國人在英國軍警槍下,流了血,丟了性命,多少人為之傷心落淚,到頭來,倒是這位趙律師說的這幾句話,聽來真有點味道,有點學問,讓家公著實想了想,在大腦皮層上新打出幾道折彎。家公後來發現,這一番話,還真對他選擇生活道路發生了些作用。總而言之,自此起,他決意不再熱心拿法律作終身職業了。
天氣很好,家公沒有心思去書局上班,甚至沒有心思去圖書館或者書店去逛。他無精打彩,在馬路上蕩了蕩,最後還是回家了事。天下諾大,喜怒哀樂之時,總覺無處可去,只有回家。
媽媽和泰來舅都在前面小天井裡,見家公進門,便都奔跑過來,撲上身。家婆在後面大叫:
「手上都是泥,莫要上身。」
家公趕忙抓住媽媽和泰來舅的四隻手,翻過來看,二十個手指都是泥。家婆在天井裡栽花,媽媽和泰來舅跟著玩泥土。
家婆喜愛花草,也會弄花草,都是在湖北黃岡萬家大灣作姑娘時學的。到了上海,有了自己的天地,家婆便把小天井開出了小花園。她在湖北鄉下,沒有見過玫瑰花。到了上海,發現上海人喜歡玫瑰花,經常用玫瑰花送禮,很覺驚奇。後來曉得那是西洋人的習慣,上海人學會了。家婆自己養了一年,發現玫瑰確實美麗,也喜愛起來。玫瑰花有許多種,顏色大小都不同。天井太小,種不了許多,家婆挑選了一種紫紅色的,一種黃色的。花朵都很大,花瓣層層疊疊,豐滿華麗。花開時,色彩嬌艷,滿院芬芳。家婆數著日子,到花開盛之後,開始凋謝時,便用剪刀把花枝一一剪下,拿回屋裡,插在瓶中,灌了清水,讓那花朵繼續在屋裡開放。等到瓶中花朵萎縮飄落下來,家婆將花瓣都扯下來,放在瓷盤裡,留在桌上,每天在上面淋些清水,屋裡便能仍然保留許多日玫瑰的花香。最後花瓣都乾枯了,家婆便都研碎,包在麵粉裡,蒸出香噴噴的玫瑰糖包來。
見家公回了家,家婆領媽媽和泰來舅到後面廚房洗過手,回到大屋來。家公站在方桌邊,看著桌上瓶中插的玫瑰花,一朵紫紅色,一朵黃色。旁邊一個小小瓷盤裡,也放了些半枯的兩色玫瑰花瓣。
媽媽爬上桌邊的凳子,問:「爸爸,你要寫字嗎?我來幫你磨墨。」
家公轉臉,看了媽媽一眼,笑了一下,說:「好呀,你來磨墨,我來寫字。」
說著,家公走到窗前書桌邊,取來紙墨筆硯,從那插玫瑰的瓶中倒出一點水,淋在硯中,讓媽媽磨墨。
家婆在屋子中間安頓泰來舅,扶他在地板上坐穩,週圍堆了些天井裡撿的小石頭子。
媽媽問:「爸爸,你寫什麼字呢?」
「我想想。」家公說完,鋪開了紙,站著,對著牆,閉住眼,沉思片刻。然後提起筆來,在媽媽磨好的墨裡蘸蘸,懸著肘寫起來。他寫了八個字:學問艱難,人生甘苦。
媽媽問:「爸爸,你寫的什麼字?」
家公說:「人生不容易。」
媽媽說:「我也要寫。」
三月中旬,日子到了,家婆一直躺在床上,好幾天了。全家大小女人們每天在家婆的屋門口等候。陶家的男人們呢,都還是不在家。太家公仍在河南任上。伯公和家公仍然在北京大學念書。自古至今,中國從來沒有女人生孩子要男人在身邊守著的規矩。太家婆派人到倉阜鎮上找了幾位看相算命的先生來診過脈,看過星相,都說一定生個男丫。
湖北人把孩童叫做丫。所以從太家婆開始,一家主僕都歡天喜地的等著,整日談論即將出生的小少爺。接生婆早請來了,在家婆屋裡忙。外面,陶家人手裡拿著鮮亮的虎頭小帽,或者繡著龍的小兜肚,還有幾張印著一個光屁股胖小子的彩畫,在門外等消息。
大姑婆二姑婆不高興。家婆生了兒子,在家裡的地位就提高了,太家婆喜歡,對家婆就會好起來,大姑婆二姑婆便不能隨意欺侮她了。可是眼下,太家婆期盼一個孫子,樂得合不上口,大姑婆二姑婆也只好悶在自己屋裡生氣,不敢到家婆房前生事。
除了兩個姑婆,陶家大院裡所有的人都聚在家婆屋門口,大小內外奴僕也一個不少,從早等到午,腿疼了,腰酸了,頸扭了,眼裂了。廚房裡喊吃飯,也沒人離開。誰第一個把喜訊報告給太家婆,就領得一份賞,或許明年會長工錢呢。
接生婆的話傳出屋門:生的是個女丫。
門外的人都愣了。這簡直不可能。
有人問:「真的嗎?算命先生掐過的呀,怎麼會錯。」
又有人建議:「再看看,細看看,小丫的雞雞太小,看不清。」
但是真的,家婆生的是一個女丫,我的大姨。家婆叫她驪珠。
所有在門外等了許久的人都嘆一口氣,搖著頭,走開了。沒有人敢去向太家婆報告這消息。虎頭小帽,繡龍兜肚,還有印著光屁股胖小子的彩畫,都丟在門口地上,再沒有用了。當然,太家婆到底聽說了,回屋把把房門鎖住,一整天都沒有出來。從家婆過門到陶家,一切都不按規矩來。家公沒有按時回家拜天地,家婆過門在轎上不哭,還沒成親家公就跑到新房去會新娘子,如今世道簡直的不成體統。現在,本來好好算過會生個兒子,卻又居然變成了個女娃。顯然,家婆命不濟,說不定前世惹了觀音菩薩,現在來懲罰她,不許她生兒。可是求老天開眼,陶家人可從來沒有得罪過哪位神仙,莫要給陶家降禍水呀。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外家婆心裡最怕的就是陶家沒有男兒後代。這是她在陶家做老太太的最大的責任。只要她活著主持陶家祖業的時候,看見兩個兒子生四五個孫子。孫子長大又生了兒子出來,她對陶家便算建立了豐功偉績,這一輩子可以完完全全滿足,對得起陶家祖先。死了以後,埋進陶家祖墳,理直氣壯。眼下,因為這倒楣的二媳婦進門,她得孫兒的夢想或許算是破滅了。
大姑婆二姑婆開門出了院子,大聲說話大聲笑,前院當中,抱作一團,打架哭鬧。
倉阜鎮上只有一個接生婆,週圍村落有人生孩子,只有找她。這接生婆從她自己母親那裡學了這套手藝,從來沒進過一天學校。也許是屋子不大乾淨,也許是別的原因,反正小女丫出生了,家婆受了感染,馬上就病倒了。
家婆躺在床上,剛出生的嬰兒靜靜地睡在旁邊。接生婆曉得生了女丫,拿不到賞錢,早早溜掉了。家婆獨自一人躺著,身上一陣冷,一陣熱,打著抖,沒人理會。
幾天下來,家婆的舌頭腫得半寸厚,不能吃東西,喉嚨乾得像要裂開,可是她不能喝水。床邊一個小小的奶瓶裡有一點水,家婆不能喝。她得留著水,給她的女兒,我的驪珠姨。因為產後就生病,家婆沒有奶,餵不成孩子。驪珠姨餓了,大哭,家婆只有忍著渾身疼,欠身舉臂,顫動著手,用一個小棉花球,蘸蘸那瓶中的水,然後取出,移過,滴在女兒的嘴裡。驪珠姨咂著水滴,便稍稍停住一會兒哭泣。
聽到有人從窗外石子路上走過。家婆用盡力氣叫:「水,給我一點水,求求你,水……」
可是沒有人答應。也許家婆聲音太弱,窗外的人聽不到。也許窗外的人聽到了,不搭理。沒有水送進來。這家裡前前後後三十多男女主僕,沒有人理會這母女倆。太家婆一連幾天鎖住屋門生氣。大姑婆二姑婆天天幸災樂禍,前院後院尋事打架。男僕人們不能進月子女人住的屋子,樂得躲開遠遠的。女僕人們都不敢進家婆屋去伺候,怕惹太家婆不高興。只有一個六十歲的老女僕,每天送三頓飯給家婆。家婆求她多帶些水,她答應了又忘記。
「水,哪位好心人,給點水……」家婆叫著,沒有了力氣,停下了,眼睛半睜半閉,望著窗外。她好像沉陷在一個巨大的泥潭中,越來越深地向下陷,周圍溼糊糊滑膩膩的骯髒泥水裹住她,壓迫她,窒息她。她除了疼痛,昏旋,悲哀,什麼也聽不到,什麼也看不到,什麼也說不出。
忽然,她似乎感覺到一個身影閃動。家婆鼓足所有剩餘的力氣睜開眼,終於恍恍惚惚看見一個年輕女人,穿著一身藍色長衣裙,輕輕地從門口走進屋來。家婆來到陶家一年多了,從來沒見過這人,但是她真高興。
這藍衣女人走到床邊,側著身子坐下來,把一隻手放在家婆的額頭上。那手涼涼的,好舒服。
「已經好幾天了,我一直想來看你……」藍衣女人開口說話,聲音柔和又溫暖,從家婆的耳朵裡聽進去,像一道清清的泉水,緩緩地一節一節,流過家婆喉嚨,流過家婆前胸,流過家婆心口,流過家婆肺腑,流向家婆全身。家婆的每一根血管和神經都在這柔美的話音裡震動通暢了。
藍衣女人接著說:「……可是家裡僱了好多木匠,在前院裡做活,我走不過來。今天木匠們都走了,我才來了。」
家婆想問問她是誰,可是嘴張不開,發不出聲,急得她出了一身汗,可還是說不出話來。「你會好起來,」那藍衣女人接著說,「你會好。丫不能沒有娘。你會好起來,你會好,你一定會好。」
藍衣女人的聲音繼續地震動著家婆的血脈,每說一次「你會好」,家婆就感到自己的身體從那裹住她壓迫她的泥濘中上升一截,她的身體輕鬆一些,呼吸寬暢一些,她那已經正在逝去的生命,漸漸地回覆到她的身軀裡來了。
藍衣女人說完了這番話,又用手最後在家婆額上輕輕壓了一壓,就站起身,朝門口走去。
家婆著急了,驚叫起來。可是藍衣女人沒有停,一直走出門去。
「莫走,莫走…」家婆拼命喊叫。
喊聲把家婆自己從昏睡中驚醒了。但是,她不肯相信那只是一個夢,她要相信那是真的,那是現實,那是她的生命力量。家婆忍著疼,從床上滾下床,用兩隻手,在地上爬,爬到門口。驪珠姨在床裡面大聲哭,家婆不管,只是往門口爬,她一定得找到那女人,把那女人找回來。她必須活下去,驪珠姨需要她活下去。
一個老女僕碰巧路過家婆房門,看見家婆半截身子在門外,橫在門坎上,張著兩手喊叫,嚇了一跳,忙顛著小腳過來扶她,嘴裡說:「呀,二少奶奶,你這是做麼什。你在月子裡呢,這樣招風,你不要命啦。」
家婆忽然覺得強壯起來。她抬起上半身,在空中揮舞著兩手,大聲叫:「快,快,把她叫回來,把她叫回來。」
那老女僕扶起家婆,問:「二少奶奶,你說的是誰?」
「那女人,穿藍衣裙。」家婆揮著手說。
老女僕問:「朝哪邊走了?」
家婆仍然揮著手喊:「那邊,那邊,快把她找回來。」
老女僕說:「我從那邊來,沒看見有人過去。那女人長什麼樣子?」
「長臉,」家婆喘著氣喊,「脖子左邊有一塊圓痣。」
老女僕聽了,想了一想,突然眼睛睜大起來,臉發白,抖著聲音說,」你說的是三小姐嗎?我的天老爺,藍長裙,脖子下有塊圓痣,就是她,三小姐。她原住這屋裡。四年前死了。我的天老爺,你怎麼會看見她,鬧鬼了。二少奶奶,你……」
「三姐麼?」家婆放下兩手,垂下頭問。
「二少奶奶,我得走了。你趕緊回屋到床上去吧。」老女僕不敢再逗留,也不敢再扶著家婆,搖著雙手,顛著小腳,打著抖走了。走三步回頭看一眼家婆,看過一眼更加快了步子跑。
家婆安靜了,坐在門口,靠在門框上,兩手擺在腿上,一動不動。屋裡,驪珠姨哭累了,睡著了,一聲不響。家婆睜大著眼睛,向天上望,什麼也看不見,只有一片藍色在閃耀,發著光亮。
這天之後,家婆的身體漸漸好起來。
過兩個月,家婆終於可以自己下地走路的時候,北京大學放暑假,家公回了家,剛好是驪珠姨過百天。這次家裡沒有人到碼頭去迎他。家公自己雇了一輛馬車坐回到陶盛樓。
年輕的父親在黑漆大門外下了馬車,揚起頭來深吸幾口氣。他還是穿著一件洗舊的灰布長衫,卷著兩圈寬寬的白袖口,下穿西裝褲,頭上戴了一頂黑禮帽,腳下穿了一雙黑皮鞋。他摘下來禮帽,在面前搧著,仰臉張望。一隻黃色的小鳥正從頭上飛過,很舒展的樣子。天空很藍,很深遠,好像一跳進去就會融化掉。
「誰說他可以回來?」
太家婆一聲吼叫從門裡衝出來,打散了寂靜的天空和大地。家公打了一個抖,趕緊提起書箱行李,走進門去。
「你好大膽,你敢私自回家。」太家婆站在堂屋門前的高台階上,兩手扠著腰,臉色烏黑,叫罵道,「你不知道我陶家的規矩麼?陶家人把功業看得重。你父親絕不會為一點家裡的小事放了學業,跑回家來……」
「母親……」家公低著頭,小聲地說。他手裡還提著書箱和行李,不敢放到地上。
「我曉得,我曉得。你媳婦會寫個把字,去了信,說她病了,好可憐。什麼大不了的事。家裡幾十人,不能看護她嗎?我們會看著她死嗎?為了老婆丟下學業,你羞死陶家的人了。」太家婆一口氣不停,叫了半個時辰。
家公答說:「母親,沒有人給我寫信。」
太家婆聽了,更加生氣,喊叫:「那麼,你這個時候回來做什麼?想老婆了?羞不羞。你是不是大男人。你怎麼敢為了看老婆跑出學堂?好,好,你不用去學堂了,住在家裡好了,守著你老婆好了,一天到晚睡在床上好了。書也不要念了,功業也不求了,沒出息的東西。陶家怎麼會出你這個不爭氣的兒。」
太家婆一邊說,轉身邁進堂屋門坎,一邊在身後揮著一隻手。
家公提著書箱衣箱,低著頭在後面跟著。進了堂屋門,看見太家婆在當中太師椅上坐下,才開口答:「母親,我大哥早回來了,快一個月了。」
「你敢還嘴,是麼?」太家婆咆嘯起來,一個手指指到天上,口裡連珠炮地罵,」你嫂嫂難產,住了武漢的醫院。兩個兒子,都不爭氣。什麼了不得的要命事,老時候,多麼難,還不是都在村裡生了。你們兩個,一個老婆生丫,要住醫院,還要去武漢,男人回來守在邊上。一個老婆生病,男人便要請假回家。學堂裡有規矩麼?什麼世道呀。以往男人在外頭舉業求功名,家裡老婆死了也不回家。現在好了,老大回來守著老婆生孩子,老二回來看老婆生病。老祖宗的規矩都壞了,都壞了。」
家公等太家婆吼完,說:「母親,學校現在放假。」
太家婆又喊:「放麼什假,學堂自古一年念書三百六十天,哪裡放那麼多假。」
家公說:「母親,北京大學是新式學校,一年有兩個假,一個寒假,一個暑假。現在是暑假,要一個半月呢。」
「什麼學堂,號稱全國最高學府,三天打魚,兩天晒網。念什麼書。」太家婆聲音雖然低下一些,還是氣哼哼,「你是陶家的男人,你該自己用功。他們放假,你不放,你自己念書。你爹爹,你父親,都是自己苦讀,成了功名。」
家公說:「母親,學校放假,就關門了。圖書館,教室,實驗室,都關了,教授也都回家了。放了假,學校裡沒有人了。」
「好,好,你有理,你有理。你住在家裡,吃,喝,看老婆。羞死人了。」太家婆一頭說,一頭站起轉身,走回旁側自己屋裡,順手一甩,砰一聲,把門摔得天響,又聽在裡面鎖住。整個前院後院,滿家裡的人,都躲在各自屋裡,廚房裡,工棚裡,從窗帘後頭,牆角後頭,偷偷地看,沒人敢出來。連大姑婆二姑婆也沒敢露面。她們懂得,她們可以在家裡隨心所欲,欺侮別的女人和佣人。但是她們到底只是女兒,碰上伯公家公兩兄弟的事情,她們最好躲開遠遠的。陶家裡,男人才是頂頂要緊。太家婆可以罵,可以訓,旁人可一點也碰不得。
家公等太家婆鎖住門,又在堂屋站了半晌,才提著書箱和行李轉身朝外走。剛邁出堂屋,走下台階,要轉身朝自己屋子去,又聽見太家婆從她屋裡叫:
「箱子放下,二福拿堂屋去。」
家公停下來,彎腰把書箱和行李放在堂屋門前當院地上。然後直起身,空著兩手,慢慢朝自己屋走。他不回頭,低著眼,走路。他知道身後有幾十雙眼睛盯著他,幾十個指頭在指他的後脊樑。
屋門在家公身後輕輕關住,他們相見面了,家公,家婆和驪珠姨。
家婆一直抱著驪珠姨站在門邊,聽外面堂屋前太家婆罵家公。驪珠姨好像也懂事,不吭一聲,望著家婆。
家公家婆都低著頭,垂著眼,不看對方。驪珠姨在家婆手臂裡,直著身子,睜著圓圓的眼睛,看著家公。三個多月了,她沒出過這個屋門,只有一個老女僕進來出去。這是第一個生人在跟前。
家公說:「我不曉得你生病。」
家婆說:「現在好了。」
家公問:「珠丫好麼?」
家婆說:「她會笑了。」
一陣小小的沉默。
家公說:「你辛苦了。」
家婆突然覺得眼裡澀澀的,淚好像要湧出來。
內文選摘二
法庭上官司一場一場過去,秋天已經到了,官司還沒有打完,書局案子一個星期一個星期拖。王雲五已經很久不再到法庭去。每次只是趙律師和家公去點個卯,每次都是英國律師說一聲沒有準備好,就算了。英國領事也不再露面。
家公雖然心裡憤憤的,卻倒是覺得不壞。每個星期,他總有一天出公差,早上八點進書局,不用打時間卡片,在辦公室坐一坐,看看材料,這一天不編稿子。十點鐘前後,王雲五總經理到了,派他的車子送家公去法庭,就算全天上工。
到法庭坐在那裡,看西洋景一般,一個案子一個案子的聽。中午又到街上吃一頓飯,或者北四川路上的新雅,或者武昌路上的廣州酒樓,都是趙律師一起去吃,由趙律師付賬,算在編譯所頭上。兩三個月下來,法律和法庭漸漸在家公的心裡減弱了原有的那般神聖光彩。
忽然今天,也沒有什麼辯論之類,英國律師提出要罰商務印書館六千大洋。趙律師不置可否,既不表同意,也不表反對,根本沒有掀起辨論的打算。
關法官轉頭,看看英國律師,又看看家公和趙律師,想了一想,說一聲:「本庭判罰上海商務印書館向英國領館賠款四千大洋。結案。」
一場英國領事狀告中國商務書局小職員陶希聖的官司,就這般結束了。兩位律師握握手,約好晚上一起到日租界的札榥酒家去吃日本壽司。英國律師走出法庭,向英國領事報功去了。書局要向領館賠款,自然是英國領事勝了這場官司。
趙律師連皮包都沒有打開,順手拎起來,對家公說:「今天很早,不到午飯時間,我們不去吃中飯了吧。我現在回辦公室,下午再給王先生打電話。你願意的話,可以回家,或者回編譯所。」
兩個人一起向門外走。
家公問:「就這麼完結了麼?」
趙律師說:「當然,還要怎樣呢?四千大洋,大事一樁,誰也沒輸,誰也沒贏,就算公
平。」
家公說:「怎麼說沒輸沒贏。書局要付賠款,英國人贏了。」
趙律師說:「英國人本來要三條判罰,一要關你坐牢,二要書局登報道歉,三要書局賠款兩萬銀元。現在都沒有做到,怎麼算贏。」
家公說:「為什麼要罰我們編譯所?我們沒有作錯事情,他們根本沒理由告我們,完全是誣告。」
趙律師停了一步,轉身看了家公一眼,又邁步走起來,邊說:「看你寫的文章,好像蠻有學問,原來是個書呆子。年輕人,你冒犯了政府,曉得麼?政府,中國政府,英國政府,都是政府。」
家公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沒有官民之分。」
趙律師搖搖頭說:「哈,果然是個書呆子。」
他們走出了門,站在高高的台階上,身上披著秋天的陽光。
趙律師拍拍家公的肩膀,接著說,」我勸你老弟,以後還是在書上作學問為好。寫寫書,可以生活在夢想裡面。作個教授,也可以在課堂上大講真理,義正詞嚴。如果沒什麼耐心的話別下來吃律師這碗飯,自欺欺人。中國法庭內外,沒有法律,全是骯髒的政治和權力,還有金錢的神通。好了,我走了,老弟好自為之。」
趙律師握握家公的手,揚長而去,把家公丟在那法庭房前台階上的燦爛陽光裡。
家公站在那裡發愣,好久好久。好幾個月時間,這麼一樁國際案子,中國人在英國軍警槍下,流了血,丟了性命,多少人為之傷心落淚,到頭來,倒是這位趙律師說的這幾句話,聽來真有點味道,有點學問,讓家公著實想了想,在大腦皮層上新打出幾道折彎。家公後來發現,這一番話,還真對他選擇生活道路發生了些作用。總而言之,自此起,他決意不再熱心拿法律作終身職業了。
天氣很好,家公沒有心思去書局上班,甚至沒有心思去圖書館或者書店去逛。他無精打彩,在馬路上蕩了蕩,最後還是回家了事。天下諾大,喜怒哀樂之時,總覺無處可去,只有回家。
媽媽和泰來舅都在前面小天井裡,見家公進門,便都奔跑過來,撲上身。家婆在後面大叫:
「手上都是泥,莫要上身。」
家公趕忙抓住媽媽和泰來舅的四隻手,翻過來看,二十個手指都是泥。家婆在天井裡栽花,媽媽和泰來舅跟著玩泥土。
家婆喜愛花草,也會弄花草,都是在湖北黃岡萬家大灣作姑娘時學的。到了上海,有了自己的天地,家婆便把小天井開出了小花園。她在湖北鄉下,沒有見過玫瑰花。到了上海,發現上海人喜歡玫瑰花,經常用玫瑰花送禮,很覺驚奇。後來曉得那是西洋人的習慣,上海人學會了。家婆自己養了一年,發現玫瑰確實美麗,也喜愛起來。玫瑰花有許多種,顏色大小都不同。天井太小,種不了許多,家婆挑選了一種紫紅色的,一種黃色的。花朵都很大,花瓣層層疊疊,豐滿華麗。花開時,色彩嬌艷,滿院芬芳。家婆數著日子,到花開盛之後,開始凋謝時,便用剪刀把花枝一一剪下,拿回屋裡,插在瓶中,灌了清水,讓那花朵繼續在屋裡開放。等到瓶中花朵萎縮飄落下來,家婆將花瓣都扯下來,放在瓷盤裡,留在桌上,每天在上面淋些清水,屋裡便能仍然保留許多日玫瑰的花香。最後花瓣都乾枯了,家婆便都研碎,包在麵粉裡,蒸出香噴噴的玫瑰糖包來。
見家公回了家,家婆領媽媽和泰來舅到後面廚房洗過手,回到大屋來。家公站在方桌邊,看著桌上瓶中插的玫瑰花,一朵紫紅色,一朵黃色。旁邊一個小小瓷盤裡,也放了些半枯的兩色玫瑰花瓣。
媽媽爬上桌邊的凳子,問:「爸爸,你要寫字嗎?我來幫你磨墨。」
家公轉臉,看了媽媽一眼,笑了一下,說:「好呀,你來磨墨,我來寫字。」
說著,家公走到窗前書桌邊,取來紙墨筆硯,從那插玫瑰的瓶中倒出一點水,淋在硯中,讓媽媽磨墨。
家婆在屋子中間安頓泰來舅,扶他在地板上坐穩,週圍堆了些天井裡撿的小石頭子。
媽媽問:「爸爸,你寫什麼字呢?」
「我想想。」家公說完,鋪開了紙,站著,對著牆,閉住眼,沉思片刻。然後提起筆來,在媽媽磨好的墨裡蘸蘸,懸著肘寫起來。他寫了八個字:學問艱難,人生甘苦。
媽媽問:「爸爸,你寫的什麼字?」
家公說:「人生不容易。」
媽媽說:「我也要寫。」